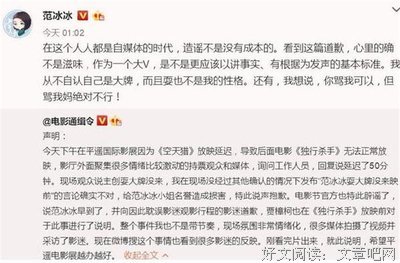自省如此,何事不成?
读曾氏《挺经》之“内圣”篇,不由得为曾氏真实严谨毫不留情的剖析自己的精神所感动。
“冯树堂来,渠近日养得好,静气迎人。谈半时,邀余同至岱云处久谈。论诗文之业亦可因以进德。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人不虚心,何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壬寅十一月。”
看来,人前逞强,非我辈庸人独有之弊,即使是位尊势高的名人伟人,也有这样的弊端,而庸人不能及时反思改正罢了。曾国藩能深刻剖析自己内心骄矜咄咄逼人的傲气,也真实的写出自己为此付出的痛苦挣扎: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表面上责怪别人而暗地里责怪自己)。
“此刻下手工夫,除谨言、修容、静坐三事,更从何处下手?每日全无切实处,尚呶呶与人说理,说他何益?”
他对自己的言行,严格要求到不说一句空话上,“每日全无切实处,尚呶呶与人说理,说他何益?”曾氏对自己的“谨言”要求到了何等苛刻的地步,人说“人微言轻”,以曾国藩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力,他仍然要求自己不说一句空话,甚至不说为妙,可见,我辈庸人,平时说了多少废话!
“窦兰泉来,言理见商,余实未能心领其语意,而妄有所陈,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伪饰,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徇外为人,果何益哉?”
对于前来与之交流的人,曾氏总是总结谈论之语,找出自己言谈中伪饰之处,并深挖病根说:这种行为总是由于心里不诚实,所以说话的语气虚伪骄傲,就是与人谈理,也是自己文饰浅陋,外表上做给别人看。
读到此处,不禁汗颜。曾国藩尚且觉得自己有好为人师自欺欺人之语,那么,我在平时的待人接物中,有多少次不懂装懂自文浅陋过?恐怕太多次太多次,甚至有些不恰当的表现至今想起来仍然惶悚不已!
“岱云欲观予《馈贫粮》本,予以雕虫琐琐深闭固拒,不欲与之观。一时掩著之情,自文固陋之情,巧言令色,种种丛集,皆以好名心发出,盖此中根株深矣。”
这里,曾氏更是无情的将自己人性的丑陋无情的晾晒在阳光下:一时遮掩笨拙的隐情,自我文饰浅陋的隐情,言辞虚伪故意做作,这种复杂的情形集中一起,都是从虚荣好名的心理出发,这中间毒株的根子扎的太深啊!
不轻易将自己的文章拿给人看,在外人看来,是低调谦逊厚重,是内敛不张扬,而曾国藩竟然真实的自我解剖自己外在文饰浅陋言辞虚伪而根本的原因是虚荣好名的心理作怪。能够将自己内心深处的隐曲解剖到如此深刻犀利,恐怕古今中外无人企及。
“会客时,有一语极失检,由“忿”字伏根甚深,故有触即发耳。”会见客人的时候,有一句话非常不检点,都于“忿”字潜伏在心中,根子扎得很深,所以一有触及,立即就发作了。
哪怕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曾氏都能深挖根子,找出此语背后的根源,难怪他能够在满朝满人得势的朝廷里久立不败之地!
用今天的话说,曾氏做到了彻底放下自我,摆平自己的心态,哪怕细小到一言一语,也要彻底摒除自我的固陋,才使得他事业平稳,人际和谐。
以下更是让我汗颜羞愧的地方:五更醒,辗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偏激,痛自苛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在那样纷乱无序的社会环境中,曾氏对自己的僚属毫无指责埋怨之处,而痛将解剖刀深入自己性格的深处:余之隘也!我天性偏激,痛加改正已经多年,而有触即发,想起来就觉得惭愧惊恐!
随时随地纠正自己性格中的弱点,刻刻不忘从自身找原因,甚至达到了痛心疾首的程度:“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苦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
对于自己言谈中动怒乃至埋怨别人的情况出现时,他总能及时反省,并且誓与旧我告别,做不好便痛苦忏悔,甚至自己咒骂自己“与禽兽相比又有什么两样?”“小人哉!”来自省,即使对那些拂逆了他的小人,曾文正也能如此劝勉自己“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用不着再举例,每读一则,我的心都深深的震撼和惭愧,自觉自己的渺小浅薄,自觉自己的无知丑陋。
慎独。主敬。求仁。思诚。今日我辈,倘能认真读读曾氏《挺经》,社会会多么和谐,人心多么向善。不用太多,只需读读内圣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