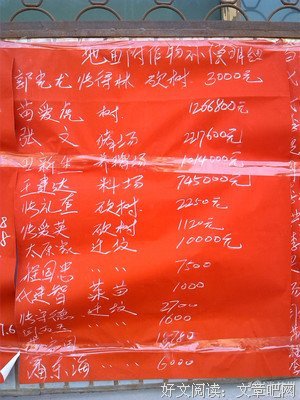活在祁县老沙堡
生活是变化无常的,没什么特定的逻辑线。年年月月就是一个熬,老百姓说的熬就是过日子。
外婆和老外婆都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美国丢失了原子弹,苏联变成俄罗斯,统统和她们没关系。她们关心的圈子就是这一个家,眼睛时刻扫射的是自己的一堆至亲,上老下小。老母鸡如是,呱呱呱,蛋下在自家的窝,呵护家庭,过好自家的小日子。
半个世纪前即是,老沙堡村卢氏一大户,千年之前一锅饭,一把勺子。不管远近,连带的都是亲缘关系。族亲繁殖的快了,渐渐有了距离。家族辈份不能丢。村里人对称呼是很讲究的,不象在陌生地方叨歇,老的是大爷,中年是阿姨,小的叫哥姐。宗亲以代际为标准。有的上了年纪的白胡子老汉,见了毛头小子还叫二爷或三爷。我外婆家算繁衍快的,我们是外甥。外婆叫我们做人,一定得人恭礼至,出门三辈小。小小年纪也梳理不出别家的长幼,所以,见了村里的男女,称呼杂乱的直皱眉头。做外甥的周转在母系窝里,放眼去都是外婆,外爷,舅舅,姨姨。那些年谁家的兄弟姐妹也是一串。钻在人堆里就发愁,三牛老外爷,二叶姨姨,猴儿舅舅…,仰起头来个个都是长辈。有时弄不清辈份,叫的发愁。
在人的世界,关系的连接是基础。不是称呼讲究的小事,是反映人家的门风教养。这也是过日子的一部分。有的家庭不在乎这一套,放养式的育儿女。娃们张口闭口没大没小,见了长辈也不知尊敬,出口老汉,老婆姨的瞎叫。人们就会戳点,吃草料长大的一样,连爹娘也捎带着骂了,嗯,猪狗人家。
老百姓祖祖辈辈绑在土地上,走出去的很少。男女成人了,结亲的不外乎也是在三五里之内,媒人说合,又组成跨村的亲缘。走亲戚姑舅的多。姑姑嫁到外乡,舅舅娶进外村的媳妇做妗子。建国以后,时兴自由恋爱了,本村男女成亲的就多了。卢姓一大户,有的已隔代出了五伏,本宗内结亲缘的多了起来。堂兄弟的亲,看起来很扯淡,估计上了战场在乎骨肉亲,平常过日子就寡气了。都是男子汉,独立自成一个家,一个利益单位,相互来往显然不及姑舅亲。
过日子离不开物质,过日子又都是长短是非的说叨,七七八八,没完没了。农耕家庭,以户为单位,一锅炉灶,一眼子蹲坑。爷爷爹爹孙子,几代人同处一屋。弟兄多的,娶了婆姨,生了娃只,实在一屋子盛不下的,才分家,另起炉灶。穷困人家,一般也没什么值得爭吵打闹的财产。老房子一劈几瓣,分开住分开锅灶,老黑瓮破罐子均分一下,搬腾几件,就独立成了人家。弟兄多的,赶紧的到大队划块地势,七攒八抠盖几间新房。
人家是什么,就是你吃你的,我喝我的,往来不往来得对缘。即使亲兄弟,各自有了小窝,打起自家的小算盘,利益起自己的小家院。不对劲的,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面对走过来,歪头咧脖,连个″吃嘞沒了″也不问。
吵闹是家常便饭。如今是小康社会,城里面文明,听不到半个咋唬声。到了大小乡村,静悄悄的,看不到人影,听不到人声。
半个世纪前,人都扎堆在土地上。呛人的柴火烟,夹杂的人声,娃娃哭,鸡鸣,狗叫,马牛的嘶吼,还有就是成天从早到晚不绝于耳的吵闹声。
穷吵饿闹,还真是这么回事。一个穷字,不但限制了人的想象力,而且缺吃的没穿的,心里过的很肮脏。无论大小男女,脾气不打一处来,一眼看不顺,一句话对不上就是骂。
骂的很难听,听惯了也不觉甚。
你啊死下人了?没啦惹你,这呢就这么欺负人…。日你先人的,张口闭口喷茅粪,X…
一个比一个恶毒,没有恶心,只有更恶心。骂的不过瘾了,人人还不愿做怂囊子丢人,圪抻圪抻凑过去动了拳脚,撕扯到一起打起来。看热闹的赶紧拉架。家败甚了,好好地耍,七嘴八舌评察一阵,散了。没过几天,臭骂的打架的,好象也不记仇,一达儿扛着镢头上地了。
这是在大街上的风景。人家也是,骂几句算什么,爹娘一沤气,拳脚上去了。口中骂骂咧咧,你这个讨吃鬼,妨主鬼,狗日的,不是外东西…
骂儿骂女都是如此的舌下不留情,根本没有斥解过内容,实际是骂的自己。
沙堡人都很善良。老的小的念过书的不多,一张嘴很粗鲁,但心地很淳朴。骂声中叱咤,支眉瞪眼,可谁家有了点儿事,老少男女一大堆扑过去,搭手搭脚,完事儿后给吃上一根洋旱烟,乐滋滋的散去了。
那阵子没什么农业机械,生产队收割打场都是人工。人割了庄稼,马车拉到场儿上。辅助运输的还有小平车,独轮车。这也比山里人先进的多。不用肩扛,挑担。生产队的场儿上,打粮靠牲口碾压,骡子马儿还有毛驴牛等拉着石头碌碡,绕着圈子作业。碾压出壳中的米谷,再上人工风扇去皮。人工摇扇得好后生才干的动,有臂力,绕着摇把,姿势很优美。然后支开麻袋,簸箕装进了筛出来的成粮。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场面十分的热闹,男女老少杂拌成一堆,东吼西叫,叽叽喳喳。不乏有男女撩猫逗狗,十分的爽朗开心。那首歌还是我们那代人唱热的,″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阵子仿佛刚从原始社会走来,跟天离的近,跟地贴的紧。一到夜间,月亮高悬,繁星满天。人们一伙一伙坐一起叨歇,有滋有味。
村里较大的动静,是家户发生的婚丧嫁娶。谁家吃婆姨(娶媳妇),嫁奴儿,谁家的老人归天了等,全村都会掀起波浪。反正村子不大,涌过去凑热闹见稀罕。年轻的搭把手帮助干点活儿,老少们凑个人气。吃婆姨帮忙笑的,人死了感染了陪哭的,人情味儿很浓。
死了赚一口柏木棺材,是村人的羡慕。记得北头祠堂里,阴森森的,摞着不少棺木,猴鬼们在门缝里偷看,看着头皮就发涨。
吃婆姨或者奴儿嫁,那是人家的大事情。穷困也不是二尺红头绳能办了的。借钱凑合,也不能丢了体面,总得有三间住屋,有几个红包袱,几床绸缎面被子。在院子里办几桌宴席。亲戚本家上礼,一块钱足够。水果糖很贵买不起,就把块儿的白冰糖捣碎了,红纸里包丁点儿撒给猴鬼们抢。味儿甜啊。奴儿出嫁,戴上花冠,穿上绣花鞋,陪几个红包袱做嫁妆,人们啧啧的惊讶大方。如果发现手上戴有银戒指金戒指的,″啊呀,阔气了,这辈子可算没白活了…″。到了70年代,再给媳妇买辆飞鸽牌自行车,摆架缝纫机,更要在全村传说,吵嚷半个月不止。
村里人过的日子差不离,也不觉大的好赖差别。文革时期红袖章,语录本也不差城里的,打倒谁反对谁,跟着喊了就是。天高皇帝远,都懒得思考与吃饭不相干的事儿。文化人不多,也没有明显的宗教,可都有敬畏心,信谁呢,老天爷。老天爷就是各路神仙的总称。按时节按习惯敬土地爷,月亮爷,关老爷,灶王爷…。蒸馍馍,烧香,磕头,都是很虔诚的。谁也不敢惹下老天爷。
谁在村里是公认的好人,好人家,谁是有威信的,那就看百年后的葬礼。老沙堡的土话叫“属丧”,给老人送终。不信可看,街门囗一贴白纸,不到半个小时,全村人都知道了。祭不祭奠是村人自觉的事,也不用掏钱,亲自上门送一道白纸,表示对逝者的尊敬。
我的外婆,老外婆去世几十年了。现在老沙堡的老人们还在回忆,那是村里的一道奇观。辛苦种下的人缘吧。老婆婆,外婆直至传授给我妗子,几代是村里的接生婆,有恩于全村的几代男女。还有,我老婆婆是远近闻名的土医生,治病救人无数。沙堡人感恩。全村家户,包括那些不管天不管地的老光棍们,一家不落地送了白纸。打墓,抬材,祭奠,送葬的那天,满村的男女都站立两旁送行。
不用最后等老天爷审判。人心就是过日子的最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