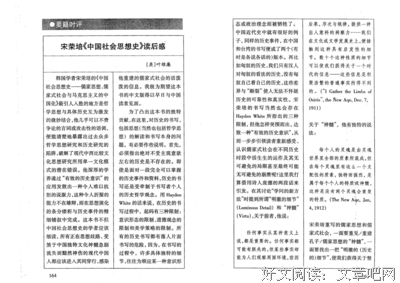人类思想史读后感1000字
《人类思想史》是一本由沃森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43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类思想史》精选点评:
●欧洲何以中心?此书对中世纪思想暗流、外界对欧陆影响的分析是不错的综述。
●就像一本大杂烩一样,什么都有,什么都说不清楚,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是支支吾吾的,而且参考书籍也无多少新意可言,很难给人以新的启迪。当然,翻译是一个大问题,可能读原文要好很多。
●: B1/3149-1
●不如20世纪思想史写的那么耳目一新,有时候觉得该详细的地方一笔带过,不必要的地方反而罗嗦。
●厚。需要耐心的一本书
●在对权威的不断冲击中, 人类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人类思想史》读后感(一):挺不错的一本书
这本书对于学习法律,尤其是法理学和法制史专业的学生来说挺值得一看的,相比于许多冗长的著作,这本书对于每一阶段的每一个学者和流派都有简练却深刻的阐述,很适合那种有了一定历史基础的人去阅读,可以梳理清楚西方中世纪到近代那些错综复杂的脉络。
唯一我觉得可惜的,是翻译的水平,有一些纰漏和前后不统一的地方。
《人类思想史》读后感(二):《人类思想史》获多方好评
一部历史领域的杰作……沃森从至今仍对西方思想禁锢至深的文化狭隘主义中解脱出来,令人耳目一新。他自由地穿梭于历史的时空中,他的研究包括了中国和印度思想中给人启迪的片断;对吠陀传统的描述也大有裨益,吠陀传统认为人的个性是一种幻觉。主流的思想史著作通常墨守成规,把从柏拉图到北约的思想进程讲得枯燥无味,本书则旁征博引涉猎广泛,对于那些渴望引人入胜的精彩叙述的读者而言,将是无价之宝。
——约翰·格雷,伦敦经济学院欧洲思想专业教授,《新评论》
沃森独具慧眼,能够发现历史的生动细节,他使档案中那些蒙尘的名字再次鲜活起来。只待读者意犹未尽地啧啧赞赏……一本书不可否认的实力就在于,它对精神生活的热情令人振奋,它强调智力的历史不可思议地独立于技术,而它的视野也更为全球化。
——《伦敦时报》
沃森是驾驭语言的天才……他如此才思敏锐,能够巧妙地化繁为简……这是一部宏伟的著作……人类思想的历史理应在这样的规模中讨论。
——菲利普·费尔南德斯一阿莫斯图,历史学家,《标准晚报》
这是一部特别的新作……它是关于“思想”(ideas)的历史,这是前所未有的。
——诺埃尔·马尔科姆,《星期日电讯报》
《人类思想史》读后感(三):我看到《人类思想史》的精彩片断
宗教裁判所虽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始终是“邪恶帝国”,却也是罪孽深重。每一件发生的事情总隐含着强烈的讽刺--因为异教在当时迅速牢固生根的一个原因是神职人员自身道德松弛和腐败,而正是这些神职人员在执行梵蒂冈的新法律。例如,阿维尼翁议会提到过一个牧师为了苦修而用骰子赌博的案子,还有客栈的招牌上挂着教士的硬白领。巴黎议会(同样也是1210年)揭露了由拥有妻子或者情妇的牧师举办的弥撒以及由修女组织的聚会。英诺森三世在1215年第四届拉特兰教堂议会上所致的开幕词中承认“民众的腐败根源于神职人员的腐败”。
说异教与12世纪随处可见的魔法行为和根深蒂固的迷信(包括在教堂自身)少有关系这一点很重要。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记述过这些魔法行为所达到的程度--有些人相信奇迹的作用是“展示(教会)垄断真理的最为灵验的手段”。例如人们相信圣体变成肉体这一点有时并没有夸张。一位历史学家引用了一位塞戈维亚(Segovia)犹太银行家接受圣体作为贷款担保品的例子。另一位历史学家也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女人嘴含圣饼亲吻她的丈夫,目的是为了“得到他的爱”。基思·托马斯也提到了一个诺福克(Norfolk)女人的例子,这个女人曾七次施过坚信礼,“因为她发现这能治疗她的风湿病”。教会清楚地解释了异教(顽固坚持与教义相违背的信念)与迷信(包括像前面提到的不虔诚地使用圣餐)的区别。无论如何,异教徒本身对魔法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它滥用/误用了他们自己所反对的圣礼。
教会最初还能勉强容忍异教。直到1162年,亚历山大教皇还拒绝对兰斯(Rheims)主教交给他的一些卡特里教徒判刑,根据是“原谅那些罪人比夺去无辜人的生命更好”。但是,反对卡特里教徒的宗教战争对很多人有利。它可以带来物质和精神的利益,而不需要冒险和开支去中东从事一段艰辛而又危险的旅程。实际上,其影响是混合性的。起初在贝济耶(Beziers)有7000人被屠杀。这个事件太恐怖了,这使十字军战士从此获得了一把永久的心理利刃。而与此同时,卡特里教徒被迅速驱散--这意味着他们诱人的请求比用其他方式传播得更广、更快。作为回应,第四次拉特兰教堂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发表了一份《对正统信仰的详细明确的陈述》,其中包括新的法律程序的最初的大纲。
……
《人类思想史》读后感(四):发现时间——《人类思想史》序
1859年5月1日,星期三,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乘坐夜轮,从福克斯通(Folkestone)出发,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布伦(Boulogne),接着又乘火车去了阿布维利(Abbeville),在那里与英国著名地质学家约瑟夫•普雷斯特维奇(Joseph Prestwich)会合。第二天早上7点,海关总长雅克•布歇•德•佩尔特(Jacques Boucher de Crevecoeur de Perthes)便在阿布维利约见了他们。这位总长同时还是一位业余的考古学家,埃文斯和普雷斯特维奇此次法国之行正是受他之邀来调查一些考古发现。
自1835年以来,工人们在阿布维利市郊一条河流中挖掘砾石,他们挖出了远古动物骨骸及不同类型的石器。这些石制工具让布歇•德•佩尔特相信人类的出现远远早于圣经中的记载。许多权威的教会人士断定人类起源于基督诞生前的6000—4000年间,他们的计算是基于《创世纪》所提供的宗谱。布歇•德•佩尔特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当阿布维利地区为修建一座新的医院挖掘地基时,出土了三把石制的手斧和一种早已在法国灭绝的大象的臼齿,这更加坚定了布歇的看法。
但是,布歇却很难让他的法国同行相信他的“证据”足以将人类的历史提前几十万年。当时的法国并不缺少专业知识,他们有天文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地质学和自然历史专家居维叶(Cuvier)、拉尔泰(Lartet)和斯科罗普(Scrope),还有古生物学家皮卡(Picard)。但是在古生物学领域,这些专家们似乎不够专业,古生物学的爱好者分散于全国各地,他们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与知名的学术机构相脱离,而这些机构却是公开其研究成果的重要渠道,比如法兰西学会(French Academy)。而且,就布歇•德•佩尔特个人而言,他的可信性是个大问题,因为他年过半百才开始从事考古,之前他写过几个五幕剧,再加上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形而上学方面的成果,他的著作竟达69部之多。在一些圈子里,他被看成是个杂而不精的人。现在,他认为原始人类在一场世界范围的大灾难中彻底毁灭,稍后又被重新创造出来,那些挖掘发现便是证明。对于这一奇异的理论,他从前的那些成果没有任何帮助。但英国人却有同感,这不是因为英国科学家比法国科学家更优秀——绝对不是——而是因为在海峡以北的萨福克(Suffolk)、德文(Devon)和约克郡(Yorkshire)都有类似的发现。1797年,在萨福克的迪丝(Diss)附近一个叫霍克斯内(Hoxne)的地方,约翰•弗雷尔(John Frere)——一位当地的文物工作者——在地表以下17英尺的自然地层中发现了许多手斧和灭绝动物骨骸。1825年,在德文郡托奎(Torquay)附近,一位天主教神父约翰•麦克恩纳利(Father John MacEnery)在挖掘肯特(Kent)山洞时,找到了一个“毋庸置疑的燧石工具”和一颗绝种犀牛的牙齿,它们都静静地躺在石笋层之下,不为人知。 然后是在1858年,距此不远,仍然是在德文郡,人们开掘布雷克斯汉姆(Brixham)港时,许多小洞穴暴露出来,于是,皇家协会(Royal Society)和地理协会(Geographical Society)设立了一个知名的委员会来资助那次挖掘。在石笋层中,发现了猛犸象骨骼化石,还有狮子、犀牛、驯鹿以及其他已灭绝的更新世的动物化石,此外,在石笋层以下,还找到了“显然是出自人类之手的燧石”。同年,布雷克斯汉姆考古挖掘资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著名的英国古生物学家休•福科纳(Hugh Falconer)博士在前往西西里的途中恰巧拜访了布歇•德•佩尔特。福科纳为眼前的一切感到震惊,于是他说服了普雷斯特维奇和埃文斯亲自来法国看看这些从阿布维利地下发掘出来的东西,作为专业学者,普埃二人的研究领域与此关系最为紧密。
这两个英国人在法国仅仅待了一天半。星期四早上,他们到了阿布维利的砾石挖掘坑。根据埃文斯在日记里的记述,在那儿“我们下到坑里,在11英尺深的地下,砾石层保留得很完好,一把斧子的利刃清晰可辨……这次发现最值得一提的是,斧子和这些动物遗骸都是在同一地层中被发现的,而这些动物几乎都已经灭绝了。其中有猛犸象、犀牛、一种叫乌拉斯(Urus)的老虎,等等。”埃文斯和普雷斯特维奇当场给一把手斧拍了照。返回伦敦后,5月底,普雷斯特维奇向伦敦的皇家协会报告,声称最近在英国和法国的考古发现已让他确信人类拥有漫长的历史,6月,埃文斯向文物工作者协会(Society of Antiquaries)报告,也阐述了相同的结论。另外还有几位著名学者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表示支持他们关于原始人类起源的新观点。
正是从这些事件中,现代的时间概念得以确定,人们意识到人类拥有漫长的历史进程,迄今仍无法想象,这种观念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圣经》中所设定的人类年谱。这一改变与我们对石器的研究密不可分。
这并不是说布歇•德•佩尔特是第一个对《旧约全书》中的描述提出质疑的人。人们对燧石斧子的认知至少始于公元前5世纪,一位色雷斯(Thracian)公主的随葬品中就有一把,可能是为了乞求好运。这些奇怪的物品分布甚广,由此引发了人们对石器的各种奇异的解释。其中一个较为流行的说法认为石器是“石化的雷电”,普林尼(Pliny)也支持这一观点;另一说法则认为石器是“神箭”。17世纪中叶,艾尔德拉梵德斯(Aldrovandus)认为石器应该是一种由雷的发散物和含有金属物质的闪电合成的混合物,尤其是在乌云中,四周的水分凝结,然后聚集成一大块(就像是面粉和水相混合),最后遇热变硬,就像砖。
然而,进入16、17世纪,随着探险时代的到来,水手们在美洲、非洲以及太平洋上发现了仍然过着狩猎和采摘生活的原始部落,那些人还在使用石器。基于此,开始有科学家提出在欧洲出土的石器很可能出于人类之手的观点,其中包括意大利的地理学家乔治乌斯•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1490-1555)和米歇尔•莫卡提(Michel Mercati)(1541-1593)。后者是梵蒂冈植物园的主管,还是罗马教皇克拉门特七世(Pope Clement VII)的医生,对那些作为礼物进献给罗马的来自新大陆的石器相当了解。还有一位便是法国人伊萨克•拉•佩莱尔(Isaac La Peyrère),作为一名信奉加尔文教的图书馆工作者,1655年,他的书是较早向《圣经》中有关人类起源的说法发起挑战的著作之一。此外,像爱德华•Lhwyd(Edward Lhwyd )也开始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拉佩莱尔的书更为普及,有证据表明,他的说法普通民众乐于接受。他的书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英译本名为《人类早于亚当猜想的神学体系》(A Theological Systeme upon that presupposition that men were before Adam)。他在书中将“雷电陨石”看做是“亚当前”人类的武器,这些人的存在早于希伯来人、亚述人和埃及人。他的结论是亚当和夏娃只是犹太人的始祖,亚当前人类后来就成了异教徒。拉佩莱尔的书遭到了公开的谴责,被抨击为“亵渎神灵和邪恶”的著作,他本人也被宗教裁判所逮捕、关押,他的书在巴黎被当街焚毁。他被迫放弃了他自己的“亚当前”观点,甚至宣布背弃自己的信仰——加尔文教,最后备受精神折磨,死于一所女修道院。
尽管拉佩莱尔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但正如我们所见,人类具有久远历史的观点不但没有就此消亡,反而从新的考古发现中找到了更有力的证据。不过,所有这些发现都没有发挥出它们自身的影响,因为在那个年代,地质学——石器发现的基础原理——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令人吃惊的是,直到18世纪晚期,地球的年龄才成为地质学家们研究的主要范畴。他们最关心的是,地质学的记录是否与《创世纪》中所记载的地球历史相一致。地质学家分化成两大阵营:灾变说和均变说,详情参见本书第31章。“灾变说者”,又称为“洪积论者” ,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坚持《圣经》中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法,这也是欧洲人所能找到的最古老的文字记录。据《圣经》记载,在连续的大灾难中(主要是洪灾,因此称为“洪积论者”),生命几经毁灭,上帝让他们重生,并让他们不断完善。由此看来,《创世纪》中记述的诺亚洪水的故事记载的是这些毁灭中距今较近的一次。由于得到了教会的鼎力支持,多年来,虽然有物证存在,洪积论者却一直立于不败之地。例如,人们曾一度认为,《圣经》中所说的创造天地的那五天,即对应着地质纪年中的不同时代,每一时代都历经千年或千年以上。这意味着上帝造人的“第六天”发生在公元前4000年,大约又过了1100年左右,诺亚洪水爆发了。
传统的灾变说观点还从19世纪的中东考古大发现中找到了一些间接的证据,特别是在尼尼微(Nineveh)和神话传说中亚伯拉罕(Abraham)的家乡卡尔迪亚人的乌尔 (Ur of the Chaldees) 城。人们发现了用楔形文字书写的《圣经》中的国王的名字,比如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还有犹大王国的国王,比如希则克雅王(Hezekiah),这与《旧约全书》中记载的年表一致,大大增加了《圣经》是一部历史文献的可信度。当这些历史遗物被送进伦敦和巴黎的博物馆后,人们开始谈论这些“典籍地理”。
与此相反,所谓的均变论观点也开始得到支持。他们持相反的论调,认为地质学的记录过去没有中断过,现在仍在继续,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大灾难,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是自然作用的产物,从古至今相差无几,而且我们还能看到:河流穿山劈石,造成峡与谷,携带着淤泥奔向大海,淤泥沉淀在海底变成了沉积物,偶尔会有火山喷发和地震。但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些过程都非常缓慢,所以均变论者认为地球的历史远比《圣经》中所说的要长。在这一点上,比拉佩莱尔更重要的一个人是贝奴亚•德•马耶(Benoît de Maillet)。他的著作《耶马德》(Telliamed)于1748年出版,但很可能写在世纪之交,书中勾画出一部地球的历史,与《创世纪》中的叙述完全不符。(因为这个,德•马耶是把这本书作为一本荒诞故事集出版的,署名为一个印度哲学家,并把自己的真名倒着写就得到了耶马德这个词。)德•马耶指出, 地球最初是一片汪洋,滔天的巨浪造就了山脉,海水退去后,山脉便暴露出来,它们受到侵蚀,岩屑沉积到海底形成了水成岩。德•马耶认为,直到他生活的年代,海洋每年仍在减退,只是速度缓慢。而他最有意义的观点是,据他推算,最近一次洪水并没有发生过,而且他还指出,根据他所说的地球形成的方式,在人类文明出现以前,还有一段漫长的历史。他认为生命开始于海洋,任何生活在陆地上的生命都能海洋中找到相应的存在形式(比如说,狗就是海豹在陆地上的存在形式)。跟拉佩莱尔一样,他也认为人类的存在早于亚当。
后来,仍是在法国,伟大的博物学家布丰伯爵(Buffon)计算出(1779年)地球的年龄是75000年,后来又改为168000年,他的观点已接近50万年了,可在他的有生之年却没有将其公之于众。他还更为大胆地指出,地球的形成历经七“世”——这让正统的基督徒们以为他所说的七世类似于《创世纪》中所描述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七天。
现在看来,这些观点极富想象力,而在当时可不是这样。总结“均变说”观点的经典之作是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出版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共三卷,1830年到1833年发行。其中利用了很多赖尔本人对西西里的埃特纳火山(Etna)进行观测的结果,也使用了一些他在欧洲大陆结识的其他地质学家的研究成果,比如埃田内•塞尔(Etienne Serres)和保罗•图尔诺(Paul Tournal)。在《地质学原理》一书中,赖尔十分详细地陈述了他的结论,他认为,过去是一段悠长而连续的历史时期,是地质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持续到今天几乎没有改变。这种关于地质史的新观点还间接地表明,有关人类自身的历史问题也可以如此回答。很多读者对赖尔的书爱不释手,并深受其影响,其中就有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即使均变论逐步取得了胜利,证明了地球历史悠久,也并不表示人类也很古老。多年来,赖尔本人就只接受地球古老的看法而不承认人类也同样如此。《创世纪》也许有错,但错在何处?错了多少?法国解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的工作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他对现存动物,特别是脊椎动物,进行比较解剖学的研究,这引导他开始重建动物的完整骨架,虽然有的只有几根骨头。18世纪晚期,骨骼化石的研究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居维叶的方法证实是非常有用的。当散落在岩石中的骨骼化石被重新组合到一起后,我们便有了更深的认识:那些动物不但与现存的动物完全不同,而且它们再也不存在了。人们曾一度认为这些不寻常的生物还可能被找到,在地球上某个未知的角落它们还活着,但是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人们很快认识到历史上发生过一连串的创造和毁灭。这说明均变论适用于生物学和地质学,而且再一次与《创世纪》不符。这些石头证明了创造和毁灭经历了漫长的周期,而那些埃及法老的木乃伊作为拿破仑的战利品被运回法国,这不但表明人类历经数千年而没有改变,还让人类的古老历史显得越发真实。
其后,1844年,一位博学多识的爱丁堡(Edinburgh)出版人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出版了一本匿名著作《造物遗痕》(Vestige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正如詹姆斯•斯科德(James Secord近来所指出的,这本书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中引起了轰动,因为向公众介绍普通进化论思想的是钱伯斯而非达尔文。钱伯斯并不清楚进化是怎样进行的,也不知道自然选择如何促成了新物种的产生,但他的书指出,远古太阳系最初是一团“火雾”,由于重力作用而凝结冷却,在地质发展过程中,开始的时候巨大而激烈,然后逐渐减弱了势头,但其影响仍将历经数十亿年,论述翔实,令人信服。钱伯斯完整地构想出了生命的自然物质起源,而且公开表明,人类“并不是被神灵从动物中划分出来的,而是长期进化发展的直接产物”。 书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那么,我设想的关于地球有机体的进化观点也适用于其他任何类似的生命体,那就是,最简单最原始的类型孕育出高一级的类型,相似的产物则居于从属地位,如此又产生出更高一级的类型,照此类推直到最高一级,高等生命不会大量存在。或者说,生物的进化是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所以现象总是简单而普通的。”
当时,另一新兴学科——考古学——也取得了类似的发展。虽然19世纪早期有过一些激动人心的考古挖掘,主要是在中东地区,但是其实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人们就对研究及搜集古物兴趣浓厚,这种兴趣一直持续不减,尤其是在17世纪。 在前文中,我们曾经介绍过一种三分观点——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现在我们确信无疑。这种观点最早出现于斯堪的纳维亚,缘于一些不寻常的历史因素。
1622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IV)颁布了一条文物保护法令。瑞典于1630年成立了“国家文物办公室”,同年,瑞典开办了一所古代学院,而奥尔•沃姆(Ole Worm)则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建立了沃尔姆(Wormianum)博物馆。19世纪初期,丹麦民族主义蓬勃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丹麦与德国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战事连连,而1801年,丹麦海军又在哥本哈根港与英军(英军正与拿破仑及其强行集结的大陆盟军作战)的一次交战中几乎全军覆没,英军还在1807年攻打了丹麦的首都。这些武装对抗直接导致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也激起丹麦人研究本国历史的热情,他们希望“从中获得安慰,鼓起勇气迎接未来”。 另一方面,丹麦境内史前遗址相当丰富,特别是巨石造成的山脉为数众多,这些都为探究其远古历史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在此,有一个重要人物不得不提,他就是克里斯蒂安•尤根森•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此人最初是一个钱币收藏家。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古希腊和罗马有了新的认识,好古之风盛行,其中之一便是收集钱币,在18世纪尤盛。从钱币上的字迹和日期将它们依次排列,历史发展的脉络便清晰可见,不同的风格都能找到其特定的历史年代。大革命之后,法国政府在巴黎建立了国家文物博物馆。1806年,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的馆长雷斯莫•尼鲁布(Rasmus Nyerup)出版了一本著作,倡议模仿法国的做法,在丹麦建立国家历史博物馆。次年,丹麦政府宣布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负责保护和收集国家文物,为国家博物馆的建立做准备。1819年,汤姆森成为第一任馆长,国家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馆内所有物品均按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分门别类,并依次摆放。这种分类法虽然早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卢克莱修(Lucretius)——但是这一次是第一次有人照此顺序陈列文物来陈述这一想法。到那时,丹麦的文物收集在欧洲国家中可谓名列前茅,而汤姆森不仅绘制出了历史发展的年表,而且展示了各种风格的装饰物的变化过程,从而得以进一步探究不同时代的更迭演进。
虽然博物馆1819年就正式开放了,但是直到1836年,汤姆森才仅在丹麦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和学说。其著作《北方古代文物指南》(Guide book to Northern Antiquities)在1837年被翻译成德语,1848年有了英译本,这已经是钱伯斯出版《造物遗痕》的四年之后了。从此,三大时代的理论体系才在欧洲传播开来。文化进化的思想和生物进化的思想平行发展。
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一些学者,像弗朗索瓦•德•儒阿特(Francois de Jouannet)等,开始注意到各种石器也存在差异,和某些灭绝动物相同时代的器具上有缺口,而从一些地方的墓穴中发现了相同的器具,打磨却更为光滑,这些墓穴的年代较近,在那些灭绝动物的时代之后。这些观察结果最终将历史年代的顺序细化为四个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
因此,1859年5月,当埃文斯和普雷斯特维奇跟布歇•德•佩尔特在阿布维利见面后返回时,石制手斧的制造用途、重要性和实用性都已不容置疑,也无可争议。全欧洲的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都致力于描绘这幅壮丽的图景。不过,各种分歧依然存在。跟普雷斯特维奇一样,居维叶的接班人爱德华•拉尔泰(Edouard Lartet)坚信人类拥有久远的历史。但就像我们在前文中看到的,赖尔多年来一直反对这一看法(他曾致信查尔斯•达尔文,请他原谅自己不愿意“变成一只猩猩”)。就在普雷斯特维奇和埃文斯从法国返回的那一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the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一书,该书的宗旨并不是要证明人类的历史有多古老,而是旨在说明一个物种是如何进化为另一物种的,所以是基于钱伯斯的观点,否定了造物主存在的必要性。这场有关进化思想的革命起源于拉佩莱尔和德•马耶,钱伯斯将之发扬光大,而《物种起源》一书则证明了自然选择极其缓慢。因此,尽管不是达尔文的主要意图,但是他的书还是强调了这一事实,即人类的历史要比《圣经》中所说的古老得多。自然选择可以用来解释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古生物学记录的改变。人类的古老历史由此确立。
这一观点被普遍接受后,思想便飞速向前。1864年,爱德华•拉尔泰和一个伦敦银行家兼古董商亨利•克里斯蒂(Henry Christy)率领一支英法联合考古队,在法国的佩里戈尔(Perigord)挖掘岩洞,他们取得了不少发现,其中之一是在拉玛德琳(La Madeleine)找到的一根猛犸象牙,上面刻了一头全身长毛的猛犸象。这件物品“充分证明人类曾经与更新世的灭绝动物共同生存过”。
1867年,巴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在布置庞大的考古成果展时依据的就是四个时代的理论体系,参观者漫步于各个展室,犹如穿行在欧洲史前历史的长河之中。科学的考古研究取代了古物收集者的惯例。“现在,人们可以想象出一部没有文字记录的文化史,英法两国铁器时代的墓葬、瑞士铜器时代的湖上房屋、新石器时代丹麦厨房里的垃圾,沿着这一路走来,我们回到了旧石器时代……”查尔斯•赖尔最后终于还是接受了这一新观点,1863年他出版了《古代人类的地质迹象》(Geological Evidences of the Antiquity of Man),在开头的几周内就卖了4000本,同年再版了两次。
从此以后,世界各地都陆续发现了古代石器(我们将在第一章论及),它们分布广泛,形式多样,这让我们重新思考那遥远的过去以及远古人类的思想活动。在普雷斯特维奇和埃文斯证实德•佩尔特发现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制作石器的最早日期不断被提前,最后人们到达了270万年前埃塞俄比亚的戈纳河(Gona),这也是本书的起点。
(【英】彼得•沃森著,姜倩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