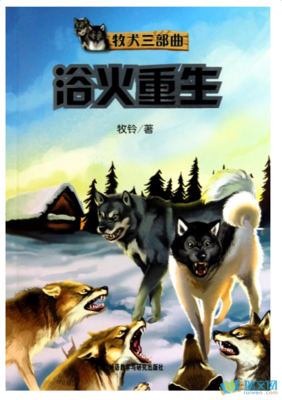复仇之书读后感1000字
《复仇之书》是一本由蒋蓝著作,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复仇之书》读后感(一):朱晓剑:是侠义还是复仇
古代的侠客是很多人的心中梦想,他们力挽狂澜,千金一诺,蓬勃的生命、淋漓酣畅的元气、亢直的性格、特异的武功……构建出一幅侠客的美好图景。如袁中道《李温陵传》所说:于古之“侠儿剑客,存亡雅谊,生死交情,读其遗事,为之咋指斫案,投袂而起,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若不自禁”。但在古代的侠不是一门职业,它起源于原始家族成员互助的古风,诞生于春秋,盛行于战国,大倡于同盟会。不过,在侠客的历史上,总是与复仇紧密相连,从而构成了一种被命名“复仇文学”的样板。在作家蒋蓝的《复仇之书》中,我们能读到的既有侠客的豪爽,也有复仇的思想,它们混搭在一起,构建了一个貌似矛盾而又统一的世界。
《复仇之书》可以说是侠客复仇的一部简史,梳理了先秦时代至民国年间的历史,在总结侠客复仇的历史的同时,对每个时代的侠客精神有独特的概括,但最终可以归结为:侠之大者,惟有德者居之。蒋蓝将侠客分为三个时代:
独侠时代:在先秦时代,一种“独侠”的意象强力跃升为生与死的强悍主体。鲁迅先生认为,在王道文化所推崇的儒家恕道的“王土”之外,民间一直流淌着放血追义的复仇精神,这是民族得以葆有风骨、剔除杂质的生命活力,更是对正义的一次次深犁。可以括之称为一个独侠时代。游侠时代:中国封建时代的侠义事迹,是顶起旷大黑暗的一茎烛火。一方面在于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固,侠义之刃已经难以靠近独夫民贼;另外一方面,一己的恩仇逐渐成为行侠仗义的主因。游侠俨然成为了封建时代的一抹亮色,作为先秦侠义的“剩余价值”,这是一个侠义逐渐式微的时代。从暗杀到明杀的时代:晚清时节,同盟会·光复会先烈对腐败朝廷的铁血一击,是对远古侠义精神的一次大招魂。在辛亥革命前后,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开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止,付诸行动的暗杀,共五十多起。由“暗杀”到“明杀”的嬗变,展示了中国侠义精神的大纛,使彪炳千古的暗杀时代,成为了轰天绝唱。
复仇者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为国家大义、为朋友、代父母兄妹、为自己、为不相识的平民和失败的复仇。从这些复仇的侠客身上,我们不难找到他们的精神共性,这包括复仇者将自身死亡作为一种追求;对复仇不懈的执着;复仇人是非观念,复仇正义感模糊。正是这样的理念造成了种种悲歌。在古代侠客史上,他们的身影是孤绝的,走进历史的深处,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纵观中国的侠义史,或许我们可以发现墨、儒两家的侠义观最为接近,这也就此造就了中国古代的侠行的正义叙事。不过,也并不是这么绝对的,亦有为了一己认为“正义”挂念,做出侠义的事情来,这样的侠义你不好去判断它的真伪,但在推动时代的发展的视野下观察,我们才能够区分侠义中的是非。《复仇之书》并没有在理论上做出相应的探索,在具体的事件中探讨侠义与复仇的可能性,如果说复仇乃春秋大义的话,那么侠客在具体的复仇行动中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动机,构成了复仇的基因。而在不同的侠义叙述中,我们能读懂侠义与复仇,这才能读懂中国。
《复仇之书》 蒋蓝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定价:35元
《复仇之书》读后感(二):复仇背后的豪侠义士
复仇是一个庄重的词,与这两个字相生相伴的是正义与勇气。同时,在古代中国,复仇也是一个光明磊落、豪气干云的词,是中华文明中无法忽略的一页。
早在2007年,蒋蓝就出版了《拆骨为刀》一书,《复仇之书》在初版基础上改写了10万字,并新写出15万字,这个全新的30万字版本2011年10月由成都时代出版社推出,标志着蒋蓝思考6年的“侠义系列”的一个终结。
《复仇之书》不是一本让人隐约感觉到某种狭隘的复仇心理的书,这是一本让人不忘耻辱和恩义的书。
蒋蓝认为,侠有辅助、挟持之义;義字指羊,是“用我来宰羊以作祭品”的意思。又因“我”字指宰羊的兵刃,故義字从我。侠义之魂戛金断玉,响彻古中国的锈红色长空。侠义之士就是放弃自我的一群人。拆骨为刀的推刃行为是一种自戕,竟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喜欢武侠的人,知武而不知侠,慕侠而不重义,就是本末倒置。
蒋蓝在《复仇之书》中这样写道:“激烈的复仇,在古代中国是以‘血亲复仇’为枢纽的,是指君主、师长、朋友等被人杀害或者侮辱后,不惜代价对仇人采取暴力报复,以杀死仇人为最高目标的行为。这个复仇范畴,其实就是孟子所说的‘五伦’范畴,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从这个精准的概括中,我们对中国古代的复仇便有了感性而深刻的认识,也可以从中窥见其在中华文化中的坐标。
“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刺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属于“正史”,在《史记》中有着浓墨重彩的书写。在司马迁的眼中,为复仇而出现的刺杀充满了侠义,复仇者拥有侠肝义胆,值得歌颂。事实上,司马迁从不吝惜笔墨对豪侠义士的赞扬。
《复仇之书》是蒋蓝对中国历史上关于刺杀与复仇的一次梳理,在他笔下呈现了一大批豪侠义士,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忠,用鲜血书写了义。荆轲、专诸、要离、聂政、豫让、吴樾……这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壮士,谱写了一曲曲华丽而壮阔的悲歌,也让浩瀚的历史更加荡气回肠、让人概叹。他们用匕首、利剑,以及更为先进的手枪,为一段段历史画上了漂亮的惊叹号。
在《复仇之书》中,作者对复仇的动机和类型进行了归纳,大致分为为国家大义复仇、为朋友复仇、代父母和兄妹复仇、为自己复仇、为不相识的平民复仇以及为失败复仇,处处彰显忠孝与民族大义。虽然作者在文中不断地对豪侠义士们的人格、情绪、处境、复仇的心里动机以及使用的复仇器械进行分析,但是,这并不是一部枯燥的理论著作,而是一部有血有肉的历史传奇,人物形象丰满,故事跌宕起伏。
在历史与文字里,蒋蓝是一个技艺精湛的魔术师,手指轻轻一拨,就把我们带进了历史时空,感受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壮举。但是,作者不仅仅是讲述历史,更是对侠义精神进行提炼与张扬,对侠肝义胆给予激赏。《复仇之书》激活了尘封已久的历史,那些人物和故事立即跃然纸上,被我们捧在掌心。那些只身赴死的刺客们肉身早已腐烂,但他们的心跳从远古穿越而来,在信仰稀缺的今天,如一道闪电那般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蒋蓝说,本书的书名本来叫“推刃之书”。《公羊传·定公四年》:“父不受诛,子复雠,可也。父受诛,子复雠,推刃之道也。”何休注:“一往一来曰推刃。”说的是父亲因罪被诛杀而儿子为父报仇,仇家之子亦必报复,则形成一往一来的循环报复。后用“推刃”泛称刺杀或复仇行动。出版社考虑到过于生僻,才改为《复仇之书》。
历史是否靠刺杀书写,刺杀是否改变了历史,在后人们看来已经不重要了,复仇背后展示的勇气与正义,却从古至今一路奔腾而来,且将永远奔向远方。
《复仇之书》读后感(三):高维生:粗砺的铁血精神
轻微的声音,如同锐器划过丝绸,在空气中传出很远。躲藏鞘深处的剑,耐不住寂寞,瞬间窜出,剑尖滚动冰冷的激情,执剑的手,紧紧地攥住,凸现了坚毅的线条。指缝间冒出一股股杀气的冷雾,在空间颤动。五根手指像伺机的狮子,在等待猎物的出现。剑和手的结合,形成了一股钢力,炽热的血烫伤了肌肤,温暖了剑炳。剑锋和目光在特殊的时刻,纠缠一起,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力量,冲出了喷泻毒汁的仇恨之花。
2008年,重庆出版社推出蒋蓝的新书《拆骨为刀》,讲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侠义事件。看到那些冷静的文字,我有些控制不住情绪,一个个冷颤打湿了窗外涌动的阳光。我翻动书页,文字复活了历史深处的人物,侠者踏响了辽阔的大地。
江湖早已沉寂,入鞘的刀剑孤独地体味漫长的时间苔藓味道,等候主人的归来。而深埋地底下的刀剑,从此不见天日,在泥土里一点点地被腐蚀,爬满斑斑锈痕。折断的刀剑,流尽最后一滴精神,不可能再有人修复了,横断的碴口,结满了锈迹,一层层地盖满。一代代侠义的勇士走了,后不见来者。蒋蓝走进尘封的历史中,如同进入陌生的峡谷,找寻一条道路,这是十分艰难的。文化大散文不是把历史资料,和旅游观光的情感,放在文本的臼子里,用文字的槌猛烈地捶捣。在文字槌的撞击下,形成黏稠的液体,让它在纸上流淌,散发的气息,刺激人们的欲望。不是资料的分析,放进时代的佐料,调制一盘流行的色拉。
蒋蓝不是贩卖历史人物,玩智力游戏,为了弹击阅读者的神经,削几条弧线, 打几个擦边球。从堆积的资料中寻出“刺客”,让他们手中挥舞的刀剑,袖中的铁椎,弹奏复仇的古琴,披上时代的装束,戴上娇情的面纱,热热闹闹地开一个展销会,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蒋蓝剥开时间的外衣,露出真实的肌体,推翻传统达成的共识,对这些侠义的人们重新评价。
剑不过是一种工具,它是人生对信仰的反映。对于侠客们来说,它也是检验忠信的尺度。一诺千金写起来不会费太多的笔划,但是做为标尺,行动中却十分艰难。它是一座高万仞的山,沉重地驮负在肩上,不会轻易地甩掉,险峻的路上埋藏了无数的杀机和陷阱,这都不会阻挡侠客们前进的脚步。“聂政杀侠累,不仅是一个为‘知己’刺杀复仇的过程,更是用生命去实践侠义的举动——那就是一诺千金。”蒋蓝拨开厚重的历史的积雾,举着思想的灯,推开了一扇大门,沿着时间的痕迹,梳理侠客们的言行和守诺,而不是为了取悦一些人的喜闻乐见,虚构情节,把他们演绎成媚俗的戏说。
蒋蓝用笔敲落侠客身上淤积的尘埃,恢复了真实的情景,走进了侠客们的心灵世界。侠是一个厚重的大字,蕴含了太多的意义,说是非常容易的,真正做到位并不简单。侠是一种精神,万丈豪气,在掷地的诺言中,他们实践自己的言行。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很多的人与事,值得我们向侠义的人行注目礼。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了消费的时代,侠的精神更是被商品吞噬地无影无踪。侠义变作了传说,只有在人文历史中能觅到他们的影子。蒋蓝的文字像他的性格,冷峻中透着一股温暖,他整理的不仅是资料,更多的是侠义的精神。他怀念热血暖热的冷兵器时代的侠义之客。蒋蓝喜剑,他不是为了风雅,在书房里挂着一把剑。读书累了的时候,拔出剑来舞弄两下,在剑锋上抓住一股执著和侠义的血气。
秋蝉的叫声,送来了夜的寂寞。在这安静的长夜,手中蒋蓝的书越来越重,二十多万字的书,却山一般地压在手上,抬不起来。一曲《广陵散》流传千古,其刚烈的弦乐,震撼多少人的心。《铁血斑斓的彭家珍》从投出炸弹的瞬间,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快意恩仇施剑翘》,到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了。我看到了刽子手行刑时残酷的手段。这是丧失人性的一击,那把铁锤将徐锡麟的睾丸砸碎,血肉沾染冰冷的铁块。刽子手又无情地、活活地剖开徐锡麟的胸腔。这一刻的文字渗出哭泣,在书房里缠绕不散。刺激眼睛,模糊了我的视线。“可以说,徐锡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位被专制体制‘吃’掉的人物。辛亥革命进程中,以徐锡麟之死最为酷烈,在这血淋淋的过程里,中国专制权力放之于人的‘身体政治’,同时也得到了最为狰狞的展示。”这个结论,蒋蓝在纷杂的历史中寻找到了。
思想是一座炉火,它在熊熊燃烧,各种情感和思绪被投进炉中冶炼。从这里锤炼出的东西,去掉了杂质,去掉了虚娇。蒋蓝在后记中写道:“复仇并非是一味仇杀,而是伸冤。复仇,除了‘忠孝’的道德基础之外,尚有‘春秋大义’的伦理基础。这里的‘义’既有‘适宜’的意思,它说明了复仇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也有‘道义’‘荣誉’和‘正义’的意思。俗话‘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就包含了这些意思。所以,复仇是‘为人’的前提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古人的复仇,在当今环境中不可胡乱效仿的。这样的复仇意识,与现今的所谓恐怖主义,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窗外有一片空地,种满了青菜和长着几株树,秧蔓上攀伏几朵黄色的花,不像盛夏开得那么狂烈了,激情被初秋的风吸尽。我还是想摘下来,用这种朴素的、生于大地的花,敬献到书中侠义的人们的墓前。我似乎注视到蒋蓝,点燃了一颗烟。这一刻,他的眼前出了遥远的过去,闻到了历史的气息,看到了江湖的险恶。蒋蓝的文字像巴蜀阴柔的雨,润湿了寂寞的情感。我这个年龄不青春了,不是易动情感的季节了。我在蒋蓝的文字引领下,在历史中行走,感受剑风刀雨的淋漓。
2008年8月28日 于一苇庐
——《中华读书报》2008年12月3日
《复仇之书》读后感(四):尉迟克冰:没有手柄的利刃
一把没有手柄的利刃,闪着凌厉的寒光,刺穿历史的长空,腥红的血漫漶了几千年。利刃一头连着赤诚重义的侠客,一头连着无边无际的黑暗。复仇的光芒,擦亮利刃,死亡就如同归乡。
鲁迅先生认为,在王道文化所推崇的儒家恕道的“王土”之外,民间一直流淌着放血追义的复仇精神,这是民族得以葆有风骨、剔除杂质的生命活力,更是对正义的一次次深梨。
《复仇之书》是一部厚重的大书,凝结着蒋蓝先生六年的心血。它如同一部侠客复仇的简史,记述了从先秦时期至民国年间的侠客历史,且对每个时代的侠客精神有独到深邃的总结和概括,对他们的复仇观念进行了研究和探索。每一篇都具备从历史深处走来,越过现代精神高地,逼近社会底层,接通大地人心的宏大气象。奇异的故事,独特的视角,别样的叙述,诗化的语言,渗透其间的生命感悟和哲学思考,带给读者的不啻是一番赏心悦目的审美惊奇。从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些侠客激荡的血液在奔流。
文丛里,我们听到刀剑之声,嗅到骨血之气,读来酣畅淋漓,荡气回肠。那些文字不仅仅是用来看的,更是用来听,用来咀嚼和填满精神的。他的文字与他的灵魂紧紧融合在一起。蒋蓝说,真正的写作就是放血,用生命去写作。那些文字里氤氲着血气、体温和灵性,你觉得它们鲜活,会说话,长着双足和眼睛。这本著作,引领你进入泛着葱郁光芒的精神领域,他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播撒种子、耕耘收获——以博学做土壤,施良知之肥,灌血液为浆;以责任为首义,执正义之笔,书天下奇文。
蒋蓝的出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在这个盛行伪装粉饰,虚浮自大,追名逐利的社会里,他却能独树一帜,反思批判,悲悯众生。他站在一个制高点,俯仰之间,洞悉世事,明察秋毫,以犀利的文字为刀枪,刺穿历史,直逼现实,让你感受到火热的激情和浓烈的杀机。蒋蓝说自己是汉语写作的异端,“我像一只飞蛾,在越来越危险地靠近火苗”。这是一种较量,不是飞蛾葬身火焰,就是火焰被飞蛾的翅膀扑灭。他的写作,让某些所谓的大家汗颜。那些文字极具杀伤力,直抵生命深处,直逼灵魂内里,敢于正视,敢于直面,戳破虚伪的谎言,昭揭暗藏的本质。“我从来坚信,一个软骨症患者,即使上演一番拆骨的‘形而上’之秀,他抽出来的多半是一根牛皮菜。于是很多人就跟着形而上起来,不料却跟着栽进了制度的裤裆……”
有极少数人为文字而生,蒋蓝先生属于这样的人。一个文字王国缔造出的精英,他自由驰骋,奋笔疾书。我惊异于他的智慧、勤奋和高超娴熟的驾驭文字的本领,文字在他笔下,流淌成一朵朵奇葩,一刃刃锋芒,一脉脉高山。他能汇聚起滴水,使之变成恣肆汪洋,也能调遣云朵,使之成为滂沱大雨。历史在他笔下呈现出的不是简单的线状,而是庞大的网状。而且,他能够把沉入时间缝隙深处,躲避、遮掩起来的历史,重新构建起来,使之凸显出意义。如在《西秦暗杀考》一文里,他作为一个民间调查者,循着历史的足迹,荡开迷蒙的烟尘,揭开重重帷幕,将多个与刺杀嬴政有关的人物和事件收入文中,并融汇深刻的思考。荆轲、唐雎、高渐离、张良等等,所有的形象和事件在蒋蓝独特的叙述中,展现得丰满而酣畅,且水到渠成地引出自己对“侠”的认知——“侠”有“辅助、挟持”之义;“義”字指羊,是“用我来宰羊以作祭品”的意思。又因“我”字指宰羊的兵刃,故義字从我。侠义之魂戛金断玉,响彻古中国的锈红色长空。侠义之士就是放弃自我的一群人。拆骨为刀的推刃行为是一种自戕,竟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喜欢武侠的人,知武而不知侠,慕侠而不重义,就是本末倒置。
历史并不完全是固化的客观存在,它具有多面性和多义性。不同时代、不同观念、不同立场的人对某一段相同历史的解读和认知,未必相同。春秋时期发生的“弘演纳肝”事件,为历代帝王和史学家称颂,几千年来,弘演一直被视为侠义之士,备受推崇,成为礼教标榜的人物。然而,蒋蓝先生却对此进行了严正的批判,原因是弘演剖开肚子,收藏的是昏聩国君卫懿公之肝脏。这样一来,弘演便身装了权力的垃圾,成为权力的垃圾桶,却接纳了数千年的道德香火,会让后人对权力崇拜产生严重错觉。这种对固有史观的大胆批判,对侠义内涵的厘定和确认,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读蒋蓝的文章,总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寒光和锐气。他的愤世嫉俗不是狭隘的,而是更为广阔的,站在社会和历史的高度,怀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呼唤正义、良知,追求民主、平等和自由。他的冷眼和横眉从来都是朝向压制人、扼杀人的机器和制度。“面对一架从不停歇的绞肉机,为什么还是有那些请命者,把自己的血肉一点一滴送进刃口?我逐渐感觉一种豁然的死,在我眼中变得清晰起来。死不是大限,死的确如一场归乡的跋涉。归义即死,即是归乡。死亡并不能左右死,它只能使义更敞亮地到来。”这种对国家机器的批判,对死亡的追问和对大义的解读,充满了血性和骨气,如同一声惊雷,划破暗夜的死寂。在这样一个万马齐喑,缺少真话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全民娱乐,麻木浮躁的时代,蒋蓝的呐喊行为,显得弥足珍贵。他是真正的先锋,一个站在时代浪头顶端,与风雨搏击的先锋。
这样的人,注定了孤独。正如蒋蓝所言,先锋多了,就意味先锋的死去。尼采认为,只有创造者才是孤独的,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是孤独的。创造者和哲学家的命运注定了他一生孤独,他的命运已经包含在他的性格和使命之中,他的真诚、勇敢和创造性注定了他的孤独。孤独不是精神上的弱小,不是对人生的回避,而是精神的丰富、强大,是生命力的旺盛和对人生的热爱。
蒋蓝的灵魂高贵而孤独。他穿越时空隧道,游走在侠义之士的精神世界里,钻进他们的骨髓和血脉,融为一体,他用自己的呼吸感知他们的呼吸,用自己的脉搏感知他们的心跳,与他们倾心交谈,成为知己。骁勇的专诸,决绝的要离,惨烈的豫让,悲壮的荆轲,凌厉的武松,刚毅的徐锡麟等,众多英雄人物在他的世界里复活,并大放光彩,让我们触摸到生命的钢质和热度。他又能旋即反转,跳离,回到现实,站在更高更远处,用犀利的目光审视。所以,蒋蓝会比他们自己更认知自己,比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他一点点把历史的铁,放置在思想和灵魂的火灶上,锻造出一件件锋利的武器和兵刃,直刺黑暗的夜空,划出道道刺眼的光芒,兵刃上沾满肮脏的斑斑血迹。侠士的魂魄站在蒋蓝的骨头里,使他成为不折不扣的文侠。他少年习武,豪爽义气,体格强壮,精力充沛。蒋蓝身高一米八,挺拔威武,这样的身高,在四川人里,的确罕见。他的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文人少见的英武之气。他的人格理想、精神气质已与侠义风范黏合一起。
独特的气质和性情注定了他独特的文字。他的文字世界让你感受到奇绝陌生。汉语语素在他的调遣下,脱下制服和套装,变得古灵精怪,喻像、意境激荡人心,在蒋蓝的重塑下,它们有了生命和特质。他的写作从不循规蹈矩,更不老生常谈,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和高妙的哲学思想,让文字灵变而又坚质。“时间如过火的灰烬,从来不曾让我想到复活,因为灰烬不过是火的睡眠。”“要离用血勾勒出一个区域,并拆下了自己的骨头为刀,在践诺之后,又用骨头挖好了自己的坟墓,他跌进去了。”“其实,张文祥是用自己的血肉,把古中国侠义的豪情和悲壮,钉在了凌迟的木桩上!让我们至今相信,侠义不是乌托邦,侠义不是文人酒后的臆想。”……书中,这样富含张力的文字比比皆是,它们刻骨夺目,给人带来视觉和思想的动荡与冲击。
历史如果缺失了烛照现实的作用,终将是苍白无力和乏味的,历史永远生存于意义中。蒋蓝先生担负起这样的使命,让有意义的历史逐渐复活起来。在这样一个主张和谐、和平的社会里,探讨侠义精神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其实不然,我们中国国民现在缺乏的,就是具有良知、敢于担当、信守诺言的侠义精神。侠义精神不等同于恐怖主义。单个的“侠义精神”体现在救助困难群体,而放大了的“侠义精神”则是民间力量和声音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责任与态度。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中国人历来对英雄主义的崇拜,让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叫做“侠义”的因子,现实主义的蒙蔽或许让这种豪情一时消减。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唤醒中国人骨子里那种“侠义精神”的知觉,远离麻木和冷漠。蒋蓝先生自觉地做出了这样的担当,是多么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