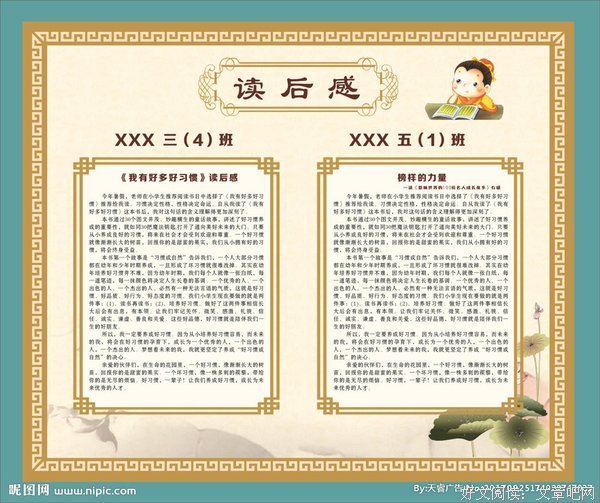The New Yorker读后感锦集
《The New Yorker》是一本由著作,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The New Yorker》读后感(一):当你要对IHT感到厌烦时候,朋友推荐了这个赏心悦目的杂志
首先喜欢它的封面,每期都是美丽的绘图,值得收藏。
内容上非常丰富,文字似乎可以翩翩起舞。带有一点点傲气和调侃精致生活的意味。
放松心情,坦然阅读每个小小的话题,你只会觉得世界可以是另一番胜景。
《The New Yorker》读后感(二):喜欢看纽约客的朋友可以找我,每周按时更新
扣扣:2631186670
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看,很方便。
《纽约客》(The New Yorker),1925年创刊,周刊,美国纽豪斯家族属下的康德·纳斯特出版公司主办。综合文艺类刊物,内容涉及政治观察、人物介绍、社会动态、电影、音乐戏剧、书评、小说、幽默散文、艺术、诗歌等方面。该刊强调精品意识,注重刊物质量,编辑方针严肃认真。 《纽约客》原为周刊,后改为每年42期周刊加5个双周刊。从创刊伊始,《纽约客》就特意表明,该杂志面向那些能够欣赏其幽默和深入报道的读者。它将纽约市作为杂志的中心,使得这个城市的网络,这个城市对戏剧、电影、博物馆的宠爱都成为一种具有吸引人的商品。
《The New Yorker》读后感(三):推荐专栏letters from China
喜欢 New Yorker~里面的文章平和而睿智~而且那个Letters from China专栏的作者很赞。现在那个作者和之前的那个作者在中国生活多年,文章很温和,对中国了解也蛮多,很合我心意。我曾经一度把NY Times作为浏览器主页,后来发现那些关于中国的头版头条实在让我无可忍受,那些记者基本超级bigoted,严重怀疑他们都被brainwashed了,经常看得我怒火中烧,血压升高。果断设置New Yorker 为home page. 再也不会上火了。
我一个米国朋友喜欢组织book club,经常讨论的就是New Yorker里面的文章,她也很很喜欢Letters From China 这个栏目。有一次我们book club 一起讨论这篇文章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09/10/26/091026fa_fact_hessler。我很喜欢这篇~
《The New Yorker》读后感(四):“事实核查员”与“女性杂志”读者
杨小彦的一篇《顶尖杂志的梦想》登在8月21日的《南方周末》上,介绍作家出版社王栋的新书《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做过多年编辑和主编的杨小彦,对一个问题感到震惊,那就是各个杂志都设有的“事实核查员”这一岗位:
“‘事实核查员’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查对所有的来稿中涉及的事实,复按所有的来稿中的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以保证杂志所传达的知识是准确无误的。这一点,在《国家地理》杂志中更甚。他们的编辑部一共有20位事实核查员,以保证刊出的内容准确无误。结果他们在读者中建立了‘不出错’的信誉,以至于有一次弄错了美国加州一个小镇的名字,居然成为当天的新闻。”
腾讯读书上有该书的电子版连载,王栋采访最富盛名的综合性人文期刊《纽约客》的执行总编辑多萝西•威肯登(Dorothy Wickenden),总编辑的原话是这样的:
“谈到编辑,我认为把《纽约客》同其他杂志区别开来的重要一点是:编辑的深度和为文章的出版所做的细致工作。我们编辑的工序,比其他任何杂志都多:我们有非常非常认真负责的事实核查员,他们一丝不苟,每篇文章、每个事实,都小心查证。然后有原稿编辑这一层。还有资深编辑,他们会从头到尾跟踪一篇稿件的情况。一篇稿子在刊登前也许会经过上百次的编辑——其他杂志可能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需要各个部门的互相配合,需要所有人都非常非常仔细地工作。要注意很多东西,包括风格、精确性、报道的深度。如果一篇稿件的报道不够充分,我们会让那个记者再回去做更深入的采访……”
令人欣慰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杂志都坚持这般的尽善尽美,据说很多女性杂志,尤其在涉及性爱报道上,为了吸引读者,或多或少地编造着谎言。《小姐》(Mademoiselle)、《大都会》(Cosmopolitan)、《魅力》(Glamour)、《玛莉嘉儿》(Marie Claire)……都是如此。国内的女性杂志,《读者》、《知音》、《女友》、《家庭》……在编造故事这一点上,完全与国际接轨。
更可喜的是,幸亏此地没有死板、僵化、铁面一张的什么“事实核查员”,可以尽情地发挥与想像,小谎无伤大雅,不是吗?更何况是写给小孩子看的教材呢!无所谓,随手写几个小故事敷衍一下就是了——闻一多的讲演,尽可以去骨;斑羚会按照年龄老幼分两拨,展超级的轻功;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帮人挖井;建大坝胡乱移民,低劣食物引发中毒而产生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Tibet来了菩萨兵……
翻阅了许多本这样的教材之后,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读不懂《纽约客》了,因为多年的阅读训练,只是为了把我培养成一个资深的“女性杂志”读者。
僵卧孤村不自哀,上下左右,老老少少,不都是“女性杂志”读者嘛,天天开心地读讲下去,长久地雌服,终有一天彻底领悟玄牝哲学——独乐乐,与众乐乐,孰乐?不若与众!
《The New Yorker》读后感(五):转载:困困《纽约客痴迷症》
欧逸文现在真像个明星,总是能在报纸或杂志上看到他的照片。我第一次见他却是在一个非常松弛的场合,松弛得简直让人发了疯:在愚公移山看一个瑞典人演出,当此人沉闷地敲了半个小时吉他把儿后,我们都被震摄了,不知道该为这种奇特的艺术形式欢呼,还是该大声咒骂,因为左右为难而尴尬地怵在场下。过了几天,我邀请欧逸文再探愚公移山,这回看的是朋克演出,他说他有点胆怯,不知道是不是该在耳朵里塞两团棉花再去。
欧逸文是《纽约客》杂志驻京记者,美国人,主持“中国来信”栏目已有4年,写过贾樟柯,胡舒立,疯狂英语李阳,拳击冠军邹市明,愤青唐杰⋯⋯。他最新的作品是《跟着中国旅游团游欧洲》,春节的时候他报名参加一个欧洲五国大巴游旅行团,从上海出发走了一趟。这篇文章迅速就被译言给翻译成中文了,有人说:看,写得太棒了,非虚构写作!还有人开始挑毛病,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的反弹——以前欧逸文写点东西也就在媒体小圈子里传看,现在一定会被大范围传播,他红了,喜欢他的人和不喜欢他的人一齐增多。
好几年以前,我总是约欧逸文出来闲聊,他告诉我纽约时代广场康泰纳仕大楼下的咖啡馆,完全就是个媒体集团风格集萃:一桌美男的那是《GQ》,衣衫不大讲究的来自《纽约客》,美女就不用说了,是《Vogue》的,你永远都看不到《连线》的编辑,他们不愿意离开电脑⋯⋯。我兴奋地在脑中展开这幅画面,热络地对欧逸文说:以后咱们就是同事啦!那时候我为康泰纳仕旗下一家时尚杂志中文版工作,自觉从此以后离《纽约客》仅一步之遥。很快我发现这是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幻想,我就不干了。
感谢媒体前辈的费力宣传,对《纽约客》的痴迷,起先主要来自那些熠熠闪光的名字和花边轶闻。第二任掌门人威廉.肖恩,在位35年,阳春白雪的守门人,他奠定了《纽约客》的文风与形像——“与洁净的指甲、大学、支票账户和良好的意图一样成为阶级标志的一部分。”《纽约客》的撰稿人也有如明星——像宪法修正案一样风格永存的E.B怀特,把最后一部短篇小说发表在《纽约客》的赛林格,与编辑互相成就(消解?)的雷蒙德.卡佛,从来不谈文学只谈怎么劈木头的约翰.契佛⋯⋯。好多杂志养名作家,那是妓院里弹钢琴的,《纽约客》全是弹钢琴的。
2004年,《纽约客》第一次派出常驻中国的记者:何伟。他是欧逸文的前任,据说因为他“恰好在中国”。何伟曾经出版过以中国为描写对象的两本书《江城》和《甲骨文》,今年他的第三本书《寻路中国》出了中文版。这是本知名度进入了通俗领域的畅销书,能在报纸上看到无数赞美与大段的摘录,我也要跟个风,发出我的赞美之声——看一个老外细心地描写被我们忽略掉的盲区,真是又好玩又让人汗颜。
1960年代,曾经在美国有过短暂的记者名流化,报纸耐心地塑造一个又一个新闻记者,为他们描述了别人的巨大的痛苦,别人的疯狂的喜悦,别人的了不起的成就而欢呼,好像这些痛苦喜悦与成就都是他们的。之后那些赞许的目光就从他们身上撤走了,除了《纽约客》记者。至今仍然能够在姊妹刊或相好的媒体上见到莉莲.罗斯(书评人,威廉.肖恩的情人),大卫.格兰(犯罪题材记者),Raffi Khatchadourian(《维基揭秘的秘密》作者)的访谈。在中国,《纽约客》明星是何伟与欧逸文。
最近一次见到欧逸文,是一群人吃老北京涮肉,我们分别聊了聊最近都在采访谁,有什么写作计划。我觉得再也没有以往那种不切实际的兴奋之情,《纽约客》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寄托了太多幻想的符号,但它仍旧值得尊敬,它变得更加触手可及,更加真切,它派出了两个大活人扔给中国记者实打实的压力——写中国,怎么还写不过外国人?
《The New Yorker》读后感(六):信息时代的生长之道
让飘散的信息——委身——引爆
早就有人把当今的世界说成是信息时代,但信息时代究竟是怎么回事,似乎谁都在说,谁又都不太能说清楚。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的时候,这样的局面也许正在发生改观。在常常使人不知从何说起的世界中,像《引爆点》、《长尾》、《人人都来了》这些畅销书的问世和传播正在帮助人们增进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畅销书常常名不副实,但也有列外。仅仅是这三本书的副标题,就可能让人有所启发:“小东西如何产生大影响”,“为何商业的未来是在更多中卖得较少”,以及“没有组织的组织的力量”。
《引爆点》的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从病菌的流行研究当初不起眼的现象如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比如纽约地铁的犯罪率在1990年代初期出人意料的大幅下降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一个简单的行为:交通当局接受专家的意见坚决清除列车上的涂鸦,大大消解了因环境的混乱造成的犯罪传染性。
《长尾》作者克里斯•安德森提醒人们注意细分市场对传统大众市场的挑战如何给更多人的生活带来机会和价值,比如一本当初不为人瞩目的登山探险之作因为将近十年后另外一本类似主题之书的流行而获得新生,原因在于网上的口碑相传。
而《人人都来了》的作者克莱•舍基向读者描述那些看似没有组织的组织却在全球各地不可思议的组织起来,比如由无数使用者自发添加的维基百科——“维基”(wiki)来自夏威夷方言,意思就是“迅速”——迅速超越各种传统的百科全书,使得知识的累积和传播超越了一时一地的限制。
综合起来,这三本书传递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在前所未有生长的信息网络中,各行各业的人如何能够更好地安身立命,而不至迷失在信息的洪流中。
换言之,这是一个在看起来浑沌的世界中辨明秩序的问题。心目中有了这世界的秩序,人生的旅途就有章可循。
这三本书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从众多谈论世界的言论中脱颖而出,尽管可能有种种因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的确在这个让人常常不知所云的世界中勾勒出了一些比较清晰的图景。
不仅如此,无论从书中的故事还是作者自己的经历,他们其实都在深化一个可能超越时代的人生经验,那就是,委身于一项专业并持久地做下去是生存的一大关键。
正是各行各业的人在各自的位置上作出的贡献,使得全球的社会空间长成如今的规模,反过来,人们在各自位置上对专业的推进也得益于这个生长的空间给予的营养。
格拉德威尔、安德森和舍基都是在他们所在领域进行长期研究的人。他们在发表上述作品的时候都是至少将近40岁的中年人,之前的预备期可能从小时候——甚至是父母那一代——就开始了。
一万小时深处的新生命
出生在英国的格拉德威尔也许是这三位中最常被世界舆论说起的,然而,人们可能大多停留在谈论他的书,至于他的成长故事似乎却还没有多少人在意。
格拉德威尔的父亲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数学教授,母亲是在牙买加出生的研究婚姻和家庭的精神治疗专家。因为父亲的喜好,他们把家安在乡下,家里没有电视,却养了几只羊。夫妻俩都是长老会的成员,几乎每个晚上都教格拉德威尔和他的两个哥哥读《圣经》以及各种文学作品,比如狄更斯的《双城记》。
母亲在格拉德威尔6岁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叫做《褐脸庞,大主人》的书,讲述了自己作为褐色人种的牙买加人如何面对种族、社会、婚姻以及信仰这些复杂而痛苦的问题,“大主人”是她小时候对上帝的称呼。
格拉德威尔长大后回忆说,是母亲以及这本书成为他从小立志写作的榜样。他在16岁时因一篇采访上帝的文章而获奖。在乡村长大,也让他爱好运动,他在中学是出色的中长跑选手。
21岁的格拉德威尔在1984年从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的历史学专业毕业,大学时,跟当时很多追随社会主义的同学不同,他的宿舍墙上张贴的是里根的海报。
然而,他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多年后他更像一个自由派。而从新闻专业的角度,后来在《美国观察家》、《华盛顿邮报》和《纽约客》的同事都认为他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记者。他的不同寻常之处是不太按照周围现有的风气写报道,而是常常从他自己多年形成的观察点包括自然科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解读人和社会。
从2000年出版的《引爆点:小东西如何产生大影响》、2005年《眨眼之间:不假思考的思考力》到2008年的《出类拔萃之辈:成功的故事》,格拉德威尔表现出的倾向显然的确不是一位记者,更像一位科普兼励志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人们通常是经验多但理论少。我的角色一直是给人提供将经验组织起来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格拉德威尔这样非常规意义的记者却很可能是信息时代最亟需的传媒人才之一(如“信息Information”这个词的本义所指的:形成主意)。
因为在信息社会进一步深入更多人生活的年代,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在内的传统新闻媒体正在遭遇空前的危机,每个人都可能通过网络做起记者的工作,格拉德威尔式的记者却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到的。
在《出类拔萃之辈》中,格拉德威尔反复重申的一个因素是所谓“一万小时规则”,他认为任何领域中成功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在于,你是否在你所在的一项专门工作中有至少一万小时的付出。
这样的总结总是免不了过于简单化的嫌疑。然而,通用的道理常常不是耸人听闻的,真正可能耸人听闻的是竟然有人真的这么去做。对于格拉德威尔,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不是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而是他自己真的这么去做了。
他认为在《华盛顿邮报》关注科学、商业和纽约的九年是他的一万小时付出,而在这之后,他认为自己在1996年加入《纽约客》杂志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飞跃,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那一年6月3号的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引爆点”的文章,更是由于这本杂志给予他宽广的创作自由,格拉德威尔自己称之为,“一旦你到了《纽约客》,各扇门就打开了。”
因此,除了个人自己的长期付出,格拉德威尔最为重视的有益于人生发展的因素是要有好的社会传统。就像他自己的经历显示的,他从小在科学、信仰和文学上受到的熏陶给他在成人后看待社会增加了丰富的维度,好奇心和专心研究的能力不是新闻专业本身就足以提供的。
好的社会传统也不是单个人可以形成的,格拉德威尔的故事不过是千百年来无数个人成长史中的一个,但因为跟他的同行安德森——《连线》杂志的主编还有与他同在纽约的舍基——纽约大学教授——都在近来的十年间增进了对信息社会的理解,他们的经历的确值得一切关注如何在当今世界生活的人加以注意。
在他们看来,至少这世界是个有章可循的世界,如果你委身于你的专业越深入持久,这个世界的秩序通过你的委身所呈现出来的就很可能越清晰,也就越有利于人们了解世界的真相,并且可能帮助别人委身于他自己的位置。
再进一步说,通过他们还有构建信息社会各环节的人所做的工作,信息时代给人的印象不再仅仅是茫然一片不知所云,是既有广度又有纵深的立体图景,飘散在空中的信息总是能够在具体的位置汇集起来,在时空的深处产生让人惊喜的新生命。
这就像格拉德威尔的母亲从牙买加的教会学校来到遥远的英国,遇上未来的丈夫,他们又移民加拿大,孕育出这位不合常规的未来记者,而美国的媒体预备着这位多伦多大学毕业生的到来,所有这一切的合力通过这个人的长期钻研深化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总之,这是一个极富秩序和意义的宇宙,了解它真相的有效方式不是随着无数的信息飘来飘去,而是将所有可能相关的信息集中于一点,深入下去,在信息时代,可能在任何时代,每个人的生命是这样扎根成长的。
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信息时代的形成离不开互联网在世界的延伸。今年是英国物理学者提摩太•约翰•伯纳斯-李(Timothy John Berners-Lee)——一个至今都并非家喻户晓的名字——发明万维网20周年。
在1989年那个全球的多事之秋,互联网是如何悄悄诞生的,在那个微不足道的点中怎样长出如此影响人类的生命来,那是下一篇要学习的。
《The New Yorker》读后感(七):Mastering the Machine
Ray Dalio 是对冲基金BriedgeWater(下简称BW)的创始人,他是一个宏观投资人,这意味着他靠经济趋势,比如汇率,通胀和GDP增长率挣钱。为了寻找可获利的机会,BW基金在全世界买卖超过100种的金融工具——从日元债券到伦敦铜到巴西货币合约。
07年,Dalio预测房贷泡沫破裂。随后他通知布什政府全球很多银行在资不抵债的边缘。08年,很多对冲基金消亡,但BW基金扣去手续费之后,仍然有9.5%的收益率。
尽管Dalio很富裕,但是其实他和索罗斯很像,他们都喜欢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展现在世人面前。08年10月,金融危机爆发时,他写了一篇名为《一个理解当下在发生什么的框架》的论文,在文中他提到了整个经济不是简单的衰退而是一个“去杠杆化”的阶段——人们减少负债重新储蓄——这个冲击会持续一代人。这个观点并非Dalio所独有,但是经历三年的经济停滞之后,这个观点仍然没有过时。
不同于别的对冲基金管理人,整天盯着电脑屏幕,Dalio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思考怎么把经济和金融事件放入一个统一的框架里面。他说几乎所有事情都是机器,自然是一个机器,家庭是个机器,人生也是一个机器。他的终极目标是:理解经济机器是怎么运作的。包括这台机器如何面对金融危机,去杠杆化怎么进行,什么是人类的天性和怎么运作一个团体去挣钱。
Dalio认为他对市场的理解也能运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工作。BW基金有很多特别的规则,Dalio坚信这些规则并不像外人所认为的那样不可理喻。而恰恰是这些看起来特殊的规则,让BW基金在08年大部分对冲基金破产的时候,仍然活了下来,并且取得了盈利。
Dalio认为,认识错误,研究错误并从错误中学习是成功的关键。他写道:“痛苦+反思=进步”。BW基金把这个公式贯彻到很多方面,包括冗长的评估过程,在这些过程中雇员需要发现自己的错误。
Dalio会把和同事的会面用摄像机记录下来,并且公司的其他同事也可以观看。他说这保证了客观翔实,并让所有人知道公司正在发生什么,包括他和高级雇员的谈话。“他们可以通过视频看到我的所有错误,和我人性的所有方面”
W基金的客户主要是大型的机构投资人,大约1/3是社保基金,包括柯达和通用公司;大约1/4是国家主权基金,包括新加坡主权基金。相比其他对冲基金,BW基金更加透明,这吸引大额资金的流入。
Dalio对于风险的态度是:“控制风险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风险的可怕不在于风险的本身,而在于你有多了解风险。”“你需要知道悬崖在哪,并与它保持安全的距离。”
Dalio通过分散投资的方式规避风险:任何时候,BW基金都有30或者40个不同的头寸。“我经常想知道我认知正确的概率”Dalio说,“假如我不确定,我不希望有任何一个集中的交易。”这种观点在对冲基金行业已经被认为是过时的保守主义了,索罗斯在92年卖出了价值100亿美金的英镑。几年前,保尔森做空了美国的MBS,并挣了几十亿美金。
Dalio通过不同市场卖出或者买入不同的头寸,10年的头寸包括做多美国国债,日元和黄金,做空欧元和欧债。一个潜在的问题是,全球大部分资产价格是联动的。BW基金的方式是,做大量的比价交易。买入被低估资产的同时卖出被高估的资产。比如买铂金抛白银,或者买30年国债卖出10年国债。回报来自比价,而非整个市场。对此Dalio的评价是:“我们同时做对和做空国债,我们的阿尔法收益不来自任何一个资产或者市场,并且这种方式在任何环境下都适用。”
他的同事Bob评价Dalio是个:同时具有全局思考和市井智慧的交易员。很多经济学家通过从上到下的方式思考问题,他们观测宏观数据——通胀率、失业率、货币供给——并以此推断这些数据对于特定行业,比如汽车、科技行业的影响。Dalio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在任何一个他感兴趣的市场里面,确定谁是买主,谁是卖家。估计他们最有可能的需求和供给,并且找出他所发现的需求供给数据是否已经反映在价格里面。如果没有,那就有钱可赚了。在美国国债交易市场,BW基金仔细观察每周的拍卖,谁在买——美国银行、外国央行、共同基金、养老基金还是对冲基金——和谁没买。对于商品市场,BW基金也做同样的功课,他们确定有多少需求来自于企业,有多少来自于投机资金。“这所有事情都可以归结为谁将要买和谁将要卖,以什么原因。”Dalio解释道。
为了指引投资,BW基金有几百条“交易指引”。这些指引是Dalio信条的金融版本。早期,Dalio把某些信条写在一个活页本里面,现在BW基金把他们编入了计算机。其中的一些指标比较具有普遍性。其中一条说,某个国家经过通胀调整的利率下降的话,它的货币将贬值。某些具有特定性,比如一条说,从长期来看,黄金的价格等于流通货币除以黄金储量。如果市场价格偏离这个基准,那么存在买卖的机会。
在任何一个市场,BW基金都有超过一打的指标。尽管如此,即使有时绝大部分或者所有指标都指向一个方向,Dalio也不会完全依赖软件。除非他和Jensen,Prince认定这个交易合理,否则公司并不会做这个头寸。尽管认为因素加入到了投资流程中,Dalio仍然坚称BW基金的投资流程是“制度化”的。“当我思考‘今天在发生什么?’的时候,我同样需要把这个问题和‘如何把这个事件结合到我们的投资框架中?’结合起来。”Dalio说。最终,这样的流程保证了BW基金系统化分析和系统化投资,并有别于其他对冲基金。“我听了太多描述今天在发生什么的论调,但不结合历史背景和经济机器如何运转这个框架。
由于视整个经济为一个整体,Dalio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创造信用这个方面有特别的关注,他认为信用对整体消费的影响巨大。这尽管看起来像常识,但实际上大部分经济学家只关注实际的货币——纸币、银行存款——这些由央行确定的东西,而忽略信用的影响。
Dalio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有多少BW的成功来自于BW公司的组织结构,或者所谓“完全透明”的企业文化?又有多少来自于创始人Dalio的个人投资能力?虽然BW基金投资上百个市场的不同产品,但是通常认为绝大部分的利润来自于Dalio精通的两个领域:债券和外汇市场。不像其他的对冲基金,BW很少在美国股票市场挣到很多钱,因为Dalio在这个领域不算是专家。“BW基金其实就是Dalio”,一个公司的前雇员这么跟我说。“那些关键的决策——导致公司挣大钱的决策——都是Dalio做出的。绝大部分关键的事情都是Dalio在Greg和Bob的帮助下做出的,这个公司用40个或者50个人来运转和目前的1000人差不了多少。”
Dalio本人反对这种观点。他坚持自己仅仅是一个大团队中的一员,Greg和Bob则是作为联合首席投资官而存在。他把前雇员的评论比作对前任配偶的闲言碎语。Dalio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精神导师,就像新加坡的李光耀一样,他虽然90年就退休了,但现在还保持着影响力。
Dalio看起来很消瘦,甚至略显病态,但是他坚称自己状态很好,消瘦是因为“减肥”。他说自己也没有计划退出BW的投资项目,虽然日常的管理工作已经交给了其他高级雇员接手。目前已有的两个基金规模已经太大以至于不再接受新的投资者,但是第三个基金“主要市场阿尔法”已经开始筹备运行。
去年,Dalio出售了自己20%的股份给公司的雇员,并且他说自己最终将卖掉自己所有的股份。但是不像某些对冲基金管理人,Dalio并没有让公司上市的打算,他说“我并不想让公司上市,或者被公司以外的人控制,那样只会把公司搞糟。”
Dalio减持钱不是他的首要目的。他生活的很好,但是从来不奢侈性消费。他和妻子结婚35年,拥有两套房产,一套在康州的格林威治,另一套用来度假。除了狩猎和探索未知地之外,他最大的爱好是音乐。最近他加入了由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设立的慈善基金,并宣誓捐出自己50%的财产。在一封他和他妻子的公开信中提到,“我们认为,除了保证自己基本需求的金钱之外——有质量的人际关系,健康,刺激思想等等——拥有更多的钱,尽管很好,但不那么重要。”
Dalio认为所有社会系统都遵守自然法则,所有个人参与者从与这些法则的和谐互动中得到奖赏或者遭到惩罚。而金融系统也是一种社会系统,奖赏和惩罚的法则是类似的。“那你必须做的精确,不然你就要遭到惩罚。阿尔法是零和博弈,你要得到比市场更多的钱,就必须从别人那边拿。”
今年春天(11年),Dalio告诉我说,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开始放缓了。这部分是由一些经济的经济政策导致的,比如奥巴马团队的刺激政策到了尾声,一些国家的负债率持续上升,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必须出台控制通胀的政策。现在看来经济放缓已经来临了,Dalio对自己的同事说:“我们仍然处于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并很有可能持续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Dalio认为那些高负债的国家,包括美国,最终会选择印钞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债务,这将导致货币和债券市场的崩塌。“没有一个国家历史上不是通过印钞贬值货币的方式来结束危机的。”他说,“一些国家,比如欧元区,没有选择印钞的余地,那么他们注定进入萧条。”对于欧元区想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努力,Dalio认为“人们往往只关注一件特定的事情,但是忽略了背后更为强大的力量,这就是导致我们债务危机的原因。”
Dalio的分析听起来非常合乎情理,但作为一个全球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分析整个经济走势才是整个游戏的第一步。至少同样重要的还有时间。我问Dalio这一切什么时候会一起来。“我想是2012或者2013上半年会是另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他回答道。
——纽约客2011年7月25日文章摘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