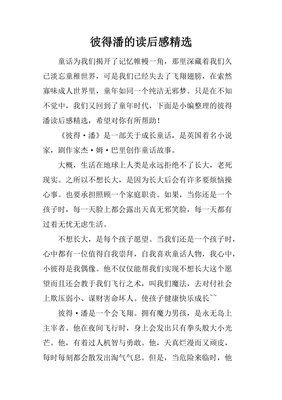社会如何记忆读后感精选
《社会如何记忆》是一本由保罗·康纳顿 / Paul Connerton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50元,页数:1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社会如何记忆》精选点评:
●: C912/0225
●翻譯實在太差
●以后当找英文本一读。
●虽然是小册子,但读的慢。仪式,身体,建构社会记忆。
●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
●从精神分析、社会学和历史学来结构社会记忆,强调体化实践对于人的认知决策的重要性,从而在社会对身体的构成(constitution)之外强调社会实践队身体的建构(construction),而这建构是流动的,灵活的,又是与传承细密链接的,从而反驳了以列维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而其中对于空间如何塑造记忆的描写,可以和德赛托以及列斐伏尔对比阅读了。
●不易读,翻译看得人内心崩溃
●社会记忆远比书中解释的复杂。
●还真要附注,那不添加了
●incorporating & inscribing
《社会如何记忆》读后感(一):。
社会记忆紧密地与身体联系在一起,所以作者没有着眼于各种口述史的社会记忆传承(即使它们是社会记忆传承的一种基本方式),而是重视仪式性操练对于身体的影响,从而说明社会记忆在此中的传承。他在首章就转向了记忆本身作为一种生理事实的研究。仪式的行为好比一种语言(个中的符号蕴含了不少意义),同时作为行为它也与身体相关,故而重演性仪式语言带来了某种牢固的身体社会记忆——操演(仪式)的记忆。“仪式操演”一词无疑是群体成员之共同身体记忆如何被社会造就这一过程的一个切中肯綮而且具有一般性意义的描述(作者把语文传承作为“刻写实践”纳入这种身体史的研究范畴未免穿凿)。回到前面,仪式保留了种种符号,它们背后的意义通过体化仪式而被身体理解,即使这个理解程度着实有限(要知道体化实践的记忆系统不会像文字、口述那样“刻意”地去记忆什么东西),它的作用仍不可忽视。仪式行为作为一个意向行为,对其意义的诠释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该行为质料的史料价值——发掘仪式传承的回忆的内容。
《社会如何记忆》读后感(二):操演:习惯-记忆
一、社会记忆:纪念仪式;身体习惯。
记忆申述:个人记忆申述;认知记忆申述;在现某种操演的能力(“习惯-记忆”)。前两种已被详尽研究,第三种被忽视。本书关注于第三种研究,即“习惯-记忆”。
二、纪念仪式。在操演中延续。
仪式:表达性、形式化、效用不限于仪式场合、重复性。
对纪念仪式塑造社群记忆的怀疑主义形式:精神分析立场(符号表象)、社会学立场(编码准文本表象)、历史立场(再现)——皆将仪式解释成一种符号表象形式。
难点:关注仪式内容而非形式;忽视重演倾向。(重演性仪式语言:日历的,口头的,手势的)
三、身体实践:体化实践(姿势),刻写实践(字母系统)。
习惯:技能,癖性,符号。
刻写-文本:享有被解释特权的对象,因为解释活动本身成为反思对象。文献的真实性。
身体:社会、政治意义载体,被关注。
强调操演,尤其是习惯操演对表达和保持记忆的重要性。
《社会如何记忆》读后感(三):20世纪80年代集体记忆研究代表作之一——《社会如何记忆》书评
“集体记忆”最早是由社会学家胡果在1902年提出,他认为 集体记忆是一种控制性的力量,也是不断积累而来的东西。 可惜他并未对此进行详细的阐述和研究,集体记忆研究伴随时间的流逝,被搁浅,甚至是遗忘。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1(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在其师——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理论基础上,于1925年出版了《记忆的社会框架》一书,其中他第一次开创性地、明确地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从此名声鹤起。哈布瓦赫打开了“集体记忆”深入研究的格局,虽然其诸多贡献不可遗忘,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哈布瓦赫理论中的忽略点,也慢慢地被后来学者加以重构。
保罗.康纳顿(Paulo C0imerton,1989,2000),他认为,哈布瓦赫在研究集体记忆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社会如果具有记忆,那么它又是如何保存和传承记忆的昵?他以研究社会如何记忆为主题,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集体记忆的实践性层面。他以三个篇章:社会记忆、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来详细阐释社会作为一个记忆单位,是如何去选择和传承记忆的。其中,康纳顿对于仪式、习惯、风俗、身体实践等重要记忆形式的解读分析,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P40 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P50 所有的仪式是重复性的,而重复性必然意味着延续过去。但是,有一类独特的仪式,它们具有一特明显的返现和时序的性质。国家社会主义节日,就属于这一类。 P69 与日常言语相比较,仪式语言的特色不仅变现在标准排比之上,业保险在有限的词汇、排出一些句法形式之上,表现在言语行为序列的固定性、发声的固定音量模式之上,表现在音调变化的有限性之上。所有这些特征促使仪式言语行为朝同一个方向发展。P73 周期性庆典并非传统社会的专利。但是,周期性庆典是一种补偿手段。它们的意图是安定人心,它们的情调是怀旧。……哈布瓦赫把集体记忆解读为一种当下社会建构,而康纳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读为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传承的实践活动。他认为:应当把社会记忆与称之为历史重构的活动区分开来,并明确划分出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记忆研究范围。认知记忆和个体记忆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集体记忆则是关于身体习惯、纪念仪式等的记忆,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康纳顿与强调集体记忆服务当下社会功能不同,他更重视研究社会如何选择集体记忆的材料,强调群体如何记忆,即保持集体记忆传承活动的重要功能,比如操练、仪式、习俗、节日传统以及习惯等实践活动的展开和延续。这些都为后来的很多研究,特别是重视对一些纪念性仪式进行分析等,奠定了基础。
总而言之, 康纳顿一方面赞同哈布瓦赫的基本观点,即认为存在着可以成为市集体记忆或者社会记忆的东西,同时又开拓了一种关于集体记忆的新思路,即便记忆是当下的建构,但其记忆本质还存在着过去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记忆本质内容和精神的维护及传递是社会传承记忆的重要功能体现。
《社会如何记忆》读后感(四):(导论)读书笔记
集体记忆或者社会记忆,在哪里显得最举足轻重且可供操作?
本书涉及的问题: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
【群体一词用于广义,既包括小的面对面社会(如村寨和俱乐部),也包括广有领土的社会,其多数成员并不能彼此亲知(如民族国家和世界宗教)。】
问题: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会导致对社会记忆作为政治权力的一个方面,或者作为社会记忆中无意识因素的一个方面加以关注,或者兼而有之。
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当今社会,借助信息处理机来组织集体记忆,不仅仅是个技术问题,而是直接影响到合法性,是控制和拥有信息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此外,我们不再相信那些历史“主体”——政党、西方——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些宏大支配话语的消失,而是意味着它们作为我们当今形势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无意识中仍然起作用,即它们作为无意识的集体记忆,存而不去。
本书关注点:一关注记忆本身,二关注社会记忆。
记忆本身: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相应于我们能够追溯的不同的过去,我们对现在有不同的体验,于是从今我推演故我就有困难:这既是因为现在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歪曲)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也因为过去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或者歪曲我们对现在的体验。这个过程触及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延伸到民俗学部分,民间故事特别是人物传说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故事,民俗活动中带有地方特色的部分,如静安村颁金节等人工创立的节日。
Eg:我们描述成“看见我们认识的某个熟人”,这般看似如此简单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心智过程;因为我们在这类谋面者的形貌上,倾注了事先形成的所有关于他们的概念,在我们头脑中形成的关于这些谋面者的图像中,这些概念占有首要位置。我们每次见到这张脸或者听到这个声音,都会辨出这些概念,听出这些概念。
社会记忆本身: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可以说,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
问题: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
答案涉及把回忆和身体这两样东西,以我们不曾想过要做的那样放在一起。Eg:法国大革命。
不曾想要做的原因是因为在回忆被当成文化活动而非个人活动的时候,它容易被看成是对一个文化传统的回忆;反过来,这种传统也容易被想成是某种刻写的东西。
社会记忆
记忆如何作用于两个特殊社会活动领域的方式:纪念仪式和身体习惯
废除一种制度的仪式,只有通过反过来回忆另一些迄今为止确认那个制度的仪式才有意义。
革命时期,服装也有改变,这是从既定制度旧规中得到的暂时解放。穿戴举止是社会阶层的准确象征。
历史重构不依赖社会记忆,但是对于社会记忆,历史重构是必须的。
《社会如何记忆》读后感(五):愿你能拥有美好的社会记忆
有人说,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被遗忘。可见,好群居的智人们,总喜欢在他人的记忆当中留下点什么,以此来证明自身某个方面的价值,反过来说,一个人的记忆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感知周遭事物的程度。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库利也用“镜中我”来比喻人们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来形成自我认知;这些林林种种的社会实践,使得一个“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而其中,个人记忆的作用至关重要。
保罗·康纳顿在书中提到,当我们回溯,或由于我们一整天和他人发生的直接或间接关系而唤起记忆时,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求助自己的记忆,来回答别人提出或想象他们提出的问题;为了回答问题,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同属于对方群体的成员。由此可见,群体给个人提供了他们在其中【定位记忆的框架】,而各自有【不同过去】的【不同社会部分】,将拥有【不同的记忆】,这些不同记忆附着在当事群体所特有的【心理界标】之上。可以说,个人如何保存和重现记忆,与社会如何保存和重现记忆,关系密切。
要想了解社会记忆,可先以法国革命历史为例,或者直接回忆自身所在的社会历史。书中以路易十六的审判和处决、巴黎改革时期的服装样式,论证了任何一段社会记忆的开始,都不可避免地【回溯】了其特有的社会记忆模式。但除了去剖析各种含有【回忆】因素的【开头】,社会记忆的构建也涉及到,持有不同立场的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重构,以及更加非正式的程序和更广泛的文化分布——非正式的口述史中。可见,我们对于历史的学习和传统的传承,或多或少都在构建属于我们的社会记忆。
可以说,社会记忆既不是个人记忆的简单相加,也不是有机组合,作者通过对记忆申述和构建行为的论述,指出社会记忆这种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而这种操演有两种类型: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纪念仪式】通过限定性的仪式语言和周期性的重复性操演,使得社会群体可以有效地形成相应的社会记忆,而由于纪念仪式本身的明喻或隐喻,人们在纪念仪式中被记忆的,是【个人和认知记忆的集体式变体以外的东西】。
而【身体实践】中的体化实践,通过它们的【存在方式】和它们的【获得方式】,获得了特别的记忆效果:它们不会独立于它们的操演而“客观地”存在。获得它们的方式不需要明确反省它们的操演。这两点也是【纪念仪式】的特征,因此,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保险性,【避免在所有话语实践里必然存在的积累性质疑过程】。这是它们作为记忆系统的重要性和持续性的源泉。
我们曾在国庆阅兵式中狂欢过、也曾在降旗哀悼日中悲恸过;我们有属于自己日复一日的生活记忆、有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规矩、也有准备传授给后人的习惯记忆......大多时候,我们身处社会记忆的构建而不自知,但笔者相信,更多时候的我们可以“扬弃”我们所逐渐获得的社会记忆。世上最可怕也许不是死亡,也不是被遗忘,而是无法记忆。
愿你能拥有美好的社会记忆。 http://t.cn/A6AXQ87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