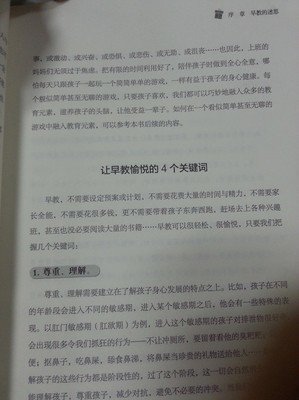《职场妈妈生存报告》读后感1000字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是一本由(美)凯特琳·柯林斯 (Caitlyn Collins)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4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读后感(一):中国妈妈,每况愈下中持续昂扬
这本书的排版真是让我越读越丧,一开始的瑞典妈妈是我们无法企及的一种存在,到最后焦虑之中度过的美国妈妈,却能引起共鸣,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小结的那一章,我彻底无奈了,从表7.1 妈妈们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感受来打勾,冲突最大的意大利妈妈和美国妈妈8项中有7项都存在,仅有“是否因追求事业而受指责”空白,然而这一项,我相信中国妈妈们都会勾选吧,我真是怒气冲冲的觉得,我为什么要看这本书啊,为了让我自己生气自己出生地错了吗?我自己都能冷笑一下。
这本书还有一个地方让人无奈,书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生育减税的待遇,嗯,目前我们的报税系统貌似也有这种设置,当然我觉得我们普通收入者减少的税率可能微乎其微,但是一个号召就让多少家庭开放了二胎,甚至于许多40多岁的高龄产妇趋之若鹜,我只能说,我们好乖。
作为一个普通职场妈妈,我只能跟意大利妈妈一样求助于我自己的父母来带孩子,不对,意大利妈妈们都是祖母(婆婆)带孩子。然后就没有其他了。办公室的妈妈们经常扪心自问,怎么做一个不那么累的妈妈?我觉得不可能,除非你变成爸爸。我甚至不知道所谓的“男女对立”究竟是谁的原因。我时常怨怼我最爱的枕边人,因为育儿投入的精力巨大差异和社会对“妈妈”这个词赋予的理所当然的期望,一步一步的淹没了你。
我经常想,孩子的未来就是这个国家的未来,而孩子的“早教”水平大都停留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老年妇女身上,尤其是这其中经济条件较好的外婆或者奶奶会出钱让妈妈们请一个农村或者县城的阿姨来带,那么我可以明确的说这一代孩子的水平基本上就是那一代低收入老年妇女的水平,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而我们焦虑吗?怎么不焦虑,焦虑弥漫的到处都是。很欣赏意大利妈妈们说的“先选择人,再生小孩”,也同意美国妈妈们的“如果你没钱,你就没资格要小孩”,可是,生育权究竟是谁做主,“看不见的未来”在主宰。
前两天听说,呼吁立法取消彩礼这个项目,我想说,女性物化自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深陷泥淖,如果你的婚姻失败了,你就是一个沉没的单亲妈妈,贫病交加。如果这个社会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还需要去依靠那房产证上的名字和少的可怜的彩礼吗?在社会保障条例几乎没有的情况下,难道仅靠基因的传承就能确保未来吗?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读后感(二):“我只是生了孩子,为什么整个社会都要惩罚我?”职场妈妈困境背后到底是什么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施晨露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引发热议
“我只是生了孩子,为什么整个社会都要惩罚我?”面对这篇爆款公号文的标题,不少女性感到“扎心”。
工作还是带娃?全职太太还是职场妈妈?成为母亲之后,选择坚守职场要面对什么?如何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关系?这样的“女性困境”话题频频引起热议。
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孩子,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职场妈妈们还需要轮“第二班岗”。几大招聘平台最近两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职场女性平均贡献了近四成家庭收入,65%的职场妈妈认为自己有潜在抑郁倾向,超八成的妈妈对孩子感到愧疚,九成人认为生育阻碍了自己的职业发展。社会学家玛丽·布莱尔-洛伊提出,职场妈妈面临“竞争的奉献”:花了太长时间照顾家人的职业女性会被认为亵渎了工作奉献图式,避开家庭责任或将家庭责任委托给他人的女性则被认为违背了家庭奉献图式。
职场妈妈面对的仅仅是工作与家庭的拉扯吗?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和杨帆是一对年轻的新手父母。作为爸爸的杨帆说,家庭生活的平衡是个体层面的,即便个体再努力,没有好的政策环境,平衡依旧无法达到。因此,准确地说,不是家庭和工作的平衡,而是家庭和工作的公平。作为妈妈的沈洋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问题:即便是在对女性十分“慷慨”的家庭政策环境下,比如瑞典夫妻共享480天育儿假,且任意一方必须至少使用三个月,女性仍然有权利这样想——我不想把生活全部分配给工作及家庭。“不是工作与家庭的二元对立,女性不是生了孩子以后就不能拥有自己的时间了。”
引发沈洋与杨帆讨论的是近期由世纪文景推出的新书《职场妈妈生存报告》。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凯特琳·柯林斯选取了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非常不同的四个国家——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对135位职场女性进行访谈,调研她们想要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以缓解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从国家制度、市场配置、文化氛围等角度,试图勾画对职场妈妈更公平并能提供更充分支持的社会图景。
在凯特琳·柯林斯调查的四个国家中,瑞典以两性平等政策闻名。瑞典推行双职工/双照顾者模式,施行16个月性别中立的带薪育儿假,包括不用即作废的“爸爸月”,再加上健全的公立幼托体系,使得瑞典女性很少成为全职妈妈。“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瑞典其实也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沈洋认为,基于瑞典的经验来看,政策的确可以改变文化与观念,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能实现,男性因政策的推动,越来越多地参与育儿责任。
值得注意的还有德国的福利悖论现象。过去,德国女性可以得到三年育儿假,看似家庭友好型的育儿假政策却没有得到女性的支持。实际上,在三年育儿假期间,女性不仅承担了更多育儿和家务劳动,并且极大影响了事业追求。最近几年,德国将育儿假修改为一年,在这样的情况下,目前70%的德国妈妈从事兼职工作。“我国在制定育儿假政策时需要谨慎,需要有性别视角。”沈洋说。
在《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中,凯特琳·柯林斯也提出,单靠政策无法解决女性的问题。缓解她们的外在冲突与内在矛盾,需要对各国社会有关性别平等、就业和母职的文化观念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她调查所涉的四个国家中,女性都处于不切实际的“好妈妈”标准之下。
什么是“好妈妈”?在杨帆看来,社会对于“好妈妈”的想象往往是浮动的,更值得考虑的是孩子眼中的“好爸爸、好妈妈”。“孩子对什么是‘好爸爸、好妈妈’的标准,是在成长过程中互动构建的。如果单向地接受所谓社会一般标准,并且家庭努力迎合这个标准和期待,并不利于培养孩子圆满的人格。”
沈洋提到,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即便是在将育儿责任更多地交给育儿嫂、住家保姆的家庭中,女性一般也承担了更多的育儿认知劳动。“比如,奶粉几十种、上百种品牌怎么选?‘双十一’刚过,你给孩子挑东西、买东西花了几个小时,娃爹却觉得你只是在玩手机?所以,在育儿环境比较和谐的家庭中,男女双方都要对彼此的职业内容有更多了解,并且认可对方付出的认知劳动价值。”
杨帆提出了另一个概念——认知过劳。“一些家庭研究文献关注到男女在育儿中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形式,即女性大量进行育儿劳动,尤其是以规划、筹备、采买决策等为代表的认知劳动。需要反思和提防的是,‘育儿认知劳动’是否正滑向‘育儿认知过劳’?对育儿要投入的认知劳动的度到底在哪儿?实际上,这种过劳是现在很多家庭,不只是妈妈,也是爸爸的压力所在。”
在杨帆看来,零工经济、线上经济的发展,让自由职业者增多,给了女性更多就业机会,同时也给了男性参与家庭和育儿实践的更多机会,“这是当下时代的一个机遇。”时代在进步,女性要真正走出困境,还要激发男性的觉醒,从个体家庭到公共社会,是时候重新分配育儿责任了。达成工作与家庭平衡的目标,不应是女性需要独自承担并解决的困境。大到国家政策,社会对于女性、男性、家庭及职业的主流看法,小到工作构架,与伴侣、朋友、亲戚、孩子乃至同事们打交道的细枝末节,女性需要的是更公平的对待,而非教她们如何去平衡。
栏目主编:施晨露文字编辑:施晨露图片来源:出版方提供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职场妈妈生存报告》读后感(三):他乡的妈妈
2019年,周轶君的《他乡的童年》引发了全网热议,让中国家长在养育鸡娃的疯狂中,看到了外部世界多元化的育儿观和育儿方式。
那么,他乡的职场妈妈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她们能同时兼顾好员工、好妈妈这两个角色吗?政府、社会、家庭和公司,给了她们什么样的支持?或者,你有深究过:育儿只是妈妈的天职吗?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里采访了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四个不同国家的135个中产阶级妈妈,在4种迥异的家庭福利政策模式下,职场妈妈们获得的支持不同,境遇也不同。
如果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那么他乡的政策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另外一种可供参考的范式,给我们一种可供预期和努力的目标。
全球的职场妈妈还好吗?2021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拼多多23岁女员工加班后猝死”的新闻刷爆网络,又引发了一轮对996的热议和讨伐。
更讽刺的是,一边是员工猝死,一边是拼多多股价暴涨,虽然这两则消息没有因果关系,但是不得感叹:我们并没有选择。
“过劳”已是打工人的生活底色,而且有大批量的人是“主动过劳”。这个时代的职场,既不欢迎35岁以上的人,也不欢迎想同时兼顾育儿的职场妈妈。
因为这些群体被普遍认为不能承受高强度的加班,而一些职场妈妈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必须表现得比其他员工更加努力,在大厂工作的同学说:她的同事剖腹产后一周就已经回公司上班了。
那么我们可以关注第一个问题,各国的职场妈妈有多少育儿假可休。
欧盟明确地将性别平等、女性就业、家庭支持视为所有成员国的发展目标,所以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以及德国等国家,都在制定对职场妈妈友好的政策,让职场妈妈们有充足的时间照顾、陪伴幼儿。
瑞典不仅有超长的育儿假,而且育儿假是性别中立的,爸爸和妈妈都可以休育儿假,政策鼓励夫妻双方平分假期,从政策和文化的角度来推动性别平等,从而让大家意识到育儿不仅仅是妈妈一个人的事。
最为友好的是,瑞典不限制16个月的育儿假一次性休完,在孩子8岁之前休完即可,有些家长会选择后几个月的假期,每个月休息3天。
当然,美国因为是联邦制国家,没有统一的法律政策规定育儿假,个别的州会有单独的育儿假政策,美国的职场妈妈只能把自己的带薪假期用来育儿。
除去休假制度外,职场妈妈是否能够获得来自家庭、社会的支持,分担育儿的压力,也决定了她们是否能够轻松地回到职场。下面是各国的调查结果:
从结果可以看到,瑞典和前民主德国地区的妈妈们,不仅能得到来自配偶的支持,还有完善的幼托体系可以依赖。
而在工作方式上,瑞典允许拥有8岁以下孩子的家长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将工作时间减少四分之一,还支持兼职、远程办公、弹性工作制等多种方式,德国的妈妈也有较多的兼职机会,而意大利和美国则完全不支持。
在客观的数据以外,每个妈妈的主观感受也更能直接说明情况。
瑞典妈妈是最有幸福感的一个群体,因为有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支持,她们则为是否能成为理想妈妈而焦虑。
工作和家庭能不能兼顾?很多成功女性都会被人问到一句:如何平衡家庭和生活?现在更多的职场女性都承认:这是无法平衡的。
企业期待一个把时间全部投入工作的理想员工,家庭期待一个尽心照料孩子的理想妈妈,大部分女性都有两个角色都未能扮演好的愧疚感。
她们需要面对的是愤怒的老板、没有同情心的同事,还有不允许她们使用现有政策福利的雇主。
有了孩子的女员工被想当然地认为不会尽全力工作。大部分人的女性都会在职场弱化自己身为“妈妈”的角色,在职场里对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绝口不提。
看到瑞典、德国等国家在育儿假、多种灵活的工作方式,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有这样的疑问:休这么久的假,老板和上司会不会为难我?我还能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吗?我会不会失去晋升的机会?
在作者的调查结果来看,仍然是瑞典的妈妈最能够放心地休假、也能继续开心地做自己的工作,因为瑞典推动的性别平等,爸爸和妈妈一样承担育儿的职责,所以职场里的爸爸们也同样会休育儿假,或者早下班去接孩子,包括管理人员和公司老板,所以,整个社会的文化也是在支持着政策的落地。
但是即使在瑞典,职场妈妈们也承认:在国企工作休假的容易程度要高于在私营企业。
作者在采访前联邦德国地区的职场妈妈时,意识到“文化与政策在我们或许无法预料到的地方互相作用着。”
德国虽然有着和瑞典相似的育儿政策,但是因为整个社会推崇的文化不同,所以德国的职场妈妈和瑞典的职场妈妈有着不同的境遇。
德国的妈妈虽然能够有较多的兼职工作机会,在男性并不被期待承担育儿责任的环境下,兼职工作意味着很多女性从此放弃自己的志业,并且文化期待她们能够回家照顾孩子,有了孩子还在追求事业的人被称为“乌鸦妈妈”,每一个想兼顾工作与育儿的妈妈都备受道德谴责。
尤其对于前联邦德国的职场妈妈而言,“男人挣钱养家、女人照顾家庭”仍然是文化主流,尤其是政策已经提供了良好的休假政策、有灵活的兼职方式工作,女性似乎更不应该再在工作上发力。
这里的职场妈妈不能向配偶或者父母公婆倾诉自己的压力,因为会被指责“那是你自找的”。责难不仅来自家庭,其他的妈妈们也会苛责她们是“事业狗”,尽管她们自己也很享受离开家庭去工作的时段。
职场妈妈为了避免自己被贴上“乌鸦妈妈”的标签,就会指责身边其他在她们看来更接近“乌鸦妈妈”形象的女性,比如工作时间很长的妈妈,以及对事业进步很有志向的妈妈。
许多女性本来拥有和配偶一样的学术追求和工作职位,可是为了照顾孩子,不得不暂时中断自己的工作,很多女性在孩子长大后,发现自己无法再回到职场而充满了怨气。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有偿劳动中甘于后退”以及“重新定义成功/降低期望”,是大多数职场妈妈应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方法。
意大利和美国的妈妈因为需要承担家庭的经济支出,所以不得不工作,但是即使是向自己的上司公布自己怀孕的消息,都让她们备受煎熬。
有人在公布自己怀孕的消息后,迅速地被上司强迫降职降薪,还有的被迫交出自己的客户资源,更有甚者经历了上司的暴怒“他把垃圾桶从办公室的一头踢到了另外一头。”
虽然工作-家庭冲突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瑞典的政策来看到一种改善的可能性。
“改变文化中母职和父职的定义;重新建立工作制度构架;所有的职场妈妈和她们的家庭都应该得到公共支持。”
作者指出:文化的转变总是落后于例如政策改革等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化。因此,可以想见,在一个抗拒变化、保守着传统文化态度的社会中,要施行先进的、推动性别平等的工作—家庭政策很可能会给妈妈们造成压力,就如同联邦德国女性经历的那样。
文化的滞后或许是无可避免的,就如埃里克·奥林·赖特主张的那样“我们想要一个乌托邦般完美的终点,即便那是无法抵达的地方,仍有一个个我们能够到达的中途站,指引我们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你是理想妈妈吗?各国的职场妈妈尽管因为文化和政策的不同而面临不同的压力,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焦虑:为了达成理想化的母职标准而倍感压力。
完美妈妈的定义是多样的,因为对好妈妈的期待是由妈妈们所在的文化环境以及可享受的工作—家庭政策决定的。
瑞典的妈妈们享受慷慨的政策和强大的支持体系,但是同样也面临完美母职的压力。在北欧国家,大家对于购买服务和物质有着天然的抵触:孩子的饼干应该是妈妈亲手烤的,家里的家具应该是爸爸亲手打造的。
但是有的妈妈更擅长在职场里发挥自己的才华,而不是囿于厨房昼夜与爱。
当德国的妈妈比其他家长更晚地接孩子时,面对周围人的责难,她也很希望“请让我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做事。”
意大利的妈妈抱怨政府,美国的妈妈只抱怨自己。所以美国的职场妈妈把“提高条理性/工作效率”也当做是自己应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方法,尽管她们本身已经累到了极限,但是时刻表上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将让她们的生活陷于崩溃。
有人说:职场妈妈是时间上的贫困户。太多的职场妈妈已经像陀螺一样旋转,但是仍然为自己不能长久地陪伴孩子而自责。
妈妈们究竟将什么时间留给自己呢?在某个时间段里,她们不是妈妈,不是女儿,不是伴侣,不是朋友,只做自己?简短的回答是,她们基本没有这种时间。
我们可不可以鼓励多元化的完美妈妈定义?职场妈妈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内心去选择,而不是迫于文化政策压力、迫于周围人的评论?
人们对于现有生活条件不满意的程度部分取决于他们是否认为还有其他可行选择的存在。
妈妈们对于“工作—家庭平衡”的渴望和期待以及她们对于工作—家庭冲突的解释和解决方式都受限于她们自身的生活世界,是由她们个人的经历与交际、组织和习俗构筑出的,女性能够为自己想象的就业与育儿的所有可能。
政策支持需要去满足妈妈们做出的多样选择。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应该有一个政治程序,在制定政策和实行政策的过程中让女性的声音得以被听见,让女性的意见得以被作为参考。妈妈们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定新政策的时候,她们的观点应该被获得充分了解和优先考虑(还有爸爸们的观点)。
最后,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可期待的社会: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和权利尽情参与到有偿劳动和家庭照顾之中。
愿天下的妈妈早日过上瑞典妈妈的生活!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读后感(四):【专访】社会学者凯特琳·柯林斯:孩子是一种公共品,养育孩子应是集体责任
“性别平等要求去除加诸在女性身上的枷锁,让她们从日复一日的、家庭中的、职场中的、日常生活中的有限选择中解脱出来。”
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在一档节目中的言论日前再度引爆中文互联网内对“全职太太”的争论。在部分网友认为当不当全职太太是个人选择、他人无权评判的同时,许多网友强烈反对女性选择当“全职太太”,认为退出社会公共生活不仅在个人层面风险重重,而且在社会层面削弱了女性的公共话语权,为男女平等事业带来负面影响。
然而纷争背后更少被讨论的另外一面是,女性如果选择坚守职场又要面对什么?她要如何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关系?职场女性恐怕立即就会发现,社会文化规范对女性的期待充满了自相矛盾,让职场女性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
以美国的情况为例。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发现,美国女性背负着“密集母职”的强大压力——所谓“密集母职”,指的是认为维持婚姻和成为母亲是女性首要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几十年来,这种理念使得女性相信她们的丈夫和子女迫切需要她们的照料,社会要求女性——尤其是白人中产女性——成为全职妈妈。另一方面,有事业心的美国女性又接受了“理想员工”意识形态的规训,被要求在情感上和时间上将工作放在第一位,由此获得独立、地位和满足感作为回报。吊诡的是,也正是这一意识形态让男性在职场中取得优势,与女性一步步拉开距离。
因此,问题的真正核心不是“当全职太太是不是个人自由”,而是为何女性难以在“全职太太”的选项之外拥有更多的选项?柯林斯指出,长久以来社会文化规范传递的性别化信息(女性在育儿、家庭、职场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处于怎样的位置)给妈妈们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境,这种冲突决定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和职场中对“好员工”的标准,导致“所有社会阶层的女性都将如何对自己的家庭最为有利作为工作抉择的前提”。
即便如此,依然有一些国家的女性能更轻松地做到家庭工作两不误,而另一些国家的女性则举步维艰,进退维谷。柯林斯花了五年时间在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采访了135位职场妈妈,探讨四种迥异的家庭福利政策模式对职场妈妈日常生活的不同影响。她最重要的发现是,政府政策需要和更强调平等分工、合作育儿的社会文化规范协同作用,才能真正帮助女性兼顾工作与照顾所爱的人。仅靠进步主义的政府政策(比如优渥漫长的产假)不仅不能帮助职场妈妈,反而会令她们陷入不利的位置,乃至被迫退出职场。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妈妈们身处的生活世界是被性别、做家长以及就业的不同规范框定的,”柯林斯在《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一书中写道,“我所遇到的最为满意的妈妈们能够获得工作-家庭政策在各个方面的支持,而且主流文化态度也鼓励妈妈们和爸爸们兼顾有偿劳动和育儿职责。而最不满意的妈妈们必须得依靠市场提供的服务来缓解自己的工作-家庭冲突,不受到自己伴侣的支持,且所在国的文化环境认为育儿就是女性的责任。”
在中国,人们争论“全职太太是不是女性的选择自由”;在瑞典,柯林斯发现一些妈妈抱怨女性必须成为职场妈妈、家长必须亲力亲为的文化规范。我们该如何理解性别平等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张力呢?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柯林斯给出的回答是:
“女权主义帮助女性(和男性)获得多种选择,来追求他们想要的生活,而不是所有人只能按照一种模板生活。性别平等要求去除加诸在女性身上的枷锁,让她们从日复一日的、家庭中的、职场中的、日常生活中的有限选择中解脱出来。”“这一代的女性集体喊出‘我受够了’肯定是个激动人心的转折点”
界面文化:你为什么选择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这四个国家做田野调查?
凯特琳·柯林斯:这四个国家代表了西方福利国家的四种经典模式:瑞典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德国是一个保守主义福利国家,意大利更偏家庭主义,而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它们代表了国家提供福利的四种经典路线。
界面文化:在进入田野之前你有怎样的预设?其中哪些预设被证明是错误的?
凯特琳·柯林斯:在五年的采访时间里,我对中产职场妈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体验政策的实际影响有了长足的了解,这和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往往是不一致的。在纸面上,一项政策也许看上去很诱人、很慷慨,但要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起作用,你需要通盘考虑。比如说瑞典有480天的带薪育儿假,把它搬到美国就不可能发挥完全同样效果,美国人对女性、男性、工作和家庭有非常不同的文化观念。我们需要考虑到文化和政策的交叉作用。
界面文化:在你的研究过程中,有什么最印象深刻或难忘的故事吗?
凯特琳·柯林斯:我采访了一位瑞典女人,我在书中称她为卡莎。她向我解释了日常生活方方面面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包括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的重要性,而这在斯德哥尔摩是很常见的。为了向我解释拥有一段平等的亲密关系、育儿过程中与伴侣平等分工的好处,卡莎给我讲了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她的女儿艾芭去朋友家过夜,做了一个噩梦,醒来后喊道:“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对卡莎来说,这意味着她和她的伴侣成功地与女儿建立了一种同样亲密的关系。我喜欢这个故事,它展示了平等如何融入亲密关系的肌理。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美] 凯特琳·柯林斯 著 汪洋 周长天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10界面文化:近年来出版的若干新书都讨论了文化规范和政府政策如何塑造职场妈妈和全职妈妈的生活经验,包括沙尼·奥加德(Shani Orgad)的《回归家庭》(Heading Home)、艾米·韦斯特维尔特(Amy Westervelt)的《忘记“拥有一切”》(Forget “Having It All”)和斯蒂芬妮·兰德(Stephanie Land)的《女佣的故事》(Maid)。我们是否走到了当代女权运动的某个转折点上?
凯特琳·柯林斯:我喜欢这些书和作者!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女权运动在美国乃至全球取得了数不清的成就,我认为现在的新关注点在于,有孩子的女性开始意识到,她们的生活不应该如此艰难,如此压力重重,如此孤独。她们意识到男性、雇主和政府需要在女性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中承担起责任,施以援手。这一代的女性集体喊出“我受够了!”,肯定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转折点。
“孩子是一种公共品,养育孩子应是一种集体责任”
界面文化:长久以来,瑞典及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被誉为性别平等的堡垒,你的研究告诉我们,进步政策、文化规范和叙事必须协同作用才能真正帮助到职场妈妈。当我们需要整个社会减轻女性负担的时候,哪一个部分应该先行呢?是政策(自上而下路线)还是文化(自下而上路线)?
凯特琳·柯林斯:这是一个经典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故事。我认为我们需要两者同时作用——既要有自上而下的策略,也要有自下而上的策略。事实上,这就是我在书中想要传达的。美国的城市、县、州都在出台进步的家庭政策,许多草根组织也在致力于推动性别、工作和育儿文化观念的转变。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瑞典政府从1970年代开始出台性别中立政策,支持育儿集体责任,这显著地改变了瑞典人对性别分工的态度。这一范式转向的背后动力是什么?瑞典人是不是刚好在一个对的时间做出了对的选择——当时恰逢战后经济繁荣期,整个欧洲都奉行社会民主主义?
凯特琳·柯林斯:这个转变得益于多年的女权组织活动,唤起了人们珍视并实际支持养育工作的意识。
界面文化:虽然一个国家的政策或许不能在社会和文化环境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国家奏效,不过我们能从瑞典经验中学到什么?
凯特琳·柯林斯:孩子是一种公共品。养育孩子也应该是一种集体责任。养育下一代既是女人的权利与责任,也是男人的权利与责任。我们不需要盲目迷恋工作——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东西。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一些瑞典妈妈抱怨女性必须成为职场妈妈、家长必须亲力亲为的文化规范有些时候令人感到窒息。在中国,有许多人在讨论“成为全职妈妈到底是不是女性的自由”。我们要如何理解性别平等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张力呢?
凯特琳·柯林斯:我在书中引用了亚历山德拉·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观点,“最终,女权主义事关女性选择自己期许的命运。”女权主义帮助女性(和男性)获得多种选择,来追求他们想要的生活,而不是所有人只能按照一种模板生活。性别平等要求去除加诸女性身上的枷锁,让她们从日复一日的、家庭中的、职场中的、日常生活中的有限选择中解脱出来。
界面文化:你是否计划继续你的职场妈妈跨国研究,比如说把发展中国家纳入讨论范围之内?
凯特琳·柯林斯:我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我希望其他学者能够再接再厉,将这一研究拓展到更广泛的地域和人群中。我很有兴趣研究单身妈妈、爸爸和低收入家庭。
“平等不是吃披萨,不是我多吃一点你就只能少吃一点”
界面文化:我的感觉是,性别平等的主要障碍是许多人(特别是男性)认为女性的获益一定会带来男性的损失。我们要如何克服这种心态?鉴于当代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构建在父权制的基础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承认旧制度难以运作下去了?
凯特琳·柯林斯: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我很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性别)平等不是吃披萨,不是说我多吃一点你就只能少吃一点了。集体解放意味着男性和女性都能从父权制和性别不公中解放出来。男性需要理解,性别不平等也在伤害他们。我认为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在她的作品中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
界面文化:在美国,生育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几乎没有任何政府支持,因此妈妈们将工作-生活冲突视作需要自我消化解决的个人问题。奥尔加用“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neoliberal feminism)这个词来形容女性是如何被鼓励拥抱自我赋权、自信、适应性和创业精神,但回避直接批判现存不公平的制度的。“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全球现象?
凯特琳·柯林斯: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认为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身具有全球影响力。这种对独立和个人主义的痴迷掩盖了如下事实:我们的生活其实是高度联结、彼此依赖的。除非我们理解女权和民权组织的典型局限、明白我们当中许多人享有的自由和优势是建立在压迫他人的前提上的,我们无法改变这个系统。
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白人女性,我的获益建立在针对有色人种的污名化、伤害、仇恨和暴力之上。这是不可接受的,我有责任去利用我的特权改变现实。我把小马丁·路德·金的一句话贴在了我的书桌上,时时提醒自己,在我工作的每一天都要反思自己的特权和偏见:“只有当所有人自由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
界面文化:根据盖茨基金会的数据,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这一危机也在放大性别不平等。一些早期数据显示,女性失业的概率是男性的两倍。鉴于在可见的未来经济依然充满不确定性,我们很难不对职场妈妈肩负的重担感到悲观。我们该如何应对挑战,继续推进性别平等议程?
凯特琳·柯林斯:新冠疫情给全球女性和母亲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它也向我们揭示了照料工作对于我们的社会和经济来说是多么必不可少。没有它,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运转。新冠疫情让我们的集体想象产生了裂缝。是时候狠狠撕开这些缝隙,带来所有家庭都迫切需要的改变了。
我认为我们当下拥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机会来动员人们为照料工作提供支持、呼吁我在书中提出的“工作-家庭公平”(work-family justice)、开创一个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能拥有机会和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全情参与带薪工作和家庭生活的世界。这是我为我们设立的目标。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