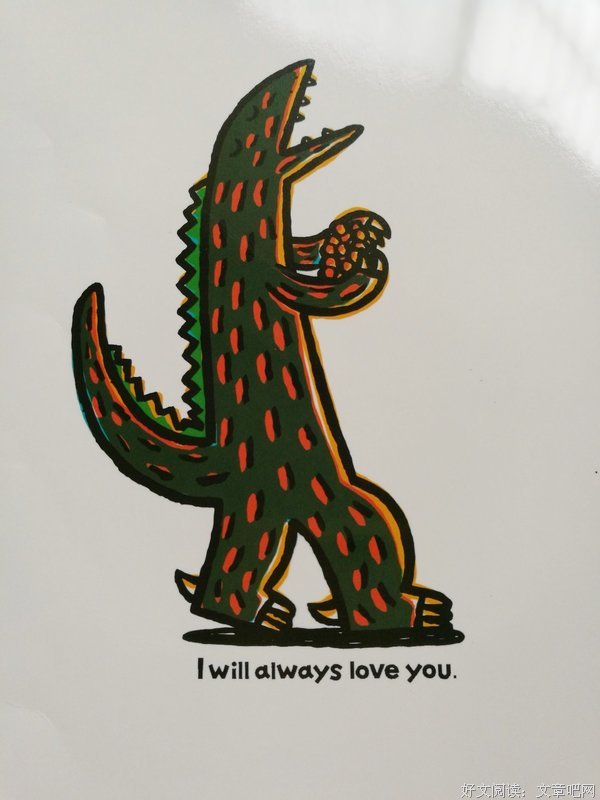好吃读后感100字
《好吃》是一本由(美)哈里斯著作,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60,页数:2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好吃》精选点评:
●Marvin Harris的书,看这一本就够了(除非你对他那套“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感兴趣)
●因为好吃才想吃:) ,饮食(经纪)人类学 *2
●不止于任意符号的解释;作为营养的食物,最佳(优)搜寻原则;经济策略;人口、生态、政治、饮食之“变化”;综合;前因后果
●从农业结构、文化偏好、社会阶层等主要方面科学的分析主要民族的饮食偏好之谜。
●学术性知识的重要意义之一即是祛魅,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其典型对象包括:传统和国家想像,巫术与巫医,神话与禁忌,等等。另外,人类学真是有趣极了。
●关键词:收支理论,反刍动物。写得很棒,分析全面观点也十分合理。(今天脑内不断浮现出大体老师的时候正好看到吃人那章结果整个没胃口了…
● 为什么不同地区的人,可吃、好吃以及禁食的动物食品如此不同?作者认为跟文化、宗教关系不大,主要原因是当地获取动物性食品的收益/付出比值,当然,本地是否适合驯养某种动物提供了比较的范围。看过戴梦德《枪炮病菌和钢铁》的,对此应该不会太诧异。
●仅仅是因为自然环境导致的饮食习惯差异吗?不见得,比如中国佛教因为梁武帝的原因普遍吃素,这和自然环境有什么关系?不过必须要说,作者在资料研究方面做得很用心。
●问题提了许多,解答却不让人满意。
●虽然充满了翻译学的想象力 但是作为人类学启蒙读物还是受益匪浅!(文化唯物主义什么的)超科学!这种感觉真是美好!虽然这个版本的插图什么真是呵呵呵
《好吃》读后感(一):说是食物与文化,其实主要就是讲肉的
本书主要涉及的是人类的动物性蛋白质饮食习惯。对吃牛肉、吃猪肉、吃马肉、吃人肉、吃猫、吃狗、吃虫子,还有为什么不吃肉等问题都有很有趣的展开。
至于小麦、土豆、辣椒、豆腐等,作者敬谢不敏啦。
所以素食者可以绕开走了。^_^
《好吃》读后感(二):马文哈里斯:一个群体选择论者
在《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中,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尝试解释诸如印度教崇拜牛、穆斯林讨厌猪这些广泛存在的饮食习惯/禁忌。这些话题以往常被当做无须解释的文化现象,而哈里斯从文化所处的地理、生态环境等处入手,以自然选择的观点,提出了许多极富洞见的看法,廓清了常见的文化神秘主义观点。但不幸的是,哈里斯是个彻底的群体选择论者,这使得他的许多观点的基础不够牢靠。
……
余下部分因为书评里不能贴图,请移步
http://www.douban.com/note/477725306/
《好吃》读后感(三):《Good to Eat: Riddles of Food and Culture》摘记
1、人们爱吃的食物比回避的食物更具性价比,营养、生态等方面成本收益平衡。
2、食谱差异主要源于生态限制。
3、动物性食物在人类种属的营养生理学上扮演着特殊作用。人类是沿着食肉动物的漫长过程进化出来的。动物性食物的实用性与稀缺性。
4、节约蛋白质饮食,如果不在吃肉的同时伴以碳水化合物,则肉食中的蛋白质会被当做热量吸收掉,不能完成其他的生理效应。
5、多数动物肉的问题是太瘦了。问题是,现代的碳水太精了。
6、印度瘤牛:能够在炎热、干旱条件下拉犁;不在草场和农田放牧,不与人争食;牛粪提供燃料;母牛生产公牛,提供牛奶;禁忌打消人们在干旱时节杀死绝产和病弱家畜的念头。
7、对于犹太人和穆斯林,猪肉生产效率低,而且猪没有其他用处,所以厌恶猪。对于马,马肉生产效率低,但有其他用途,所以和印度牛类似,禁食。羊肉生产效率低,在需要羊毛时普遍,但受到了其他纺织品的冲击。牛肉与猪肉,密西西比大草原更适合养牛,还有生活方式的原因。但牛肉正在受生产效率更高的鸡肉的挑战。
8、乳糖不耐受,牛奶中的钙需要和乳糖一起吸收,变成酸奶无助于钙吸收。没有养牛的环境,因此乳糖耐受基因没有优势,没有大规模复制。维生素D对钙吸收至关重要,或者通过光照,或者通过进食获取维生素D(深海鱼油)。乳糖能够替代维生素D。通过光照获取维生素D,通过进食深绿蔬菜和豆类获取钙;或者进食深海鱼油;或者进食牛奶。
9、昆虫作为蛋白质和脂肪来源生产效率太低。宠物也是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吃人肉是战争的副产品,尤其奴隶没什么用的情况下;极个别情况,在美洲阿兹特克,如辉格所言,是为了获取人肉和发动战争,也可以说人是当地唯一的大型动物。
《好吃》读后感(四):人类的饮食禁忌
在人类眼中,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摆在一条线的两侧,左边是“食物”,右边是“其他”。“其他”包括岩石、树叶、汽油、钢铁等,它们难以下咽,也无法消化。有趣的是,人类会千方百计地开发出能吃的土,反而主动放弃某些食物,避之唯恐不及。明明可以消化却坚决不吃,这就是人类的饮食禁忌。
在“食物”的一侧,人类的饮食又可以分为素食和肉食两种,一般人都不避讳吃素(除葱、蒜、香菜等少数几种),因此人类的饮食禁忌实际上就是肉食禁忌。素食和肉食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吃素是为了不死,吃肉则为了活得更好。但有人偏偏不吃某些肉类:印度人不吃牛肉,犹太人不吃猪肉,美国人不吃狗肉,大多数人都不吃昆虫、宠物和人肉……不吃昆虫和宠物是全球性的,不吃牛肉和猪肉却是地域性的,其中的差别长久地困扰人类。
饮食禁忌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因地域而不同?
传统观点认为,人类吃什么或不吃什么完全由文化决定:印度人不吃牛肉是因为崇拜牛的文化,犹太人不吃猪肉是因为憎恶猪的文化——饮食禁忌是历史的偶然,是任意的、随机的和不可解释的。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在《好吃:人类与文化之谜》一书中给出了超越“文化决定论”的解释,认为文化之外必然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营养、生态和收支平衡。总之,人类的饮食禁忌是可以解释的。
与宗教有关的饮食禁忌
印度教禁止吃牛肉,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禁止吃猪肉,两者都与宗教有关,但根本原因各不相似,产生的结果也互不相同。
印度人不吃牛,是出于内心的尊敬。印度的法律明文禁止宰杀和食用牛肉,尽管印度拥有3亿多头牛,位居世界第一。印度之所以存在牛肉禁忌,根本原因是禁食牛肉对印度人大有好处。印度人非常依赖农耕,而瘤牛是唯一一种能在高温、干旱的条件下拉犁的动物;它消耗的饲料很少,用来耕地的性价比甚至比拖拉机更高,而且粪肥可以提供燃料。牛可以产奶,是印度人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耕种收获的农产品用于培育其他动物,使印度人能够吃到更多肉食,而不是更少。牛在印度被尊崇为“圣牛”,就是因为它有用。
中东人不吃猪,则是出于内心的鄙夷,因此中东很少有家猪。《旧约》和《古兰经》都禁止吃猪肉,从字面上看,是因为中东人把猪视为不洁净的动物,但这不是禁食猪肉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猪和人类一样是杂食动物,并且也不能反刍,无法像牛羊一样以青草为食,因此人类必须拿出自己的部分口粮,转化成猪身上的肉,而且转化率只有35%。猪不能拉犁、不能产奶,猪毛不适合纺织,因此经济效益比不上牛羊。猪没有汗腺,只能躺在湿处(如水中或泥中)降温,这一方面污染了中东有限的水源,另一方面使猪变得很脏;中东温度较高,猪不易存活,因此养猪的代价很高。基于上述原因,猪在中东是无用甚至有害的,因此被厌弃和禁止。
值得一提的是,中东人也不吃骆驼,因为骆驼在中东的沙漠中十分有用,这与印度人不吃牛肉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没有上升到宗教的程度。
与宗教无关的禁忌
有很多饮食禁忌是与宗教无关的,比如昆虫和宠物。
从来没有规定说不许吃昆虫,但这仿佛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被世界上大部分人严格地遵守。吃昆虫的行为是有的,但大多数人只能望洋兴叹,有时出于好奇想尝一口,又因为恐惧而放弃;有些人甚至看到“蝗虫”、“蚂蚱”、“蚂蚁”这样的字眼就感到恶心。看上去这就是人们不吃昆虫的原因。
事实上,恶心并不是人们不吃昆虫的原因,而是结果;换句话说,正因为人们不吃昆虫,才觉得昆虫恶心。人们不吃昆虫,与印度人不吃牛肉、中东人不吃猪肉有着相似的经济原因——搜寻和捕捉昆虫耗费的时间较长,其表面的几丁质硬壳及体内可能携带的致癌物使昆虫处理起来很麻烦。为了避免因为食用昆虫付出太多精力,人类进化出“觉得昆虫很恶心”的生理惯性;人们一看到昆虫就倒胃,自然不会因此浪费时间,转而去寻找牛、羊之类更有价值的动物。
人们不吃昆虫,是因为昆虫没有价值,也就是“无用”。不仅无用,昆虫还会肆虐庄稼,因此和中东的猪一样有害。
现代人类也不吃宠物。几乎所有的宠物都在人类的食谱之中,马、狗、猪甚至蛇,人们都能大快朵颐。可一旦这些动物成为宠物,就拥有了不被端上餐桌的豁免权。原因很简单:宠物对人类而言有非常重要的情感价值,帮助人们克服孤独、焦虑和挫败,也不会使人变得无聊和冷漠。
童话《小王子》中,作者用“驯化”一词形容人与宠物的关系:驯化,就是建立某种联系。当人与宠物产生了非常紧密的情感联系,宠物就变得很有价值;只要还有其他的食物,人类就不会对自己的宠物下手。
吃人的禁忌
在所有的饮食禁忌中,吃人是最特殊的一种,因为吃人涉及到人类自身。吃人的问题很复杂,但吃人的禁忌解释起来却十分简单:对于人类这个群体而言,没有什么比人这种动物更“有用”了。从情感的角度来讲,人与人是同类,基因相似性达到99%;从安全的角度来讲,禁止同类相食可以确保社会群体的生活与秩序;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人口数量越多,分工合作越明确,生产效率就越高;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人口数量的壮大催生了现代国家的诞生,后者又通过立法保障公民不被食用。
即使是原始社会,人类也不会以同族或亲属为食,而主要是针对战俘和死尸。这两者的价值较低,为什么现在也不行呢?
战争吃人这种事情,随着现代国家的诞生而消失。这跟现代国家的文明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因为活的战俘比死的战俘价值更高。如果一个军队优待战俘,在行进途中遇到的阻力会减小;但如果杀死甚至吃掉战俘,敌人就会拼命顽抗,因此中国古人说“杀降不祥”。对于死尸,吃掉本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由于吃人是最严格的禁忌,为了避免打破禁忌的诱惑,就不能允许任何例外。
人类的吃人禁忌必须一分为二地看:人类不吃活人,是因为活人的价值很高,是有用的;人类不吃死人(战俘归在这一类),是因为死人的价值较低,是无用的。
最佳搜寻理论
非常有用的动物和非常无用的动物都会被排除在人类的食谱之外,有用的动物吃了浪费,无用的动物不必费力饲养和抓捕。“有用”和“无用”是相对而言的:猪肉在中东被厌弃,但在东亚和东南亚却十分受欢迎,因为猪肉比较廉价;宠物有非常重要的情感价值,但如果碰上饥荒,也可能成为人类的盘中餐。
马文·哈里斯用“最优化搜寻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人类会选择最高效的方式寻找最有效的食物,而拒绝那些代价过高、收益太小的食材。尽管人类可以消化的东西很多,但实际吃的很少;在食物充盈的情况下,人类只会选择更高效的食物来源。也就是说,如果牛羊充足,吃虫子的永远都是少数。
如果考虑宗教的因素,“最优化搜寻理论”同样成立。只是在这个时候,经济的或营养的判断并不重要,人们会更多地考虑到遵守宗教禁令带来的情感安慰,以及违背宗教禁令招致的惩罚。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人不吃牛肉、中东人不吃猪肉其实也是在追求当下环境中更好的饮食。
人类的饮食禁忌并不会降低人类整体的饮食质量,而是为了“吃得更好”,追求更高的效率。人类放弃了经济效益低的食物,而朝着更多样、更方便、更美味、更营养的方向发展。然而集体的最优化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的最优化,宗教的强制性会破坏人类自由选择的权利,因而抵消了“吃的更好”的良善初衷,使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被裹挟进祖辈、父辈强加的饮食禁忌里。人类的饮食禁忌本应该是一种手段,却在某些文化中变成了目的,这是有违初衷的。
本文首发于无界Daily,有修改
《好吃》读后感(五):Classical work, good to read
国泰里的那间商务印书馆旗舰店好象前两年才大张旗鼓地开出来,结果金融危机一来,竟然维持不下去了,六月初发出布告来,要关门洗货。我在抢购中觅得此书。
此书之原作即为Marvin Harris的Good to Eat,在关于食品的人类学著作中影响极大,其中之观点曾以零售的方式从很多渠道听说过。其核心之理论是以生态的约束与经济的计算来解释食物偏好与食物禁忌方面的文化传统及行为。其所批评的正是从Marshall Sahlins到Mary Douglass等这些以食物的象征意义来解释饮食习惯的文化至上论者。全书论及各文化关于以下几种食物的偏好与禁忌:牛肉(印度的禁食与美国的热衷)、猪肉、马肉、乳类、昆虫、猫狗之类的宠物,以及——人肉。
我对其观点十分认同。文化的形成必然有其道理。有些文化因素可以完全是因为与物质条件无关的象征意义而产生,但食物却必须从自然界中长时间、大规模地获得相对稳定的供应,有关食物的文化规范不可能完全独立于物质世界的制约而存在。因此,种种有关食物文化的文化因素,其根源还是要从文化形成之初所处的生态制约与所面对的经济计算中去找。
具体关于各项食物,他的结论可以极其简单地总结如下。首先,总的来说,人都是要吃肉的。虽然现代科学发现从营养的角度而言,人其实不是非吃肉不可,但古往今来,除了少数宗教团体之外,没有哪个文化是不想吃肉的。而且,在吃植物方面,很少有什么文化禁忌,反正植物无生命;而在吃肉方面,规矩就多了,就连百无禁忌、什么都吃的中国文化,起码也还不主张吃营养最好的肉——人肉。所以,关于食物的文化规范实际上是关于吃肉的文化规范。
从将植物转化为肉这个角度来讲,最经济有效的动物是猪。但猪有两个缺陷:一是杂食,即不能光吃草(还得吃点他自己的便便之类的其它东东),二是不产奶(猪的乳房没有储藏功能)。因此,对于有些生态条件来说,最好的选择是能高效地将草转变成肉和奶的动物——鲁迅先生都知道,这就是牛。所以,吃猪肉与牛肉是缺省的选择,不吃这两样中的一样才是奇怪、异常。这一来,首当其冲需要解释的两个怪现象便是印度的牛肉禁忌与中东的猪肉禁忌。
印度不吃牛肉因为印度(尤其是北部干旱地区)的黄牛是重要的生产力,印度的干地不象中国的水田,没有牛就犁不开地。而且牛还不用饲料专门喂养,只需吃些剩余和杂碎即可,不与人争粮争地。同时还能提供牛奶。所以牛活着远比杀了吃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以下的这个地区差异很能说明这种生态选择的过程:印度北部需要牛耕地,所以公牛的比例远高于母牛;而印度南部种水稻,地小,用不上黄牛耕地,但需要母牛产奶,则母牛比例远高于公牛。而且这个性别差异的造成不是通过地区间贸易,而是通过对不同性别的小牛犊有选择地倾斜营养的分配。
中东人不吃猪肉,说到底也是因为在中东干旱、少树的生态环境下,养猪是个不划算的事情。既然不划算不养就是,何必以宗教戒律的形式严厉禁止呢?这一点上MH的解释不是很有力。他只是说,猪既然不能大规模养来吃了,这种动物便成了个对人全无用处,而且还令人生厌的东西,而人又总喜欢把什么东西都分个三六九等,于是在文化上对其之贬低与丑化便出现,猪变成了最低级最可恶的动物。犹太人及埃及人历史上都是养猪也吃猪肉的,只是在当地生态发生变化之后、生产及生活方式改变了,猪肉禁忌才出现。
欧洲很多国家都吃马肉,但英美文化中却对吃马肉很反感。而且马肉在餐桌上的地位在历史上忽上忽下,时而可吃,时而不可吃。马在人类生活中有特殊的地位:没有什么地方是专门养了马来吃的(虽然马肉好吃),因为在产肉及产奶方面,马远不如牛羊有效率。历史上马养着都是为了打仗的。所以,在没有生态条件养马,却又需要马来打仗的地方和时候,吃马肉是被禁止的。而对于象蒙古人这样以马为生,又有充足的马匹供应的人群,则虽然不会专门养马来吃,但在需要吃的时候(比如行军或转场时,没有其他粮食了),吃马肉则没有禁忌。在西方国家,马肉往往是穷人吃的。其原因在于,这些马肉都是来自为了其他目的而养的马身上,是当这些马出了问题,或者通过其他正规渠道获得猪肉及牛肉变得困难时,这些马肉才能以便宜的价格变得对穷人有吸引力。
在美国人的餐桌上牛肉取代猪肉成为肉食中的首选却只是二十世纪中期的事情。其原因在于本部各州feedlot这种新式的喂养方式的兴起及快餐业所带来的汉堡包的普及。此章中谈及另一个问题:不同人群对乳糖的不同耐受程度。北欧人基本上没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但中国人中乳糖不耐受者达95%(这个数字有点夸张,其准确度可疑)。这背后的进化学上的原因我以前已知道:北欧人群只能从牛奶中获取足够的钙,所以有进化压力要产生对乳糖的耐受性;而其他各地的人群,要么靠晒太阳,要么靠吃蔬菜和海洋哺乳动物来获取充足的钙,没有压力非得耐受乳糖不可。只不过今日之世界,北欧人种坐大,结果搞得喝牛奶变得正常,不喝牛奶倒显得病态与落后了。联系前几天看的China Study一书,更可见今日中国之所谓振兴乳业、让国人多喝牛奶是个巨大的误区,中国人其实根本不需要牛奶所带来的那些额外的钙,而牛奶中的脂肪与蛋白质却会带来诸多害处。下一代的中国人将为此付出健康上的代价。
世界上不少地方的人(尤其是落后地区和野蛮部落)还吃各种各样的虫子,这又是为何?从营养角度来看,象虫蛹这之类的东西其实是很好的,我在云南时也有幸品尝过,并不恶心。MH的看法是,各个人群在寻觅食物时都在进行最优化的计算,如何以最小的热量消耗来捕获最大的热量供应。如果生活在一个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地方,没有人会耐烦去捉蝗虫吃的,因为花那些力气去获得那么点热量,实在不划算。但如果一个地方大动物稀少或难捉,而小昆虫多的是,那人们在捕获大动物的过程中,见着小虫子则也会捉来一并吃了,以增加热量供应。当然,这并不是说亚马逊丛林里的人都精通运筹学,时时刻刻在脑子里解多元方程式,算出捉这个虫子到底在热量上是赚了还是赔了。形成这种文化的是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压力。哪个部落的头,做了个错误的决定,放着大个的食蚁兽不打,却忙着找蚂蚁吃,最终这个部落也就完蛋了。
吃不吃狗肉跟吃不吃昆虫的道理也差不多。如果用不着狗打猎,而又没有其他如猪、牛、鸡之类的廉价的动物食品来源,狗肯定是要吃的。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如Hawaii),把狗当成最宠爱的宠物来养,甚至用人乳来哺育小狗,但养大了,却还是一样要吃掉。
这些动物性食品都讲完之后,最后就要讲吃人了。饿急眼了吃人,或者象张献忠那样的变态狂人发起的吃人,并没有长期的文化规范的支持,在此不论。MH讨论的是形成了文化规范的战争性食人——就是专门通过暴力把外人捉来吃(肯定是吃外人,自己内部的人经不起几吃)。他的看法是,我们一贯以来问为什么会有人吃人这个问题其实提错了。真正奇怪的,是这些所谓有文明社会,用各种各样残酷的手段杀人、饿死人、且用尽手段屠杀动物以获取动物性食品,却偏偏不准人吃人,哪怕是已经因为其他原因死了的人,哪怕人肉其实是最有效的蛋白质的来源。岂不是很没有道理?
在MH看来,这是因为对于形成了国家制度的社会来说,当国家政权有能力将俘获的人作为劳动力来驱使时,把他们留着来养猪养牛或做其他苦力,比起把他们简单地一吃了事,要有用得多。这当然只是统治阶级(肉食者)的想法,但肉食者鄙,下层人民未必能从变成奴隶的俘虏身上获得短期的利益,所以,如果没有严令禁止,草民们为了填饱肚子,少不了要跑到战场上去割了死人肉或私擒俘虏,好回家煮了吃。一旦此行为出现,不仅统治阶级得不到奴隶,其他部落知道一旦打败必然被吃掉,便也再无妥协之余地,只能死战到底,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建立。因此,统治阶级必然要创造出严禁吃人的文化禁忌来制止此行为。
对这一规则的唯一例外,据MH说是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又有其特殊的生态与历史的理由。
最后,关于此书的翻译说两句。批评人家的翻译是个不厚道的事情。翻译之事实在是吃力不讨好。这本书之翻译总的来讲还不错,很多动植物的拉丁文专业名称、各种文化中奇人异物,译者还都花了功夫搞清楚了怎么译。文字虽然仍然是很重的翻译腔,但总的来说还算通顺,读来还算顺畅。这里要讲的是两个小笑话,正好和前一阵子传出的北大某教授将Chiang Kai-shek译成“常凯申”有异曲同工之妙。书中第11页说到有一个苏联领导人曾宣称苏联要超越美国,此人唤作尼基塔-库斯科夫。略知苏联历史(哪怕是中国近五十年历史也行),此时不需看其英文原名Nikita Khrushchev,大概也能想到,此君实乃我们所熟悉之修正主义大头目,赫鲁晓夫同志是也。到了第71页,又出现个叫作帕斯陶的科学家,发明了炭疽病及其他一些病的疫苗。一看英文原名才知,此人其实是我们以往称作巴斯德者也。当然,这两个问题比起译错了蒋介石来算不得大问题。毕竟老外的名字本来就是个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