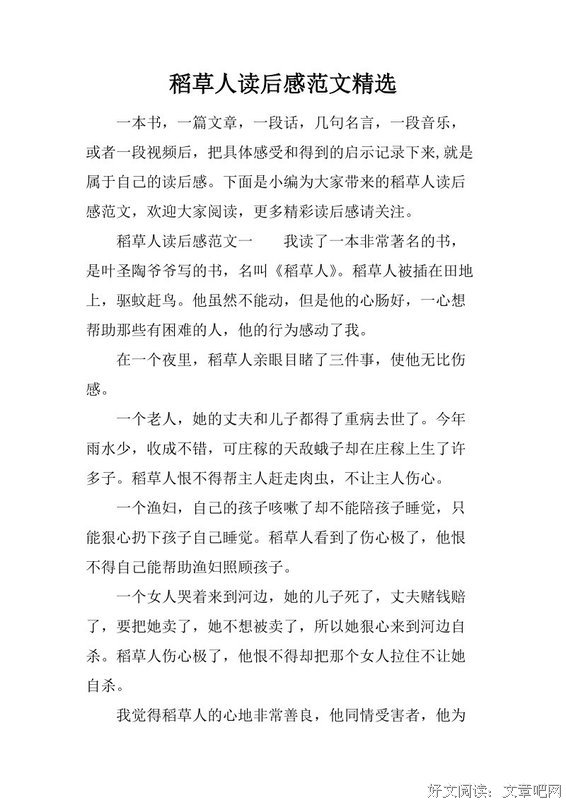《沙粒集》读后感精选
《沙粒集》是一本由张新颖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9,页数:1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沙粒集》精选点评:
●随笔不是巨著,写随笔的好处是写完一篇,不久就可以再写一篇,也就是说,不断地有下一次。它给不断的写作者提供了不断的机会。人不可能一次性地把自己变得足够好,就一次又一次地、一点又一点地慢慢来。
●看到书的一半,后半部不是很感兴趣了
●好书1
●有底蕴,不卖弄技艺,写出来的东西真的好。
●写到沈从文时的感情是真的藏也藏不住
●写复旦和沈从文穆旦之类的,有点看腻了,讲小学的倒是有趣。印象最深的是苦闷的拉二胡的老师和寂寞到对牛弹琴的爱因斯坦。也有套路,复旦人的聪明。这种聪明有学问打底才能漂亮,且不能学。
●张老师文风一贯的从容而有余韵。喜欢讲穆旦和艾略特与中国的一章。
●(2019.159)考试周熬夜读完,有点失望,因为专业性太强了,中文系门外汉的我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张新颖老师对沈从文的研究原来是站在了“巨人”凌宇的肩膀上做成的。也算是稍微了解了一点张新颖研究沈从文的心路历程和学术过程了,《沈从文的后半生》以及《沈从文的前半生》这两本书可以加入书单了。
●这是一本随笔集,但最后几篇,比如关于艾略特诗歌的研究,学术性还是较强。读完这本小书,印象最深的是张老师的母亲。当别人认为年幼的“我”是天才,建议跳级,母亲面对别人描绘的前景很平静,不松口,她的意思很简单,也很坚定:我的孩子我知道,不是什么天才,就是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做出一道难题就是做出一道题,不说明其他方面。母亲的观点是路还是要一步一步走。 “孤独使精力专注,劳动让身心踏实。”
●作为一本书来说,这个集子有点太凑合了。写作使你发现的不足,也许会从语言文字、情节结构、想象力、现实感,扩充和深入到你自己生而为人的方方面面。这个时候,写作使我们发现的不足,就不仅仅是对写作有意义,更对生命有意义——写作使我们产生对于自己的认识,进而使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沙粒集》读后感(一):离开沈从文,张新颖老师魅力大减
总是和自己说,不要看了不要看了,这是2019最后一本、最后一本,结果这种不到两百页的随笔,非常传统式的写法,根本不费我什么气力,三四天就读完了。 这本书收录了张新颖老师近几年来的随笔、文学讲稿、书评和部分沈从文研究后记的内容。张先生自称这些文章是“微不足道”的,是不起眼但却自有硬度、形状、颜色的沙粒。在我读来却毫无沙粒的质感,反而异常光滑,语言是平和如砥的那一种,有高尔泰《寻找家园》里的那种风格,还传承着一种很庄重的写作精神与态度。 写法上虽然有此很纯粹的东西,但其实收录的这些随笔文章有些零碎,没有形成内在的一定的逻辑。不像张新颖先生的那些学术专著具有系统性,比如《沈从文的后半生》和《沈从文的前半生》,还有《沈从文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等。 张新颖先生的治学精神与治学之方法论堪称一绝,但这些小随笔确实如书中一老师规劝的那样,“随笔这种类型,不太适合年轻人写;等你老了,阅历多些,读书多些,再来下笔,才会得心应手”。 三十年过去,张新颖先生到了那个“老”的年龄,但随笔好像并没有写出那种该有的沉淀的味道来,难道老师说错了吗?在我看来,或许是张先生把劲都使在了要紧的地方,所以这随笔就有点蜻蜓点水的泛泛之意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非常糟,只是因为我常写随笔和一般性日常散文,多少知道况味与滋味如何咂摸,张先生让我咂摸他的人生和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某些局部,但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在乎他的个人经验分享。 那个做沈从文研究的张新颖是我热爱的,但《沙粒集》里的张新颖确令我有些腻味了。 ——《沙粒集》读书笔记
《沙粒集》读后感(二):沙粒即碎金
和许多读者一样,我第一次听闻张新颖老师的名字,缘于《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记得又一年,张老师来我的母校进行讲座。一时之间特别动心,翻出了《沈从文的后半生》想回中文堂听讲座顺便求个签名。可惜当天加班未能成形,不仅遗憾地错过了讲座,也没能达成和张老师见上一面的愿望。 但这并不妨碍我做一个安静又忠实的读者。接下来的几年中,我陆陆续续地读完了张老师的多本文集,同王安忆共同完成的《谈话录》,以及研究沈从文的系列专著。 欣喜地看到《沙粒集》的出版,这是2019年继《谈话录》修订再版后,译林出版社为张老师出的第二本书。 《沙粒集》的序言短短几行,却充满了朴素的诚意——“不起眼的沙子,每一粒却自有硬度,自有形状、颜色,它们的构成携带者各自的经历。我从小喜欢沙粒,如今借文字用到书名上来,仿佛触着了坚实之物。生命不断流逝,或许并不止于完全虚无,总有一些沙粒不肯消失于无形,不妨把它们当做时间的馈赠,生活的纪念。”
尤为青睐“随笔”这个文体,随笔适合终日奔走在通勤线路上的我,不长不短的篇幅使我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一段又一段完整的阅读。随笔的体量虽小却能容纳广博深厚的情感与思想,阅读好的随笔时常能收获思想的启示和心灵的感动。
一本质地饱满、感情深厚的随笔集,就像一个老友。翻开书页扑面而来的亲切与醇厚,叫人感慨良多,读了再读。
《沙粒集》的文字流畅熨帖,从头到尾都不见晦涩的词句。无论是记录往事回忆还是分享学术心得,张老师也是毫无保留,满怀真诚,绝无半点炫技之意。每当他写到文学研究过程中的人和事时,都让我这个从中文系毕业多年又时常怀念校园生活的人倍感受用。
从他的文字中,我时刻能感到一颗赤子之心闪闪发光。他从来都是谦逊而低调的,做学术研究,读书,写诗,译诗,点评作品,提携新人……这些事仿佛都是天然的使命,是与生俱来应该要做的。正因为把自己沉浸在生活中,拥抱世俗,理解平凡,才让他的随笔显得开阔、舒畅、温厚而自由。
虽然不曾谋面,却仿佛通过《沙粒集》拥有了再一次同张新颖老师对话机会。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临近年末的匆忙生活中一件治愈又满足的事情。
《沙粒集》读后感(三):张新颖:我更看重写作中的捉襟见肘
一则短评,也是摘录,看见好的句子就想抄下来。
关于练习,关于审视自己的不足,在张新颖老师的新书里,我遇到了更为恬淡和深入的说法。在《沙粒集》(感叹一下他真会取书名),有一篇文章,题为“写作使我们发现自己的不足”,是他写给复旦大学MFA毕业同学的寄语。
刚开始写作,我们会发现自己这样那样的不足。我觉得,这是重要的时刻,是真正理解写作的起点。……只有在你写的时候,你才意识到某一方面或很多方面的不足……写作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出来了。发现自己的不足,才是真正理解写作的起点。这句话对有些人无效。什么人呢?那些在写作中获得自信和骄傲的人,且不能体味到自身不足的人。有些不足,短暂的练习可以奏效。有些不足,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还有的方面,可能一辈子也不行。最后一点,很多人一辈子也不知道。所以不要轻易地鼓动人去写作,尤其是已经有稳定即便是艰难的生活,身心一旦被蛊惑就再也难平静地看待自己。
坚持写作,就是持续发现自己的不足。当你写得越来越好,写作会帮助你发现新的、更重要的不足。张老师还说,一些成熟的作家,不再发现自己的不足,或者发现了选择绕过,还有人写了一辈子,几乎从未发现自己的不足。张新颖先生的文字言简意赅,没有多余的话,思考到处,语言即抵达那儿。
推及自己,冷汗都出来了。写作的过程,我是否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是否还可能写得更好些?这都是问题。读这本书,恍然坐在张老师的身边,看他抽着烟,慢条斯理地说着。有读者说这本书淡,是没有能力体会到一个学者时刻审视自我的努力,大概也是自身没有遭遇过这样向上或者说变得更好一些的艰难。新颖老师谈到随笔写作时说:
我更看重写作中的捉襟见肘,这是重要的提示,清楚地标出了自己这方面哪方面——知识的、情感的、想象的、表达的,等等——的欠缺。我常常把自己推到这样窘迫的境地。还有更动人的篇章,是新颖老师写贾植芳先生,说谁谁是坏人,那些脸转来转去,转过去是谄笑,转过来的时候刻了两个字:岸然。先生说:坏人。感谢时间的验证,那些坏人之间的同类,终于会被不断认出。对恶的认识,才更能感受善,如此才不会做一个糊涂蛋。
学会识别恶,正如识别善一样,这也是一种练习,甚至是更大更久的练习生活,这需要在更缓慢、更漫长的生命中练习,而且还得有方向的练习。大多数时候,这种练习仅靠自己是难以完成的,需要一些老师、一些朋友的提点,遇到这样的灵魂才是生命之幸。
《沙粒集》读后感(四):回忆张新颖老师
有关张新颖老师的记忆,大多停留在《沈从文精读》和《中国新诗》的课堂上,除了后来还有一次,大四下半学期,春末的某个傍晚。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专业课,我和学姐在政通路的东门口等人,大约二十米开外,张新颖老师迎面走来,我们不约而同地注视他,直至他走近。
我们高声喊道:“张老师好!”他背对着烧红的晚霞笑盈盈地回应:“你们好啊!”我立刻站得笔挺说:“我们在迎接您呢!”他原地愣了一会儿,接着往前走:“你们这是在迎接我吗?”做出一副好似惊慌又怀疑的表情。我说:“当然啦!”脸上每块肌肉都极尽全力笑开。随后在我们不由自主的持续注视下,他穿过东区的斑马线,渐行渐远。我转头对学姐说:“真是美好的一天啊!”学姐连连点头,眼里闪着星光。那时候,在我们很多同学心里面,张老师是这样一个温暖又明亮的存在。
近两日读张老师新出版的随笔《沙粒集》,眼睛扫过他的文字,脑海里却跟放电影似的,浮现他在讲台上娓娓道来的神情和声音。他讲沈从文,逐章逐篇分析文本,印象中他的风格,正如书中援引王佐良回忆燕卜荪讲课:“只是阐释词句,就诗论诗,而很少像一些学院派大师那样溯源流,论影响,几乎完全不征引任何第二手的批评见解。”于我而言,这是一位“知内情,有慧眼的向导”。甚至偶然地,凝视张老师朗读原文的身形出了神,恍惚间幻想是沈从文本人站在那说话,虽然我从来没见过那位老先生,也不知道他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样。
那时我读沈从文也是入了迷的,全集中散文和小说通读一遍,大三下学期《沈从文精读》开课前,我记得是一个寒假,背包里揣着一本《湘行散记》,我就跑到湘西去了。龙山、里耶、花垣、茶峒、吉首……兜了个大圈,体验了惊险和曲折,也敢对自己说,我已经见过世间最美的风景。回到学校后,我将千言万语浓缩成一篇短小的散文,题为《给湘西的一封情书》。实在记不清切,后来是张老师还是我自己在课堂上把这篇小文章念了出来,或者可能根本就没念过,但它确实是被交到了张老师手上,否则我这趟“朝圣之旅”就不能够形成闭环了。
认识不少写作的朋友和长辈,观察到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有的作者平日待人接物的形象,同他文字中所呈现的,全然是两幅面孔。有人现实中木讷拘谨,词句却灵动放逸,或者是,眼见他开阔明朗,笔下却有萧瑟畏缩之意。因此我觉得有趣好玩的是,张老师文字中的平实亲切、幽默可爱,同我记忆里他的言语是一样的,而我曾经从他眼睛里看到的诚恳与真挚,如今从他的字里行间也一样能捕捉到。
此书取名《沙粒集》,在翻开它之前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奇它与博尔赫斯《沙之书》的关联。读罢小序,似乎并无直接影响:“不起眼的沙子,每一粒自有硬度,自有形状、颜色,它们的构成携带着各自的经历。[…] 生命不断流逝,或许并不至于完全虚无,总有一些沙粒不肯消失于无形,不妨把它们当作时间的馈赠,生活的纪念。”博尔赫斯给他的短篇小说集取名沙之书,指向“无限性”与“未完成性”两层含义。根据博尔赫斯的论述,沙可以是一个短篇故事,故事彼此独立,不依循时间顺序,汇拢在一本书里,聚沙成塔;而沙也可以是一本书,书没有开头没有结尾,保持开放,无穷无尽,扩大成宇宙,聚沙成巴别图书塔。Le livre de sable,既是收容“沙”的书,也是作为“沙”的书。“Tout, au monde, existe pour aboutir à un livre”,世上存在的一切,皆为抵达一本大书,马拉美亦作是言。张老师谈对随笔体裁的偏爱,隐隐呼应了这种无限性和开放的状态,“写随笔的好处是写完一篇,不久就可以再写一篇,也就是说,不断地有下一次。它给不断的写作者提供了不断的机会”,“趋向之前未曾见识和体会过的许多东西,趋向更多一点、再多一点的自由”。遥远的相似性应当是存在的,至少两种写作的初心都令人感动。
无限的、碎片化的、拒绝封闭的写作,令我想起做硕士论文时读过的诺瓦利斯《Das Allgemeine Brouillon》,中文译名“全面题材装订草稿”(怪别扭的)。一批德国浪漫派诗人和哲学家似乎在为“断章、碎片”正名,施莱格尔全凭兴致,仰赖“Witz”的乍现,诺瓦利斯的断片是渐次被发现的拼图,漂浮于不可见世界中的雨丝风片,遵循一个系统的分类准则,建立一部“科学精神的百科全书”。每一节片段,短则寥寥几个单词,长的也有十几行,把一个观点(une idée)完整说尽则止,如同语言学中音素、语素的概念,它是组成“科学精神”的最小单位,无法再向下拆解的基本元素。张老师谈到写《三行集》的构想,在巴掌大的纸页间,以三行为界,写自由的句子。剔除繁冗,留下骨骼,提炼字与词所能构成意义的最小形态,像一场创作的冒险游戏。写作者的虚荣心,总是以长文、长篇甚或大部头为最高理想,若是能从篇幅的执念中脱离出来,倒是也让人松一口气。
张老师说过的话,我始终记得这一句: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不会被浪费的。我用铅笔把它写在《沙粒集》的扉页。依然是在大三那年《沈从文精读》的课堂,我已经忘了这句话发生的前后语境,大概当时他正带领我们解读原文,所有同学低头盯着讲义里的文本。张老师讲完了一大段内容,话音落下来,几秒钟的静默之后,张老师缓缓说道:“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不会被浪费的。”忽然我感到一阵暖流从心底升起,我抬头望向张老师,他迎住我的目光,与我对视,周围的人仍旧低着头。我心中的暖流从眼眶涌出,张老师回以我一个温柔且坚定的眼神,像照进岩穴间的日光,细如丝线,却有力量。
《沙粒集》中出现了好些熟悉的名字,陈思和、梁永安、陆谷孙、王安忆……我恰好修读过他们的课程,或是旁听过他们的讲座。于是很不争气地,我怀念起大学时光,虽然才离开校园没几个年头,就已忍不住感慨人事。大学最令我怀念的,其实正是这些师长,曾经聆听他们讲授经典,是我的幸运。那时学生与老师之间通常很疏远,除非是跟着他们做论文题目,倒有密切交流的机会。可是这些老师啊,他们就像我夜路中的一盏盏灯,不刺眼,却能照见来路上的每一块标识,过去是这样,现在依然是。
2016年,摄于巴塞罗那圣家堂《沙粒集》读后感(五):摘抄
◆ 一九七五年夏天
>> 又过了很多年,我成了一个教书匠,参加一个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她细心地注意到冯至写梵高的十四行诗,提到“剥马铃薯的人”,而梵高画的是“吃马铃薯的人”,一字之差,却是劳动和消费两种行为之间的差别,大有文章可做。我犹豫再三,还是用不确定的语气告诉她,其实可能没有差别,剥和吃两个动作是连在一起的,基于我少年时代在北方以红薯为日常食物的经验——煮熟了,吃的时候,边剥皮边吃——梵高画的吃马铃薯,大概也是如此。北方人冯至,或许就是因此而没在意两个动词的差别?至今,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 收录机
>> 我们那时候不懂,他得有多孤独,才会锲而不舍地长期对牛弹琴。
◆ 读钱细事
>> 余冠英、何其芳
◆ 歌
>> 而印象最强烈的,是布罗茨基的青铜雕像。
那是一颗头颅,放在一个破旧的旅行箱之上。
雕像就坐落在小花园一角,粗糙的水泥地,周围不是草、树和花。诗人的流亡生涯和颠簸命运一下子就凸现出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旧居也注意到一只旅行箱,但比起来,那只真实的旅行箱比这个青铜雕塑的破旧旅行箱,似乎要好一些。布罗茨基有一张照片,那是一九七二年六月四日他离开列宁格勒飞往维也纳,开始流亡生涯之时拍的,照片上他双腿分开,骑坐在旅行箱上。这座青铜雕像让我想起这张照片,但雕像去掉他的身体,旅行箱上只有一颗头颅,更有表现力。
>> 他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最后写道:“写诗的人写诗,并不是因为他指望死后的荣光,虽然他也时常希冀一首诗能比他活得更长,哪怕是稍长一些。写诗的人写诗,是因为语言对他作出暗示或者干脆口授接下来的诗句。一首诗开了头,诗人通常并不知道这首诗会怎样结束,有时,写出的东西很叫人吃惊,因为写出来的东西往往超出他的预期,他的思想往往比他希求的走得更远。只有在语言的未来参与进诗人的现实的时刻,才有这样的情形。……有时,借助一个词,一个韵脚,写诗的人就能出现在在他之前谁也没到过的地方,也许,他会走得比他本人所希求的更远。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或烈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在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可以称之为诗人。”
◆ 此时此地
>> 窗口的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我随手翻开,读到这一段:
“夏季是一段绿色的、紧迫的、很多爱丢失或找回的季节。这是一年中最紧张的时候,就北半球的自然界而言,几乎是一下子有数十亿动物从冬眠中苏醒,还有数十亿动物从热带地区迁徙而至。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上演着求爱、交配和喂养下一代的狂野派对。夏季的主要任务是繁殖,而机会窗口的打开是短暂的。表面看来,夏季是嬉戏的集会,但这掩盖了潜藏的竞争和斗争,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物种的新生命而言,这个物种中都必须有平均相等数量的死亡。此外,对于大型动物而言,它们的生存需要成百上千的小型动物作为食物,这样它们才能繁衍出自己的后代。而那些小型动物也都进化出了降低被捕食概率的机制。”
这本书叫《夏日的世界》(Summer World: A Season of Bounty),是博物学家贝恩德·海因里希(Bernd Heinrich)对一块树林空地及周边生物的观察、记录,他特别关注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文版(朱方、刘舒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封面上,印着几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米勒(Roger Miller)的歌词:“夏季,当树木和叶子变绿,红色的鸟儿歌唱,我会是蓝色(忧郁)的,因为你不接受我的爱。”
>> 古久以来对柿子树的赞美,都落在那种很朴实的“德”上,所说的七德,一长寿,二多阴,三无鸟窠,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可供临书。
>>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详细记录过日落景象,他说日落是一场完整的演出,开始、中间和结尾,全都具备;它好像把一个白天所发生的一切,战斗、胜利及失败,重演一遍,只是规模小了一点,速度放慢了一些。
◆ 写诗的事——关于《在词语中间》
>> 今年五月,在一张小纸片上涂成一首《乌鸫》,用手机拍下来,发给一个朋友看——
昨天的乌鸫站在另一条颤动的长枝上
啄食樱花落后结出的小果子
已绿里透红(也是一种樱桃)
转过街角后听它鸣叫
粗一声 细一声 接着婉丽跳荡
远应山涧溪水 而不是它眼前平缓的河流
我初以为是一群鸟呼引唱答
直到去年 发现它喜欢模仿其他鸟鸣
今年我知道 天微明的时候 就是这只
包含了很多种鸟的鸟 把我吵醒
隔了一天,朋友才回微信——
先看见字。
然后是,笔迹,
韵脚。
突然,听见了鸟鸣,
我返身——拽着它——
深夜仰脸走进光灼灼的晨间树林。
原来是这样读一首诗的。
◆ 关于笔记本的书评
>> 有好几次,王安忆说,现在的笔记本印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在笔记本上写啊?她到现在还用笔写作,而且是写在本子上。她的长篇小说初稿,是一个接一个笔记本。她不是唯一的例子,但这样的人实在不太多了,还在维护笔记本原来的功能。
笔记本的空白,似乎是发出邀请,希望在上面写写画画;但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邀请极少得到回应。
或者,空白根本就不是邀请,空白本身就是自足的,这样就好。现在笔记本的“文创”,基于这样的理念?
再或者,空白是一种态度和立场,是一种包含了拒绝的坚持?印制得精美,是一种抵御的方法?它清楚鲜明地标示一种审美精神和趣味,这种审美上的敏感,使得一个人无法把无聊的会议、腐败而流行的词语、霸道的陈词滥调,如此等等,写进这里面?
笔记本会不会说,有些东西,就让他们写进书里好了。
◆ 沈从文与五四
>> “多数”有“思想”或要求“思想”,“没有思想”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就需要没有潮流力量支撑的个人的坚持,沈从文有的,就是这种个人的坚持:“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 他的文学遭遇了新兴文学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他个人的文学无以应付,就是他个人的文学所属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也遭遇尴尬,也就是说,他不能依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来应对新兴文学;况且,他个人的文学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的主导潮流,并非亲密无间。但他又不愿意认同新兴文学和新时代对文学的“事功”“要求”。
◆ 凌宇与沈从文研究
>> 宇何其有幸,在沈从文生命的最后十年,读其书,见其人,忘年交往,也因此共同经历了八十年代政治文化的晴阴变幻而波及作家和研究者的可见和不可见的风雨。
◆ 点评
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