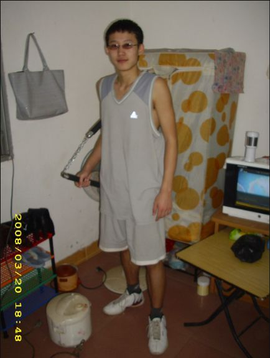智障女孩嫁老汉,这句“嫁得好”我夸不出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每天热搜上会出现多少词条。
在微博上,这个数字是——50。
热搜轮动,不断有词条出现,也不断有词条消失。
而我们的注意力,就在这一次次“出现”和“消失”之间,被牵引向各个方向。
牵引着我们的,是什么呢?
不得不承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无效信息。
而那些真正值得我们讨论和深思的问题和信息呢?
幸运的,可以牢牢霸占热搜榜。
掀起一波舆论热潮,引来各方博弈,最终带来一些小小的变化。
而不幸的,则在大数据的算法和机制之下,短暂出现,又迅速消失。
前两天,她姐注意到的一个话题便是如此。
#55岁男子娶年轻智障女孩#。
从出现引发讨论,到当事人回应,再到官方回应,前后不过十几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之后,事情“水落石出”,热搜被下一个话题占领。
高效吗?
她姐只觉得好笑。
因为,这件事情不只是关乎一个个体和两个家庭的选择,更是一个群体的隐身和失声。
而这样的一个话题,不该被如此轻飘飘地覆盖过去。
1+1>2?
事情的最初,是一场“误会”。
一则视频被配上了“驻马店老人娶女童”的文字后,在网上疯传。
如果只看画面,的确容易“想歪”。
两人一眼看过去年龄悬殊极大,男子甚至还拿出来纸巾为“女童”擦鼻涕。
几天后,驻马店的官方人士回复称,这是因为女方“娃娃脸”而引起的误会。
事实上,女方今年已经20周岁,并不是网传的女童。
但,另一个事实也随之披露——
女性虽然不是女童,却是一个智力障碍者。
这两个人的结合,并非什么冲破世俗的爱情。
一个穷。
当事男子今年已经55岁,但因为家境不好,一直未娶妻。
家里只有几间小平房,和一个坑坑洼洼的土院子。
早几年的时候,他还出去打工。
但近年来,因为家中八旬老父亲的身体欠佳,他就回家照顾老父亲,靠种地为生。
一个残。
女孩2001年出生,是家中的独女。
五六岁时因高烧患病,从此成了智力障碍者。
不会说话,也不能走路,完全无法自理。
因而,这个结合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
于他们而言——
是退而求其次的各取所需。
是“皆大欢喜”的“最优解”。
没钱的55岁男子,结婚是他此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因而即便女方是智力障碍者,也不妨碍,“我能结上婚,很高兴”,没准儿将来还能有个孩子。
拥有一个智障女儿的家庭,也无所求。
父母年纪大了,没有办法长期抚养,所以张罗着给女儿找一个“长期饭票”。
没要彩礼,也不求其他,“饿不着就行”。
即使,获得这个“长期饭票”唯一的筹码,是这个智障女孩的生理优势——“性别女”。
旁人也是看好。
录下这个视频的女性,边录边说:
“虽然说年纪大点,但也对得起她了,她也不会自理。是吧?”
“你这还享福呢,正常人还没有这种待遇呢,新郎官对你多好。别哭了,别哭了,到新家了,别哭了。”
事情披露出来,网上吵吵嚷嚷撕成一团。
指责男方的——“就是娶过来给他生小孩”。
指责女方父母的——“父母拿女儿当着包袱扔了”。
指责网友的——“换位思考下你愿意娶还是你愿意嫁?两个可怜人最低的生活需求也要跳出来指责?”
事情闹大,官方倒也回应得迅速。
同居不违法,但不能办理结婚证;如果有了孩子,可以办理准生证和上户口。
当地残联紧随其后付诸实际行动帮扶这个特殊家庭:
给提供了智障女孩提供了轮椅等助残设备。
男方家里坑坑洼洼的小院,也得到了“会帮忙修缮”的口头承诺。
至此事情盖棺定论。
骂战噤声,热搜结束。
隐形
围观了全程的她姐看到这里,不仅不觉得松了一口气,反倒只觉得悲哀。
因为这场景如此熟悉。
前阵子的“方洋洋被虐致死案”的前半场,和这个事件并无二致——家境不好的男方娶了智力障碍的女方。
而最终事情发展成了,男方一家对方洋洋长期虐待,最终致其死亡。
悲剧曾经出现过。
但即便有了前车之鉴,这个20岁的智障女孩,依然被默认可以进行这样一种资源的置换。
这种置换,还得到了官方的认证和加码。
而这一切,都跟她本人的意愿无关。
悲剧一次次出现,而他们一次次被隐形。
被隐形的群体,到底有多大?
201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残疾人口总数是8502万人。
其中伴有智力残疾的有568万人,多重伴有智力障碍的430万人,自闭症的200万人。
一个个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以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这样的一群人,到底过着怎样的一生?
2020年的一档纪录片《一切都会有的》,就将镜头对准了这样一个特殊群体。
更具体一点,是对准了像上文的智障女孩一样的,心智障碍者群体。
这档纪录片通过长达几年的拍摄,记录了北京丰台区某机构的一群心智障碍患者的日常后,给了我们问题的答案——
“无法自控”。
大部分心智障碍者,都是在很多人看不见的角落,过着失控的生活。
情绪上来了,处理的方式常常异于常人。
尖叫。
把头埋在工作人员的腰间,拼命尖叫,叫到嗓子疼,也不知道停。
砸玻璃、砸车。
患有自闭症并伴随智力障碍的刘斯博,两个月砸了十几块机构的玻璃。
以及暴走等等。
失控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情绪。
因为无法和自己的内心和世界正常交流,无法表达自己的需求。
因而,他们的人生也全然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他们一生都在等待。
等什么?
“如果是住在机构里面,等吃等喝等上课,如果还可以回家就等妈妈接。
我今天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我永远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等死。”
“等待”的这个结果,大多是跟他本人的意志无关的。
而心智障碍者,能做的只有接受——接受别人的安排、接受别人的操控。
对心智障碍者的安排和操控,涉及到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比如,纪录片中,一个叫小南的社工,因为不耐烦患者,选择拿起棍子吓唬他们。
刘斯博有一阵子情绪极度失控,动不动就要拿砖头砸汽车、砸玻璃。
后来工作人员一步步推导、调查,才发现是因为那个阶段他的奶奶去世了。
而家人的处理方式是——
不告诉他,也没有让他出席奶奶的葬礼。
20岁被迫嫁给55岁男子的智障女孩也是如此,因为不会说话,结婚前父母都没有跟她商量。
两家一合计,就把她送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
尽管她在婚礼上一直在哭泣,家人却依然坚信女儿“会幸福”。
发现了没?
心智障碍者接受的安排和操控的背后,是他们的想法、需求、权利,被尽数剥夺。
作为人这个个体在世界上存在,却没有享有作为人的权利。
这种剥夺,可能是经济上的、思想上的、人格上的,也可能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上的。
而对剥夺他们权利的,不是别人。
反而是跟他们相处最久的人。
他们常常是一线社工、家人、父母……
困境
她姐对这些做法不赞同。
却也无法作为一个旁观者,说着轻飘飘的话,对置身其中的人的做法一棒子打死。
和心智障碍者的沟通,确实是需要极高的成本的。
无论是人力、物力、精力,以及时间。
即便刘斯博已经在机构住了好久,但李立洁助理和他沟通起来,依然要花费巨大的时间成本。
砸了玻璃之后要交流砸玻璃的原因,就要分成四个阶段。
先稳住情绪——“中午吃饭了吗?”
再保证安全——“慢一点慢一点,丢下石头来”。
两个阶段平稳度过后,才能稍微靠近正题。
即便如此,也要一步步来理逻辑。
玻璃没错——砸玻璃解决不了问题——有问题要用嘴说出来。
《出处》
二十分钟后,情绪爆发的原因才被找了出来。
而费尽周章问出来的原因,也并非什么大事。
或者说,换到正常人身上,根本都不会成为问题的事——“同伴老叫我名字,我就不高兴了”。
而这种有着巨大沟通成本和需要极强的耐心的工作,李立洁一做就是六年。
六年间,工作期间,她几乎就需要给患者提供全天24小时的陪伴。
即便是专门从事服务型工作的一线社工,长时间下来都会疲惫不堪。
更何况是父母。
有句古话是:久病床前无孝子。
而照顾一个一生都将有心智障碍的孩子更是如此。
在某网站上,一个“有一个你不想要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感觉?”的问题下,有一个育有六岁的自闭症患者的妈妈的回答让她姐印象深刻。
“养育她的感觉就像我在养一只麻烦难养的宠物,而且这只宠物永不会进化成更高级的存在。”
“我还是会跟她说话,跟她玩,但多年来没有得到任何回馈,真的让人灰心。”
“我和我丈夫已经老了20岁……我们的大脑每天都在尖叫和持续噪音里煎熬。我们互相争吵,脾气暴躁。我们是一个空壳,曾经的人格已不复存在。这会让任何人崩溃。”
而,像刘斯博,或者像被迫嫁人的20岁智障女孩一样的心智障碍者,在国内有上千万。
上千万个心智障碍者的背后,是上千个因此而疲惫不堪的家庭。
刘斯博的父母提起照顾儿子的这三十多年,担忧的从来不是过去,而是以后。
因为,这是一场看不见尽头的马拉松。
照顾1973年生的刘浩的,是她的老母亲。
她已经九十多岁了,但依然不得不硬扛住。
“我要再倒下来就完了,也没人来照顾我呢。”
一边是特殊需求群体的人权和尊严。
一边是承担着照顾者角色的人群,在看不见尽头的付出和没有明天的日子里的消磨。
无尽的困境。
看不见的明天。
明天
如果说,把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寄托在一个个弱小的个体身上。
明天永远也不会来。
但,这类问题的解决,从来不该只是一个家庭的责任。
对弱势人群、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是社会文明的标志。
是我们的社会,需要给这些有特殊需求的群体,提供普遍的、有尊严的、保障人权的照料。
我们的社会显然做得还不够。
但纪录片《一切都会有的》里,其中的北京智利康复中心的模式或许指出了一条道路。
在给特殊群体提供帮助的时候——
不是把他们当成一个被照料者的角色来对待,而是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看。
比起强调能力,更多的是强调权利。
让她姐印象深刻的,是几个男性心智障碍者要根据机构安排在外面租房子住。
机构不是自己看了房子就定下来让人搬过去,而是全程让这几个心智障碍者参与看房、比较、签合同。
搬到新家,吃什么自己决定,做什么饭也是自己动手。
刘浩和刘斯博单独租房在外面住的时候,第一顿饭,是刘浩做的。
做之前刘浩放的米很少,注定不够吃,但社工在旁边也仅仅是看着。
比起可口的饭菜、比起帮助特殊群体一步做到位。
社工更倾向于让他们通过实践,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不在于一时的味道的好坏、一时的饥饱,而在于给予他们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利。
不是永远把他们放在一个被照料者的角色里,安排、操控他们的人生。
而是更多地去关注——
你的感受是什么、你在想什么、你想怎么做、你想吃什么……
给予他们学习的机会,以及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
但其实,他们生而为人,本就有做人的权利。
只是问题在于,我们这些所谓的幸存者的“另眼相待”,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他们的尊严和权利。
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部分了。
我们可能无法分担特殊群体的痛苦。
但我们至少可以改变自己看向他们的探究的眼光——
即便他们是“孤独的野花”,也依然是和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的活生生的人。
以及警惕可能会出现在我们脑海里的“不嫁出去你给人养吗”的类似想法。
不要把这类问题的重点,放在个体行为和事件本身上,而忽视群体背后面临的切实困境。
这种想法,无形之中就把我们和他们放在了对立面,站在了“我不会是特殊群体”的先决条件之下。
但,她姐想到此前有人关于反对种族主义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当你有种族主义想法的时候,请把自己代入那个种族主义伤害的角色。”
换到特殊群体这件事上同理,“当你歧视特殊人群的时候,请把自己代入特殊人群的角色中去”。
其实这句话可以用来解释说明任何事——
当你有慕强/慕富/……的想法的时候,请把你代入弱者的角色里。
不只是同理心的问题,而是只要我们是人、会变老,我们就总有一天会成为某种程度的弱者。
1%的人掌握了世界上99%的财富和话语权。
而我们,要学会永远站在弱者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