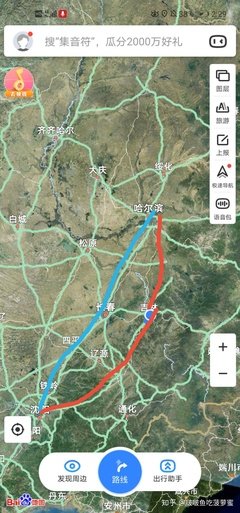《滨线女儿》的读后感大全
《滨线女儿》是一本由王聪威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3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滨线女儿》读后感(一):乡愁、变迁、迷茫和坚守
读《滨线女儿》的时候,心猛然一颤,突然想起13年前的一部电影。主人公阿嘉在台北追逐音乐梦想受挫,回到家乡小镇做了一名邮差,在工作中他偶然发现了一封60年前寄出的信,信中凄美的爱情故事打动了一直鼓励阿嘉追逐梦想的友子,在她的不断坚持下,阿嘉和小镇上的音乐爱好者,在海滩上献上了一场精彩的音乐演出。
这是个发生在现代的故事,影迷很容易通过一封60年前的爱情信件,回味几十年当地风土的变迁,感受到主人公阿嘉鼓起勇气寻找自我的决心和不易,抓住了大时代下人心的敏感和坚韧。和电影不同的是,《滨线女儿》的描写以阿玉为主要视角,众多女性纷纷登场,夹杂着外地人在本地谋生的故事,展现了斗转星移下人性的复杂以及历史的沧桑,既是一次乡土风情的全面记录,也提醒人们对时代变迁进行思考,表面上文艺琐碎,实际上一路读来却略显沉重。
哈玛星曾经繁华,在琐碎细致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它命中注定的沧海桑田,从历史学的角度,这叫做民间记忆,一些日常简单的细节都被用文字叙述出来,虽然细小却极具张力,尤其是读完小说再回头看前几十页对阿玉谋食等行为的描述,很容易让人产生矛盾的心态:我们希望阿玉一家过上更好的日子,但乡间的一些寄托着幸福或者难忘的记忆的载体,希望一辈子都能留下来。
这就是生活的无奈,鱼和熊掌不能得兼,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每个人都会同过去告别,在成长中难免失去自己的一些精神家园。在整部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有点让我揪心,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对某个物品产生了别样的期盼,比如一辆自行车,一双小白鞋,或者其它某种玩具,而阿玉的学生衫,正是她心底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但结局是得而复失,显得非常戏剧化,更是一种残忍,让人不忍直视。
学生衫好比象征性的预言,预示了整部小说的失落和物质,用书中的话说,就是“时光蜿蜒流动,抵不住繁华褪色”。我相信,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都曾在“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天真中,感受到灵魂的出窍。同时我还相信,这种迷茫是暂时的,我们还有文字、有影像,随着旧时光进入博物馆,可以打造新的精神家园,包容过去的一切,只要坚守住,一切皆有可能。
《滨线女儿》读后感(二):《滨线女儿》:一部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人物志
乡土文学发展到今天似乎已比较成熟,它早已成为地方风景,乡村住民,土俗民风等的代名词,显得清新而自然。该题材在台湾文学史中亦同样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以卓著的反思和现实关怀精神, 使台湾乡土文学成为中华文化思潮中独具个性的一脉,是台湾人由惶惑到反省, 由沉默到呐喊, 由悲情到自救的心灵历程。
台湾知名作家、杂志编辑王聪威撰写的长篇小说《滨线女儿》是一部近年来少见的乡土文学佳作。小说以母亲的家乡——台湾高雄市鼓山区哈玛星为写作背景,以细腻独到的女性视角描绘了一幅高雄鼓山港边哈玛星的庶民风景。尽管书中结构纷杂交错,除了线索性人物阿玉外,其他人物面目并非全都清晰可辨,但每一个故事线条依然梳理得井然有序,除了因文化隔阂导致的些许阅读障碍外,无论故事情节还是主线结构,抑或对人物命运的体悟与刻画上,王聪威的表现力度均可圈可点,并无其他可指摘之处。
我们来简要分析一下小说主人公阿玉这个人物。从我个人读完这本书的直观感受而言,无疑,这是一个总是求而不得、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具体表现在她每次卑微的小愿望都会无情地落空。偷喝指甲盖大小的弟仔的西洋牛奶粉被发现而被骂;心心念念盼来的白袜仔因没看顾好弟仔而被阿爸用剪刀划坏;想去稍远的地方看王丽珍坠楼的大新百货上的电梯中途却发生意外;想骑一下阿爸从日本社员那里顺来的“丰田”脚踏车却在巷口摔倒;梦寐很久的校服裙衫得而复失。在我看来,这一细节是小说中最残忍的笔墨之一。其中固然抒发了对阿玉的残忍,却也不乏对阿姊的残忍,更有在此两种残忍之间,对于人性拷问的残忍。
当小学肄业,为了负担家计而早早去上工的阿姊在阿玉入睡之后,最后一次穿起她旧日的学生衫时,对于自己昔日及今后的命运,会生出怎样的感慨?在阿玉日以继夜的期盼中,透露出的是已经失去期望的阿姊的心情。然而,阿姊在第二天却落水而死。因必须提供死者生前穿过的衣衫,这件承担了姐妹二人希望的学生裙衫作为惟一可供日本道士招魂的道具而被毁坏,王聪威再一次以其雕琢细节的能力,将衣衫的毁坏写得一波三折,缓慢,却足够让人疼痛。当阿玉望着那被毁坏的学生裙衫时,想起阿姊前一晚和她说过的悄悄话,想起自己那点不满阿姊将衣服送给她后还偷偷试穿的小心思。在这里,究竟是失去姊妹的悲恸大一些,还是生命中难得可期冀的事终于还是落空的失望更大一些呢?
在《滨线女儿》一书中,阿玉作为绝对的主线人物在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围绕着她的命运,我们看到了她那重男轻女的阿爸阿母;小学都没读完就去上工、后不幸落水而死的阿姊;面目清秀却不得已去给人扫便所的外省仔;总在等待日本情人的马公婆;独自守着大院、芳华一天天逝去的刻薄姨婆;还有那个传说中从电梯顶跌落、漂亮得活像日本人偶的女教师兼富家千金王丽珍;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拉着阿玉一起看相册回忆往昔的疯千金;未曾露面的澡堂老板和他的发迹史;以及在姨婆过身后接管了大院、昙花一现的小姨等等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TA们共同填充、活跃和构成了哈玛星这块地方。这就让我们更能够理解小说的结构,而阿玉正是小说中哈玛星的最后一代,作为后辈的她有责任也有义务记录下故土的历史与变迁!
《滨线女儿》读后感(三):你好啊,滨线女儿!
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每一个人在小的时候都会沉浸在“东家院进,西家院闯”的愉快氛围中,那是独属于童年的美好回忆。那个时候邻里之间的关系胜似亲人,不像现在邻里间“冷淡”。(现在我家邻居每次在电梯里碰到都装不认识,也因此不好过多的打招呼~更不用说现在有些小区独门独户,不能川串电梯的隐私化设计~) 而在这部经典的新乡土文学作品《滨线女儿》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大院生活的酸甜苦辣;见识了那个时代人性的复杂与生活的艰难困苦;也借由一位位登场的女性凸显出历史情节,彰显出在战后那片土地的人们最真实的生活百态和人生态度。
作者王聪威其实,《滨线女儿》是作者王聪威献给母亲家长的一部地地道道的乡土回忆录。书中不仅再现了哈玛星人间百态,更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来深化这个故事的主题。 作者通过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角色的刻画,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展开详实的讲述了太平洋战争前后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种种,细数了那个时代的前尘往事。书封及内页滨线,这个曾经最忙碌的渔港,是台湾南部现代化进程最早的缩影,因为繁华的进城吸引了众多人前来。但是伴随着战争的落幕,军队的撤退,越来越多的人跑来避免,又因为政策规划滨线的市中心东迁,以往的繁华之景消失殆尽,当地人看着家长发生的聚变,在感慨的同时也无从心力去改变。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为我们娓娓讲述了一部感人肺腑的电影,让我们再见证战争对人的残酷的同时也为战后的滨线增填了一份温暖,在作者王聪威笔下那些下的人、留下的痕迹,都构成了一副隽永的画卷,永远停留在历史长河中。 在作者笔下,我们认识了女孩阿玉,她一心宠爱弟弟,但是却由于父母的偏心,家境的贫寒遭遇到了一系列“不公的待遇”,她经常幻听到街角巷头的铜罐仔人喊她“收婴仔”,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是刻入骨髓的嫌弃,正是童年的遭遇造就了她日后的性格。(看到这里,我条件反射的想起来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忙而被同学们说是收破烂捡来的孩子,那种难以遗忘的自卑感,真的让人很难受)
字体设计的很有创意所以,阿玉的那份痛苦我真的深刻的理解。作为线索人物的阿玉从一出场她的地位就以及便被作者刻画的无比清晰,她只是因为偷喝了弟弟一丢丢的奶粉而被母亲责备的狗血淋头,甚至被母亲指责心狠毒,说她是想让弟弟饿死。更不用说,后期她那些卑微到尘埃里的小愿望,作为一个小女孩她渴求的不过是同等年纪女孩再正常不过的白袜,校服衫,但在阿玉这里一切的获得都自动加上了筹码,变成了父母给予她的“馈赠”。作者的每一个字符都在彰显着命运的不公和对人性的拷问。 生活对阿玉是残忍的,但是对阿姊来说又何尝不是呢。当看到作者描写衣衫被毁的片段时真的感受颇深。作者深入浅出的描述,联合前面所表达的悄悄话,更加深化了阿玉的悲痛。衣服虽然被毁坏,但是又怎么能敌的过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呢?在作者细腻的笔下,写的是悲痛的故事,但刻画的却是时代的缩影。
推荐语录在这里有重年轻女冥顽不化的父母;有意外落水而亡的阿姊;有相信爱情,独自守护的马公婆;有性格大大咧咧,独守空房,假意收租的姨婆。小说里诚然还有很多人物的出现,每一个人物都有血有肉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每一位人物都经历了时代所留下的烙印,她们经受住了女性之苦,她们完成了从小女孩到老婆婆的跨越。故事波折起伏,情节颠荡,每一位读者犹如看了一部电影一般,笑中带泪地领略每一个人物的风采。
排版也细致这个故事是作者基于对历史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的转述,作者在个人情感和细腻的叙事笔法之间进行了完美的融合与平衡,使得让这部作品不仅保存了历史源头的追溯感,还呈现了那段历史后最为真实的温度,作品的问世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跨度,是写给那个时代,写给所有人一部难以遗忘的赞歌!
《滨线女儿》读后感(四):高雄乡土志,鼓山儿女情
打开《滨线女儿》,不见“滨线”,扑面而来的是“哈玛星”——让人恍惚误入一出太空歌剧。不要怀疑,这绝不是一本悬于空中的奇幻书,而是一卷闻得到泥土清香、鱼市微腥,早市里飘出炸粿、番薯煎、咸汤圆的香气的乡土故事。在走进台南寒冷的深夜前,首先,我们需要厘清“哈玛星”与“滨线”的关系。
哈玛星在台湾名气很响,现在的“哈玛星铁路文化园区”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景区,但这个有些奇幻色彩地名的来由,即便是当地人也很难说上来。
哈玛星铁路文化园区哈玛星最早指的是台湾高雄鼓山港边的一块七万坪(大约23万平方米)的“海埔新生地”,历史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初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日本人为了修筑铁路、码头、街市用地而填海造陆,这片土地在当时包括了新滨町、凑町和寿町。当时,从新滨町港边至渡船头边的鱼市场,有一条专为转运鲜鱼的滨海铁路,日本人称为“滨线”(发音:Hamasen),渐渐地,当地人便以“哈玛星”来称呼这片区域,今天的哈玛星也泛指南鼓山地区。
在历史的大叙事中,二十世纪初,哈玛星因为街道宽广、海陆便利,见证了高雄港现代化发展的滥觞,上世纪二十年代,哈玛星更是成为了高雄市最早的行政中心,但对于王聪威,哈玛星的特别有一个简单的理由:这片土地是他母亲的家乡。
哈玛星铁路文化园区哈玛星的历史十分复杂,但《滨线女儿》这本小说并不是这段历史的解说,也非滨线风光导览——正是这段特殊的、有记载的历史让这部具有私人意义的虚构作品踏上一条并不容易的道路:如何面对历史、重述历史、超越历史,叙述者如何在历史的大河里取出属于自己的一瓢,这些都是《滨线女儿》在编织书中这段时光时遇到且做出尝试的问题。
“只要能买齐有关会社员的一切,那又何必花费日夜期盼他的心力呢?”
作者王聪威是现任《联合文学》杂志总编,他是著名的杂志人,操刀过时尚杂志MarieClaire、FHM,让《联合文学》这样正统的文学期刊面貌翻新;他也是很有建树的小说家、诗人。《滨线女儿》是他的小说代表作,出版伊始即获《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奖”,并位列去年年底《文讯》杂志评出的“最耀眼”台湾七零后作家作品之列。
《滨线女儿》透过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角色的视角展开,讲述了太平洋战争前后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二十世纪上半叶,滨线地区工商业繁荣、机遇无限,吸引了诸多背景各异的人来此逐梦。随着战争的结束,日军战败撤退,外省人、外地人跑来落脚;因为市中心东迁,滨线渐渐繁华不再,当地人被迫面对家乡的疮痍与没落,个体的命运则好像凝固在战争留下的痕迹里。
王聪威王聪威对这些留下的人、留下的痕迹的叙述,为残酷的战后滨线故事添了一些温度:
杂什仔郎们耐心倾听她诉说会社员的个性、喜好与细微的心情,于是第一个杂什仔郎给了她会社员惯用的发油,以及一套猜想他必然爱穿的灰色条纹英式内衣裤,接着另一个杂什仔郎挑了一件洁白直挺的衬衫、一条藏青色英国毛料西装裤、一对镶了绿水晶的袖扣和一双正统小牛皮鞋,一个杂什仔郎则卖她机械表与一条苏格兰格纹领带。他爱吃的天妇罗差不多快炸好了,然而等待的同时,有人劝她将买了的威士忌换成葡萄酒,并叫她替会社员玩了一次猜甘蔗节的长短,有点不怀好心地偷偷改变了他不苟言笑的模样。“这样便差不多是他的全部了吧……”她想只要能买齐有关会社员的一切,那又何必花费日夜期盼他的心力呢?然而,这些年来她几乎未曾想起他了,或许有什么片刻曾经记忆起,不过她总是忙于日常平静的生活,对于他的事便不再放在心上。但就是有那样忆起的时刻,也使得遥远异国的会社员忽然有了片羽闪光的感应:“我是否忘记了件什么事呢?”要买来一个人的模样和动态,听来是要让人落泪的,可在以上文字里,这种可能性、这场买卖让一场被战争拆散的、若有若无的浪漫变成裹挟着市井气的悲欢离合。悲情被一件件商品、一句句笑骂冲散;分别的时间久了,追忆成了习惯,追忆的对象也失去了具体的容貌,成为一个远方的符号。人对人的感情如此,王聪威表达的对故乡和历史的态度也是一样。
书中的哈玛星人间百态,如一部镜头静止的长篇电影般展开。我们看到女孩阿玉,尽管疼爱弟弟,却因家境窘迫、父母偏心,幻听到街角巷头的铜罐仔人喊“收婴仔”,而非“收锡仔”;马公婆曾与日本海员生情,可是战事紧张,情人返乡,留下她一人独守会社员宿舍;姨婆作为大院的收租婆,整日骂骂咧咧却好像并非真的在意租金,她也曾是千金小姐,但在一个空袭的下午被所有人遗忘后,性情大变……读者如坐在观影席上,笑中带泪地读完这些人物的长卷。
“或许即使没有了她, 他们还是能够继续生活下去。”
尪婿忙着和囝仔打闹,只是嗯了一声,没再与她说话。她到房间的床顶躺下,拉上了遮阳的布帘,房间里有种清淡的光亮感,带着一点点的阴影。有点微微烘热的感觉,但是她扇了葵扇,就清凉了许多,不觉得燥热。海洋的风吹到岸上来,带点咸味,透风良好的大院,好像拥有自己的风可以吹。在她仍醒着的时候,她又唤了尪婿一次,要他赶快来自己的身边。她想要在睡前,在这个偷来的时光耗掉之前,与他搂一搂,说说家里的事。今天早晨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大院里的事,她想跟他说个两句。在饭桌上,她没能插嘴他说富源行的事,也没能插上他和囝仔的打闹游戏,在这个偷来的时光,她希望能轻声细语跟他说几句话。无邪地说几句话,她脸红红的,她想总不能午觉的时候太亲热吧。但是尪婿没有回话,只听见他们父子俩还在玩的声音。在文学史中不乏男性作者塑造的女性故事,而女性作为叙事主体也越来越常见。当我们面对现当代文学中的女性角色时,难免不去想眼前的女性——母亲、妻子、女儿——是不是一张张被涂上夸张色彩的脸谱,如果没有那些来自刻板印象的描写,那我们便会松一口气。比如著有《妻妾成群》等作品的苏童,大家常称他为“妇女之友”,原因是他写了许多以女性视角来叙事的小说,讲封建家庭和现代家庭的婚姻生活、女性之间的各种关系、女性在社会中的体验等,这些小说往往没有男性作家的“鬼影”,没有女人就要惹人生怜,或是写女性就要把她们塑造成“大女人”的思维定式。苏童的女性故事脱不开现实中的女性要切实面对的各种难处,但这些苦难被作者细腻的文笔和心思转化成看似祥和的风景中一次次无法回避的波澜;起伏之后,生活继续。
王聪威的滨线女儿们也承受着时代的女性之苦,肩负着去标签化的女性创作这样的任务;作者还要完成从小女孩到老婆婆的跨越,去理解、重写她们各自的体验和反应。引文中的“她”就是大院的主人姨婆,尽管今日的姨婆是大伙避之不及的、絮叨甚至恶毒的收租婆,年轻时的姨婆也曾向往午后温热暧昧的羞涩时光。至于姨婆是如何失去这份少女烂漫的,王聪威只告诉大家,这天下午有轰炸,只有姨婆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丢在家里,其他人都逃去躲炸弹了:
她觉得眼前一片黑暗,好像空袭警报的开始与结束之间,是一段空白,而她被这些人给抛弃掉了。一时之间,她好像忘了这几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未来要怎么活过去。或许即使没有了她, 他们还是能够继续生活下去。其实现在大院的租客也几乎不按规矩给租金,姨婆多数时间也在屋里,偶尔出来嘴上不饶人几句,而大院里家家户户都还算安定地住着,只有关于姨婆的流言一直在飞。姨婆是被抛弃的人,她也认定了自己将会永远被抛弃。
姨婆的形象不是一个可怜的前千金小姐,也不是一个可恨的刻薄收租婆;她不是一个单薄的女人,她是一个早已失去生命的顽强生命,好像活着只是为了抗争所有抛弃她、鄙夷她的人,抗争她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命运。
书中另一位角色马公婆(她在稍前的引文中向杂什仔郎购买与情人会社员相关的物品),第一次看到哈玛星时,城楼上“云霞斑斓相连,像是逆流的虹瀑”,多年后,“她还以为此处的事物将永远不变”,但其实全都变了样。情人离去,留她一人拖着一车杂什走向看不见的未来。王聪威把马公婆前半生的爱恋藏进她后半年一趟趟搬运自己数不完的杂什里,藏进她偶尔想起过往的光景里。时间留给她的只有一车车的物品,记忆也依赖这些物品,不然就会全部跑走。
这样避免让全书浸润女性化气质的尝试让读者不会过分共情于某一个女性角色,以至于忽略了作者想要构建的更宏观的叙事。王聪威的文字细腻、温暖、哀而不伤,透过多样的女性声音,绘制了一个战后的小世界,这里失落与温暖并存,历史与当下斗争,个体与家庭命运的起伏被更厚重的社会的命运所笼罩,个人的挣扎也由此被赋予了悲凉与无奈的色彩。
每一个脆弱的美丽的名词,都收于此书中
王聪威的《滨线女儿》献给他母亲的故乡,读来也仿佛是献给每位读者心底的故乡。这依靠的不是滥情的书写,而是对素材理性而精心的处理,以及对虚构这一文学种类的老练掌握。
《滨线女儿》中,王聪威实验了文白夹杂的行文,对一些闽南语词汇的保留捕捉了滨线最生动的过往,既让读者更沉浸于他细细勾画、虚实相间的故事背景中,又传递了作者对这片土地、这段时光最深情的敬爱。在文本内容上,读者似游一间哈玛星博物馆,看得到街头的摊铺,美国人、日本人留下的外来品,孩子们的游戏,普通家庭里的家什,都有些破旧,却带着岁月和市井的温度。这样的细节一方面传递了滨线彼时的世情、人情,一方面也使我们慨叹战争给这个小小地方带来何种翻天覆地的改变。这样的文本特点让人不禁想起金宇澄的《繁花》,虽然后者讲述的是上海故事,但两者都在语言上做出尝试(将沪语选择性地书面化),在对环境、氛围上的刻画也极尽详细、生动。金宇澄对《滨线女儿》做如此评论:“饥饿、匮乏、惊恐、迷失……这是王聪威为‘滨线女儿’们书写的战后人物志——她们的情感与形象、她们的隐忍或爆发,汇成这部有关命运和创伤的历史寓言。”当我们浏览滨线女儿们的人生时,她们的个人故事组成了一幅特殊而有力的群像,以此为背景的关于创伤和复原的寓言,则展示了在灾难中和灾难后,人如何拾起和挽救自己被压抑的主体性,而个人主体性复原的过程又如何复原了由他们组成的社会。
作为一部“新乡土文学”作品,《滨线女儿》展现了“溯源”和“重写”这两者间的平衡。王聪威在小说中展现了恰到好处的克制。这种克制源于作者在文学创作上的训练有素,同时也源于作者本身和这段往事、这个地区之间的距离。王聪威在小说后记末尾写道:“我多希望秋兰阿姨能够永远快乐地在这里,照看她最爱的哈玛星,并化身岁月人情飞逝的滨线女儿故事里,我深深亲爱的一页。”王聪威把温情毫无保留地献给这篇后记,献给母亲的朋友秋兰阿姨这位真实的滨线女儿,却没有让温情成为整部小说的基调,使其变成一部传记式的作品。王聪威曾在一篇自述中提到自己对于“各种写作技术和美学主张”的热情,他对家乡故事的个人情感不会吞噬他对技巧和风格进行实验的持续欲望。滨线女儿们的故事是基于历史的转述,而历史与作者的特殊距离,以及作者在个人情感和叙事笔法之间的平衡,让这部作品不仅保存了历史较为真实的温度,更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得以成为一部写给所有人、所有时代和地区的往事之歌。
作家周嘉宁对《滨线女儿》的读者们给出这样的建议:“为了不要迷失在时间的迷雾中,也为了找到陆地的闸口,请一定放慢阅读的速度。因为洪流来临时,每一个脆弱的美丽的名词,都被滨线女儿们一再捕捞,编织和守护,收于此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