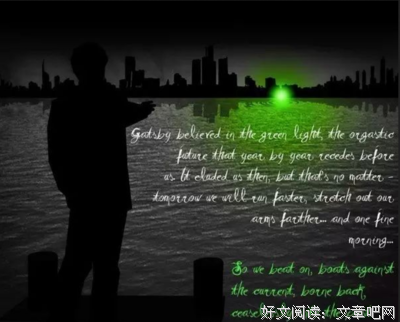《追寻“我们”的根源》读后感1000字
《追寻“我们”的根源》是一本由姚大力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9.00,页数:5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追寻“我们”的根源》精选点评:
●本书包括作者对蒙古族(元)、满族(清)、回族、维吾尔族等几个民族在历史上的认同变迁的追溯,兼评新清史学派以及拉铁摩尔和以赛亚·柏林的一些观点。从上述这些层面,作者构建出一幅作为民族国家的认同图景,尤其强调其中的多元性。
●本以为是部专著,结果是文集,略失望。字里行间似有替官方背书的感觉。为什么美国“熔炉政策”在贵国行不通呢?不解释就这样断定有些武断吧。
●可别名「吐哺集」,书评结集。读来似懂非懂。注外文书为什么不出原书名,又没有附参考文献,照现在半通不通的译名,如何复按?页90注2,胡春惠作“胡群晖”、“李达嘉”作“李大嘉”,还是隔行如隔山呀
●姚老师有时候不得不叼飞盘
●书评、访谈及部分已刊论文结集出版,导致内容彼此重复太多。对国家观念史述评的一文相对比较完整,可以细看。其余浏览而过。对民族问题不乏尖锐看法。
●后面就挑着读了
●重复的内容有点多。
●我的认识是,民族与国家认同总是强制性的。
●本书是论文集,最初读到的是《上海书评》上的几篇文字,觉得精彩。全书读毕,汉唐、内陆边疆两种国家建构模式的创见,传统的族裔认同、伴生性原民族主义与政治认同的区分等论述固然精彩。但更让我敬佩与感动的,还是姚先生那种书生式的、作为民族史研究者的关怀(作者是江南的汉族)。“怎样在统一国家的宪政框架下,让这些历史地属于各民族、各人群的世居家园都获得富有各自独特性的发展。这是中华文明史留给当代中国人的一个无比重大的问题,一个考验他们良知和政治智慧的问题”。
●字里行间透露着强烈的现世关怀
《追寻“我们”的根源》读后感(一):元朝依然是个迷
大部分篇目都不错,但因为是集子,核心观点——中国的两种建构模式,外儒内法的专制帝国和内亚边疆帝国的论述重复太多。 除此之外,对元朝是否中国的论证感觉不够有力。按照作者的观点,元朝大部分领土、人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今日中国域内,以及元朝统治集团族裔属于今日中华民族组成部分之一,是两个证明元朝属于中国的有力证据。按照这种逻辑,就会遇到那个很棘手的问题——岳飞、文天祥为代表的“民族英雄”,他们的“民族”主体性如何界定?如果金、辽、元等少数民族政权都毫无疑问地代表中国,那么抗击外族入侵的历史叙事如何自圆其说? 这种“国家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带来的复杂性,似乎作者本身也没有完全理清。 与元朝情况相似的清朝,这种复杂性因为清朝统治者明确的中国正统认同,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而元朝统治者,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国”概念,也没有以中华帝国继承者自居的明确表述。至少从本书,还是没能解除元朝与中国关系复杂性的疑惑。
《追寻“我们”的根源》读后感(二):民族观点与双轨制治理
历时一个多月,兜兜转转终于看完。虽然是一本论文集,但几乎做到了篇篇出彩,本书新在民族性,新在在吾等非主流民族视角来看待诸多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触碰点(姚老师真是很有想法且敢说)。
以前读罢姚老师和袁剑老师关于拉铁摩尔的文章,破除了在汉地所受教育中的中原迷思,能够直视吾族所处之内亚。现在读完这本书,对儒学的地位的相关思考因而产生。儒教在内地的统治作用尚有彰显,可是放诸内附外藩,效用几乎为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王朝的疆域控制能力与汉唐软弱涣散的边疆治理形成鲜明对比,究其缘由,还是前者因时因势治理的变通式治理能力较强,能够巧用本地资源并因势利导,而非一味强力推进汉化,强迫统一式治理。读这书的时候,脑海中多次回想新清史对于清朝推行的内地的儒教与外部藏传佛教的双轨制治理模式的多次探讨与言说,(借用双轨制一下哈哈哈)思虑良久再结合这本书的主旨意识,豁然开朗的同时,对这种模式有了更深的体悟。
《追寻“我们”的根源》读后感(三):追寻“我们”的根源
作为世界范围内罕有的既非由中世纪帝国分裂而出亦非由殖民帝国独立而成的现代多民族国家,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往往存在着诸多因照搬西方概念而导致的误区与迷思。本书姚大力对中国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思考的文集,分别从 “中国”观念的历史根源、诸多民族在“中国”建构中的作用、蒙元汉三者关系、部分少数民族族群认同与民族形成四个角度追溯与梳理该问题上,形成本书的四大部分。如果说只有认清自己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那么本书将有助于中国在现代世界中探索出一条更适合自己前进的道路。
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史上的族群及国家认同 姚大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1/69.00
子扉我 2018年春 申城西楼
原载季风书园微信2018年3月20日
《追寻“我们”的根源》读后感(四):姚的观点是汗八里需要的,但汗八里的百姓未见得能容他
作为一本文集,此书在论点和论据上重复都过于多了,编辑是要负责任的,作为读者,跳跃着看就好了。
总结下来姚大力的观点主要是以下几个:
1、一手反皇汉主义,一手反满蒙非中国论。事实上姚大力也同意在欧美和日本的学界并没有多少学者真的认同满蒙非中国,这个靶子其实是一些党务工作者自己竖起来打。2、认为早期民族主义有相当大的民主主义成分,而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应该导向这一点(进而解决汉与非汉族群之间的张力)。3、民族主义不完全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也不是“纯粹想象的共同体”,当一个特定的精英群体想要发明一个民族的时候,必须从相当多“客观存在”的“前民族要素”中挑挑拣拣,再缝缝补补,最后制造出新的民族认同来(讲回部和回回都提到了)。实际上这种立场正是当下的汗八里需要的。但是当下的汗八里自身正在越来越快地抛弃它从清帝国身上继承的内亚智慧(对多元认同的包容),转向一个基于汉族的民族国家。高铁、飞机、现代医学、现代农业、互联网、金融等技术加强了中原政权对拉铁摩尔线以外地区的控制,所以汗八里的这种变化趋势可能会加速。
与此同时,汉族民众可能也不再会容忍那些包容多元认同的言论了。所以,姚大力在知乎被喷是毫不令人意外的。
《追寻“我们”的根源》读后感(五):历史如何照进现实
上个月老友来泉城考试,多年未见,自然要把酒言欢一番。伴着咸到发齁的饭菜,老友跟我说了些做学术的苦恼,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不知道现在所做的研究能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老友目前是做元代文学的,他说的现实意义自然不是将成果转换为现实的利益,而是说元代文学研究如何能关照当下、对今天的中国产生影响。我一时语塞,因为我一向反对在严肃史学研究中直接代入现实因素,我并不认为,在严肃学术著作中将古代兴衰与现实相联系,与「儒法斗争」、「古为今用」时期的文章有多大区别。我当时举葛兆光的例子与老友说道,你想将研究与现实相结合,不妨在学术著作之外多写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评论性文章,这样既保持了学术著作的严肃性,又可以发挥己见。我当时并未提到姚大力教授,倒是老友 提到了姚教授的新著《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三联书店,2018年),并认为此书完全是在为当局服务。
姚大力教授在2016年和2018年分别推出了两部新书,《读史的智慧》(修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追寻“我们”的根源》。二者都是文集,前一本基本都是书评,主题相对松散;后一本则是专业论文与书评结合,主题相对集中。从前一本的书名就能看出,姚教授主张从历史中找寻智慧。后一本虽然无法从书名看出端倪,但看完全书,能明显感受到作者从历史与传统中找寻现实解决之道的取向。
《根源》一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何为‘中国’””、第二部分“‘中国’的多样性”、第三部分“换一个角度看元朝”和第四部分“民族认同与民族形成”。实际上,这四个部分都是在谈论一个问题——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来源。前两部分都是以历史学为基点深入当下,谈论民族多样性与当代中国的;后两部分则以严谨的史学方法梳理了前现代时期满-蒙-回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
后两部分使我获益良多。在阅读此书之前,我对民族与国家的形成理论认识深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影响,以“想象的共同体”来看待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这当然是没有错的,但若不去深入讨论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得以成形、发展以及扩大的历史根源,仍旧不能解释现代民族的起源的原因与机制。可以说,姚教授的文章对这一原因与机制形成的历史根源——即“想象的共同体”的基础做出了十分完美地梳理,我认为这是本书最为重要的成果与智慧之一。
而对当下的民族政策问题,姚教授的立场与主张也颇值得玩味。姚教授在两本新著中多次提到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他的民族主义观属于格林菲尔德所归纳的“英国式民族主义”,即主权在民,保障疆域内不同身份的人民都享有基本平等和自由,这一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民族主义与争取个人自由、脱离王权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姚教授的立场显然并非一时兴起,从收入《智慧》一书的对于约翰·密尔《论自由》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英国式自由主义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并且很大程度上赞同英式自由主义。
对于自由、民主的认同,很自然可以推导出对于多元主义的认同,这是姚教授另一主张——即主张保存各民族的民族特性,反对推行美国熔炉式“均质化”政策——的思想来源。我想,因为“美国熔炉式”这样的字眼,很容易让人觉得姚教授采取的是一种反对美国反对西方的立场。事实并不如此,姚教授所反对的应该是以民族学者马戎为代表的主张取消自治、推行共治、消解民族特性的作法。实际上,这种政策是否可以称为“美国熔炉式”也是可以怀疑的,美国熔炉式政策并非是自上而下强行推行的政策。
姚教授对多元格局的认同伴随着对一体格局的坚持,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传统的“大一统”史观所致,还是因为数十年来对历史特别是蒙元史、民族史的研究,使他坚定地认为只有一体格局才能发展。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式智慧,对未来的预言无论多么精准,在未来成为历史之前都会被人看作神棍学。所以,这里就不对这一观点多作评价。
正因为历史提供着经验式智慧,我从姚教授书中读出向蒙元-满清传统寻找解决之道的倾向,大概不算误读。然而就像当下某些学者向孔孟之道找寻思想资源一样,从成功解决多元格局的内亚性帝国身上找寻经验是否可行?历史智慧的现代运用不能脱离语境,这包括历史的语境与现实的语境。历史语境不必多说,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蒙元-满清时代都与当下有质的差别。现实语境也是如此,仅从中国而言,20世纪50年代进行民族调查时采取斯大林民族的定义,其渊源识者自知;与此同时,列宁主义式政体的动员-组织能力更是蒙元-满清政权所不能比拟的,而它们之间的治理逻辑自然差别甚大。因此,从旧帝国的经验中找寻解决之道大概是不可能成功的。
至此,再回到老友的问题。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仍旧不是那么容易实现,从历史中吸收个人的处世智慧相对容易,想籍此探寻现实解决之道却是异常困难的。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循环,但会押韵”,押韵总归是押韵,而不是复读。此外,还需要澄清开头预留的问题:这本书是在为当局服务吗?显然不是,当我们抛开民族视角来看,英国式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有何区别?与其说姚教授的主张是基于历史视角的建言与献策,不如说是一个自由多元主义者的无奈与瞻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