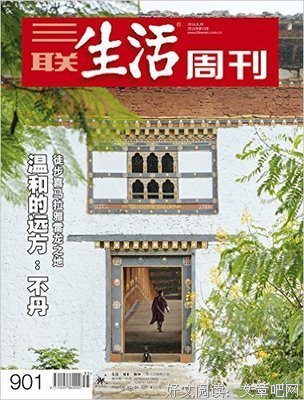第三极的馈赠经典读后感有感
《第三极的馈赠》是一本由[美] 乔治·夏勒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第三极的馈赠》读后感(一):回报--第三极的馈赠
看过几本夏勒的书,听过老爷爷的讲座,高大的身材,深邃的目光,这一本收入后,读了个开头,觉得十分好看。
里面感谢他妻子的部分,让人感动。中国人好像很少这么表达对妻子付出的感谢,在他来看妻子对他的照顾和付出是一笔非常丰厚的财富,话里话外充满了感激。
接着在看藏羚羊这一章,雪灾的开头让人揪心。虽然见到了大规模的羊群,但是公路沿线的尸体很扎眼,可以看出作者的情绪已经很不好了。
没看完,看点儿再写。
《第三极的馈赠》读后感(二):乔治.夏勒:严肃的科学家和忧郁的诗人
乔治.夏勒:严肃的科学家和忧郁的诗人
作者:佚名
去年下半年,我在出去旅游时碰到几位美国游客,为了锻炼自己蹩脚的英语,便跟他们东拉西扯地闲聊起来。闲话中,偶然提到乔治•夏勒博士,我说:他在做研究的时候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家,可当他提笔写作时,却成了一位忧郁的诗人。听了我这句话,几名美国游客张大了嘴,作了一个夸张的惊讶表情,同时暗示自己没听说过夏勒博士。
也难怪夏勒博士在美国普通民众中知名度不高,在最近三十来年里,他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亚洲,尤其是青藏高原一带。可以说,如今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和一些主要物种能得到一定的保护,都跟他的研究与努力有着莫大的关系。如今老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仍不顾高原环境恶劣,坚持到野外做研究。
从那次出游回到家中没几个月,夏勒博士的新书《第三极的馈赠》出版了,约略算来,这好像是他在中国出版的第6本科研和科普作品了吧,在主题上也多多少少跟以前的几本书有些联系。
但是,不同于前面几本的是,这本新书用更多的篇幅,更加详尽地介绍了他近二十几年在青藏-帕米尔高原一带的多次考察,从他为挽救藏羚羊而一次次远赴高寒无人区考察研究的羌塘之旅,到几度深入藏西南秘境圣地,以及为保护马可波罗盘羊和雪豹,不顾当地局势动荡,而造访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各国。
野外考察充满艰险,研究过程往往枯燥,夏勒博士及其团队经常需要测量和计数,每天都要撰写笔记,但这一切却是获得第一手资料,了解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必由之路。而这些考察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希望改善当地居民与大自然的关系,通过生态旅游之类可持续的方式,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在保护动物的同时,也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凭借这样的研究,以及每天坚持不懈的笔记记录,夏勒博士在与各国研究者撰写出高质量的科研论文之后,还能通过他创作的一系列兼具科学性和趣味性的科普作品,向普通读者介绍他们的科考过程与结果,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
在夏勒博士参与保护的物种之中,最著名的除了大熊猫,大概要算藏羚羊了。正是因为夏勒的野外考察,才发现了沙图什的血腥真相;正是因为他和同行们在亚洲和西方的不断努力,才使得沙图什贸易最终被禁;也正是因为他的研究和呼吁,唤醒了根植于藏人宗教意识中的护生观念。如此,藏羚羊的命运方才得以暂时扭转。
但他关心的不单单是这些大型旗舰动物,他也曾为青藏高原上一种长期受到误解的小动物而呐喊呼吁,那就是小小的鼠兔。在他涉足青藏高原之前,有相当一段时间,这种小动物都被一些部门当作导致草原退化的替罪羊,而遭到大规模毒杀。是夏勒博士发现了它们对高原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竭力阻止这种屠杀。
在《第三极的馈赠》中,夏勒博士不仅以妙趣横生的文笔,讲述自己在青藏-帕米尔高原上的科考与研究,而且也在“野性难驯的博物学家”一章中,提到了自己早年的一些经历和趣事,例如他怎样在少年时代从“二战”后的德国来到美国,怎样以令人艳羡又令人发笑的方式,入读阿拉斯加大学,然后抓住一切机会发展自己对博物学的爱好,最终得以进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以及他随后在世界各地进行的各种具有开创性的研究。
(tbc.)
《第三极的馈赠》读后感(三):心灵的馈赠
我先直接说几句,这本书手记不像那些偏重人文纪实的游记,更多的是野外考察纪实,是本流水账。书中第五章是我最喜欢的章节,写了作者对自己人生选择的思考,还有对甜水河一带产仔地新生与死亡并存场景的细致生动的描绘。另外书中对荒野的体验描述我也很喜欢。如果你关注野生动物保护、关注自然生态保护,这本书我想会带给你启发和思考,甚至会带来思维或观念的转变,如对鼠兔的认识。
乔治•夏勒博士与我想象中的博物学家不同,如他自己所说,“在研究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过程中,保护这些研究对象渐渐成为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确切的说,成为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于是我不再像传统的实践型科学家那样,全心全意地专注于发表满篇数据和图表的学术论文及专著,不管那有多么重要,我仍是将工作重心转向宣传生态保护的必要性。我开始追问自己:‘我需要掌握哪些情况,才能更好地保护及管理自然栖息地上的这种动物?’(第193页)乔治•夏勒博士认为,“博物学仍是自然保护的基石,必须脚踏实地去完成,去提出问题,用心观察,聆听,记录,亲自走进荒野”。(第116页)。在这一思想的驱动下,我们看到了乔治•夏勒博士一次次长期野外考察,看到了乔治•夏勒博士积极推动一个个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本书主要谈论的保护对象是藏羚羊。作者第一次见到藏羚羊是1985年,1988年开始追踪藏羚羊,寻找藏羚羊的产仔地,经过1992年、2001年两次追踪,终于在2002年在绍尔库勒湖南面的山丘上,看到雌性藏羚羊以及二十多只新生幼仔,由此确定了藏羚羊羌塘西部种群的产仔地。在2005年,作者进入绍尔库勒湖藏羚羊羌塘西部种群的产仔地进行观察,并提出保护建议。在2007年作者去羌塘中部种群的产仔地甜水河一带进行观察,详细记录了新生与死亡并存的情景,其中新生过程的描绘的详细又动人,作者自己动情写道:“这一幕超越科学,唤起温情,触动我的心。它更巩固了我许下的誓约,一定要帮助藏羚羊生存下去。”(第121页)
藏羚羊产仔地的发现也就意味着保护措施可能因此进一步升级,比如建立保护区之类的措施,但作者也清醒认识到:“建立一个保护区是项相对简单的行政举措;要有效维护并管理这片保护区,则是一项长期工作,永远没有完结的一天,因为环境会不断改变,新的威胁也将随之出现。”(第77页)例如“公路伸进它们的领地,开矿和石油勘探造成破坏,牧场被围栏圈起,以及过度放牧和气候变化导致的草场退化”。
在历经2006年从拉萨出发穿越大羌塘之行后,面对上述等问题,作者写道:“环境管理实际上是人的管理。要让野生动物与牧民相安无事,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和谐的生态环境,那么,就不能对当地人忧心的问题视而不见。解决问题从来没有简单的方法,总归需要采取综合手段,而不是毒杀鼠兔那样的单一方法。让当地社区全面参与规划、实施管理,生态保护工作才有可能成功——如今这已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第190页)
最后再摘录一句书中话作为结尾:“看到这么多动物延续着古老的生活方式,似乎并未受到人类的干扰,这无疑是份心灵的馈赠。”
《第三极的馈赠》读后感(四):荒野追羊者
美国博物学家乔治·夏勒第一次看到藏羚羊,就被它们的美迷住了。那是1985年10月一个寒冷的日子,这群生灵奔跑在青藏高原,轻盈灵巧。从侧面看,它们犹如传说中的“独角兽”,头上的角分外纤长。
当时,一场针对它们的屠杀正在发生。藏羚羊拥有世界上最细最软的绒毛,帮助它们抵御海拔最高的寒冷。正因为这些绒毛,它们被大量猎杀,尸体腐烂在雪域,血淋淋的皮毛被走私到克什米尔和印度。由藏羚羊毛织成的“沙图什”被销往世界各地,披在名流的肩上,是财富和优雅的象征。
在此之前,贩卖沙图什的商人一直谎称原料来自于西藏北山羊,购买披肩是帮助穷人改变生活的善举。直到1992年,在西藏进行自然考察的夏勒才发现两者间的血腥联系。一块沙图什披肩,背后是3只藏羚羊的尸体。夏勒粗略统计过,20世纪90年代,至少有20~30万只藏羚羊被猎杀。
美国《时代周刊》曾把夏勒评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在到达青藏高原之前,他曾在非洲高原与大猩猩同眠,在印度半岛的树上观察野生虎群,在四川卧龙救治大熊猫。
“去了解一个没有遭到人类破坏的地方,这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在《第三极的馈赠》里,这位博物学家写道。1984年,夏勒得到中国政府批准,进入羌塘无人区研究考察。
那里生态美丽而脆弱。一场偶发的气象灾害,都会给当地野生动物带来沉重的打击。而牧场的围栏、贪婪的子弹,更会给它们带来灾难。
“要保护一种动物,首先就要了解它的动向。”为了寻找藏羚羊的产仔地,也是它最集中、抵抗力最弱的地方,夏勒坚持了17年。在追踪路途中,他还要应付怎么都使唤不顺的驴子,随时罢工的卡车,没完没了的暴风雪和一些对研究缺乏热情的工作伙伴。
在野外笔记中,他记录过夕阳中藏野驴的黑色剪影,雪豹留在雪地上的圆形足印。母棕熊、狼、公熊组成古怪队列,几千只黄羊越过一道山岭。一只浑身湿漉漉的小藏羚羊还不会站立,两千只南下迁徙的藏羚羊群,夹着几百只刚出生的幼仔,犹如一片粉红色的云。
美好夹杂着残酷。22具被剥了皮的藏羚羊尸体横陈在一个猎人营地,失去母亲的幼仔在草原上无助地叫唤。毫无戒心的褐背拟地鸦突然在枪声中丧命,一只死去的艾鼬在投放毒药的鼠兔栖息地被发现。
“人类眼看着环境日益恶化,威胁着自己的未来,却仍旧执拗地破坏大自然,撕裂大自然。”夏勒说。
每个物种都是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当夏勒第一次进入青海时,发现鼠兔已无迹可寻。在他眼中,没有鼠兔的草原仿佛“一座死亡之城”。
他从中国队友那里打听到,因为鼠兔是“坏动物”,吃光了牛羊需要的草,挖洞造成水土流失,政府从1962年开始大规模毒杀鼠兔。
夏勒观察后发现,这些兔子的近亲挖洞时,会把底层的矿物质带到地面滋润土壤。坚硬的土壤也得以翻松,能避免板结和水土流失。它们是整个脆弱生态链的关键组成部分。
19世纪末,美国数百万头野牛被冷酷猎杀,剩下幸存者生活在黄石公园。20世纪70年代,草原犬鼠被定了“破坏牧场”的莫须有的罪名。在青藏高原,夏勒不停地问自己:历史将会重演吗?
发现沙图什的肮脏交易后,他撰写文章呼吁,试图将藏羚羊遭屠杀的认知渗透到公众意识里。沙图什问题被提上国际议程,全世界大多数人开始抵制这种带血的奢侈品。在中国,占地近30万平方公里的羌塘自然保护区建成,为藏羚羊的生育和迁徙提供保护。
为了消除长久以来人们对鼠兔的偏见,夏勒编写了12则有关鼠兔的寓言。这些故事被译成藏语制成宣传册,在青海和西藏学校和村庄发放。
“生态保护是一段漫长的旅程,而不是一个终点。”截至2011年,夏勒已造访羌塘26次,在那里累计度过大约41个月的时光。在21世纪头10年,羌塘的盗猎活动显著减少,藏羚羊数量有所回升。
2016年4月,83岁的夏勒再次踏上羌塘。令他失望的是,在超过2000公里的驾车路线和无法计数的徒步旅程中,他只看到两只雪豹,没看到一只藏羚羊。人类的居住区扩大了,满眼都是牲畜。(文/江山)
刊载于中国青年报(2017年06月14日 11版)
《第三极的馈赠》读后感(五):所思至深,所感至柔 ——乔治•夏勒博士《第三极的馈赠》编后
最初知道乔治•夏勒博士,是在纪录片《第三极》中,博士亲口讲述他在青藏高原调查“雪山之王”——雪豹的生存故事。纪录片中,博士和他的调查团队经过一天奔波,发现了雪豹临时歇脚的窝和毛发,确认雪豹出没的具体区域后,就悄悄离开了,“就像不想打扰某位朋友的清静生活”。这位有着敏锐观察力、丰富野外工作经验和慈悲之心的老人,令人印象深刻。
201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启动了夏勒博士的新作、其野外考察手记《第三极的馈赠》的引进、翻译工作,我有幸担任此书的责任编辑,也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这位了不起的博物学家。
《辞海》里说,博物是指“能辨识许多事物”。《现代汉语词典》对博物的解释是,“旧时对动物、植物、矿物、生理等学科的统称”。夏勒博士则把博物学当作是自然保护工作的基石。要想了解自然、保护自然,就必须亲自走进荒野,学习大自然的谦逊和广阔心胸。他常年在野外聆听、观察、记录这颗蔚蓝色星球上发生的生存与死亡、新生与衰老。
从1980年开始,夏勒博士与中国结缘。他是首批受邀参与大熊猫保护的外国专家。30多年来,他每年都会来中国进行野外考察。中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有了长足进步,而夏勒博士也从壮年步入耄耋。
林业部的王梦虎先生曾在夏勒博士初次踏足中国西南时说,“你会跟我们在中国继续合作40年”。夏勒博士以为这只是一句客套话,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年又一年,中国的高原诱惑着他,他无法停下脚步。
对于青藏高原,夏勒博士充满感情。这座号称“地球上的第三极”的高原美丽、神秘,在他眼中,这“最荒凉、最偏远的地方,唯有自己能够依靠,却也摆脱了社会的繁杂束缚,可以自在漫游”。
这片广袤的天地,是人类和野生动植物共同的家园。这里生活着约一万种高等种子植物;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大熊猫、藏野驴、白唇鹿、野牦牛、黑颈鹤、胡秃鹫、金雕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猞猁、荒漠猫、岩羊、血雉、藏马鸡等。这里还是有着高原精灵之称的藏羚羊、普氏原羚的故乡。
青藏高原也是雅鲁藏布江、怒江、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源头,是滋养中华文明的福地,是藏文化发祥地之一,是格萨尔王的故乡。从旧石器时代起,古羌人就与其他动植物共享这片土地。上世纪90年代,夏勒博士和同事曾发现一种大号石刀及刀片的制作技术,可能源自2.5万年前——念天地之悠悠,博士说,一想到自己或许和那些远古猎人见证了同样的野生动物奇观,就觉得神奇和开心。如果今人让这些千百年来与我们相依共存的动植物走向灭绝,就不仅仅是在毁坏现在,也是背叛历史、毁掉未来。
不过,保护动植物,并不等于可以剥夺当地居民正常的生存权利。基于脚踏实地的野外考察和对当地居民、机构和社区的随机访问,夏勒博士及其团队提出,环境管理实际上是人的管理。要让野生动物与牧民相安无事,维持和谐的生态环境,就不能对当地人忧心的问题视而不见。需要采取综合手段,让当地社区全面参与规划、实施管理,生态保护工作才有可能成功。
青海省曲麻莱县曲麻河乡的措池村,就是野生动物保护与当地居民权利保障的一个成功范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子,如今因自发的生态保护行动而声名远扬:村委会与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签订了一份首开先河的协议,自行承担起村中土地的生态保护工作。措池村关心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及村庄的未来,是出于生态认知和佛教信仰,他们知道必须先做合格的自然守护者,自己的生活才有保障。
在从玉树开车到杂多考察雪豹时,夏勒博士看到,当地人出于爱心和信仰,将散落在公路上的虫蛹一只只捡起来,再带到草原深处放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也许,只有具备了这样融入传统和习俗的生态意识,心怀善意的人类居民才会对这同一颗星球上的动植物居民与我们的关系所思至深,所感至柔,人类也才能由此行久致远。
【本文曾发表于报章,略有删节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01/30/nw.D110000renmrb_20180130_4-20.htm】
《第三极的馈赠》读后感(六):来自博物学家荒野手记的启示
找《第三极的馈赠》来看,出于对西藏的兴趣,更好奇在一个博物学家眼里和笔下,那片苦寒之地和生活其上的野生动物们有着怎样的样貌和秘密。
让我意外的是,整本书很好读,平实记述中既有科学的严谨,又有对野外工作苦与乐的细诉,更有对踏上博物学研究之路的回顾与思索。它不仅是乔治•夏勒这位博物学家的荒野手记,更让我们看到开发与保护,信仰与现实的矛盾碰撞,提醒自己反思终此一生在工作与情感上,真正值得追寻的是什么。
一、对待工作的心态决定了工作的回馈
将羌塘藏羚羊作为自己的图腾和心之所依的作者从1988年到1994年,七次进入西藏羌塘进行野生动物调查。他看来“破解一个自然谜题,如雌性藏羚羊的迁徙目的地,是件很好玩的事”,可这好玩要求具备极端忍耐力。
“不到两公里的一段路,我们的越野车竟陷下去8次——大家苦干7个小时才把车子救出来。”“6月10日至7月7日,28天里有19天下雪或下冰雹,其余的日子里,有6天遭遇猛烈的沙尘暴。”“每一天都要设法解决后勤问题,有时甚至要全力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无暇顾及其它。”高原上面目狰狞的天气,考验着热爱它绝世美景的人们,因车子深陷泥地而步行时,作者写道:“我喜欢行走在这样的原野上,荒寂的景色并不可怕,反而让人心静,给人以宏大的体验。我的心与这片土地相连,我的感官因它而兴奋。成群的角百灵、仓鼠都让我感觉亲近。”
当不顺利成为常态,乔治博士有了佛教朝圣者的心境:“我既然是来做先期调研的博物学研究者,就应专心感受这片土地,不必执着于达成某个目标。”
“独自观察动物,没有人打搅,一连几个小时就这么看着,你会觉得自己的感官功能上升到新的层次——变得更加敏锐能分辨出行为举止中的细微差别。孤独促人思考,研究因而变成了探索存在意义的旅程,不止是就动物而言更是我自己的一段内心探索。”书里类似的描述还有很多,渐渐让人理解并感动于这种忽视外在艰辛,用心融入自然的坚韧与忘我。工作的回报,在作者不仅是数据与报告,声名与成就,更是迈向自由与超然境界的修行。
二、佳偶是成就事业的关键
自1952年到阿拉斯加北部研究北极鸟类,作者就奔波于与世隔绝的地方,从非洲山地大猩猩到印度野生虎,再到中国大熊猫、藏羚羊……让人好奇如此醉心于濒危野生动物研究与保护的作者,有着怎样的家人?
书的第八章《野性难驯的博物学家》里,作者回顾了自己的成长与职业轨迹。他与妻子凯相识于阿拉斯加大学,两人兴趣相投,都热爱野营生活,凯陪伴作者在野外度过多年,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序言中,作者写道:她不仅是我的工作伙伴,还为我编辑整理手稿,养育了两个让我无比骄傲的儿子,在方方面面给予了我无法计数的帮助。长时间分别时,爱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唯一桥梁。日夜轮转,相聚别离,犹如爱与怜悯凝聚而成的曼陀罗。
他们的儿子埃里克五岁,马克三岁半时,一家人来到坦桑尼亚国家公园总部所在地塞隆奈拉,住在一幢木屋里,“有树冠平铺的合欢树为我们遮阴,长颈鹿会跑来吃树叶,偶尔有狮子在树下懒洋洋地待上几个小时。孩子们已经可以饶有兴致地欣赏角马的迁徙,大象站在树皮泛黄的金鸡树下乘凉……”多年后,埃里克和马克都成为大学教授。科学家夫妇证明了父母的言传身教抵得过名校优质教育资源。
作者能数十年以自己热爱的方式工作、生活,离不开家人的支持与陪伴。尽管书中关于家庭的部分仅寥寥数语,已足以显示“好伴侣”的选择条件究竟是什么。
三、人生的路在童年已埋下伏笔
全书的字里行间,时时能感受到作者置身旷野观察动物的欣喜与满足。是什么让他厌恶城市生活、人群、噪音和公众的目光,却对荒野艰辛甘之如饴?
1933年出生于柏林的作者,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美国人,童年时跟着父母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生活,二战时旅居丹麦,后又回到德国。1947年,14岁的作者作为敌国侨民,跟着母亲回到美国。不断地成为陌生国度里的陌生人,漂泊不定的生活,使他内心总有一份身为外来者的忧郁,性情疏离,寡言少语。
高中毕业前,作者跟着在阿拉斯加大学读采矿工程的哥哥,前往育空地区进行户外探险,唤醒了他对广袤空旷的大自然的热爱,于是申请进入阿拉斯加大学,在这里,他认识到后来作为博物学者的天命,并开启了全新的人生阶段。
“从内心里发出的声音,绝不会欺骗希望的灵魂。”作者将德国诗人约翰·弗里德里希·冯·希勒的话当做自己的人生哲学。深知“在灵魂深处,那可令我心安的归去之处,是更为价值恒久的成就,超越我个人而存在。”
四、人性与真相
第四章《致命的时尚》中,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末因其羊绒能织成昂贵的,名为“沙图什”的披肩,藏羚羊遭到大规模屠杀,为保护藏羚羊所做的不懈努力。
一块绣工格外精美的沙图什披肩可能标价15000美元甚至更高,这样一块披肩需要3到5只藏羚羊的羊绒,作者犀利地指出:“披上沙图什的女性相当于在肩头挂上了3只藏羚羊尸体——这是裹尸布,而非披肩。”
但因富豪名流们的追捧和巨大利益的驱使,阻止这样的裹尸布上市却困难重重。纽约百货公司波道夫·古德曼打出虚假广告,称沙图什由西藏北山羊褪去的绒毛制成。直到2000年8月,沙图什协会依然坚称“沙图什原料并非来自被屠杀的动物。”
上世纪90年代,作者在纽约亚洲协会讲课时,因展示屠杀藏羚羊及西藏盗猎营地的照片,触怒了美国藏族团体的成员,他们原本将所有盗猎活动全部归罪于汉人头上。作者被指控“让汉人穿上藏族衣服,拍下那些照片。”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复杂的人性面前,因立场与利益不同而扑朔迷离。不仅藏羚羊,野生虎、西藏棕熊、冬虫夏草……在人类的贪欲面前都岌岌可危。
朱光潜在《谈美》中以木商、画家与植物学家看待同一棵古松,关注重点因性格情趣不同而不同,说明美不仅是客观的更是主观的。《第三极的馈赠》如一棵苍劲的古松,有科学严谨的研究记录,有天地大美的深情描述,有与动物亲密为邻的趣味故事,有身为博物工作者的欢喜忧愁,平实而不失渊博,不同的人能从中得到不同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