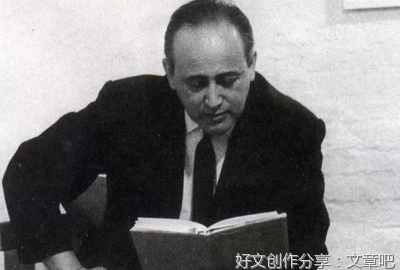《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精选》读后感100字
《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精选》是一本由保罗·策兰著作,雅众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5.00元,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精选》读后感(一):不过是把策兰的语言用大白话稀释了一遍
黄灿然是翻译界的劳模,是值得尊敬的,但必须说,尊敬归尊敬,黄译的问题也是需要谈论的,首先,对黄灿然目前有两种质疑,一是对他的译诗,二是对他的译文,对译诗的不满,几乎都集中在他的大白话风格,让人读来没有诗味,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也有人专门喜欢这种译法。对译文的不满,主要集中在黄灿然啰里啰嗦的长句子,用他自己的辩护是直译,而完全不管语法转换过程中,出现的语义重复等等问题。
如果要深入谈论黄译诗的问题,那莫过于举策兰的例子最合适了,因在黄灿然的译诗中,各国诗人都有,黄灿然最负盛名的一本译诗,是从英文转移的卡瓦菲斯的诗,第一版是河北教育出版社的,那是2000年刚出头,正好迎合九十年代末兴起的叙事写法,所以,书一经出版,无论在大众还是专业读者那里,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直至今日,它也被看作是黄译的高峰
但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无论黄灿然译哪国诗人,都是英文转译过来的,从翻译学角度讲,转译的译文不见得是坏事,经过了两次语言间的转换,会有不同的译文效果,但诗歌语言角度讲,就会出现不准确的问题,当借助的转译语言本身,在诗歌语法上和原文不一致,尤其本国诗人也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相当于完全丢失了原诗人的语言特色。拿英语来说,英语诗歌语言本身是有很大问题的,在英语现代化以来的诗人中,除了艾略特,庞德,几乎都遵循主谓宾的语法结构,并未把超现实手法达到运用自如的状态。
在各种语言的现代化过程中,超现实手法是一条必经之路,虽每种语言的具体情况不见得一致,明白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何很多人对黄灿然的译诗有微词,好像不过是分行的散文而已。必须说,黄灿然译英美诗人把诗体译成散文体,是不能指责太多的,因英文原文就是散文,但译德法诗人,就可以直接被诟病了,如黄译策兰,不过是把策兰的语言用大白话稀释了一遍
因众所周知,策兰即使是德语里,也是形式感极强的诗人,除了语义上的创新,最令人‘侧目’的就是他语法上的革新,而这在英译本中是没有做到尊重原文的,既是策兰的不可译性,也是英语自身的局限。把其他非一流和原创诗人译成散文,效果没这么明显,但策兰恰恰不一样,于是,在对策兰诗歌的接受中,尤其是诗人们,更认同王家新而不是黄灿然的译本。
必须说,诗歌翻译问题不仅仅是它自身的,本质上是汉语白话语言的问题,从胡适开始就把散文当做诗歌,以为内容的新就是新诗了,而无视若形式不过关,内容的新是无效的。说到底,黄灿然翻译的问题出在他自己的诗歌上,他的诗歌基本都是以散文写成。
《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精选》读后感(二):一点资料,我们不吵架。
诗人喜欢吵架,读者喜欢比较译本。 那就摘一首短却意味深长的诗,贴来一观。 比较有趣的是,各位诗人为译策兰争论的时候, 总也喜欢提这首收录于《罂粟与记忆》中的无题诗。
雅众文化这本诗选是黄灿然译本。黄灿然将之译为《数杏仁》。
北岛在撰文译介策兰时,将这首诗译作《数数杏仁》:
王家新版《数数杏仁》:
钱春绮译本《数数扁桃》:
按照惯例,附上英文版Count the Almonds:
德文原诗:
最后,关于吵架:
北岛在译介策兰时,点评了王家新、钱春绮的译本,不是很好听,就不做摘录了。有兴趣的可以找来一看:《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载于《收获》2004年第4期。全文看这里https://www.sohu.com/a/286579872_632464
王家新撰文回应《隐藏或保密了什么——对北岛的一个回应》,载于《红岩》2004年第6期。全文这看里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44725714/
《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精选》读后感(三):这一件野蛮的事儿——写诗
是的,2021年了,我还在读诗,读保罗·策兰的诗。
除了读诗这个行为的“不合时宜”,还有那句德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及社会学家西奥多·阿多诺的名言
读野蛮的诗,又是在如此浮躁的一个年代,这事儿本来就没用,在和平时代,好像也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特别是,如果你了解保罗·策兰这位诗人——他出生于1920年,1970年去世。他生于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这五十年间正好和“奥斯维辛”狭路相逢,他的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而他本人也在纳粹时期历尽磨难。在奥斯维辛之后,他不但写了诗,做了这件“野蛮”的事儿,而野蛮作品本身也以晦涩和语言碎片化著称。今天的我们,远离那个时代背景,不了解那段黑暗的历史,很难,得到进入这个野蛮而充满了意象的世界的门票。
但是,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它完完全全地没有吸引人的要素,才吸引人好奇。
只是,好奇之外,到底还是要充满悲悯,就算无法解读诗人的精神世界,有一点,无论如何会从诗歌中共情,那就是,巨大的、浓黑的、无法调和的也不可能被稀释被消解被遗忘的,悲伤。
在奥斯维辛70多年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又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
还是不要问了,不是什么事儿都一定要有意义。它发生过,它过去了,它把一些人的灵魂撕得支离破碎,甚至于今天,我相信,读保罗·策兰的诗绝对不会是享受,让我们来看他诗歌的关键词:纵观《死亡赋格》中178首诗歌,几乎每一首中都会出现的词汇是“黑”,出现频率仅次于“黑”的是“棺材”“死亡”“死尸”,极具意象的词汇如“杏仁”“眼睛”“鸟“烟”“姐妹”等,与之相关的动词如“看见”“看不见”“飞”“燃烧”等。除了一些抛开语境考虑的中性词,大多数词汇我们无需学术背景都会产生一些负面感受,比如,压抑、恐惧、绝望,甚至是恶心。
我不是考据派,也自然很明白翻译的美学损失,黄灿然亦或是北岛,不管我们多么喜爱和推崇他们的中文造诣,但是两种语言在转换中那微妙不可言喻的损失是客观存在,亦是无法避免的。很多时候,我们欣赏到了诗意,就要损失韵味,欣赏到了内涵,就要丢掉对仗,而最有可能的是,人不是翻录的机器,里面总有译者的领悟,所以黄灿然也说,注释更多要被视为“评论”。对于策兰,不敢用太过学术的方式来分析他的诗,以上谈到的,单纯是读诗的感性感受。
他本人不希望被过度解读,或者说,高山流水,曲高和寡,人类的悲欢本就不同,世上人万千,但是并无一人能了解其真意,策兰甚至写了《死亡赋格》的“翻案诗”,50年代后,他拒绝将其正典话,拒绝重印转发,拒绝公开场合读它。这本身也说明了他的态度,他拒绝自己的作品被过度解读,甚至很多解读和分析已经与他内心的真实南辕北辙,但是,他主观的“撤回”却再也撤不回了,但是这首诗似乎也是对西奥多·阿多诺的一种回应,尽管写诗这样的行为是“野蛮”的,但是想要说的冲动就要他直面野蛮,最终被吞噬,他唯一恐惧的是,这种痛苦成为一种媚俗和平庸,那将比遗忘还耻辱。
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位作家——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用西奥多·阿多诺的话来讲,他们都做了“野蛮的事儿”,写这件事本身就野蛮,在这灾难之后,谈艺术也是可笑的、奢侈的、不恭敬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却又应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句——活着就是为了讲述。“我们”亲历者,要一次次回到地狱去,讲给“你们”听地狱的,发生过的事儿,讲完了就是真正死亡到来的时候,因为后奥斯维辛时代,连幸存下来的生命都好像是野蛮的了——他们都是自杀身亡。
我最喜欢的一首是《花》:石头空中的石头,我追随它。你的眼睛,盲如那石头。我们曾经是手,我们把黑暗掏空,我们找到了那个攀升夏天的词:花。花——一个盲人的词。你和我的眼睛:它们照看水。生长。一片片心墙为它添花瓣。多一个像这样的词,锤子就会在旷地上挥舞。
《死亡赋格:保罗·策兰诗精选》读后感(四):诗行里那隐秘而孤独的自我对话
欧洲现代诗坛上,优秀的诗人如群星闪耀。不过在那个群星闪耀的诗坛中,三颗星星,在我眼里格外,一个是一生未婚的里尔克,一个是在一战中夭亡的特拉克尔,另一个就是最终在塞纳河投河自尽的保罗·策兰。
里尔克的诗让人动容,不无神秘;特拉克尔的诗让人着迷,充满黑暗的意象;保罗策兰的诗则多少会让人困惑,迷雾重重,却也让人欲罢不能。
策兰的诗,许多并不好理解,太过于凝练,太过于简洁,太过于跳跃,甚至有晦涩和断裂之感。他那首最初的成名作,一首批判色彩极为浓厚的长诗《死亡赋格曲》,其实并不能算作他的代表作,也算不上他的成熟之作,也与他后来的整体风格,大不相同。这首成名作之所以能备受瞩目和传唱,大约与它承担了现世的社会道德担当有很大关系。
在经历了世界大战的摧残,面对人类的苦难,诗人和诗歌似乎毫无招架之力,毫无意义。因而欧洲文艺界曾流传了这样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意思很明了,即经过奥斯维辛集中营那场浩劫之后,再写诗、搞文艺,观赏这些艺术就显得很残忍了。
保罗·策兰却是这场人间黑暗的劫难中挺身而出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用诗来控诉,尽管控诉的力量有限,却传遍了几乎整个欧洲——《死亡赋格曲》:
的确,真正的诗并非单纯的审美和愉悦,它可以兴,可以怨,可以控诉,可以给人启示,给人以震撼,让人在艰难的困境中有活下去的意志,让人有追逐自由和反抗邪恶的激情。诗,虽然不能抵抗武器,不能抵抗人间的邪恶,让那些还有良知的人萌生向美,而美可以引导人类向善,创造美好的人间生活,而不是返祖式的动物野兽般的破坏、仇恨和互相戕害。
记得有这么一句西方谚语:“没有诗人,人类的爱情不过是野兽般的低级本能。”诗人和诗歌的价值,也许看起来很缥缈,千百年来,却一直在默默地升华人类的情感,从而让人类这个灵长类动物与那些仅仅遵从本能的动物划出一道鲜明的鸿沟。正如尼采所说,人类是从残酷的野兽通往神的一道梯子。
策兰的诗的一个最大的特质,尤其是在晚年,就是极端凝练,极致的简洁,用词简直是惜墨如金。一首诗不过寥寥数行,每行寥寥数词,诗行短促,甚至一个词就是一行,从而构成了独特的节奏与诗味。这种简洁的凝练的风格,是我个人所非常喜欢的,这也应该是现代抒情诗的一个典范,一面旗帜。
一首诗诗瞬间的体验,是瞬刻的顿悟,那种铺陈啰嗦的文字,还是让给散文吧。大段成行的密密麻麻的文字,能成为一首绝妙的诗吗,让人疲惫,也容易让人昏沉,不如作为散文的更好。与当下众多喋喋不休的口水诗,夹杂太多泥沙与泡沫的那种拖拖拉拉的叙述性文字相比,策兰的那些精炼的抒情诗,无疑是罕见的珍珠,是独一无二的。
正如这首,只有寥寥三行,却足以称之为一首杰出的诗,毫不逊色于一篇史诗:
不过,这种极端的精炼,往往又容易造成了另一种略被人诟病的现象:晦涩。有些诗,的确晦涩,读来数遍,依然如堕雾里。他的诗有一层厚厚的壳,一层厚厚的茧,被紧紧裹住其中,让人很难进入其核心,窥视其中的意义。
策兰的诗在内容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质,就是诗中的“对话气质”。与大多数的诗人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对象不同,也与那些以观察者的角度叙述第三者(“他”)情节的诗也不同,策兰的诗的叙述对象是对面的某个人,或者远方的某个友人(“你”)。策兰的许多诗既不是自白,也不是讲述别人,而是像另一个人倾诉,一种孤独的对话。
诗中的那些“你”,作为读者,我们不知道他的身份,他的性别,他的背景,他的经历,是一个模糊的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某个角色。然而,诗中多少也会透露一丝隐情,那些不明身份的“你”,未尝不是诗人自己,另一个自己,或者诗人内心中的另一个身份,或者是镜中的那个自己,他与镜中的自己对话,或者他与给远方的某个自己写一首含蓄而简短的信,用诗的形式。
这是另一种隐而不现的孤独,深刻的,无人发现的孤独。诗人不想将这种孤独宣泄、暴露和分享给别人,他一个人独品着难言的内心的悲戚。于是,他与自己对话,那些对话和倾诉,却被世人偷听到,被那些狡猾地读者,正如我,窥探到,翻阅到这些隐秘的文字,那刻意隐藏在诗行中的秘密。
策兰的诗集,佳作俯拾即是,不论是前期的《从我到你的岁月》《花冠》《法国之忆》《数数杏仁》《声音》《真理》《带瓮灵的风景》等,还是晚期的《你怎样在我身上逐渐消逝》《我和我的夜晚闲荡》《我躺在自身以外》《我在世界背后引领你》《我戴着指环影子》,等等,无不是优秀的杰作。
不过在这最后,我却想分享另外一首非常喜欢的《我站立》(在此不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