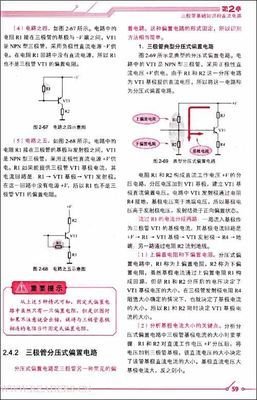无非求碗热汤喝读后感10篇
《无非求碗热汤喝》是一本由张佳玮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80元,页数:32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非求碗热汤喝》读后感(一):怎样吃喝就决定了怎样的你
据说王安石吃菜只吃离自己最近的菜,放着鹿肉他能吃完,放着青菜他也能吃完。大抵王安石这样的伟人心里只惦记着为社会福、为邦家光,有限的精力完全奉献给了变法、改革,至于吃什么、怎么吃,那都是细枝末节、微不足道。因为说到底,吃、喝也不过是人的动物性本能,而人越是追求伟大就越远离这些动物性的本能。自然,对于王安石这种超前于所处时代的人来说,吃喝实在是不值得去考虑的。
但偏偏有人就特别喜欢琢磨吃这回事,作家张佳玮就是其中之一。他自己也说了:“我从小是个馋人,见着好吃的东西挪不了步,推而广之,看到描述吃的字句或影像就目不转睛。看书看电影,总是对吃喝的情景记得最熟。小时候常为此惭愧,自觉境界不高。”而今,在篮球、足球、武侠、美术等领域证明了自己之后,张公子将天赋带到了美食界。
我对张公子的博闻强识(也有人说是掉书袋子)是十分佩服的。他架构出了一整个宏伟的世界观,在其中,每一件生活中的寻常物件都被有序的摆放,与之对应的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按照这个坐标,你能够纵向延展追本溯源、横向比较求同存异。比如《对酒当歌求其乐》中,你会知道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中就有了酿酒的法令,安东尼与埃及艳后的故事里酒做色媒人;你还能看到大禹感叹后世有人因酒亡国、曹操进贡九酿春酒等。
同时,张佳玮另一项独到的本事是他总能留意到文艺作品中的边边角角,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是说关注点奇特。比如,在我们还感慨鲁迅先生的批判性时,张佳玮已经开始说起《狂人日记》里的蒸鱼,《故乡》里的青豆、炒饭,《孔乙己》里的黄酒、盐煮笋和茴香豆,《药》里面的炒米粥和元宝茶,《阿Q正传》里的油煎大头鱼、萝卜,《风波》里“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社戏》里的煮罗汉豆等等等等。在吃的方面,张公子可谓将吃货与生俱来的动物性本能发挥到了极致,与王安石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极端。
这世界这么多人,有人欣赏王安石,自然也会有人喜欢张佳玮。到最后,你成了什么样的人,也是跟你对待吃喝的这些本能有关。
在学校图书馆里慢悠悠地逛书架,一步跨出忽又大喜转回,原是“无非求碗热汤喝”几个字活泼泼地跳入眼帘。
这本书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碗热汤,而且是碗柔美温补、回味悠长的热汤。
初读,是啜饮一口表层的清亮的汤,第一口便充满了信陵公子的特色风味——开篇第一页便旁征博引满纸开花,由诗入境,一个“鸡黍”引出列位翩翩佳公子,温润悠长的诗情被作者拿来开了个小玩笑,好像喝清汤的时候一粒榨菜闯进了嘴里,上下牙齿“咯吱”一嚼,俏皮味道全出又丝毫不失风雅。
再读下去,味蕾适应了这般清新风味,慢慢不满足于小口啜饮了,于是渐渐大口饮起来,温热的汤充满了口腔。这个阶段,浓浓的故乡的味道、家的味道、亲情的味道、童年的味道从小小的书本中溢出,引领我们的记忆,尝到厚实古朴的外婆红烧肉,看到琳琅满桌的家中年夜饭,走进万花园般的家乡菜市场。
继续读,汤已半碗下去,干物却还没吃,于是拈起干丝配菜细嚼,各样菜有各样的风味。俗话说“嘴大吃八方”,张公子的嘴多大我是不知道的,但是这八方,起码也吃了有一半吧。吃得多吃得广没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能把细腻的感受力落实在味蕾上,表现在文字中。天之涯,海之角,从国内吃到国外,食物千百种,有的传承了古典文化,有的体现了地区差异,有的沾染了民族性格,经了公子的笔尖,都一一呈现在眼前,举重若轻。
一碗汤喝道最后,沉在碗底的物事总给人惊喜,比如我总是一碗面将吃完,才发现碗底铺着一层肉丝。《热汤》的最后一章着实令我惊喜,以物喻人,妙趣横生。公子以食物为主角写童话,不掉书袋而满纸皆是典故,不引名言但慧眼可发现出处,盖才气就是如此吧。最后一章,就是压轴的几样生猛硬菜,大补之外平添了许多可供回味的余韵。
书是瘦瘦的,文字却铺展得很开。不知是书香点染了热汤,还是热汤浸润了书页。索性用热汤就着白纸,小菜伴着黑字,一齐咽下,享受一下精神上的酒足饭饱吧!
《无非求碗热汤喝》读后感(三):掉书袋卖弄的心思太重
讲吃的故事却露出掉书袋、卖弄的心思,虽然也有些出色的段落,但真心不是书名说的求碗热汤的心态,一起买回来的世间的盐感觉好很多,故事轻松幽默又不刻意,也许是两个作者年龄的差异吧,人到中年大概就没那么重的功利心了,两本书真的没法比。
写这些本来只是想提示一下像我一样被书名吸引了的豆友,这本书引经据典太多,回帖里有个豆友说的更贴切,有堆砌之嫌,没有太多真情流露,我没什么文学素养,只是觉得书不怎么好看,这几年读书不为长知识也不为攒谈资,只想偶尔从生活的苦闷中解放片刻,就这么简单。
读书是很私人的事,我几十块买错了本不爱看的书发发牢骚而已,说的都只是个人感受,我不喜欢总有别人喜欢,反过来也一样。
《无非求碗热汤喝》读后感(四):大隐隐于食
看《无非求碗热汤喝》其实十分遭罪,我看着篇幅短小于是随身携带到交通工具上看,初看极好读,随便一页便可开头,读过的再翻也不腻,但在公交地上大都是上下班的趟儿,正是饥肠辘辘但饭菜未到口的时间,一边读一边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感觉,非常纠结,书里咕嘟嘟的鸡汤,热腾腾的炒饭,都是寻常物,偏又到不了嘴,况且平日吃来也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甚少对着一碗饭食刨根问底浮想联翩,只好到地方合上书,就奔着饭菜去了,胡吃海塞,看书时候的风雅劲荡然无存。
不过这书可以快读也可以慢读,快读似评书,嘁哩喀喳就记住吃食的色香味,大开大合是一个痛快劲;慢读像听曲,摇头晃脑千回百转,要的是情景要的是韵味,要的是里面的典故可以细细品味,脑子里留下了念想和回味。
国内写吃食的老手极多,欧阳应霁、蔡澜、沈宏非、殳俏、韩良忆……男人们大都玩味食物的典故、品格、来龙去脉:女人们大都感性为先,更在意味道本身,以及食物氤氲出的温暖和美丽的气氛。就像家里烧菜的大都是娘子,厅堂里练锅的多是汉子;平日里离不开零食小菜的多是女子,偏偏追究茴香豆茴字四种写法的大都是老头。但无论是哪一种和食物有关的表达或者叙述,都需要足够的生活阅历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所以老男人和小女人在这道上是占着天时地利人和的。
可《无非求碗热汤喝》偏偏来自一个本来应该横刀怒马争夺武林盟主年纪的人。写得还极细,从家常食话,到零食小点;从应景吃食,到各地风物,从文化掌故,到童话臆想……看得感觉特像小酒馆里极度能唠的大爷,一肚子的典故,就是面前一碟花生米,也能给你说道半天。但偏偏口气里常常流露点淘气,看得人又嘴馋又心软,间或几篇还让人眼眶发热,想家想爸妈。
后来和公子有机会聊到这本书,他说这本集子集中了前些年为杂志们写的专栏,还有闲时为了讨好爸妈写的小文。他说平日写球评什么的,爸妈看不懂也不爱看,就写这种天南地北街坊小食他们喜欢。于是心中不由想起像儿时朋友里那种玩伴,看书多,语言浅,再大的事情在他们那不过谈资,一起聊天打发了时间长了见识,十分痛快,但每每考试后,他们便被家长拿来作为榜样,言语里你看谁谁谁作文就写得那么好,让人不由要产生一点羡慕嫉妒恨。所以想想其实这样的孩子聪明,写这样的书,年纪轻轻当然拼得当然不是欧阳应霁或者蔡澜吃遍全球鱼翅燕窝的阅历,反而是另辟蹊径清粥小菜的日常况味,加上文章里俯仰皆是的梁实秋、袁枚、唐鲁孙、汪曾祺……甚至拉来了鲁迅先生分析口味和闰土的食趣,融会贯通一点没有掉书包的感觉,有这样的文化底蕴垫底子,不但写起来让吃食们熠熠生辉,公子自己吃的时候那酸甜苦辣自然都伴着一个够老够大够闲的心境了。
其实每个人要掰着指头数自己吃过的东西,大菜小菜荤菜素菜厅堂料理私房小厨,或多或少都能说出五四三二一,可有人就能说出味道还能说出门道,说完门道还说说旁门左道,比如上个菜场,下饭的书,甚至是断了炊烟的恩爱时光,于是乎一下子饭菜就不是那些饭菜,还氤氲着文化,浸透着人情,慰藉着人心,而一手创造出这种氛围并且被这一切环绕着的张公子俨然古龙笔下的侠客,身怀绝技还大隐于市,一副厌了江湖恋市场的派头,一剑封喉的本领都拿来洗孩子带菜煮衣服,攻城略地后只为讨好双亲和并肩的人儿。
《无非求碗热汤喝》读后感(五):没有热汤,有热水也好
张佳玮说人生在世,冰霜苦旅,无非求碗热汤喝,是啊,热汤的慰藉比任何话语都更加暖人。
书的第一章便以孟浩然诗中的“鸡黍”为线索提到了心中臆想的“一碗黄油油香喷喷鸡汤泡米饭”,意象太过鲜明,竟让我这个看客也看饿了。想起了小时候,虽家人多次劝告,但我依然喜欢用排骨汤或者鸡汤泡米饭,再用自己肉乎乎的小手拿着大大的瓷勺一口一口吃下一碗香喷喷油汪汪的米饭,里面经常会再放些已经炖烂的肉和蘑菇,母亲嗔怪我会吃却不知道养胃,彼时的我哪里知道什么养胃,小孩子眼里好吃就是一切,而家里人也都围在一起边吃边笑,没有炉火,却也温馨无比。汤泡饭的滋味已经淡了,但是当时美好的记忆却一直留到了现在。
书中的食物都很家常,但是在作者诗词
朋友之前送了我一个保温杯,小巧可爱,保温效果简直让人感动。以前早上总是起不来,眼睛醒来身体却醒不来,自从有了那个杯子,每晚接一杯热水,早起挣扎着咕咚咕咚喝几口,在氤氲的热气中干了一晚上的灵魂似乎鲜活了过来,而身体也终于慢慢被唤醒。
旅途中的我,肠胃并不舒服,喝了几口热水,那种妥帖感瞬间传遍全身。
小小的杯子,热热的开水,宇宙中渺小的我,似乎一切都是注定好的。
旅途不苦,但有了热水,阳光似乎也幻化为具体的味道,进入到了我的胃里了。
《无非求碗热汤喝》读后感(六):见字如面,望君长安。
每次回家,姥姥都会无比心疼又略带嗔怪地捧着我的脸,一个人念叨着我又瘦了。我会认认真真地转一圈给她看,虽然浑身上下像竹竿一样干净消瘦,也算是我略显惨白的辩解吧。
姥姥是个神奇的人,让我想起《大鱼》里的老爸——刚刚18岁就从山东一个人来到了黑龙江——红卫兵、接线员,吊车司机,厨师,不一而足,倒也盘活了异乡的生活。现在想来,最值得怀念的就是某个补课晚归的冬夜,呼哧呼哧地跑回家,看见满桌的好饭好菜——锅包肉、羊肉汤、土豆泥、炝西兰花。然后讲讲学校的事,在听姥姥磨叨磨叨她那些怎么做饭,怎么救人,怎么和周总理握手的陈年旧事。所以吃之于我,从不是简简单单地填饱肚子。
小时候不吃辣,舌头灵的很。白豆腐是甜的,菠菜味苦,猪肉有股臭臭的味道……所以即使姥姥做饭人皆晓其佳,我还是不免要提些“改进方案”,有时会看见她奕奕的神采微泛萧索,却还觉得自己只是高标准严要求。看看自己现在吃的食堂里咬着咯牙的炸鸡腿,夹生的米饭,勾芡勾成浆糊的汤就恨自己当初怎么这样身在福中不知福。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混蛋的自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中二病重患。自以为是,甚至是狂妄。自然开始对老人的话语存疑,又对她的关怀反感,于是从不愿和她搭话到动辄就是一阵争吵——她只不过是在我想题时拿水果给我吃,或是怕做好的饭凉了一遍一遍催我别玩dota了,凡此种种又有何过?
所幸看到了这本书。说实话单凭内容《热汤》算不上是极品,张公子的言辞固然华丽了,却忘了无招胜有招的学问。吃食描述的太精致便脱离了我们平凡人的生活,但看厌了他的卖弄和自我陶醉决意弃书之际恰好翻到了私房小记,力透纸背的便变成了酽酽的思念之情。像被传染了一样,我开始疯狂地思念姥姥和她做的每一道菜,不管是加了两遍盐的冬瓜汤还是忘了放醋的鱼香肉丝,用心做出来的味道我尝得出来而且永远忘不掉。
不知道在我想她的时候,她会不会也做好了一桌我最爱吃的菜,一个人静静地等我。其实远行千里早已不那么重要,姥姥留下了我的胃,便天涯海角召之即来,如是而已。
《无非求碗热汤喝》读后感(七):张公子著作所读第二本
(不知道取啥标题好……)
还是先从后记里说起。张公子说,以自己的年纪,经历之浅,所见之少,要写饮食,很是不自量力。又说,本书如果还能论到什么有意义的主旨,其实就是如此:家常饮食、怀想父母,道听途说看看字,过过馋瘾罢了。
当然是有些谦虚。先说前半。写饮食这事,不一定非要经历多丰、所见多广,才有资格去写。汪曾祺唐鲁孙之老一辈自然提笔即来,但年轻一辈写吃食也是素材颇丰——以一万小时理论来较真的话,人这一日三餐外加点心宵夜等等,每天算它三小时,三乘三百六十五再乘二十六(张公子说所选文写于二十六至二十八岁间),得出来的数据有近三万!更不论张公子这种亲下疱厨悉心烹炒之人,所费时间还得再往上番。
所以呀,其实饮食上,人人都是大行家。
再说后半。家常饮食自不必言,公子写的都是睁开眼就能见到、张开嘴就能吃上的平凡小物,并没有鲍鱼人参佛跳墙这种寻常难见的大菜,读的人——尤其如我、生活足迹与公子有些重合的人,非常有熟悉亲切之感;怀想父母这方面我差了些,因九岁起与父母分开,关于自家饭香的回忆淡薄了点,但料想其他在父母身边长大的人,应该很有共鸣;道听途说看看字、过过馋瘾——看这书时不知道多想来碗梅菜扣肉加白米饭、小笼汤包加香醋呀!
除此之外另想表一枝。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总是新鲜,买个电炉子集体涮火锅也好下面条也好,吃得特起劲;后来毕了业上了班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事却总显不尴不尬。初时是觉着一个人特别不好弄,买一颗青椒一粒土豆?进了菜场却拉不下那个脸,按正常份量来买通常就是一不小心做多了。后来是觉着时间宝贵——从买菜、洗菜到切配、下锅,整一个人的饭食快则一两小时,慢则两三小时,如果兴起给自己煲上个汤时间就更无法掌控了——这些时间用来看几本书多好呀。
但另一方面又觉着出去吃不好,不卫生不合口不便宜不宜锻炼自家手艺;进了馆子点上吃完再走也总有些露水情缘的不深入感。于是就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一直这么纠纠结结着。也看过一些写食物的书,有名的有庄祖宜,但是人家毕竟是专了心当了职业来做,就给自己找了个“我这儿还得上班劳累呢”的借口,依旧是有一搭没一搭地下着厨。
看完张公子这书之后,有种感觉是,万物皆灵呀!就拿不甚起眼的茄子来说,人家原名可是叫酪酥的呢(话说我们家方言里现在还是这么叫)!比起英文的eggplant高雅了不少,红楼梦那典故更是每次读来都觉着食物这东西往精细里做,永远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其他的豆腐春韭羊肉小笋馒头面条也都有着各自的气蕴神情,都不能懈意怠慢了。
这么一感觉,选择权好像不在了自己手上。冬天的早晨可再也不能赖床了,否则辜负了刚出蒸屉那热气包子的美意;夏日的傍晚也不能对付对付就过去了,白如玉的豆腐可眼巴巴地等着被宠幸呢;白米也不能随意淘一淘就往饭煲里沉,水的份量得一再确认才是——吃一碗不软不硬粒粒分明的米饭可是不容易的!
权利变成了义务,倒也不赖,走向厨房迈向菜场的驱动力更强了些。再者《自控力》也说了,人得摄取足够能量,头脑对身体的控制力才能正常发挥。有点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意思。事实上,认真对待了一日三餐,日子过得确实美了些,干起其他的活儿来确实更有精神力气了些。往后啊,认真下厨吧。
值当。
附,热汤这件事,以前有人教导说,一顿饭里怎么着都得有汤,尤其所爱之人晚归了,菜重热卖相不美口感欠佳,但汤一热却是极其地渗入肺腑直指人心。因着一段因缘际会,排骨莲藕山药汤已成至爱;偶然开过一个网页,化腐朽为神奇的陆阿姨家汤包也已必备;再加着这书,以后这热汤,能一直做下去。
2014年3月29日
@北京—上海
---------
微信公众号:shaosling
私人微信号:shawsling/个人微博:邵司令呀
《无非求碗热汤喝》读后感(八):意外之喜
随手买了一本《无非求碗热汤喝》不得不承认多是因为看重张佳玮的名声,张公子其人,知名篮球写手。而大凡写篮球评论的风格都像极了程咬金三板斧,大开大合,多用极夸张的句式。很是对我胃口。
在看其书名《无非求碗热汤喝》颇有戏谑的味道。致我原以为是写篮球的杂文。翻其目录才大惊,竟是本正儿八经科班出身的美食随笔。
不免略有失望,想来比起篮球,美食虽也是我心头的一块肉,然终究不是我的最爱,况且比起做我更热衷于吃。这种画饼充饥的美食随笔。于我着实卖相不好。于是随手翻看几页,才惊觉这刨去了篮评的夸张句式,取而代之平实而略带古朴的文笔。竟有布衣荆钗不掩国色天香的味道。
在往下读才愈觉得饶有兴致,颇有桃花源记里,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语言古朴,遣词却极为老练。闲闻趣事,历史典故。皆以美食穿引,庞博而不杂芜,实诚又不失兴味,借食物抒旧情。
见公子奇文,可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
《无非求碗热汤喝》读后感(九):我想做饭给你吃
看这书的时候,正好是酒醒的第二天。空腹喝酒有很多坏处,醉的快,伤身体,最重要的是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绝对让你有种想死而不能的感觉。不信你可以试一试。第二天醒的很早,套了衣服就冲去食堂打稀饭喝,力图挽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胃和肝。中午吃的是屋里姑娘做的疙瘩汤,南方娃娃第一次吃这玩意儿,新鲜的很。下午还不要命的跑去上没甚要紧的公选课,这是标志性的时刻,此后一周,我都没再沾过米饭,作为一个爱吃米饭的南方人,一周都在吃面,你知道有多痛苦吗?
以上背景。
因此未来一个星期都是看着食物却没法进食的状态,恰好赶上卓越活动买了这书,靠它来解馋。我记得书里讲过粥(此书最大的好处在于,随手翻到就可读,读完一遍再读也不会嫌烦),凉粥和热粥的配菜。我小的时候暑假都在奶奶家,睡过午觉后,刷过牙洗过脸,奶奶就会端出蓝边大碗的凉粥,夹一些中午的剩菜,坐在椅子上慢慢吃,总会叫我也吃上一碗,我一定会拒绝,粥是好的,可凉粥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我喜欢热的食物。
做饭的话,我以前学过好几次,都失败了。作为一个坦荡荡的女汉子,每次都说终极目标是当家庭主妇一定会被笑话的,但这的确是我的终极目标。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你饿的时候,煮饭给你吃。我想知道倾尽一切对一个人好是什么滋味。
哎又歪了。
《无非求碗热汤喝》读后感(十):我饿了 我想你
我生来就是个吃货。
老妈经常跟我提起这个段子,说在医院第一次给我冲奶粉的时候,住在同一病房的产妇说,如果在奶粉里放点橘子汁,孩子会更爱喝,她不光是说说,还热情地往我的奶瓶里放了一勺橘子汁。果然我很开心地喝光了。下一次再喂奶的时候,我却无论如何不肯喝。大人们都觉得奇怪,上一瓶奶喝得好好的呀,这是怎么了?送过橘子汁的阿姨突然灵光一闪——这孩子该不会是喝出奶粉里没放橘子汁吧?我爸一听说,赶紧出门买了一瓶橘子汁回来,等兑好橘子汁再给我喝,我毫不犹豫地很快喝光了。老妈说,大人们为此笑了很久:刚出生的孩子啊,竟然能喝出奶粉里加没加橘子汁!从我开始记事,妈妈就不断讲起这个橘子汁的故事,直到现在我的年龄已经跟当年老妈生我的年龄相差无几,而老妈依然会笑容满面地对我讲起这个故事,她看着我的眼神,就像我还是当年那个哭着要奶喝的娃娃一样。
不再喝奶之后,我最热衷的食物可能就是羊肉串。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长大了要嫁给卖羊肉串的,那样就能随便吃了。通常小孩子不爱跟大人一起逛街,因为大人要买的东西小孩子根本不懂,街上能看的东西又都被大人们的身躯挡住,眼前晃来晃去的只有各种腿和鞋,还得时刻小心千万别跟大人走散。但我小时候却特别盼望着能去逛街,因为街上卖羊肉串的摊子是那么多,隔着老远,羊肉串的香味就飘进了鼻子里,望着那些拿着大蒲扇扇起一阵阵烟气的卖羊肉串的叔叔,发自内心地觉得他们真神气!当然如果是跟着爸妈一起去,那么肚子里的馋虫还有一点点被满足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只跟着爸爸出去,那么不要说开口,哪怕仅仅在羊肉串摊前多做停留,或是流露出某种渴望的眼神,那好,一顿臭骂算是不可避免了。如是几次之后,在街上再看到卖羊肉串的,我走得比爸爸都快。
上初中之后,某个晴暖的初夏傍晚,老爸的下班时间早到了,却迟迟没有回来。老妈和我正一致断定老爸肯定又跟某个同事聊得忘记了时间,家里的大门却突然被打开,老爸一只手推着自行车走进来,一只手神神秘秘地藏在背后。老爸停好车子,慢悠悠地朝我们走过来,眼睛发亮,忍住笑,故作神秘地问我:“闺女,你猜怎么着?”“怎么着?”“我给你买好吃的来啦!”说着,他把背在身后的一只手拿出来——一大把羊肉串!“哇塞!”我欢呼一声,赶紧接过来。“整十块钱的,这回让你吃个够!”老爸脸上的得意劲儿就像他刚当上了地球球长似的,他神气十足地吆喝老妈:“孩儿他妈,快先拿点纸来,拿了这一路,羊肉串上的油流了我一手!”
高中时期,我开始尝试各种奇葩的食谱,比如每天只靠三杯咖啡过一周啊,一天七个鸡蛋吃半个月啊等等。高二时几乎喝遍所有冲泡制品,什么红茶绿茶花茶奶茶,豆奶豆浆芝麻糊,凡此种种。我的桌子内外,共摆着四个杯子,分别有其独特的职能。一次我正在泡柠檬片,坐在旁边的男生看了,非要尝尝什么味儿不可。我警告他很苦很难喝,但他不为所动,非喝不可。我只好给他泡了一杯。要喝的时候他叫我:“欸,我要喝了啊。”我一边说好,一边盯着他的脸看。他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马上皱起来的眉毛跟费劲的吞咽逗得我乐不可支。我笑着问他:“怎么样?很难喝吧?”他做作地扬扬眉毛:“谁说的?味道好极了!”
高三开始没多久,我就已经吃不下学校食堂里的饭,每天最困扰的难题不是“这道题应该怎么做”,而是“下顿饭究竟吃什么”。一天体育课下课,班上的同学们都跑去食堂吃饭了,而我买了一包干脆面和一根冰棍儿回教室吃。我刚打开包装袋,班里的一个男生突然走进了教室。他从坐在第一排的我身边经过,看了我桌子上的吃的一眼,问:“你中午就吃这?”我说:“是啊。”他又问:“这样不会把胃吃坏吗?”我满不在乎地说:“哪能呢,咱的胃,铁打的。”他朝我笑了一下,走到了自己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座位。他的话和他的笑容,让我莫名其妙地陷入恍惚。这一恍惚,便是两年。
上大学之后,自从搬进新校区,宿舍里就没停过喝酒。有人过生日,喝酒;买了零食吃,喝酒;找个电影看,喝酒。但喝起来都是小打小闹,一瓶或一罐,喝完跟没喝一个样。大四下半年的某一天,大家不知怎的突然有了“不醉不归”的豪情,要大喝一场。于是四个人从超市里拎了16瓶啤酒、一小瓶白酒跟一大瓶可乐。超市的收银员一边给我们结账一边笑。交完钱,四个人或背或拎或抬,好不容易才把这堆杯中物弄回宿舍。一开始的两瓶,大家还斯斯文文的,喝到第三瓶,场面明显开始失控,说话的声音明显高了几个八度,笑声也开始往狂野方向上走,如果不是宿舍面积有限,估计群魔乱舞的局面也不是不可能出现。喝完第三瓶,几个人都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一开始本来商量好不再开剩下的酒了,但是拿着起子的那位突然嘿嘿一笑,一口气打开了剩下的所有瓶子。没办法,本着不能浪费的精神,只有硬着头皮喝下去。终于,有人实在喝不下逃走了,有人支撑不住跑到床上躺倒,还有人吐了个一塌糊涂。这次喝酒经历让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个特异功能,或许也可能是缺陷——不知道什么是醉。就在别人喝多了酒自顾不暇的时候,我竟然还能先默默喝完剩下的酒,再把一片狼藉的宿舍收拾停当。“拟把疏狂图一醉”,如果真的不会醉,那么人生未免清醒得太过可怕了吧。
过去,我由衷热爱过一些吃的,也切齿痛恨过一些吃的;为吃,我曾挖空心思,也曾予取予求。而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吃。
我只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