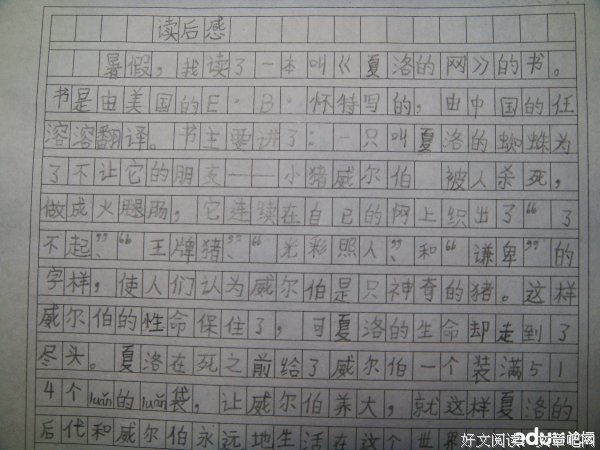《对空言说》读后感10篇
《对空言说》是一本由[美]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41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对空言说》读后感(一):邓建国 彼得斯《对空言说》译后记
Original 2016-12-27 邓建国
本书2003年有一个译本《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译者是我国著名翻译家何道宽教授。
我之所以重新翻译该书是出于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的一种焦虑,它源于“该书很重要”的认知与“该书读不懂”的现实两者之间产生的撕扯。经与校内校外很多教师同行和研究生交流,我发现这种焦虑普遍存在,于是就有了这个重译本,目的在于恢复《对空言说》的本来面目——一本联通传播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阅读的经典之作。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就是让它能被“读懂”。
我最先接触到本书是2004年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读博士期间。此书2003年被作为复旦大学“传播、文化和社会译丛”之一引进,一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的必读书。当时我对传播思想史/观念史的兴趣和了解都尚处在懵懂阶段,觉得这是一本“奇怪”的书,读不懂乃纯粹是自己水平太低。
2013年-2014年,我到哥伦毕业大学新闻学院访学,发现该书是传播学博士项目导师理查德·约翰(Richard John)以及迈克·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研讨课上的必读书。在哥大的听课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该书的兴趣和迎难而上将其攻克的决心。于是我在亚马逊上买了一本英文原著,读后发现,原著内容虽有一定难度,但英文结构清晰、表达流畅,颇好理解,读来趣味盎然。于是我决定重新翻译此书,并参考大量资料在适当地方添加注释(《对空言说》全书有译者注共250余处),以帮助读者在理解原著上进一步“跨越鸿沟”。所以读者现在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中文译本,而且也可以说是一个中文译文加注释本。
翻译的主体工作是从2013年底开始。我在离曼哈顿哥大新闻学院(116街)只有咫尺之遥的109街一间斗室里不断耕耘,窗外飘着大雪。这是一间房价极高,但条件却很糟糕的房间,采光阴暗、供暖不足,而纽约的冬天寒冷漫长。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仍唏嘘不已。翻译工作时断时续,基本与我在哥大的访学相始终。期间也会到哥大新闻学院普利策楼的5楼上课,参与两位理查德和舒德森两位导师的课堂讨论;有时候,还有幸与两位教授一起进餐,边吃边聊,地点就在学校附近的中西餐馆,轻松随意。记得有一次舒德森教授带我去了一家希腊餐馆,餐馆的名字叫“Symposium”,该词既可指柏拉图的对话《会饮篇》,也可以指“学术研讨会”。餐馆的菜单当然是“It’s all Greek to me”(英谚,字面意思为“这对我而言都是希腊文”,引申意为“我根本不懂。”),但与舒德森的聊天却很开心。他对我的学术兴趣和手头的翻译工作给予了不少指点和鼓励,让我很受鼓舞。
学术翻译是一件苦差事——它做起来极为吃力,但可见的效益(同时在学术考核和金钱回报上)却极有限。正因如此,几乎每次在结束一个翻译项目后,我都会发誓绝不再做任何翻译。然而对于自己极有兴趣的作者和著作,我常常是带着自学的想法开始,但读着读着又动“何不顺带翻译出来?”的念头,最终以令我腰酸脖子痛的翻译结束。翻译过程快乐而痛苦,痛苦而快乐,这也许就是译者的宿命罢。
在微博上,有网友说道:“现在的我对西文学术书籍的中译抱着感恩的态度,也愈发不理解一些因为翻译问题就大发雷霆的读者。其实你想想,只要原著几十分之一的价格,可以买到一本书,所有外文单词都给你查好了,尽可能按通顺的方式组合给你读,让你可以快速、高效看到书本的‘义理。这多好!而‘辞章’对学术书本来就是次要的。”
我觉得,此观点既有道理,也不全有道理。有道理是因为,学术翻译确实不易,在它不计入学术成果考核,翻译报酬“相当于零”的背景下,学术译者的辛劳得不到对等的回报,仍然不辞辛劳,迎难而上,实属不易,因此值得体谅。此话不全有道理是因为,由于版权保护原因,一本书引进后其首译本与重译本之间往往要间隔十年以上。因此译者——尤其是对名家名作——要尽量保证首译本的质量,否则会给著者作品在读者中的接受和传播带来极大的误解和阻碍。
在回复以上微博网友时,我说到,“学术翻译是否可以在学术圈内实现社会化,即将原著和译本在网络上公开,让感兴趣的读者阅读、比较、讨论,以快速实现一本的迭代改进,最后得到最接近原著的译本。”但是显然,如果保护原著版权是实现这种社会化翻译的最大的挑战。鉴于这一挑战在近期不可能克服,所以我们只能希望译著的首译本能尽量保证其质量。
何教授将书名译为《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台湾学者夏春祥教授认为这一翻译存在着三个不足:
一、结合彼得斯自述“此书为1986年文章的回应”,以及他的探究多在厘清传播领域中大众传播研究角色的脉络,communication应该译为“传播”才算是恰当的理解,毕竟他在经营、回应的是自身在传播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愿景期盼与阅读经验。
二、思想史和观念史不同,而彼德斯谈的是传播作为一种观念的演变历史,因此将“the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译为“传播观念史”比较恰当。
三、在英文原著中,“无奈”的情绪或许是书中论及传播的背景之一,也是论证的起点,但到了全书后半段,尤其是第五章与第六章,彼德斯发展了一个相当正面且积极的理解,指出媒介对于本质性传播问题的现实作用,继而带出了传播概念中“身体”面向(此时若以中文来表达,比较贴切的词汇是沟通)的重要性,因此,片面凸显“无奈”反而局限了全书主旨的彰显。另外,书的主标题Speaking into the air源出于新约《圣经》。考究圣经原文,该段话确实有“意思无法传达”、“表达出来的话语,他人无法理解”之意,但同时亦有“信念坚定,不受影响”的指涉。
基于以上三点,为了更忠实地回应彼德斯在书中的主要想法,夏教授建议将书名译为《话语的摸索与寻绎:传播观念史》。
我完全同意夏教授以上三点,但觉得他建议的中文译名为“信”而过于累赘。我认为中文中的“空”字较能精炼地译出彼得斯使用“Speaking into the air”的两个意图:交流鸿沟之不可逾越,使人如对“空”言说;因此,我们应采取“撒播”的交流观,如广电对着“空”中播音(on the air),让“有耳者,皆可听”。因此结合与彼得斯本人的交流,与复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的商定,以及与南京师大卞冬磊副教授以及彼得斯门下诸位学生(现在也早已为人师)的邮件讨论,我最后选择将书名译为:《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
在考古学界有一个貌似悖论的共识,即对古代社会,离开解读对象所在时间更久远的研究者可能要比近者更能全面了解考古对象。这是因为,相较早期的研究者,后来的研究者具有“后发优势”,能获得更多的其他考古发现和更强大的研究分析工具进行“三角校正”(triangulation),帮助解开当下的考古之谜。《对空言说》出版于1999年,距2015年已经有16年了。这给我这个译者以一个后发优势——在阅读彼得斯出版此书后的各种论文和专著后,再看这本《对空言说》,我有如具备了“上帝之眼”,对他思想的来龙去脉有更加清晰的掌握,这对于更流畅地翻译原著无疑助益巨大。另外,此译本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即何道宽教授的首译本基础之上——进行的。何教授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翻译筚路蓝缕,功勋卓著,我在此也向他致敬。
本雅明在论翻译时说,译作和原文之间无“忠实”可言,而“忠实”也不是翻译的终极目的。这当然是他别出心裁的高论,但忠实原文却实应是对译者的基本要求,因此在翻译中我力求做到这一点,然彼得斯作为“文字大师”的隽永耐读,却有时不得不“心向往之,实不能至”。彼得斯写信给我,赞赏我作为译者的艰难付出。他说,“你知道,德语词‘任务’(Aufgabe)的原意是‘放弃’。这多么有趣啊!”翻译《对空言说》这一“任务”完全源自我对该书中的兴趣,在翻译过程中也多次有“放弃”的念头。但读彼得斯,他的思想和文字让你欲罢不能,所以完成这一任务,固然艰难,却是我目前为止收获最为丰硕,最引以为豪的译事。此书的翻译从2013年底在纽约开始,能在2015年底在上海完成,这也算我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尽管我作为译者想让自己的译作尽量不留遗憾,但遗憾终究难免。读者如在阅读中发现错误,一定归咎于我,并希望能不吝来信指出,以便我改正。我的电子邮箱是:dengjianguo@fudan.edu.con。
邓建国 2015年12月30日
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办公室
........................................................
《对空言说》读后感(二):对话与撒播的交流话语对撞
彼得斯的研究目的是对一次重大变革——19世纪后期人类用“具有彼此交流的能力”来自我定义——作开创式的追问。他的研究思路有三:一是对“交流实现灵魂融合”的妄想进行批判;二是对普遍的“交流失败感”追根溯源;三是对理解交流的新思路——中立交流观——做出尝试性探索。 作为观念史书写的《对空言说》,彼得斯谈到了更为具体的观察对象——人们对交流观念提出的种种要求,这本书试图梳理这些要求的提出,并将“交流”从这些要求中解放出来。 通过这样的研究思路来实现研究目的,自然要紧紧依托变革的时间节点——19世纪后期,更恰当的(或许不够严谨?)表述或许是彼得斯所称的“詹姆斯时代”,也正如彼得斯所说的,交流(communication)是典型的20世纪观念——当然,这不是一种创造,而是类似于“后真相”一般的“重新发现”。 对于“交流困局”的研究传统来自于几个方面:各种思想家;20世纪的大众文化,尤其是科幻;20世纪的戏剧、艺术、电影、文学;(20世纪以来的)各色知识分子。 交流不可或缺,交流满是问题。交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反思的力量,也是一种建设的力量。它使得人们反思民主、反思爱(love,似不仅指男女间的“情爱”,或可理解为“兼爱”“博爱”?)、反思这个变化的时代(当是成书的千年之交);它也是解决公共及个人困境的关键。 交流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不可交流性”。这既指人与人之间性别(大男子主义)、阶级(门当户对观念)、种族、年龄(代沟)、宗教(伊斯兰极端势力)、地域(地图炮)、国家和语言(这本书中林林总总的翻译问题)的边界,更存在于人与兽、人与外星智慧、人与智能机械之间。 人们渴望交流的背后,是痛感社会关系的缺失,对越是不在场的人、事、物,这种渴望则越加强烈。 交流是载入渴望的记事本,它召唤理想的乌托邦——没有误解、坦诚相待、自在发生。 彼得斯对交流观念史的书写,采取本雅明式的建构叙事——一种积极的、六经注我的写法——以“当下”观照“过去”,试图发觉某种纵向共时性的“暗合”。 研究范围截止到20世纪中叶,也即二战结束后不久,但却上溯到苏格拉底、耶稣的时代,漫长的时间跨度是可以推测出叙事中集纳百家学说可能的。 彼得斯的史观可以摘引几句话以求管窥,“横向的空间有共现性,纵向的时间也有共时性。”“过去的现象会选择性地在当下复活。历史并非总是以单线展开,而是以星罗棋布、群星灿烂的方式呈现。”“各个时期的一切历史著述,包括那些明确号称是对过去的忠实记录的历史著述,其实不过是作者对特定时代的一种评述。”何等的精辟! “现在可以为过去描绘轮廓,从而创造出各种相会点,实现我们与过去的重逢”,彼得斯在行文过程中一直渗透着这个观念。 为什么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交流”问题?——交流的麻烦被写进了人类的境遇之中,彼得斯如是说。交流问题的产生,源自个人经验的私密性(这又因为人的感知和感情总是独特的),即,人与人之间总不能像电线那样相互连接。 这算是问题吗?不算。彼得斯关注的是另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人们在谈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从来没有把“不同心灵间无法实现直接交流”当作前提——尽管这一前提是正确的。 有关交流问题的悲观色彩(彼得斯称之为“宏大而哀婉”)又启自何时呢?——“詹姆斯时代”——这使得“交流”的观念被“重新发现”。 19世纪末围绕个体本位而产生的两个新词让“交流”营造出了两幅完全不同的梦境。个体本位文化的问题在于,围绕个体心灵立起的一堵墙。认为这堵墙难以穿透的“唯我论”让“交流”再无可能,成了孤立的个体在迷宫中摸索道路的噩梦;反之,认为这堵墙一捅就穿的“传心术”让人美梦成真,仿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瞬间可达”。 “交流”的二元属性(既是桥梁,也是沟壑)由此可见一斑。新技术的出现与招魂术对新技术的认同,则是彼得斯对这一认识的归因。 因为新技术的介入,交流的概念也从“物质迁移或运输”变成了“跨越时空的准物质连接”,交流问题的本质也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转化成了技术上的降噪问题。 交流的含义是多样的。经彼得斯梳理,“交流”(communication)一词的意义主要有:传授;(物质的及作为物质的观念、思想或意义的)迁移、单向传输(如广告、公关)、发射(如光、热);双向交换、(亲密无间地)交谈、灵魂融合(惯常所说的“你懂我”);各种符号互动。 彼得斯开玩笑式的一句话,可以给人以理解所谓“名言警句”的启发:“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格言警句,由于我们对它们太不加检视,结果任凭它们将太多的东西径直扫到了地毯下,被我们所忽视。” 彼得斯将“交流”一词按照单复数的不同,划分为两种指向。复数的communications指的是信息或意义传播的技术或手段(威廉斯称之为“制度与形式”),坟墓(与往生者交流)、象形字符(原始的人际交流)、书写、钱币、教堂(与神对话)、邮票、旗帜、时钟(这个例举很巧妙,两位译者的省略不知是何用意?用波兹曼的话说,钟表的发明引入了一种人和上帝进行对话的新形式——时钟的滴答声驱走了所谓的永恒)、报社、邮局、电信技术、摄像技术、照相机、电话、唱机、广播、电视、电缆(为什么会译为“有线电视”呢?)、电脑、因特网、多媒体、虚拟现实;单数的communication指的是“我”与“他”为达成理解而做出的努力。 这里还应该补充一种用法,彼得斯文中使用带有引号的“communication”,往往指的是将交流视作“灵魂融合”的空想,或“交流的梦想”(the dream of “communication”,此译似不妥)。 两次世界大战后,“交流”的观念也两度成为论争的焦点。20世纪20年代,先后涌现了5种认识交流的视野。这可以分为两大类:承袭19世纪后期的3种认识及2种少有人追随且彼此对立的独特看法。 Ⅰ communication是播撒管理舆论的劝说符号(何:交流是对大众舆论的管理,略改动,communication as the management of mass opinion)。 Ⅱ communication是澄清语义不和谐的手段(何:交流是对语义之雾的消除,communication as the elimination of semantic fog)。 Ⅲ communication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何:交流是从自我城堡中徒劳的突围,communication as vain sallies from the citadel of the self)。 Ⅳ 海德格尔(何:交流是他者特性的揭示,communication as the disclosure of otherness)。 Ⅴ 杜威(何:交流是行动的协调,communication as the orchestration of action)。
《对空言说》读后感(三):巴别塔与巴别塔毁灭之后
我之前洋洋自得地写过这样一段话:
传播的终极目的是对话,通过对话来抵消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隔阂和冲突。对话本身就区别于灌输和宣传,权力意味没那么浓。如果要幻想传播学的学术愿景和乌托邦,那应该是一个人人可以自由交流、平等对话、相互理解的世界。看彼得斯的《对空言说》,才意识到“对话”之论的缺陷也如此之多。在最原本的意义上,对话是少数人间面对面的具体交流,口头语言和表情动作一起承担着思想的传达工作,但对话为交流设立的标准又太高,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内,对话要求对话者自由平等理性批判,此外对话还要求回应,这种回应近乎“强迫”。而当前,我们对“对话”的一致推崇实际上已经构成了霸权般的规范,作为交流的工具,它并非是至高无上的唯一。
因此,彼得斯在“对话”外提及“撒播”,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一对重要概念。
彼得斯将对话追溯到柏拉图的《斐德罗篇》,其中描述了苏格拉底与斐德罗的故事,苏格拉底还演讲了自己对对话和文字的看法,他认为口头的对话是具体的互动,而文字没有人性,缺乏亲切感,忽视听者的个性。这种担忧一直持续到我们对大众传播的看法,在文字之后,我们担忧广播和电视。
而撒播的意象则来自圣经福音中的“播种者寓言”,其关键是“凡有耳者,皆可听,让他们听吧”。“撒播”成为一种公平公正的交流形式,它将意义的收获交给接受者的意愿和能力。这就意味在撒播的时候,更关注内容,而非接受者的回应,这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爱”。因此,彼得斯说:“单向的撒播应该是我们更加冷静的根本选择。”
然而,无论是对话还是撒播,都难以弥合交流中的沟沟壑壑。我们需要交流(不管是对话还是撒播),正是因为我们在交流中的无能为力,那些难以消除的误解,那些不被听到的声音,“我们渴望交流,这说明我们痛感社会关系的萧条荒芜”。
彼得斯笔下,交流呈现出两个方向:“传心术”和“唯我论”,这也是交流的两个极端。前者有天使学的影子,作为上帝的信使,它能实现灵与肉、神与人的对接,“传心术”就是思想的无障碍共享,是人与人之间“瞬间可达”的交流美梦;后者则认为“个体是意义的主人”,“自我”是交流的阻碍,我们的思想在脱口而出时已发生变形,在记录成文时便成为无主幽魂,人们像是被困在封闭的房间,威廉·詹姆斯写道,“这样的思想之间的割裂,是自然界中最绝对的割裂。”
在《圣经·创世记》中,关于巴别塔有如下记录:“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巴别塔构成了一种交流的隐喻,“传心术”和“唯我论”就像是描绘了巴别塔与巴别塔毁灭之后的两个世界,第一个世界人们言语相通,交流的力量非常强大,而在第二个世界里,即巴别塔毁灭之后,交流成为一种不可能。
不管是“传心术”还是“唯我论”,极端性都让它们难以轻松立足。但纵观人类的历史,我们都竭力逃离“唯我论”迷宫般的噩梦,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各种中介来实现彼此的联通,向着“传心术”迈进。也因此,每当新的媒介技术出现,人们都要感叹美梦成真,但也用不了多久,我们再次向交流之无奈低头。
先是让口语保存成文字,以为思想记录在案可以穿越时空,但在苏格拉底看来,作者的缺席让文本失去指向,成为滥交的撒播。后来,又用留声机抗衡随着时间一并消逝的声音,它同样具有两种特征:忠诚(对原声一成不变,忠实记录)和滥交(对听众不分对象,滥交撒播)。电话开始实现远距离的通讯,一对一的交流有时候却成为了相互交叠的独白。无线电广播也摆脱不了对大众传播的习惯性批判,即使它模仿对话场景,让人倍感亲切,让人以为“这是特别说给你听的话,而它实际上是说给所有人听的话”。
这让我想起《Sense 8》里的“传心术”和思想的接触,有人评价说主角们实现了人类“最大限度的不孤独”;想起王菲在《打错了》里的歌唱,电话让交流成为两段彼此隔离的独白;想起电影《HER》里,人机交流的虚伪性。一个机器对着你说话,但实际上她也对着所有人这么说,我们对人机交流的渴望,其实就是对思想接触的渴望,对“传心术”的渴望,对一个更懂自己的“哲学之爱”的渴望,但是电影中恋情的失败显然在告诉我们,依托于媒介的交流,也被媒介所阻碍。
在“死信”的篇章里,彼得斯写下这样一段话,它很长甚至“老调重弹”,但足够引发深思。
永远无法送达的信——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说明交流误入歧途之后使人扼腕的哀怨呢?我妻子在脑子里哼的曲子、我醒来时忘掉的梦境、小孩子独自与自己的玩偶进行的聊天、我躺在枕头上时耳中听到的自己的心跳、深埋在冰川表面一英里以下的猛犸象肉的气味、日本神风飞行员衣袋中的家信;对奥德修斯船舱中的船工和士兵来说,女妖都对他们唱了些什么?处于紫红色与红色之间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牙医给牙病患者施加麻醉后实施手术时,患者的牙周神经有何感觉?有哪些伟大的作品被埋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事物内部的颜色、湿度和温度如何?对所有这一切问题,我们都容易一笑置之,嘲笑这又是在老调重弹那个过时的难解之谜——“密林中一棵树倒下,若无人听见,那么树倒声还真存在吗?”但是,我却不觉得是在老调重弹。“死信处”的信化为灰烬,而发信人却不知道信已丢失,收信人又不知道信是否真寄出了。你说那被烧掉的信,其意义何在呢?意义何在呢?它们是我们存在的鬼魂,被放弃也被捕捉,是我们交流的渴望和失败,悲哀而神圣。
《对空言说》读后感(四):知识性的记录
一,对话与撒播
《斐德罗篇》《对观福音书》
彼得斯提倡撒播
二,一个错误的历史:招魂术传统
奥古斯丁
天使作为交流的完美象征,没有肉体
17世纪洛克,意义的个人属性,交流的悖论
18世纪,招魂术,催眠术
彼得斯:无法保证完美的交流
三,走向更加强有力的精神视野:黑格尔、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
黑格尔:
马克思:批判货币,撒播。
克尔凯郭尔
四,19世纪,人与人的接触经历了重要变化
信息传输、信息记录
打破时间束缚(照相机、留声机)/空间束缚(通讯技术)
唯我论、心灵研究与
唯我论的物理对应物:麦克斯韦
对动物、外星人等的讨论:人类之间的交流已经存在鸿沟,更何况与其他物种以及地外智能?
《对空言说》读后感(五):在与他者交流失败的基础上努力实现自我对话好了
“交流不是关于思想运输的社会物理学,而是一个充满风险的领域,在其中任何人说话都必须为他从来就无法完美驾驭的东西负责——这个无法完美驾驭的东西,就是说话人的言行在听话人的心灵中产生的作用。对自我或世界的真实再现不仅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充分。相反,这里需要的是,甘愿自我克制,实施行动,从而为他人激发真相。交流的问题并非源于语言的捉摸不定,而是存在于自我和对方之间无法修补的分歧。交流的挑战不是如何做到忠实于我们的内心,而是坚持即使他人不能像我们看待自己那样来看我们,我们仍然能做到宽恕待人。”(詹姆斯)
——381页
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以如此愁绪万千却又感恩于心的样子读完这本书的最后一页。
对我来说,在这段传播的观念史中,有些内容的确是极为陌生了。或者说,有些学者的思想我仍然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但对于学术性极强的这本专业必读书,我仍然想尝试去揭开自己眼前的幕布,体会另一个舞台的世界。“交流更多的是一种关系政治日常、道德伦理的东西。”这是本书一直在强调的思想。回顾整本书,彼得斯宏大视野下的交流观不得不让我钦佩,在他的引领下,我发现无论是库利崇拜的精神交流,还是上文詹姆斯信奉的教义式交流,都已经极为鲜明地为我们挑破了这个世界中暗藏于交流躯干上的血脉。
于是,回想我生存的世界,环顾我周围的环境,原来满满都是交流失败的痛苦,而这种痛苦的来源却极为简单而又现实。
无征兆的吵嚷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挡箭牌。你争我吵的埋怨式日常是我最熟悉不过的生活了,我也是沉浸于这样的环境读完了这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对着詹姆斯的那段话想了又想,读了又读,究竟是因为什么使我身边的人只能用这种方式去交流问题?究竟是因为什么才导致他们交流失败?双方之间“无法修补的分歧”又是什么?最后,我思考的结果恐怕就是——现实生活的剥削与自我消解的障碍无时无刻不在缠绕。
人们交流失败最初的表征即是双方意见出现分歧,却没有任何一方妥协或退让。坚持己见的出发点也无非是为了证明自我的存在意义,而否定对方的行为动机。渐渐地,当现实将其捆绑践踏、无情吞噬时,矛头就直接指向了身边最熟悉的对象。于是,大家误以为将争吵作为发泄情绪的有效方式,以此掩盖双方交流失败的真实样貌。这样的心理循环不只指涉了整个群体,还包括自我对话失败的模样。
如果能够站在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如果能够做到詹姆斯所说的“宽恕待人”,是不是吵嚷就不会发生。至少不会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他人,又否定自己。我崇拜库利口中的精神交流,但我却不相信它有一天会在人类中实现,至少不会是以人类的思维方式去实现。生活在充斥着金钱诱惑的现代社会里,我们需要和这些物质性产品产生共生关系,我们无法做到置身事外的模样,而人类就是这样不完美的动物。我们心怀期望地去跨越人类之间的鸿沟,却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法兰克福学派恐怕就是因此才如此抵触这个现代性社会吧。
可是在另一方面,人类却是如此伟大的。我们虽然无法以人类思维去判断外星人的思想和行为,但是至少会产生颠覆世界的思想,这个世界大至宇宙,小至个人,而这个思想却囊括了一切物质,包括尘埃。我们能够习得感恩的心态,能够改变积存已久的恶习,我们能够产生与他者交流的欲望,能够去尝试对话的可能,甚至能够接受对话的失败却从不放弃对它的探索,这是不是已经足够令我们拜托那种心里束缚了。
所有的这些矛盾、冲突、肯定、怀疑,都是人类的本性,也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不完美之处。也正是如此,才诞生了无数哲人为了让我们更完美而探索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交流之路,企图实现西方古世界宗教外衣下的“天使交流论”,这条道理毫无疑问地会被后继者继续开拓下去,而对于组成人类这个群体的每一个基本单位来说,究竟如何做才能够帮助自己完成交流的使命,如何平衡现实与自我的内心冲突,我想彼得斯已经给出了答案:
“毕其一生,每个人只有时间给少数几个人以关爱。我们这些肉身凡人只能个别地去爱;不过,没有博爱之心又是不公正的。爱之悖论是,边界的具体性和要求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我们只能够和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共度时光,只能够接触一些人而不是所有人,因此,亲临而在场恐怕是我们能做到的最接近跨越人与人之间鸿沟的保证。在这一点上,我们直接面对的是我们的有限性,它既神圣又悲哀。”
《对空言说》读后感(六):Approximation is (pragmatically) enough for macro beings
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new-theory-cracks-open-the-black-box-of-deep-learning-20170921/ 黑箱的存在可能就是信息传递的最优scal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formation_bottleneck_method 人类和人工神经网络很难解决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以及细微差别影响结果的问题; 只留下与一般概念最相关的特征,去掉大量无关的噪音数据 https://arxiv.org/abs/1503.02406
这是何道宽译的《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的重译。ironically, this translated book itself is an example of information redundancy (whereas it's not some kind of 'redundancy' for the purpose of flexibility and self-correction in many bio systems)
------------
个人认为内容(semantics)以及组织内容的函数/算符(grammer)是客观存在的,而如何认识这些内容及其组织的逻辑,不同的表达工具(representation/syntax/media),只会影响人类认知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