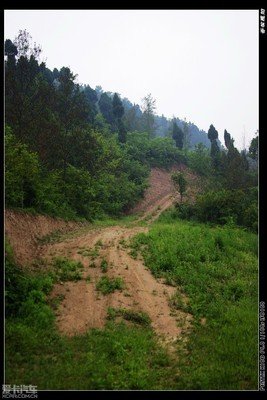此地不宜久留
夜里回家,遇到值班的公寓管家。好久不见,我说。她说,好久不见,最近工作到很晚的样子啊。我说不是最近,是很长一阵子,都是这样的了。
正打算拿钥匙开门,她继续开口说着。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你吗?我疑惑:他们?他们是谁,说我什么了?她答复:就是我们几个轮流值班的管家。
我低头笑着,又想要摇头。一些复杂的心情。
他们还说,你很温柔。你太温柔了,从你搬进来这里,我们没有见过你发脾气的样子,没有见过你恼怒的时候。你好像对谁都很客气,清洁工、快递员,还有我们这几个人。你从来不会像其他有些租户那样,会区别对待我们。
还没来得及答复些什么。她又添了一句:你的性格很好,很温柔;你努力工作,会赚钱;你应该会有很多追求者吧?
我终于叹了一口气。
我不打算跟她交谈些什么,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时机,这样的环境,都不适合我们两个熟悉的陌生人,展开一场议题这么深远的谈话。
我的脑子在飞速运转,想要找到一句话,结束这个话题。这个时候,她问出了这一句:我可以问问,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温柔吗?你的秘诀是什么?
我在发愣中,尚未找到可以答复的那一句话。她像是识别出了我的无奈,笑着说:我没关系的,我就随口一问。
我下楼去忙了。祝你晚安。
我拿出钥匙,打开门。拥抱我的板栗。一些温柔的交谈与抚摸。我们出门散步。夜凉如水,脑子里在盘旋着一些声音,关于不久之前的那些画面。
你为何总是这样温柔?因为我已经受过生活的百般虐待了,所以我的脾气已经被消耗光了。这是官方答复。
更进一步,我可以说:因为自己从前被别人,被生活为难过,我知道那种感受。所以今时今日,我尽量不想去为难别人,以任何理由,任何神情,任何情绪施压。
我还可以说:我与你们并不熟悉,所以当然不会把真实的喜怒哀乐呈现出来。——可是转念一想,那是否就意味着,我对于陌生人总是友好客气,但却对身边的亲近之人随意上演情绪化模式?
并不是这样的。我很清楚。我对所有人,大约都是温柔的。无论是陌生人,还是自己的友人与亲人。但是这份温柔,来自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二十五岁以前。关键词是怯懦。这是非良性的温柔。
我害怕与人争吵,害怕被人“进攻”——一种无以名状的社交恐惧,从久远的童年扎根,直到成年。我不敢维护自己的权利,处处忍让。我总觉得,只要不必发生争吵,怎样我都是可以活下去的。
年少时候经历父母争吵,我在河边看夕阳很久很久。不敢回到那处叫做家的地方。即便我知道,此时此刻,争吵已经结束,母亲正在做晚饭,父亲在客厅看电视。你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可是一切却并没有结束。
这并没有结束,是因为你知道,那些争吵并没有解决本质问题。来日那样的争吵会持续发生,会不断上演。他们不会离婚,不会丢弃你。可是午夜梦回的时候,你却又觉得,其实他们分开,也不是一件那么恐惧的事情。
只是奈何这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命运。大约与你无关。
再往后,一些人际关系上的困扰。从学生时代到职员阶段,我总是尽可能地避免冲突。我知道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可是我依旧困扰于那些繁琐——课堂上老师与学生的不合理争执,办公室里那位同事一面骂着上司,一面笑脸地走进上司的办公室。
为何人可以做到两面派,甚至是多面派?我充满疑惑。我的几任上司告诉我,这个世界的运转法则就是这样的——在一个能量场,会有强弱之分;你不参与斗争,但是也难免被斗争伤害;你要么忍耐,那么出局。
哪有那么多“本质”需要解决?他们说。等你到了一定年纪,无能为力了,或者被虐惯了,也就没脾气了。
有人告诉我,如果你想知道自己会在一家公司,或者一个行业做多久,去看看那些你比多入行十年二十年的人——他们的言行举止、样貌神态、气质气势。问问自己,你是否想要过上那样的生活,成为他们中的一个?
若是肯定的答案,那就努力向上,不问回头路。若是否定的答案,那就早日准备,预谋别离。——这是我在二十岁出头,得到的有效忠告。
在某个年岁,我的性格(或者说性情)极为矛盾与割裂——一方面是忍气吞声,另一方面是突然发怒与崩溃。长久以来的积压,转换成了抑郁常态化。
那时候我没有解决之道,只能沉入海底。我本以为一辈子就这样了,一辈子生活在这种忍气吞声的“温柔的我”之假象中。
我并没有被具体的谁拯救。电影中的一句话,我很爱的作家(赫尔曼·黑塞和艾丽丝·门罗),几位心理医生,一些启迪角色的长辈。他们像是一些偶然事件的运送者,各自在不同时期为我送来这些碎片拼图。
只是突然地,在二十七八岁开启之后,我就完全拥有了这份权利——第二阶段的温柔,良性质地的温顺与宽容。
我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善,我只是被那位公寓管家的话给提醒到了——
“起初我们以为你生了病,气息不稳,所以说话总是低声温柔的。可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你就是个正常的人——健康而忙碌,但是看起来胆识过人。所以我的疑惑是:如果你没有被什么力量(生病缘由)所压制,你怎么会可以一直这样心平气和地,温柔着?”
那一刻我才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真的变成了脾气很好的那一个人。不是隐忍,不是强压,甚至不需要自控力这件事。就如同吃饭喝水,沐浴更衣,这一句话——“怎样都是可以的,怎样都没关系的。”——就这样真正地被种在了我的身体上。
我并没有觉察到这件事,直到被人提醒。以及是这几年好些次这样的提醒。
从前在被问到这个疑惑的时候,我总是拿一句“我本来说话就这样的啊”答复了。可是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我本来并不是那样的人。
一定是某种启示,某种尚未被我发现的启示。
一些日子之后,收到一位旧友的消息。她问起我什么时候去深圳,她想要跟我约一个时间,从家乡(昆明)那边过来。
她与我一样,大学毕业就去了深圳工作。一年后她就离开,回到家乡去了。分别的时候,边哭着边说,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里,太残酷了。
转眼一些年过去,她说想要回去看看。想与我一起约个时间。我答复说我不一定会回去,因为找不到要回去的理由了。她的语气里带着请求,那就陪我一起去一次好嘛?
我知道一定是生活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她才想起来要进行这一段出游。果然,交谈到后半部分,她说自己刚办完离婚手续,需要一个地方出走。不想去旅行,那么就回去看看自己曾经奋斗过的城市吧。
“要是我当初没有回去家乡,我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果然,与大多数人一样,她的忏悔开场白也是这样的。
我无法答复她。命运从来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
“重来一次的人生,也不一定会过得更好。”我安抚着她,“因为一样有那个时空布局之下,对应的难题需要处理。而人的思维大约都是固定的,你如今如何处理,去到那个时空里,你也大约会采用同样的处理方式。”
“为何你总是这样不慌不忙地,安抚我,安抚你的读者。那么你自己呢?你自己的人生怎么办?”——她在挂下电话前,问出这一句。
我说,夜深了,晚安吧。
是啊,我自己的人生怎么办?
不对,这不是一句疑问句,而应当是反问句——是啊,我自己的人生,还能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那句话出现了——“怎样都是可以的,怎样都没关系的。”
终于入了梦境里。
醒来后,我给那位旧友答复信息:我暂时没有需要旧地重游的诉求跟欲望,所以恐怕不能陪你同行了;你一定会生气,因为我以前是那种被你劝说(请求)几句,就心软了答应的人;可是眼下我有自己的生活需要进行。——所以,抱歉了。
第二阶段的温柔,不是敢于拒绝别人的勇气,亦不是拥有“被讨厌的勇气”之能力。而仅仅是,这个世界太大了,人们来来往往,相识之后又别离——人们是如此,城市是如此,一种生活也是如此。
如果你知道自己有一天会痊愈,那么你还会这么痛恨眼下的这些日子吗?——心理医生这样问起我。我停顿一会儿,然后答复:对哦,好像不必那么难过了。
我说的不是安抚,而是你确定性地知道,你自己愿意修缮自己,而不仅仅只是逃离。——那么,你的负担会不会减少一点?
当然了。我答复。生活是感受的事情,而感受是受到自我价值排序以及深浅程度影响的。——他说,你看看,你什么都懂,你只是需要我帮助你“带出这一句话”而已。
如果你知道你会离开,那么你会如何对待眼下的生活?——我答复:我一直都知道,我是那个会随时离开这里的人,所以我愿意温柔地和他们说话,对么?
我会离开的。或者是,你知道你会离开的。那个人,那份工作,那种生活。你知道那不是你全部的人生,那只是你的阶段性人生。你甚至不必慌张,是否需要一个确定的时间点。因为时候到了,你知道你会离开的。
那么,那些已经安家度日,过上安稳生活的人们,他们又该释怀这平凡而又无聊的生活?——那就往更大的意义上去延伸——疾病、生死、争吵、分别。
一个知道自己要离开的人,会温柔地对人说话。一个知道自己有能力离开的人,才会温柔地善待命运的每一个阶段。
此地不宜久留。
——这“不宜”并非说的是“不好,不对,不正确”,仅仅只是,不合适。
意识到这份不合适,无论是与他人他事,还是与这个城市,与这种生活有关的一切,你都应当学会更坦然些,去应对,去改善,去解决。
而不要仅仅只是,哭泣或者愤怒。
我也有过(如今也一直是这般)哭泣的夜晚,愤怒的时刻。可是每次在这种“就要挺不过去”的片刻,觉知中的另一根线都会提醒说,请启动你的拯救计划吧,我的女孩。
一夜又一夜,得以过去。
女主角艾米丽在平行中看到了无数个版本的自己,她选择了最为满意的一个家庭——那里没有和朋友们的争吵,她与男友感情亲密和谐。于是她抵达那处时空,干掉那个版本里的“自己”,把戒指戴在自己的手上。
在舒适入睡后的第二日,她正打算跟自己的男友出门。这个时候男友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艾米丽说她还在路上,还没有到家。
电影戛然而止。
一个人,若是知道了自己在另一个宇宙时空里过得很好,会产生嫉妒,或者更多的怨念吗?倘若你可以穿过过去,替代那个时空的自己,你要做出这样的抉择吗?
我想起来自己已经好些年没有回忆过往事了。不是因为它不再重要,而恰好是因为,我知道它们太重要了,所以我知道自己不需要一直停留在那里。
你不必停留在过去。而此时此刻,也会变成明日往事。因为你知道你会离开的,所以请你多一些耐心,善待眼前的一切种种。
此地不宜久留,此地不必久留。——而下一处又会是哪里?我并不确定。但是我能够知道的是,抵达那一处的我,会比现在更加温柔。
便是足够。
✎文章配图均来自Unsplash✎我想也许有一天,你会变成像我这样的老人,并向一位年轻人娓娓道来:你是如何将生活带给你柠檬般的酸楚,酿成犹如柠檬汽水般的甘甜。——美剧《我们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