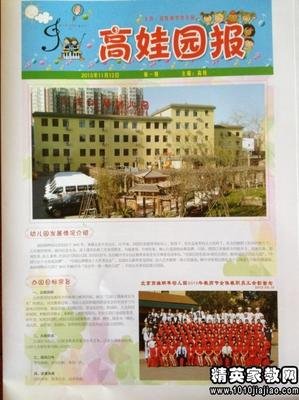海神的肖像读后感精选
《海神的肖像》是一本由盛文强著作,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2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海洋,渔民,是我们生活的一员。平常开车去海边娱乐未曾想过渔民的生活风俗。书中表达众多渔民生活,渔民对于海洋的敬畏,渔民生活画作。了解到了相关人文历史。
在大海深处,很多渔民因大风大浪沉寂在阴冷的海底,《海神的肖像》又让那些已成为海中一员的灵魂在此刻露出面容。
舟山群岛附近岛屿一件件令人敬佩的故事还在心头演说。故事,古往今来歌咏英雄壮志,抢险救难。海神妈祖的神迹在华夏大地上家喻户晓,妈祖形象代表着数位海上英雄,他们可以驱逐海怪,他们可以为人们带来吉祥。
《海神的肖像》读后感(二):《海神的肖像:渔民画考察手记》自序
东海之中,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碧色岛屿。那些绿是包裹在岛屿身外的植被,阳光照在叶片上,光斑跳跃。岛屿坚硬的石质内核隐而不见,草木织就的外壳轻盈而又躁动,到了夜里,仿佛猛兽翕张的皮毛,它们在黑暗中保持着警觉。
在看不见的水面以下,岛屿的根系直达海底,与大陆架相接。岛屿来自深渊,也是深渊的一部分。它们诞生于一万五千年前,原是冰川运动后侵蚀出的山丘,后来海水上升,变成一丛密集的岛屿。东海岛屿若论数量之多,当以舟山群岛为最。
舟山群岛保留了海洋文化的隐秘传统,还有古老的风俗与神话。近十年来,我频频往来于舟山群岛的千余个岛屿之间,做一些田野考察的功课,并整理口述史,搜集民间故事。在此期间,我结识了几位会画画的船老大,由此接触到渔民画。
渔民画的源流可以上溯到明清时期的渔船彩绘,以及神像、旗帜、服饰纹样,其中暗含着古越人的精神图腾,失落已久的民间元气。其作者多是没有受过美术教育的渔家子弟,他们拿起画笔时,几乎不假思索。渔船,网罟,海怪,大鱼,这些意象频频出现,这是岛屿常见之物,岛屿的日常即是传奇。
那些年,船把他们带到不为人知的所在,回返之后便讲起了来自异域的传奇。渔民身上都带了些海外见闻,他们心念中的世界是无尽的。他们从岛屿出发,从高处到海面,再由海面潜至海底捕捉海物,在垂直方向上经历了巨大的落差,这使他们摆脱了土地的平面。海上行船可到万里之遥远,时间仿佛无休无止,新的空间在他们面前徐徐展开。海洋环境使他们更接近于四维生物,个体生命也因此而辽阔。渔民画所传达的神秘与热烈,正是海岛渔夫的精神属性。
于我而言,这本书是考察手记、风俗记、图像志、民间故事、文学想象和历史碎片的综合体。本书的六个章节做了分工:《海神》记东海岛屿的海神家族,以及衍生出来的海神画像,这是渔民画的秘密传统之一。《素人之迹》写岛上画师与船体彩绘,他们的一生光华四射,却又籍籍无名。《岛上偷活》中既有海岛现状的实地勘察,又有海岛渔业的历史考证。《读画记》侧重渔民画里那些美的瞬间。《问答录》则是渔民画家、老渔夫和美术工作者的口述。《岛屿故事集》是与渔民画有关的民间故事的重构。各章节之间平行推进,而又有互渗,以期呈现渔民画的历史脉络与精神图景。
另外,本书对渔民画的界定是广义的,并非特指现代民间绘画,也包括来自古代传统中的东海民间渔绘。古越人的血液流淌至今,在渔民画的方寸之间,古老的基因仍在传递。
是为序。
盛文强
二〇一八年岁末于青岛
《海神的肖像》读后感(三):画里话外的渔民生活
大海无情,瞬息万变。临海族群常以绘画祈福避邪,但若说起“渔民画”,以成气候的规模而言,盛文强在《海神的肖像》里说,这种民俗绘画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分布在舟山群岛。《海神的肖像》就是他在舟山群岛的渔民画考察手记。
画作必然是这部书籍的基本元素,它们分散在字里行间,伴随着叙述和说明而出现。它们出自不同绘者,然而气脉相循,有很多共同的特点。
荀子有云:“青出于蓝。”作为最早发现的天然染料之一,靛蓝是中国民间艺术经常使用的色彩。渔民画画家普遍偏爱这种色彩,或许是因为长居海边,大海给予他们的启示吧。蓝色的海涛在他们的笔下,有时显得狂暴,有时显得幽静。玄黑、绯红、金黄、豆绿等,也是渔民画的常用色彩,自然流露古老中国的韵味。
渔民画的构图少有留白,填得满满当当,非常饱满。人物朴拙,如泥塑小人,姿体动作透着憨态的灵活。动物造型夸张,比如,杨素亚的《花色大鱼》,三条大鱼相互盘缠,肥硕丰腴;朱松祥的《大网头》,一张大网撒出去,占据了画面的大半部,鱼蟹纷涌而入。
渔民画杂糅了中国手绘、剪纸、年画与西方现代绘画的技艺,追求形式的简化,以神取胜,线条色彩有很强的装饰效果。这些画作描摹岛屿的风土人情和岛民的心理感受,不是通过反复写生而获取的知觉经验,而是记忆经验和想象虚构的混合,有些接近原始艺术的魅力,有些给我梵高、高更似的品味,有些甚至有波洛克滴画法的感觉。
渔民画既是现象的,也是抽象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据盛文强说,画家有专业的美术工作者,也有当地民间的素人工匠,这印证了我的想法。斑斓多样、各有异趣的画风,也是舟山渔民画的的特色之一吧,群岛向以独特的景观吸引八方来客。
盛文强,就是受召唤而来的异乡人。盛文强自述,近十年来,他频频往来于舟山群岛列岛之间,做田野考察,整理口述史,搜集民间故事。《海神的肖像》就是成果之一。盛文强说:“渔民画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明清时期的渔船彩绘,以及神像、旗帜、服饰纹样,其中暗含着古越人的精神图腾、失落已久的民间元气。”所有的当下,都建立在往昔之上。盛文强一直注重历史文化与民间传说的打捞,新作依然传达他的海洋史观和美学理念。
讲故事,素来是盛文强的强项。闽地渔民陈财伯舍己为人,化身活菩萨,以“善财慈航”居享香火;还有海神妈祖、台州一带的渔师菩萨、嵊泗列岛的圣姑娘娘等,都是渔家出身,这反映了渔人对于筚路蓝缕、向海洋深处进发的先祖的尊重。海神的构成非常复杂,舟山千余岛,各岛皆有神,各神皆有庙。凡人可化神,还有古代贤者、王侯将相,也有术士巫医,不一而足,均配崇献。多神信仰是原始文化的特征,正如盛文强所言,“在渔民的内心深处,每多一尊海神,便多了一份保障。”在人类学和心态史研究方面,渔民画也是有意义的。
比起之前作品,《海神的图像》的不同点,在于更注重当下渔民生活文化的观察,更有现时性,也更有一些自己的感受与见解。随着足迹所到之处,随着一位位画家的出场、一幅幅画作的面世,这些绘画的题材与背后的传说很好地相结合,通过再加工的表述,重新呈现了舟山群岛和渔民生活的前世今生。《海神的肖像》不止是海神的肖像,更多普通人的生活,结网拉绳,远航出海,丰收的喜悦,对未知的恐惧。
在《海神的肖像》里,盛文强提及了一位特别来客。早在20世纪早期,日本画家可东见之助就居留舟山,作长卷《舟山岛画卷》,记录世外桃源的浮生百相。东瀛绘画与我国颇有渊源,浮世绘在19世纪末流播海外,又影响了印象派的创作。在访谈里,舟山市文化馆副馆长徐峰说道,舟山渔民画兴起的背景是在1983年时文化部所做的一个全国农民画展览,此后几年又先后得到文化部的表彰和扶持,得以蔚然大观,舟山敞开大门迎接客人。
渔民画的考察隐约浮现的交流路线,表明文化应当开放包容,互通学习,这也是新时代的人民向往的生活。
《海神的肖像》读后感(四):《海神的肖像》| 魔方,或永不停歇的海洋想象
海洋,是地球的原始记忆,也是孕育生命祖先的巨大子宫。人类对海洋的敬畏与恐惧与生俱来,或也因为潜意识中仍保留着亿万年前的基因密码。一串串隐形DNA在时空之轮中历经无数次重新排列组合,自渔民的想象中升腾而起,幻化为神明的模样,穿越惊涛骇浪,最终返归精神故乡。
翻开盛文强的新书《海神的肖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舟山群岛图》。昏黄纸本上隐隐是青绿山水的传统笔意,工笔勾勒的对象却已换成了森罗棋布的岛屿。虎头、蛟门、乱礁洋、急水门……它们的名字是奇怪的、陌生的、凶险的——你会不自觉地将目光移向大陆的区域,直到辨认出那些熟悉的地名:奉化县、宁波府、杭州府、上海县……才觉安心。正如船上的水手们渴望归家:脚踏实地的安全感,才是摆脱恐惧的根本途径。
是的,岛屿之于我们,更像是世外之地,它们与陆地脱钩,是海神护佑的领土。而《海神的肖像》则宛如一幅以文字构建的岛屿地图,六个章节之间,彼此独立又互有连通,贯穿其中的海神信仰,则像是书中提到的彩绘古船——“这是来自海岛的幻景,人们看到这方漂移的奇迹,便已身陷其中。”
继海怪、海盗之后,盛文强将考据和书写的重心移向“海神”。在统治中国千年有余的儒家文化之外,海神信仰以群岛为根据地,保存了巫风和神性的莽荒野性,延续了渔民族群的集体记忆,也留住了人类对自然所剩无几的敬畏之心。
本书中详尽考证的中国民间海神信仰,令人想到弗雷泽的《金枝》中描述的种种欧陆自然崇拜。盛文强在《海神的肖像》第一章中,写到:“在海岛,人与神的距离近在咫尺。”而《金枝》的第七章则提到:“在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或多或少地具有我们应称之为超自然力量的社会里,神与人之间的区别显然相当模糊,或者毋宁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即便如此,陈财伯、杨甫、林默娘等平民的“人化为神”,却与欧洲巫术体系中常见的“神化为人”截然不同。盛文强将“渔民成为海神”这一现象,归结于共情与信任——
“来自寻常百姓家的海神离渔民更近,他们没有高高在上的庙堂气,也没有青面獠牙的惊人貌相,他们只是寻常人,就在渔民中间,与渔民意气相亲,他们异乎寻常的法力也只用在正途,从不会无故发怒掀起冲天巨浪,这是渔民心中理想的海神形象,他们只带来福泽,从不会动怒降下灾祸,海神在道德上趋于完美。”
中国的民间信仰,也即所谓俗神信仰,是多教合一,也是多神崇拜。海上的神明同样如此。在《海神的肖像》中,盛文强提到:“渔船中还常有诸神合祀的现象,合祀数量越多,海上渔业生产中的保障就越多,在船家的心中,信得多一些总归没坏处”。
究竟是潜意识孕育了信仰,还是信仰影响了潜意识?“来自某个家族绵延传递的记忆”真假难辨,但渔民画这一特殊的民间艺术门类,却将那些通灵之梦具现为可视的形体,在画布上铺陈出新时代的博物志。
人要如何抵达自己的心灵内部?如何捕捉肉眼不可见的精神意象?盛文强用一个道家词语“内视”来形容这种奇异的能力。现代渔民画中的海神形象,与其说是信仰的寄托,不若形容为恐惧的释放。当工业文明驱逐了神灵和妖魔,民间艺术或将成为一根连接历史和当代的缆绳,朴实、粗糙,却又结实柔韧、连绵不绝。
“如今,渔民画接续了隐秘的薪火。”
《海神的肖像》中收录的渔民画林林总总,风格各异,但无一例外地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性。精细的丝网印刷,令画作的色彩和细节都得以在书页中重现。那些变形夸张的色块和线条,那些涌动不休的幻想和梦魇,与富有诗性的文本形成了强烈的呼应对照。而盛文强在《岛上偷活》中写道:“渔民画色彩浓烈,也不全是夸张。在东海岛屿,纯粹而又热烈的色彩随处可见,海水的蓝,沙滩的白,都浓得耀眼,这也构成了渔民审美的一部分,只是不知不觉罢了。”
“时间和空间的堡垒轰然塌陷,他们在时空中来回穿梭,只为抵达稍纵即逝的往昔岁月。”
绚丽热闹的画面之外,是传统渔业在现实中的日渐凋敝。绿眉毛船踪影全无、渔绳结即将失传、巨型拖网吞噬了近海资源、只有渔村屋檐下晾晒的干鱼,是旧时光的遗骸,在风中唤醒乡愁。《岛屿故事集》中的许多故事,都隐约闪烁着盖茨比式的感伤。而浦岛太郎的故事,或可视为对古典渔业的终极缅怀——
“原来这小盒里装的是压缩的时光,一百年的时光悉数飞出,毫不留情,渔夫老死在沙滩上。”
《海神的肖像》的阅读体验,更接近于扬帆出海。无法预测会遇到怎样的景观,也不知一张网撒入水中,会有怎样的收获。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凸显了文字的张力,也放大了绘画的想象。我们在分享作者个人经验的同时,也抵达了更深邃的渔民之梦。
近年来,盛文强的海洋文学创作,早已形成了自己的脉络,正如“渔家有自己的时间表”。他也曾说过,“好的文本犹如潮间带”。在书中,他详细地描写了潮间带的存在:“这是一片海陆相争的所在——潮间带属于海洋,还是属于陆地?难以界定它的身份,它本来就在界限之外。”不被定义,才有自由。
因此,我更愿意将这本《海神的肖像》比作一个六面体魔方——鲜艳的色块不断反转挪移,它们不需要回到各自的完整中去,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移形换位中,重构不同的情节和画面。作者与读者一同进入了这个永不停歇的游戏中,海神的传说和岛屿的秘密,犹如黑暗中跳动的细微烛火,照亮了一幅幅渔民画,继而在盛文强的文字中得到重生。他者的日常成为阅读者的传奇,而那些亲眼见证了“过龙兵”的人,“再也不会为纷繁的世事感到吃惊”。
《海神的肖像》读后感(五):莫图我形:海神的肖像谁人曾见
伏琛的《三齐记略》中有这样一则故事:秦始皇于海中作石桥,求见海神,海神曰:“我形丑,莫图我形,当与帝相见。”始皇应诺,入海四十里相见。此时,秦始皇有一名画师,在人群中隐蔽身形,用脚在地上暗暗勾画海神的肖像,海神得知,大怒,海岸山石崩陷,画师溺死在海中。由此可见,海神是难以描摹的,记录海神的真实面目原本就是危险而又徒劳的行为。而在东海岛屿的渔民画中,狰狞可怖的海神肖像频频出现,岛屿民间信仰的秘密便在其中。
蔡成世《抢修》朱松祥《大网头》渔民画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东海岛屿的古地图,明清时代的船体彩绘,船中悬挂的海神像,以及服饰、旗帜等日常纹样。这些图像原是岛民“生活美学”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艺的沉淀,逐渐成为海洋文化的徽记。随着工业时代到来,旧时生产工具及生产方式淡出了视野,历代传承的图像系统便转移了阵地,由船身挪到了纸面,在渔民画当中得以延续。
海神是渔民画的常见题材,盛文强所著的《海神的肖像》从渔民画的搜集入手,进而深入到岛屿的内部褶皱之中,做田野考察,打捞到了海神的秘密。在渔民的生活场域中,海神的来源有多种途径:有普通渔民因非凡事迹而被尊为神明者,如湄洲岛的妈祖、东极岛的财伯公;有历史上的忠臣烈士升格为海神者,如网神海瑞;也有古代神话中常见的海神,比如龙王;还有介于虚实之间的精怪,比如木龙。岛有岛神,岙有岙神,岛外的海面上还有巡洋神,渔具亦有渔具之神,种种海神以职能区分,各司其职,实为饶有兴味的民俗现象。在庙堂仪典中的海神像,多为慈眉善目,或身着衮服华裘,端坐于高台之上,海神表情平静祥和,雍容华贵。这是陆地居民心目中的海神,带有庙堂气。而在岛民的海神绘像中,海神的形象多是粗豪而诡异的,有烟火气,一张扭曲着的妖异的脸铺满整个画面,有的海神俨然外星生命,鸟头人身,行走在黑红色调的海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才是海神的真面目。
孙跃国《海神》海岛渔民世世代代在海上生活,靠海吃海,出没于风浪之中。祖辈传诵的故事,亲历的种种奇遇,皆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于他们而言,渔民画中的海神便是自身精神世界的投影,是他们倾其一生都未曾挣脱的心灵漩涡,完成画作的过程,亦是完成对自身的救赎。
渔民画中沉淀了千百年来渔民的集体记忆。除此之外,还有些值得珍视的个体经验,其内容多为旧时海岛的日常生活图景,这些图景多已消逝,引发了人们长久的追忆。在渔民画中,有造船、捕乌贼、晒鱼、祭海等生活细节,图景中定格的海洋风物,是通向记忆的窗口。旧日图景日趋邈远,在记忆中愈加丰沛充盈,而当今社会的日新月异,又带来诸多困惑与沉思,这种古老而又年轻的渔民艺术,正在无意中为浩瀚的东海留下珍贵的图像史料。这些图像是不可重复的,画中的一张张面孔明明看着我们,却又望向别处,他们面目模糊,无法目睹其真容,却能与之共情,仿佛已然置身其中。
杨素亚《花色大鱼》在《海神的肖像》中,处处可见作者对图像的重视。作者并不希望以密集的图像系统作为文本的注脚,也不希望图像成为点缀和装饰,而是将图像看成文本的一部分,或者说,将图像与文本放在同一维度,让二者齐头并进,在互相渗透的过程中彼此加持,产生了一种类似互文的趣味,作者在其中溯洄久之,从历史的角度勾勒出了一个地域性海洋文化实体的轮廓。为了精准填充此间的细节,作者又深入到舟山群岛之中,以民俗考察,访谈对话等田野考察的方式,发掘更多私人化的情境,并将其作为普遍经验下的个别现象,嵌入到整体的写作中,渔民画的源流变迁与岛民生活结合起来,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完成了此题材的深度表达。
在对文本形态上的探索上,作者使用了一种跨文体的写作方式。他在写民俗时,笔调偏学术的严谨与晓畅;描摹海神故事时,又使用了近似小说的笔法;在复述访谈内容的章节,他使用了渔民的口述资料,呈现出渔民的精神风貌,而在岛屿故事的讲述中,他彻底在纸页上隐藏了自身的存在。民俗考察、故事重构、人物访谈等内容,被穿插在不同的章节中,呈现的是不同的文本状貌与文学趣味的叠加,而实际上,是反映了同一海洋文化实体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人群中的各个侧面。
打破文体的边界,注重历史场景与人物在细节上的描摹,通过细节的情境化,将客观的渔民画、民间故事、口头传说等各种艺术形式做了个人色彩的转化。在这种转化的过程当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隔膜或游离的倾向得以消解,对海洋文化的沉潜与对人生的内在关照,又始终保持克制,抵消了跨文体带来的突兀感,共同构筑成作者独特的文本风格。
王晓安《蟹神》跨文体的文学实践与地域性海洋文化遗产,碰撞出新的体验,与农耕文化心理明显的分野。他沉迷于海角一隅的地域性海洋文化,目光却在注视着飞速旋转的现代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所尽力书写的一切,似乎都在改弦易辙。他要做的,便是捕捉记忆,将一座座正在失落的海岛放置在现代人面前。
岛屿以有限的空间,经历着绵延无尽的时间之流,它具有符号的属性,其精神内蕴又浓厚到几乎能凝成实体。在岛屿,日常生活即是传奇,生活的细节便能光华四射。盛文强在岛屿看见了细节,生出寂寞与狂喜,将它们折叠进纸页之间,他的考察手记,便成为一处收藏潮声、歌谣以及梦境的镜子。
与露出微笑的大鱼四目相对,在暗夜湍流中抢修船舷,在船舱中乘兴夜饮,对渔民来说,仅仅是这些具有普遍经验的日常生活,就足以入画。而对于那些困守现代都市的人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传奇经历。这样的经历在日常便可拥有,或许就可以证明,他们是离神明最近的人,真令人心驰神往。毕竟,谁都有暗自憧憬过另一种人生,谁都曾在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世界躲避过。
俞世祥《岱衢洋黄鱼汛》终有一天,海岛上的居民搬进了高楼大厦中,入夜之后,海滨亮起了万家灯火。那时节,人们将海岛的记忆留给了海水、贝壳与搁浅的蓝鲸。长夜将尽,记忆消散如云烟,在海岛深处,会不会有人想起旧日的繁华?时过境迁,现实中的海岛如今也变幻了模样,记忆中的海岛会不会也随之沉没?
(《解放日报》2020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