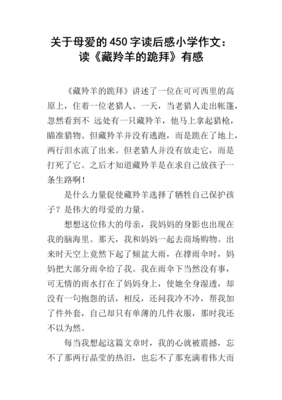《藏着》读后感100字
《藏着》是一本由[英]罗纳德·弗雷泽(Ronald Fraser)著作,格致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藏着》精选点评:
●终于读完了。在家藏了30年的曼努埃尔,政治成份属于西班牙社会党人,当村长时反对共和国政府人民阵线联盟共产党和极端无政府主义者(流氓无产者)的极端肃清行为,当然他更反对佛朗哥,不过他对革命阵营的内斗尤其是“革命小将”十分反感,说他们是老鼠屎。他躲的前两年比较危险,后来的28年,其实当局按基本法来,搜查民居要先取得执行令,家里只有小孩没有家长也不能进去,不然早就搜出来了。我更感兴趣的是佛朗哥的经济政策,比如鸡蛋的统一售价、茅草的统一收购及对“非法茅草”的取缔等等,到底是哪几年的事情?由于作者没有说访谈是具体哪年进行的,文中出现的“去年”等就让人摸不着头脑。另外,读了一小部分时,就在想:这对夫妇这30年前提心吊胆地,有没有过夫妻生活呢?好在后面有提到。
●https://athenacool.wordpress.com/2020/01/22/%e8%97%8f%e7%9d%80/
●格尔尼卡系列目前只出了一本,本系列的意图和野心尚未全面铺开。格尔尼卡选了“热门”的战争题材,但并未从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或重要政治人物入手进行译介,它想实现的不如说是这样一种“个人史”:它试图将时代的波澜与民众生活的质感结合在一起,通过一个一个民众各自的足迹和无可替代的生活经验,抓住时代的整体性。 格尔尼卡系列一方面把那些容易淹没在大叙述里的个人内在的心理契机,及日常生活的压抑和冲突放大出来,凸显个人行动的意义;另一方面又通过个人与时代动荡的碰撞,尝试把个人史与社会史/整体史连结在一起。 期待后续作品…
●新年第一读。国内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口述史这恐怕是第一本吧,赞眼光,引进不易。那场内战常被简化为反法西斯战争或是二战预演,个中情势其实复杂得多,史书是一方面,个体的记述同样也是搭建认知的砖石。说来惭愧自己自从做学术就是绕着这段历史打转,然而更多的文本研习都来自于这本书几位主人公完全不同的阶级和背景,因而读出许多新东西。以及一个小细节:主人公说他在藏身中渴望读诗歌,想读洛尔迦和安东尼奥·马查多,也想读曼努埃尔·马查多--文学史上这段著名的兄弟因政见分道,西班牙多少文人和所谓文学爱好者都因此狭隘地厚此薄彼,反倒是在这本书里看到质朴的情感。
●一星预订
●近年来,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译著多了起来,但《藏着》带给我的是一种过于真实的震撼。如果只读博洛腾、布林克霍恩、普雷斯顿或者佩恩的西班牙内战史,你能看到左右两翼的荒诞与失序,看到两个西班牙(其实更准确地说,是破裂成无数碎块的西班牙)争斗不休的闹剧,看到德意法西斯与苏联的包藏祸心。但只有读到《藏着》或者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样抒写个人经历的著作,才能惊悟到时代背后人物命运的无常,体会到有血有肉的寒意——作为看客,你可以嘲笑战争;作为亲历者,你惟愿远离战争。
●与其说平民视角的西班牙内战,不如说平民视角对政治的批判。
●这本书看完感觉很有个性的
●这种个人口述史的形式对了解西班牙内战前后的历史非常有意义,曼努埃尔堪称传奇的一生与西班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紧密相连,受俄国革命的影响,西班牙君主制的瓦解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后从共和走向内战又是二战的预演;战后弗朗哥军事独裁政府与美国的合作也可以当成20世纪拉美政治秩序的翻版。曼努埃尔先是投身工会运动,在错综复杂的党派关系中实践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理想,而后参与内战,保卫共和国直至最终失败,最后不得不在妻子和家人的帮助下在家中躲藏30年。在漫长的壮年岁月,虽然身体不自由,但他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并从未放弃自己的政治信念,即便全欧洲的社会党都让他失望。他说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关心政治也不了解世界,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或早或晚,全世界没吃过苦的年轻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
●读的时候,正好想起一则新闻:去年10月24日,#佛朗哥#的遗体被正式迁出#烈士谷#。桑切斯总理的评价是:“当代西班牙是原谅的产物,但不能是遗忘的产物。”
《藏着》读后感(一):藏着
https://athenacool.wordpress.com/2020/01/22/%e8%97%8f%e7%9d%80/
藏着:一个西班牙人的33年内战人生 [英]罗纳德·弗雷泽(Ronald Fraser) / 熊依旆 / 格致出版社 / 2020-1
子扉我 2020年早冬 申城西楼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20年1月21日,发表时有改动
《藏着》读后感(二):平凡農民的坎坷人生
西班牙內戰是歐洲上個世紀三零年代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它不僅在本國內爆發了巨大的對立與衝突,也在四周鄰近國家引起了騷動。原因在於這場因西班牙社會沉痾已久的積弊最終點燃的革命,是由極端意識形態的對立所譜寫,而這將同時是這個世紀未來歷史潮流的主軸,人們將會為此持續鬥爭數十年之久,這場內戰反而只是簡短的前奏而已。
這個主題在歐美史學界的研究作品早就多如過江之鯽,但華文圈內可供閱讀的書籍卻仍屈指可數。簡體的出版社新星、中信,曾為讀者提供了兩本通史性的作品,而上海社會科學院則推出了關於佛朗哥與國王卡洛斯的傳記,還有一本相關的作品。至於筆者自己,對於這段歷史的了解最早是來自一位作家林達的《西班牙像一本書》的描述,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反而還沒機會拜讀。這次,「格致‧格爾尼卡書系」為吾人提供這本《藏著:一個西班牙人的33年內戰人生》,真是一大好消息。
本書是英國口述史的先驅羅納德‧弗雷澤(Ronald Fraser)在採訪故事主角曼努埃爾一家三口後,編寫而成的紀實性作品。它描寫了一位在內戰中因為採取了跟勝利者相左立場而獲罪,為了活命而不得不躲藏了三十年之久的普通平民的曲折經歷。這是一段坎坷的悲情人生,但我讀完之後,卻有一種這並非「獨特」的故事。
史家霍布斯邦稱二十世紀是一個「極端的年代」,在那段時間裡,不論是在歐洲,還是其他地方,人們往往為了意識形態而彼此鬥爭,甚至到了非要你死我活不可的地步。不論是本書故事發生的中心西班牙,還是之後的希臘、朝鮮半島、中南半島,乃至於我們父祖輩經歷的戰爭都是,曼努埃爾的經歷是不難想像可以同樣發生在上述地區。而且,透過本書,筆者才赫然發現,二十世紀三零年代的伊比利半島農村,依然很大程度停留在法國大革命前的舊歐洲的水平,土豪掌握幾乎所有的可耕地,並藉此獲得了權力,迫使政權必須與之合作,共同「統治」這些農民。這是在亞洲也常見的「景色」。這種境況造成了極端的貧富差距,當時西班牙雖然開始民主化進程,但就政治學理論上來說,比較像是產生動亂的條件,而非溫和改革的根基。
曼努埃爾出身貧窮家庭的農民,父母早亡,多虧養父母收留,並依託一些人脈僥倖受了些教育,雖然不能發達,卻能接觸到當時開始散播的左派社會主義革命思想。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曼努埃爾是屬於「溫和左派」,他反對激進的暴力,並貫徹這個理念,在那個激情的內戰年代,也能盡可能善待敵人,雖然未必都能「善有善報」,至少直到三十年後他還是能堅持自己的理念,這點確實令人敬佩。他是個小人物,他的觀念與想法卻代表著許多平凡人對政治的理解,平凡,但實實在在。或許我們已無從知道曼努埃爾怎麼看待現在的西班牙與歐洲,不過書中有透漏,他對北歐幾個社會民主主義國家是很欽佩與羨慕的,或許,上帝給他開了個玩笑,讓他生錯了地方,或者提早誕生。但是,不得不說的是,也許人類社會的進步,正是有這些先輩的犧牲,才能換得吧。
故事另外一個令人敬佩的是主角的妻子朱莉安娜,沒有她的堅持,曼努埃爾根本不可能撐過三十年,更讓人不得不直言的是,真的很少有夫妻能經得起這樣的考驗,也不該隨意這樣要求。這是一種需要高度的理解才能夠做出的行為,朱利安娜雖然自承「不懂得政治,也不想去關心和理解,因為她認為那是上面的人為了犧牲底層在搞的事情。」這種想法並不奇怪,直到今日依然時時可見許多因為政治醜惡面而冷感與無力化的人們會如是說。可是,朱莉安娜自己後來又說「但是當國民軍佔領我們村莊時,我就知道政治是怎麼回事了。」或許是因為這樣,朱莉安娜能懂得丈夫的付出是為了什麼。權利不去爭取,小老百姓就永遠只能任由上層人物宰割。犧牲是痛苦的,但如果能夠換取下一代的幸福,或許就是值得。不過,或許對朱莉安娜來說,能夠跟丈夫白頭到老,就是足夠了吧。
像這樣的口述史,提供了我們微觀的面向去看待這場內戰,它是非常值得一讀的作品。歷史雖然不可諱言的,是由一些大人物在引導與影響,但它卻缺不了平凡大眾的共同參與,而他們的悲與喜卻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順帶一提,不論是弗雷澤,還是他在書中一直提到的西班牙內戰史的作品,似乎也都相當有趣,但願能有出版社願意引進。
《藏着》读后感(三):注定失败的藏着
把鱼尾巴藏在岩石缝想象 自己是一株珊瑚随着海浪的摇摆而摇摆 单调的浪把我从想象催入了梦 珊瑚虫爬上了我的身体在我柔软的鳞上,又加上了一层坚硬的壳 我不再随海浪的摇摆而摇摆 ——一首旧诗
为什么藏着?
我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恐惧中。村里的人到处说国民警卫队有一种机器,他们可以用它找到任何藏着的东西。我信以为真地听进去了:他们有这种机器,可以放在墙上找出藏着的人。这让我害怕极了。我对自己说,如果他们把那个东西拿出来搜查,那就完了。1939年4月,卡萨多上校叛变,马德里投降,三年的西班牙内战结束了。一个共和军医疗兵,原米哈斯村村长曼努埃尔·科特斯当时正在瓦伦西亚,正期待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或许能够给颓败的战事带来转机。作为战败的一方,他们被就地解散,“所有人都可以离开,回自己的村子或者想去哪里都行”。有四种路摆在曼的眼前:进入山区打游击,偷渡法国,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逃难,或者回乡报到自首。曼选择了最后一种。1936年3月,他被选为村长后,致力于为米哈斯安上电话,并且通过与中央的私人关系申请资金修筑公路;他是温和左派,在疯狂的年代,他没有利用职务做过任何坏事,反而在激进左派手下救出了许多右派的性命,制止了一场又一场可能的屠杀,拯救了教堂财物。所以,他保守地并且乐观地估计自己只会因为政治立场坐几年牢,然后便获得自由。
战时留在村子里的妻子和养父用实例告诉了他现实:这里的人最想抓住的那个人,最想枪毙的那个人就是他。“我知道如果我去自首,他们要么会枪毙我,要么会让我在监狱里蹲三十年。”曼的估计还是有些乐观:死亡,或者三十年徒刑(巧合的是,他藏了三十年不足四天,无异于一个完完整整的三十年徒刑;另一个巧合的是,曼所在的社会党,其领导人贝斯泰罗被判入狱三十年,只不过服刑第二年在狱中因结核病去世)。如果政党最高领导人也只不过被判处三十年徒刑,那么一个小小的、无权无势的村长又会有什么更糟的境遇呢?但是底层彻底陷入了疯癫:他的内兄因为曾在集体农场工作过,就被判处死刑(后来被减刑至十二年,实际服刑三年);附近几乎所有村子的村长都遭到枪决;前一任米哈斯村长在得到了不会有事的保证后回到村子,立刻被捕,一两个月后枪决。如果当时选择了自首,曼的命运似乎注定了躺在遍布西班牙的1850个无名公墓中了。
战争之后迎来的并不是和平,而是胜利者的一场清洗。为了促成这种清洗,配合着军事法庭,出现了告发制度,这让战后的西班牙陷入了一种公器私用的混乱中。
告发只需要三个人,一个在内容上签字,另外两个当证人。他们可以轮流行事,随心所欲地以任何“罪名”控告一个人。这种情况下军事法庭能做什么呢?只有告发在不断进行。我想澄清的是,这不是他们的错,错就错在不该给人们告发的自由。在我们这样的村子里,永远存在个人恩怨……【一则关于告发的讨论。曾与@倶利伽羅紋々讨论过关于举报的事情。住户举报电梯设备间非法住人,则这种举报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若不举报,则存在安全隐患,合法居住的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其经济利益受到了不平等待遇;若举报,则让那些非法住户无家可归,或者举报等同于打小报告,是绝对的政治不正确,所以宁可与违法者同流合污。上述问题又变成了哪些举报是可以的?哪些是不可以的?或者所有举报都是不可以的?(《精神现象学》关于审核法律的理性)这是一个自己对法律的认可问题,比如不认可思想罪,哪怕思想罪已经入法了。良心需要面对成文法、法律秩序、政权。(以下并不是之前讨论内容,系对这个主题进行阐发。)以西班牙的例子为例,告发者必然存在两种,一是战前战时的私仇,可以通过告发这个工具,以政治上非常高的帽子定人死罪,虽然告发者并不相信这些政治说辞,但能够最终肉体消灭仇家,也是达到了同样目的。二是,告发者真心相信,思想罪是一种罪,对于他来说,告发思想罪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消灭思想犯是必要的。但从良心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从历史上来看,从今天来看,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合理的。曼以为这不应怪罪告发者,而应归结于告发制度的始作俑者。我以为……每一项恶的制度给每个人打开了地狱之门,试探着这个人……人应该培养出一种不使用恶的善。】
如何成为曼努埃尔?
女性读者可能会对性格鲜明的朱莉安娜更有共鸣(如译者、复审领导)。我则钦佩于曼,他信仰社会主义,但却从来没有强迫过妻女认同他的政治信仰。他不信仰神,但却从未阻止过妻女信仰自由,或者阻止他们参加弥撒。他不强迫女儿,相反,他试图让女儿了解自己:“我不明白,就算对外面的事情无能为力,做父亲的至少可以在家里保证思想的延续,让一切不会随他而去。我认为,孩子永远要知道父亲的思想,应该了解自己的源头。虽然我有个女儿,而且我从不强迫她接受我的观念,但我总是教她了解我的看法。”
最终,走出三十年的躲藏后,曼说:
我一点怨恨也没有。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能原谅,一切都结束了。我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我不恨任何人。人活着重要的是不伤害别人,不是吗?这些可以说是一种迷人的、坚硬的善良和大度。
人总是有一种传教热情,如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三部分命题三十一:
绎理:每个人总是尽可能努力使他人爱其所爱,恨其所恨。因此诗人说:“对于相爱的人,愿希望与恐惧相同/那必是铁石心肠的人罢,才爱别人所厌弃的。”附释:这种使人人赞同我所爱或所恨的东西的努力,其实就是“野心”(ambitio)。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每个人生性总是想要别人依照他的意思而生活;但如果人人都同样如此做,那么人人都同样会互相阻碍,并且如果人人都想要被所有其他的人所称赞所爱悦,那么所有人都会陷于互相仇恨。正如同我想要让读者知道这本书,阅读这本书,喜欢这本书的“野心”。
周作人《结缘豆》说:
写文章本来是为自己,但他同时要一个看的对手,这就不能完全与人无关系,盖写文章即是不甘寂寞,无论怎样写得难懂意识里也总期待有第二人读,不过对于他没有过大的要求,即不必要他来做喽罗而已。煮豆微撒以盐而给人吃之,岂必要索厚偿,来生以百豆报我,但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见时好生看待,不至伥伥来去耳。古人往矣,身后名亦复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读之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所能留赠后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几颗豆豆,吃过忘记未为不可,能略为记得,无论转化作何形状,都是好的,我想这恐怕是文艺的一点效力,他只是结点缘罢了。我却觉得很是满足,此外不能有所希求,而且过此也就有点不大妥当,假如想以文艺为手段去达别的目的,那又是和尚之流矣,夫求女人的爱亦自有道,何为舍正路而不由,乃托一盘豆以图之,此则深为不佞所不能赞同者耳。该如何成为曼努埃尔?成为这样善良、大度、开明的人?
曼努埃尔并没有读过什么书,他是一个理发师学徒,在养父的店里帮手。和所有穷孩子一样,在接受了最基础的教育后退学,继续在理发店工作。此后他入过伍,在学校和军队时,认识到了社会的不公,开始萌生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他的确并没有读过什么社会主义的书籍,藏着时,他想要读读《资本论》,因为他听到其他社会党人提及过这本书,但显然他弄不到,他只能读妻子的女性小说打发时间,否则会疯掉。
养父是他人格养成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如曼走出躲藏后批评了现在的年轻人的父亲: “伙计, 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他们什么也没做。因为他养父给他一种正面榜样:“我们也因为政治差异流失了一些客人,不只是有钱人。但不太关心政治的父亲并不在意,他常说:‘那些不想来的人不用管。’”
但更为重要的还是自身……曼说:
我的精神很强大。于我的“野心”,不过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曼这样的人,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读后,养成这种善良的人性。
藏着什么?
最初与曼努埃尔·科特斯相遇,或者说与作者罗纳德·弗雷泽相遇,是在《史学理论手册》页447:
史学理论手册9.6[加] 南希·帕特纳(Nancy Partner) [英]萨拉·富特(Sarah Foot) / 2017 / 格致出版社制作中藏着的故事没有什么可说的,很荣幸能够与译者、朋友相遇在这本书中。
最终的成果就是这本,封面上艳丽的、炫目的、令人作呕的红色,如人血,而曼努埃尔变身成了漆黑的鼹鼠,在血海中迷茫……
《藏着》已经问世一周多了。它还在藏着。某网络售书平台明确表态同类书太多,不喜欢这本书。日本的朋友说钦佩我的勇气,“视角难得,难写好,更难推销”。微博上的一些评论庆幸右派当权,恨不得杀光西班牙所有的左派,正落入了我最不想看到的极端……
这些……都不是我在意的。我在意的是: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沉默和等待。
我只是在期待另一个读完这本书的读者而已。
我不认为她们会为我而唱歌。我们留连于大海的宫室,被海妖以红的和棕的海草装饰,一旦被人声唤醒,我们就淹死。——T.S.艾略特《J.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藏着》读后感(四):他一出生父母就先后离世,内战时同僚全员覆没,他靠在暗格中藏了30年幸存
米哈斯小镇西班牙米哈斯,这座位于黄金海岸线上的著名旅游胜地,白墙红瓦是它的标志建筑,整个小镇依附在海岸边的山麓之上,1小时左右就能逛完,每年吸引了大量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往。
然而在旅游名片背后,米哈斯藏着一段和内战、生存有关的惊人过去……
1.出生
1905年,一个名叫曼努埃尔的男孩在米哈斯出生,当时的西班牙正值旱灾,且医疗水平极不发达,像米哈斯这样连公路都不通的小镇,“人们像苍蝇一样死去,特别是小孩”。
曼努埃尔出生17个月母亲就过世,5个月后父亲又因为支气管炎去世。可怜的小曼努埃尔被一对有爱心的养父母收养——那对夫妻之前生了12个小孩都夭折了。
在曼努埃尔5岁的时候,他又感染了天花,这在当时被视为绝症,所有人都以为他要死了。是养母义无反顾地用“一种液体”在他身上大力擦洗,把天花弄破让脓流出来的土办法,才使得感染痊愈。虽然留下了满身疤痕,但和那些没能活下来的小孩相比,已经足够幸运。
靠着养父的理发店和一小块农地,这个小家庭得以在灾荒中生存,曼努埃尔还拥有了上学的机会,很快他学会了读写,度过了艰苦但还算快乐的童年。
成年曼努埃尔2.当选村长
凭借着一点学校教的知识和聪明的头脑,曼努埃尔渐渐成了村子里公认的“有知识的人”,他从小喜欢阅读并对看过的书本内容过目不忘,因此在学校提供不了教育的时候,他就被人们请去开学班,他对这些请求也从不推脱。
一来二去,曼努埃尔逐渐累积了不错的群众基础。
这时曼努埃尔20岁,年轻气盛的他梦想着在军队干出一番事业,于是毅然去服兵役,但是很快他发现在独裁统治下的军队腐败丛生,服兵役的那一年反而影响了他今后的政治观念,使他更清楚独裁压迫的含义。 出生农民阶级的他天生就对少数地主阶级的垄断压迫大为不满,也对广大农民阶级充满同情,回到米哈斯继承理发店时,他接受到社会党观点的启蒙,并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1930年,25岁的曼努埃尔开始组建米哈斯小镇的社会党工会,他们很快聚集了2000多人的组织规模,全部来自工农阶级。
1931年,西班牙君主制瓦解,共和国成立,社会党、激进党和激进社会党地方选举成立,曼努埃尔被推选为米哈斯小镇的副村长。
纪录片《30年的黑暗》剧照年轻的副村长参与到了一系列解救劳动阶层的改革中,在个人成长的同时,也认识到许多改革的困难,一方面是当权政府制定的政策合理性问题,另一方面在米哈斯小镇上参与社会党工会的很多人没有接受过教育,组织严肃的会议、开展议题讨论都有相当的困难。
“在所有的事情中,有一件事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那就是教育群众的需求……要记得农民阶级中存在缺乏文化、文盲普遍,以及落后的现象。革命基础是有的,但这个基础由于缺乏文化教育而准备不足。”
当副村长的几年里,西班牙政权再次动荡,地主阶级眼看自己的利益被削弱,开始鼓励激进社会党扩充势力,其目的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领地。
1933年卡萨斯别哈斯事件爆发,“无政府主义农民上了直接行动和暴力宣传的当”,共和国政府受到了极大挫折,右翼再次掌权,勒鲁任总理开启了“最黑暗的两年”,直到1935年因为财务丑闻再次下台。
这之后的大选人民阵线获得了胜利,曼努埃尔被全票推选为米哈斯村长。
3.内战
新官上任的曼努埃尔先是想尽办法去首都马德里,落实米哈斯的公路修建和电话接线申请,但是没想到仅在短短3个月后,内战爆发了。
先是针对社会党人的暗杀四起,随后城镇逐个沦陷,血腥的武装袭击恐怖笼罩在人们的头顶。
曼努埃尔一家准备逃离米哈斯,但是最终只有他一个人逃了出去,妻子朱莉安娜和女儿玛丽亚只能和他分离,等待他们一家的命运是未知。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就算几百年过去也不可能忘。我现在还能感受到当时的痛苦。在那个农场里,身边只有母亲和女儿的情况下,还要对他说:‘你快走。’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而且人们在说:‘他们来了,一路上都在杀人……’实在太痛苦了,提起来就伤心。”
孤身一人,曼努埃尔从巴塞罗那辗转到瓦伦西亚,拥有坚定社会主义信仰的他再次毅然加入了警察队伍,成为了一名共和国的突击队员。
内战3年他一直待在前线,“我们只缺武器,不缺人。我们带着对共和国事业的信念而战,如果我们坚守住,就可以为同盟国对抗纳粹和意大利打下基础。”
“然而,共和国已经投降。”
4.侥幸存活
内战结束后,所有参加战争的士兵民被遣散,大家以为战争结束了,面对他们的顶多是几年牢狱之灾——但是他们想错了。
这些士兵,有的被关进了疏散中心,一进去就出不来;有的被当作战俘押到马拉加的一处军营;有的人登船去了法国却在紧接着爆发的二战中被德国人抓住,死在了纳粹集中营;还有一些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向政府报道,结果遭到枪决,因为他们遭到了报复性告发——告发只需要3个人,一个签字,另外两个作证。唯一的裁决只有:枪决;有些人不相信自首,也无法逃到国外,选择在山林里流散,最终也一一被抓出来枪决。
在这些选择中,曼努埃尔接受了妻子朱莉安娜的极力奉劝:藏起来,活下去!
这最终使他成为了西班牙内战仅有的幸存者之一。
5.藏着的30年
“如果不是我的妻子,我不可能活下来”
谁也不知道藏着的日子要过多久。
在曼努埃尔从小长大的养父家里(那是一个理发店和小旅馆),最沿街的房间里有一个被封起来的碗柜,谁也不会想到有人藏在这儿——他们决定就是这里。
碗柜的空间很小,只能塞得下一个儿童座椅,曼努埃尔在里面勉强可以站起身子,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墙上挖了一个洞供他钻进去,然后挂上一副装饰画把洞遮住。
在这里藏着的两年只有靠看书度日,不能发出声响,连咳嗽都不能。朱莉安娜每天准备好午饭和晚饭装在篮子里,在确保没人看到的时候从旅馆的后门进去送给他。每天都在恐惧之中度过。
“有时他很绝望——在那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不绝望呢?但必须忍耐并坚持。毕竟生命是美好的——太美好而不忍心将它放弃,不是吗?对我来说也是,必须经历这些,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你能做到境遇要求的一切。”
最初的两年是最恐怖的。搜查队时不时就要到家里来搜查,把朱莉安娜抓到军营里进行盘问。一些以前对曼努埃尔有个人仇恨的人跳出来想尽方法刁难她,逼问她人在哪里。
但机智坚定的朱莉安娜都扛了下来。
与此同时,朱莉安娜还要靠卖鸡蛋养家。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到各家各户去收集鸡蛋,然后走30里路去马拉加卖鸡蛋,再走30里路回到米哈斯。多年来天天如此,一边照顾藏起来丈夫的安危,一边应对搜查队的盘问,一边养育年幼的女儿,年复一年。
女儿玛丽亚很小就要帮忙做家务。起初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藏在旅馆里,那时她还太小,朱莉安娜无法告诉她事实。
“妈妈经常带我去爷爷家。她会说:‘我们去看看那只猫吧,它现在生小猫了。’当然,这不是让我去和小猫玩,而是让爸爸能看我。我从没见到过他。有时我会觉得无聊,并说:‘我们回家吧。’妈妈会说:‘不,我们再待一会儿。’”
6.结束藏着
“没关系,什么也不用怕。现在我们能对所有人说外公的事了。”
藏着的30年对曼努埃尔一家来说,每一天都不容易,尤其是朱莉安娜:“三十年,说起来容易,但要亲身经历……”
1969年3月28日,电台里播送了一条新闻:国家首脑和内阁批准了一项法案,特赦1936年7月18日到1939年4月1日内战期间的罪犯或者假定罪犯。
虽然以前也有过赦免,但每次都留下了告发的机会。在米哈斯这样的小村子里,告发权总是充满了威胁。
4月12日,在完全确认了赦免消息后,曼努埃尔第一次重新出现在米哈斯小镇的阳光下。
“我们到的时候广场上挤满了人。村长把车停在了他代理的银行外面,我下了车。消息已经传开,所有人都上前迎接我。女人们亲吻我,男人们和我握手,拍我的背。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欢迎我——他们是村里的劳动者,真正关心我并为我感到高兴。尽管我不是多愁善感的人,不会被情绪掌控,但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就像一个人明白自己因为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而受到人们的尊重那样……”
现在我们知道曼努埃尔绝对不是什么扫把星,他比同时代的很多人都幸运得多,他的幸存背后包含了诸多艰辛和不易,更离不开妻子和女儿长达30年的付出。
他们一家人的生存故事,因为曼努埃尔成功在墙中藏着并且最终活下来而变得有意义——它震惊了整个西班牙乃至西方世界,让世人知道了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时真相。
1969年,在曼努埃尔重见天日的事件震惊全国后,英国口述史先驱罗纳德·弗雷泽赶到了米哈斯小镇,请求记录下他们一家过去30年的这段经历。
曼努埃尔同意了历史学家的请求,他们的故事最终被书写成册——《藏着》(英文书名:InHiding: The Life of Manuel Cortes)1972年出版,2010年重版。
2020年1月,该书中文版终于被引进翻译。阅读此书,可以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西班牙内战,了解小镇米哈斯的历史,了解曼努埃尔一家人深藏的过去。
《藏着》读后感(五):西班牙的枪响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使者
作者:Muzuer
校对:litcave 工作室
配图:online
hoto byOnline
2020年,国人本以为有个欢腾的开始,结果却迎来似无止境的禁足。
而且随着形势戒严,许多商场店铺都不得不关闭,就连公司园区也不得不封闭戒严延期上班,不管是北上广还是十八线小城市,中国大多数的城市此刻看起来都像是荒无人烟的死城。
此时此刻,人们被局限在狭小的格子里,或许一开始还欣喜着假期的延长,但渐渐地也开始疲倦室内枯燥单调的生活。
而就在今日,某位医生的离世,再次让朋友圈「沸腾」了起来,一下子人们再次变得充满斗志,群情激愤,而整个世界也重新认识了「吹哨人」(Whistle Blower)这个词。
这位吹哨人的勇气是值得尊敬的。
然而人们唉声叹气,网络点烛仪式再次花开神州,除了媒体赚足泪水和点击之外似乎就再也没有什么浪花。
回想起来,很多时候我们的新闻评论除了新闻本身之外,意义似乎少得可怜。
在后真相时代,在许多不痛不痒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又见证了伟光正的时代和明天,殊不知这一遍遍人间悲剧,不过是历史重演。
时光倒退到一个世纪以前,南欧伊比利亚半岛上,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悄然降至。
而根据最新历史报告,当时的西班牙叛军为了铲除「反西班牙」的破坏分子并恐吓民众,总共谋杀了十万人。
历史直到1997年才正式以《历史记忆法》之名让那些战场上的灵魂重新安息。
2010年初,西班牙《国家报》(El Pais)报道,1850个为标记的公墓最终被绘制在了西班牙近一半的土地上。
hoto by @Kapil Dubey
今天要提的这本书是《藏着》,副标题为《一个西班牙人的33年内战人生》,作者则是上世纪60年代的口述史先驱「罗纳德·弗雷泽」(Ronald Fraser),书借助「曼努埃尔」、「朱丽安娜」(曼努埃尔的妻子)、「玛丽亚」(曼努埃尔的女儿)的口讲述了横跨大半个世纪的西班牙历史,从个人的视角呈现了当时西班牙整个社会的动荡与混乱。
书的主人公名为「曼努埃尔」,是一个忠实的社会党人,因为1936年那一场政变和随后的内战,他不得不躲在家中足不出户,而且每次家里来人都需要小心翼翼,甚至连咳嗽都不能让别人听见,因为一旦被别人知道,他便很有可能被拉去枪毙。
而这一躲,就是30年。
hoto by Online
其实说起西班牙,大家也都十分熟悉,早期的海外殖民者和海上霸主,若不是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后退位让贤,它本应该是欧洲乃至世界的霸主。
在它的强盛时期,它不仅在欧洲拥有许多飞地,更是在全世界拥有大量殖民地,而且还占据着大量银矿。
然而这样的资源渐渐变成了诅咒,西班牙本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白银资源的收入短期给国家财政提供了收益,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欧洲整体的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扩大。
而缺乏国家支持的制造业小生产者并不能获得殖民利益,反而深受其害渐渐走向更底层甚至最终破产。
此后国家本身的人口和发展问题以及欧洲他国的强盛,使得这个国家一直处在二三流的水平。而到了近现代,极端的政治运动和民族问题更是成了两座大山压制着这个国家的发展。
而1936年的右翼军官政变便是我们要说的那场「人间惨剧」的开始。
西班牙内战爆发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了苗头。
1931年,西班牙王室被推翻,社会党人组建了共和政府,史称「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然而这第二共和国的政权并不稳固,不仅仅是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民族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国内左右两派势力更是明争暗斗,内耗严重。
而反观当时动荡的欧洲,一战结束后整个欧洲政治两极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是以保守派和军国主义为代表的右翼势力逐渐强大,而德意的法西斯政党借着民族情绪也纷纷抬头,另一方面是列宁领导的第三共产国际也在不断发展,红色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游荡在欧洲的幽灵而是无数口号一致的红色队伍,他们深入了欧洲的每个角落和当地的政党和人民结合起来,寻求政治上的突破。
这样的国际形势也间接造就了第二共和国政权飘渺不定的局面。
1931年共和政府临时执政的是共和党右翼代表「卡拉·萨莫拉」(Alcalá-Zamora),而在正式选举后,当选的右翼政府并没有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满意。
「当时的西班牙以农业为主(事实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无产阶级群体(多数为无土地散工)大概与工业无产阶级相当——各有两三百万人。除此之外,还有两百万佃农、租地农以及小土地拥有者——同时,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数也不超过两百万。除却他们所有人,五万大地主却拥有西班牙超过西班牙一半的土地。」
而这种情况没有因为第二共和国的建立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hoto by @Online
可以说在第二共和国建立之前,西班牙大多数农村都是党魁当道,一般来说村里都有一些重要人物:「两三个地主、一名医生、一名校长、镇书记、一两个商店老板、一名牧师,以及任国民警卫队指挥官的下士或者中士」。
这个阶级就组成了村里的统治阶级,而更有可能的是,这阶级中某一个人物会组建支持自己的队伍,从而形成一个更为稳固的统治队群体,他不仅仅会在自己的阶级中吸收成员,更会从更低的阶层中选取成员,久而久之,一个党徒集团就形成了,而这其中的主导者就是所谓的党魁。
当然国民警卫队的指挥官一般来说在当地拥有极大的权力,因为其是唯一拥有军事性武器的人员,而且还接受中央或者地方的任命,由此他们一般来说是农村的重要人物,是当地统治阶级的重要一部分,但是却不依赖于它。
从主角曼努埃尔出生的1905年开始,整个西班牙农村就笼罩在党魁阴影之下,那时候学校的不公渐渐在曼努埃尔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曼努埃尔家很穷,但是因为曼努埃尔的父亲是当地校长何塞老师的好朋友,曼努埃尔便得到了一些关注。
曼努埃尔对他是如此评价的:「对那些他想关心的学生来说,何塞算得上一个好老师……但他关心的就只有富人家的孩子,他对穷人的孩子置之不理。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聪不聪明并不重要。」
然而这只是当时那个时代社会不公、人性势利的冰山一角。
就在曼努埃尔12岁那年,他看到党魁的几个暴徒把一个他们打得半死的人用骡子驮到村里。这个人有一小块土地。他们用绳子把他的双手捆着,确保村民会看到他,好唤起村里的恐惧。
在这场事件中,这些党魁的暴徒声称这个人没有把镇公所声称的他所欠的税付清,所以去他家没收他的财产,而这些时候那些党魁的暴徒总是拿着猎枪保护镇公所的官员。而这次当他们试图将这个人耕牛的轭拿走时,他做出了反抗。
那是他唯一的轭,也是他谋生的饭碗。
在那个被党魁统治的时代,其实连正规的政党都没有,民主根本无从说起。
而等到出现选举的时候,曼努埃尔的父亲(其实是养父)也和当时的村民一样,他们认为:
「我投票做什么?反正不管我投不投,他们都会按自己的套路来。我不投。」
而在第二共和国没有成立之前,选举似乎只是一种形势,这次是自由党登场,下次就是保守党上台。
有时候选举会进行而大部分情况下,只会有一个候选人——通常来自即将执政的党派,在不经选举的情况下根据根选举法的第29条被宣布获胜。
当然如果出现多名候选人的时候,整个西班牙便会出现一场闹剧,
「党魁们会忙碌起来,省长会任命一个政府代表来到村里,在大选当天把对立党派的所有领导成员都监禁起来。那不是选举,而是一种恐吓」
而在那个时候,人们被勒令如何投票,不仅仅是因为缺少文化教育,还因为害怕。
当然随着事态的发展,买卖选票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曼努埃尔说那个时候「每票5比塞塔(比塞塔为当时货币)」,人们便会在毫无政治意识的情况下出卖自己。
等到1931年,最终共和国政府成立,人们切实感受到了一些自由,但是这对西班牙人来说才算开始,因为接下来,左右两派的极端政治斗争最终将西班牙带入一场血与火的内战之中,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场灾难带给底层穷人的是不幸和悲哀。
正如「曼努埃尔」的妻子「朱莉安娜」所说,这些底层人总是承担所有的后果,好让那些身居高位的人爬得更高,而且直到战争硝烟散去之后,朱莉安娜依旧秉持着这种看法。
但是就许多对政治抱着心态的人,例如「曼努埃尔」,在他们看来,共和政府本身是有救的。
最终以民主立身的共和政府失败,则是因为他们没能妥善地解决好土地问题。
hoto by @Online
当时,许多政党在自身合法化之后都开始推行自己的主张。
1933年,拥有军队力量的右派联合激进的共和党人最终赢得了选举,自此西班牙进入了其左翼人士所谓的「黑暗的两年」。
那个时代一切百废俱兴,而强大的宗教势力、民族矛盾、劳资矛盾和土地矛盾一下子涌到了政府面前,铸就了一次次的权力斗争和流血冲突。
那个时候西班牙国内政党林立,而法西斯势利和共产国际的势力已然蔓延到了全国各地。
右翼势力试图以极端的军事强权策略稳定国势,控制媒体舆论和人民示威,而左翼势力则开始宣传土地改革和人民自由,而激进的人们也开始寻求暴力的方式去冲击国家机器。
当时作为左派代表的「人民阵线」联盟是如此宣传的:
「法西斯为你带来「工作」,也为你带来饥饿;法西斯为你带来「和平」,也带来了五千个坟墓;法西斯为你带来「秩序」,也带来了绞刑架。人民阵线提供给你的,是面包、和平与自由!
土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以致于农民和无产主义者都纷纷投向左翼,甚至很多投机分子也纷纷参与进来,企图通过蛊惑文盲集体来侵占公共财产。
「曼努埃尔」经历的正是这样的历史,在右翼政府摇摇欲坠的时候,他站到了「人民阵线」这一边,也就是所谓的左翼这一边。
「曼努埃尔」自述,当共和国建立之后,他们最希望政府做的就是两件事:
首先,用土地改革的方式结束大庄园主式的农耕,
其次,用教育改革扫除文盲。
而在1931年到1933年,通过竞选上台的右翼政府在教育上下了很大功夫,但是对于土地问题,他们一直无动于衷。
虽然很多地方渐渐成立的实施改革的委员会,但是这个局面在某种程度上十分尴尬。
当时有些人认为应当采取集体耕种的方式,然而效果很差。像「曼努埃尔」这样的人则认为应当将土地私有化分给个人,并给予一定的工具、种子甚至是政策倾斜。
「曼努埃尔」原先是一个理发师,在当地的工会建立后他成为了领导者,所以很多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经常到他理发店来,一来二去,他的想法也渐渐说服了自己遇到的那些人。
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但是在示威中,这些人并非是理性的。
当作为政府代表的下士们试图阻止示威的时候,人们群情激愤,若不是「曼努埃尔」的阻拦,那些下士便会被人群吞噬,那个时候是曼努埃尔第一次意识到了人民的力量,而那次事件也使他渐渐意识到运动中不理性因素的存在。
hoto by Online
1936年,右派政府开始组织选举,为了赢得民众好感,大选期间他们更是取消了部分媒体管制,但是这样的中间化路线并没有讨好任何一方,反而让极右势力更加愤怒,而「人民阵线」也最终在左派人士的组织下成立,一时间西班牙全国各地示威抗议右翼政府声援「人民阵线」的声音四起。
各地冲突流血事件徒增,民众在政治的狂热中进行抗议、示威和拉票,面对这样的局面,似乎站队成为了最为直接也最为有效的参与政治的方式。
最终1936年2月16日,「人民阵线」代表的左派宣布赢得选举,正式开始组建政府。
而在西班牙乡村,「曼努埃尔」也成为从右派势力手中接过村长一职,并开始组织委员会对当地的管理。
但他没能想到的是,这次左派的胜利只不过是灾难的开始。
不仅仅是因为政府改革无法短时间内实现,更是因为在两极化的站队斗争中,没有人能够幸免。
虽然「曼努埃尔」是左派,但是他依旧秉持着公正对待村民的态度,无论是地主或是国民警卫队,他都没有因为对方的身份,而让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可是情况并不因为「人民阵线」当选而渐渐好转,反而向着更危险的方向发展下去。
「人民阵线说要加速改革,但是渴望土地的人民以为只要他们赢得大选就够了」
由此,农民们在政府的大旗下开始进行暴力运动,而国民警卫队则手握武器进行抵抗,而这些运动和冲突愈演愈烈,流血牺牲不断出现。
书中最严重的一次是「耶斯特」事件:
「警卫队逮捕了在一个大地主的庄园砍树的六个农民。剩下的人在警卫队押走他们的同志时,拿起干草叉、棍棒和石头袭击了他们。而最终警卫队开枪打死了18个农民。」
政治运动在无序中愈演愈烈,而在「曼努埃尔」看来,「人民阵线」最大的问题便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
这些人借着革命的名义,冲到村子里去破坏国家机器,他们私自处决那些地主和下士,企图制造暴乱和恐怖,而「曼努埃尔」更是发现,这些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背后不过是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分子在煽风点火。
然而这都是一家之言。事实上,无论无数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在那个风雨飘渺的时代被暗杀,而这场由左派政府主导的「改革」最终也成了内战的引子。
无论「曼努埃尔」如何抱着一颗对左派政府和土地改革热切的心,他都没有时间了。
就在「人民阵线」宣布赢得大选的3个月后,弗朗哥所属的右翼以「整个西班牙晴空万里」为暗号发动军队政变。
由此所有原先被控制的国民警卫队在军方的领导下开始向左派政府和民兵组织反扑。
西班牙内战就此开始。
高中历史课本里其实也提到的过西班牙内战,大体上也不过是右翼军方代表弗朗哥将军发动政变,在德、意等法西斯政权的6万多装备精良的军队支持下,最终击溃了3万共产国际的联军,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独裁统治。
而在那个时候英、法无动于衷,只有共产国际愿意出兵相助,由此西班牙的共产势力不断强大。
但是乔治·奥威尔的经历似乎被一些人刻意忽视了。
由此很多人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不仅模糊而且片面。
因为政治局势的影响,左翼和右翼各执一词。左翼人士宣称弗朗哥政府是恐怖的独裁政府,在弗朗哥执政时期,无数人因为政治因素被迫害枪杀,而西班牙却在这场独裁中躲过了二战。
hoto by Online
反过来说,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同样描述了在左翼战场上让人觉得心寒的经历。
那些由反对右派组成的抗击组织似乎都是些无望取胜的民兵,而奥威尔自从在东南亚殖民地觉得良心有愧之后就决定站在了失败者这一边。
但是没想到的是,这场战争中他不仅仅看到了这些拿起武器的战友的无畏,也看到了借失败而打击左派内部政敌的苏共的冷血。
一个个共和政府士兵撤回时不仅被当时控制局面的长官审问,更是动不动就怀疑成间谍要拉去枪毙。
当一个个撤退的战友被诬陷为法西斯内奸时,左派的阵脚渐渐乱了。
而在彼此的暗杀和混战之中,整个国家陷入了极端的恐怖之中,无数的平民陷入这种政治恐怖和斗争之中。
站错队伍的人们很有可能就会被当作敌人处决。
整个状况持续到了1939年的春天,西班牙首府马德里最终被右派军方占领,旋即,西班牙内战宣告结束,弗朗哥独裁政府正式上台,类似「曼努埃尔」这样的左派人士也立即遭到追捕和处决。
在书中所讲处决一个人,只需要三个人,一个人在内容上签字,另外两个当证人,由此右派可以随心所欲地处决任何人。
由此,弗朗哥所制造的恐怖再一次席卷了整个西班牙。
而这一次,是左派人士遭到了清洗。
hoto by @Nathan Anderson
这本书的主人公「曼努埃尔」从内战结束后的1939年开始便一直躲在家中。
他在妻子的照顾下躲了30年,直到1969年政府宣布大赦之后他才从家里走了出来。
人们对于弗朗哥政权似乎也褒贬不一,在独裁时期,他在国内制造恐怖,导致无数人被暗杀而他一生也至死也害怕被暗杀。
但是从结果上来看,他所主导的政府最终也没有参与到惨烈的二战之中,无论是自顾不暇还是明哲保身,这对西班牙来说亦或是躲过一劫。
但是不管怎样,那么多生命在这场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浩劫中消亡,而这些逝去的灵魂,在肉体消亡时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能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才能得到安息。
而对于这场灾难,人们感到更加疑惑的是,战场上的所有人似乎都认为自己在做对的事。
就像一场雪崩中,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过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