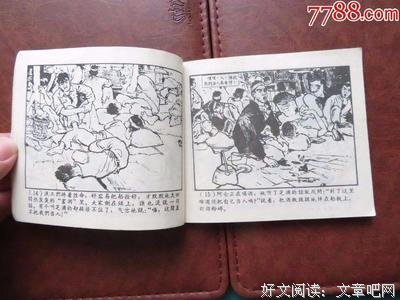蟹工船的读后感大全
《蟹工船》是一本由(日)小林多喜二 著 / (日)藤生刚 绘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25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小林喜多二。那个1920年的金融男,为了这本小说,三年后即遭民警殴打致死。启发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斗士么,像夏衍,鲁迅等等。《蟹工船》不愧是1920s无产阶级文学的巅峰了。
●今天资本主义任然存在的现象:1.不同部门员工竞赛,挑起群众斗群众。2.民族主义激发员工超负荷工作
●現在又有誰會像小林多喜二先生一樣能站出來為我們說話?ZG正在走一條別人曾經的路,只是這條路比那時的更長。
●以一条蟹工船解剖资本主义,冷峻写实的笔调深得现实主义精髓。作者意在塑造群像,以对工人生活细致入微的刻画成功达到了这一目的。尽管已过去近一个多世纪,“蟹工船”却仍在世界各地航行,悲夫!
●年代的确是无法跨越的一条线,尤其是流行于一时,一部分群体,社会现象胡.在看过很很多其他小说,类似电影后,这本书就显得无从接受了. 另外,作者正本书的节奏把握的很不错..... 只是推荐小说,漫画是没有时间的选择.
●这还是艺术加工的结果,一旦小说被推上现实,2682就是最好的舞台,监工的压榨是秩序的暴力,残虐杀戮的工人则是无序的暴力,对于每一个左派而言,反思西班牙内战都是第一课。
●当下的上班族们,和《蟹工船》里的博光号渔民们的境遇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蟹工船》读后感(一):海那边的“水深火热”与海这边的“歌舞升平”
诚如翻译者秦刚在序中写的那样,80年代以后天朝的国情变了,原本那么根红苗正的《蟹工船》也从读者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最近十年里《蟹工船》的译本满打满算也就三个,这个小说漫画合体本应该是最佳的。
作者小林多喜二是真正用生命写作的左翼作家,29岁那年不幸被特高打死。3年后堀辰雄发表了《起风了》,虽然堀辰雄是因为自己得了肺痨有感而发写下了这篇小说,但在笔者眼里,跟小林多喜二比起来,那简直就是无病呻吟的娘娘腔。
2008年在日本出现的《蟹工船》热潮真的很奇妙,这也正说明了日本的就业状况已经恶劣到一定程度了,之前在看芥川奖得主津村记久子的获奖作《绿萝之舟》,可以说两作在反映底层劳动者凄惨生活这一点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记得哪个日本作家说过,日本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日本社会尚且被认为是“水深火热”,大家抢着买《蟹工船》看。反观天朝,如假包换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年来反倒没什么为劳苦大众、屁民蚁族大声疾呼的作品问世,却都是些《小时代》之流歌舞升平的玩意,连鲁迅被都请出语文课本了,呜呼哀哉……!
《蟹工船》读后感(二):如此激昂而沉静——《蟹工船》别解
这几天都睡得颇晚:读写画跑,赶一些任务,忙着奔波着,灵魂要跟不上脚步了;最期待的就是洗漱后躺在小床上,开小灯,读一小段《蟹工船》。它并非休闲小品,更象是战斗檄文,“林中响箭”。可是,在睡前读上一读,让我觉得惬意和温暖。这就象一个英国作家描绘的那样,在深夜的火炉前读着行人在凄惨之夜的泥泞中颠簸行走,那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这样说,似乎辜负了小林君的美意。似乎读完了《蟹工船》,应该拍案而起控诉资本主义的万恶制度才对。但又觉得若要向小林君学习、向他的生活和战斗经历学习,应该不是这样的办法。看书中小林君的年谱,在他短暂的廿九年华中,少时爱水彩画,爱写和歌,演童话话剧,爱和平,反对对华战争,做过待遇优渥的银行职员(后因写作本书被辞退),为卖身女赎身,写作也是如武士用剑,从容沉着。看小林君的照片,还有他躺在屋中和众战友在一起的遗照,正如他的文字一般,如此朴素而深厚,如此激昂而沉静。我想,还能怎么样呢?不要急于去战斗去抗争去呐喊,去真实地体验生活,才是“第一要务”,此后,才有实事求是的写作和动静合宜的行藏吧。
而只有细腻地爱生活的人,才能如此敏锐地写非人的生活吧——尤其是写出在非人的生活中的温暖和幸福。我的观感就是这样,读这本书,觉得有趣,快意,对工人的亲切多于对资本家的憎恶。一来那是一个遥远的时代,我们都知道无产阶级革命应该怎样了;二来我的父母都是工人,他们的朋友也多是,我爱他们,尤喜和爽朗而清贫的工人交谈过往。在我看来,小林君真切精准地写出了他们的情感,他们也真正值得书写。他们太不同于愁容满面的现代的年轻的人们了。现代的年轻人,即使是工人,也习惯于攀比赚钱的多少,处境的优劣,有房无,有车无,对生活缺少热诚,精于算计,不团结,不大度,不纯粹。他们被总结为“贫而不清,富而不贵”。我想,人是不可能毁于困顿的,正如书中所述,这只能让人们更团结,即使麻木的人也会清醒而明智地求生,去投身工会和给他们真切希望的党派;而人是可以毁于平庸享乐的,让人斗志凋零,不辨南北,丢掉勇气,迷失在生活的棉花套中。人的幸福固然可喜,追求幸福的能力更为可贵,那才是人的闪光之处吧。
我想,只有大笔如椽,才爱写海上劳工。夏衍的《包身工》,直接地学习了它的笔法,它的取材,甚至是它的情怀,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而这个时代的文学讲究技巧,讲究风格,讲究情调,惟不讲究立身之本了。是的,这个时代盛产悲伤,却不生悲悯;盛产奋斗者,却不敬信仰;盛产偷窥式的写实,却对劳苦大众的朴素之实退避三舍。所以需要这样的书,让更多的人看到,即使不从事文学写作,对“直面人生”也是有益处的吧。我劝我辈读书人,吃点素的,读点质朴的,身体力行,为社会做一点有用实事,比那些虚的浮的高的响的,要好得多了。
所以我对这本书的包装也有一点小小的意见:如果封面能沿用老旧的封面感,漫画的字体更粗糙、更手写一点(我相信原版应该是这样的),我会买两本。一本放在床边,和那些单纯可爱的蟹工们一起哭一起笑;一本送给我将来的孩子,告诉他/她,如果你遭遇不公和不幸,看看这本朴素而有力量的书,看看这些曾经的无产者吧。
《蟹工船》读后感(三):两岸猿声啼不住 号子一喊浪靠边
二十多年前,文学的裁判官在渴求知识的目光中,陆续重返失乐园,便像鉴宝专家一样,随着神经质的配乐,登堂入室,粉墨登场,忙不迭地开始了拉网式重新评定现代中国文学的表演.一些布满了脂粉与烟灰的书本,被加盖了"永恒人性"的大图章,旋即发往新落成的文学神坛和自由市场;而另一些,则要么遭遇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的春秋笔法,要么干脆被扣上"政治宣传"的屎盆子,藏之穷山,传之无人.以客观中立自居的学者们,辛辛苦苦地拉了二三十年的偏架,终于, 张爱玲战胜了丁玲,钱锺书战胜了赵树理.看起来新的操作系统马上就会被一劳永逸地安装在现代中国文学上,而在我们的近邻日本,一根桅杆却刺穿了据说将永远平静下去的历史的海面,一艘蟹工船像被遗忘已久的幽灵船一样,很不凑巧地从苦寒的鄂霍次克海漂了回来,八十年后,那夹杂着汗臭的螃蟹的腥味,再次席卷了日本,波及到中国.
没有人开香槟,没有人挂彩带,没有"尘封33年终于出版"的的噱头,也没有请读者"一窥作家私密情事"的玄虚,这艘低调返航的蟹工船,却如同悄悄归来的基督山伯爵,很快便来日方长显身手,畅销无阻,似乎小林多喜二和他的同志们的文学运动,随时会出其不意地杀出一计回马枪.就连漫画先行,小说跟上的阵法,也呼应了当年鲁迅和小林崇敬的藏原惟人,以及更多的左翼知识分子提出的,采用包括连环图画在内的旧形式,创造进步的大众文艺的构想.革命文学不但未曾像很多人诅咒的一样像交际花一样迅速失去了荣光,反而和它声称要推翻的资本主义一道历久弥新了.这让遍及中外,依照永恒的人性与善变的行市判断文学作品的专家,多少有些"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的感觉了.
然而这"时空错乱的革命文学"让人在思考文学的同时,更多地回忆起了革命.切格瓦拉曾在给卡斯特罗的亲笔信里信誓旦旦地宣称:"正义的事业从来百折千回, 格拉玛号还会一次又一次启航."然而自那时起,格拉玛号似乎已经搁浅,可是从墨西哥湾到大堡礁,从白令海峡到好望角,我们只看到被翻修一新的博光号们正在百舸争流.几十年间,资本主义已完成了由Peter Parker到蜘蛛侠的蜕变,不但威力大增,界面也变得友好起来;而小林多喜二同他的战友们为之奋不顾身的事业,早已在自由市场里资不抵债,沦为岁月眼中的一段插曲,如果算不上是人类碰了壁的话.不过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还不是最可怕的,人们已经像马孔多的居民一样患上了会传染的集体失忆症,忘记了这个世界还有改变的可能,在电视机和显示器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一方面已经不能理解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式的政治激情,另一方面却把同样的激情献给了常常是毫无指望的工作,献给了雷克萨斯,苍井空和各种数码奇技淫巧.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却如春潮带雨晚来急,像来得更猛烈些的暴风雨,骤然掀翻了人们朝不保夕的生活之舟,而抛锚已久的格拉玛号,却"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人们抬起疲惫的双眼,发现世界依然没有地覆天翻,"越有钱便越有钱"的现实如同数学公理一样不可撼动,而吃方便面喝速溶咖啡换来的中产阶级生活却是那么不堪一击,虽然有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告别革命,可是革命似乎从来没考虑过要告别我们.可以断定,再度风行的<蟹工船>,不同于海盗电台里遭遇浪劈波斩的爱之船,仅仅带给大家性感的怀旧,它是惊醒了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怒吼,是那段激情历史的不思量,自难忘.
正如革命并非让无产阶级去拉拉资本家的衣角,撒娇般地说:"请您不要这么残忍嘛."革命文学的目的,不在于让读者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也不止于忆苦思苦,而是让我们"站起来,又一次地".<蟹工船>不应成为徒有其表的含笑半步癫,顶多骗对手三天不笑不走路,小林多喜二若地下有知,也不会因为<蟹工船>和花花绿绿的成功学同时出现在畅销书的书架上而感到满足.好马配好鞍,<蟹工船>需要能使读者"站起来"的评论,过多地纠缠于语言,风格,手法这样的命题,娱乐记者似的专注于作家八卦,或者讲一些风靡豆瓣的印象派和印象过剩派呓语,都会像用帅或不帅评价本雅明一样,多多少少是一种辱没.另一种将削弱<蟹工船>价值的倾向,是热衷于把它变成某几个人的心路历程甚至情路历程.在长达六个小时的电影<巴黎公社>里,导演沃特金斯在展现巴黎公社的斗争的同时,不忘反思影像的意义与可能,他断言,他的电影里"群众代替了个人,这是资本主义最害怕的".小林多喜二之所以要另辟蹊径,写一部没有主角的小说,也并非心血来潮,确切地说,他的小说,主角是忍受着压迫与侮辱的人民,布满了劳动者愤怒而坚毅的面孔的<蟹工船>封面,反抗的不正是明星大头贴一样的好莱坞电影海报吗?小林多喜二这番苦心在世界文学上的开创意义,似乎至今仍然没有得到重视.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由松田龙平和西岛秀俊这些据说干净而安静的男子主演的电影<蟹工船>将把这艘航船引向何处,将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毕竟, 当我们看到杰克伦敦,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鲁迅,聂鲁达等人都相继遭到去政治化或者说去势,成为了不值得迷恋的传说和无毒无害的标本,甚至就连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变成了不过是分析<包法利夫人>的有趣方法而已的时候,对于小林多喜二及其<蟹工船>的前途命运,我们捏一把汗,不是没有道理的.<蟹工船>热销的大潮能载舟亦能覆舟,载舟覆舟,我们不得不所宜深慎.
《蟹工船》读后感(四):我想:青春是不朽的
也许我们曾理所当然地以为,在中国、在革命已经式微的今天谈论“革命”是一种奢侈、无奈甚至讽刺。而在日本、在这个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却暗涌着一股“赤色”的思潮。被奉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圣经”的《蟹工船》在八十年后重获追捧,小说再版、加印,电影版、漫画版、舞台版纷至沓来,入选2008年日本十大流行语。有趣的是,热心拥趸中不乏被认为是冷漠、自私、一切无所谓的日本的80、90后。小林多喜二笔下的“博光丸”在新世纪的光与影中复活,这是日本式“红色文艺”的怀旧翻新,还是流行文化的匆匆过往?是历史的善意巧合还是意料外的情理之中?或许只能从船舷边的咸味海风中寻求答案。
“嗨,要下地狱喽!”
两个蟹工倚着甲板栏杆,望着像蜗牛伸展开身子一般环绕着海湾的函馆市街区。他们中的一个扔掉了快要烧手的烟蒂,随口啐了一口吐沫。烟蒂嬉戏似地翻着筋斗,顺着高高的船体落了下去。他浑身散发着酒气。
堪察加海像一头等候多时的饿狮一般猛扑过来。蟹工船简直比一只小白兔还要弱小。朔风卷起的漫天飞雪,看上去像一面卷动着的白色大旗。天色越来越暗了,但汹涌的海浪丝毫没有平息的迹象。
小说在开篇先用素描笔法勾勒出蟹工疲惫、无奈的神态,不着痕迹地以“烟蒂的翻滚”带来些许轻松的审美,可能是意在缓和“要下地狱”的沉重。这一“轻”一“重”的巧妙安排,反映出蟹工将地狱般的劳作习以为常——苦中作乐和举重若轻是迫于无奈,也别无选择;也是将矛盾按下不表,为后文情节的发展留一个伏笔。
接着作者运用排比和比喻罗列了“博光丸”上工作环境的各种脏乱差,渗出文字的恶心教人读起来直皱眉头。有人曾精辟地将小林的这一技巧评论为“过剩的比喻效果”,多重意象的叠加营造出一种超现实的幻觉,场景的不断转换借用了电影的蒙太奇手法。
《蟹工船》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1920年代,日本渔业公司的蟹工船“博光”号从函馆出发,颠簸在堪察加海的惊涛骇浪之中,驶向日苏边境海域作业。几十名蟹工命悬于手拿皮鞭、吆五喝六的监工手里。工人们在暗无天日、炼狱般的环境中卖力,受尽虐待,不满和反抗的情绪日益增长。一次意外中蟹工船抛锚在苏联海岸,.工人们受到俄国人和中国人的“赤化洗礼”,上船后准备罢工。虽在“日帝护航军舰”的干涉下失败,但马上发起了第二次斗争,并获得成功。
小说取材于真实事件,1926年因“秩父号”沉没而引发媒体对蟹工船问题的追踪报道成为小说的直接素材。
这是一部意义和影响远大于其文字情节和内容架构的小说,篇幅不足百页紧凑完整,无一处闲笔,图穷匕见、单刀直入的版画风格:棱角分明、张力凸显。与其说是浪漫的文学,更像是一本操作性极强的实用“罢工指南”技术手册。
作为一部功能性很强的小说,《蟹工船》也因其时代背景所限,难以逃离阶级文学“简单粗暴”的樊篱。人物设计简单化,善恶道德判断两极化和一边倒,不外乎“群众斗恶人”,一而衰再而捷的喜闻乐见的戏码。檄文般的振臂高呼不乏“就这样,他们站起来了——又一次地!”的结尾,但如细心阅读也不难发现:作者努力在作品中再现蟹工的真实状态,小林笔下的工人是未经刻意拔高的、“原生态”的、直率而可爱的人。
将《蟹工船》作为一部青春文学来解读,或许就能够摆脱传统的意识形态审美的条条框框,绕开枯燥的“阶级”、“革命”话语。将人还原给“人”:处在蟹工船这个特殊“场景”中具体的、鲜活的人——蟹工,这些原本是矿工、农民、渔民、学生、小贩出身的年轻的人们,设身处地地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欲求需要,才会理解斗争是他们的唯一的、本能的选择。
因为他们每天需要面对的是“壮实得像个建筑工地头领的监工浅川”,一只脚踩在铺沿儿上,不时地用牙签剔出塞在牙缝间的东西,一边说道:“我们不能把蟹工船事业仅仅看作是某一家公司的利益,这可是个国际性的大问题。这是一场事关我们日本帝国人民伟大还是老毛子伟大的,一对一的战斗!你们必须知道,是为着日本帝国的伟大使命,我们才拼着命去北海乘风破浪的!”
浅川与蟹工们的第一场对手戏就基本奠定了他随后的基本扮相:总是将乏味的捕鱼捞蟹无限神圣化,包装成日苏间的“渔业战争”;总是企图用一通家国天下、民族主义的说教把工人们侃晕,煽动起“奴隶”们的劳动热情,好少吃几碗饭、多逮几只蟹。
如果按照戏曲的脸谱来划分,浅川无疑是“黑脸儿”、集众恶于一身的大反派。对工人极尽呵斥、辱骂、鞭打、恐吓之事,当得知有人因不堪忍受,私自藏匿时他悬赏“发现杂工宫口者,赏蝙蝠牌香烟两盒、手巾一条”,他亲自书写“此人不忠,没病装病,不得松绑”的纸牌,挂在骨瘦如柴的学生渔工的脖子上,作为捕蟹公司代言人的他与船长抢占权威、抢夺话语权,执意要强压一头。当友船“秩父号”接连发来SOS信号紧急求援时,他果断指示船长不予理睬,坐等对方沉船。几百条人命的顷刻间丧身也不敌“公司投过的保险”可以大赚一笔的诱惑。“博光号”实在是浅川的个人王国,“浅川就是蟹工船,蟹工船就是浅川。”
与之相对的,作者小林多喜二却没有着力呈现一个“红脸儿”的“正面形象”或者“好人”来与浅川呼应。取而代之,他把蟹工作为一个整体形象表现。整部小说中出场、有台词的蟹工和杂工不下二十人,却几乎都无名无姓,戏份也没有太多集中到哪几个角色身上的迹象。关于这一点,小林在与评论家的通信中也坦然承认:所谓“主人公”的缺失是为了凸显集体的尝试。
蟹工船尽是些破船。工人们死在北鄂霍次克海,和丸之内大厦内的大老板们毫不相干。
不尊重劳动者做人的尊严,当他们的利用价值被耗尽后,便像使用过的工具或器物那样将他们丢掉。文学评论家小森阳一在漫画版《蟹工船》的推荐语中说:日本的许多年轻人强烈地感受到“那里面描写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现实。”
小林多喜二传奇而短暂的一生将他定格在了知识青年、文学青年、革命青年的标签上。人生因传奇而短暂,因短暂而传奇。我一直以为世人是偏爱那些早逝的英年的,比如这位29岁便被东京筑地警察署特高拷打致死的消瘦的年轻人。因为锁定在青春的文字里的永远是不羁与希望,是反叛与抗争。我想:青春是可以不朽的。
《蟹工船》读后感(五):真正的个人主义需要勇气——由《蟹工船》展开的对谈
受访人:金卷俊洋 (26岁,日本籍,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任职于上海某日资成衣公司,业余组有THE SNOTS乐队。)
F VISA:《蟹工船》看完后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金卷:吃惊。没有想到日本有过那样一段历史。公司方面几乎完全不考虑人权的问题,工人像奴隶一样生活着。
F VISA:不过日本现在的工作环境和当时完全不一样了吧?
金卷:嗯,完全不一样。现在虽然有种种不景气,但即便是临时工,工作条件也好多了。我觉得,大部分日本人是因为不了解国外的情况,只盯着自己的社会,结果完全不知道日本的好。
F VISA:不过就像刚才说的,和《蟹工船》里的贫穷没法比。
金卷:是的,我想那种绝对贫困基本消除了,但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在加大。二三十年前的日本社会有很庞大的中产阶级,贫富差距不大。而现在有不少人落到了所谓下流社会,同时流行起了WINNER(胜者)/LOSER(败者)的说法。人的生活好像就是赶班车,错过一班就成为LOSER,而且永远翻不了身。另外日本社会很喜欢比较,很多时候自己的价值和幸福度要通过和别人的比较才能确立。
F VISA:怪不得泡沫经济破灭后LV在日本还是很好卖。
金卷:嗯,那个是最明显的比较,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社会确实富裕。高中女生打工一段时间,也能买得起名牌手提包。
F VISA:说起打工,日本的临时工人数在增加是吗?
金卷:是的。泡沫经济破灭后,大公司很希望削减成本,雇临时工对资方来说是很合算的,因为不用买保险,裁员起来也很方便。这样的临时工一般由劳务公司组织,劳务公司从中收取中介费,这一点和小说里倒是有点像。请稍等(转身打开电脑,上网搜索,向采访者展示网页)。你看,这是2004年通过的《劳动者派遣法》,这样日本企业可以更容易地雇佣临时工,我认为这是经团连游说政府的结果,这个经团连就是由大公司和财团代表组成的。
F VISA:有人反对这样的立法么?
金卷:做这个网页的人应该就是反对者。你看下面有很多对《劳动者派遣法》的批评。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使用网络,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因为电视是被大资本家控制的媒体。
F VISA:既然年轻人对社会现状有不满,为什么不通过选举来解决问题。比如抗议甚至阻止类似《劳动者派遣法》这样的法律通过?
金卷:日本是个老龄化的国家,参加选举的也是老人比较多,年轻人的政治想法不容易通过投票来表达。而且从年轻人在学校受到的教育也有问题,学生对“爱国”没什么概念。简单说来,年轻人如果不出国,很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日本人。总之日本人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团结,尤其在年轻人中,流行着一种变了味的“个人主义”。就是万事以自己为先,要求别人什么都听自己的,把所谓的“个人”和“个性”放到很大很大,同时又不愿意承担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F VISA:嗯。“个人主义”原本没那么糟糕。它的前提是义务的承担和对个人选择的负责。那个秋叶原的杀人犯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可能就不会下手这么狠。你一会儿还有事吧,那我抓紧时间继续。能谈谈你在上海的工作么?
金卷:好的。我在成衣业工作,是一家在日资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我们有点像一家中介,负责联系中国的供货商和日本的客户。我在上海的收入不如在日本的同龄人,不过生活质量不错。我的弟弟在日本,在一家大公司做白领工作。他每天加班到10点左右,周末陪女朋友、购物、打扫,属于自己的时间几乎没有。我在上海每天5、6点下班,很少加班的。所以有自己的时间练习贝斯,组织排练和演出。
F VISA:这个我倒没想到,你的老板不错嘛。
金卷:因为中国的供货商都是准时下班,我们联系不到下家的话,加班也没用。其实在日本的总公司还是每天加班到很晚(笑)。
F VISA:你对日本共产党有什么概念么?他们的主张,最近的活动什么的。
金卷:我完全不知道。日本共产党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遥远和边缘,影响力很小。我想绝大多数日本年轻人都不会注意他们。日共比较有名的是在60年代,我父亲在念大学的时候。
F VISA:对,弄出了不少新闻。那你和日本的年轻人都对那段历史没什么兴趣么?我的意思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对历史普遍没兴趣。
金卷:(笑)听起来像老人家的抱怨啊。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就这么抱怨了,在他们的壁画上有老人对年轻人的抱怨,被抱怨的年轻人活到现在也已经两千多岁了。
F VISA:囧,那我岂不是更老了(笑)。
金卷:我还是建议日本的同龄人多去国外走走。去欧洲、去中国、去非洲都可以。日本每年出国旅游的人当然很多,不过兴趣大多停留在表面。来上海吃吃小笼包、看个东方明珠什么的。我的意思是日本年轻人有条件去国外住上一段时间,比较深入地去理解当地的文化,这样再反过来看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也会有新的认识。我觉得日本文化不单单是艺伎、茶道,文化可以是广义的。日本人现在的礼貌、守信也是从长久的历史里发展起来的。
F VISA:你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来到中国的么?
金卷:应该是的。在中国,生活还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这个是我在日本不可能拥有的。
F VISA:那有什么代价么?
金卷:如果说代价的话,可能是收入没日本高吧。
F VISA:但这点对你不成问题吧。
金卷:是的,完全不是问题。我不看重那些“价值”。这可能和我的家庭有关吧。我的家族从武士时代起世代行医,从来没有间断。我的爷爷做过军医,但这段经历好像给他很不好的回忆,所以后来一有机会,他就转行去做船医了。就是那种一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漂泊在海上的远洋轮船医。这样他开始有机会和海外接触,这一定影响到了他的世界观,对子女的教育也开始不同于一般日本人。我的父亲报考大学那年正赶上学生运动的高潮。他投考的东京大学干脆停止招生。第二年再考的时候,竞争当然格外激烈,于是没被东大医学院录取,转去了千叶大学,也没有学习医学。家族的行医传统就这样结束了,好在爷爷对此也表示接受。我的一位叔叔学了心理学,在东南亚的一家螺丝公司干了几年后,带家人一起回了冈山老婆的娘家。在乡下盖了一幢房子后就定居下来,每天种种地。我回去见过他,感觉他生活得很健康,他还和我聊了老子和庄子(笑)。爷爷自由派的教育方式也遗传给了我的父亲。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了选择的自由,不过父母也会说清楚选择的后果,这个必须自己承担。
F VISA:乡下生活也好,来中国念哲学也好,都是很明确的自我选择。这是一种能力。
金卷:没错。我在复旦大学念书的时候,身边太多的同学缺乏这样的能力。他们都是很会读书的好孩子,各方面的能力也很强。不过说到个人选择和个人责任方面,则是娃娃级的水平。他们回答不好“你想做什么?”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从别人或者媒体上得来的。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心理是相类似的,日本人会说“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也会这么说。所以说,真正的个人主义是需要拿出勇气的。我能够理解那些从《蟹工船》里获得同感的上班族,毕竟早上9点挤东京的地铁不是什么开心的事。
但现代社会还是有更多的可能性。下流社会的年轻人在打工之余可以选择不去秋叶原和弹子房,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网络来自学充电。FREETER应该看到这一点,自己更加努力。我手头有个很好的例子。我在东京的一位朋友,原来是物流行业的,但他很有经济头脑,业余会自己炒外汇,挣了600万日元后就结婚,并且有了个孩子。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突然离婚,由于婚礼花了不少钱,而且要承担孩子的高额抚养费,他欠下了1000万日元的债务,还辞了职。说实话我当时挺担心他,并且预感到他可能就此落到下流社会,从此不得翻身。但后来的结果是他在家埋头苦学了半年,真的是心无杂念、非常努力地学习。然后就通过了外汇交易员的资格考试,被一家金融公司聘用。虽然现在的薪水不高,但我相信他的年薪不久将超过1000万日元,超过所谓WINNER的标准。这样的可能性在《蟹工船》时代是不存在的。
F VISA:谢谢,的确是很生动的例子。不好意思,已经超过你说的采访时间了。说句题外话,你正在学习意大利语么?本子上面是你的笔记吧。
金卷:是啊。意大利语够难的。不过服装业也好,摇滚乐也好,欧洲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想学完意大利语后去那里看看。
* 原要附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里,后被毙。谨以此文纪念三年Freeter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