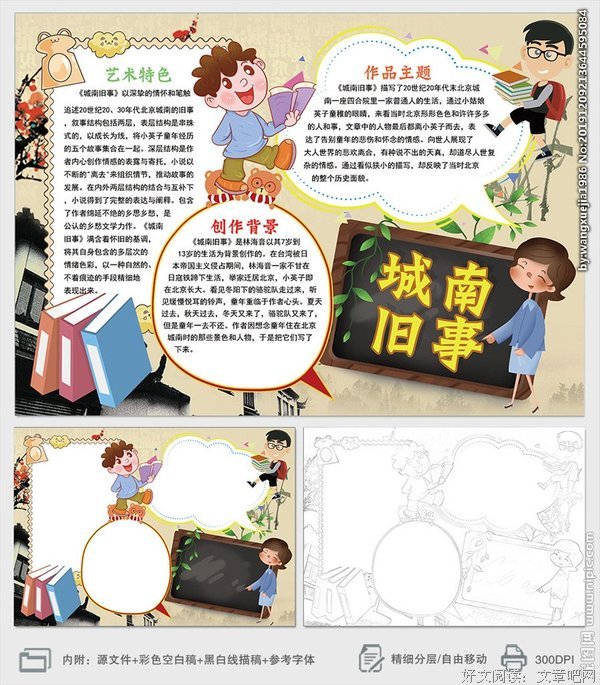往事不寂寞读后感锦集
《往事不寂寞》是一本由李菁著作,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0.00元,页数:51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往事不寂寞》精选点评:
●总是喜欢看这些历史人物的轶事,或许是一种窥私癖在作祟。历史到底是什么,越遮掩,我却越好奇。
●一口气读完的 纯粹为了找个人说话
●三联的文集之一。当初购入只因目录很吸引我,看过之后感触颇深。印象最深的是,黄宗江那篇。老先生在幽默玩笑中,将自己和他人跌宕起伏的一生娓娓道来,韵味悠长。本书虽然价格较高,但值得推荐。
●可怕,写这本书的评论竟然还要审查,悲哀啊
●还可以啦,最后李菁那句由于多种原因好多史料不能重见世人,真是无奈啊
●在迷茫时读过,感觉有些大收获
●信息量愉悦感俱佳的口述史。赵匡胤建朝时说不杀文人士大夫,宋士文化最盛。后元明清红四朝知识群体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后枪毙,任仲夷为她平反作批示那段在网上都被阉割。“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大历史下的个人视角
●在大连的一家文化气息浓厚的小书店买的,原因是翻到了那篇 我的父亲储安平。
●红色贵族的部分可以更恶心点
《往事不寂寞》读后感(一):寂寞的不是往事
2序“ 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心力----心高气傲与舍得付出结合的结果,而能否在瞬间产生激情也至关重要。”
“相对于光鲜的人物,她对尘封的那些人物身上已经过去的历史烙印甚至苦难更感兴趣。”
全书只是以人物访谈为主,缺乏一个背景介绍,在感染力上还是有些缺憾的。
《往事不寂寞》读后感(二):评《往事不寂寞》
通读这本《往事不寂寞》,是需要细火慢烤地慢慢品味和幽寂沉思的。
亲切、随意、简略,给人洁净而又深沉的感触,这样的书我久矣读不到了,今天读来实在是一件叫人高兴之事。
作者审视历史,拷问灵魂,洋溢着哲思的火花。人生是一段段的旅程,也是需要承载物的。因为火车,发生过多少相聚和分离。当一声低鸣响起,多少记忆将载入历史的尘梦中啊。
其实这本《往事不寂寞》一开始我也没看上,是朋友极力推荐加上书封那个有点像史努比的小人无辜又无奈的小眼神吸引了我,决定只是翻一下就好,不过那开篇的序言之幽默一下子便抓住了我的眼睛,一个词来形容——太逗了。
《往事不寂寞》读后感(三):那个年代那些人
一、龚澎
章含之有个帮她宣传的好女儿,龚澎则掩埋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中。
40年代初,龚澎充当了与外国记者、外国使节打交道的新闻发布员。当时很多外国友人成为了她终身的朋友,直至80年代,那批在二战中到中国采访过的记者都对龚澎念念不忘。这便是她的个人魅力。
解放后,龚澎成为了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余名正司级官员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她才华横溢,而又沉稳低调,坚定、果断,正是在她的影响下,锋芒毕露的乔冠华才迎来了外交生涯的高峰。而也正是她的离世,加之与章含之的结合,让乔冠华陷入了复杂的政治漩涡。
二、任仲夷
全书并没有专辟章节写任仲夷,知道他的年轻人可能也不多了。我也是在张志新的章节中才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
文革阴霾还没散去的情况下,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执意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烈士的就是他。
他在常委会上说过:“今后处理案子,凡属政治思想犯,千万不要杀。”
他解释“和谐”为:“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
《往事不寂寞》读后感(四):历史没有真相
从小就爱说自己喜欢历史,其实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历史人物的故事。
比如:
汉武帝60多岁了还能遇到十多岁的钩弋夫人,那双握了十几年玉勾的小拳头还刚好就让他给打开了,多传奇呀!
张学良在日本人打到家里边来了的时候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共舞于北平的舞厅……
马克思在图书馆看书,每遇激动处就跺脚,以至于把脚下的地都跺出了坑洞,多好学啊!
华盛顿把父亲的樱桃树误砍了,主动认错,多诚实啊!
……
可看的书多了,才知道:
那钩弋夫人许是小儿麻痹症患者,更有甚者可能只是别有用心之人的棋子,传奇只是表象。
张少帅在“九·一八”那天压根不在北平,也始终不识传说中与自己共舞的“舞蹈皇后”。
马克思喜欢跺脚也许不假,但却没有哪个图书馆的地因他而遭殃。
至于华盛顿,谁知道他们家有没有种过那棵可怜的樱桃树呢?
……
就连这些历史人物的小八卦都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真正错综复杂、牵扯众多的大历史就更没有绝对的真相可言了。我们大部分人如今读历史、思历史、评历史……其实只是“一切唯心造”罢了。
比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人,在文学界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可到了“爱国知识分子”眼中就成了所谓的“汉奸文人”、“软骨头”;同样是北师大的女校长杨荫榆,在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中,她不可逆转地站在了历史阵营的反面,而在杨绛先生的《回忆我的姑母》中又是另一番模样。
孰真孰假,孰对孰错,谁又能说得清呢?
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口述史的重要性了。比如对于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抗战史,台湾有《一寸山河一寸血》,大陆有《我的抗战》。其它零零散散不成系统的口述史、回忆录也并不少见。
这本《往事不寂寞》在这一类书中并不出挑,但三联的质量保障还是有的。
与历史教科书上寥寥几笔的描述相比,这样的口述史显然更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窥视欲,也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看起来我们似乎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近了。
可是再一想,这些口述者确实是历史的亲历者,但同时也是上了年纪的普通人,也是那些历史名人的亲人或者后人,他们的记忆真的可靠吗?他们的描述真的客观吗?
答案恐怕是无解。
历史是没有真相的,从它成为历史的那一刻起。
我们如今看到的史料不过都是旁人的八卦罢了。写帝王将相家史的所谓正史,是高端八卦;而历史的边角余料,那些鲜香麻辣的野史,则是八卦界的业界良心;至于如今甚嚣尘上的戏说历史、白话历史,本就是辗转多道的八卦,还被夹带私货,添加了现代人自己的佐料,充其量只能算二流八卦;而像这样的口述史则可算是资深八卦。
可惜的是,这样的历史亲历者越来越少了,前几天看杨绛的近作,说亲眼见证过五四运动的人如今只剩她一人了,不禁心有戚戚焉。
虽然说历史没有真相,但能看看卸妆后的历史,哪怕只是盲人摸象式的片段性接触,也算得上一大幸事了。
《往事不寂寞》读后感(五):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2009-07-24 李菁 采写 书摘 唐德刚 李 菁:唐教授,我们都知道您为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
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
2009-07-24 李菁 采写 书摘
唐德刚
李 菁:唐教授,我们都知道您为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做了口述史,您的书在大陆也有很多读者,能介绍一下您当时是怎么开始口述史工作的吗?
我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是为哥大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做助理,因为我会讲汉语。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口述史就是胡适的。
李 菁:有人说您的运气很好,您在为胡适做口述自传的时候,是胡适先生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有时间给你讲自己的那些经历。大陆这几年出现胡适热,您的作品又再度广为流传。
唐德刚:我开始认识胡适的时候,也正逢国内清算两个姓胡的,胡风和胡适。胡适怎么敢回去!胡适虽然有大使的退休金,但在美国过得很辛苦,他那时在美国跟我们一样,也没饭吃。胡适大博士,英文也讲得那么好,但他也找不到工作,他不想教教书?但谁让他教啊?他也不好意思开口求别人。
胡适那时候时间太多了!胡适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还组织文学社,不但胡适,林语堂也在。林语堂比胡适过得好,因为他写英文书,英文书出版拿一笔稿费,翻译成中文又拿一笔稿费,所以他过得比胡适好。胡先生那时也很可怜,他生病也没医院保险,我们在学校念书,还有医院保险。他后来连看病都看不起。胡适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别熟,我会开汽车,胡适和他的小脚太太都不会开车,我替他做的事可多了,他经常打电话,说:“德刚,过来帮帮忙!”他搬个东西都搬不动。
李 菁:除了胡适,您还给李宗仁、顾维钧这些人做过口述史,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唐德刚:给李宗仁做(口述史)跟给胡适做,完全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胡适是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哥伦比亚大学为了省钱,我和胡适讲的都是英文。打出来直接交给哥大就行了。那时候李宗仁在美国也没饭吃,但李宗仁日子比胡适好得多,他在银行存款还几十万哩。李宗仁是军人出身,文学、历史完全不懂,完全由我来扶植他。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顾维钧的英文比胡适还厉害,我跟胡适平时还要中文聊天,顾完全不讲中文,一开口就是英文,有时讲的英文单词我还不懂。
有一次顾维钧告诉我他每天都写日记,我问他,你的日记用哪种语言?他不好意思地说是英文,他的中文不够用,他的母语其实是英文。后来他所有的材料都给我了,我一看,他几十年的日记,没有一篇是中文写的,有英文,有法文,我和他谈话百分之九十九是英文,那百分之一就是在说人名,像提到“袁世凯”的时候才用一点中文。
李 菁:我们知道当时很多人都在同您联系,想做自己的口述史,后来为什么只做了那几个人的呢?
唐德刚:国民党高官那时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他们都想做自己的口述历史,因为美国人给钱。宋子文找过我多少次,宋子文我并不认识,但他知道我,我也想做宋子文的,他是多重要的一个人!他和顾维钧差不多,都是英文比中文流利,批公文都是“OK!”不像其他官员,“准”或“不准”。宋子文和顾维钧是桥牌伙伴,他告诉顾也想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说想找唐德刚。顾先生跟我提这件事,但我没办法,在哥伦比亚我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主持政策的人。
李 菁:给他们做口述史,“哥大”会给宋子文、胡适和顾维钧同样的报酬吗?
唐德刚:不同的。它衡量每个人值多少钱、你有没有钱。美国人也知道胡适可怜,像他这样的人不能死在美国吧? 那样就成了美国的大笑话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给胡适薪水。我跟哥大讲好了,给他三千块钱一年。胡适高兴死了,那时候三千是笔巨款。所以胡适和我两个人合作,他说“你怎么着都好”,我要他签字他就签字。(李宗仁呢?)一个铜板没给,他有钱!但胡适是穷人,everybody knows。顾维钧也没给钱。
我还要提到一个人是陈立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做过院长,蒋介石的左右手,他是蒋介石的family member,但国民党破产,台湾也讨厌他,只给他一笔路费把他赶到美国来。他后来真是吃饭都成问题。自己开了个鸡场,上饭馆卖鸡蛋,卖鸡蛋的不是他一个人啊,大家还要排队,陈立夫也要排队,卖鸡蛋的都是穷人啊,结果到最后喂鸡的饲料比鸡蛋还贵,很多卖鸡蛋的都破产了。我后来到大陆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这个词,但我在北京就说,陈立夫可不够资格,他过得还不如我,我也不是陈立夫的什么人,我讲老实话嘛!
李 菁:大陆很多人都认为,您没有给张学良做成口述史是个很大的遗憾,您怎么看这件事?
唐德刚:我跟张学良很熟,但我跟他接触后发现,他的话我可以听,但张学良的书我不能做。你不做这一行你不知道,这个张学良是大而化之的人——你要听我的话,做学问,我是排长,你是小兵——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你不能校正他。他的录音现在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像我跟胡适合作,我写,你读,所以胡适留在哥伦比亚的原版录音带其实是我的稿子,胡适照着念的。
但跟张学良不能这样工作。我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
他说:“你知道什么?!”他是少帅,我连少尉都不是,所以他说:“你要听我的话!”
我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
“什么笑话,我讲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话!”
所有的官场要人,都是如此。他们一出来,都在替自己说话,都认为自己对得不得了。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
我跟张学良说,汉公,你这个事情记错了,他说:“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顾维钧那么仔细的人,还有错,何况张学良?搞口述历史如果没有相当经验,没法搞。
李 菁:那您是怎么处理和这些被访者的关系的呢?
唐德刚: 对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办法。李宗仁也是我建议哥大为他做口述史的,但当我刚开始找到李宗仁时,他不敢谈。顾维钧最初对我存戒心,他们知道我的老婆是国民党 CC系要人的女儿,我是CC的女婿,所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谈话都很小心(注:唐德刚的岳父吴开先为国民党元老,也被认为是CC大将之一)。有一次我们随便谈到这儿时,他说,德刚,这CC有功劳啊,我说,CC也未必有什么功劳。他说,德刚,你也敢讲你丈人啊!我说我是搞历史的,中立的,跟官僚不一样。他很高兴,赶紧让郭德洁多做饭给我,李宗仁我给他搞了六七年,慢慢处得像家人一样。
李 菁:您接触过的这些名人,像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这几个人,哪个好相处?
唐德刚:还是胡适。胡适本身经过学术训练,能理解我的工作,有时比我还严格。有时我要记下他说的话,他说这个言出无据。胡适对我非常信任,我和胡适还有些私交。有些事情,我还可以教训胡适一顿。胡适一辈子教了很多的学生,我是他最小的一个。
李 菁:所以他也愿意把他和陈衡哲的一段恋情告诉您吗?
唐德刚:他没跟我讲,也没跟别人说,是我自己考证出来的。
因为我跟胡适搞熟了,我同他乱讲,我说,你认识了陈衡哲,你是不是要同她结婚? 他说,我和陈衡哲感情好得不得了,但她也知道我不能同她结婚。我要不同她(注:指胡适夫人江冬秀)结婚,三条人命—— 我太太自杀,妈妈也自杀,孩子也生不出来,所以三条人命。我说,胡先生,我们都不如你呀,我们都没你那么忠厚,不认得字的太太还要娶,那你也有比我们好的地方,你还有一个女朋友哩! (笔者插话:你开这样玩笑他不介意吗?)我和他很熟了,他也经常打电话到我家。胡先生打电话到我家来,有天我不在家,我太太的妹婿也是一个博士,在这接电话,问你是哪一位?对方说,胡适,胡适!妹婿紧张得把听筒扔掉了,谁不知道胡适大博士的名气啊!所以你interview学者或政客,你如果不同他搞得很好,他要隐藏很多东西。
李 菁:可是这种关系如何平衡——既要和他们保持密切关系,让他们对您毫无保留,又要在操作上保持一定距离,不能有闻必录?
唐德刚:我这个人可能运气好,很容易和他们搞到一起。胡先生很厉害,对我像家长一样,经常教训我怎么做学问啊;李宗仁跟我连距离都没有了。李宗仁的太太到香港了,就剩我和李宗仁两人在家,李宗仁在家烧饭给我吃。我跟李宗仁也熟到我可以问他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的地步;顾维钧则始终跟我保持距离。 怎么平衡?我讲的是历史,是历史真相。我们学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李 菁:我注意到除了历史著作外,您也有许多涉及时政的文章或评论。有人认为,历史学家更应注重发掘新的证据或事实,过分跟进当下发生的事情、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做出评断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唐德刚:谁说历史学家不能对现实说话!我是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可以对现实发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对,对不对需要时间来检验。搞历史的要有一套历史哲学,我们不能拿中国的历史跟英国、跟罗马比。
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有上有下,许多历史,恐怕还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评断。
(摘自《往事不寂寞》,三联书店2009年1月版,定价:5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