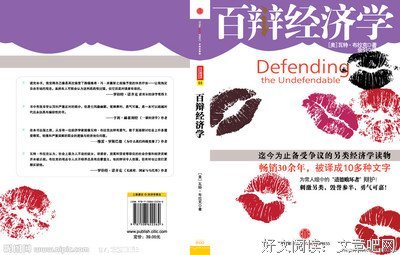《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读后感精选
《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是一本由图洛克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98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200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2012-01-05读毕,感觉如果没有对寻租有一定了解,这本书读起来,还是不容易的,总结部分介绍中国的地方比较容易读,也有启发
●翻译扣星
●......之所以这么穷的最主要原因是,这种体制使得经济进步很难发生
●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图拉克的文字本身就是如此晦涩难懂,这样的文章水平甚至称不上通顺和连贯,更别说让阅读者通过理解并思考经济学问题了。书名很牛逼,但是内容不敢恭维,举例和论证过程简直让人抓狂。另外我认识到,如果经济学家在写经济论文时却卖弄自己的文采,对读者将是一种灾难。
●写得比较晦涩,时间也早了些
●图洛克是个经济直觉的天才,但是训练实在太差。用含混不清的语言讲故事一样写论文,把一个又一个好问题都糟蹋了。能不能得奖就看后天了~
●读到就这儿就算了了哇,头大头大头大...
《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读后感(一):特权与寻租
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都标榜权力属于所有人民,或者也是统治的阶层。但是,实际上,权力的施行都需要有一部分人来执行,来代表,当权力受不到适当的监督时,这种权利就成了事实上的“特权”。
寻租为何会存在,是因为寻租能带来巨大的利益。要阻止寻租,方法一是提高寻租的难度,二是提高寻租行为曝光后给交易双方带来的损失。
寻租很难彻底避免,但并不代表就无需采取措施来减少寻租,或者认为寻租并非全然有害。
《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读后感(二):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读书笔记
在这里我要批评作者或者译者中的一个或两个。虽然我是凡人,但是因为这本书的晦涩难懂我也要挑战一下经济学家和翻译家的权威。
书很好,但是没读懂。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图拉克的文字本身就是如此晦涩难懂,这样的文章水平甚至称不上通顺和连贯,甚至我感觉逻辑推理性都很差,更别说让阅读者通过理解并思考经济学问题了,让人感觉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图拉克的论文集,由于我没有去专门查阅英文文献,对于图拉克原文的写作风格无从知晓,从前言中图拉克的生平介绍中我发现图拉克竟然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法律专业出身,后从事公共政策研究,译者甚至提到他在芝加哥大学仅仅修过一门经济学课程,是亨利西蒙斯讲授的,重点是这仅仅一门经济学课程也没有上完。更搞笑的是译者提到了图拉克很多论文被期刊拒掉以至于后来他自己把所有被拒论文编成一本书出版。译者提到了这么多的图拉克黑历史是不是在翻译的时候也对图拉克行文如此散漫咬牙切齿啊(斜眼),以至于纷纷抛出图拉克的黑历史以便表明这绝对不是我翻译水平的问题,而是作者行文本来就是这样,你们看书感叹文字如此艰涩时不要把炮火对准我,请对准图拉克。
更奇葩的是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发现,图拉克说本书是口述形成的(至少一些章节是),我心里就像吃了翔,这也就印证了本书框架和逻辑如此糟糕的一些原因。所以我觉得读者还是不要把这本书当成经典,把他当成经济学科普读物来扩充知识面比较好。
《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读后感(三):简单备查笔记若干
相关书目:
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分析:
“我们还不清楚投票者利益分化的利弊。利弊分化带来的损害可能不像推行社会公利带来的损害那样大。”(P32)
“在这方面,苏联的科学界是典型的例子,法国也差不多。实际上,俄国人在科学研究上投入比美国更多,但因为他们是中央计划体制,所以取得的进展很小。在那里,这意味着,实验室中所有最聪明的人都在钻中央计划体制的空子,而只有第二层的人在从事实际研究。”(P55)
“寻租理论在这里的一点小贡献是,它指出了如果垄断是通过利用某种政治过程得到的,那么资源也被浪费在获得这一政治支持上。”(P63-64)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政府的转移支付不是从富人转移给穷人,而是从政治上组织不力的人那里转移到政治上组织得好的人那里。”(P72)
“寻租的减少并不是因为我们发现了什么神奇的方法,仅仅是因为政府的规模相对变小了。”(P92)
背景知识:
1.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是威尔逊政府早起的国务卿。他当时积极的中国政策的目标是对中国快速皈依基督教不加干预,当时他认为这种变化正在发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革命是由威廉·霍华德·塔夫脱Taft总统引起的,当时他为了使美国银行家获得特权而做出了不明智的决策。为了做这些事情,他耽误了一些重要的铁路建设。这一耽误通过一系列间接的机制,诱发了中国的革命,……(P33)
买这本书的时候大学书城还开着,标价人民币5.5元。
《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读后感(四):寻租的文化
小明家是卖臭豆腐的,每月收入5万块,因为老婆生了孩子开销增加,想要增加每个月2万的收入。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两个主意。一个是去隔壁街区再开一个臭豆腐摊。第二个是收买城管,把附近所有的臭豆腐店或者臭豆腐摊都赶走。这样他不仅可以增加销量,还可以提价,因为产生了垄断。最后扣除给城管的费用,也可以增加每个月2万的收入,而且还风险小,于是他决定采用第一种。
第一种方案叫寻利。在个人获利的同时,社会总财富是增加的。
第二种方案叫寻租。个人的获利是对他人利益的转移,而且对社会总财富是负效应。(臭豆腐提价对消费者有害,而且有人因为贵了,可能就不买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和制度下可能有不同的发展故事。
比如在一个法律、舆论监管强度大,丑闻代价高的地方,城管就会用低效高成本的方式去履行和小明的合约。比如走法律手段,规模小于多少的豆腐摊被定义为违法,卫生条件达不到某个标准的被定义为违法。与此同时,小明家也要增加自己家店的卫生设施以符合要求。于是城管在降低丑闻风险的同时,增加了履行的成本,比如,他们可能还要和卫生部门去分享贿赂。所以对城管来说,从小明手里拿到的3万块钱贿赂,最后可能到手只有5千。这种低效的方式,限制了寻租的规模。因为可以的获利空间小。
而在一个监管缺失,舆论压力小的地方。城管可以用高效的方式去履行和小明的合约。比如野蛮执法,强行拆除。这种情况下,城管基本0成本。在这个系统里面,尝到甜头的城管会去拓展其他的业务,比如延伸到蛋饼摊,烤串。。。等等。。。
这条街上,小明的主要竞争对手小红,知道了小明的计划。他不愿意坐以待毙。于是小红也去贿赂城管。就是参与寻租。于是小明不得不增加对城管的贿赂,这个进一步增加了他寻租的成本。最后竞争的结果是,城管决定除了小明和小红其他的豆腐摊都拆除。
于是小明预期的垄断没有形成,价格的提升没有预期的那么多。然后他寻租的成本也增加了。最后没有得到2万的利润,而只获得了5千。对小红来说,他的获利维持在原来的水平,但是他当时如果不参与寻租的竞争,就可能要关门失业,所以比起来,这个寻租行为对他还是非常有利的。
在整个过程中,消费者的利益受到的损害,社会的总财富减少了。只有城管和小明获利。而且他们的获利比起他人的损失来,要少。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寻租文化开始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被破坏。通过勤劳致富的思路被依赖寻租获利的思路取代。
事实上,如果一开始,小明光明正大的去投资一家新店,他可以获得2万的利润,这个比5千的寻租利润高。同时,小红也可以把参与寻租竞争的成本投入到增开新店,这个也可以增加他的收入。而这种寻利行为,不会损害这条街上其他臭豆腐摊的利益,增加了社会总财富。
以上这个故事就是俺看完《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之后虚构的。作为一个微观模型,大家不要对俺的数字的准确性太苛刻了。
当初在思考中国经济现状的时候,顺藤摸瓜的找到了这本书。没想到,作者在最后一张总结中说,启发他想到寻租这个概念的,是他在中国当大使的生活。。。
作者对于垄断也有很犀利的表述。
在一个自由度高的市场中,真正的私人垄断是很少的,大部分的垄断还是政治垄断。
现在,天朝的国有经济比重高达80%。而这80%,因为他们的寻租依赖,所以注定是低效的。
《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读后感(五):廉洁不比腐败好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国企。我的第一个领导是出了名的正人君子,不弄虚作假,不贪污贿赂,一切公事公办。其实,给这种人当马仔很痛苦。他是工作狂,所有满足感来自于业绩增长,公司上下经常加班加点。更要命的是,他讲廉洁,漠视私利,公司效益好时,他不给员工多发一点钱,效益差时,他却带头勒紧裤腰带。这样卖命,集团领导当然会表扬他,说他大公无私、任劳任怨,可是公司员工都很讨厌他,因为付出多而收获少。后来他调走了,据说是因为不会做人,逢年过节也不给集团领导进贡。于是公司来了新的领导,风格明显不同,非常腐败。他重用小人,谁送礼,谁奉承,他就提拔谁。这种人对业务一窍不通,可是他命好啊,前任留下了丰厚家底,够他挥霍好几年的了。他最擅长的是巴结上级,还把集团党委书记的二奶安排在公司,让她不干活白拿工资。这个女人和我一个办公室,坐在我的对面。夏天时,她穿着短裙,常常百无聊赖地晃动大腿,我总能不经意地瞥见她的蕾丝小底裤。那段日子就是我在国企最快乐的时光,每次下班回家,我都感觉浑身充满力量。当时我有一位同居女友,我历任女友里就数她对我的性能力评价最高,但她绝不会想到强劲动力的真正来源。按理说,我的这位新领导如此下贱,应该招人厌才对。其实不然,大家都爱戴他。他自己捞钱,也与员工分享。有一年明明亏损,他硬是把帐做成盈利,年底发双薪加奖金,皆大欢喜。
腐败比廉洁更好,这就是国企教会我的。一直以来,我对自己抱持这样的罪恶想法很惶恐,甚至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受了集团党委书记的二奶的影响。她雪白的大腿,配上一条纯黑的蕾丝小内裤,这个画面让我今天回想起来,还是忍不住猛咽口水。不过,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图洛克的《特权和寻租的经济学》,终于明白过来了,我的想法其实没有错。图洛克指出,在这种受到政府呵护的国企里,滋长腐败是必然的,个人廉洁毫无意义。直接地说,在一个错误的体制内,怎么做都是错。
图洛克是借助“寻租”的概念来说明问题的。关于“寻租”,他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利用资源为某些人牟取租金,并给社会带来负的价值。”这个定义太粗略了,容易造成歧义,貌似在政府行为之外,市场中也有“寻租”。 图洛克似乎并不强烈否认这一可能性,他说“寻租研究的基本是非市场行为或者是那些通常被认为不合意的市场活动”。但实际上,他自己的论述始终围绕着“非市场行为”。他举过一个例子,两家钢铁企业都追逐利润,一家通过竞争获得定价优势,一家通过政府限制进口钢铁,但只有后者才是“寻租”。不过,无论怎样,我所在的那家国企都是“寻租”的典型。它从事的是特种行业,从政府获得经营牌照,有的自营,有的出租。每年政府都做一次清理整顿,有些牌照可能会因违规经营被吊销,所以公司年底都会去“游说”政府,争取多发牌照。在这一过程里,可以想象,“腐败”也是不可免的了。
不过,这里要插入另一位经济学家罗斯巴德的观点。他认为,像我们公司这样,为了取得牌照而向官员“行贿”不是犯罪,只是被迫支出“成本”而已。真正罪恶的是政府干预,使得自由经营变成了特权经营。其实,图洛克的观念差不多。他甚至将“行贿”视为激励。他说,“通常,政府不是天然就来做好事的,必须要有激励来诱导它做好事。”但同时,他强调这种制度安排本身很糟糕,“我的建议是用寻租(我经常这么做)来表示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事情,不管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有趣的是,引发他思考“寻租”问题与他在中国的经历有关。图洛克说,他来到中国很困惑,原因是“芝加哥尽管也很腐败,但却没有那么穷困。”然后他通过观察发现,中国“拥有高素质的人和辉煌的历史”,却陷入了“经济进步很难发生的”的体制,“这一体系将财产视为特权“,而其“造成的结果就是,很多精力都被投入到现在我们称之为寻租的领域了。”如何摆脱这一困境呢?图洛克给出的答案很简单,西方的成功经验是,“寻租的减少并不是因为我们发现了神奇的方法,仅仅是因为政府的规模相对变小了。”他还反驳私人垄断的说法,强调“大部分定价高的垄断是靠了政府的保护。”
“寻租本身浪费了资源,寻租所产生的制度本身也有成本”,这是图洛克的结论。他指的是其外部的、社会性的负面影响。但对于企业乃至企业内部的人员,“寻租”是否会有利于牟利呢?图洛克的回答是“不”。他举了一个例子,纽约出租车经营牌照,由于政府控制数量,价格很高,除了第一批拥有牌照的人能通过转手获得丰厚利润外,以后进入该行业的人,都要先付出很大一笔钱赚取普通的投资回报。罗斯巴德的说法就更直接了,他说,特权存在会导致消费者的估价不变。从长期来看,特权被授予之后,投资这类企业只能获得一般的利息回报。这两种说法都解释了为什么众多的大型垄断国企效益不佳,都无人竞争了,却还能够一亏再亏。至于垄断国企的工资福利高,其实也是神话。我在国企的那段日子,经常被有些朋友批评为“体制内”,好像过的是吸血鬼的生活。但实际上国企内永远是塔尖上的寥寥数人得益,绝大多数人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稍微风光一点的时候,就是那位腐败的领导当政,全靠他的大无畏精神,才蹭上了几顿好饭吃。
我的国企生涯还教会我另一条宝贵的常识:国企是永远搞不好的。除了有产权不清晰的原因外,还有先天性的寻租依赖症。从这类企业身上,哪里看得到所谓“规模经济”。它们规模越大,就越是寻求政府的保护,阻止别人与之竞争。这样的模式,必然造成一方的获利以他人的损失作为代价,破坏了自由市场最大化社会效用的功能。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郎咸平是错的。国企全面退出,其实才是社会之福,也是百姓之福。如果郎咸平不信,不妨找个国企呆上两年。不过不能让他坐党委书记那个位置,而只能像我这样,用一介平民的眼光看世界。但我不能确定,该不该在他办公桌对面也安排一位公司领导的二奶。郎咸平太情绪化了,我担心他定力不够啊,弄不好会因此加倍地热恋国企。或者,从此染上了偷窥裙底春光的恶习——唉,就像可怜的我,现在一想到国企,一想到自己虚掷的光阴,就很想抓起手机到百货大楼里闲逛,尾随穿短裙的长腿美女,将罪恶之手悄悄地伸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