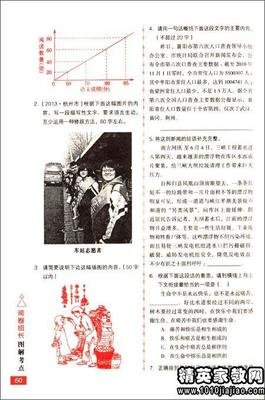《无名盛宴》读后感摘抄
《无名盛宴》是一本由糖匪著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3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名盛宴》精选点评:
●打分虚高了吧。。。实在没兴趣,一章弃。
●茅奖大师推荐的作品必然值得期待!
●别说科幻,既不像魔幻又不像言情,只剩下絮絮叨叨,乱七八糟。
●难以分类,云里雾里。
●我可能克科幻小说吧……买来很久了但阅读起来实在艰涩 所以这就是它被称作“异质”的原因?
●缤纷而萦回的弱者歌谣,虚无而庞大的命运谜团 金宇澄、刘宇昆、黎幺 诚挚推荐!
●并非长篇。不好看。
●无名者,赴盛宴。 世间事,多如此。 我们都是历史中的无名者,侥幸能留下只言片语,于是成为他人人生的过客。我们不可靠的记忆,在别人眼中,便成了虚构的故事。无关现实,无关理念,这些水上漂走的声名,终将消逝,最后只有师出无名的一家人,赶赴各自付之一炬的结局。
●糖匪的文笔轻盈飘逸,很多章节读起来宛若仙境,且在必要情景里又不失直击人心的力道。强推!
●敏感,脆弱,绝望,缤纷,然而难以抹去刻骨的孤独
《无名盛宴》读后感(一):糖匪:好故事可以抵御恶(访谈节选)
何平(文学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当下小说不同类型的作者他们各自被关注范围好像有一个无形的边界,比如你,一般而言是被视作一个科幻小说家,你写星际旅行、人工智能、虫洞,……但我觉得你的小说不一定要当科幻小说来读,或者说你的想象并不完全依靠“科幻”之“科”,而是你自身的源发的想象力,是一种已有文学类型暂时很难规定的幻想文学,至于你这种幻想文学向哪个方向走,我现在很难做一个肯定的判断。
糖匪(作家):在你我的这个宇宙里,按热力学第二定律,随时间,孤立系统熵不会减少。这个问题关系着时间的流向,到生命的生理代谢,宇宙的起源,也关系着你的热咖啡为什么会变冷这样的小问题。而我设想的平行宇宙里,熵正好相反。What if,是写科幻小说的重要乐趣之一。重新创造了一个世界,从动力学到生理代谢到时间还有投掷骰子的概率,都相应改变。最重要的,是人和社会在这样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动机、生存方式所发生的改变。到了这一条,读者不需要了解热力学定律,不需要get到之前的趣味与恶趣味,他是可以直接理解的。“在一个什么都自动完成的世界里无定是个笨蛋。”就这样可以了。这样,他就可以和无定一起上路西行。
对小说分类,不是作者的工作。分类有利于传播营销推广,现代文明社会里需要将信息扁平化便于最大限度地传播扩散,也可以帮助有类型期待的读者更快找到他们想要的内容。我非常理解它的作用。但这不是我的工作,所以,就这样吧。
何平:你曾经和我说过:“有时候觉得当代文学正变得越来越有形式感,在这种形式感里丧失掉最原初的那点生命力。”我觉得科幻文学现在就面临着你说的这种危机。
糖匪:这几年我看科幻小说比较少了。坦白说,我十多年前就对大事记、传奇类的科幻故事失去了兴趣。这样的故事,比起文字,有更适合的媒介。比如电影,动漫,甚至游戏。像菲利普·迪克、巴拉德、克拉克、西弗尔伯格,包括特德姜这样的科幻作家,他们小说核心、独特的意趣和世界观,都是无法影视化再现的。只有文字可以。不排除好的导演影视他们的作品,但这就是另一部作品了。至于文学形式化,很大原因是因为感受力的丧失。姿态变得重要起来。
何平:你应该是特别迷恋讲故事的人,讲童话一般清澈干净的故事,甚至你的几个小说都用“讲故事”做了小说叙事的核心,比如《黄色故事》《蒲蒲》,比如长篇小说《无名盛宴》。
糖匪:好故事可以抵御恶。一个世界,如果只需要中心思想或者只向往高潮,不仅可悲,而且危险。人类最早的艺术形式,无论绘画还是音乐,还有口耳相传的故事,其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小宇宙。到了文字出现的时代,诗歌和故事都是在传达一种无法言明又必须言说的内容。在我心目中,诗歌更高洁纯粹,有些难以够及。我喜欢现在这样灰扑扑地坐在路边讲故事的样子。
(原载于《花城》2018年第6期)
《无名盛宴》读后感(二):敞开内心写小说很“危险”,为何我依然奋不顾身
敞开内心写小说很“危险”,为何我依然奋不顾身
——《无名盛宴》后记
文/ 糖匪
我清楚地记得,小说《无名盛宴》这场盛宴是从哪里开始——先有了马戏团的畸零人,有了幻境,才有了幻境之外的真实城市——先有了影子,才有了物。
马戏团的故事写于2005年春天。我清楚地记得完稿那天清晨的光在瓷砖地上颤动几乎要溢出的样子,清楚记得身边狗一夜偎贴后留下的余温。保存文本之后便不作他想。我想把它结束在那里。但是影子已经成形,物就只好生成。起先是在暗处。
一年过后,我写下第二章,捡起马戏团畸零人奋力挣脱扯断的命运线头,逆流追溯,走进故事里的那座城市,在那里编织迷题。人们总以为现实生幻境,但在这场盛宴里,恰好颠倒。由幻境生出的现实,血统多少不正,来路终归不明,被人问及“出身”,一定是会心虚的。
即便要问,也不应该问作者本人。一旦定稿,白纸黑字定格在电子文档,小说便与作者无关。今后但凡有人寻上门提问,作者只需两手一摊完全撇清就好。越是在乎这小说,就越是要撇得干干净净。因为之后,小说就属于每一个阅读它的人,在永远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地被阅读者“再制”。
《无名盛宴》并不是一个可以单线去理解的故事。它由碎片构成。然而这些碎片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贴合出一个完整拼图。它们如此调皮、顽固和任性,率先成为自己并且只满足自己,它们不顾全大局,令拼图局部残缺局部堆叠,由此二维的拼图捕获到另一维度,立体起来。碎片们蓄意为之,它们大声质疑:“这世上真的有这样一个完整拼图存在吗?还是说,人们殷殷盼望的完美拼图,即世界的真相只是人工制品般的存在?”
匪,在古代,是容器。作者,其实做容器就可以了,端端正正安安静静盛放美好之物,以这样的方式隐匿其中。没有比隐匿在作品中更好的事了,召唤着物的体积、密度、实感、从它表面流动的空气、腐蚀它的时间。创造了影子和物,作者随之消失其中。这观点听着傻气十足。即便如此我仍旧坚持,并且去实践。
——你看,我说了那么多,只为了什么也不说出口。
写小说是件危险的事。仅次于信仰。
敞开从来都是危险的,意味着最大程度的暴露和放弃防范任何侵入。哪怕是博尔赫斯那样纯智性书写,或者穆齐尔式哲学写作,都是将作者内心世界最隐秘幽暗处曝露于日光之下,面对可能而来的暴风骤雨的奚落又或是冷遇。你永远不知道这两者哪个更糟。
但是很多作者还是会选择敞开,即便其中一部分人出于下意识,我不是在鼓励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式的阅读。恰恰是把作者当作精神病人来剖析的阅读方式才令写作变得更加危险。
那为什么作者仍然会选择从事这一危险的行为?也许是因为敞开不仅意味着任人伤害,也意味着爱和被爱的可能。
我想令我笔下的人物得到幸福,想令这个世界上和他们一样笨拙的人也拥有被爱的可能。
那些人,如同波函数所描述的粒子:他们不存在于牛顿物理框架下的宏观世界。不像苹果、行星及一切能被直接感受到宏观事物。他们只存在于量子物理世界,他们没有固定位置、速度或者能量,只有概率。
那些人,不仅不可见,而且不存在,又像薛定谔的那只猫,活着同时死去。
在量子物理里,波函数在被测量后,就会获得真实、具体性质,从概率波变成粒子。因着测量行为,许多潜在的结果瞬间减少到单个观测结果。海森堡称其为粒子波函数的“坍缩”。
对于那些人,是否也存在着一种“坍缩”,使他们被确定,被辨认,被当作鲜活生命温柔以待。至少在文学的世界里,这并非不可能。书写他们就是这种坍缩。阅读他们也是。当目光落到他们身上,他们诸多可能的命运就展露出其中一种。
啪,轻轻一声,比树枝在烈火里爆裂的声音更轻微,他们就确确实实存在了。这场盛宴切切实实属于他们,欢庆他们的新生。
《无名盛宴》读后感(三):看画:一场90年代的湿热午觉
说实话书还没细看,先被里面的插画吸引了。
像小时候美术书上的黑白版画,以前欣赏不了,现在却突然懂了妙处。
硬要形容的话,就像一场90年代的午觉,空气湿热,芭蕉、蕨类和向日葵野蛮疯长,你歪在亚热带老房子的藤椅上,电扇页慢慢旋转,做了一个关于遥远世界的梦。
糖匪的小说,大抵给我这样的感觉。
《无名盛宴》读后感(四):漂浮的读者
如何用文字带来新的体验,不仅仅需要作家大量的文字积累,更是一种天赋和直觉。
比如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雅塔把不善言辞的针线女孩带到一群娇生惯养的大小姐面前炫耀时,对针线女孩的“通感”的描写。
作者的原话如下:
“雅塔叫她的名字。
她听到带着倒钩的声音。无数小小的倒钩扎在肉里。她好像她嘴里的一块肉。”
正是因为这样的表达手法,《盛宴》不能被单纯分类为“奇幻或者科幻”作品,说它是难以被定义的异色小说也许更准确。
人类是如何用语言这么匮乏的方式表达“异”的概念?
人类如何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中讲述诡谲和陌生?
最难的是:如何用你的眼睛看我的世界?
没人能确定这样的自我表达会不会招致误解,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如果把误解本身作为完善表达的一种方式,是否才有可能接触到表达的本质?
毕竟只有同时看到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我们才能知道完整的硬币是什么样子的。
作者完全不想讨好任何读者,他尽力把我掷入虚空,然后任由我坠落,若是感觉自己竭力抓住了什么,那一定是虚无。
更糟糕的是,我明明很认真的读了,仍旧有一种无力感。那是无法到达作者的精神世界的无力感,我怀疑他抛下了读者,只是选择用一种“大部分人都熟悉的语言”来描述“说了你也不懂”的世界。
这么说也许有些偏激,我不妨假设一下,这里的文字如果是由读者本人念出来,在除却语言之外的表情,语调,停顿之类的辅助之下,才会变得容易理解。
故事的开篇是一场悲剧,也是整本书最重要的表达:人和神一样无助,都是这场盛宴中的宾客。
从来到这样的世界中开始,就被无声的力量左右着,在感情和理性之间摇摆不定,平凡中到处是神迹。看似没有逻辑,却在一环扣一环的内容中完整勾勒出这个多层宇宙的全貌。
从这些故事的设定上来看,《盛宴》时不时会呈现出《鼠疫》的既视感。在封闭的时间和空间中,有个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第三者”,它掌控一切,带给人绝望,却无法在任何地方寻找到它的影子。
也许糖匪的视角正是如此。
我们常常在小说中看到对“弱者”的描述,千篇一律甚至形成某种固有成见,即穷人永远与不幸连接在一起,弱小代表着随波逐流和得过且过。曾几何时,小说主体的人成为了单向度的存在,被解剖,被概括,被标签化。批判的眼光慢慢消失了,性格约等于标签,角色约等于人设,读者用高高在上的眼光剖析人群,这样的写作方式随处可见,也许因为这样更容易。
《无名盛宴》中的弱小者打破了这个局限,我们不需要怜悯弱者,他们强大而不显露,与命运搏斗而不自怨自艾。
每个人都在进行一场独一无二的时间旅行,我们终将知道自己的结局。但是总有那么些人早早预见了一切,在自己的剧本上平白添了那么几行字,并称其为宿命。
在白赛仲路章的开篇,作者写道:
满月那天他被杀死在自己的床上。
对此,她并没有太吃惊,还能企盼什么离奇的结局呢?
她的故事不过如此。不能再好,不能再坏。
在讲述死亡时,用的是过去式。
从死者的角度回溯,故事的全貌逐一展现,环环相扣的爱与恨,因与果……而却对她的死亡一笔带过,似是不值一提。
生是人类的本能,可意外的是这里的每个人都如此坦然的面对死亡,仿佛那是从一间屋子里信步走出来,抬眼看天时的心境。
我坚信人类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感同身受。伤口不在自己身上,是不会知道痛的。弱者的死亡也是如此,他们超然的态度,冷漠到让人难以产生共情。
有人说过,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值得被讲述。
每个人都值得当主角,却很少有观众。
在离开舞台的阴暗处,有一双眼睛在观察万物,用无人能懂的语言记录一切。
这本书是给每一个无名之人的盛宴,这里有你的故事,也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