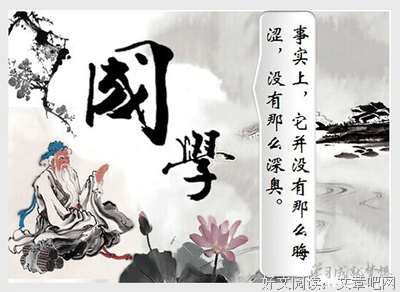《清代宫廷社会史》经典读后感有感
《清代宫廷社会史》是一本由[美]罗友枝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元,页数:47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清代宫廷社会史》精选点评:
●研三读过,感觉一般。
●没看完,不是很感兴趣。从资料来看是很丰富,不过似乎二手用的很多?满语资料也没用多少。我倒不是史料原教旨主义者。想通过对清代宫廷社会的研究展现清初统治者多元的文化并以此统治境内不同民族。我还是比较同情不过火的新清史的...
●導論目標定的很大,但後面有些接不上。好像還是以制度的描述為主。焦點似乎也無法集中。
●翻译文字倒是通顺,但最不能忍受的是页下注引用的外文文献(没有汉文版)居然也翻译成了中文,然后又在最后列了一个中外文合体的参考文献,而且一直没太明白它的排列顺序导致找一个注释的英文书名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更何况一些注释翻译还弄错了。关于书的内容,满族因素肯定是影响了清的统治的,书中强调这一点,也觉得无可厚非,哪怕是片面深刻,对于我们认识的推进也是无疑的
●本书最重要的是这句话:清朝的统治范式不是民族国家,统治的目标不是构建一种民族认同,而是允许多元文化在一个松散的人格化帝国之内共存。近代民族性的意义并不存在,同时国家也不想去创造这种民族性。
●17年 微信阅读补记
●可以反思《天朝沙场》写的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虽然很多人猛批“新清史”,但并不影响此书的资料性和说服力。此书主要围绕清朝统治上层进行了精湛研究,基本观点在于:清朝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其针对帝国之内亚边疆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采取富有弹性的不同文化政策的能力(第9页),清朝之所以成功,原因正在于它不是汉族王朝(第372页)。我一直觉得清朝确实是最富于魄力的一个王朝,统治手法相当娴熟,奠定了近代国家的基本雏形,而我们可从清朝寻找到一些病源和经验。历史学是要基于现在的关怀去认真研究问题,而不是整天袖手叫骂。
●我要再读两遍才得…
●勒色。
《清代宫廷社会史》读后感(一):补记
2017年记
《清代宫廷社会史》读后感(二):[转]一本研究“满洲共同体”的好书——评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
近些年来,美国史学界对清代历史的研究,出现了一种新趋势,这股学术历史被冠以“新清史”学派。其中,柯娇燕的《半透明的镜子:清代帝制意识形态下的历史与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欧立德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the manchus way :the eigt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路康乐的《满与汉:1861-1928晚清和早期共和国族群关系和政治权利》(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罗友枝的《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被认为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各自的著作亦是新清史的代表作,并被称为研究满族的“四书”。
总的来看,当国内学者陷入清朝政治的泥淖之时,比如国内学者多关注满洲共同体的形成时间、乃至如何予以界定;而国外学者如罗友枝等已对此进一步作了深入研究,对满洲共同体的形成,以及在将近三百年统治历程中如何保持自身的认同,维持自身统治地位,作了深入思考。
--------------------------------------------------------------------------------
[1] 房德邻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第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http://blog.163.com/fengjianyong_2008/blog/static/30984003201010735322580/
《清代宫廷社会史》读后感(三):转:新清史四书及标志性著作
近年来,美国清史学界一些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专著相继出版,议题都涉及到清朝统治的满洲因素,势头之强劲令人惊诧,因为作为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特定领域,对于与满族史相关的清史研究,中国学界几十年中都鲜见如此集中地、大量地出版过如此重头的研究成果。其中四本著作后来被学界一些人誉为“新四书”。以下介绍的便是“新四书”和其他几本重量级的代表著作。——荐书堂
“新清史”四书
《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
罗友枝(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最后的皇族》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专著。通过艰苦的档案搜集工作,罗友枝发掘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资料,这使她的著作成为研究清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满族宫廷的公开和非公开礼仪的珍贵手册。罗友枝的专著是一个里程碑,代表了研究中国的新历史学的开端。此书于2009年出版过简体中文版(《清代宫廷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半透明的镜子:清代帝制意识形态下的历史与认同》
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半透明的镜子》洞见深刻,标志着十年来清史研究的巅峰。柯娇燕与美国历史学家欧立德、濮德培等人的出色合作,使柯娇燕将我们对于清帝国早期现代民族身份之形成的理解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既包涵复杂性,又有理论清晰度。目前还没有中文版。
《满与汉:1861-1928晚清和早期共和国族群关系和政治权利》
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路康乐在书中分析了满族作为一个世袭军事特权阶层(“旗人”)向一个独立的族群的转变,也详细描述了清朝与汉族改革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这一互动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中达到了顶峰。《满与汉》是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将改变中国历史学者研究清亡原因的方式。同样,该研究也澄清了族群学者关于满族作为职业军事特权阶层的起源问题,分析了满汉关系的变化,以及满族从边疆“蛮族”到统治者,再到被统治者的历史发展。此书于2010年出版过简体中文版(《满与汉 : 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满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华帝国晚期的族群认同》
欧立德(Mark C. Elliott)(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满洲之道》是欧立德教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多年修改打磨,才修订成书的,自2001年问世以来,已经引起西方中国研究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界有多篇书评,大加推崇。目前还没有中文版。
其他重要的“新清史”著作
《孤军:满洲三代家族与清世界的终结》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虚静帝国:清代中国的佛教艺术和政治权威》白瑞霞(Patricia Berger)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中国西征:清朝对中亚的征服》濮德培(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马背上的朝廷》张勉治(Michael G. Chang)(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来源:甲骨文 编辑:荐书堂)
《清代宫廷社会史》读后感(四):【转】黄丽君:皇帝的包衣奴才——罗友枝《最后的皇族》中未呈现的清宫廷
罗友枝以“宫廷”为选题探讨清王朝统治的内亚性,本身就别具慧眼。陶博(Preston Torbert)在The Ch’ing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A Study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Principal Functions, 1662-1796.(《康雍乾内务府考》,1977)已指出,管理清代宫廷的主要机构——内务府是八旗制度与传统中国官僚体制的结合,也是融合满洲色彩并折衷汉制的政治机构。但在“兼容满汉”之外,罗友枝透过物质文化、社会结构和宫廷礼仪的考察,进一步告诉读者清代宫廷文化的多元内亚性,包括了满、蒙、藏、伊斯兰文化等面向。
清代宫廷制度的重要特色,在于内务府这个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宫廷管理机构。内务府的主要人员是皇帝直辖的上三旗包衣(booi),他们在身份上属于皇帝的家仆。换言之,清朝皇帝偏好任用包衣家人来为其管理家务,与传统王朝喜好任使太监的作法不同,也是清代不曾发生宦官乱权的主要原因。但包衣若仅在内廷为天子执家务,很难在清朝的政治制度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因此更为重要的是,清代的几个重要税差皆属内务府包衣专缺。乾隆皇帝即言:“各省盐政、织造、关差,皆系内府世仆。”在清代国课收入之中,盐课和关税分别是第二、三大宗,这些税收均由皇属包衣经手,得见内务府在清代财政功能上扮演重要角色。
罗友枝内务府包衣出任重要税差的代表性例子,莫过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从史景迁的研究可知,曹寅之母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乳母,因此曹寅与皇帝虽然名义上是主仆,实际上更像自幼一起长大的兄弟,二者亲密逾恒的家人关系,这也是曹寅可以久任两淮盐政、江宁织造的原因。康熙皇帝曾六度南巡,曹寅四次接驾。然而,接待皇帝的高昂成本被转嫁到盐政、织造衙门,造成财务亏空。康熙皇帝死后,雍正皇帝与曹寅的私人关系不如其父,在亏帑无法弥补的情况下,曹家被查抄,迅速走上衰颓的命运,这显示出内务府包衣的仕途与家族起伏受到皇权影响的戏剧性。《红楼梦》这部小说描述贾府从荣显到落败的过程,很大程度折射出曹雪芹家族的自身经历,也因此曹雪芹才能用一种极为透彻的笔调描写贾家“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起伏与苍凉。
内务府包衣受到皇权影响而仕途起落的例子不止于曹寅,嘉道朝显宦英和的落败亦是一例。英和自幼聪颖,科场顺利,乾隆五十八年考取进士时年仅二十三岁。和珅曾想把女儿嫁给他,英和的父亲德保却拒绝了这桩婚事,因而遭受和珅忌恨,受谤甚多。但祸福相倚的是,嘉庆皇帝亲政之后,英和竟因拒婚而得到皇帝的重用,仕途自此飞黄腾达,爬升为朝中的一品大臣。然而,作为包衣英和必须为家主当差,即便在外朝任职,也必须兼任内廷差使,负责为皇家监修陵寝。应道光皇帝节俭的作风,英和“裁省”物料,不料道光八年陵寝发生漏水事件,皇帝大怒之下,英和被夺官发往黑龙江当苦差,二子奎耀、奎照也连同罢职遣戍。英和家族在清代中期是“四世翰林”,通过科举得到外朝任职的机会,其仕途荣显在内务府包衣群体中可谓异数。即便如此,皇帝意志对家族命运的影响,使其跌宕起伏亦比外朝官僚更具戏剧性,呈现出内务府包衣的独特身份特色。
皇帝两个公私分明的钱口袋
上三旗包衣既然常任重要税差,内务府在清代财政体制中亦显得突出与关键。但差异在于:内务府的收入属于皇帝私人所有,户部管理的则是国家财产。内务府的经费来源大概有几种:关税、庄园、人参和毛皮的专卖事业、官员的罚金(议罪银)、官员被抄家之后的人丁财产、贡品、宫中变价出售的物品、经营当铺、发商生息等。据赖惠敏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清朝皇帝如何精明地管理他们的家产。例如,开设当铺就是皇帝经营资本的一种手段,但由于官营当铺利息不能太高,以致于收益不多,经营困难。相较之下,皇帝更喜欢将内帑银两借给商人作为经营资本,即所谓“发商生息”。清代资本雄厚的商人莫过于盐商,内务府包衣常任盐政,通过出任此差,包衣可替皇帝与商人搭建起联络的管道,也可以代替内廷监督商人的经营资本与还款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满洲统治者虽然有权运用内务府与户部两个口袋,却始终公私分明,从未混淆,显示了清朝的行政理性原则。甚至在大部分的时候,皇帝都是以内廷经费支持国家用度。乾隆四十六年的上谕就提到:“以内帑论,乾隆初年内务府尚有奏拨部银备用之事。今则裁减浮费,厘剔积弊,不但毋须奏拨,且每岁将内务府库银拨归户部者动以百万计。”到道光、咸丰初年,清廷仍可维持“户部用部库之钱粮,内务府动内府之进款。时有特沛恩旨,颁发内帑,以为赈济、河工、军饷之需,从无内务府向户部拨借银两之事”的规模。直至太平天国乱起,内务府的财政受到严重的冲击与重创,自此改由户部支持内廷。但即便晚清皇室收入不足,统治者对于公私两个口袋的财用仍持谨慎心态,未尝改变,兴修颐和园即是一例。
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的论述影响,后人多认为清廷为了筹办慈禧六旬大寿,动用海军经费整修颐和园,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但光绪十四年宣布兴修园工的上谕中,具体宣布“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亦属无伤国计”的筹款原则,并为负责园工的醇亲王与李鸿章所遵守。与过去我们对于慈禧太后穷奢极欲的印象极为不同。
替皇帝招待西洋人
冯明珠、陈国栋对于礼仪之争中几位包衣角色的讨论,即可具体说明皇帝如何利用内务府管理西洋人。明末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在利玛窦的主张下,尊重中国人祭祖、祭天、祭孔等传统习俗。但康熙三十二年时,福建宗座代牧颜珰打破利玛窦规矩,教廷亦随之在康熙四十四年派多罗使者来华,宣布禁止中国礼仪。多罗入华之后,皇帝派遣内务府包衣一路照料,之所以如此,与包衣身为皇帝宠臣,熟悉家主的想法,可以承宣旨意而不易出错有关。此外,康熙四十五、六年皇帝亦曾两度派遣传教士回罗马,欲与教皇沟通中国礼仪问题。在多年得不到响应的情况下,康熙皇帝发出“红票”,由商人、传教士带回海上,广为传播,终于促使教廷遣回传教士。有趣的是,“红票”亦以内务府官员署名发出,得见包衣在康熙朝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关键地位。
除了康熙朝的礼仪之争外,乾隆五十八年马嘎尔尼来华,乾隆皇帝也同样派遣总管内务府大臣金简、伊龄阿接待使团,长芦盐政征瑞则从使团自天津上岸之后,负责护送英国人一路到京。乾隆皇帝非常在意英国人觐见时的礼仪,曾私下交代征瑞“则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觐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虽尔国俗俱用布扎缚不能跪拜,但尔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亦属甚便”。乾隆在征瑞面前流露出最真实的想法,显示出二者亲密的主仆关系,也是皇帝信任内务府包衣负责这项差事的原因。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再度遣使阿美士德来华,中英双方再度为了礼仪问题僵持不下。周旋期间,内务府包衣苏楞额、广惠等也被皇帝寄予教导英人礼仪的期待。直至晚清,内务府包衣因经常出任粤海关监督,与西洋人有丰富的往来经验,亦是朝廷办理洋务之初必须倚重的对象。《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即载,内务府出身的恒祺“当庚申与英法议约,佐恭邸最出力。危急时,欲以身殉,始得挽回颓势。惜其不久即逝,未得大用”。在康熙朝礼仪之争以降,皇帝如何利用内务府来管理西洋人事务的研究是一个有趣且重要的课题,可惜目前尚未得到太多的研究关注,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皇家的艺术品“代购”
在经济角色之外,内务府包衣外任重要税差的另一较少被提及的功能,即与宫廷的工艺制作与收藏相关。清帝喜欢的内廷式样的工艺品多交养心殿造办处成造,但受限于原料和工匠技术,仍必须将部分作品交付地方制作。陈国栋很早就注意到,内务府包衣外任税差的地点多为水路交通要道,无论是购买物料或代寻工匠,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由于包衣熟悉皇帝家主的艺术品味,通过他们来办贡或传办内廷对象,不容易失准出错,亦有节省宫中开支的优点。最有趣的例子,莫过于乾隆三十年皇帝将《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交由粤海关承办代觅商人发往法国制为铜版画。《得胜图》的制作时间长达十一年,经手的五位粤海关监督有四人均为造办处出身。唯一不曾在内廷行走的方体浴,亦被要求来京陛见后到造办处行走实习,方得回任粤海关。由此得见承办这些特定差使,亦是皇帝选任税差的重要考虑。
简评罗友枝《最后的皇族》
罗友枝《最后的皇族》探讨的清宫廷与笔者上述的宫廷制度,主题虽不完全相同,但仍有诸多面向叠合之处。本书的行文剪裁十分精彩生动,可惜与上述的讨论相较,仍属静态的宫廷制度史,较少探讨宫廷多元文化与制度具体运作的情况。举例而言,本书第五章以“宫廷奴仆”为主题,逐一介绍太监、包衣、辛者库、旗奴(保母、奶妈)、谙达、艺术家和工匠等人的身份、职称与作用,姑且不论作者的分类是否正确(这里所指的旗奴不少是包衣旗人),书中的讨论偏重于“介绍”,较少深谈这些人物在帝国秩序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如何与皇帝、制度、社会之间互动,颇有不足之处。然而,这点遗憾实不能苛责作者,毕竟这本书出版距今将近二十年前,多少受到时空的研究局限。现在我们若可以谈到更多宫廷制度的动态趋势,亦是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才能有更进一步的成果。
罗友枝《最后的皇族》相较之下,本书最容易受人批评的缺失,恐怕是对二手研究与汉文档案的大量依赖。作者想要讨论清宫廷的内亚性,却缺乏运用非汉文字史料的能力,无疑形成自我的悖论。罗友枝的学术见解建立在诸多二手研究之上,是她与何炳棣的论战时被着力批评之处,本书亦有类似的情况。以第一、二章为例,学人的研究成果比重高达七成以上,史料和档案的比例甚低。若再仔细检视书中运用的材料,则以《会典》、《玉牒》与《内务府奏案》(奏案是内务府档案中以汉文为主的材料)为最大宗,论证多引汉文史料,不见作者对于满文档案的辩证与讨论。但诚如作者的主张,满洲统治者身为非汉政权,存留大量且具有价值的非汉文字史料,但本书探讨清朝的多元宫廷文化时,却不以此为据,这样的治史方法具有多少的说服力?恐怕不无疑义。
虽是如此,《最后的皇族》仍是一本引领我们认识宫廷制度的好书。其写作浅白,没有太多困难的制度名词,可以同时作为通俗读物与学术作品,也显示出作者研究、写作的功力。透过阅读本书,有助于一般读者廓清清代制度的迷障,尤其是近年来盛行的清宫剧,无论在剧情或场景、对白等,多以汉人为思维逻辑来建构,与真实的清代氛围颇远。《最后的皇族》这样兼具通俗与学术面向的著作,提醒我们清宫文化的不同面向,是将学界研究介绍给普罗大众的最好的一扇窗口,可以让我们更正确地理解清代宫廷的制度,以及生活在里面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