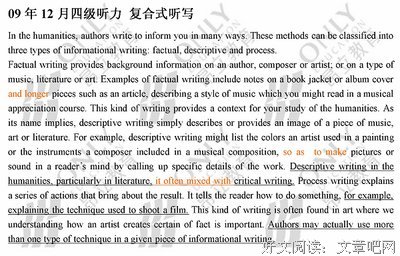聽聽那冷雨读后感锦集
《聽聽那冷雨》是一本由余光中著作,九歌出版的平裝图书,本书定价:230元,页数:25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聽聽那冷雨》精选点评:
●高中时读听听那冷雨,觉得有着除了古诗词外的中文美。2010年搬家时,却清理了好多书,其中就有这本的大陆版。那一年,丢弃了很多东西,也丢弃了一部分的自己。我忽然有点想念我的粉红色旗袍。
●在成都灰蒙蒙的雨天读到这篇美到极致的散文 ,安东尼奥尼黑白片的味道 、台北 、大陆 ,前尘隔海 。古屋不再。
●古屋不在,可又哪仅仅是因“前尘隔海”!
●抄写过一遍的文章
●小楼一夜听春雨!
●那个冬天,面对结冰的北海,朗诵听听那冷雨,最幸福的时光
●这个应该是再版吧~记得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嫌我写的东西境界太小,就把这本书推荐给我,说:“看看相同的东西,人家是怎样写的吧。”
●昨儿写作文的时候又读了两遍 余老能把乡愁融进牧童遥指的杏花雨里 浥渭城轻尘的朝雨里
●满满的学生时代记忆。。。。补标记
●後面的詩論、樂評,若不是相關愛好者,可能不知所云?
《聽聽那冷雨》读后感(一):前尘隔海,冷雨纷纷。
突然看到余光中先生早上在高雄逝世的消息,心里一阵错愕。 抬眼窗外,冷雨纷纷,在这曾令诗人魂牵梦绕的土地上的我,与千年前曾浸染过秦砖汉瓦的冷雨相遇,也是一种巧合吧。 在哪交错或零散的五颜六色的伞的另一端,便是那长长的厦门街尽头雨中的那暗色的灯吧。 前尘隔海,古屋不在。 先生走好,愿天堂也有乡愁。
《聽聽那冷雨》读后感(二):再读雨
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篇写雨的文章,雨有南北之分就如人的性格一样,春天南方的雨总是敲无声息的来临,而又在不知不觉中匿去。细细滑落天际的雨带给人许许多多的相思和缠绵。北方的雨我未曾亲眼看过,有人赞美它的酣畅淋漓,赞美它的粗犷。而我则喜欢在细雨中漫步的感觉,用手用心感受着在我手中悄悄滑落的细雨。没有太多的牵挂没有太多的忧伤,感受古人的那一种:“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呼吸着略微带有泥土清香的空气,似乎是和自然融为一体,感觉不到雨的声息,就像王维所说的:“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不过这种机会不是很多,因为喧哗的街市,来来往往的人群,或是干脆越下越大的雨不经意地把我拉回了现实的世界。更多的时候,只是呆在书桌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雨声。细细的小雨,打在窗子上,虽然那声音微乎其微,但是可以用心去感受它,不仅仅是风,雨也是大自然的呼吸。
俞平伯说:“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中粘地絮”。雨寄伤感抒寂寞,有喜有悲。一喜一悲之间,千年已过,斯人已逝,而雨还是雨,依然还是淅淅历历的敲打着世间的一切。也依然会有更多的人,把情感撒在蒙蒙细雨中。蓦然回首间,也许王维,也许杜甫,也许柳永,也许朱自清,他们眼中的雨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心中的雨落在后人的心里。其实,雨是一个不可错过的题材,即使是最烂的诗人,见到雨时,也会“才思如泉”。因为美的并不是诗,而是那片雨!^_^
《聽聽那冷雨》读后感(三):读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
说起余光中 就不得不想起他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初读这首诗歌的时候,突然让我想起戴望舒的《雨巷》,他们二者并无必然的联系,只是那种读诗的心情,读起来都给我一种莫名的喜悦。我还是比较相信自己的感觉的。简简单单的几行字,却诉尽了心中的千言万语。喜欢他的作品就是从《乡愁》开始,爱读他的诗歌,也喜欢他所写下的散文。
在他的眼里,诗是情人而散文是妻子,他更喜欢花长长的时间去推敲一篇短小而精悍的散文,因为他爱散文,就像爱自己的妻子一样。他曾说过:“我认为散文可以提升到更崇高,更多元,更强烈的境地,在风格上不妨坚实如油画,遒劲如木刻,宏伟如建筑!”这是他心目中真真正正的散文。《听听那冷雨》是我很喜欢的一篇文章,我个人喜雨,所以对它可就“情有独钟”了,雨是什么时候都会有的,古往今来,写雨的,赞雨的,伤雨的,多如牛毛,可以回忆,杜甫笔下身价千倍的“春雨贵如油”,陆游那“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伤国忧心,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再话巴山夜雨时”的离别之思……余光中是这么写的:“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中国也好变来变去,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罢,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存在。”况且雨本身就是一个象形的文字,从字面就可以看出“落入水中皆不见”,那意象,非英文“Rain”之所能比,写雨抒意,抒的是非古人之情,非常人之意。我想,这也许就是余光中先生的境界吧!
《聽聽那冷雨》读后感(四):风雨中飘摇的“中国感觉”
——读余光中《听听那冷雨》
一、中国存在于在哪里?在文化感觉中
余光中谈雨,其实是谈人,谈人安身立命的心灵依傍之所。
余光中在《听听那冷雨》中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他问今天一个中国人的中国在哪里?当“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遥指已不再,剑门细雨渭城轻尘也都已不再。然则他日思夜梦的那片土地,究竟在哪里呢?。”余光中真是问了一个好问题,醍醐灌顶。
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那里面是中国吗?那里面当然还是中国永远是中国,他只是现象中国。犹如在报纸的头条标题里、香港的谣言、傅聪的黑键白键、马思聪的跳弓拨弦里。照此类推,还有族性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符号中国,如方块字,亦如故宫博物院的壁头和玻璃柜内,又如京戏的锣鼓声中,还如太白和东坡的韵里?还有“二十五年,一切都断了”的政治中国。
这些都是中国,却不是余光中探问的“日思夜想”的中国,更不是他要的依傍之所。
余光中所日思夜梦中磕求,所赖以依傍的中国,是从“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从故乡环境和精神成人而来的文化感觉下的中国。这感觉切入体肤、渗入体温,构成个人精神灵魂情感意志,化作血肉与灵魂自己的那一个来自中国的感觉。
简言之,余光中“日思夜想”的中国土地,是随一个人的自然生长和精神生长而形成、而内化了的基质性的“中国感觉”。余光中要寻找存在于自己体感中的这个中国,是个体性、私人化的“中国感觉”下的“感觉中国”。每个人的成长,都从感觉自己身边的事物开始,而后深入生存现象背后地从感觉古典、感觉文化开始,最终到直觉、直观神州大地,形成整体的观照。所以,“中国”乃感觉中的中国。
由此,日积月累,形成了自小至今的自己,也成为一个人在大地上行走时,去看中国、看世界的“中国感觉”。一个中国人将依傍这个关于中国的“感觉”、这个形而上的“中国感觉”,去形成原则,去指导行动,去用来评判效果。
二、纤弱的中国体相与意象,如今也已残破不堪
余光中的“中国”从肌肤中诞生,来自个体的听:“听听,那冷雨。”来自特别的看:“看看,那冷雨。”自口感鼻感:“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余光中的中国来自于感觉的集合,抵达直观感觉、审美感觉、宗教感觉之上。他整体的“中国”统一于感觉化意象:“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余光中构建日思夜梦的中国土地,其所依凭的是“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感觉”;其所熠熠生彩的质感,则是来自文化养成的记忆和文化个体、文化经历中滋养下的生命意象。
总之,余光中的“中国”落脚在“中国感觉”上。不过,余光中的中国感觉下的中国意象与体相太纤弱了。那片“日思夜梦”中的土地, 他将其物化为中华独有的“雨”意象和传统文化中纤弱的“女性”体相中:“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
“听听,那冷雨。”前一个“听”是主动词,是现场的动作;后一个“听”是被动词、私人感觉的对象,是历史与文化选择下感觉的结果。因为耳朵总是往想听的地方听,舒服的地方听;听是个人历史文化经历所选择、所塑造的结果。同样,看、嗅、闻、舔都是文化的器官和结果。——纤弱意象,是日暮途穷之文化感觉的必然。反之,美国的山川自然则不然,不服从于这个感觉:
“第三次去美国,在高高的丹佛他山居住了两年。美国的西部,多山多沙漠,千里干旱,天,蓝似安格罗萨克逊人的眼睛,地,红如印第安人的肌肤,云,却是罕见的白鸟,落基山簇簇耀目的雪峰上,很少飘云牵雾。一来高,二来干,三来森林线以上,杉柏也止步,中国诗词里‘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的意趣,是落基山上难睹的景象”。
美国文化规定了美国的山川河流,用中国感觉看不到美国。
所以,余光中到了美国,同样是天地山水雨雪,但他看不到,因为他的中国感觉失效了,找不到大自然中的“荡胸生层云”或是“商略黄昏雨”中国韵味、中国意趣,从而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中国感觉。他便无根,无所依傍。于是,他“晕”美国的丹佛他山。犹如韩少功《马桥词典》里进城的乡下老汉,站在城市大街上“晕街”一般。
一个人的生长环境和文化,决定了他的感觉框架。不适合这个框架的,他就失去了依傍,他就不能与环境一体、就会生活方式紊乱、就失去了判断力和控制力,就迷失了自我,就丧失了完整性。其实,余光中面对的何止是丹佛他山,他面对的是整个分裂的世界;尤其是,何止是余光中已有的感觉不知道如何收拾破碎的世界,整个中国人都在世界面前需要重新构建自己的感觉。
还有,可以这样认为余光中《听听那冷雨》中的作为:他是不得不向残剩的文化中国意象回溯,就是要重新弥补残破的中国感觉,应对分裂的世界,重新找到或弥补自我的残破个体。
三、权力话语是变迁的,个人感觉是传承的
自然的人化,人化的自然。中国山水已经被古代传统文人意象化了,后人接受中国大地上的山山水水,实际上接收的是中国文人化的山水。犹如余光中下文说的“云萦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中国的山水、风景、景观,由来都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那已经不是自然本身的样貌了。
这感觉,是源自苏东坡。所谓“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所谓“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余光中这一句说的特别高妙:“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
《听听那冷雨》是有偏好和立场的。余光中的中国是文人中国,他不承认政治中国,正如聂华苓小说所宣布的:既不要毛泽东(的中国),也不要蒋介石(的中国)。余光中们的中国是传统文化中国,具体落实到自己中国文化感觉的中国;当然,也不是大陆左派的“苦难中国”,更不是今日世界给予的“世界工厂的中国。中国在哪里?在方块字,更在方块字而来的、私人化了的”中国感觉“中。
中国感觉下的中国与权力话语下的中国,二者是不一样的。
你赵匡胤可以有你的霸王中国,你美国人可以有你的“世界工厂中国”,而我则取我一瓢饮,我的目遇耳得,从而我可以有我的山水中国。你垄断你的,我分有我的;你统霸天下,我独享感觉。权力话语是变动不居的,有时效的;山水中国是血浓于水的,是血脉传承的。余光中具有的“中国感觉”是独有,所获得的天地万物之感觉的和——印象——也是独享的。
这种“中国感觉”在历史上能够应对王权,但今天是否能应对更阔大得世界呢?这犹如余光中飘洋过海来到美国,他比郑和走的远得多。他在美国西部丹佛他山,他的中国感觉发现看不清楚丹佛他山。接下来,他“看”到的丹佛他山当然地也并不是美国人看到的西部。犹如中国风景源于中国感觉,美国西部风光则笼罩在美国精神下。没有美国精神框架的视线,是看不清西部的山川草原的。
所以,传统的余光中们是要面对王权,现代的余光中们则是要回应世界。如果说中国感觉能够较好地应对了王权,那么今天能够回应世界吗?
四、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文化灵魂,其格调是迥异的
在大迁徙的19世纪,美国移民为了躲避欧洲的腐朽来到新大陆时,发现东部已不再是梦想,纷纷迁徙西部。充满希望的人们在广阔肥沃的处女地上施展梦想。
“在美国作家们的心目中,西部是一块净土,是纯自然之子,西部的农业社会呈现出朴实,美德和知足的田园,自然让人联想到‘伊甸园’。”美国西部,已经构成象征性的神话,“充满挑战和奇迹的乌托邦。不仅连接着文明和野蛮,也连接着人类和自然。”(邓珊:美国文学西部意识对美国民族精神形成的影响)
而中国山水呢?铺染的人文气太浓、摩挲得太糜烂、搁置得太腐朽、氤氲的气息太颓废,萧索的隐士和吟哦的文人,已经没有开创新世界的新人在里边。所以余光中凭借来观照山川日月的“中国感觉”,当然看不清丹佛他山。余光中的山水随“中国感觉”而比兴来的意象,只有与主流对待的另类,与庙堂对待的江湖,与建功立业对待的隐逸人生,与锱铢必较的交换市场相对待的空寂文化寓意山水。
所以,余光中听丹佛他山的雨,便不会自然亲切串联到惠特曼的雨感觉。在惠特曼的美国感觉中:“暴风雨的壮丽乐曲,那么恣肆奔腾、呼啸着越过大草原的强风,森林树冠的嗡嗡震响——是高山的萧笛,人一般的阴影——是你们管弦乐队的潜形,你们,机警地手执乐器的幽灵的小夜曲,将一切民族的语言与大自然的天籁混合在一起;你们好比伟大作曲家留下的和弦——你们是合唱,你们这些无形的、自由的宗教舞曲——你们来自东方,你们这些河流的低调,奔瀑的轰鸣,你们来自远方的铁骑纵横中的枪响,连同兵营中各种军号的回应,这一切骚动地集合着,充塞着深沉的午夜,压迫我这无力的弱者,当我进入孤寂的卧室时,你们啊,怎么把我抓住了?”(惠特曼《暴风雨的壮丽乐曲》)。
同样,当丹佛他山的美国人来台湾溪头诸峰过夜,也不会获得余光中的中国感觉:“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
美国人是美国意念、想象和感觉上的美国人。美国人在山野中一夜暴风雨里,不会产生佛老“仙人一样谁去”的感觉。他们日思夜梦中,反而“看到了新鲜的不吝施与的密苏里的巨流,看到了伟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看到了在平原上吃草的野牛群,看到了多毛的,胸腹广阔的牡牛,看到了大地和岩石,鉴赏了五月的花朵,见星星、雨、雪而感到惊异, 研究过反舌鸟的歌喉和山鹰的飞翔,听见过天晓时在水杉中隐居的无比的鸫鸟的歌。它寂寞地在西方歌唱着,我也歌唱着一个新的世界。”(惠特曼《草叶集》)
这与余光中隐喻在“中国风景”中雨打风吹,或清风明月的意象,趣味和意志是迥异的。
“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再笼上一层凄迷了”
中国的雨,从不无所依傍倾泻下,总是要下在梧桐或者荷叶上。就像朱自清的月色,一定要洒落在池塘荷叶荷花上,一定要流淌出南朝的民歌声。这是中国雨的风姿,也是它的格调。中国的雨不会去和狂风相绞杀、不会引来残忍的东西,它总是那么的诗情画意。就犹如中国画中的秋天,决不是光秃秃的淡蓝天空,它总是和大地上的一垄垄麦子,天空中谈谈的白云、单飞的叫雁,还有庭院里的黄枇杷树、树下一张木桌和桌上的壶浆,这些物件一起组合拼成一幅秋景图。中国的雨是丝雨,中国的风是片风,雨丝风片,它们总是有形有感有画面、诉诸感官,带有情愫的。即或是人的一生,也要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虞美人•听雨》)
如果像余光中那样比拟雨为人的灵魂,那么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文化灵魂,其格调是迥异的。
五、一个纤弱文人,退步于五四
“……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鼻音与喉音。或是在江南的泽国水乡,一大筐绿油油的桑叶被噬于千百头蚕,细细琐琐屑屑,口器与口器咀咀嚼嚼。”余光中的雨声是比拟得这么女性,这么朝向依偎母体的安稳企盼,这么立于农田桑麻的闲静神情,这么草长莺飞、小桥流水一般诗情画意,这么细细、小小、碎碎的他乡游子的思家念国的绵邈心思。
在这样的听雨中,我们怎么会不安,如何不安静睡去。余光中笔下的中国人是睡在“中国风景”中,“仙人一样睡去。”鲁迅笔下的中国人是睡在“铁屋子”里的,“从昏睡入死灭。”
余光中的雨塑造的是一个纤弱文人,退步于五四文人,是“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的传承人,甚至连《雨巷》里的那个丁香花一样的女人,都不有向新的力量。余光中的抒情形象,却是一个把古典而颓废(什么叫颓废?颓废就是有功能而没有意义)的华贵衣冠披在身上,破袍正在渐渐褪尽落地,不得不被迫忧愁于安身立命的,正在退出历史的“忧郁的中国”形象。
在大洋彼岸,沃尔特.惠特曼已经“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地区,大平原,落基山脉和太平洋斜坡”,为西部“自由健康的生活,简单的膳食,洁净而甜蜜的山泉,轻松而庄严的面容,明澈的眸子和健美的体格”在歌唱。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中的主人翁“他”,确是不能比拟的。不是如同“万宝路香烟盒上,那个目光深沉,皮肤粗糙,粗犷、豪迈的男子汉”似的阳刚。“他”不是“袖管高高卷起,露出健康的手臂,跨着雄壮的高头大马驰骋西部,开拓未来,进取、活泼而健康的形象。”“他”在余光中笔下听雨、看雨、嗅雨、舔雨,这么细腻如女人的“他”呀,“他”是阴性的。
“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
“他”日思夜梦的望中追忆的东西是“都已不再”的过去,是“虚无之间”,是繁复朦胧的“潮潮润润”的“古典韵味”。余光中要的是坐看山水闲云,要的是霄寒岑静,“仙人一样睡去”。“他”像一个病人,“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又像一个末路人,“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还像一个遗老,一个最后的文化贵族,“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在。”
在《听听那冷雨》中,余光中不知不觉成为了一个“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的送葬人,在给中国文化的意象山水抛撒纸钱;还是一个喊魂人,“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谁”,在朝《诗经》里的韵里,喊“有音韵的雨季”。反观前引惠特曼诗句中的雨,则是对“一个新的世界”的歌唱,是一帮充满男子汉英雄气概的“新来的移民”,他们具体化为“农民、山地人、伐木工、牛仔等”,他们“美国新的民族”形象。
中国文人的意向和形象,是儒弱和向后追忆的。
六、没有力量的中国风景,拿什么做为开陈布新的资本
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中国文人的意向和形象,是儒弱和向后追忆的;而其所构成的“中国风景”已经没有了现实的根基,渐渐退色:“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咯咯,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
忧郁的中国人,随着月桂、枫树、柳树和椰树的褪去,随着“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随着“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咯咯,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随着自然社会不再被赋予的意象,随着“中国风景”的消逝,那曾经的英雄,如“江南人,常州人,南京人,川娃儿,五陵少年”,他们会随余光中们一同死去。因为余光中们已经几十年没有到“雨的祝福”。
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们会随雨的消逝而死去。在死去之前,余光中用残存的方块字写了一幅挽词,挽词中残想有“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近代中国的文化人,在打碎了传统后,有依赖于传统意象消失,期望残剩的中国文化做资源,在天上仙界里,获得一个完整的灵魂。
当后来人在他们的感觉中彻底消褪了“中国风景”,他们会拿什么做为开陈布新的资本?要建立什么样的“中国感觉”以应对分裂的世界?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涂抹得一塌糊涂的扇面画,不是一张白纸,一张新的现代“中国风景”将以何处立基,将从何处开始,将以什么样的意象来布置,当凋零了的余光中从生命到文化彻底凋落之后,将会是什么样的“新儿女英雄”出场,来赋予新的“中国风景”以什么样的想象和气魄呢。古屋不再,而未来不可知!
这些,或许应该才是余光中“听听那冷雨”来叩问的真问题。
六、腐朽的“中国风景”只是用来欣赏的
余光中的雨感都来自乡土的记忆,积淀于大陆童年、少年时期。人生像漏斗,风里行雨里走,他写《听听那冷雨》,是要重新打捞那些已经不多的诗情画意的雨和雨感。人生像漏斗,本来不多的遗产都要遗漏得消逝殆尽。人尽黄昏,又发现却原来是立在残砖断瓦上,基本上一无所依,所以其追问也尤其恸心。令人不得不随之一同哀鸣。前尘隔海。古物不再。听听那冷雨。
美国西部文学之父詹姆士.库柏写了《开拓者》,《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内容写了美国新人“宽广的心境和淳厚的思想”。其实,但就书名看,就好像隐示了“中国风景”今天的方向。
或许余光中们会在中国传统文化雨的意象低吟浅唱中渐渐老去,生者依然在悠久颓废的历史文化回忆中沉浮。他们的时光,就是杜牧牧童遥指的闲诞,王维渭城清雨的孤寂,杜甫荡胸生层云的际遇,姜夔黄昏雨的沧桑,还有蒋捷白头听雨的迷茫,王玉稱黄州竹楼焚香嘿坐、消遣世虑的生存摸样。他们的时光不会倒流。
一个是新兴蓬勃的文明,一个是行将就木的文化,两厢比较冷人扼腕。两种还要继续对峙下去的“风景”,其实已经昭示了两种不同的未来。
除了以通过传统文化的认同,来姿态性的表达对现实政治认同的抵抗外,《听听那冷雨》中,那“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的雨的美感,实在太颓废消极。中国多的是旧臃肿,缺少的是新资源。想起了一句精辟的话:欧洲太腐朽,腐朽的欧洲是用来欣赏的。大概“中国风景”也是仅止于供人来欣赏的。
自由健康、简单洁净、轻松而庄严、明澈和健美的品性,对于现实中国的存在感、对于新“中国感觉”更有意义。“中国风景”的问题,“中国感觉”的问题,其实是“中国人”的现实塑造问题。让我们撕开人文与人文的冲突裂口,激发出爱与恨、善与恶的交汇处,从“心”开始。
如果“感觉”太好了,是有问题的。一种文化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听听那冷雨》撕开了感觉的裂口,提供了思考的契机,故要谢谢余光中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