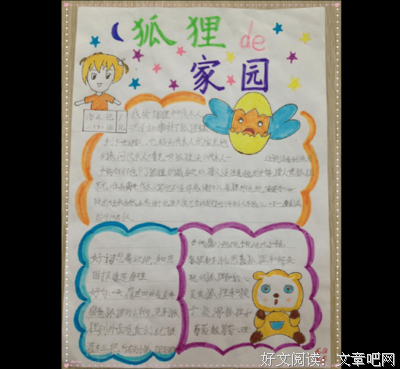《何典》读后感1000字
《何典》是一本由张南庄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0.43,页数:132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何典》精选点评:
●虽然恶心 但属佳作
●鬼故事。好多杂糅的影子!
●满篇鬼话,却似人间,有趣有趣,道是古典,原来是B级片
●当年让我惊艳的书,不可不志
●用语低俗,结构巧妙,细节荒诞,政治正确
●鲁迅在序言里说到陶成章“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的往事,其实还是很怀念文学革命时期的刘半农,荷戟独彷徨中,当年的朋友从战士变成了“士大夫”,这才是他痛心之所在。
●找时间写个读后感。
●倒像动漫一般
●口味太重了……
《何典》读后感(一):语出何典。。。
是在一本旧书摊上买的,好像花了五个胖子,物超所值,甚是喜爱,读来,尤爱不释手。原先只是听说过何典,当真读了,确名不虚传。幽默,诙谐,见人说人事,见鬼说鬼话,鬼话连篇,乱改成语典故。
再看看作者的自我评价。。。“且由我落开黄牙床,指东说西。天壳海盖,讲来七缠八丫杈;神出鬼没,闹的六缸水弗浑。岂是造言生事,偶然口说无凭;任从掇册查考,方信出于《何典》。”
。。。。。。。。。。。。。。。。。。。。。。。。。
这是一个自由的作品。虽也完整的讲了个结局大团圆的故事,并假托鬼事儿,如果作者能更拉风些,更自由些,会更有意思的多。看这个东西,总感觉我们一边看,作者一边在后面偷笑,仿佛这完全是他拿来糊弄我们的一个东西,完全是玩票儿的作品,而我们倒读的津津有汗味。
故事分十章,我一直觉得改编成电视剧比较好,肯定会火,但是还没有时间精力去搞这个。初次读完何典,深受启发,也顺势写了个价值三万余字的东西,号称“鬼事儿”,现在翻来,偶尔还忍俊不禁。有好事者可给我留信箱发配之。
评论一件东西不是容易的事,要有技术,有良心,有高度。现在看的姑且不能称为评论,算是读后感吧。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何典说的对: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此句极其简明扼要的道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本质。
《何典》读后感(二):附注老是写不下……
《何典》的情节其实并不复杂。文言小说自有一个写鬼的传统,而当时章回小说里借鬼世写人世的小说亦不少,如《何典》和《斩鬼传》,而《老残游记二集》等的“科普鬼界以行教诲”亦是一类,《宪之魂》等侧重政治投射的亦是一类。《何典》的鬼界设置并不巧妙,也并没有对自己的假定自圆其说,如鬼死了之后变成了什么,鬼的投胎、轮回是怎么实施的,为什么这些鬼会滞留各地形成村落……张南庄还推翻了历来鬼不吃食物、行步如飞等等的习规,使得鬼几乎没有一点鬼气。
它的精彩处在语言。张南庄将三家村的方言俚语故意“落实”,使其具备两种效果:既让人想到这些江南俗语带着泥土气的原意,又拥有了因随意落实到某一字上而产生滑稽效果的不谐感。和屠绅、陈球之流使用典雅的文言和骈文使小说抬高身价相反,张南庄却拒斥这种高雅,沉醉在生动的、低俗的游戏笔墨的趣味中,有意无意间将小说的重心转移到语词,也算是一次有趣的、不算失败的实验。正是这种排斥高高在上的文学正统的力量,所谓“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的勇气,吸引了吴稚晖刘半农和鲁迅诸人,其好处正如鲁迅所言: “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但到站直之后,究竟都还是长衫朋友。不过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
它的局限也在语言。比吴语小说以方言拒人更甚,《何典》的俗语、歇后语大多出自江浙沪各地,我这个吴语区的人大概也只能看懂十分之一,这既是时代变更导致语言的变更,恐怕也是区域的问题。如果不看注释,妙处几乎无法显现。而它常用粗鄙、生理性的词汇,也更使笔墨仅仅滞留于游戏而已。其书尾海上餐霞客所写的跋中说张南庄的十余册诗稿”在咸丰初红巾据邑城时尽付一炬,独是书幸存,悲先生以是书传之非幸“,未免有点张爱玲讽刺逃太平军的难到上海的南京人都说曾经家底丰厚一样——烧了的东西,怎么说也没关系。恐怕他是嫌这本书登不得大雅之堂,找个遁词而已。
《何典》读后感(三):中国后现代文本典范
(1) 果然犯实了症候,莫说试药郎中医弗好,你就请到了狗咬吕洞宾,把他的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第三回,新注本,下同)
(2) 形容鬼道:“你是个好人家囡大细,家里又弗愁吃弗愁着,如何想起这条硬肚肠来?即使要再嫁,也该拣个梁上君子,怎么想嫁那刘莽贼?(第四回)
(3) 活死人不敢与拗,只得拿了一把班门弄斧,走出门去。(第六回)
(4) 那活死人已有十几岁,出落得唇红齿白、粉玉琢的一般,好不标致;更兼把些无巧不成书,都读得熟滔滔在肚里。(第五回)
(5) 活死人看这道士时:戴一顶缠头巾,生副吊蓬面孔,两只胡椒眼,一嘴仙人黄牙须;腰里绉纱搭膊上,挂几个依样画葫芦。(第六回)
(6) 道士道:“为人在世,须要烈烈轰轰……。你去寻着他,学成了大本事,将来封侯拜相,都在里头。”说罢,化阵人来风,就不见了。(第六回)
(7) 轻骨头鬼听说,便拿了一把两面三刀,飞踢飞跳去了。(第九回)
(8) 那轻骨头鬼在城中,得知信息,自料孤掌难鸣,不能救应,欲回山报信。……看见路旁有一大堆柴料,便心生一计,上前放了一把无名火。(第九回)
(9) 下首是苦恼天尊,信准那个冷粥面孔,两道火烧眉毛上打着几个捉狗结,一个线香鼻头,……。(第一回)
(10) 正在说笑,形容鬼忽觉一阵肚肠痛,……道:“……这里可有应急屎坑的么?”和尚把手指着,道:“相公从这条肉弄堂里进去,抄过了弄堂便是。”(第一回)
(11) 活鬼道:“……只是寻那块屋基地,又要好风水,又要无关碍,却倒千难万难。” 扛丧鬼道:“村西头那片势力场,青草没人头的,精空在那里,何不就起在上面?……”(第一回)
(12) 等个好时辰,把尸灵掀在破棺材里,道士摇着铃注卵子,念了几句生意经,脗了材盖。(第三回)
(13) 那消几日工夫,到了城外。转到点鬼坛前,见有个铁将军把门,便上前报了名。(第十回)
(14) 回到殿上,只见阶前一个拽马鬼,牵只异兽,生得身高六尺,有头无尾,……。阎王指示活死人道:“这是独人国进贡来的,名为衣冠禽兽,……”(第十回)
(15) 一到断过七,形容鬼撺掇着,就在阴山脚下寻块坏心地,做了鬼坟坛,在太岁头上动了土。(第三回)
《何典》读后感(四):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原来这句名言出自《何典》里的开场白:
词曰:
“不会谈天说地,
不喜咬文嚼字,
一味臭喷蛆,
且向人前捣鬼。
放屁放屁,
真正岂有此理!
——右调《如梦令》”
书中于吴方言的运用,真正叫绝。活鬼和雌鬼(江苏宜兴人有一个话搭头,就叫‘雌鬼’)生了一个儿子,叫活死人。看来金庸也是看过此书的,不然怎么搞出个“活死人墓”来呢?讲到“吃”字,书中注释不错,苏浙一带的人,凡入嘴的全部叫“吃”,而没有喝、吸、抽这类北方语词的细分法。吃饭、吃菜、吃老酒、吃根香烟、吃只八万,都是这么个意思。书中提到的“眉花眼笑”,确实比现在常用的“眉开眼笑”来得有味。还有个很有意思的词儿:冷粥面孔。这个词好,生活中确实常见到,尤其是头儿和老板,常给人脸色看,不正象是冷了的粥一样,在脸上聚了薄薄的一层冷冰冰在那儿么?描述旧时小姐不下楼,北方话里说“真象个深闺小姐”,这个词在《何典》里,写成了吴语“畔房小姐”,也是活灵活现,很有意思。书里还有些现在仍在口头常讲的吴方言妙词,兹录如下:
面熟陌生:例如常用于人见面时的搭讪语,“这个人有些面熟陌生,在哪儿见过的吧?”
一觉睡到八国里;
弄怂:例如上海话讲,“他是在弄怂你,白相你呢。”
拆壁脚;听壁脚;掘壁洞;
萝卜不当小菜;
墨测黑:例如天晚了,外头墨测黑。
新箍马桶三日香;例如张爱玲《半生缘》里,讲到翠芝刚嫁给世钧时,其母冷落寡嫂,也用过这词儿。
猢狲撮把戏:猴子耍把戏之意。
做人家:节俭之意。例如你看到一个亿万大壕平时只吃几元钱的香烟,你可以开句玩笑:“啊呀,你真做人家!”
更有意思的是,学林版《何典》里,收录了江苏江阴人刘复(即刘半农)和浙江绍兴人刘大白七十五年前的一场掐架。比起上次我看到两个上海人傅雷和张爱玲的掐架,那是好看多了。当是时也,刘半农官居北京中法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大白官至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这两个人各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来解读两百年前上海人张南庄写的《何典》。为着书里的一句“飞奔狼烟”作何解,一直发挥到物理学上去,又赤手捋臂地吵相骂。吵到后来,刘半农说:
“但是我想,守庄君(这个林守庄也是个参与掐架之人,据其自讲住得离上海不远,似乎更有些发言权,对刘半农的批评,刘也接受了)所说的‘凭空臆测’,‘咬文嚼字’,‘钻到牛角尖里’,决不是指你刘大白先生。刘大白先生,请你不要多心,我亲爱的刘大白先生。”
后来刘半农退出掐架,写了篇《不与刘大白先生拌嘴》。刘大白是个可爱的掐架好手,他最后写了篇长长的《介绍‘吾家’刘复博士底几种巧妙法门》:
“读者们看,小孩子合人吵嘴的时候,如果觉得有点吵不过人家了,总是常常取这样的方式的:是的,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我不合你伴嘴了!于是回头来向他底母亲,姊姊,嫂嫂们,哭,骂,诉说,撒娇,一切都来了,引起他们底同情。”
现在看看,这帮文人真是好玩。书里还收了鲁迅的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众所周知的,鲁迅是掐架的一等高手。我也弄不清其间有什么因头,他在《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一文中,顺便掐了汪原放、胡适一把细肉:
“疑其颇别致,于是留心请求,但不得;常维钧多识旧书肆中人,因托他搜寻,仍不得,今年半农告我已在厂甸庙市中无意得之;且将校点付印;听了甚喜。此后半农便将校样陆续寄来;并且说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然而我还很踌躇,我总觉得没有这种本领。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刘半农,李小峰,我;皆非其选也。然而我却决定要写几句。为什么呢?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
这帮文人还真够酸的。既然是七十多年前的方言之争,不由我又想到了王朔与金庸于此也有过的未完之掐架。王朔在《我看金庸》里说:
“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
金庸在《南方周末》上回击道:
“王朔的我看过一本《盗主》(大概是指《顽主》——记者注)。他反映北京街头青年的心态,对这些人我没有接触过,不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看过就算了,也没有深入地好好地去研究。他的语言,有些话我也不懂,京味特别重,讲的京油子的话,地方色彩特别重。”
一个说你是在做“死文章”;一个回骂你是京油子,“地方色彩特别重”,旁观至此,我不由得要活学活用,骂一声:
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何典》读后感(五):历史的问号一箩筐
我找来《何典》,从头翻到尾,找不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原话,唯一能附会的一件事只有书中男一号活死人的雌鬼老娘带着活死人改嫁。这一段说雌鬼的活鬼老公死了没多久,雌鬼无端得了难言之隐的皮肤病,为治病,雌鬼戴了三分风流孝,到庙里勾引懒和尚,求他裤裆里的跳虱做药方,结果懒和尚顺水推舟作了花和尚,才引出改嫁的下文。
听我这样说,很多人会想这部奇书除了鬼人物、鬼名字,一切听起来多么像是澡堂子里的段子啊。没那么夸张,翻开《何典》,鲁迅题记:“作者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 展示归展示,这本书到底是充斥着脏话,不过全用上海松江方言裹了一层而已。有多脏?我只能说,如果让周立波一字不落地念一遍《何典》后马上漱口,吐出来的漱口水和澡堂子里的泡澡水一样浑。
我从《何典》里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情节。活死人穷途末路时奇遇一个老神仙,老神仙要送他使人足智多谋的灵丹,活死人止住道:“我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怎么?”老神仙哈哈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靠托那之乎者也焉几个虚字眼搬来搬去,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我这药是使人足智多谋的第一等妙药,如何倒不要吃?”果然,活死人一吃妙药,就会肠子转弯。一个忠厚老鬼要把娇女许给活死人,活死人心里纵然一百厢情愿,嘴里喷的却是另一套:“令爱天资国色,只宜配王孙公子。若与我这拣出乡下人相配,岂不是唐突西施?还宜另择门当户对的为是。”
江南在他所著的《蒋经国传》里说:“蒋先生(蒋介石)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限制,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指南针。蒋经国仅10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蒋经国也在回忆录里说:“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
历史的问号一箩筐。开头提到的“九•一三”林彪出逃时的飞行路线现在还扯不清。有一说,林彪乘飞机从山海关突然起飞,先244度照直飞行4分钟,这与去广州的航向基本一致。飞机之后用极缓慢的动作转弯,对着正西并在这个方向平飞了3到4分钟,这个航向是回北京。然后该机又开始转向到310度,向西北方向飞去。接下来继续转到345度,又最终调整到325度左右的航向,朝苏联飞去。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在空中画出一条轨迹,从雷达上显示,是一个硕大的问号。广州?北京?苏联?飞机在空中似乎做出过不同的选择。
扯不清的问号留给时间的长河去冲刷,能够弄明白的就不要留问号。“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既然不是出自《何典》,那么它又出自“何典”呢?
我在新浪围脖:@二古月
2010年8月17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