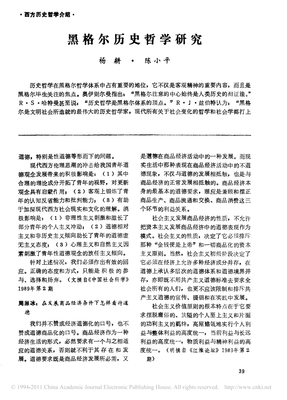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读后感1000字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是一本由贺麟著作,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精选点评:
●讲“知行合一”的那一部分内容完全可以删掉。
●年少时翻阅
●wanker
●真是哲学家!
●团子的书里比较适宜携带出行者,于去南站的路上和从长安回来的路上读完一二章,今日在大苦逼运通110加十号线上看完,基本和昨天判断无差。以陆王为抓手梳理近代哲学史的变迁未尝不可,但即便在80年代修改后出的版本,对孙的知难行易的意义评价似还嫌过高,捧角儿嫌疑深重。贺麟认可蒋后来的调和还是在知行合一的路上,但和蒋自己60年代表述的调和王孙的路径不同。本书最好的还是对译介黑格尔和康德的评述上。另外从编注可以看到40年代版本和80年代重印版本的不同,综合起来又是一种思想史的表现。
●知行合一,显隐关系,可以有进一步的认识。
●上篇很有趣,对几位现代中国哲学家的一些三言两语的评论很有启发性。下篇则比较混乱,有点不知所云
●当事人的眼光总还是不能回避,中国现代哲学的框架基本上构造出来了
●可以把民国年间这么多思想的家的思想梳理得清晰,很见功夫。
●此书应该读2012年上海人民版。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读后感(一):受政治影响
这本书总体上是很不错的,对于中国那个五十年的哲学发展给予了一个概括的介绍,并且还予以了简略的评价。但是,对于孙文“知难行易”和蒋中正“力行”哲学的评价,包括对毛泽东《实践论》的评价,让人有一种吃了苍蝇的感觉。在对上述的评论中,有很多是纯粹的符合和吹捧,不知是否出于政治上的投机。但是,这也不是个案,还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那一代。不知是否跟但是的社会大环境有关。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读后感(二):重觅贺麟的“时代精神” 转自《新京报》
作者:高全喜
现在的年轻人,在面对思想学术文化时,尤其在历史传承这一层面,或缺很多。虽然近年来,有一个所谓的“民国热”,但仍然流连于媒体上的表面热闹,甚至带有很多想象的成分。很多人对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耳熟能详,对其生平上的一些八卦津津乐道,但都是浮于表层的认知。若要真正进入厚重的历史思想文化的内在文理之中,需要一个缓慢的深入了解的过程。
我希望在热闹之后,大家回到真实的历史,以开放的心态,静心阅读。延续被中断的思想文脉,需要返璞归真,而非浮光掠影地消费其逸闻趣事。对前辈学者的尊重,最好的方式就是认真读他们的作品,要认识、理解他们的历史时代,将他们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上去理解他们。
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意识,今天我们借着贺麟先生诞辰110周年来谈论他的学术思想,作为他的学生,亲炙他的教诲,不禁自问:贺麟对于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贺麟先生是卓越的黑格尔研究家,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西汇通的典范,是学者,是导师,等等。
但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或许都是外在的。我们更愿意透过这些,洞悉一个思想家的心灵,看思想家们是如何面对他的时代的。我认为,在两个贺麟先生的背后,或许有一种精神的力量透彻其间。贺麟先生的学术人生,成就于早年的超迈激越、发奋图强,与其时代共呼吸,至晚年则天地相隔,或沉潜译介,或发配劳动,一代心智流于凡俗。
每每念及此,不由得感慨万端。历史有时是诡秘的,黑格尔说,它时常捉弄人,只有超越历史的时间之限,才会发现人与时代的无法摆脱的关联。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于前人,我们应该做的,是珍惜前人遗赠给我们的精神。
检视今天,我们的时代诉求新声,重新觅得贺麟先生念兹在兹的“时代精神”,这或许是对于他的最好纪念。从大的方面来说,中西汇通,继而发扬中华文明之精神,可谓我辈之使命。从小的方面来说,在熙熙攘攘的世界,能够持守那一份心灵的澄明之境,也就不错了。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读后感(三):他的贡献还未为学界充分认识(转自《深圳晚报》)
来源:深圳晚报 时间:2012年9月23日 作者:李晓水
贺麟先生弟子张祥龙谈恩师
他的贡献还未为学界充分认识
贯通中西哲学
贺麟,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二年级,又先后到美国的奥柏林、芝加哥和哈佛三所大学求学,受到系统的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严格训练。1930年夏,赴德国柏林大学系统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一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36年成为正教授。
1926年夏,贺毕业于清华大学。多年的求学生涯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为此,他决定远涉重洋,赴美求学。在奥柏林大学两年的求学中,贺麟最大的收获是接受了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并由此跨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大门。
1942年,贺麟出版《近代唯心论简释》,1945年出版《当代中国哲学》,1947年出版《文化与人生》。此三书确立了他在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家学术潮流中的重要地位。1950年,他翻译的黑格尔《小逻辑》出版,以后多次印刷和再版,影响巨大。到“文革”前,他的一些译作已陆续出版,比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知性改进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上卷,与王玖兴合译)、《哲学史讲演录》(前三卷,与王太庆等人合译)等。1955年,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一级研究员。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受到触及,“文革”中被严重迫害。“文革”后出版和出齐了多种重要著作和译著,担任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1992年9月逝世于北京,享年90岁。
一生两大成就
张祥龙在评价恩师时,认为贺麟先生一生最大的成就有两个。一个是:沟通中西主流思想的方法论,由此而为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找到一条新路。在西方一边,他自斯宾诺莎那里获得理性观照的直觉法、自黑格尔那里得到辩证法的提示,并力求打通两者。在中国一边,他揭示了宋明理学的直觉法,既言及陆王的“不读书”、“回复本心”、“致良知”的直觉法,也阐发朱熹那“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直觉法。至于辩证法与直觉法(他又称之为“辩证观”)的关系,可以简略说成,辩证法需要直觉法的引导,而直觉体验则需要辩证法的曲折往复的磨炼和开展,两者在历史、艺术、文化和人生的变化过程中相摩相荡而一气相通。
另一个是:对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精当阐发和翻译,使之生意盎然地传入中国。贺先生的译文以深识原著本意、学问功力深厚、表达如从己出、行文自然典雅为特点,得到学术界一致赞许。他志在向中国人介绍和翻译西方的大经大法,或“西人精神深处的宝藏”,所以无论是在选题择人、版本选择还是在实际翻译上,都认真严肃,还往往对照其他语言中的相关译本。而且,只要情况允许,他会在译著前加上有分量的导言,或在论文、著作中加以阐述,以便于中国读者的领会。
张祥龙认为,贺麟的学术活动、著作和学说,以其内在的思想素质和成就,在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界中属于最出色之列。而且,人类世界将进入一个各种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相激相融的时代,那些能够站在这个交汇之处,能真正有助于理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学说将获得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在这个数理化、技术化、商品化的时代,那既不躲避,亦不苟从,而是能在“理”中不失“心”源,或以新鲜的方式体会出“心即理也”者,当有蓬勃的活力和未来。他相信,贺麟思想会随着此套《全集》的出版和时间的拉长,而愈来愈显露出多维度的深意。
全集编辑细致入微
张祥龙介绍,这套《全集》想为学界贡献一套研究贺麟学术和思想的最具权威性的定本。为此,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编辑,做了大量细致认真的校对和梳理的工作。除了重新设计版式,纠正此前版本的少量讹误,统一同一书稿前后不一的译名等工作外,编者还依据贺先生自存本上的手迹,校改了部分由于时代因素或出版上的考虑而曾作调整的文字,以最大程度体现先生本人的真实意愿。此外,有的译作因出版年代相隔多年,加之部分内容是集体翻译,并经过数次修订和多个版本的相互校勘,译文呈现出某种前后不一致的现象,这次借重新编排之际,编者也尽量做了统一处理。
张祥龙说:“贺麟先生是引导我走上哲学之路的恩师,他的学识和人品是我所崇敬和终生感怀的。我一直觉得,他对于现代中国哲学事业的贡献,还没有为学界充分认识和估计。这套《贺麟全集》的出版,或许会有助于改变这种局面,为未来的贺麟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并泽及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读后感(四):中国哲学真命书生(转自《北京青年报》)
◎昆鸟
纪念贺麟先生诞辰110周年
贺麟:“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今年是贺麟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他去世20周年。在世90年,贺麟先生可称高寿。而1902年至1990年间的许多年头,中国多事,众生都在劫中。贺麟的足迹,在这近一世纪间倥偬辗转,不仅折射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也寄寓这中国哲学的百年身世。
贺麟小传
1902年9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1926年赴美留学,1929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1931年后长期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1947年任北大训导长,保护不少进步学生。1955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研究室主任。翻译出版黑格尔、斯宾诺莎等经典专著。1992年9月23日病逝,享年90岁。
梁启超经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
贺麟早年浸淫于儒家文化之中,8岁入私塾,其父常教他读《朱子语类》和《传习录》。所以,贺麟对宋明儒家的性命之学感情颇深。迷上黑格尔之后,他还做过很多打通宋明儒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努力。1930年,为纪念朱熹诞辰800年,他写了《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这篇文章可说是中国比较哲学的成功试验。
然而,贺麟最钟情的,不是程朱理学,而是陆王心学。这可能有性情上的原因,贺麟不大喜欢理学,是觉得理学支离繁琐。显然,陆王心学的直指本心和勃勃生气对他更有吸引力。1919年,贺麟进入清华之后,受到了梁启超的指点。梁启超的哲学根底,主要就是阳明心学。当时梁启超在清华讲的课,是“国学小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初期听课的学生有200多人,可是到了后来,很多人准备出国留学,到课的学生已不剩几人,贺麟就在其中。梁启超很喜欢贺麟,经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还指导贺麟写出了自己的国学研究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这一经历对贺麟的影响是既深且久的。
比较亲近心学一路的哲学家
在清华期间,贺麟确实幸运。梁漱溟曾在那儿做过短期的讲学,也让贺麟给赶上了。他去找梁漱溟请教过数次,梁漱溟告诉他:“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和王心斋(即王艮,阳明后学)的书可读,别的都不可读。”由于贺麟是带着崇拜者眼光前去求教,所以字字句句都听得很真,入心也深。“二梁”就这样成了贺麟国学研究的启蒙者。
读贺麟的《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我们会发现,自康、梁以来的中国哲学,或者说让他觉得比较有价值的哲学,多是陆王心学开出来的,要么就是具有陆王气象。文中,章太炎是“渐趋于接近陆王”;欧阳竟无是“感慨杂学无济,乃专治陆王”,对其佛学建树却一笔带过。仅有“内圣”是不够的,还得有“外王”。心学中人能“内断疑悔,外绝牵制”,易把人导向行动,拯救中华,这大概也是贺麟的块垒所在。当年学界中人,多抱学术救国之志,贺麟又何尝不做如是想?从清华毕业的时候,他跟好友张荫麟说:“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所以,他说“孙中山先生就是王学之发为事功的伟大代表”。文章初稿中,此句还提到“当今国府主席蒋先生”。蒋介石服膺王阳明,故对贺麟也是颇为器重,曾前后四次会见贺麟,待遇算是很高的了。
后来的贺麟在自我批判时说:“我把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欧阳竟无、熊十力、马一浮均装扮成陆王派的思想家,并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以及蒋介石的所谓‘力行哲学’陆王学派发为事功的具体表现。”对心学的钟情,也让他比较亲近心学一路的哲学家。贺麟和冯友兰都是积极参与到时代大潮中的人,且二人的求学经历比较像,国学功底深厚,曾留学欧美,都是通晓中西哲学的大家。但两个人一直无太深交集,因为冯友兰于中国哲学用功处是程朱,于西方哲学用功处是新实在论;而贺麟是研究陆王心学和斯宾诺莎、黑格尔。程朱派与陆王派不但在哲学进路上不同,体现在气质上也迥然有别。因此,倒是一味独行孤往的熊十力与贺麟相交甚笃,除了两人学说上相似之处很多,熊十力身上那股狷侠气可能也是贺麟所喜欢的。
处处体现着
“有我”的精神
周谷城说贺麟在学问上“博而不杂,专而不窄”,说中了贺麟的治学之道。这点在贺麟治西学的过程中最为明显。1926年,贺麟来到美国,进入奥柏林大学,跟着耶顿夫人研习黑格尔和斯宾诺莎,读到鲁一士的《近代哲学精神》,对《精神现象学》发生浓厚兴趣。1928年,贺麟转到芝加哥大学,除了学习《精神现象学》,还选修了“生命哲学”和摩尔的伦理学。学到这些东西,他都介绍到中国来,后收入那本《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里。贺麟的介绍从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加入很多自己的理解和评价,处处体现着那种“有我”的精神。
因为贺麟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精神蕲求,对西方哲学的取舍也是态度鲜明的。他离开芝加哥大学去哈佛,就是因为“不满于芝加哥大学偶尔碰见的那种在课上空谈经验的实用主义者”。贺麟自始至终都喜欢不起来实用主义哲学,觉得它“重行轻知,近功忽远效,重功利轻道义”,“在主义上无确定的信仰”。而由于胡适的倡导,以詹姆斯、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在中国声势很大,所以,在《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中,贺麟将其作为一个重要思潮进行了批评。
从这一点上讲,贺麟与胡适是对不上路子的。而另一个因素也可能使他不那么接受胡适这个人,在哈佛期间,有一次怀特海请贺麟等人到其家中做客。席间谈到中国哲学,怀特海提到胡适,说他全盘否定中国哲学有过分之处。贺麟当然深以为是,在《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中》,贺麟就对“五四”期间全盘否定古文的倾向批评了一通,不满当时的人只顾着实用。至于1949年后,贺麟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实用主义,已经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在这篇文章中,辩证唯物主义也是贺麟拿来剖析和批评的思潮。
立志引进西方的大经大法
翻译黑格尔成了贺麟最广为人知的成就,也让他在以后的研究中获得了一些便利。因为黑格尔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源头,研究马克思,离不了黑格尔。以贺麟的成就和地位,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都是香饽饽。北平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汪子嵩等人做贺麟的工作,要他留下;蒋介石数次通知他坐飞机离开,贺麟没有走。
1951年,贺麟写了《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开始批评自己的唯心论思想,后又多次参与批判胡适、朱光潜等人的思想。1956年,“双百方针”的鼓舞下,贺麟写了《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一文,1957年又写了《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但此文很快受到批判,被认为“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自此,贺麟对有政治意味的哲学问题再不关心,专心翻译、研究西方哲学。但“文革”期间,还是被当做“反共老手”批斗。所幸,贺麟以斯宾诺莎的“为真理而死难,为真理而生更难”,不改其志,忍辱负重。若非如此,《精神现象学》下卷和《哲学史讲演录》我们可能很难看到了。
供图/昆鸟
《贺麟全集》 贺麟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版
就学时的贺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