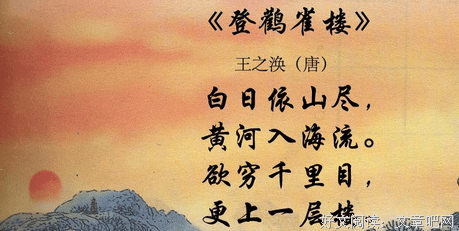Gone for Good读后感锦集
《Gone for Good》是一本由Harlan Coben著作,Dell出版的Mass Market Paperback图书,本书定价:USD 7.99,页数:4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Gone for Good》精选点评:
●大反转啊~
●great
●为什么没有拍成电影呢?最好的角色-the ghost
●Nice plot, weak, or should I say implausible, ending. Some of the key characters are not well developed - pardon me, but nobody is saint as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One is draw to the story until the abrupt end. And we never really fully udnerstand ken - he seems to be so smart, which is until he is not in the last few pages. I can go on and on
●哈兰科本小说里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也是所有读过的crime thriller里面的最爱之一,推荐给周围的朋友大家也都异口同声的说好看。不知为啥中文版打分那么低,难道是翻译的锅?
●Same old story, same good story
《Gone for Good》读后感(一):一波N折
写下这些文字,只是为了表达下自己的心情;我在落笔之前,就打定主意绝对不透露一个字,假如剧透了,那可真是作孽啊
该书近400页,直至最后第二页,都有情节的大逆转发生,作者Coben在全书中设置了重重悬机,虽然从情节进行到一半时,读者就约摸可以知道最大的反派Boss是谁,但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是要等到最后一页才等到清晰的解释。
赞!抽丝剥茧的高手!Harlan Coben。
《Gone for Good》读后感(二):Harlan Coben,崇拜死你了……
Gone For Good是在文庙旧书市场里买到的,10元钱,问摊主还有没有科本的小说,他问答说没了,我有点失落,但用便宜价格淘到一本科本的书,也不错。在上海外文书店里,他的书都要70-80RMB呢!
[之后有剧透,勿看]
Coben的这本小说,好像是上上个礼拜看完的,之后就摆在书架上一个稍低些的角落里,每次看到,我都会回想到最后10页里的大转折,出乎意料,实在是出乎意料。
o Second Chance里Coben击碎了友情的美好幻想,而Gone For Good里,Coben又重创了兄弟之情。我今天突然发现了这一真相。Coben的小说里总是撕碎历史与过去的谎言,把真相暴露给读者看。虽然稍稍会感觉有些突兀,却回想过去时依然是合情合理。
故事主人公的哥哥Ken在十一年前谋杀了主人公的前任女朋友,逃逸得无影无踪,FBI发出全球通缉令,但依然没有捉住他。案发现场是在女孩的家里的地下室,现场有女孩和Ken的血迹,因此警方认定Ken是凶手。可主人公一直不相信这个结果,他相信哥哥是无罪的,而且现在已经死了。
主人公的母亲在去世前几年经常念叨着Ken没有死,主人公以为这是老年痴呆症造成的,也没留意。直到母亲离世后整理她的遗物,竟然发现哥哥的一张近照,主人公惊呆了。
在之后那天,主人公的现任女朋友失踪了。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凶案现场,竟然发现了她的血迹,警方认定主人公是谋杀他女朋友的嫌犯……
追查真相,追查却越让人吃惊,Ken到底是不是杀人凶手,自己的两任女朋友的死亡或者失踪与之有没有联系……
不想把真相都写出来了,因为案情实在复杂……
顺便说一下,这本书大陆与台湾方面都还没有翻译!
《Gone for Good》读后感(三):No More Than a Twisted Story
Gone for Good, a twisted story contains a murder-charged runaway, untold family love, identification exchange, informant, childhood scars and more murders. These fantastic plots ask too much for turnings leaving rare descriptions for further feelings extension. Although it is of high attraction, less space leaves for mental-level discussion.
Take the biggest mysterious person, the murder-charged runaway Ken as an example. He was a brother-loving type in childhood. To protect his younger brother Will, he broke his arms, which stopped him from the chance of becoming a professional athlete at Harvard. And this was not the only one help he got from Ken but the most impressed one.
When wanting to hang out with Will’s ex-girlfriend Juliet, Ken asked Will for permission.
.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above, Ken, as a brother, revealed a kind image, but the result refuted it. “You I’ve hurt and betrayed more than anyone.” this is Ken’s confession to Will. Ken, not only strangled Juliet, but did not plan to show up to save Will and Katy under the Ghost’s hand although he promised he would. The filthy things he did were more than these, which Will first thought Ken wasn’t involved in any.
Another example is Will. He went through lots of “surprise”, like first thinking Ken might be innocent, he strongly stick to his thought bit by bit during his search for Ken; and then a sharp turn surprisingly came out to refuse his thought; near the e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tle girl and Will raised a sudden surprise too.
Here my questions popped up- When and what changed Ken? And why Will had few confusion or mental fight with fast-changing encounters. I found it hard to tell from the novel. THAT IS IT seemed the answer the writer left, for there left no enough or strong hints in terms of discussion.
o the writer’s focus decides this novel is no more than a twisted story.
《Gone for Good》读后感(四):C 1
杳无形迹
哈兰·科本 作品
乃鼎斋无机客 无私奉献
首章
母亲过世那日的三天前,她告诉我,这些并非她的最终推论,可真相很可能就是那样,我的哥哥依然还活着。
这就是母亲说的话。她没有添枝加叶。她仅仅讲过一次。她讲得也不那么清楚。吗啡已经起了效用,让心脏收缩得不那么厉害。母亲的肤色介于蜡黄色和褪色后的古铜色肌肤之间。她的眼珠子,深深地陷了下去。她大半时间都睡着。假如刚才母亲真的神志清醒(我对此相当怀疑),那么实际上,母亲应该再清醒一会儿,好让我有机会告诉她,她是个伟大的母亲,我十分爱她,再道声别。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哥哥。那并不表示我们不会想起他,就仿佛哥哥也正坐在床边。
“他还活着。”
这些就是母亲的原话。假如它们是真的,我不知晓这会是件好事或者坏事。
四天后,我们下葬了母亲。
当我们回到家中来度过七天的犹太居丧期,父亲急匆匆地冲过客厅里铺着的地毯。他的面色因为情绪激动而发红。我当然也在那儿。我的妹妹梅丽萨和她的丈夫拉尔夫从西雅图坐着飞机赶到了这儿。塞尔玛舅妈和默里舅舅跟在后头。希拉,我的女朋友,坐在我的身边,紧紧握着我的手。
到场的亲眷们也就这么几位了。
送来的只有一份鲜花,非常漂亮。希拉微笑着,当她细看留言卡时,她捏了下我的手。没有留言,没有口讯,只有一幅图。
父亲一直不停地往凸窗外望,在过去的十一年里,同一扇窗户被空气玩具枪射穿了两回。在父亲的呼吸声中,还可以听到他的呢喃声“都是些狗娘养的”。他转过身来,想着还未路面的亲戚朋友。“见***鬼,你还以为伯格曼一家至少会***露下面。”接着,父亲合上双眼,扭过头来。怒火会再一次令父亲形容枯槁,与忧伤之情相融合、汇聚,使我也没胆量面对。
十多年来的第二回背叛,令父亲感情激动。
我需要放松一下。
我站起身。希拉抬头关注地望着我。“我想去散会儿步。”我轻声说道。
“你想要我陪你么?”
“不用。”
希拉点了点头。我们在一起已经差不多一年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位伴侣,与我着实古怪的生活节奏那么合拍。她又摁了下我的手掌,意味着“我爱你”,温暖的感觉随之传遍全身。
家里前门上摆着的擦鞋垫属于粗糙的人工草垫,就像是从高尔夫球练习场上偷盗回来的,左上角还有一朵塑胶的雏菊花。我踏过擦鞋垫,沿着Downing Place街往北漫步。沿街道两旁,是普通到让你麻木的铝合金门窗的错层式房屋,都建造于大约1962年。我依旧穿这我那件深灰色的外套。浑身热得有点发痒。凶猛的烈日晒得火辣辣,我异乎寻常地想到,今天真是个让尸体腐烂的好日子。我母亲在生病以前,简直能照亮全世界的灿烂微笑的画面又映现在我眼前。我挥走了怪念头。
我知道自己在去往哪里,尽管我怀疑我是否敢承认真相。我被吸引着去往那里,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牵扯着。有些人会称呼其为受虐心态。其他人会留意到,这也许与了结一切的心态有关。我想它或许两样都不沾。
我只是想去看下一切得以了结的地方。
夏日郊区的景致与声音扑面而来。孩童们骑着自行车尖叫而过。Cirino先生经营着10号高速公路上的一家福特/水星汽车代理店,正在忙活着割草坪。斯坦一家建立起一溜子五金连锁店,却被另一家更大的连锁公司给吞并了,夫妇俩正手牵手地散步。在莱文家正上演着一场触地球比赛,尽管参赛选手我一个都不认识。从考夫曼家的后院里,升腾起烧烤的烟。
我走过格拉斯曼家的旧宅。“傻蛋”马克·格拉斯曼在六岁时,曾经跳着撞向玻璃滑移门。他正在扮超人。我还记得那声惨叫和淋漓的鲜血。他一共缝了不下四十针。“傻蛋”长大了,成了那种通过IPO[首次公开募股]而起家的亿万富翁。我想人们再也不会叫他“傻蛋”了,但你永远不知实情如何。
路转弯处,是马里亚诺的家,依旧笼罩着一片恐怖的痰黄色,一只塑料鹿守卫着屋前的走道。安吉拉·马里亚诺,我们这片儿的不良女生,比我们都大上了两岁,就像是某种上级,令人心生敬畏的族类。偷看安吉拉在后院里晒日光浴,身着挑战重力、肋骨凸现的露背装,我那时头一次感觉到心头涌起的、荷尔蒙引起的强烈的性渴求,真让人难熬。我的嘴里竟真的口水直流。安杰拉过去经常与父母争吵,在屋后的工具房里偷偷吸烟。她的男朋友骑着一辆摩托车。我去年还在市中心的麦迪逊大道上撞见她。我本以为她看上去会很糟糕——你常会听到早恋的人会有不幸的遭遇——可安吉拉看上去棒极了,似乎还很快乐。
Downing Place街的Z3号,是埃里克·弗兰克尔的家,门前草坪上的洒水器缓缓地旋转着。在我俩还都是七年级时,埃里克在Short Hills[1]上的一家太空旅行主题的Chanticleer进行了男孩的成年礼。天花板属于天象仪风格,黑色的天穹上点缀着星座。我的座位卡上告诉我,我正坐在“阿波罗14号桌”上。餐桌中心的绿色火箭发射场模型上摆着一座精美的火箭模型。侍者们穿着几可乱真的太空服,每个人都装作是“水星7号”的成员。“约翰·葛林[2]” 招待了我们。辛迪·夏皮罗和我悄悄溜进了小包间,胡搞了一个多小时。这是我的头一回。我压根就不明白自己在干些什么。但辛迪知道。我记得那段经历愉悦无比,辛迪的舌头以种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抚触着我,令我为之颠狂不已。可是我犹然记得,在约摸二十分钟之后,最初的惊叹转化为唠叨个没完:困惑不解地问起“下一步该干嘛?”,外加天真无知地问起“做爱就是这回事?”
当辛迪和我暗地里悄悄潜回肯尼迪角的“阿波罗14号”桌时,我俩衣衫不整,一幅热吻之后的模样(Herbie Zane乐队正在用一首《飞我上月球》征服听众),而我的哥哥肯拉我到了一边,想要听细节。我呢,自然心欢情悦地一股脑告诉了肯。他给了我一个微笑以作奖赏,还向我击出了“Happy Five”。那一夜,我俩躺在双层床上,肯在上铺,我在下铺,音响播放着蓝牡蛎合唱团[3]的《不要畏惧死神》(这首歌是肯的最爱),我的哥哥想我解释一个九年级学生眼中的性知识。日后,我才知悉肯在大多方面都说错了(他有点过于看重乳房了),但是每当我回想到那一夜,我总是笑个不停。
“他还活着……”
我摇着脑袋,转过身对着屋主的旧宅子旁的Coddington Terrace。肯和我总是走这条路去伯内特山初级学校。两幢房子中间过去有一条铺就砖的小径,以让路途更短些。我心想着,这条路是不是还在。我的母亲——每个人,每个孩子都称呼她作“阳光妈妈”——过去常半明半暗地跟着我俩去学校。当妈妈突然躲到树后面时,肯和我就会骨碌着眼珠子。到了如今,我一边微笑,一边想起母亲的呵护有加。这在过去让我尴尬无比,可肯只是耸了下肩。我的哥哥十分沉着冷静,并不理会此事。我却不是这样。
我感觉心头一痛,继续往前行。
兴许这纯属我的想象,但人们开始注视我。随着我的穿过,自行车、下落的篮球、洒水器、草坪上的割草机、玩耍触地球的选手的叫嚷声全都似乎静寂了下来。一些人是出于好奇而注视我,因为在夏日的傍晚,一个身着深灰色外套的陌生男子独自散步有几分奇怪。但大多数的人(还是看上去的情况)恐惧地观望着,因为他们认出了我,不敢相信我敢踏上这片受到神佑的土地。
我毫不犹豫地走向Coddington Terrace 147号的宅子。我松开了领带,双手插进衣兜。我在人行道与小径交接的地方踢着路面。为什么我在这儿?我望到书房里的窗帘被移开。米勒太太的脸孔从窗口露出,面色憔悴,宛如鬼魂。她怒视着我。我没有移动身体,也没有转过头。她继续瞪视着我,接着出乎我的意料,米勒太太的脸庞变得柔和起来。仿佛我们共同的痛苦构成了某种联系。米勒太太冲着我点了点头。我回应地点了点头,感觉眼泪开始涌出。
你也许曾经看过zo/zo、《黄金时间直播新闻》[4]、或者其它一些类似的无聊电视节目上的故事。对于那些没有看过的人,以下就是官方的报道:十一年前的十月十七日,在新泽西州的利文斯顿镇,我的哥哥肯·克莱因(那年二十四岁)残忍地强暴和勒死了我们的邻居朱莉·米勒。
案发地点在她家的地下室里。Coddington Terrace 147号。
在那儿发现了她的尸首。并无确信的证据表明朱莉确实是被谋杀在那间草草装修的地下室里,还是在死后被抛尸在那座带有水渍的斑马纹沙发椅后面。大多人假设为前种可能。根据官方的纪录,我的哥哥逃离了抓捕,后又跑路到不知何处。
在过去的十一年里,肯逃脱了国际抓捕网。然而,有好几次所谓的“目击报告”。
头一次是在谋杀案发生后的一年,在瑞士北部的一个小渔村里。国际刑警突袭那儿,却不知何故哥哥又逃脱了抓捕。据说他听到了风声。我想象不到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又是谁走漏了消息。
下一次目击报告,发生在四年后的巴塞罗纳。引用了报纸上的报道,肯租借了一栋“可观海景的庄园”(巴塞罗纳并不靠海),根据报道,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身材柔软、深色头发的女子,可能是一位弗拉明哥舞者”。一位正在那里度假的利文斯顿居民一股脑地都转述了,说看到肯与他的西班牙情人在海滨共享美餐。我的哥哥被描述成一个肤色古铜色、身体健壮、穿着一件衣领打开的白色衬衣,不着袜子地穿着一对平底便鞋的男人。这位里克·霍洛维茨曾经是我在亨特先生教的四年级班级里的一位同班同学。在那三个月里,里克在休息时吃着毛毛虫来取悦大家。
在巴塞罗纳,肯又一次逃脱了法网。
最后一回有人据称看到我的哥哥,他正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专业雪道上滑雪(非常有趣,肯在谋杀案发生之前从没滑过雪)。没有后续新闻,只有《46小时新闻》[5]上的一篇报道。这么多年来,哥哥的亡命生涯已经变成了“Vhi Where Are They Now”的犯罪剧版。当一个新闻网络的垃圾新闻料不够时,或者无论何时、只要有流言扶摇而上时,哥哥的故事就会冒出来。
很自然地,我痛恨电视台对“出麻烦的郊区”的“狂轰滥造”报道,或者任何他们急中生智想出来的类似“可爱”的绰号。他们的“特别报道”(只有一次,我想要看到他们称呼报道为“正常的报道,每个人都报道过这个故事”)总是打出同一张照片:肯穿着白色网球服,一副极为自得的样子。有一段时间,肯曾是一位在全国范围有排名的网球选手。我想不到电视台是从哪儿搞到这些照片的。在相片中,肯看上去英俊潇洒,而人们也正因为这而立马憎恨起肯。傲慢自大的外貌、肯尼迪式样的发型、裸露在外古铜色的肌肤映衬着露出洁白牙齿的笑容,照片里的肯瞧上去就像是权贵人士中的一员(他并不是),凭借着个人的魅力(他只有稍许魅力)和信托基金(他压根就没有)而享受着人生。
我曾在一次新闻报道上露面。很早的时候,一位制片人找到了我,声称他想要“公平地展现正反两方”。他特意提到,他们有不少准备诋毁我哥哥的人。为着所谓的“平衡”,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某个能够向那些家庭读者描述出“真正的肯”的人。
我应承了。
一位稍有银发、金发碧眼的女主持人,举手投足间带着同情心,采访了我一个多小时。我实际上挺享受这个过程。它能疗慰我的心灵。女主持人向我致谢,引着我走了出来,当节目播出时,他们只用了一个片断,剔除了她的提问(但是你肯定不打算告诉我们,你的哥哥是完美无缺的,对吧?你还不打算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圣人,对吧?),他们还剪辑了我的话,播放一个拍得我鼻孔上翘模样的特写镜头,配上戏剧性的音乐,说道:“肯不是圣人,黛安。”
不管如何,那就是官方纪录下的事件原委。
我从来没有信服。我并不是说,这不可能。然而,我相信一种更为可信的情节:我的哥哥死了,在过去的十一年里他一直都是个死人。
说得更准确些,我的母亲总是认为肯已经死了。她坚定地相信。毫无保留。她的儿子并不是一个杀人凶手。她的儿子是一位受害者。
“他还活着……他没有杀人。”
米勒家的前门开启了。米勒先生走了出来,他把眼镜推上鼻梁,拳头紧贴双臀,摆出令人同情的超人姿势。
“你***滚出去,威尔,”米勒先生对我吼道。我照他说的做了。
下一回的巨大震惊发生在一个小时之后。
希拉和我正在我父母的卧室里。同样的家具,坚实牢靠、业已褪色的漩涡花纹灰色蓝边墙纸,自打我记事起,就装饰着这间卧室。我俩坐在加长尺寸的卧床上,床垫的弹簧有点发硬。我母亲最私人的物品——她藏在塞得满满的床头柜抽屉里的东西——此刻四散在羽绒被上。我父亲依旧在楼下,坐在凸窗边,挑衅般地望着窗外。
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想要清查母亲觉得有价值、保存并藏在身边的东西。这会伤到人心。我心知肚明。在存心对自己施加痛楚与获得宽慰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关联,就好比某种治疗心伤的玩火游戏。我需要这么做,我在心里猜测。
我望着希拉翘向左侧的漂亮脸庞,双目低垂,凝视下方,接着我感觉到心在翱翔。这个说法听上去有点儿怪怪的,但是我可以几个小时地一直望着希拉。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美丽,——不管怎么说,希拉的美丽并不属于那种古典美,她的五官有点儿中心错位,也许是基因原因,更可能是因为希拉隐晦不清的过去——更是因为她所具有的活泼朝气、好奇心、娇嫩柔弱,就好比再一击就会令她支离破碎、无法挽回。希拉使得我想要——在此处请容忍下我的肉麻话语——为她而变得勇敢。
希拉头都没抬,就半露微笑,说道:“住手。”
“我什么都没干。”
希拉最终抬起头,看到我脸上的表情。“什么事?”她问道。
我耸了耸肩。“你是我的世界。”我仅仅说了这句。
“你自个儿就是个超辣男人。”
“是啊,”我说,“是啊,这倒挺对。”
她对着我的方向,故作声势地拍了一巴掌。“我爱你,你知道。”
“为什么不么?”
希拉转着眼珠,然后眼神落回到母亲卧床的边上。她的脸色变得平缓下来。
“你心里在想啥?”我问道。
“你妈。”希拉微笑道,“我真的很喜欢她。”
“我真想要你早就认识她。”
“我也是。”
我们开始翻找几叠黄色的剪报。梅丽萨、肯和我的出生证明。关于肯网球成绩的新闻报道。他的奖杯,所有发球中姿势的铜制小人都还放在肯的旧卧室里。还有照片,大多数都是谋杀案发前的旧照片。“阳光妈妈”。自孩童时起,这就是母亲的绰号。这很衬她。我找到一张母亲担任“教师父母协会”主席时的照片。我不清楚母亲在干什么,但她站在舞台上,戴着一顶愚蠢的帽子,而所有其他的母亲都在捧腹大笑。还有张母亲打点学校交易会时的照片。她穿着小丑服。“阳光妈妈”是我的伙伴中最受欢迎的成年人。他们喜欢母亲让他们搭车。他们想要在我们家里进行班级野餐。“阳光妈妈”是父母中的“酷人”,从不会让人厌烦,只是有点儿过分,兴许还有点疯狂,那样你永远不清楚她下一步会干什么。在母亲的周围,总是有一阵骚动,假使你愿意,还可能变得闹哄哄。
我俩一直看了两个多小时。希拉从容不迫,细细看过每张照片。她特别停在了一张照片上,双眼眯缝起来。“那是谁?”
她递给我那张照片。在左手边,是穿着一条性感过度的黄色比基尼的我母亲,我得说,母亲很青春,曲线十分地优美。她的手臂挽着一位矮个子男人,那名男子留着黑色胡须,脸上挂着快乐的笑容。
“侯赛因国王。”我说。
“再说一遍?”
我点了点脑袋。
“约旦王国的那位?”
“是的。妈和爸在迈阿密的枫丹白露海滩遇到了他。”
“然后呢?”
“妈问国王,能不能和她合影一张照片。”
“你在开玩笑。”
“证据说话。”
“那他有警卫么?”
“我猜母亲看上并没全副武装。”
希拉嫣然一笑。我记起母亲告诉我的事情原委。她和侯赛因国王合照,父亲的照相机出了故障,他呼吸声下的嘀咕,他试着修理相机,母亲瞪视着父亲催促他快点,国王颇有耐心地伫立着,他的警卫长检查相机,查明了问题所在,修好了机器,又把它递回给父亲。
我的母亲啊,“阳光妈妈”。
“她多么漂亮。”希拉赞叹道。
警方发现朱莉·米勒的尸首时,母亲的一部分也死了,这真是糟糕的老套说法,但老套说法的另一层含意就是它们往往道出了真相。母亲的热闹生活平静了下来,几乎让人透不过气。在听说谋杀消息后,她从未动怒,也没有歇斯底里地大哭大叫。我经常希望母亲能发作一场。我那多变的母亲变得平静下来,让人畏惧。她的一举一动,都变得稀松平常——单调、毫无热情会是最佳的形容词——在一个像母亲那样的人身上,这种变化会比见证最为怪异的表演更令人痛苦。
前门铃声作响。我望向卧室窗户外面,看到Eppes-Essen熟食店的送餐车。给送葬者吃的碎牛肉饼。父亲过于乐观地订购了太多份数。到头来是一场痴想。他待在这栋房子里,就像是泰坦尼克号的船长。我记得在谋杀案后不久,窗户第一次被人用玩具汽枪击穿时,父亲面对挑衅摇晃拳头的样子。我想,母亲那时想要搬家。爸爸不愿。在他看来,搬家就意味着投降。搬家就是承认他们儿子的罪过。搬家就是背叛。
沉默无语。
希拉注视着我。她的温情几乎可以触及,我的脸上浮起更多的灿烂光芒,在那一晌,我任由自己沐浴在这片温情中。约摸一年前,我们在工作时结识对方。我是纽约市41号大街上的救济所的高级主管。我们是一个慈善机构,致力于帮助年轻的出走者在街头幸存下来。希拉是作为一名志愿者过来的。她来自爱达荷州的一个小镇,尽管从她身上几乎看不出一点小镇里长大的女孩的影子。她告诉我,她在好多年前也是一名出走者。关于希拉的过去,她告诉我的仅此而已。
“我爱你,”我说。
“为什么不么?”她回应道。
我没有转动眼睛。直到最后一刻,希拉都对我母亲关怀备至。她会搭乘公共巴士线从港务局赶到诺斯菲尔德大道,然后步行走到圣巴纳巴斯医学中心。在母亲患病以前,母亲最后一次待在圣巴纳巴斯医院就是她把我生下来那回。其中,大概存在着某种让人心伤的生命轮回关系,可我那时无法参透。
但是,我看见过希拉和母亲待在一块儿。这不禁让我寻思。我要冒次险。
“你应该叫你的父母来。”我轻声说道。
希拉看着我,仿佛我刚刚冲她脸上掴了一个耳光。她滑下了床。
“希拉?”
“时机不对,威尔。”
我拾起一个相框,里面放着一张我肤色黝黑的父母度假时的照片。“现在的时机和平常一样呀。”
“你对我父母一无所知。”
“我想要知道。”我说。
她扭过身,背对着我。“你是在和一个出走者打交道。”她说。
“那么?”
“你该知道,这会有多坏。”
我知晓。我再次想了想希拉稍许中心错位的五官——譬如说鼻子上泄露出实情的肿块——,然后想知道。“我也知道假如你还没谈起过,那会更糟。”
“我已经说过了,威尔。”“没有跟我说。”
“你不是我的治疗师。”
“我是你爱的人。”
“是的。”她转身对着我,“可不会在此刻说,好吧?请原谅。”
我没有回应,但也许她是对的。我的手指心不在焉地抚摸着相片框。就在那时,事情发生了。
相框里的相片稍稍滑向一侧。
我低头望了眼。另一张照片从底下开始露出身影。我进一步移开了上面的照片。底下的相片显出一只手。我使劲把它推出来,可相片一动也不动。我的手指摸到相框背后的夹子。我把两张相片滑到一边,任由相框背面落到床上。两张照片随之飘落下来。
上面那张相片里,我父母站在一艘游艇上,看上挺开心,挺健康,很闲适,我几乎不记得父母曾经有过这样的快乐时光。但抓住我视线的,却是第二张相片,躲藏在后的相片。
印在相片上的红色日期标明是在不到两年之前拍的。相片是从一片旷野上空、山丘或者类似地方上拍摄的。我从背景里看不到房屋,只有白雪覆盖的山脉,就像《音乐之声》的开片场景那样。照片里的男人穿着短裤,背着背包,戴着太阳眼镜,脚踏磨损了的旅行靴。他的笑容很是熟悉。这就是他的脸孔,尽管如今更富线条感了。他的头发更长。他的胡子夹杂着灰鬚。但我不会弄错。
照片里的男人就是我的哥哥肯。
[1] 新泽西州地名,与美国东岸的“贝弗里山”齐名,居住着大量中上层人士。
[2] John Glenn是世界上第一位环绕地球太空航行的美国宇航员,后担任参议员,并在1998年成为“发现号”太空飞船机组成员,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太空人。
[3] Blue Oyster Cult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成立的一支迷幻/重金属摇滚乐队,《不要畏惧死神》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
[4] Prime Time Live是美国ABC电视台的一档新闻直播栏目,创立于1989年。
[5] 48 Hours是CBS公司的一档新闻节目,名称的寓意是采撷48小说的新闻素材,浓缩在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里。节目创立于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