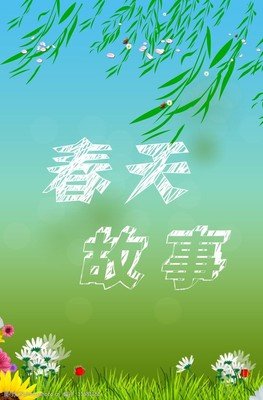|背景故事
游览故事中的实景地是一种想象行为。真正的目的地在书迷的脑海里。
驱车逼近冥界的大门,驾驶变得惊险起来。塔楼破败不堪,原本农民开垦的梯田已经沦为荒芜,令人绝望。周围便是崖顶的一条道路,通向摩尼半岛南端的尽头。而摩尼半岛则是伯罗奔尼撒最荒野的地区。蝉鸣渐渐消失了,狭长的土地将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分隔开来,这里似乎只有荆棘生长。这个荒无人烟的美丽海角名为马塔潘角或塔纳罗角,是通往冥府的入口。
希腊古典时期的作家欧里庇得斯或许暗示过该海角是冥府入口;其他作家则将冥府入口设置在希腊的更北边,或者靠近那不勒斯,又或在土耳其海岸线某处。游客暂且把怀疑抛之脑后,走在荒废小教堂与寂静小海湾之间的蜿蜒道路上,对于这些游客而言,此处便是赫拉克勒斯把地狱三头犬刻耳柏洛斯拽到阳间的地方,也是俄耳甫斯救回欧律狄刻而欧律狄刻在黑暗中永远消失的地方。
200年前,拜伦曾引发过游客对古典著作地标的狂热,然而甚至在此之前人们就会游览文学地标。在荧幕改编的推动下,文学旅游自此成为一种大众热潮,
疫情后假期的旅游热便证明了这一点。哈利波特粉再次在国王十字车站的9¾站台标志前排起长龙摆拍,这里是J.K.罗琳书中开往霍格华兹的火车起点站。附近的其他普通站台上,书迷们踏上从伦敦到巴黎的旅途,再次解读《达芬奇密码》。6月16日,也就是《尤利西斯》中情节发生的日子,都柏林人将庆祝以詹姆斯·乔伊斯书中主角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命名的“布鲁姆日”,人们会身着小说中的服装,到小说中的酒吧庆祝这一日子。
6月16日是一年一度“布鲁姆日”(Bloomsday),旨在纪念20世纪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巨著《尤利西斯》的诞生,6月16日是《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利奥波德·布鲁姆在爱尔兰街头游荡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世界上60多个国家的乔伊斯爱好者都会聚在一起,举行各种各样庆祝活动。
一项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英国游客在国内旅行时乐于在“书中之地”驻足流连。从表面上看,这种追寻虚构场景的冲动相当古怪,甚至不合常理。倘若更仔细地探究,就会发现,除了游客自发的热情之外,这些旅行还能揭示出故事和读者间神秘奇妙的联系。
参观作家生前写作的地点和逝世地点也就罢了,比如徒步前往霍沃斯的勃朗特牧师住所,或者沿着堤坝前往海明威在基韦斯特的度假屋。与之相比,更奇怪的举动是去寻找那些虚构小说中的求婚地或古老神话发生地。毕竟,小说中的人物是虚构的,他们从未去过那里;有些地方甚至连作者也没去过。而更加荒诞古怪的行为是去寻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地方,比如托尔金的中土世界。托尼·霍维茨在《阁楼上的邦联》(Confederates in the Attic)描述道,曾有游客在乔治亚州寻找斯嘉丽·奥哈拉的家——塔拉庄园,尽管《乱世佳人》这部电影大部分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拍摄的,《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也明确表示她所描绘的种植园与真实的种植园并不相像。
很显然,对这种“文学旅游”冷嘲热讽很容易,但想去亲自参观和触碰书中场景的愿望可能只是好梦难圆。有人说,在人们的脑海中,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主角,然而对许多人而言,似乎能成为别人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就已经足够了。追寻虚构人物或场景的计划似乎注定要以失望告终,除了那些企业家和营销人员——他们靠兜售福尔摩斯戴的猎鹿帽或吸引游客去简·奥斯丁待过的巴斯旅游来从中渔利。
也许,难以找寻书中场景才是关键所在,毕竟真正的目的地在朝圣书迷的脑海里。受后结构主义影响,一派文学批评家自上世纪60年代起以一种关联法分析文学作品,将解读文学作品视为一种协作,而非作者的一言堂。该学派认为,作者并不具有主宰作品内涵外延的绝对力量,读者也参与了作品的创造过程,而非只是被动接纳书中所述。哥廷根大学的芭芭拉·沙夫(Barbara Schaff)是文学旅游领域的专家,在她看来,文学旅游的游客也共同参与到作品的创作,这促成了“作者之死”(借用罗兰·巴特1967年发表的著名文章标题)。她认为,国王十字火车站里嵌入墙体的哈利波特行李推车,正是支持“读者具有创造文本能力”这一观点的“重要证据”。
在为摩尼半岛写的游记中,帕特里克·莱斯·弗莫尔爵士(Sir Patrick Leigh Fermor)将冥府入口设置在岬角海岸旁一个泛着磷光的洞穴中。这不重要。在塔纳罗角海湾,森然可怖的密林中隐藏着一处洞穴,洞口高悬,可知此洞颇深。入洞遂见一处死水潭,潭后是个阴湿渗人的凹穴。此中昏暗,看不真切,不知深几许。许是个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