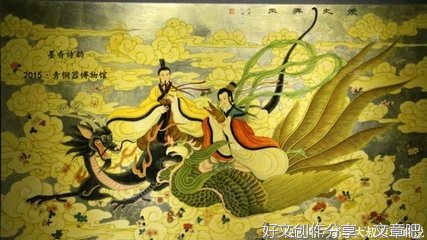《鱼猎》经典读后感有感
《鱼猎》是一本由史迈著作,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32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鱼猎》读后感(一):大概是一篇读后感和一些发散
2022/5/4
前几天我看完了《鱼猎》,是在某个煮泡面的夜晚,这篇文的文笔还行,至少强于绝大多数网文,题材和内容偏现实向,讲了一个女孩为另一个女孩复仇的故事,俞静和何器。我感到悲哀的便是,这个故事太真实了,我相信在很多地方都一直在上演,而这种不能被称作是happy ending的结尾,毕竟何器死了,但总算是把有权有势的凶手送进了监狱。可就是这样的恶人终究会受到法律制裁的结局,现实中怕不是稀有。
读这篇文时,我一直感受到一种恐惧,一种随时会被来自男性的恶意摧毁的恐惧。虽然我已经毕业好多年,我不是中学生,我在中学也没有类似经历。但我相信每一个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体验到相同的感觉,不是说你一定经历了类似事件,而是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凝视和恶意从没有消失过。
社会对于男性的宽容放任,另一面是对于女性成长过程中的打压,性方面的羞辱。一半人口对另一半人口的长达几千年的压迫却成为理所应当的事,这在自诩于现代文明的社会也是个笑话,而这种笑话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连出生都不能被保证的女孩,在成长过程中又会受到多少来自异性的伤害。恃强凌弱是动物的特征,我们之所以需要文明,是因为文明会保护群体里的弱小者不被欺凌。放任自己的欲望伤害他人的人不配为人。
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中,最为低劣的且根深蒂固的为性伤害。强奸是摧毁一个人灵魂的暴行,我一直认为强奸罪应与杀人罪同罪。摧毁人的不仅是肉体的伤害,精神伤害导致的后果甚至更加严重。男性仗着体能优势/身体结构的区别,去威胁,凌辱,谋杀女性的灵魂,甚至以十月怀胎作为威胁,胁迫羞辱女性,枉顾自己也是被女性十月怀胎带到世界上的事实,做出这般卑劣之事,让人愤怒不已。强奸便是谋杀。
何器,一个善良,聪明,勇敢的前途无量的女孩,为了保护自己的朋友,保护更多的女性同胞不受伤害,被她的同学,一个低劣的男性妄图用谋杀灵魂的方式胁迫。是的,才十几岁的未成年男性,就知道怎样去谋杀女性,这是天生的吗?这是这个男权社会教给他的,卑劣的压迫手法。在性别凝视下,她们不是他们的同学,她们是可以被肆意欺凌的物品罢了。
没有冒险故事的主角是女性,没有十分之九的常委是女性,没有对男性的性羞辱,没有说嫁出去的男人泼出去的水。为什么换一个性别就能这么习以为常呢。
鱼猎还让我看见了,被谋杀的女性原本的样子,她是一个善良,聪明,勇敢的前途无量的女孩。而不是出现在新闻里的一句话,一个性别。
一个善良,聪明,勇敢的前途无量的人,被一群卑劣的杀人犯,谋杀了。
无数个善良,聪明,勇敢的前途无量的人,被一群卑劣的杀人犯,谋杀了。
《鱼猎》读后感(二):饱暖思淫欲
7月,北方的一座沿海小城,海浪退去,一具衣冠不整的女尸映入眼眶……
俞家台,俞静正在水产店里玩手机。老俞看到她又是这副模样,气不打一处来,他顺手拿起手中刚打捞起来的鱼往她脸上砸去,俞静瞬间倒地,不省人事……医院求助无果,老俞只能去找会民间巫术的二姑奶请求驱邪。二姑奶举行叫魂仪式后,俞静果然醒来了,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俞静居然说自己是“何器”。她有条不紊地应对着老俞的盘问,从她口中得出的信息以及她的言行举止只能证明:她就是何器!老俞只能联系何器的父亲——何世涛。 “爸,你怎么才来?” 何世涛一脸震惊地看着这个与自己女儿性格一模一样但面庞不同的女孩。 何器说自己要调查自己的死因,要何世涛将事件始末原原本本告诉她。她发现,杀害自己的人竟然是周言阳——自己的高中男朋友。何器前往狱中看望周言阳,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是冤枉的。 她该相信他吗? 在调查的过程中,高中时代的同学与故事一一重现——痛苦浮上心头,往事不堪回首。 有人要挟她,有人隐瞒她,有人畏惧她,有人远离她。 这么多人,谁是凶手? 俞静与何器在高中又经历了什么?
大泉港。何器的父母离婚很久了,她由父亲抚养,何世涛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家自己的饭店,但他现在一贫如洗。何器在高中毕业的聚会后失踪,三天后被人发现了在沙滩上的尸体。警方根据案发现场的线索以及同学杨百聪的证词将周言阳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将他收入监狱。 一切归于风平浪静? 何世涛不知哪里来的钱,开起了饭店,渐渐就忘记了这件事。 直到“何器”复活,风平浪静再度被打破! 周言阳对“何器”说,高中的那个红色密码本上,写的死因居然与何器现实中的死因一模一样! 预言杀人? “何器”知道,她必须重新调查高中那个红色密码本以及它的主人了。
借尸还魂、李代桃僵,案件的真相是怎样的触目惊心? 性侵、校园暴力、重男轻女、拜金主义,直击当下敏感话题!
鱼猎通“ 渔猎 ”,即捕鱼打猎,“今宁安金氏皆圣叹之子孙,其人多以鱼猎为生。”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古代,自然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到了今天,“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鱼列摇身一变,成为了淫欲与贪欲。时代的进步,总是将光明置于青天下,将黑暗掩藏于心灵深处。多少人在时代进步的浪潮下欢笑,多少人在社会角落里哭泣。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办? 应该怎么解决? 希望有一天,所有人都能面带笑意、无忧无虑地奔跑在阳光下。
《鱼猎》读后感(三):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你会不会感到惭愧?因为自己替代他人而活下来? 特别是,死去的那个人比你更慷慨、更敏感、更有用、更聪明、更有活下去的意义?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去年四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和朋友在家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我告诉她,我想好第一本小说要写什么了,我要写一个发生在海边的故事,开头的第一句话是,“冬天的海边很少见到乌鸦了”。
当晚,我回到家里,在《鱼猎》和《受爱者》两个题目之间选了《鱼猎》,在“何器”和“何颂”之间选了一个更有力量的名字“何器”,然后写下了这个故事的核心设定——一个女孩死了,另一个女孩要“成为”她,两个人因为信任和默契而完成了一场复仇。
这些就是正式落笔之前确定下来的东西,其他的一切都是未知。
接下来的几个月,伴随着北京变幻莫测的天气,我往返于出租屋和望京一家营业到深夜的咖啡馆,在朋友们的鼓励和“威胁”下,卡着豆瓣阅读拉力赛的连载死线,有惊无险地完成了这个故事。
一年后的今天,我脑海中那场盛大悲壮的“火烧云”变成了这本书的封面,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像一块燃烧的甲板。
回忆整个创作过程,我首先想起的,是我贴在墙上的两张绿色便签纸。一张是网上看到的一句话——“性暴力伤势反复绵延,绝不是快准狠的一次事件,而是长久的无视与麻木”;另一张是波伏娃的名言——“男人之间的友谊大多建立在他们的兴趣爱好之上,而女人的友谊是因为她们处在共同的命运之中。”
这两句话带给了我很多灵感,也是我在一开始找到的两座灯塔。每当我又一次陷入自我怀疑,质问自己“写这个故事究竟有什么意义”的时候,这两座灯塔的微光就会穿过海雾,提醒我写这个故事的初衷——我想写的何器不是一个“被害死”的少女符号,而是一个想要活下去、应该活下去、需要活下去的人。俞静要追问的,也绝不仅仅是那一晚上的真相,而是在她们漫长的成长过程中,那些本不应该发生、却一次次毁掉她们的瞬间。
在写作初期,一种愤怒而悲伤的情绪始终笼罩着我,因为在“何器”的身上,叠加了太多现实中女孩的身影,她们大多面目模糊,在无数个看似安全的地方——厨房、教室、烧烤店、繁华的大街、飞驰的车上、摘百香果的路上——失去生命。就像在《鱼猎》的最后,俞静总是忍不住想象那个有何器的世界会是什么样,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我也总会忍不住想象,如果那些女孩没有死,她们接下来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她们可以开口说话,她们会说些什么?
然而,现实中不会等到答案,但故事可以。完成这个追问,也是我写作这个故事最大的动力。
尽管我喜欢悬疑故事,但我并不着迷于残酷的叙事,相反,书写那些黑暗暴力的桥段是最让我感到痛苦的部分。我需要关上门,戴上耳塞,手指放在键盘上,强迫自己去代入和回忆那些曾让我感受过恐惧的时刻,那些被封存的无助和被遗忘的怒意,我必须先“成为”她们,才有资格开口说话。
写作《鱼猎》的那段时间,我正陷入巨大的人生低谷,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写作,是这个故事还有它带来的一些奇迹把我一次次打捞上岸。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愈合的过程。
写完「番外」的那个下午,我从咖啡馆走出来,在家附近的一条河边溜达了很久。刚下完雨,路灯还没有亮起,阳光把墨绿色的水面照得金灿灿的,我觉得异常释然和平静。俞静完成了何器交给她的任务,我也完成了这个故事的使命。
林奕含在最后一次采访时说道,“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屠杀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而是房思琪式的强暴。”这句话深深震撼过我,所以当我看到那本写奥斯维辛的书籍《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时,书里那句话也与我想表达的主题精密咬合。
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代替他人而活了下来。
被淹没的“何器们”再也没有机会说话了,但是留下了一些火种,而被拯救的我们,要替她们活下来,替她们发声,用不同的形式留下印记,并且永远不要遗忘。
我希望大家看完这个故事,记住的不是悲伤,而是勇气。合上书,在深不见底的海面上,是一场无边无际的火烧云,尽管她们再也看不到了,但是我们可以。
希望有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享受这些而不必感到抱歉。
史迈 2022年7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