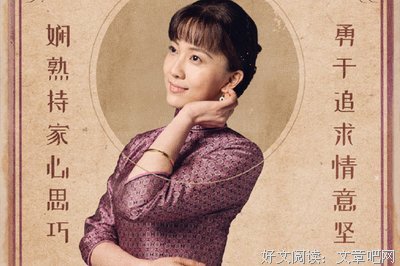压在心头的愧疚念想
最近一次乘公交车,刚上车,一位只有十几岁的小男孩立即给我让了个座位。
他后背背了个沉重的书包。经问,是个在本市省重点中学读书的学生。“谢谢你,小朋友!”我说。他说,“不用谢,应该的。”我祝他将来能考上重点大学,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他微笑着点点头,红着小圆脸回应:“爷爷,我记住了!”我想,在当时,我只能这样对他给我让座表示如此感激之情了,我为自己及时回应人家的好处感到欣慰。
一次,我参加某白酒订货会。按照常规,中午12点钟前到达会场也不耽误抽奖、聚餐。但这次破例提前开了席。楼上楼下所有的大厅和包间都坐满了,而且已经近乎杯盘狼藉。
我在一个大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位坐下来,会友提醒我,你得先去把抽奖卡放进抽奖箱以便抽奖。于是我起身去到另一个大厅投放抽奖卡。谁知,有一位比我来得还晚的会友正想坐我那位子,同桌子的人便不让他坐,说这里有人,他去放抽奖卡去了,马上就回来。他们正说着,见我到了,那人很知趣地另找座位去了。
试想,如果同桌的人对我不负责任,任凭后来人坐了我的位子,也实属正常,因为素不相识嘛,人家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为你保住这个位子。于是,我便很感激在座的桌友,吃饭时一再站起来举杯,虔诚地向这些为我“护位”的桌友表示感谢,不禁心中极为安然。
这两宗小事,虽然过去一年多了,但却不时地在我脑海里浮现、萦绕,让我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由此让我想起了我在部队时有恩于我的两个人。一个是指导员季元府。我在汽车教导队学开车的时候,季指导员特别关心爱护我,有意识地培养锻炼我增长一些各方面的知识,让我在实践中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升,并且还介绍我入了党。
据战友们说,汽车教导队是个临时的单位,能在这里入党,之前之后几乎没有过,所以我很感激季指导员。另一个是带兵的人,当年我当兵体检的时候,是在冬季,不知什么原因,血压有点偏高(也许是激动的吧),那位带兵的年轻解放军军官总是站在我身边,似乎是在和医生“通融”,让他说出像这样的血压是可以当兵的话来,好像医生坚持了原则,始终没被“通融”通。
于是,他就把我一次次地带到凛冽的室外寒风中,让我捋开胳臂,试图让刺骨的寒风把这高出部分的血压“冻”回去。你还别说,最终我的血压真的回到了正常的范围,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绿色的军装,当上了一名人人羡慕的解放军战士。
但就是这样的好心人,我却因为年轻懵懂,当时并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感恩意识,以至于造成终生的遗憾:从汽车教导队结业回到原单位团部小车驾驶班,却不知季指导员是仍在教导队呢,还是到了其他什么单位?从此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
那位带兵的人,我到部队后,就一直没见过他,也没想起来打听一下他在哪个单位,甚至连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
想起这两个人,是最近在战友群聊天时的事情。一些失联几十年的战友,通过微信聊天都取得了联系。我便强烈地萌发了通过微信聊天,寻找我的入党介绍人季指导员和千方百计执意带我到部队的人的念想。
让我失望的是,群友们有的说认识,有的说不认识,但是即使认识他俩的,也都不知道现在在什么地方,人生境况如何?这让我失望至极,让我无法对他俩表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感激之情。而留存在心中的都是满满的愧疚和惆怅。
行文至此,倏然地想起了孔圣人说过的一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意思是说,当你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时,父母却已不在人世了,要让人们在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及时行孝,不留遗憾。我觉得这句话在家庭之外关系的人群中也同样适用。
人生在世与人接触,总会遇到一些有恩于自己的好人,即使你在他人身上所得到的哪怕是点滴的恩惠,也要适时地去实施报答,并将他们的恩惠永远地铭记在心。不然,同样会留下心理上难以弥合的缕缕伤痕,以致于成为终生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