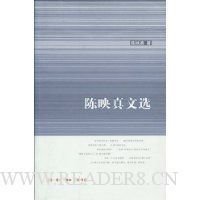《陈映真自选集》读后感1000字
《陈映真自选集》是一本由陈映真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其他图书,本书定价:31.00元,页数:45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陈映真自选集》精选点评:
●“他的形容傲慢、犬儒的心,逐渐在溶解。他忽然说,‘喂,你可知道,这是头一次,有人为我过生日’”——《夜行货车》
●中短篇小说集,《赵南栋》挺不错的。
●很好的作品,有新意
●一千零一夜
●(夜)爱国马克思主义者赵南栋
●难以理解的文字 但是不愧为大家
●不太适应这种有些古老的文风,但还是被《将军族》打动了,现在的人是否已经写不出这种真的感觉了呢?
●现代主义很强烈。最近喜欢台湾文学。
●陈先生的中篇都好
●看来看去还是《将军族》。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作。早期作品具有浓重的五四遗风。
《陈映真自选集》读后感(一):又寂寞又温暖
陈映真的书在内地真的不好找,还好三联书店出了一套他的自选集,封面虽然怪异,排版也中规中矩,但内容可算经典,值得收藏。
一本厚厚的书足足看了半个多月,午休值班的时候看,下课的时候看,开会的时候偷偷看,前半部分看的意兴阑珊,断断续续的,尤其备受好评的《我的弟弟康雄》,那样晦涩难懂的文字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里所隐藏的巨大含义,我无法解读出来更无法体会,所以于我也只是白扯。
但《将军族》又搭对了我的脉,虽然依然带着五四时期的浅白文风,偶尔觉得文字拖泥带水不够利落,但是人物写得真的好,轻轻点点的两句白描,内心感情便表露无遗,一个是流落台湾的外省人,一个是被家人卖给妓寨后出逃的小姑娘,没有爱情,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陈映真是悲观主义者(或许理想主义者都悲观吧)以为历经千山万水的苦难后意外重逢会有温暖的结局,结果只是为了来世的“干净”,这世便双双自杀。
接下来的几篇关于夏日关于文学流派我看的又心不在焉,陈写社会精英就是难打动人啊。
从《铃铛花》开始又欣喜不已,结果由于太投入数度哽咽,尤其在自习课上看的时候眼圈发红,面对台下写作业的学生,实在难为情。而到了《赵南栋》简直是感情失控,哭得稀里哗啦,尤其我一看到“小芭乐子”这样的字眼便条件反射似的泪不能已。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你做了妈妈了,受不了骨肉分离的惨别。
作为亲历台湾二二八以后时期的戒严社会,甚至为此坐牢的陈映真,他写遭受白色恐怖迫害的人物更加的清醒,相对大陆的所谓伤痕文学来说。
更注重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写,写她们的母爱,他们的友爱,即使那些家国情怀也是知识分子的忧心忡忡,不是我们主旋律电视剧里的那般狗血。
没有什么表现身体痛苦,心灵折磨的文字,更没有什么大段的心理描写,都是白描性的简洁文字,天上漂浮的云,流了一夜的泪,都已说尽。
“那堙远的、荒芜的五十年代,在那天神都无从企及的,一个噤抑的角落里,日日梭巡于生死之际。”
wenge更是。
以前看汪曾祺去美国做访问交流期间给施松卿的家书中提及陈映真,应该算是陌生人吧。两人讲到动情处,流泪,分别拥抱再流泪。真是性情中人,也觉可爱。
《陈映真自选集》读后感(二):如果这是左翼,那就左翼吧
我感到惭愧。
一个从小学开始课表上就有“品德课”,到现在上大学已经快上满五节“思想教育课”,在这样社会中存在的我,居然在近几天才听说了这一种关于“左翼”的定义。
左翼是什么?右翼又是什么?
我不清楚,如果要两周前的我来说,我会讲:左翼就是激进、革命和倾苏共国际,右翼是主张民主、自由、资本。这样一个估计任何一个学者都会发笑的模糊的概念。
间或地读过一些描写文革的句子,间或地度过一些建国初期的鬼魅般不知真假的“史实”,还有我以为被删减了太多、意识形态太多以至于缺乏最基本的思辨能力的历史课本和“马克思主义”课本。
上过美国大学的一些讲正义,讲心理学的课,或者是关于贫困的调查的书。感觉美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另一套世界观,另一群人,趋于一个更高水平的社会的平衡。
“左翼”和“右翼”,我模糊地感觉,在国内国外是有两种定义的。因为我切实地察觉到,好似欧美,右翼是保守,左翼是激进。
所以我有时甚至不能理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含义。
我并不想用“左翼文学”来描述陈映真老师的文章。我认为这些标签本身是为了适应读者心中一种隐隐约约的分类。如果非要分类,我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写作。
关注宏大的叙述背景下个体的悲哀——我一直以为这是文学跳动的灵魂
反“资”么?
我并没有深切读到。我认为陈映真老师笔下的人形,都是一群真实的普通人,和我们一样,拥有相同的“民族性”这种长期传承下的东西,拥有瘦弱的“公民体质”,和我们不同的不过是在不同的处境下。
就像饼干套上什么模子,始终都要受到机器的巨大的挤压和社会的火辣般的烘烤。
我不敢断言,但我怀疑,如果陈映真老师在当年的文革的漩涡中,这样成长起来,作品说不定就被称为反社了呢。
不,如果非要套壳子,我会说这是批判现实主义,让我们把视角从GDP的宏观增长,让我们把目光从欣欣向荣的跨国企业上收敛回来,用放大镜看看支援着这一切的微小的人。
最近看的作品好像都有这个趋向。
从《生活与命运》到《是,大臣》,从《娱乐至死》到《野火集》,从《重说中国近代史》到《陈映真自选集》......
若是在三周前,我会对把左翼这个名牌挂在我身上的人翻白眼,但是我越发地感觉,若陈映真老师这种叙事视角,被称为左翼的话,那么这个用于简化的标签贴上也无妨了。
近期因为写作需要的原因,断断续续地在迫切地了解关于公司内部运营的知识,以及矛盾中惯用的伎俩。理由是我一贯的借口,为了写东西要多了解些世事啊,宽慰自己的话是一贯的,满足好奇心,多了解点东西对我对整个世界的了解就会多一分,写作时对整个社会的描述也更好些。读到《华盛顿大楼之三》时,忍不住拍案叫绝,忍不住感谢已经不在人世的陈映真老师,他的描写太真实了,他要花多少功夫去问具体的人?感知具体的事?才能写出如此真实的刻画啊!
《陈映真自选集》读后感(三):几篇小说的笔记(《我的弟弟康雄》《将军族》《凄惨无言的嘴》《一绿色候鸟》)
《我的弟弟康雄》
“旷野里开满了一片白绵绵的芦花。乌鸦像箭一般地刺穿着灰色的天空。走下坟场,我回首望了望我的弟弟康雄的新居:新翻的土,新的墓碑,很是丑恶的!于是又一只乌鸦像箭一般地刺穿紫灰色的天空里了。”这一段话中,白色芦花、丑恶的新坟、倏飞的乌鸦,这几种意象,在《药》最后一部分中也都是出现的了。意思上,当然不如《药》丰富,也不能与《药》做同解。
小说中大概有不同的几种人生:“我”、康雄、父亲、长头发的画家、丈夫/公公(或约上等人)。其中,对“我”的描写是直接的,对其他的几位则主要通过“我”的观察。康雄的有生而死的轨迹,正如三本日记展示的那样:思春的苦恼、乌托邦理想、理想破灭后的虚无、等待而宗教救赎直至死亡。对此,“我”的理解是“……少年虚无者乃是死在一个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我”的转变同样重要,此外还有“父亲”。
这篇小说,大概能在思想上对当时的知识分子造成冲击。
《将军族》
好处在于,最细致而全面的的刻画了两个人——“三角眼”和“小瘦丫头”。
两处高潮,一是给钱,二是自杀。给钱,是“三角眼”的自我救赎,所以“绝不是心疼那些退伍金”。这不是空穴来风的,前面有所铺垫;关于思乡的故事、他的觉得自己老了、她的弱小激发了他的同情。二是自杀。到再一次相见,“瘦丫头”已经能够领会“三角眼”的情义,她自知无以为报,而之前说嫁给她只是玩笑话,到这时自然是心甘情愿,只是“身子已经不干净了,不行了”,那么,对于她来说,自杀是一种自我净化。她说的“还钱是其次,我要告诉你我终于领会了”,其意思应当是“如果有必要,牺牲自我,成全他人乃是大的爱”。另一方面,在“三角眼”那里,之前他说“老婆有了女儿,大约也就是这个年纪罢”,而再次见面,是“他的母亲便曾类似这样笑过”。再次的会面对于他来说,本来应是怀有一些希望的。既然,两人都为对方做出了牺牲——他让渡微博的退休金,她为获得报答他的机会,而卖身——而又能真的再次相见,应该有一种继续走下去的可能。但陈映真决意让他们去死,所以有了以下的对话:“下一辈子罢!”他说:“此生此世,仿佛有一股力量把我们推向悲惨、羞耻和破败……”远远地响起了一片选填的乐声。他看看表,正是丧家出殡的时候。伊说:“正对,下一辈子罢。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
或许,不死不足以强化批判的力度吧。或许,吕正惠老师所不满的陈映真将知识分子的命运和情感投射到底层小人物的原因之一吧。或许,所有的故事都发生着,但是不包括给钱,也不包括自杀。温暖的东西或许存在,但没那么“浪漫”,尽管是自我牺牲和向死而生。
《凄惨无言的嘴》
首先,被杀雏妓的刀创引发了“我”对莎翁之关于凯撒诗句的回想,继而才有那奇怪的梦。在梦里,有每样东西都长了长霉的黑屋并一女子,她的身上无数个嘴说着“打开窗子,让阳光照进来罢”。这句话,原却是歌德临死的时候所说的。然后,一罗马勇士(在见到被杀的雏妓之前,也见到了有匀称有力小腿的工人)划破了黑暗,最后霉菌及一切坏事物都死,而“我也枯死了”。不难发现,这勇士随着“我”的讲述,变成了我。
模仿鲁迅的地方就不用多说了,精神病人,黑房子,同归于尽之于“铁屋中的呐喊”,病好之后,而又忘记一切之于《狂人日记》。但这都是外在的技巧性的使用,陈映真想处理的问题与鲁迅不同,这是由他的人生经验所决定。那个精神病院的信基督的同龄医生、高小姐、作为群像的其他精神病人、健硕的工人、雏妓的尸体、一心去美国的同学,这些形象显示了陈映真对于小说主题所寄予的庞大野心。考虑到我的病之由来与编号与上述一切有关,那么考究一下会比较有意思。
《一绿色候鸟》
按吕正惠的说法,这是现代主义的小说,主题是知识分子的失落感。
候鸟自然是有强烈的象征意味的。小说中三个教授的婚姻(我、赵教授和季教授)到了末,都呈现悲剧的色彩。先是候鸟的出现,似乎对于季夫人的病有缓解,但很快的急转,以至于死掉了。因了这个死,于是又季教授的恸哭,而赵教授终于和我说起了自己的情感经历并为之自耻,进而老年痴呆了,同时我的妻子也在季夫人死后变得无比忧伤,竟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去世了。再后来,我见到了季先生与他的儿子,也发现妻子死去的那天正好是候鸟消失的日子,而且也有感于季教授家的竹子花开得太茂盛了。
以写实而言,有些情节似乎不是特别的合理,尤其是赵教授的痴呆和妻子的死,但小说之前后却也都有铺垫。具体而言,三个教授的婚姻,都谈不上圆满:我对妻抱有介怀、赵教授玩世不恭伤害他人、季教授之婚姻则为俗世所指摘,他们仨的妻子或情人,命运更以心死或身死而告终。
出路何在?大约在后来人了,所以文末有季教授对于儿子的期望:“不要像我,也不要像他的母亲罢。……。然而他却要不同,他要有新新的,活跃的生命。”这一段话,不但意思,连语气也与《故乡》中,鲁迅对于宏儿与水生的期望有相同。
写在后面:陈映真的笔下有一个我们大陆人知道不多的台湾,他的小说值得每一位有兴趣的读者去阅读。台湾的吕正惠和赵刚两位教授,都有关于陈映真的很好的文章,尤其是赵刚教授,几乎有对所有陈映真小说的细读,非常好看。事实上,赵刚几乎做出了完整的解释。自己的这个笔记,也就当做关于阅读的回忆吧?或许,会有阅读的友谊?
《陈映真自选集》读后感(四):一曲忧郁而雄壮的时代悲歌
詹宏志说他是“文学的思考者”,南方朔称他为“最后的乌托邦主义者”,蓝博洲笑谈,“陈映真就是我的一个阴影。如果没有他,我尽可以赚钱去、快乐去、堕落去……可是不行,他就在那里。”
1959年以小说《面摊》出道以来,陈映真的文字伴随着一代代读者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旅程。他用文字来参与政治,用笔刀来改造社会。“荷戟独行的战士”、“孤独的风中之旗”、“台湾的良心”……评论家和读者用这些林林总总的称谓表达对陈映真的敬意。我愿把他比作一曲忧郁而雄壮的时代悲歌,曲调悲凉,却慷慨激昂、恢弘大气。虽颇有曲高和寡之意,但静而思之,其意之高远,境之深邃,那种真诚、那种力量、那种执着,将在历史长河中化作永恒。
一. 台湾/中国
“这种只产于北地冰寒的候鸟,是绝不惯于像此地这样的气候的,它之将萎枯以至于死,是定然吧。”
——陈映真《一绿色之候鸟》
如同小说里那绿色之候鸟可预见的难以逃脱的宿命,来台湾生活的大陆人身上镌刻着现代中国最剧烈的阵痛。1962年,在军中服役的陈映真真切地接触到外省士官的痛苦和悲戚,他“深入体会了内战和民族分裂的历史对于大陆农民出身的老士官们残酷的拨弄” 。其实,早在幼年间,陈映真即感受过内战带来的惧怖与创伤——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的老师,被人打在地上呻吟的外省客商,住在后院被人带走的外省人陆家兄妹……陈映真在创作中发泄来自内心深处的愤懑与焦虑。他早期的作品里浸透着忧虑与腐臭的气息。
1975年,陈映真出狱。随即而来的是乡土文学论战的高潮。此时的他“已不再是以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主观内省的心态观察现实与剖析社会,而是怀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去思考各种社会矛盾” 。陈映真把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归因于帝国主义的干涉。二十年代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旧文学的斗争,三十年代初的第一次乡土文学论争、三十年代台湾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和文学运动,“都是作为帝国主义从中国割让出去的台湾对帝国主义和与之相为依存的封建主义,在文学领域进行斗争的文学。” 在他的笔下,小说《夜行货车》中,女主人公刘小玲在爱情摇摆中最终选择的詹奕宏勇敢地对美国说“不”。
陈映真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在一系列的社会思潮论争中,“中国人”的认同是他最清晰而坚定的立场。我想,陈映真最想成为的,当是他自己浓墨重彩地书写过的那一类人,“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籍不分大陆本省,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 。
二. 物质/精神
“没有杨伯良、荣将军,没有腐败的阴谋、没有对于副经理的那黑色的假皮的座椅的贪欲,生活会有多么的不同啊。他沉默地想着。”
——陈映真 《上班族的一日》
在小说《上班族的一日》中,已下定决心追随本心重拾自己电影梦想的黄静熊终究心甘情愿地回到公司继续那“一个大大的骗局” 般的上班族生活。陈映真毫不掩饰自己对物欲的鄙夷,他的笔触直指台湾资本主义化过程中人性的异化和堕落。1983年,《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和《万商帝君》定名为《华盛顿大楼》(第一部)结集出版。在这四篇小说中,陈映真无情地披露跨国资本自由民主的假面,鞭辟入里地解剖在财富和舒适中被扭曲的人性。这些文字,无论何人在何时何地读到,都会觉得触目惊心。其意义与影响,已远非文学自身的价值所能覆盖。
八十年代的台湾,经济的发展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在全球化的浪潮里,在一片自由民主的声浪下,缺少的是对种种困境的尖锐质问,对消费时代的理性思考。在周围自私虚伪冷酷卑鄙的包围中,陈映真从未丢掉那颗真诚、火热的赤子之心。他的视野不仅仅局限在台湾,如王安忆所言,“一个人在岛上,也是可以胸怀世界的。”陈映真思考的,是个人的尊严,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命运。他要干预现实。他觉得愚昧的、不公的、丧失个人人格和民族气节的行径,他就要抗议,大声疾呼。
但消费和享乐的欲望还是席卷了整个中国,从台湾到大陆。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子就说“人为物役”。人生价值的实现,其实离不开欲望、金钱、权力。这正是陈映真的悲剧性之所在——他不能放弃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但他终究无法以一己之力战胜世俗的一切丑恶。他只能如同鲁迅诗中所写一般,“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三. 理想/现实
“我不是说了吗?回来了,好。可是你找不到你的角色,你懂吧。整出戏里,没有你的词,哈!”
——陈映真 《赵南栋》
小说《赵南栋》中,赵庆云、叶春美他们走出监牢之后发现自己成为了“浦岛太郎”,有一种“跳接到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的苦恼” 。他们面对崭新的社会,不知所以,唯有沉默,在沉默中回味过去。“过去的经历既是赵庆云们沉重的历史负担,使他们被阻隔在现社会之外,成为零余者;另一方面,这段逝去的炼狱生活又是他们弥足珍贵的精神宝藏,是他们慰藉衰颓老年的精神补品。” 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左翼运动经历着世界范围内的落潮。我不知道,身处彼时的陈映真,会不会像赵庆云们一样,在历史的进程前,满是艰涩心酸的无力感?
作家刘继明在《走近陈映真》一文中讲述了陈映真对阿城关于“人民”的解释勃然大怒以及听完张贤亮的“污染论”要与之辩论的两则看起来笑话一般的轶事。这并不难理解。是时,大陆文学界莫不以巨大的热忱反思文革,与国际接轨,他们最嗤之以鼻的反抗压迫、阶级斗争正是陈映真所固守和坚持的。于是,陈映真之于大陆,仿佛就成为了赵庆云们之于赵南栋。后者体会不了前者理想主义的壮怀激烈,前者更难以理解后者的纸醉金迷。陈映真的尴尬,不是造化弄人又是什么呢?
然而毋庸置疑,这个时代需要陈映真。他那继承自五四以降左翼文学对社会现实细致入微的观察,对黑暗丑恶不遗余力的鞭挞,在信仰迷失、价值混乱的当下显得弥足珍贵。文革之后,出于对政治的恐惧,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对政治唯恐避之不及的趋势,“越是远离政治和现实生活,就越是具有文学性” 。而与此相伴的,是文学影响力的不断下降,像《红岩》能够突破1000万册的发行量几乎成为天方夜谭。究其原因,撇开政治与现实的企图和追求纯粹文学的目标恐怕难辞其咎。
可惜,陈映真只有一个。他是孤独的,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但是他选择坚守,坚守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家国命运的注视。他的孤独,是先行者的孤独,是革命者的孤独。
在小说《赵南栋》的结尾,叶春美“费力地扶着瘦弱、一身臭汗、神志不清的赵南栋” ,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作者暗示耽溺在肉欲与物欲中的精神迷乱者最终回到了前辈的怀抱。而陈映真本人,是不是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小芭乐呢?
我想一定会的。那一曲忧郁而雄壮的悲歌,定会绵延不绝地激荡着,在台湾的上空,也在大陆的上空。或许它没有多么响亮,但那洁净的声音永远不会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