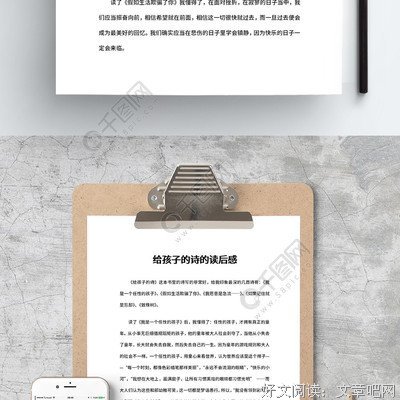《诗之旅》读后感100字
《诗之旅》是一本由[美] 高居翰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1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诗之旅》精选点评:
●中外对文人画的评价还是无法统一。还是很难理解诗意画。马老师说是抒情的漫游梗贴切。
●基本上是綜合許多他人研究的一個大雜燴,從宋體院畫、晚明吳派一直東渡至日本南畫
●机械而不解中国文化之偏见解读
●个人看来,明清的文人绘画无论在观赏性或是骚客们追求的诗意表达都不如宋代院体画家们的创作甚矣。那种柔美的用色以及朦胧的退晕都足以让人沉醉在这技法的使用上。关于技法与风格的讨论让人联想起帕慕克的杰作《我的名字是红》里的表达。
●西方的美术史研究和中国的画论果然是十分不同的东西。这种不受中国传统评价体系和序列的影响,对院画家纯粹的绘画技巧进行肯定、鄙夷文人画缺乏技巧和再现能力的观点,的确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对吴门画派的轻蔑似乎有点极端了)。尽管高居翰对“诗意绘画”的内涵一再做了比较明晰的界定,但作为中国人,对“诗意”和激发“诗意”感受的过程的理解与他抵牾较多。而且,我觉得他解释中国晚明后山水画失去诗意的原因和解释芜村的成就的机制不大一样。。
●为院画一脉正名之作。立论看似标新立异,实则具体论述并不见新颖之处。In a lot of cases claim (judgment) rather than analysis.
●薄弱,诗意画概念的提出是想突破院画与文人的二元对立,但过于玄妙,仅凭此书暂时立不起来,对与谢芜村的解读也不够充分。
●思路发散的厉害,主题不清楚,论证不客观,论点不新鲜,也不算有颠覆性,所以时有故作惊人之语的感觉。关键问题语焉不详,史料比重远大于论述,照理只值3,但看在图多,时不时有有价值的段落冒出的份上打个4吧。
●翻译得太绕口,图片质量也下降了。
●南宋的杭州,晚明的苏州和江户时期的日本,图片多,质感好,艺术鉴赏类的好书
《诗之旅》读后感(一):整体
1. 在画上题诗和画的诗意是两回事。
2. 唐代将诗意文化推向巅峰,为宋代画的诗意埋下伏笔。
3. “人们能够在他们的画面上自由走动,有时面对作为一个单元的整片山景或树林,有时走到一个封闭的景观,那里有无限丰富的细节供人探寻发现。这个移动阅读的方式,像是接近真实景物的视觉经历,仿佛有身临画中的感受,唤起观者记忆中相似体验的共鸣。”现代人缺少山水中的相似体验,所以难以产生共鸣。
4. 技巧并不与诗意相悖,从宋画来看,技巧不仅不会阻碍诗意的表达,反而会帮助诗意的表达。
5. 宋代花鸟画和风景画的兴起是否与西方的风景画、静物画一样,也与市民阶层的兴起,对室内装饰的需求紧密相关。
6. “宋代院画家典型的采用了非个人化的声音,在他们的绘画中,不会非常清晰的表现个人手笔;相反,他们有意将自我隐去,创造了一个并不占有它的世界。在这一点上,他和文征明及其他文人画家不同,后者以很个性化的笔记和对个人关怀的昭示,在其创作的世界中,表明他们的存在。”
7. “一个农夫在寒冬中走近他河边的屋舍……夏珪用同样这个题材表示“回归到那些本质而自然的东西””
8. “山水画是为满足那些……因为家国之事而滞留城市的人而作。”
9. “把观众吸引到不确定的,暗示性的,未完成的叙述中。”
10. 中国画把空气透视法用的很绝。
11. “在宋亡之后,急骤转向以笔法为主得审美观认为,如果不在画中展现出画家的书法修养,就像在赵孟頫的画中表现得那样,就不能为艺术鉴赏提供重要得依据。”(书法入画为画带来表现形式的更多可能,但并不应是必须项)
12. “他们以减少作品中的变化,提高欣赏这类作品所需的鉴赏水平……我们被喋喋不休地告知,看画应当是看笔法,而不是看景物的描绘。……以区分微妙变化来指代一种更高层次的鉴赏形式,在我看来是颇为荒谬的。……如此限制内容的变化,必定要使艺术枯竭……并非因为难于欣赏就意味着它们一定比别的画好。“(陶瓷、京剧……中国很多艺术形式都是这样的方式发展)
13. “是张宏和苏州画家,而不是同时代的文人业余画家,最好的实现了诗歌的理想:如所见一般的描绘景物,通过活生生的个体,而不是对过去诗文的引述,来对景物作出回应。“
《诗之旅》读后感(二):看懂一本书与看懂一幅画
我坦白,这是一本专业方面的专题研究报告,于我这种缺乏基本知识完全靠感觉的外行而言,不容易看懂。其实这是我看过的该作者的第三本书,之前的两本,多少有点走马观花离手即忘的意思。几个月前接触到“康奈尔笔记法”,依循这种笔记法开始“写”笔记 (真的是用钢笔写),果然这本书收获稍多一点点。至于所谓“康奈尔笔记法“,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
为什么扯来高教授(其实他并不姓“高”,不过淘气一下)的书看?因为前年在纽约MET错过了很多精彩的中国书画藏品,回想起来我大约就只在韩干的《照夜白》前驻足片刻,其他都是一扫而过。一扫而过但有点印象的是八大山人的三幅条幅,心里当时就在想“他画的是个啥呀?”。后来接触到三联关于MET中国书画藏品的专刊,很是羞愧,中国人看不懂中国画!
至于为何非拉扯高教授的书,而不去看中国的传统高论。事实是中国的传统高论我也买了,只是没看完。另一方面,我个人特别喜欢高教授这种跨文化的学者写出来的东西,有一种“不在此山中”的妙趣。
高教授在这本书里掰扯一个概念,叫做“诗意画”,不知道这个概念在国内的理论里有没有,但是在高教授的语境里,我还是认同它的存在。如果以文体来比拟画作,中国大量的古画作,尤其是山水画作,确实都特别像中国的诗词,凝练,高简,给读者、看客留下更多感受和发挥的空间,美不是一种丰满或者酣畅的美,有更多克制甚至隐晦,使得其中的深意非俗人可悟。
所以我这个俗人看不懂,是正常的。
在此书中,高教授详细剖析了三个历史时空,一个是南宋之杭州,一个是晚明之苏州,还有一个是江户时代的日本。 宫廷画师在北宋已有,绘画作为一种社会性表达,甚至跟政治撕扯不清。到南宋所谓院体画的繁荣,画家这种身份逐渐单独确立,有他们特定的受众,并以唐宋的诗词为营养,在诗意画上有所建树和突破。然而元朝起文人画对院体画的否定,认为基于市场或者权势需求而作画,且在文学方面没有深刻理解的专业画家的作品格调低下,不值一提,最终成为一个源远流长的主流看法。高教授作为非此山中人,不为所谓主流思想所拘束,认为专业画师的作品,即便在詩意畫這個領域亦有其重要的价值,不應與文人畫有高下之分,这是他这本书主要想表达的观点之一。
瞥一眼西方美术史,且看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家作品,少有孤清的文士之作,大把的是富商、权贵和教会供养的艺术家的作品,其中亦不乏各种立意明確的委托作品。至于说立意之雅俗,让我想起有一次在奥克兰艺术馆看的一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展,其中一幅作品就是艺术家为供养者全家作画,畫中凡人为天使所环绕赐福,试图以艺术形式使商人出身的供养者身份神圣化,這樣的立意在我们看来,簡直俗出天際无法更俗,然而也不過是人家的尋常操作。
主觀地以身份论高下,确实有歧视的意味,此文人有所长,彼画师有所短,倒是完全可能存在的客观情况。所以高教授的争辩,我愿意从积极的意义去看,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观点。
《诗之旅》读后感(三):诗意画:可视的诗篇与想象
在一个诗歌创作及作品如此满盛的国度里,诗意之浓郁竟然像漫过缸沿的水,潺潺越过了诗歌的边界,逐渐侵染到了绘画的领域里。二者矫揉在一起,便交杂出了诗意画——中国绘画诸多画种中最奇异的一种变体。人们常以“诗情画意”来表达美景不可言说之妙,不管是袁枚形容的“放棹西湖发浩歌,诗情画意两如何”,还是毛祥麟《墨余录》中所说“诗情画意;尚可言传;惟此一片深情;当于言外领味”,都极具画面感。如诗也如画,竟成了从艺者和观艺者衡量艺术创作丰腴意境的一杆美学标尺。
中国的诗词因为汉字的声、形之特点天生具有音律和气度之美,诵之,字字珠玑;默想之,心生兰香。相信许多文人在提笔写诗作词时胸中早已铺开了一幅卷轴,所以,他笔下的文字才充满了栩栩画意。比如宋代词人周密一阕《清平乐•横玉亭秋倚》“诗情画意,只在阑杆外,雨露天低生爽气,一片吴山越水。”短短二十多字,便将吴越胜地的玲珑山河之美点润开来,令人仿佛身临其境,如览画中。
如果诗歌表现的是凝练、含蓄的画意,那么,在文字之美的启发下,许多画家纷纷以手中画笔将诗歌的内容和意境用可视的绘画元素充分的表现出来,就令这内蕴的画意更加丰满和厚实。难怪有人作此形容,“画如无声诗,诗如无声画”,何等精确地点明了两者之间相互转化、互为补充的辩证联系。
高居翰用他的《诗之旅》,以诗和画为双桨,一下下的翻飞,似乎激起了我们幽幽的怀古之情。这是一趟艺术之旅,也是一次心灵之旅。作为观念和实践的中国诗意画虽起步于北宋,可能高居翰觉得北宋太刚烈,便将始发站放在了南宋的杭州,大抵偏安于临安的这个没落王朝,浑身上下的靡靡之风才最贴合诗意画的风骨。更重要的是著名的皇帝艺术家宋徽宗以皇家的浩荡王权以及个人强烈的艺术感强力推动着诗意画的发展,不仅在宫廷画院里建立了“作画要有诗意”的制度化的理念,还在招募画师时严格考察其是否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因此,这一时期的诗意画(院体画)皆充盈着强烈的欲语还休、意犹未尽、迟暮和失落之感,多半暗示的是欢乐的消失以及始终处于含苞待放状态的欢愉感,这与朝中上下里外洋溢的精致而脆弱的末世感倒是十分符合。
及到两百多年后的晚明,封建制度虽已日暮西山,然而,统治者们仍然苟延残喘地打造出了世界上一个伟大的中华帝国,作为富庶之地的苏州集财聚富,人们已有雄厚的财力和文化底蕴来欣赏和创作诗歌,将其视为上流社会的高雅标志,在这样的环境里,流行以诗为题的绘画同样成了文人墨客钟情的一种风雅。
在高居翰看来,后期中国绘画批判观念过于严苛和死板,使得画家们的题材和风格越发狭窄,同样,诗意画的发展也陷入到一个逼仄的境地,日渐势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是令人感到吊诡的是,近邻日本的画家因为宽松的文艺评论的环境而获得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因此,发端于中国的诗意画被引入东瀛,在江户时代得以再次复兴,以谢芜村为代表的日本画家们在对中国的古典样板的摹仿中注入了更多本国元素。就连这些变形的诗意画的用途也仿效中国,被受画者买来,用作新年、寿辰、生子等重大场合的礼物。
诗意画是对诗歌所做的图解和二次创作,它不仅暗含和传递着诗人和画家的情感体验,并且洋溢着由此而激起的诗情。在中国艺术史的演进历程中,它始终伴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学语境的更迭从而周期性地起伏,代表着传统中国一种特有的古典情怀和雅致意境,所以,到了喧嚣无比的现如今,一般人恐怕是再也无法潜入其中,因为,关于诗意画的欣赏,不仅需要看画的雅兴,还需有读诗的心情,这两者竟是我们时代的稀缺之物了!
《诗之旅》读后感(四):立体的旅行
诗之旅8.0[美] 高居翰 / 2012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高居翰的《诗之旅》打开了笔者对中国__bk:dt329绘画史书写的想象,同样,也更新了观看绘画的目光。作者显然对这些艺术品烂熟于心,不同作品的风格特征的来龙去脉了然指掌。
《诗之旅:中国与日本的诗意绘画》由1993年赖世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讲座及中国美术学院首届潘天寿讲座的基础上增订而成。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叙述了南宋杭州,晚明的苏州及江户时期日本的诗意画。以南宋人物点景山水画为源,经晚明苏州一带画家和江户时期日本画家承续,二者既不断回应又不断偏离传统,本文只关注南宋时期的诗意画一章,企图厘清高居翰自然流畅的文笔中隐含的复杂结构。
高氏对于“诗意画”的定义是:通过暗示性的描绘,融入诗人的抒情体验,唤起我们对以往经历的重新感知。换言之,这是与叙事类型的风俗画主题不同的绘画,它并不描述一个较完整的时间和对象。而诗意画最先明确被提出是在北宋文人圈中,以蜀派文人为主,特别是苏东坡,诗画互转共通的概念在此时尤为突出。
在共同创作诗意画的人中,大致可分为创作者和观赏者(消费者)两类。需要强调的是,诗意画并非是北宋以来的自觉创作主题,而只是高居翰对11世纪由北宋文人广泛明确提出以诗入画,以画入诗的点景人物山水画的概括,它“是被辨识和体验出来的,而不是被有意创造出来的”高居翰首先提到的自然是苏东坡,黄庭坚,李公麟等人,特别是画家李公麟,黄庭坚称赞其“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尽管他们作为文人画实验的先驱,但高居翰挑战了人们的一项共识:文人画具有诗意特点而院画具有描绘特征。“院体画家的技巧必然导致对“形似”的一味追求和陈陈相因的套路,而文人画家由于自己是诗人,学识广博,于是就被先验的赋予了创作一流诗意画的特权。”并举出《潇湘卧游图》(佚名)为例“(文人画家)尽管他们满腹经纶,读书万卷或以书法为日课,却不能企及这位画家所取得的成就。”这批士人的画论延续到北宋末年,确立了宋代后期宫廷绘画的基本模式。文人和贵胄,朝臣画家可归入业余类画家,11世纪后期,徽宗的宫廷画院制度化后,叙述的主角转向供职于皇家画院的全身心投入绘画创作的职业画家;在徽宗1110年建立的画院中,对于入选者要测试文学才能,依据命题诗句作画。但是在保存下来的实物中,并没有看到有作品是徽宗时代根据命题诗句而创作的。
《诗之旅》第一章至少有三条线索:
其一,高居翰叙述的主线“诗之旅”描述了出走在时空中展开的多种方式。
南宋山水大致分为四种叙事类型。第一阶段是静止的隐居生活画面,大多数是士人端坐在居室中,如凉亭读书之景;第二阶段是各种要素构成的画面,或许就是要获取新鲜的感受,人物走出了建筑物,这往往是动态的,使观者有序的看到一次旅途,如云关雪栈;第三个阶段,行者又停驻下来,体验景物中一些特别的细节,如大量的观瀑图,赏月图,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旅行者返回家乡和隐居地,回到安宁的环境中。“这些画面常常是对称的,标志着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之所的分界”。这样的分类也和“旅行”呼应了起来,在离开与返回中,高居翰统一了山水画的时空序列,不仅一幅画中有时间感,在画与画之间也有相呼应的时间层次。
其二,风格变迁和南宋绘画生产机制的关联。
宫墙之外,在杭州这个人口上百万的国际都市,巨大的消费空间孕育了大批鬻画为生的画家。高居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说,画院内一个主要画家创作的新颖的构思,通过复制和模仿流传到院外,是那些二流画家对皇家画院画家优秀范本的重新演绎和呼应。高居翰的假设改变了研究风格形式的演变的思路,从原来纵向人为划分出不同时期绘画的不同品质,变成为了同时代横向比较,而不必将这些作品归为后期元明时代的摹本临本。虽然看上去只是一个绘画作品断代史判定的转变,但是其中也体现了高居翰有意将社会史引入艺术史的视角。杭州城中绘画风格从皇家画院流传到宫外就体现了政治地位在绘画中影响。高居翰继承了沃尔夫林的学术传统,对风格在艺术史上的变迁非常重视。他曾说:“风格也是观念。”因为“当画家有意识的选择风格时,这选择就别具他意,其中有附属于风格的各种特殊价值,这些价值包括地望、社会身份甚至思想或政治的制约。风格于是暗含了超越艺术限制之外的东西……一旦达到这样的情形,绘画史就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开始近似于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许多命题也就开始相互衔接。风格成了观念。”
其三,此书最为核心的,在探究作品与现实的关系中,他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的绘画视觉呈现,是谁眼中的世界?难道这仅仅是画家个人的眼界?还是仅仅是根据诗句呈现的一个具象世界?这其实就带出了“诗意画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南宋画家及其追随者为了他们的观众创作。
高居翰显然并不仅仅将这些观赏者作为单纯的审美主体—南宋观赏山水画的众多贵族,士人,乡绅,富商,普通居民在获得美感经验的同时,他们窗外发生了什么,杭州改变了什么,南宋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正是自然在日常经验中的退场,才引起人们对山水世界的无限向往。这些画家是在拥挤繁忙的杭州城创作出的饱含远方诗意山水画。杭州虽然有着清丽的山水,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拥挤的人造花园。西湖就是最为著名的人造景观,任何时候都有上百艘船游弋其上。杭州在1275年的人口统计已近百万,而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不过数万居民。而此前三十年,人口数目约为50万。“诗意画不是生活方式,而是理想状态,对于接纳了他们的人来说,这些想法可以缓解生活中糟糕的现实。”高居翰讲述了人们与地理空间环境相互适应,调整,改变的过程,这些亲密又富于张力的关系如何一一体现在山水画的视觉呈现上,在空无一人的画面中其实如何体现着人的目光规范自然的痕迹;在点景人物活动的场景中,怎样体现隐居生活的社交化,或社交生活的隐居化。在现实这一层面,不仅叙述了自然景观的改变,还有南宋压抑的外在政治环境,以及新晋的商人阶级和乡绅阶级文化心态的变化,都汇聚起来成为影响山水画风格改变的原因。高居翰注重社会史的引入艺术史写作与其老师有着密切关联,其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是德国艺术史学家罗樾(Max Loehr),二战后从德国来到美国密西根大学任教,其师承可上溯至美术史大师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1864-1945)。罗氏以河南安阳青铜器纹样风格研究的开放性而闻名,这为今后学者将风格分析引入中国绘画史的学科范式做了重要铺垫。高居翰同时吸收了当时欧洲新的艺术社会学探究方法,试图从视觉图像中探究出画家的时代背景,生活情境。引入社会学的角度,跨学科研究早已在19世纪欧洲如火如荼的展开,高居翰对中国学界的重要影响在于将这一种学科范式成功地引入了中国绘画史的具体研究,介绍画家时代背景并不新奇,而在于如何构造现实与作品相互影响的具体联系。相比较之下,国内大多数教科书中虽然也提供了社会史内容,但现实往往被压缩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阶层的崛起”一类空泛的话语。“艺术品如何被创造”的回答也被简单化两种目的:或是幻想逃遁的世界;或是抨击不堪的现实。现实被概念简化后,画面的内容也成为了空洞的表达。
有意味的是,高居翰将诗意画的兴起和恰恰和人口密集的城市发展联系起来,那么诗意画的兴盛是而出于缓解现实压力的创造,算不算一种对焦虑现实的逃避?它仿佛是人们给自己建造的精神花园,仅仅在画面上徜徉罢了?
这个关于“现实”的问题还要进一步追问其前提:可对于南宋人来说,什么才是现实?是这座人造景观正逐步改变人们视觉感受的城市真实,还是远在人类生存之前就已生生不息的自然真实?此时北宋灭亡的记忆想必还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些亭台楼榭,雕梁画栋在战火中夷为平地,花费人力财力历时数年修建的坚固城池毁于一旦,更别说战乱流离中无数凡胎肉体的生命。一方面是新兴城市由于经济发达而逐步吞噬了自然景观,另一方面,记忆中战乱的凋敝印象仍盘亘不去。和人事更迭不定相比,山水是一个更为永恒和静谧的世界(限于宋代的生产力水平)。“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放归自然的樵隐是山水画中的重要主题,沉重的历史记忆在更为宏大漫长的时间维度中被放空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苏轼《赤壁赋》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发无疑是被山水画深切感动的观者的写照:一切都在流逝,而自然却是无尽藏,“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没有否认人与自然物在时间上的差距,但他举出看似永恒而实则不断变化的水,月,“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非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这一洞见道出了中国文化中对自然的不言而喻的预设:自然无尽。这种永恒感,使得“自然”和改朝换代的人类社会相比,更为真实。段义孚在《逃避主义》中说,逃向自然是依赖于逃避自然的。正是由于人口压力和社会束缚的与日俱增,产生了逃向自然的必然后果。这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矛盾。逃避自然一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在从人造景观逃向自然的同时,那自然必定是被人文化了的自然,是“自然”这个概念,这一概念是人们经验与历史的产物。将人与山水的关系抽象化诗意化,画面呈现的具体自然山川在人文中获得深度。
向前追溯,这种永恒感的自然观与所处地理位置的具体经验紧密相关。无法想象这样一种文化气息可以对应美国西部的壮丽峡谷和浩瀚星空,或者青藏高原的辽阔平原和雄伟雪山,从画面表现的地理空间解释,诗意山水画不可能描绘未经人类踏足的空间,蛮荒之地因为被排除在人类视野之外,不具备人的气息,中原地区对四服之外的周边民族如此忧惧,那里的自然是野蛮的,险恶的,地理空间、原始的自然状态和文明的程度紧紧联系在一起;人文的程度代表了文明的高度。而山水画中的自然,语境又大不相同,画家描绘的地理环境已容纳了人类上千年的文明,于是尽管云海幽深,也还有飞檐一角;高山崎岖,也总有山径蜿蜒;溪流潺潺之上,必然有木桥可行;烟波浩渺之中,可见舟子横斜。换句话说,在亚热带温带的丘陵平原中,富足亲切的自然使得人与山水的关系是相对平和地生活了上千年。这种文化气息将人与山水的关系理想化,山水画在人文中获得感情的深度。山水画是自然而然的诞生在这种文化之中。诚如高氏所说,它“是被辨识和体验出来的,而不是被有意创造出来的”。最早的山水画据说追溯到唐代诗人王维,在山水画的源头就与文人紧密相关。而这种人文自然观的思想源头,我们也许还可以追溯到魏晋山水玄言诗。虽然我们没有找到徽宗时期的实证来探究根据命题创作的山水画,但至少表明,山水画的创作的文化背景就是“诗画互转”。而视觉的山水画又反过来丰富加强了这种文化思想的表现力。
南宋的山水画在绘画史中无疑是一座高峰,高居翰以其过人的眼光洞察了隐藏在山水画中,创作主体和欣赏主题复杂的心态,那些嘈杂与压抑积淀反而孕育出诗意的旅行。在这场旅行中,画与人的关系,画与现实的关系,画与画的关系交织紧密。而高居翰的贡献在于,他将风格史,社会史的写作思路引入艺术史,同时也从视觉形式中看出作品与作者,观者,自然造化之间丰富的关系。在目光的移动中,观赏诗意山水画的路径也延展出不同方向,与现实的多个层面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