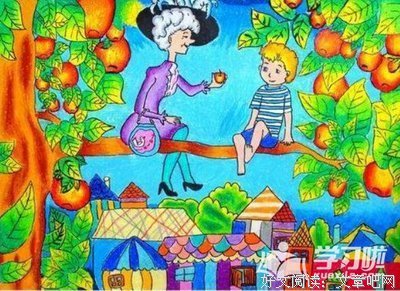全球城市读后感1000字
《全球城市》是一本由(美)丝奇雅・沙森著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44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全球城市》精选点评:
●书不错,先翻再读
●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李强爷爷请还我的时间TAT…………
●没有想象中有趣,所以未曾仔细读。只觉得此书过于注重宏观结构。印象最深就是全球城市的社会和空间两极化。
●略读
●最后还是快速读了中文版。
●妙不可言。生产者服务业、城市空间两极化、全球城市等等都是极其犀利的概念,准确地把握那些处于全球经济网络中的节点的载体——全球城市。
●萨森大妈的经典著作,偏向城市经济学,说实话读得不是很懂,但对于理解城市的转型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城市分工有很大启迪。另外,翻译确实不太好。
●暂时读了前半本 写作此书需要耐力和勇气 比较难啃 专业积累要求很高 在全球经济联系愈发紧密的同时 集聚效应的作用也会更加显著 又是一个两端分化的例子 中文版翻译出了一些瑕疵
●观点不错,论述冗余,数据扎实
《全球城市》读后感(一):关于译文
本想用中文本快快过一下,因为萨女士谈一件事不惜笔墨。但看来还是老实去看英文版吧。
1.中文版P4,第三个假设中的融合经济,原文为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2.中文版P6,第七个假设中的信息化,原文为非正规化informal,informalization,这样才解释得通。
《全球城市》读后感(二):全球城市的乳腺癌
原文地址http://qiuin.com/bookreviews/251.html
如果说全球化用左手碾平了世界,那么他却用右手为世界隆胸。这些隆起于平地之上的就是全球城市。沙森在《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里着重关注了三块丰腴之地,而这几块胸部却都患有严重的疾病。
把世界看作是“平的”,强调的是经济组织的区域分散化、劳动分工全球性合作。然而,萨森却认为在经济活动空间分散化的同时伴随着集中化趋势,并且前者强化
了中心控制与管理的功能。也就是说,经济越是全球化,中心功能在少数几个全球城市里聚集的程度越高。全球城市成为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点,金融机构
和专业服务公司的主要聚集地,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以及产品及其创新活动的市场。
全球城市其中最主要的经济动力是生产者服务的增长。生产者服务的主要特征是为机构提供服务,而不是最终消费者,因此它是一种中间产出。像跨国公司总部不再
是一个制造商品的地方,它“生产”管理、控制和协调等服务。制造业和关键服务产业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装配时,金融和生产者服务所主导的新产业在一些全球城市
里集中。这导致了原有工业城市的衰落,如底特律、大阪等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萨森认为新的生产者服务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原有工业部门衰退的基础上
的。
新的增长最终导致了收入结构、公司和家庭竞价能力的不断分散化,也就是说全球城市的发展并不是扩大了中产阶级队伍,而是造成了收入的两级分化。一方面是金
融专家、技术人才在全球城市的聚集,其收入的大规模增长;另一方面是更多低层次的服务成为城市所需,而丧失了原有产业工会的支持,其收入非常低。
中等收入者在生产过程中被全球化的力量所消除,中产阶级文化也遭到了新兴高收入技术专家的侵蚀。这种世界性的职业文化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美学观。新的高收入
者成为艺术品、古董和奢侈品的主要候选人,开发商通过引入艺术家工作室把贫民区改造为豪宅来吸引这些“收入新贵”。这个阶层的增长已经促使了消费结构的重
组,“重要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烹饪技术,不是衣物本身而是设计商标,不是装饰本身而是公认的天然艺术。”(P321)
全球城市抹去了原有国家间的界限。“私有化、放松管制以及全球化的关联增强,国家作为空间单位的角色已经部分地改变或者至少是弱化了”(序言)。跨国公司
的头头们坐在全球城市的总部里,“战略”性地部署其属下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上决斗,各个国家的首脑们频频地向他们抛下渴望“临幸”的媚眼。
经济组织分散化伴随的集中化、在工业衰退伤疤旁生长的生产者服务、中产阶级的萎缩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国家界限的淡化,让全球城市高耸的胸部里暗藏着癌症的危险。在中国一个个城市都渴望成为全球的胸部时,我们是否注射了抵御癌症的疫苗?国有企业的在可能的全球城市中的力量会越来越大,从而加速而不是分散了垄断;工业渐渐转移到更不发达国家时,生产者服务却无法成长;中产阶级还未形成就遭遇着日渐扩大到收入两极分化;以及全球城市没能抹淡了国家的力量却增强了对它的依赖。正像在中文本序言里作者所说的,“世界对上海的想象似乎已超过了她的真实力量”,中国还有更多的城市正在意淫着自己作为“全球城市”的想象。
:希望这个评论不被误认为是反全球化的证词
《全球城市》读后感(三):城市作为空间概念的延拓
太晚了,简直乱写。
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学认为空间形式和组织是生产方式的产物,同时带有政治性和策略性。空间同时作为资源被争夺,作为国家意志的表现形式被分配,作为社会关系的反映者被观察。
上世纪80年代全球化进程开启以来,发达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金融行业转变,金融交易额的巨幅增长,全球城市以一种适应性的侵略姿态诞生了。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化的产物,由于制造业的空间分散化以及金融业重组创造的集中化和集中化导致的控制和管理总部的迁移造成了全球城市的出现;另一方面,全球城市作为金融服务中心,用强大并且不断上涨的全球控制能力掌控着广泛分散的国内外生产系统。
因此从表观空间上来看,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看到总体不断平缓,并且由高势点向低势点扩散的状态下(尽管全球化带了贫富差距),在以国家区域为单位的某些点(城市)有着明显突起——的动态图像。凸起部分是空间资源争夺的结果,极高密度的经济集聚伴随着大规模的运营、复杂的交易和多样化的专业服务而诞生,它抢占了原本属于制造业的空间,并将其挤入了国内的其他城市,挤入了第三世界。尽管失去了大部分的制造业可能导致财政问题,但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潮流,消费品的生产不再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专业阶层在这些城市替代了普通的中产阶级,这样的趋势以正反馈的形式走上历史舞台。
同时,我还看到了空间作为资源在空间上的延拓。全球性的城市网络在形成。书中很形象地表明了这样的趋势。“每一个市场都是成长中的制度化网络的一员。这三个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在相同的商务活动上,不是简单的相互竞争。它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具有互补的功能。简单地说,在80年代,东京是资本输出的主要中心;伦敦是资本运营的主要中心,其主要是通过国际银行网络以及欧洲市场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连接;纽约作为主要的资本接受地,是旨在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与生产创新的中心。撇开经常提及的弥补时差的需要从运行的角度表明,不同跨区域经济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虽然现在的情况也许会有不同,但是“输出”、“运营”、“输入”的相互关系必然仍在全球几十个全球城市之间存在。而这样的关系的存在,意味着这是一个物质空间与信息空间并存的经济时代。这样的空间交互产生了铁路、空路、还有在卫星之间反射的电磁波所构成的繁忙情景。书中提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智能建筑”的概念,希望用高速铁路和电信手段将东京、大阪和名古屋连接起来,产生“直线型集聚效应”。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城市的经济模式对于纵向与横向的空间资源的需求,使得物流、铁路和电信工业成为了争夺的一部分。
最后则是空间在文化、政治上的延拓。专业阶层对中产阶级的取代,福特主义的衰落,绅士化,艺术家作为组群的权力建模。而艺术家对日产生活结构关键要素的“价值嵌入”深会我意。在经济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嵌入生活的艺术与社会消费与社会心理遥相呼应,本身赋予时代、赋予历史以美学价值。当然,全球城市所带有的文化战略性意义,也成为被争夺资源,在城市演化过程中带来遐想。
《全球城市》读后感(四):《全球城市》读书笔记
(城市社会学作业)
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似乎是刚刚习惯与适应了大工业机器的声声轰鸣与狂飙突进,城市在最近几十年又逐渐开始面临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在普遍意义上,依靠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拉近了城市与城市的距离,构建了新的“城市—区域”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有空间层次与体系的消解。不管是何种名称——“首要城市”(primate cities)、“世界城市”(world cities)、“国际城市”(international cities)、“超大城市”(mega-cities)或者是Saskia Sassen自己命名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这样一个事实是极其明显的:在全球化带来的趋同化背景下,仍有一批城市——按照Sassen的说法,大约是有40个左右的城市——从中“脱颖而出”,跨越国别的限制,承担起指挥全球经济发展与资源调配的重任,同时也直接推动了一个多层次的世界城市网络新体系的形成。
这样的“全球城市”有哪些?Sassen在《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中以纽约、伦敦、东京三座城市为例,探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系列新现象:分散与集中的新形式、外国投资的新模式、金融业的扩张、“全球城市”的社会秩序与空间极化……而且,Sassen在本书第一章的总论中即指出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在崛起为“全球城市”的过程中,上述三座有着不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背景的城市“在经济基础、空间组织和社会结构三方面都经历了巨大而又相似的变革”,这似乎暗示了世界经济变革的强大力量;而这些“全球城市”也顺应地衍生出了特殊的“空间、内部动力和社会结构”,走上了自我的蜕变之路。
尽管这个书名看起来像是对这三座城市的分别论述与对比,但是Sassen还是把文章的主要篇幅留给了关于“全球城市”的理论阐释上。当然,无论是在讲城市的理论还是现实情况,Sassen都毫不吝惜笔墨;尤其是在对比纽约、伦敦、东京三座城市与其他城市时,更是采用了大量的数据与表格来进行比较——众多繁复的数据固然使得此书变得不那么“好读”,但是它却很好地、可信地展示了所谓“全球城市”与普通城市在扩张趋势、产业结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差异;而为什么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有些大城市走向了相对的衰落,有些大城市却更进一步,Sassen也通过一系列数据和对比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通过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Sassen主要是依赖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来衡量、测定一个城市是否为“全球城市”的标准的,比如某些特定行业的就业比重、所吸纳的资本份额、个人收入的分布与变化等等。也就是说,对应着当下的经济全球化趋势,Sassen所谓的“全球城市”,主要还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而较少涉及到一个城市对区域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力。
assen的观察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制造业呈现出空间上的分散化与国际化的趋势,导致了为“管理与控制空间经济的服务节点集中化的加强”;生产者服务业与金融业越来越集中于像纽约、伦敦和东京这样的“全球城市”,以加强管理与协调。所以,全球化相当于世界城市层级体系的一次大洗牌,诸如底特律、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制造中心面临着或者已经衰落,而纽约、伦敦和东京则作为金融和高度专业化的服务中心得到了进一步扩展。
而在对同一国家的不同级别的城市的对比中,Sassen也发现,和本国的另外一些主要城市相比,“全球城市”之所以拥有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影响力,其最显著的区别还是在于生产者服务业和金融业的集中程度的大小上——在另外的主要城市中,并非没有出现类似的产业集中趋势,但这些集中的等级更多地是基于区域性而不是全球性的过程。
而对于“全球城市”各自的职能定位,Sassen也作了简要分析。略微出乎我意料的是,不同的“全球城市”也各有其发展的侧重点,彼此之间并非是完全的竞争关系:如在80年代时,东京属于“资本输出的主要中心”,伦敦是“资本营运的主要中心”,纽约则是“主要的资本接收地”,是“旨在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与生产创新的中心”。
上述职能分工的差异使得这三座城市间保持了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在GaWC小组的三位成员——Jonathan Beaverstock、Richard Smith和Peter Taylor——撰写的《世界城市网络:一种新的后地理学?》一文中,他们对55个国际性大都会间的关系网络做了数据分析,发现纽约、伦敦与东京这三座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确实是最频繁的(虽然香港同纽约、伦敦间的联系也处于同一层级):伦敦与纽约“共享”了全球最大的46家公司办公室中的45家,与东京是37家,而纽约与东京也是37家;而除了伦敦对东京的直接联系稍弱外,纽约与伦敦、伦敦与东京的双向直接联系与东京与伦敦的直接联系的概率都在0.95以上——这体现了一种极其密切的联系
也正是在这一维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Sassen所定义的“全球城市”,早已跨越所谓的国境限制,构筑了一个跨区域的、在国家形态之上的城市网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资本与信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交换与生产,其中所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正在改变着全球的经济产业,也在改变着城市的空间结构与阶层分布。
“全球城市”促进了制造业的分散化与生产者服务业、金融业的集中,但它们是如何影响了城市的空间结构、社会秩序与阶层分布?最明显的影响仍是通过经济/产业这一媒介发挥作用的:“全球城市”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变——生产者服务业与金融业代替制造业——最终导致了城市空间与制度层面上的新区域联合体的逐步形成,其外在表现包括:豪华办公楼与住房的复合体、大型公共建筑项目以及大量占用市内土地,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大规模的、国家引导的城市空间上的重组。在纽约,著名的建筑师Robert Moses成为这一重组过程的倡导者和设计者,而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他也因此受到了来自Jane Jacobs的猛烈抨击,新一轮对“什么是真正的城市生活”的讨论与反思由此纷纷展开,但这依旧不能改变城市空间结构改变的既成事实。
此外,“全球城市”带给自身的还有阶层与空间的断片化倾向:Sassen指出了纽约城市的居住空间的三类分化:“第一种空间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新富阶层及供其消费的各种商店所占据;第二类空间被大量的移民社区占据,各种地下经济在这里悄悄进行;第三类空间是那些衰败的城市街区,被众多的穷人和被迫搬迁的人所占据”——这一景象在现在的大城市中仍存在着;城市内就业关系的临时化、对不同产品和服务的大量需求,也使得城市表现得越来越“全球化”。
当我们回过头来分析Sassen的“全球城市”概念时可以发现,这一概念不仅仅是对Peter Hall和John Friedmann设想的“世界城市”话语体系的简单继承与发展,而是选择了另辟蹊径;当然,同为GaWC研究小组的Honorary Founders,三位大师的相关思想直接影响了Peter Taylor等人关于全球城市区域网络的研究,如此一脉相承,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有生命力的关于现代城市网络的理论体系。
《全球城市》最初出版于1991年。作为Sassen在书中的分析对象的三大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毫无疑问是80、90年代城市之翘楚;但数十年过去,各大城市的地位也有了微妙的变化:GaWC从1999年起尝试为世界级城市进行定义与分类,而在2012年发布的数据中,伦敦与纽约依旧位居前列,获得了唯二的Alpha++(即最高级别)的评级,而东京只获得了Alpha+的评级,其排位在香港、巴黎、新加坡与上海之后,北京之前;在2005年出版的《全球城市》中译本中,Sassen也专门写了一篇中译本序,深入探讨了上海作为全球化城市的思考,并对自己的理论做了修正——或许,当我们说起主要的“全球城市”,东京已经不是一个可以脱口而出、毫无争议的答案。
我们应当注意到,东京的入选,不仅仅是因为它有着极高的国际化程度;Sassen选择了三个分别位于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全球城市”来进行分析,相信也是有意为之。对比90年代和2012年各个城市的排位变化,我们可以感受到世界经济——尤其是亚洲经济——的剧烈变化,包括中国的上海、北京等城市开始更开放地面向世界。有理由相信,全球化是一股重塑世界城市格局与网络体系的强大力量,Sassen的理论研究,也仅仅是开了个头而已;未来的二十年,谁会走向衰落,谁又会走向崛起,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14.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