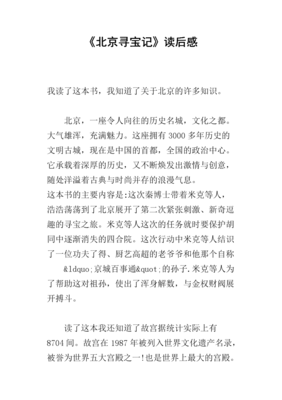《北京乎(上下)》读后感精选
《北京乎(上下)》是一本由姜德明著作,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60,页数:84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北京乎(上下)》精选点评:
●看着看着就没兴趣了
●非常喜欢北京
●编者徒有虚名,编辑毫无章法,有些文章非常恶俗。
●里面必有你喜欢的文章
●如果说人间只能有一套写北京的书,我会选择这套。
●李健吾,朱自清,宋春舫,叶灵凤,名家果然雍容可观
●最早的北平情结过去后,很难不把目光投向那些普通不起眼的底层人民。在战乱动荡的年代里,他们无力也无心去欣赏那个传说中的“金粉北平”,北平对他们而言也不过是一座混杂着苦难和屈辱的城市。不同作家带来不同的视角,残酷而真实。
●即使是北平, 往后合集还是少看些.
●编者的出发点不错,如果大家保护北京旧城就如同作者搜集关于北京的旧文字,那么北京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垃圾场了!
●北京乎?北平乎?南方的孩子从小就离它很远,但又总能听到关于它的种种。总之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向往了。
《北京乎(上下)》读后感(一):别有一番怀旧的阅读感觉
盈盈一个小册,竖排版。很适合怀旧的心境。
还是很多年前买的了。
还是可以让今天生活在支离破碎、拥挤世俗的新北京里的我们,依稀还能忆起一点点昔日的风华。
当年,这是一座怎样的城,怎样的一群人。
世居于此的我的祖辈们,是如何待人接物,是如何恬然安居。
各家随笔编辑得还挺全的,
琉璃厂访笺的那篇随笔似乎还印象深一点。
《北京乎(上下)》读后感(二):散文的北京
看散文本就会有种淡淡的感伤,这里说的是好散文。众多文人对自己身处其中的旧京絮絮叨叨地讲述着身边的是是非非,看上去那么遥不可及又仿佛在身边。而笔下的悠闲与惬意也早已不属于现在京城的模样了。恐怕这些敏感的文人生活在今天一定写不出来这样潇洒的文字,而最可能的是在另一个城市说首都多么的不好吧。因为至少我知道书中的描写在现今是毫无踪迹了。
这种怀念徒增了伤感的忧郁和愁绪罢了。
《北京乎(上下)》读后感(三):黄裳写的不错
看了下册,没有再去看上册了,打算如果真的去北京玩,那是一定要找几个书里提到过的时间去的,好景还需要好季节啊。
黄裳的那几篇不错,第一次看黄裳写的文章,说的京戏,很喜欢其中唱戏人的韵味的描写。
后面有几篇,忘记是谁写的啦,写北京房子都要坐北朝南是因为建筑师感觉既然大家都这么建,反正卖的出去嘛,也都这么建。。。看的我有点无语,要讽刺人家不思考墨守陈规的作者同学,你也思考下好不好。。。北京建房子朝南是因为人家需要采光。。。
《北京乎(上下)》读后感(四):今夜月,到青龙桥去,忆北平的风度
雨后,着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闲人,咬着烟管在雨后斜桥影里,树下一立,与熟人用缓慢悠闲的调子微叹唱合”唉,天儿可真凉了……”“可不是,一层秋雨一层凉啊”。
这段文字,仿佛是明代中国画中人物,清疏而雅致,且透着层层的秋凉。这色浓、味永的秋,正是郁达夫先生笔下的北平。
高中语文课本中《故都的秋》,是我读的最仔细,私下最喜欢的文章。在文本中间、课本边缘,还写满密密的点评。故都的秋,“特别地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郁达夫真是才子,二十年足不出户的我,读着这段文字,也能体会到北平秋天的清静与萧瑟。
郁飞回忆,1934年7月杭州酷热,郁达夫和妻子带着六岁的郁飞在青岛住了一个月,随后去了故都北平。郁达夫一生虽然没有在北平久居,但对故都北平却是情有独钟,他不惜笔墨、着力描摹北平的风土气象,先后写有《故都日记》、《故都的秋》、《北平的四季》、《平津道上》等文章。
北京昔日的风貌早已荡然无存,旧时的片段只有到《故都的秋》一类的记述里去领略。《北京乎——现代作者笔下的北京(1919-1949)》就是一本充满旧时文人趣味,记叙燕都北平风貌的书。
《北京乎》名字取得好(虽然更好的名字应叫《北平乎》),书的装帧设计素朴而雅淡,排版是简体竖排,透着北平隐隐风尘、朗朗青天。我初见此书,似乎是在北京友人的书架上,目录上的文章的篇名,自可集成一首小诗:
今夜月
到青龙桥去
在我们这巷里
忆北平的风度。
(孙福熙 《今夜月》;冰心《到青龙桥去》;潘漠华《在我们这巷里》;陈学昭 《忆北平》;徐訏 《北平的风度》)
江南的秋天多雨而少风,全无燕赵的悲凉、深沉,只是几分暧昧和凉薄,也难怪郁达夫先生愿意以生命三分之一的零头,去换却长留北国的秋天了。
2007.10.16
昨日之岛 http://tlccd.tianyablog.com
《北京乎(上下)》读后感(五):为迷人而迷人:林语堂的北平
林语堂〈迷人的北平〉,见于姜德明 编《北京乎》(北京:三联书店,1992),507-515。
林语堂为幽默而幽默,为性灵而性灵,也为迷人而迷人。这个“为”出来的迷人可以从《迷人的北平》一文看出来。且看开头第一段:
“北平和南京相比拟,正像西京和东京一样。北平和西京都是古代的京都,四周是环绕着一种芬芳和带历史性的神秘的魔力。那些在新都,南京和东京,是见不到的。南京(一九三八以前)和东京一样,代表了现代化的,代表进步,和工业主义,民族主义的象征;而北平呢,却代表旧中国的灵魂,文化和平静;代表和顺安适的生活,代表了生活的协调,使文化发展到最美丽,最和谐的顶点,同时含蓄着城市生活及乡村生活的协调。”
第一句话有些发虚发飘。原因在于,当林氏写下“比拟”两个字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也知道如此的“对比”不能当真。第二句话要把中国的北平比做日本的西京(京都)。然而二者究竟如何才算神似?林语堂说不出具体的语言图像,只好说“四周是环绕着一种芬芳和带历史性的神秘的魔力”。
在林文此段的第三句话里,林氏把南京(一九三八以前)和东京归为一类,“代表了现代化的,代表进步,和工业主义,民族主义的象征”。这很牵强。且不说南京当时的现代化和工业主义比日本的东京差得太远,南京就是跟临近的大上海相比,也被公认为“乡下”。在一般人眼里,南京生活的宁静正好对比着上海的繁华喧嚣。对当时南京的党国要人来说,南京是办公的地方,安稳的六朝古都;上海才是现代大都会,“东方的巴黎”。(不过话说回来,我毕竟没有在三、四十年代生活过。照国民党元老回忆,南京政府机关,在抗战之前,确实有一股紧张活泼,奋发向上的气氛。年青职员,不敢涉足舞厅,赌场,周末下馆子都有顾虑。大家把上海当成腐败的地方,从这个意思上说南京也没准儿一度象征着“主义”与“进步”。)
林语堂写此文的时候应该是“一九三八”抗日战争爆发和南京沦陷以后。这篇文章是收在一九四一年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的《语堂随笔》。当时,包括北平和南京在内的众多名城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呻吟。(南京大屠杀之事,不知当时的国人是否已经知道?)能“随”出这样的“笔”来,拿北平比日本京都,拿南京比日本东京,确实别具一格。
其实也不必对林语堂过于苛责。他可能只是觉得北平南京的“南北”,正好可以配东京西京的“东西”,煞是迷人。
这种“迷人”是禁不住细看的,还是在第一段里——如果你问林语堂:文化发展“最美丽,最和谐的顶点”到底是什么样子?“城市生活及乡村生活的协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他很可能也不知道。
以上是对林文第一段的分析。
林氏此文一共二十七段,每一段都是这样为了迷人而迷人。如果每一段都分析一下,连语法带逻辑,太累。下面就只从全文正中挑出第十三段,粗略地读一下:
“这里也是多色彩的——有旧的色素和新的色素。有王家宏大的,历史时代的,和蒙古平原的色素。蒙古和中国的商人带着骆驼队从张家口和南口来进入这有历史的城门,有数里相接的城墙,四五十英尺阔的城门。有城楼和鼓楼,那是在黄昏时报告给居民听的。有寺宇,古花园,和宝塔,那里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树,以及每一座桥都有历史和古迹的。”
林氏在此段的第一句话里,提到了“多色彩”——“ 有旧的色素和新的色素”。当然,这个色彩学是个比方,其实是说北京在视觉上既有历史遗存,又有现代场面。然而,在这个主题句后面的四句话里,“新的色素”完全看不到了。(这跟林语堂的方言有无关系?北京话说得好的人如老舍、梁实秋,可能不会这样写。不过也难说,沈从文一辈子讲不好普通话,但是善于描写地方景物。把他们两人的文字比一比,可能会有的说。)
读者所看到的都是诸如“王家”、“宏大”、“蒙古平原的色素”、“骆驼队”这样的字眼,还有城墙、城门,城楼鼓楼寺宇古花园宝塔等等古老的建筑与空间。这些“旧的色素”的运用,在风格上感觉像是意大利歌剧《图兰朵》里的北京城布景,或者像几十年前洋人观光客写给纽约时报的小文,而不像现代中国作家用中文描述的北平。
我真怀疑这篇文章本来是用英文打的底稿,原本是想投合洋人口味的。那个时代每个对中国着迷的洋人到了中国都幻想着自己是踏上这神秘东方的唯一西方人。于是他们眼中的北平就总也离不开马可•波罗为“汗八里”(马可•波罗所称呼的元大都)定下的“色素”。
殊不知,曾经有成千上万的洋大人端着毛瑟枪、来复枪、机关枪、拉着迫击炮、加农炮、榴弹炮,从塘沽一路杀进北京,再大包小包地把宝物都运走。在那段时间里,这座古城是屠宰场、废墟和匪窝,一点也不迷人。那是在一九零零年。更不用说在之前四十年圆明园就被洋人烧掠一空。“那里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树,以及每一座桥都有历史和古迹的”。是的。不知从咸丰皇帝以来的事儿算不算历史?林语堂没有说。不过他也建议读者到“避暑山庄(圆明园?)中意大利式宫殿的废墟上去凭吊古迹”。(第二十四段)凭吊哪般古迹?他也没说。连带着,东交民巷的洋房汽车洋兵,六国饭店的繁华,以及属于现在进行时的“新的色素”,也都将“真事隐去”,不去说它了。
从前清的京师到民国的北京、北平,这座城市饱尝了国破家亡的味道,特别是林氏写作此文的时候,北平早已落入日寇手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样的泪水不会闪烁在洋大人的眼中,在这篇以迷人为目的的随笔里也是没有的。对林语堂来说,泪水也要溅得迷人。于是就有了《京华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