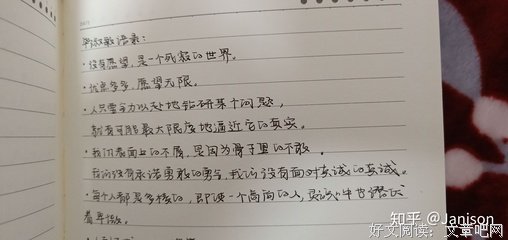和语言漫步的日记读后感摘抄
《和语言漫步的日记》是一本由[日]多和田叶子著作,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19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和语言漫步的日记》精选点评:
●P16削铅笔,成为妨碍你的一个因素,喜欢这么一个细节。对铅笔使用的喜欢。 学习日语时,或者闲时翻阅着嚼嚼,语言的味道,感觉也不错。
●在多语环境中成长起来,所接触的各种文化也是非常丰富啊。日记记录了三个半月的漫游生活,读者也跟着作者从德国漫游至美国、伊斯坦布尔、法国、威尼斯等地方,人的见识就是在这样广泛的交流中增长的。读的作品是托马斯•曼、川端康成,同行的人有阿多尼斯,这样的文化生活真是惬意。语言类型学这种东西就是在这种多语环境生活,并且掌握多种语言的人才能得出最深刻的体会吧。
●在国际和语言边界的游走。
●断断续续读了很久,昨晚读罢想来一个题目:不懂德语和日语者能否看懂此书,或者说不懂德语和日语者该以何种方式切入。《狗女婿上门》收录的与那霸惠子专论中多次提到“(地方)共同体”的概念,此书中多和田自己也多次使用,语言既与共同体相伴相生,作为使用者又需要不断打破语言与共同体间的联系,以便脱离单一意识形态的危险,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只懂得母语的使用者,还是像多和田这样熟练掌握另一门外语的使用者,都适用的。
●作者吐槽日语长句真想跟她high five。作者认为わたし和彼与其说是人称代词不如说是名词的想法很有趣。语言学的内容还是少了些,真地是简单的漫谈。
●文字高敏感度人士的跨文化笔记。
●感觉她很心累,文化碰撞下的不适夹杂在她的创作或生活的压力下,日式文化不想麻烦别人那种小心和谨慎,和德国比较温和开放的乐观氛围的融合和略微的不适感。当然还有一点在异乡的孤独。
●作者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自己对于德语和日语为主的不同语言之间差异所引发的感想。词汇和语法在意义之外,也承载了许多文化的构建。
●满书的假名和德文词汇,作为一个既不懂日语也不懂德语的人实在不应该读这本的……
●看了两遍也不能全部搞懂,毕竟不懂德语也不懂德语词语的那种精妙的差别,日语倒是懂,有些地方偏学术,研究语言学尤其是日语和德语的里头举了一堆例子,譬如日语里说话省略主语省略助词,还有词语的变化。里头还讲了德国一部长学术不端,把引用的话改写用自己的话去说,前几天和导师说老师说这种算是剽窃,但这种投机行为只要用的不多也还说的过去,毕竟本科生。今天又看了这本书想想以后还是少改写别人的观点了,直接说自己观点多好或者大大方方引用,自己改写还费脑子。不过前提是田野调查和调查问卷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像我现在写的这种论文理论性比较强,自己写一大堆还是有点难的。
《和语言漫步的日记》读后感(一):《巴黎评论》多和田叶子访谈节选
Q:你在什么时间写作?
A:我像是那种刚醒来时不能思考的人,因为我还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那是我干活儿的最好时间。
Q:你觉得作为多语言写作者是一个逆反的活动吗?
A:作为多语言者是个挺复杂的事儿。我觉得虽然我只在两种语言之间游荡,但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学习两种语言之中的空间给予了我很多诗意。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周旋于多种语言的国际人士。
Q:你在大自然里待的时间多吗?
A:德国人经常去森林,我也喜欢去。东京没有森林,所以人们把盆栽树设置成他们的电脑背景图案,之后通过屏幕进行“森林浴”。我必须得说,我更喜欢挪威的森林和景色。出于冥想的原因,我还喜欢在柏林打太极拳。
Q:日本的确看起来像是一个现代,先进的国家,但是它又遭遇了别国没有的许多自然以及化学灾难。
A;在灾难事件发生后,日本仍然有一种岛国思想,就是人民必须留在被破坏的土地上,然后重建它。欧洲人不一样,人们逃离了切尔诺贝利。
Q:日本人的这种,与痛苦共处,学习它而不是抛弃它:听起来有点儿受虐狂倾向,还倾向于神道教?
A:绝对是这样的,它来源于历史:相对于离开,还是呆在原处比较好。保持独立,保持与祖先的连接。我一直很喜欢海之日和山之日的声音,但事实上,因为它们是在先帝时期被创造的,所以我不喜欢他们。这只是政府绕开禁忌试图将政治与宗教连接在一起的法律方式。比如说日本人不可以用假期的形式庆祝天皇的生日。这是神道教。他们用海之日之类的节日作为代替。像东德一样。
Q:你觉得80年代初期你在德国的学生时代,相对于自由的,快乐的时光,是你近年来写小说的基础吗?
A:80年代在汉堡,我开始了我的一切。它独一无二,你可以随意出入你喜欢的任何课堂。它开拓了我的学习和阅读。在我早年的俄国文学时光。多思诺夫斯基对我来说是一种病,一种瘾。后来是本雅明,爱伦坡,斯泰恩,之后是博尔赫斯。
Q:你觉得人们还跑到柏林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
A:这个城市和别的地儿不一样。它像是一个巨型的艺术家计划。作者,艺术家,表演,演唱会,演讲,持续不断。它是一个舞台而不是一个城市。
原文
-
阅读多和田野子让我想念以前的一些时光,还有看到未来的一部分我自己。
《和语言漫步的日记》读后感(二):和語言漫步的日記
一月二十六日
還未展卷,已經愛上書名,且不自量力,竟也想借題發揮,仿寫幾篇。
多和田葉子是旅居德國的日本小說家,以日德雙語寫作,其作品近年始有中譯。這本仍是「小說家言」,不是語言學專著,根本連題目也沒有,不過是日復一日,即景生「思」,將德語、日語的細節絮絮道來。轉為中文,自然又隔了一層,不過「隔」也未必不是另一種「生新」,從二重奏到三人行,「必有我師」——不如就以此阿Q精神化解慚愧——我讀的也只是中譯。要和語言自在「漫步」,還是非得下一番苦功。
我深知中英文在體內的失衡,讀和聽還好,一旦提筆、開口,真得「長歎息」。雖然中學悶頭苦讀《新概念》不可謂不用功,可畢竟沒有機緣讀文學啊。說來簡直不可思議:直到大三看《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羅瑟琳(Rosalind) 出場,我才第一次在英文中感受到無上的滿足。那情形像極《威尼斯商人》(Merchant of Venice) 的名言:(英文)不是出於勉強,它如甘露從天上降臨塵世……(The quality of mercy is not strained; It droppeth as the gentle rain from heaven / Upon the place beneath.)
一旦如天啟般感受到「外」語之無上美麗,「外」也就成了永遠無法離開的「內」。實在被Rosalind迷得移不開眼:看她真誠熾烈地表達愛意,與叔父義正言辭地抗辯,以驅逐為探險,甚至好不容易與愛人重逢、還幾次三番追問愛的真意(不只是刁難對方,更是叩問內心)。她留給我的永恆空洞,即便是紅樓女兒也無法填補。古典詩詞中的愛情晶瑩剔透、幽微婉轉,不過沒一個Rosalind這樣的「真正的女孩子」。
到底什麼人能演她呀?這一問盤桓數年,最後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趙蘿蕤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就演過羅瑟琳,當時葉公超也在。喬志高眼裡的「古典美人」,巫寧坤回憶中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孔慧怡筆下的「庭中玫瑰」,就這樣和我心中的Rosalind完美重合。好奇找了趙蘿蕤的散文,〈廚房怨〉那幾篇妙不可言。這位「西南聯大教授夫人」整天出入冷飯熱湯之間(夫婦不可同時任教聯大),可不僅思想活潑,也玩夠了中文的「彈性和韌性」。趙蘿蕤雖早已是翻譯界共仰的「先生」,卻似乎現在還沒入「文選家」的法眼,連本像樣的集子都沒有,更別說專門研究。不知道芝加哥大學還有多少她的遺澤,又有幾人知她也曾在這山這海之間行走?(趙蘿蕤1993年受邀訪問中大,講學兩週。)
說了半日,自不是什麼文章,還是像寫了十幾年的日記,野馬跑得甚遠。不論書內書外,遇到掌握多門外語的人,總是既敬且愧。一直想好好學語言,到如今也還是一無所長,連文言也讀不太通。不過,「文」「言」不一,倒也給了日記好些素材。朋友總愛問我是不是說「吳儂軟語」,戲曲課上也用宜興話勉強念過昆白,可宜興話比蘇州話「硬」多了,充其量能扮凈末丑,生旦的風味是絕學不來。(好些宜興人只會說宜興話,也算是宜興的「本土主義」。)小時候跟外公學過一點上海話,也還大致聽得懂。廣東話則是十七歲來港讀書,捧著《初級粵語》也像當年翻爛《新概念》,一字不差地背過。可「紙上得來終覺淺」,到底還是和local熟絡了,才有「躬行」的機會。寶玉安慰黛玉,總愛說「親疏有別」、「先來後到」,到頭來還不是「姐姐」、「妹妹」地亂叫——廣東話和宜興話之於我,如今也正如此。和家人聊天,竟也偶爾「癡傻」;寫文更是有意「頑愚」,混入「日頭」呀、「落雨」呀之類的詞。那是廣東話、宜興話共用的「公筷」。
Shiori
2019.1.26
《和语言漫步的日记》读后感(三):和语言漫步
和语言漫步
说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是这样的场景:一双脚,走在蔚为大观的语言之海中,是像跑着,又如跳跃般的步伐轻盈,在语言中行走,应该是为漫步了罢。
在语言中观察到的,多种可能性,由语言本身带来的也好,因为语言而造成的影响也罢,总之,不可避免的多次提及“语言”一词,确实是必要的,是必须的。
【01】尝试在不同语言中发现可能性。
就作者而言,在德语和日语间转化与漫步,带来的体验和可能性也是尽可能多的。不同语言体系,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单就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语言是文化的表达,是文化输入输出的门户,这一点,语言更是不可或缺,不能懈怠的。从不同的语言体系中,看同一个词的意思,也大为不同。例如文中提到的:“在德国,临近一年的最后一天,人们会互相寒暄说,“Guten Rutsch!”直译过来就是“滑好!”,意思就是祝你顺利地滑入下一年。我每次听到这样的打招呼声都会想到,因为在年和年之间有什么障碍物,所以也有人不能顺利地滑入,永远地留在边界线上了吧。我虽然喜欢留在边界线上这种意象,但是,留在时间的接缝上则意味着死亡。”这个例子,我觉得有趣又很有探究性。可探究性的有趣之处在于,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这样的例子和对比其实数不胜数,文中也提及他例,但我个人对此最有兴趣。不由得让我想到,跨文化交际课程中曾学到的,在东西方语言文境中,对“龙”一词的认识与理解。
东方文化语境中,赋予“龙”以“吉祥:富贵”一意义,而与之大不相同的是,西方语境中,用“master”来形容“天子的象征”。这点是非常有趣的。原来,东方的天子在西方文化的理解是怪物,头发茂盛的学士指着天空中漂浮的龙样的祥云大喊:“Help!Help!master!master!”这与东方皇室王朝成员看到此忍不住纷纷下跪并惊呼:“上天有灵!上天有灵!”截然不同,比较起来也也颇有趣味。实际上,语言离不开文化。说文化是语言的支撑、语言是文化的表达,其实并不过分。也再次证明,尝试在不同语言中发现语言的可能性。
【02】尽可能多的了解不同语言的可能性。
似乎从一种语言看文化、阅读文本,会稍显孤僻,在打出孤僻这一词时,又蹦出“不足”一词,也有贴切之感。用再情绪化和感情丰沛的话来形容:“甚至些许的寂寞呢”。
这也提醒我,是不是借助另一种更贴合文本的语言去读文本本身,得到的理解也会更丰富、更也好茂盛?在此,我的脑海里不由得有一种蔚为大观的场面。
书中这样的句子,很有阅读和原文摘抄的必要:“我无论做什么都以语言为指南针,决定前进的方向。语言里保存着智慧,比我个人大脑里的要多。而且,语言不是一种。虽然有时候,两种语言各有主张,会发生口角,但是,我认为,比起一种语言嘟嘟囔囔自言自语,让两种语言在自己的头脑里对话,能产生广度更大、密度更高的答案来,难道不是吗?”
这种,两种语言打架的情况,似乎与我曾遇到过,甚至现在还在遭遇的,意识打架的情况有些相像。起先,我对这种“打架”感到痛苦和苦闷,再后来,我似乎慢慢接受这样的打架和挣扎了,因为比起此前脑海里“非黑即白”这样简单的思维,我更慢慢享受,两种或者多种思维碰撞、“打架”的感受了,火花总是在这种状况下产生,念及此,我便由衷的感到幸福和满足。之所以提到我个人的这段经历,是在更好的说明,我自己有在感同身受作者本身的遭遇罢了。但这样的理解是否过分浅薄?或是不自量力?我觉得,在文字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天生形成的壁垒与屏障。去感同身受,去置身于其中,这样真诚的感情,我认为是不分高低和没有门槛的。主动抒情与在作者的带动下“被动抒情”,两种抒情方式不同,并不能由此决定所抒发的情感的好坏,更无所谓高低。一个人所能抒发的感情的可能性,与这个人本身的经历境遇,是脱不了干系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也是不接受“感情之高低贵贱的”。这也让我想到余华和食指的小我与大我之争。即:站在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经历来评判他人的感情,其实在评判的过程中,这种行为就相当于是把一个人的遭遇也加以批判化了的。这一点,我还是不能苟同,是否有些残忍和不堪呢?
【03】在不同语言中发现语言本身的可能。
这里提到的“语言本身”是纯粹的和不加以任何修饰的。单用语言来解释稍显枯燥和晦涩乏味,用书中的例子来阐述更有趣一些:“从“外(外面)”这个日语单词里我感觉不到快乐。倒不如说,它让人感觉不安。我说的快乐的“外”接近于“アウトドア”,(原文注释:日语用片假名标识外来语,此处为outdoor,户外。)但是这个外来语稍稍沾染了商业性的油垢,让人觉得不够买露营用品或滑雪用品就不许与大自然接触似的,这一点令我不爽。不要片假名,单单“到外面去玩”就行了,难道不是吗,我想。像孩子那样。”最后一句,“像孩子那样,”莫名地打动我。这是语言本身的吸引力,在阐述中发现语言本身,不带过多的修饰和点缀,就像孩童那样单纯,反而显得十分珍贵。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也始终认为,如此珍重语言本身。也引发我的另一个思考,独立使用语言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在愈来愈严苛的语言环境下,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让这样纯粹,回归于语言本身的表达,显得渺茫却如此珍贵。
语言回归语言本身,单纯的美好,甚至于为一种追求。我又很自然而然的想起,泉水接受采访时的话:“我十分重视语言。”这样的话,我一直铭记于心,并时时想起。语言在时代的大环境下,能保持本身就已经十分珍贵而不易了。独立使用语言的可能性,我悲观地想,大概是不会存在了。便放任成一种理想主义好了。
【04】语言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对生活的影响。
“在野外漫步搞调查,所以应该属于“filed work (田野调查)”,然而是因为让诗人“野放し(放任自流)”太危险还是怎的,好像被警察误会为形迹可疑的人了。”
书中提到这样的例子,还是一副画面进入到我的脑海里:拿着放大镜的研究学者,专心致志搞研究的时候,突然从背后被警察揪起衣服领子,这样的画面确实有些滑稽。可笑之余,其实不免发现,这便是语言影响实际生活的体现。既生动又常见。不同语言环境下,漫步的步伐是否也会不同?连漫步的频率、保持的呼吸也不相同?我对这样的问题充满好奇,与此,又抱有困惑。甚至于漫步的姿态也不相同了呢。
【05】在镜子中发现语言和与语言漫步。
提及书中文字的来源,我喜欢作者这样的话:“我决心用日记这种镜子,照照自己头脑中的活动。”用“和语言漫步”概括显得更有情感和吸引力。较之于,晦涩乏味的理论化用语,我更倾向,也更喜欢用感情丰富的词汇来表达。与语言漫步是作者每天的经历,也是我每天的遭遇,前者是规范化的创作和研究,而后者,就我来说,只是读和体会罢了。
之所以如此沉迷“与语言漫步”这样浪漫的表达,也更印证了我对语言通俗化和浅显化表达的倾向。似乎有这样一幅画面在我眼前浮现:壮观的语言之海,我步履轻缓于之上,也仅仅只是走在那片大海中的小小的小小的海面之上。只是想到这样的画面就让我觉得光明和希望。
在镜子中与语言漫步,我把这样的行为视为一种反思。“决心用日记这种镜子,照照自己头脑中的活动”。这句话也莫名打动我也戳中我的心。
【06】在语言中娱乐语言。
“我试着给不能拆分的单词加上矛盾的形容词,感觉脑子的一部分放松了。”
更吸引我的是这样一段话:“我在温泉中做着这样的文字游戏,代替了按摩,享受其中的快乐。封闭的门户开放、无视国民的民主主义、病态的健康、失败者的胜利、憋屈的自由、能干的无用之人、年老的年轻人、无益又费钱的节约、奢侈的贫困、花功夫的即兴创作、便宜的高级货、危险的安全保障。如此收集起来一看,我甚至开始觉得,这不是单纯的游戏,而是透视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修饰技巧。”
刚刚下注释:我并不能理解这样的趣味。在我把一个字一个字迁到屏幕上时,我似乎又得到了一种新的、一种不同的感受。这种亲近文本的最古老又笨拙的方式,让我获得了一种新体验,是与仅仅是肉眼、笔触碰到过文字不同的感受,似乎也更加深刻了。
这也让我自然而然的联系到另两段文本:
“所以通过这些“工具”的手感,能抓住赋予自己描绘的人体以触感和体温的契机。现在全部用电脑来操作,所以在这一点上变得困难。”
“颜料、纸、画笔这类东西不单单是作为工具对艺术做出贡献,而是一边反抗,不甘心听凭艺术家摆布,一边和艺术家共同创造出艺术史,这样来思考的话,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不很好地引进电脑作为“物”的顽固性、笨拙性和缺点,那么无论多么便利,电脑也不能完成它作为工具的任务。”
这些器具本身就有其意义,过分地(过度地)将其取缔与消减也确实会影响“手感”,也就是灵感。在我得到的另一个体会便是:对工作来说,重要的是存在妨碍你工作的因素。
【07】在与语言漫步中创造语言的可能性。
书中举有非常多的例子来说明语言美。美在文字、美在发音,美也在于“其中不少词,中国人感觉到它的美丽,逆向输回中国,当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心里非常高兴。”
““空港”这个词也许不是日本人的创意,而是将欧洲语言原样翻译过来后产生的词语。英语的airport、德语的Flughafen等等,直译的话,就成了“空の港(天空的港口)”。从某种外语直译过来,就能创造崭新的词语,这也有点不可思议。”
因此,美不仅仅美在形式、美在发音,也提供了另一个发现美的可能性,美在创造和传播,甚至于,更深刻的来认识,在语言再加工与反向输回输出地的这一过程中,这种交替和传播,也确实很美,是语言中所包含的美。也是,语言创造与再创造中的美。
“我不认为光是词汇量大,小说就会变得丰富,可是,仅因为想不到“肘窝”这一单词这样的理由就不谈“肘窝”了,实在有些可悲。”创作不仅仅是表达感受,如何用精妙的语言言情达意,也尤为重要。这再次说明语言无鄙视、情感更不分高低的道理。
《和语言漫步的日记》读后感(四):和语言漫步
和语言漫步
说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是这样的场景:一双脚,走在蔚为大观的语言之海中,是像跑着,又如跳跃般的步伐轻盈,在语言中行走,应该是为漫步了罢。
在语言中观察到的,多种可能性,由语言本身带来的也好,因为语言而造成的影响也罢,总之,不可避免的多次提及“语言”一词,确实是必要也是必须的。
【01】尝试在不同语言中发现可能性。
就作者而言,在德语和日语之间的转化与漫步,带来的体验和可能性也是尽可能多的。不同语言体系,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单就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语言是文化的表达,是文化输入输出的门户,这一点,语言更是不可或缺,不能懈怠的。从不同的语言体系中,看同一个词的意思也大为不同。
例如,文中提到的:“在德国,临近一年的最后一天,人们会互相寒暄说,“Guten Rutsch!”直译过来就是“滑好!”,意思就是祝你顺利地滑入下一年。我每次听到这样的打招呼声都会想到,因为在年和年之间有什么障碍物,所以也有人不能顺利地滑入,永远地留在边界线上了吧。我虽然喜欢留在边界线上这种意象,但是,留在时间的接缝上则意味着死亡。”这个例子,我觉得有趣又有探究性。可探究性的有趣之处在于,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这样的例子和对比其实数不胜数,文中也提及他例,但我个人对此最有兴趣。不由得让我想到,跨文化交际课程中曾学到的,在东西方语言文境中,对“龙”一词的认识与理解。
东方文化语境中,赋予“龙”以“吉祥富贵”一意义,而与之大不相同的是,西方语境中,用“master”来形容“天子的象征”。这点是非常有趣的。原来东方的天子在西方文化的理解是怪物。花白头发茂盛的学士指着天空中漂浮的龙样的祥云大喊:“Help!Help!master!master!”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方皇室王朝成员看到此忍不住纷纷下跪并惊呼:“上天有灵!上天有灵!”比较起来也颇有趣味。实际上,语言离不开文化。说文化是语言的支撑、语言是文化的表达,其实也并不过分。再次证明,尝试在不同语言中发现语言的可能性。
【02】尽可能多的了解不同语言的可能性。
似乎从一种语言看文化阅读文本,会稍显孤僻,在打出孤僻这一词时,又蹦出“不足”一词,也有贴切之感。用再情绪化、感情丰沛的话来形容:“甚至是些许的寂寞呢”。
这也提醒我,是不是借助另一种更贴合文本的语言去读文本本身,得到的理解也会更丰富、更也好茂盛?在此,我的脑海里不由得有一种蔚为大观的场面。
书中这样的句子,觉得很有摘抄的必要:“我无论做什么都以语言为指南针,决定前进的方向。语言里保存着智慧,比我个人大脑里的要多。而且语言不是一种。虽然有时候,两种语言各有主张会发生口角,但是,我认为,比起一种语言嘟嘟囔囔自言自语,让两种语言在自己的头脑里对话能产生广度更大、密度更高的答案来,难道不是吗?”
两种语言打架的情况,似乎与我曾遇到过,甚至现在还在遭遇的,意识打架的情况有些相像。起先,我对这种“打架”感到痛苦和苦闷,再后来,我似乎慢慢接受这样的打架和挣扎了,因为比起此前脑海里“非黑即白”这样简单的思维,我更慢慢享受,两种或者多种思维碰撞、“打架”的感受了,火花总是在这种状况下产生,念及此,我便由衷的感到幸福和满足。之所以提到我个人的这段经历,是在更好的说明,我自己有在感同身受作者本身的遭遇罢了。但这样的理解是否过分浅薄?或是不自量力?我觉得,在文字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天生形成的壁垒与屏障。去感同身受和置身于其中,这样真诚的感情,我认为是不分高低和没有门槛的。主动抒情与在作者的带动下“被动抒情”,两种抒情方式不同,并不能由此决定所抒发的情感的好坏,更无所谓高低。一个人所能抒发的感情的可能性,与这个人本身的经历境遇,是脱不了干系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也是不接受“感情之高低贵贱的”。这也让我想到余华和食指的小我与大我之争。即:站在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经历来评判他人的感情,其实在评判的过程中,这种行为就相当于是把一个人的遭遇也加以批判化了的。这一点,我还是不能苟同,是否有些残忍和不堪呢?
【03】在不同语言中发现语言本身的可能。
这里提到的“语言本身”是纯粹的和不加以任何修饰的。单用语言来解释稍显枯燥和晦涩乏味,用书中的例子来阐述更有趣一些:“从“外(外面)”这个日语单词里我感觉不到快乐。倒不如说,它让人感觉不安。我说的快乐的“外”接近于“アウトドア”,(原文注释:日语用片假名标识外来语,此处为outdoor,户外。)但是这个外来语稍稍沾染了商业性的油垢,让人觉得不够买露营用品或滑雪用品就不许与大自然接触似的,这一点令我不爽。不要片假名,单单“到外面去玩”就行了,难道不是吗,我想。像孩子那样。”
最后一句,“像孩子那样,”莫名地打动我。这是语言本身的吸引力,在阐述中发现语言本身,不带过多的修饰和点缀,就像孩童那样单纯,反而显得十分珍贵。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也始终认为,如此珍重语言本身。也引发我的另一个思考,独立使用语言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在愈来愈严苛的语言环境下,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让这样纯粹,回归于语言本身的表达,显得渺茫却如此珍贵。
语言回归语言本身,单纯的美好,甚至于为一种追求。我又很自然而然的想起,泉水接受采访时的话:“我十分重视语言。”这样的话,我一直铭记于心,并时时想起。
语言在时代的大环境下,能保持本身就已经十分珍贵而不易了。独立使用语言的可能性,我悲观地想,大概是不会存在了。便放任成一种理想主义好了。
【04】语言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对生活的影响。
“在野外漫步搞调查,所以应该属于“filed work (田野调查)”,然而是因为让诗人“野放し(放任自流)”太危险还是怎的,好像被警察误会为形迹可疑的人了。”
书中提到这样的例子,还是一副画面进入到我的脑海里:拿着放大镜的研究学者,专心致志搞研究的时候,突然从背后被警察揪起衣服领子,这样的画面确实有些滑稽。可笑之余,其实不免发现,这便是语言影响实际生活的体现。既生动又常见。不同语言环境下,漫步的步伐是否也会不同?连漫步的频率、保持的呼吸也不相同?我对这样的问题充满好奇,与此,又抱有困惑。甚至于漫步的姿态也不相同了呢。
【05】在镜子中发现语言和与语言漫步。
提及书中文字的来源,我喜欢作者这样的话:“我决心用日记这种镜子,照照自己头脑中的活动。”用“和语言漫步”概括显得更有情感和吸引力。较之于,晦涩乏味的理论化用语,我更倾向,也更喜欢用感情丰富的词汇来表达。与语言漫步是作者每天的经历,也是我每天的遭遇,前者是规范化的创作和研究,而后者,就我来说,只是读和体会罢了。
之所以如此沉迷“与语言漫步”这样浪漫的表达,也更印证我对语言通俗化和浅显化表达的倾向。似乎有这样一幅画面在我眼前浮现:壮观的语言之海,我步履轻缓于之上,也仅仅只是走在那片大海中的小小的小小的海面之上。只是想到这样的画面就让我觉得光明和希望。
在镜子中与语言漫步,我把这样的行为视为一种反思。“决心用日记这种镜子,照照自己头脑中的活动”。这句话也莫名打动我也戳中我的心。
【06】在语言中娱乐语言。
“我试着给不能拆分的单词加上矛盾的形容词,感觉脑子的一部分放松了。”
更吸引我的是这样一段话:“我在温泉中做着这样的文字游戏,代替了按摩,享受其中的快乐。封闭的门户开放、无视国民的民主主义、病态的健康、失败者的胜利、憋屈的自由、能干的无用之人、年老的年轻人、无益又费钱的节约、奢侈的贫困、花功夫的即兴创作、便宜的高级货、危险的安全保障。如此收集起来一看,我甚至开始觉得,这不是单纯的游戏,而是透视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修饰技巧。”
刚刚下注释:我并不能理解这样的趣味。在我把一个字一个字迁到屏幕上时,我似乎又得到了一种新的、一种不同的感受。这种亲近文本的最古老又笨拙的方式,让我获得了一种新体验,是与仅仅是肉眼、笔触碰到过文字不同的感受,似乎也更加深刻了。
这也让我自然而然的联系到另两段文本:
“所以通过这些“工具”的手感,能抓住赋予自己描绘的人体以触感和体温的契机。现在全部用电脑来操作,所以在这一点上变得困难。”
“颜料、纸、画笔这类东西不单单是作为工具对艺术做出贡献,而是一边反抗,不甘心听凭艺术家摆布,一边和艺术家共同创造出艺术史,这样来思考的话,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不很好地引进电脑作为“物”的顽固性、笨拙性和缺点,那么无论多么便利,电脑也不能完成它作为工具的任务。”
这些器具本身就有其意义,过分地将其取缔与消减也确实会影响“手感”,也就是灵感。在我得到的另一个体会便是:对工作来说,重要的是存在妨碍你工作的因素。
【07】在与语言漫步中创造语言的可能性。
书中举有非常多的例子,来说明语言美。美在文字、美在发音,美也在于“其中不少词,中国人感觉到它的美丽,逆向输回中国,当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心里非常高兴。”
“ “空港”这个词也许不是日本人的创意,而是将欧洲语言原样翻译过来后产生的词语。英语的airport、德语的Flughafen等等,直译的话,就成了“空の港(天空的港口)”。从某种外语直译过来,就能创造崭新的词语,这也有点不可思议。”
因此,美不仅仅美在形式、美在发音,也提供了另一个发现美的可能性,美在创造和传播,甚至于,更深刻的来认识,在语言再加工与反向输回输出地的这一过程中,这种交替和传播,也确实很美,是语言中所包含的美。也是,语言创造与再创造中的美。
“我不认为光是词汇量大,小说就会变得丰富,可是,仅因为想不到“肘窝”这一单词这样的理由就不谈“肘窝”了,实在有些可悲。”创作不仅仅是表达感受,如何用精妙的语言言情达意,也尤为重要。这再次说明语言无鄙视、情感更不分高低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