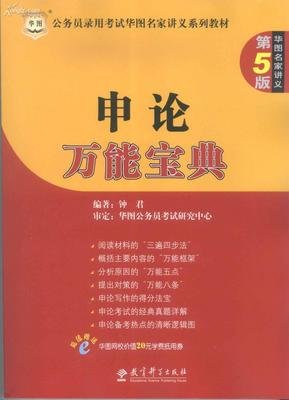义疏学衰亡史论经典读后感有感
《义疏学衰亡史论》是一本由乔秀岩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3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义疏学衰亡史论》精选点评:
●皇侃义疏之科段法可谓结构主义,二刘及孔义疏之文献法可谓实用主义。看起来是趋近细读的一种跨越,但义疏并非普通文学,用乔秀岩的话,是「文字通理之学」。「通」为首要,而皇侃倾向于经文之上创造建立逻辑论理之结构,二刘及孔氏倾向于经文之下分析罗列现实事实之细目,故「二刘打破旧义疏学传统,以后义疏学已不得更为义理、义例之思考探讨,此所以义疏学之不得不衰亡。」乔秀岩的这一文献分析,其实颠覆了传统义疏作为文献证据的看法,而将义疏作为作者的独立创作,以此探讨魏晋时期学术思想演变,文献举要与结论十分清晰,可见读书时的洞察力之要紧
●义疏学并不是实事求是的学问。
●以纯文献学的手段从茫茫注疏中,探索诸家以何作、何以作,爬梳材料之力不可谓不勤。此种读书法甚有启发。缺点在引文不够通畅,结论稍有浅显。
●读书极细密!
●对皇侃、二刘、孔颖达、贾公彦的不同治经方法,以及隋唐之际义疏学学术范式之转变的梳理极为细致。过去读贾公彦《周礼疏》、《仪礼疏》,即疑惑贾疏文辞敷衍,多有窒碍难通之处,还有不少明显违戾经、注的低级错误,读完本书第五章立即涣然冰释了。
●对正文细致的比对梳理实在没啥兴趣,看了各章的引言和结论。门外汉不做具体评价,但是感慨于作者写作旨趣。附录有趣。
●标题党!跟衰亡没啥关系,就是对几本义疏的研究
●粗读一过,收获到的最大启示是跳出定式化的经学史名词概念,真正发现经学文献的可读性。旧义疏学重在通理、建立逻辑结构,自二刘至孔氏而转为“现实、合理、文献主义”,亦即旧义疏学之衰亡。作者于字里行间无处不流露出的诚意令人钦佩。
●明天开始将要在京大上一星期作者的汉唐经学注疏史课,姑且预习一下。本书为乔秀岩先生的北大博士论文,在细读中觅得了许多平实而准确的规律,探知了许多困惑前人已久的悬疑(如贾公彦常犯张冠李戴、附会强解的毛病;又如不可机械地以汉学的“章句名物”破宋学的“义理心性”,须知郑玄义疏,仍以内部解经为宗旨。凡此不一而足)。若非通览自汉至清诸经主要注疏恐怕不能为之。本书最大的缺点作者自己也提到了:令人窒息的大段引用配上忘带回车键的排版。想必要处理十三经注疏这样的复杂文本,博士生时期的乔先生也不是没有头疼过。
●现实、合理、文献主义与胥吏之学,实用,不留余地;思维、推理、经注主义与君子之学,不敷实用,精美,多胡说、废话(精辟)
《义疏学衰亡史论》读后感(一):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的内容与方法
全书以《论语义疏》、《左传正义》、《礼记正义》、《周礼疏》和《仪礼疏》为核心材料,辅以《礼记子本疏义》和《孝经述议》等佚书材料,详细分析了皇侃、二刘、孔颖达和贾公彥的态度立场和学术方法。皇侃在整理旧说的基础上建立科段,为讲明经文先后条理之逻辑关系,穿凿附会在所不惜,是义疏学之典型。二刘力排穿凿,广引群书以书证事例平实解经,呈现出现实、合理、文献主义的特点,是义疏学转折之关节点。其后孔颖达等继受二刘的方法和立场,虽分科段但专主罗列事实分析经文、不为抽象附会,又以“疏不破注”的原则统一解释体系;贾公彥仿效逐句疏解的形式,抄撮旧疏,但好援他例比附释经,又喜引用改造先儒之巧说,故每多舛误;义疏学至此已丧失内生的活力。观作者探讨经学家的风格和缺陷,好似谈论亲朋近友,极为熟稔。又思考作者的论证方法,心得有三:
第一是读书为本。首先,作者所有立论的根基都在于“读懂每一句话的所以然”,欲做到这一点读书必须细致,连经学家用字的语气都要反复推敲。如第一章论皇侃引书特点,有“径称其名引录”,还有间引自江熙者,二者便书法不同。又如第二章论辨识二刘《书》疏之法,考虑到“窃以为”与“今删定”之间语气迥异。
同时对读比勘时,一字或数字之差亦需留意深思。如第二章分析引文33二刘《左传》疏引《大宗伯》注而窜入“三百里”,并改“方三百里”为“方四百里”,想要发现其中二刘饰己意的痕迹,思维必须转三道弯:先究明《大宗伯》注之义为何、再将之与《诗》疏和《左传》疏对比分离出二刘之论、最后探究二刘为何作此论。又如第四章分析《礼记子本疏义》与孔疏差别,发现孔颖达等基本全袭皇侃,却改“尊尊”为“尊宗”, 一字不同便致意义大异。
其次,作者的论证过程实际上就是作者读书的过程,主要分析也是由一条条读书札记构成。如第二章以《左传》僖公四年“筮短龟长”论二刘与贾公彥之不同,第三章中以《乐记》的《乐本》、《乐论》二章比较皇、孔之不同,第五章以贾公彥解“三德教国子”和“摄盛”谈解经特色,即使将这部分单独分离出来,也可当一篇精悍的札记。不过,文章采取这种“札记体”,在行文时大段征引经疏,又将论证以案语的形式附后,这往往会给读者造成很大的困扰,使人初不知论旨所在。
最后,作者每一章基本都是以一到两部经疏为中心展开分析。有论者以为是书不是“以问题为中心”,而是“以书本为中心”,导致是书结构松散。而以鄙意猜度,作者恐怕是有意抗拒现代美式学术的“问题中心主义”。作者在序言中以为“学术随时而异,唯读书千古无替”,在第六章中又说义疏学非实事求是之学,清代学者以己度人实失其旨,“盖学术无绝对之标准,今日风气趋于追求历史真实之科学,亦不过一时风气而已。”因此,作者分析经疏一方面是为讨论问题,另一方面是为将理解经疏的方法和过程展现出来,而且后者可能更加重要,故书中知此“斯可以读义疏”之类的语言屡见不鲜,第三章更以读通《礼记正义》之法作为最后结论,皆不啻在为读经疏者指点门径。
第二是不校不读。首先,经疏中引文必核原书。第一章“皇侃引书杂识”中指出皇侃注意《集解》抄本之不同文字、既据《尚书》伪孔传又特引郑注、多引《白虎通》无引《家语》、除《白虎通》《韩诗外传》等外引书绝少,作者必是先一一检皇氏引文原书。第二章中指出二刘好罗列事例为证,且多出自史传,并旁及诗赋,亦由先一一检查二刘例证出处。检查原书、前后对比的过程中,皇侃之故为巧说、二刘之机械作为等特点,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
其次,讨论经疏必以其他相关经疏参验,尤以第四章“佚书验证”为典型。作者取早稻田大学藏《礼记子本疏义》与《礼记正义》孔疏所引皇侃之文对读,故知孔疏歪曲皇侃之说,不取其大义而撷取末义,以致论理不通;又删减皇侃疏文的声训和修辞。作者又以日本林秀一复原的《孝经述议》与《尚书》孔疏所引二刘之说对读,故知孔颖达等大删二刘非诋先儒之语,进而知孔疏所引二刘前后矛盾之由。
最后,引用经疏必择适当版本。作者另有《文献学读书记》专门讨论版本问题,仅以本书而言,文章小注中,作者多次提到经疏不同版本间文字的差异。附录《〈仪礼〉单疏版本说》详细考察了《嘉业堂丛书》本、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张敦仁顾千里校本、宋版单疏原本和公善堂覆刻本等版本的价值与相互关系。
第三是先通义例。作者在目录后小序中说“读书须知三事:知文、知事、知意。”所谓“意”即经学家立说之旨趣。作者前两章有一个基本预设,即每位经学家必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解释风格和方法,这也就是经学家个人的义例。作者讨论问题的思路,就是先读懂疏文、比勘它经、归纳义例,然后将经疏各还本家、为之树立方法主义。第二章末作者便总结归纳出皇侃是思维、推理、经注主义,二刘是现实、合理、文献主义,后者是前者之反动。之后三、四章便是以《礼记正义》、《礼记子本疏义》和《孝经述议》等书反复验证此观点,一章之内竟至7次重复。第五章又是用同样的思路归纳出贾公彥编订旧疏时所创之“新义”。
第六章看似作者是在延续前文继续申论贾疏,但作者此章实欲讨论整个义疏学之义例,相当于全书真正的结论。作者认为义疏学是通理之学,义疏家所论只是想讲通经注背后深意,不为实事求是,历史事实为何既非其所知,亦非其所欲知。故通义例方为义疏学之要旨,发现义疏家的通例才能理解他们发论之由,了解义疏家的训诂才能明白为何不许他训。发现义疏家通例的方法,又在于精细读书,留意义疏家反复提到的训诂和解释,思考经疏说法间的体系。此方法进路与皮锡瑞等传统经学家依赖史传等外缘性材料立说大不同,非深入到经学文献内部不可。
本文为读书后反思学习作者方法之作,不欲仿效书评体例故意吹毛求疵,但读完全书仍有一些想法不吐不快。是书所论从皇侃到二刘的学风嬗变只能说是义疏学衰亡之表征,而义疏学之学风嬗变的原因是书大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言二刘为皇侃之反动,只说“二刘出自卑贱,又值世乱,不负任何传统,故敢破坏旧学传统”;谈南北朝学术风气,是书只举刘炫、王邵和颜之推三例,且后二人都只寥寥数语。第六章末尾谈“训诂固化”,以为训诂之说趋于定势,学者套用成说多不思考,遂致唐以后义疏学废绝。凡此涉及历史背景和长时段的解说都太过简化,有论者称可谓知其人而不论其世,与书名“史论”颇不相符。经学家是否都是哲学家,都能超越于时代之上只专注于经学文本?恐怕这只能是读书人美好的想象吧。
《义疏学衰亡史论》读后感(二):华喆:读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
2013年9月,乔秀岩先生的博士论文《义疏学衰亡史论》在台湾万卷楼出版。从我第一次读到本书全文,到今天为止,正好十年。十年之中,在当今学者的不断努力之下,有关南北朝隋唐义疏学的论文、专著大量涌现。然而像这部书一样,在艰深的经说分析中,既能让读者保持继续阅读的热情,又能激发读者更进一步思考的著作,可以说绝无仅有。
本书原题叫做《南北朝至初唐义疏学研究》,是乔秀岩199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论文,在2001年作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由东京白峰社出版日文版,改题《义疏学衰亡史论》。由于日文版读者有限,长时间以来,乔先生的博士论文仅在以北大为主的一部分教师与学生中小范围流传。2013年,恰在日文版发行一纪之后,本书中文版终于出版。故此不揣鄙陋,将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记录下来,希望能够让更多读者了解此书的价值。 首先,请允许我简单梳理一下本书的论题与主要线索。 由原题和后来改用的题目“义疏学衰亡史论”可以看出,本书的主旨在于描绘出从南北朝到唐初义疏学盛极而衰亡的过程。然而这富有冲击力的题目却是对读者常识的一大挑战——我们都知道所谓“十三经注疏”,其中《五经正义》成于孔颖达之手,《周礼》《仪礼》二疏为贾公彦所作,此外唐疏还有徐彦《公羊》疏和杨士勋《穀梁》疏,以下《论》《孝》《雅》《孟》四疏均成于宋代,更不用说清人还创作新疏,成果斐然,自谓胜于唐疏。本书研究断限只及于初唐,并不涉及宋代以降的群经义疏。如此说来,将南北朝至初唐义疏学称之为“衰”,固无不可,却以“衰亡”命名,那么宋代以降的义疏作品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作者在书中并没有作正面解释,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我们阅读此书必须把握的一个关窍所在,即在作者眼中,义疏学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乔先生看来,义疏固然是一种经学文献的编排方式,但义疏学并非只是以注解经,以疏释注的形式,而是有其特定的学术方法。所谓“义疏学衰亡史”,是指义疏学作为学术方法的衰亡,而非义疏作品的消失。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乔秀岩先生充分认识到了唐初以前义疏与宋人乃至清人义疏有着根本不同,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清人义疏以“实事求是”自命,然而义疏学并非实事求是之学——但义疏学到底是什么,作者却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读这部书的“书眼”,必须时刻带着这个问题进入本书的每一段讨论,故此这里请恕我先卖个关子,到了后面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本书第一章的研究对象是皇侃的《论语义疏》。对于南北朝义疏学研究者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文献不足征。尽管《隋书·经籍志》中冠以“义疏”“讲疏”之名的著作不下几十部,然而今天能够看到全貌的,却只有皇侃《论语义疏》一部而已。前人对此研究相对较多。作者将皇侃《论语义疏》的学术特点概括为两点,一为建立科段,二为整理旧说,且从皇侃引书的一些特点出发,分析皇侃整理旧说的基本手法,为前人所未曾注意之处。 本书的第二章是关于二刘即刘炫、刘焯的学术风貌。这实际上是本书写作中的第一个重大关节点。二刘著作除《孝经述议》的一部分内容以外,今天已经无法看到。然而由于孔颖达《五经正义》中对二刘多有征引,经过清儒刘文淇作《左传旧疏考正》之后,我们已经可以通过《诗》《书》《春秋》三部唐修注疏,来讨论二刘的学术特点。书中通过对孔颖达《正义》进行文本分析,确定其中出自二刘的部分。同时又与皇侃《论语义疏》、贾公彦《周礼》《仪礼》二疏进行比较,将二刘学术特点概括为“现实、合理、文献主义”,与皇侃所代表的南朝学风,以及贾公彦所代表的北朝学风,有明显不同,并说明了二刘对于孔颖达以降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乔氏与以往经学史家的不同之处。自皮锡瑞《经学历史》以降的传统经学史著作,均强调南北朝至隋唐的经学流变,存在南学与北学的分合问题。在《经学历史》中,皮锡瑞对于南北学的分立与统一有一个著名论断: 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1] 这段话对于后世南北朝隋唐经学史,乃至学术史、思想史的影响,研究者有目共睹,自然不必多说。在皮锡瑞看来,南学北渐,最终取而代之,正是从二刘开始。他的理由是从李延寿的《北史·儒林传序》而来。《北史》记载北方《尚书》学传习,有“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的记载,皮氏以费甝《尚书义疏》是南学产物,自然是二刘“北人而染南习”的例证。除此以外,按照北朝史料之说,北方学者《左传》用服虔注,二刘开始研究杜预《集解》,自然代表南学立场。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尚书》用孔传,《左传》用杜《解》,又广泛吸收二刘之说,充分说明了《五经正义》是立足在南学基础上的经学统一。皮氏的观点立足于史传等外缘性材料,并未对与二刘有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在今天看来,实在过于简单粗放,有其自身的时代局限在内。然而这一结论却被后来的经学史研究者甘之如饴,奉为金科玉律,并没有人去反思它成立的根据何在。 乔秀岩先生这部著作的精华恰恰在于,他直接从学者的经说个案出发,来判断学者的研究旨趣与学术特点,而非借助隔着一层的外缘史料,避免了雾里看花、管中窥豹之弊。实际上,二刘的学术风貌并不是南、北学中某一支派的延续,而是代表了义疏学研究方法的一次转折。简单来说,皇侃等人更为注重经书文句的内在逻辑,从经、注之中概括出大量的词例、句例,立说务于精巧,有时甚至不无附会之嫌。二刘的学术特点则与此大相径庭,注重史事对经书的外部证明,往往以“无义例也”否定经文义例的存在,排斥穿凿附会之说。可见由南朝至隋代,在当时最顶尖的学者之间,学术旨趣的变化是相当明显的,而且隐隐有针锋相对之意。故此本章结尾处强调义疏学的衰亡始于二刘,正因为二刘打破了南北朝义疏学的既有传统,使得“义疏学已不得更为义理、义例之思考探讨,此所以义疏学之不得不衰亡”。那么二刘何以能够不受旧有传统的约束?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二刘身份卑微,并不是在南朝建康这样的文化学术中心成长起来,而是生逢乱世,并没有接受任何学术传统,在他们眼中,传统义疏学不过是“皇帝新衣实无其物”而已。故此二刘以知识的广博代替了思考的精细,重新树立了解经的规则与方法,形式上仍为义疏之学,但在内容上已经截然不同。作者在后记中将此评述为“隋代的学术革命”,乍看起来似乎夸张,仔细品味却会觉得恰如其分。 本书第三章是《〈礼记正义〉简论》,实际仍是上一章话题的延续。因为上一章中已经说明,孔颖达《诗》《书》《春秋》三部正义,本自二刘义疏,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特点,也与二刘相合。但是《礼记正义》的性质更为复杂,按照孔颖达的说法,他“仍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也就是说,《礼记正义》是以皇侃疏为基础,参考熊安生疏编纂而成的,那么《礼记正义》是否同样具有二刘的学术特点呢?作者用了五个小节,分别从孔疏不取科段、摒弃附会之说、疏不破注、否定义例等几个方面,论证《礼记正义》学术风格仍与二刘保持一致。由此可见,尽管《礼记正义》主要参考皇侃疏,但其学术方法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正好可以说明二刘对于孔颖达影响之深,同时也可以印证作者提出的“义疏学衰亡”之论。 本书第四章是佚书验证,即作者利用日藏皇侃《礼记子本疏义》与刘炫《孝经述议》两种佚存资料,对前三章的结论进行验证。这两种残卷目前分别藏于早稻田大学与京都大学。《礼记子本疏义》在19世纪末即已被人发现,罗振玉在1916年使用石印技术对这一残卷进行了复制并撰写题跋,当时国内学者如孙诒让、胡玉缙等人都曾对这一残卷进行过初步研究。《孝经述议》残卷出现的时间略晚于《礼记子本疏义》,是1942年武内义雄在整理舟桥清贤旧藏时发现的,仅有一、四两卷。1953年,林秀一出版了《〈孝经述议〉复原研究》一书,利用日本所藏诸钞本,恢复了此书大体面貌。由于时代原因,这两种残卷多数清代学者都无法看到,直至20世纪后半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才开始陆续出现。除了林秀一对《孝经述议》进行复原研究以外,还有铃木由次郎、山本严等人对《礼记子本疏义》所作录文及考订,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文献复原、整理层面,对于文献的学术史意义发掘犹嫌不足。比起今天的学者足不出户即可在网络上看到这两种残卷的全彩图像,本书作者在写作之初,却只能利用《子本疏义》的珂罗版复制本和林秀一书中模糊不清的图版,条件相差甚远,但这却是最早一篇针对这两部残卷,从学术史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作者比较了《礼记子本疏义》与《礼记正义》之间的文字异同,确认《礼记正义》大半袭取《礼记子本疏义》,同时又删去皇侃科段、义例等附会之说,从中可见皇侃、孔颖达的学术倾向,大体与本书第一、三两章所得到的结论吻合。至于《孝经述议》,又与本书第二章的结论吻合。由此可以确认作者所论的“义疏学衰亡”以及“隋代学术革命”之说。 本书第五、第六章分别是“贾公彦新义”与“贾疏通例”,均为有关贾公彦《周礼》《仪礼》两疏的研究。这是全书之中作者着力最深的部分,也是阅读起来最为艰涩的部分。贾公彦不仅曾经参与《五经正义》的编订工作,而且两疏成书均在《五经正义》之后,是否贾疏也如孔疏一样,是二刘的学术方法的延续呢?作者认为恰恰相反,《二礼疏》中的内容与二刘的学术方法大相径庭,有着明显不同。那么岂不是与作者的“义疏学衰亡”之论正好相反吗?作者指出,贾疏因袭南北朝旧疏,完全抄撮而成,前后矛盾之说处处可见,体裁又仿效二刘、孔颖达,堪称“新瓶装旧酒”之作。仅就态度而言,二刘、孔颖达对于南北朝旧疏不满,一一予以改正,有自己鲜明的学术立场。但贾疏却完全不同,我们通过贾疏只能看到南北朝旧疏的学术立场,贾公彦只是将旧疏删改整理,置于经注之下而已,而且态度极为草率,导致错误丛出,甚至文辞不通,故此很难就《二礼疏》来讨论贾公彦的个人特点。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作者所说“义疏学衰亡”的理由何在,二刘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虽然是对传统南北朝义疏学的否定,但他们仍然尝试提出新的经学解释,只不过这种文献主义、合理主义的解经方式并不具有活力,在孔颖达之后并无法延续下去。贾公彦的《二礼疏》已经放弃了在这方面的努力,仅仅是重新编排整理旧有文献,在《周礼》《仪礼》二疏之中没有学术理想,只是单纯弥补礼疏之阙而已。 关于第五、第六两章,我们应当注意到,不论是在正文,还是在后记中,作者都自称这部书稿其实是他在阅读《仪礼疏》时的副产品。也就是说,作者在这两章中所处理的问题,其实是作者在本书写作之初所思考的基本问题。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读者在阅读第六章“贾疏通例”时,可能会感到这部分似乎游离于本书主题之外。实际上,当第五章“贾公彦新义”结束时,其实有关“义疏学衰亡”的讨论已经可以到此为止了,但作者仍然要加上这一部分,意在回到我们前面提出的那个基本问题——“义疏学是什么”。作者将此章分作三节:第一节“义疏学不为实事求是”,明确义疏学与清人学术的不同,将义疏学确定为“文字通理之学”;第二节“通义例为义疏郑学之要旨”、第三节“训诂之固化”,说明《二礼疏》乃至义疏学整体的主要内容。这三节表明了作者对于义疏学的基本理解,这种理解恐怕没办法用鲜明的定义表现出来,以至于我们只能通过作者整整一章的分析去体悟何为义疏学。所以这三节内容看似与“义疏学衰亡”的主线无关,但却是理解这一主线的关键。而且对读者来说,第六章可能是全书最具示范意义的部分,等于在为我们一一演示,阅读义疏学著作应当留心哪些地方,遇到难解之处应当如何解决。假如读者有尝试阅读义疏的打算,那么第六章就是尤其需要我们仔细对待的部分,其中不乏金针度人之处。这里面包含着作者多年浸淫于《仪礼疏》中最为深粹的功夫。我以为如果乔秀岩先生当初不写这本书的话,第一至四章的内容,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也许会有大陆学者来完成,但是恐怕永远不会有人能够把第五、第六章写出来。 从皮锡瑞1907年在长沙思贤书局出版《经学历史》一书以来,“经学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然而回顾经学史在这百年间所取得的学术积累,我们却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现当代学者在经学史的基本问题上仍然重复着皮锡瑞、梁启超等清末民初学者的观点,比如两汉今古文问题、南北学问题、汉宋之争问题等等。他们不仅仅在经学史观上难以超过前人,而且对基本文献的掌握程度又大大不及,导致我们看到目前市面上冠以“经学史”之名的著作虽然不在少数,结果内容往往大同小异——或将中国哲学史改头换面,又或从经学的角度对中国通史加以串联,还有些干脆只是加长版的目录提要罢了。能够突破以上诸多窠臼者,不过数人而已。本书之所以能够突破传统研究思路的羁绊,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在于作者能够直接回到具体的经学文献讨论中,直接面对《五经正义》等经书注疏。当作者把一个个具体的“点”如皇侃科段说、二刘的文献主义倾向、孔颖达与二刘关系、贾公彦抄撮旧疏等等夯实之后,关于“义疏学衰亡”的这条主线也就自然浮现了出来。 关于本书的研究特点,或许作者本人不同意,但我还是认为,这与日本学者的中国经学研究积累不无关系。在日本,中国经学研究隶属于中国哲学研究方向之下,而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又少有高谈义理者,大多都以朴实的文献研究见长。在我看来,作者精读文献的功夫,包括对于文献版本的选择以及搜集文献资料的视野,都与他在东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学术训练相关。至于作者在文章中的一些用语,比如描述二刘学术时,使用的“文献主义”“合理主义”等词语,在日本前辈学者的论著中也一直使用(参见加贺荣治《中国古典解释史·魏晋篇》等),在此前的汉语学术著作中却从未见到过。然而这并不是说本书只是一部非常典型的由日本学者完成的中国经学研究专著,我们可以注意到,本书恰恰没有多数日文学术著作所具有的通病,即资料收集完备,而结论不够明晰,又或个案分析充分,但整体线索不够突出。事实上,作者在下结论时毫无日本学者惯有的迂回婉转、拖泥带水,其中某些结论反而具有相当的“穿透力”,同时主线又非常明确,经常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如果读者并无意纠缠在本书的诸多细节分析之中的话,我认为只是阅读每一章后面的结论部分,就足以了解作者的主旨了。 当然这并非是说本书是一部无可挑剔的学术著作。其中仍然也有问题存在。从宏观角度来说,本书讨论的是一个从南北朝至唐初学术方法的演变问题,然而实际讨论的对象却集中在礼学方面,仅有皇侃、二刘、孔颖达、贾公彦等有限的几人或几部著作,这些例子是否具有足够的普遍性?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各自时代的学术主流?由于我们没办法看到更多的义疏学资料,只能利用现存文献来讨论这一问题,故此我们只能说在现有条件下,作者的分析与结论是成立的,但“义疏学衰亡”是否是曾经存在过的一个历史过程,恐怕还仍需存疑。[2] 在全书结构上来说,现有篇章安排虽然也有完整的内在逻辑,但是略微给人以过于围绕研究对象,而非问题本身的感觉。譬如第一章讨论皇侃《论语义疏》,第四章讨论皇侃《礼记子本疏义》,是否有可能合并为一章,直接分析皇侃的学术特点,而不必再保留第四章《佚书验证》?这样似乎在结构上可以更加紧凑。在具体结论方面,本书偶尔也会出现前后摇摆不定的情况。譬如本书第二章《二刘学术风貌》第二节“二刘学术推论”中,提到“贾公彦撰疏与孔颖达同时或稍后,而其专门礼学,渊源北朝,方法态度与孔疏大异”。贾疏与孔疏内容大异,读者读过第五、六章之后应当没有异议,但贾公彦“专门礼学,渊源北朝”,作者在第五、六章中竟然没有相关论述,根据究竟何在?我猜测作者的理由在于,《旧唐书》贾公彦本传中称其为洺州人,地处北方,贾氏《仪礼注疏序》中又列举《仪礼》疏家,仅有黄庆、李孟悊二人,很可能都是北方学者,所以作者才有这样的推论。但是今天讨论北朝义疏学,仅能利用《礼记正义》中引用熊安生的只言片语而已,并不足以反映北朝义疏学的全貌,贾疏内容是否渊源北朝,根本无从判断。从第五章的内容来看,作者明确指出贾疏直接抄自旧疏,但就算《仪礼疏》抄自黄、李二家,那么《周礼疏》抄自何处,现在也不得而知。作者在第五、六两章干脆不去讨论贾疏到底应当归入南学,还是应当归入北学的问题,而是把贾疏中的一些通例作为六朝义疏学的共同特点进行介绍。如果作者仍然认为贾疏渊源于北朝的话,岂非贾疏中的通例有可能只是北朝义疏学的特点了吗?故此像这一类问题,我以为还是暂时存疑,置之不论为是。 作为乔秀岩先生的早期作品,这部书虽然在经说分析方面极具特色,堪称精妙,但尚未到达入微之境,因为当时他对于郑玄经学的深入研究还没开始,对于学术史发展的整体脉络把握尚嫌不足。如果读者是资深“乔粉”的话,当然不会漏掉他的另一本书《北京读经说记》。《北京读经说记》中所收录的是作者近年来的重要论文,两相比较之下,大家就可以看到作者在经学研究方面的进境如何。我非常期待日后乔秀岩先生能够重写这部书,立足于他对郑玄以降学术演变的理解,应当会诞生一部全新的作品。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对于一部分读者,包括作者本人而言,本书的真正价值或许并不在于“义疏学衰亡”等等历史问题,这些不过是为了符合现代学术要求而设计出来的“皮相”而已,这本书的意义其实是在引导我们与古人交流。在当代历史学者纷纷努力转变为海量知识的生产者时,这本书在历史学著作中无疑显得有些“异类”。本书作者是一位纯粹的读者。他在阅读相关文献时,能够做到放下肤浅的一己之是非,去专心倾听文献作者的观点。即使他意识到这个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他也会坚持站在作者的立场上去理解作者为什么会出错,而不是对错误结论置之不理,所以他在书前识语中说明,“本论文并非经学家之经学史,而是读书者之经学史论故也”。假如读者能够耐心看完他的每一个分析,一定能够感受到他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在与不同文献的作者进行亲密的对话。这样的阅读体验,是其他的历史论著未曾带给我的。 注释 [1]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第193页,中华书局1959年。 [2] 乔秀岩在《孝经孔传述议读本·编后记》中提出从隋唐之际至唐前期《孝经》孔传文本演变与接收的问题,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作为“义疏学衰亡史”的一个补充。参见乔秀岩、叶纯芳《孝经孔传述议读本》,叶山小书店出版部2015年,第189至221页。 * 本文原载于《哲学门》2015年第2期
《义疏学衰亡史论》读后感(三):面对旧有的经学传统,乔秀岩先生这部作品中提出了许多亮眼的新见
按:新版的《义疏学衰亡史论》已于2018年1月由三联书店推出。这本书在2013年面世之时,即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面对旧有的经学传统,乔秀岩先生这部作品中提出了许多亮眼的新见。他的研究直接从学者的经说个案出发判断学者的研究旨趣,非借助隔着一层的外缘史料,从而避免了雾里看花、管中窥豹之弊。本文是华喆老师于2015年为《义疏学衰亡史论》所撰书评,借此文愿与读者们再次分享阅读《义疏学衰亡史论》的乐趣。
读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
文 | 华喆
*本文原载于《哲学门》2015年第2期
2013年9月,乔秀岩先生的博士论文《义疏学衰亡史论》在台湾万卷楼出版。从我第一次读到本书全文,到今天为止,正好十年。十年之中,在当今学者的不断努力之下,有关南北朝隋唐义疏学的论文、专著大量涌现。然而像这部书一样,在艰深的经说分析中,既能让读者保持继续阅读的热情,又能激发读者更进一步思考的著作,可以说绝无仅有。
本书原题叫做《南北朝至初唐义疏学研究》,是乔秀岩199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论文,在2001年作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由东京白峰社出版日文版,改题《义疏学衰亡史论》。由于日文版读者有限,长时间以来,乔先生的博士论文仅在以北大为主的一部分教师与学生中小范围流传。2013年,恰在日文版发行一纪之后,本书中文版终于出版。故此不揣鄙陋,将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记录下来,希望能够让更多读者了解此书的价值。
首先,请允许我简单梳理一下本书的论题与主要线索。
由原题和后来改用的题目“义疏学衰亡史论”可以看出,本书的主旨在于描绘出从南北朝到唐初义疏学盛极而衰亡的过程。然而这富有冲击力的题目却是对读者常识的一大挑战——我们都知道所谓“十三经注疏”,其中《五经正义》成于孔颖达之手,《周礼》《仪礼》二疏为贾公彦所作,此外唐疏还有徐彦《公羊》疏和杨士勋《穀梁》疏,以下《论》《孝》《雅》《孟》四疏均成于宋代,更不用说清人还创作新疏,成果斐然,自谓胜于唐疏。本书研究断限只及于初唐,并不涉及宋代以降的群经义疏。如此说来,将南北朝至初唐义疏学称之为“衰”,固无不可,却以“衰亡”命名,那么宋代以降的义疏作品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作者在书中并没有作正面解释,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我们阅读此书必须把握的一个关窍所在,即在作者眼中,义疏学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乔先生看来,义疏固然是一种经学文献的编排方式,但义疏学并非只是以注解经,以疏释注的形式,而是有其特定的学术方法。所谓“义疏学衰亡史”,是指义疏学作为学术方法的衰亡,而非义疏作品的消失。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乔秀岩先生充分认识到了唐初以前义疏与宋人乃至清人义疏有着根本不同,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清人义疏以“实事求是”自命,然而义疏学并非实事求是之学——但义疏学到底是什么,作者却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读这部书的“书眼”,必须时刻带着这个问题进入本书的每一段讨论,故此这里请恕我先卖个关子,到了后面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本书第一章的研究对象是皇侃的《论语义疏》。对于南北朝义疏学研究者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文献不足征。尽管《隋书·经籍志》中冠以“义疏”“讲疏”之名的著作不下几十部,然而今天能够看到全貌的,却只有皇侃《论语义疏》一部而已。前人对此研究相对较多。作者将皇侃《论语义疏》的学术特点概括为两点,一为建立科段,二为整理旧说,且从皇侃引书的一些特点出发,分析皇侃整理旧说的基本手法,为前人所未曾注意之处。
本书的第二章是关于二刘即刘炫、刘焯的学术风貌。这实际上是本书写作中的第一个重大关节点。二刘著作除《孝经述议》的一部分内容以外,今天已经无法看到。然而由于孔颖达《五经正义》中对二刘多有征引,经过清儒刘文淇作《左传旧疏考正》之后,我们已经可以通过《诗》《书》《春秋》三部唐修注疏,来讨论二刘的学术特点。书中通过对孔颖达《正义》进行文本分析,确定其中出自二刘的部分。同时又与皇侃《论语义疏》、贾公彦《周礼》《仪礼》二疏进行比较,将二刘学术特点概括为“现实、合理、文献主义”,与皇侃所代表的南朝学风,以及贾公彦所代表的北朝学风,有明显不同,并说明了二刘对于孔颖达以降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乔氏与以往经学史家的不同之处。自皮锡瑞《经学历史》以降的传统经学史著作,均强调南北朝至隋唐的经学流变,存在南学与北学的分合问题。在《经学历史》中,皮锡瑞对于南北学的分立与统一有一个著名论断:
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1]
这段话对于后世南北朝隋唐经学史,乃至学术史、思想史的影响,研究者有目共睹,自然不必多说。在皮锡瑞看来,南学北渐,最终取而代之,正是从二刘开始。他的理由是从李延寿的《北史·儒林传序》而来。《北史》记载北方《尚书》学传习,有“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的记载,皮氏以费甝《尚书义疏》是南学产物,自然是二刘“北人而染南习”的例证。除此以外,按照北朝史料之说,北方学者《左传》用服虔注,二刘开始研究杜预《集解》,自然代表南学立场。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尚书》用孔传,《左传》用杜《解》,又广泛吸收二刘之说,充分说明了《五经正义》是立足在南学基础上的经学统一。皮氏的观点立足于史传等外缘性材料,并未对与二刘有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在今天看来,实在过于简单粗放,有其自身的时代局限在内。然而这一结论却被后来的经学史研究者甘之如饴,奉为金科玉律,并没有人去反思它成立的根据何在。
乔秀岩先生这部著作的精华恰恰在于,他直接从学者的经说个案出发,来判断学者的研究旨趣与学术特点,而非借助隔着一层的外缘史料,避免了雾里看花、管中窥豹之弊。实际上,二刘的学术风貌并不是南、北学中某一支派的延续,而是代表了义疏学研究方法的一次转折。简单来说,皇侃等人更为注重经书文句的内在逻辑,从经、注之中概括出大量的词例、句例,立说务于精巧,有时甚至不无附会之嫌。二刘的学术特点则与此大相径庭,注重史事对经书的外部证明,往往以“无义例也”否定经文义例的存在,排斥穿凿附会之说。可见由南朝至隋代,在当时最顶尖的学者之间,学术旨趣的变化是相当明显的,而且隐隐有针锋相对之意。故此本章结尾处强调义疏学的衰亡始于二刘,正因为二刘打破了南北朝义疏学的既有传统,使得“义疏学已不得更为义理、义例之思考探讨,此所以义疏学之不得不衰亡”。那么二刘何以能够不受旧有传统的约束?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二刘身份卑微,并不是在南朝建康这样的文化学术中心成长起来,而是生逢乱世,并没有接受任何学术传统,在他们眼中,传统义疏学不过是“皇帝新衣实无其物”而已。故此二刘以知识的广博代替了思考的精细,重新树立了解经的规则与方法,形式上仍为义疏之学,但在内容上已经截然不同。作者在后记中将此评述为“隋代的学术革命”,乍看起来似乎夸张,仔细品味却会觉得恰如其分。
本书第三章是《〈礼记正义〉简论》,实际仍是上一章话题的延续。因为上一章中已经说明,孔颖达《诗》《书》《春秋》三部正义,本自二刘义疏,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特点,也与二刘相合。但是《礼记正义》的性质更为复杂,按照孔颖达的说法,他“仍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也就是说,《礼记正义》是以皇侃疏为基础,参考熊安生疏编纂而成的,那么《礼记正义》是否同样具有二刘的学术特点呢?作者用了五个小节,分别从孔疏不取科段、摒弃附会之说、疏不破注、否定义例等几个方面,论证《礼记正义》学术风格仍与二刘保持一致。由此可见,尽管《礼记正义》主要参考皇侃疏,但其学术方法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正好可以说明二刘对于孔颖达影响之深,同时也可以印证作者提出的“义疏学衰亡”之论。
本书第四章是佚书验证,即作者利用日藏皇侃《礼记子本疏义》与刘炫《孝经述议》两种佚存资料,对前三章的结论进行验证。这两种残卷目前分别藏于早稻田大学与京都大学。《礼记子本疏义》在19世纪末即已被人发现,罗振玉在1916年使用石印技术对这一残卷进行了复制并撰写题跋,当时国内学者如孙诒让、胡玉缙等人都曾对这一残卷进行过初步研究。《孝经述议》残卷出现的时间略晚于《礼记子本疏义》,是1942年武内义雄在整理舟桥清贤旧藏时发现的,仅有一、四两卷。1953年,林秀一出版了《〈孝经述议〉复原研究》一书,利用日本所藏诸钞本,恢复了此书大体面貌。由于时代原因,这两种残卷多数清代学者都无法看到,直至20世纪后半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才开始陆续出现。除了林秀一对《孝经述议》进行复原研究以外,还有铃木由次郎、山本严等人对《礼记子本疏义》所作录文及考订,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文献复原、整理层面,对于文献的学术史意义发掘犹嫌不足。比起今天的学者足不出户即可在网络上看到这两种残卷的全彩图像,本书作者在写作之初,却只能利用《子本疏义》的珂罗版复制本和林秀一书中模糊不清的图版,条件相差甚远,但这却是最早一篇针对这两部残卷,从学术史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作者比较了《礼记子本疏义》与《礼记正义》之间的文字异同,确认《礼记正义》大半袭取《礼记子本疏义》,同时又删去皇侃科段、义例等附会之说,从中可见皇侃、孔颖达的学术倾向,大体与本书第一、三两章所得到的结论吻合。至于《孝经述议》,又与本书第二章的结论吻合。由此可以确认作者所论的“义疏学衰亡”以及“隋代学术革命”之说。
本书第五、第六章分别是“贾公彦新义”与“贾疏通例”,均为有关贾公彦《周礼》《仪礼》两疏的研究。这是全书之中作者着力最深的部分,也是阅读起来最为艰涩的部分。贾公彦不仅曾经参与《五经正义》的编订工作,而且两疏成书均在《五经正义》之后,是否贾疏也如孔疏一样,是二刘的学术方法的延续呢?作者认为恰恰相反,《二礼疏》中的内容与二刘的学术方法大相径庭,有着明显不同。那么岂不是与作者的“义疏学衰亡”之论正好相反吗?作者指出,贾疏因袭南北朝旧疏,完全抄撮而成,前后矛盾之说处处可见,体裁又仿效二刘、孔颖达,堪称“新瓶装旧酒”之作。仅就态度而言,二刘、孔颖达对于南北朝旧疏不满,一一予以改正,有自己鲜明的学术立场。但贾疏却完全不同,我们通过贾疏只能看到南北朝旧疏的学术立场,贾公彦只是将旧疏删改整理,置于经注之下而已,而且态度极为草率,导致错误丛出,甚至文辞不通,故此很难就《二礼疏》来讨论贾公彦的个人特点。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作者所说“义疏学衰亡”的理由何在,二刘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虽然是对传统南北朝义疏学的否定,但他们仍然尝试提出新的经学解释,只不过这种文献主义、合理主义的解经方式并不具有活力,在孔颖达之后并无法延续下去。贾公彦的《二礼疏》已经放弃了在这方面的努力,仅仅是重新编排整理旧有文献,在《周礼》《仪礼》二疏之中没有学术理想,只是单纯弥补礼疏之阙而已。
关于第五、第六两章,我们应当注意到,不论是在正文,还是在后记中,作者都自称这部书稿其实是他在阅读《仪礼疏》时的副产品。也就是说,作者在这两章中所处理的问题,其实是作者在本书写作之初所思考的基本问题。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读者在阅读第六章“贾疏通例”时,可能会感到这部分似乎游离于本书主题之外。实际上,当第五章“贾公彦新义”结束时,其实有关“义疏学衰亡”的讨论已经可以到此为止了,但作者仍然要加上这一部分,意在回到我们前面提出的那个基本问题——“义疏学是什么”。作者将此章分作三节:第一节“义疏学不为实事求是”,明确义疏学与清人学术的不同,将义疏学确定为“文字通理之学”;第二节“通义例为义疏郑学之要旨”、第三节“训诂之固化”,说明《二礼疏》乃至义疏学整体的主要内容。这三节表明了作者对于义疏学的基本理解,这种理解恐怕没办法用鲜明的定义表现出来,以至于我们只能通过作者整整一章的分析去体悟何为义疏学。所以这三节内容看似与“义疏学衰亡”的主线无关,但却是理解这一主线的关键。而且对读者来说,第六章可能是全书最具示范意义的部分,等于在为我们一一演示,阅读义疏学著作应当留心哪些地方,遇到难解之处应当如何解决。假如读者有尝试阅读义疏的打算,那么第六章就是尤其需要我们仔细对待的部分,其中不乏金针度人之处。这里面包含着作者多年浸淫于《仪礼疏》中最为深粹的功夫。我以为如果乔秀岩先生当初不写这本书的话,第一至四章的内容,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也许会有大陆学者来完成,但是恐怕永远不会有人能够把第五、第六章写出来。
从皮锡瑞1907年在长沙思贤书局出版《经学历史》一书以来,“经学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然而回顾经学史在这百年间所取得的学术积累,我们却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现当代学者在经学史的基本问题上仍然重复着皮锡瑞、梁启超等清末民初学者的观点,比如两汉今古文问题、南北学问题、汉宋之争问题等等。他们不仅仅在经学史观上难以超过前人,而且对基本文献的掌握程度又大大不及,导致我们看到目前市面上冠以“经学史”之名的著作虽然不在少数,结果内容往往大同小异——或将中国哲学史改头换面,又或从经学的角度对中国通史加以串联,还有些干脆只是加长版的目录提要罢了。能够突破以上诸多窠臼者,不过数人而已。本书之所以能够突破传统研究思路的羁绊,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在于作者能够直接回到具体的经学文献讨论中,直接面对《五经正义》等经书注疏。当作者把一个个具体的“点”如皇侃科段说、二刘的文献主义倾向、孔颖达与二刘关系、贾公彦抄撮旧疏等等夯实之后,关于“义疏学衰亡”的这条主线也就自然浮现了出来。
关于本书的研究特点,或许作者本人不同意,但我还是认为,这与日本学者的中国经学研究积累不无关系。在日本,中国经学研究隶属于中国哲学研究方向之下,而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又少有高谈义理者,大多都以朴实的文献研究见长。在我看来,作者精读文献的功夫,包括对于文献版本的选择以及搜集文献资料的视野,都与他在东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学术训练相关。至于作者在文章中的一些用语,比如描述二刘学术时,使用的“文献主义”“合理主义”等词语,在日本前辈学者的论著中也一直使用(参见加贺荣治《中国古典解释史·魏晋篇》等),在此前的汉语学术著作中却从未见到过。然而这并不是说本书只是一部非常典型的由日本学者完成的中国经学研究专著,我们可以注意到,本书恰恰没有多数日文学术著作所具有的通病,即资料收集完备,而结论不够明晰,又或个案分析充分,但整体线索不够突出。事实上,作者在下结论时毫无日本学者惯有的迂回婉转、拖泥带水,其中某些结论反而具有相当的“穿透力”,同时主线又非常明确,经常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如果读者并无意纠缠在本书的诸多细节分析之中的话,我认为只是阅读每一章后面的结论部分,就足以了解作者的主旨了。
当然这并非是说本书是一部无可挑剔的学术著作。其中仍然也有问题存在。从宏观角度来说,本书讨论的是一个从南北朝至唐初学术方法的演变问题,然而实际讨论的对象却集中在礼学方面,仅有皇侃、二刘、孔颖达、贾公彦等有限的几人或几部著作,这些例子是否具有足够的普遍性?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各自时代的学术主流?由于我们没办法看到更多的义疏学资料,只能利用现存文献来讨论这一问题,故此我们只能说在现有条件下,作者的分析与结论是成立的,但“义疏学衰亡”是否是曾经存在过的一个历史过程,恐怕还仍需存疑。[2] 在全书结构上来说,现有篇章安排虽然也有完整的内在逻辑,但是略微给人以过于围绕研究对象,而非问题本身的感觉。譬如第一章讨论皇侃《论语义疏》,第四章讨论皇侃《礼记子本疏义》,是否有可能合并为一章,直接分析皇侃的学术特点,而不必再保留第四章《佚书验证》?这样似乎在结构上可以更加紧凑。在具体结论方面,本书偶尔也会出现前后摇摆不定的情况。譬如本书第二章《二刘学术风貌》第二节“二刘学术推论”中,提到“贾公彦撰疏与孔颖达同时或稍后,而其专门礼学,渊源北朝,方法态度与孔疏大异”。贾疏与孔疏内容大异,读者读过第五、六章之后应当没有异议,但贾公彦“专门礼学,渊源北朝”,作者在第五、六章中竟然没有相关论述,根据究竟何在?我猜测作者的理由在于,《旧唐书》贾公彦本传中称其为洺州人,地处北方,贾氏《仪礼注疏序》中又列举《仪礼》疏家,仅有黄庆、李孟悊二人,很可能都是北方学者,所以作者才有这样的推论。但是今天讨论北朝义疏学,仅能利用《礼记正义》中引用熊安生的只言片语而已,并不足以反映北朝义疏学的全貌,贾疏内容是否渊源北朝,根本无从判断。从第五章的内容来看,作者明确指出贾疏直接抄自旧疏,但就算《仪礼疏》抄自黄、李二家,那么《周礼疏》抄自何处,现在也不得而知。作者在第五、六两章干脆不去讨论贾疏到底应当归入南学,还是应当归入北学的问题,而是把贾疏中的一些通例作为六朝义疏学的共同特点进行介绍。如果作者仍然认为贾疏渊源于北朝的话,岂非贾疏中的通例有可能只是北朝义疏学的特点了吗?故此像这一类问题,我以为还是暂时存疑,置之不论为是。
作为乔秀岩先生的早期作品,这部书虽然在经说分析方面极具特色,堪称精妙,但尚未到达入微之境,因为当时他对于郑玄经学的深入研究还没开始,对于学术史发展的整体脉络把握尚嫌不足。如果读者是资深“乔粉”的话,当然不会漏掉他的另一本书《北京读经说记》。《北京读经说记》中所收录的是作者近年来的重要论文,两相比较之下,大家就可以看到作者在经学研究方面的进境如何。我非常期待日后乔秀岩先生能够重写这部书,立足于他对郑玄以降学术演变的理解,应当会诞生一部全新的作品。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对于一部分读者,包括作者本人而言,本书的真正价值或许并不在于“义疏学衰亡”等等历史问题,这些不过是为了符合现代学术要求而设计出来的“皮相”而已,这本书的意义其实是在引导我们与古人交流。在当代历史学者纷纷努力转变为海量知识的生产者时,这本书在历史学著作中无疑显得有些“异类”。本书作者是一位纯粹的读者。他在阅读相关文献时,能够做到放下肤浅的一己之是非,去专心倾听文献作者的观点。即使他意识到这个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他也会坚持站在作者的立场上去理解作者为什么会出错,而不是对错误结论置之不理,所以他在书前识语中说明,“本论文并非经学家之经学史,而是读书者之经学史论故也”。假如读者能够耐心看完他的每一个分析,一定能够感受到他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在与不同文献的作者进行亲密的对话。这样的阅读体验,是其他的历史论著未曾带给我的。
注释
[1]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第193页,中华书局1959年。
[2] 乔秀岩在《孝经孔传述议读本·编后记》中提出从隋唐之际至唐前期《孝经》孔传文本演变与接收的问题,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作为“义疏学衰亡史”的一个补充。参见乔秀岩、叶纯芳《孝经孔传述议读本》,叶山小书店出版部2015年,第189至221页。
(华喆,1981年生,北京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三礼学、经学史等方向的研究,在《中国史研究》《文史》《文献》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另有著作《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即将在三联书店出版。)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jQzNTAyNw==&mid=2651129086&idx=1&sn=bbb0b08fc89d51ac40a3d0920b6c4761&chksm=8490ffc2b3e776d43645770fee732325f8cdb41411ecbac371e1421627615674aaffbd4db9f7#rd
《义疏学衰亡史论》读后感(四):华喆丨读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
2013年9月,乔秀岩先生的博士论文《义疏学衰亡史论》在台湾万卷楼出版。从我第一次读到本书全文,到今天为止,正好十年。十年之中,在当今学者的不断努力之下,有关南北朝隋唐义疏学的论文、专著大量涌现。然而像这部书一样,在艰深的经说分析中,既能让读者保持继续阅读的热情,又能激发读者更进一步思考的著作,可以说绝无仅有。
旧版《义疏学衰亡史论》,由台北万卷楼于2013年出版本书原题叫做《南北朝至初唐义疏学研究》,是乔秀岩199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论文,在2001年作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由东京白峰社出版日文版,改题《义疏学衰亡史论》。由于日文版读者有限,长时间以来,乔先生的博士论文仅在以北大为主的一部分教师与学生中小范围流传。2013年,恰在日文版发行一纪之后,本书中文版终于出版。故此不揣鄙陋,将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记录下来,希望能够让更多读者了解此书的价值。
首先,请允许我简单梳理一下本书的论题与主要线索。
由原题和后来改用的题目“义疏学衰亡史论”可以看出,本书的主旨在于描绘出从南北朝到唐初义疏学盛极而衰亡的过程。然而这富有冲击力的题目却是对读者常识的一大挑战——我们都知道所谓“十三经注疏”,其中《五经正义》成于孔颖达之手,《周礼》《仪礼》二疏为贾公彦所作,此外唐疏还有徐彦《公羊》疏和杨士勋《穀梁》疏,以下《论》《孝》《雅》《孟》四疏均成于宋代,更不用说清人还创作新疏,成果斐然,自谓胜于唐疏。本书研究断限只及于初唐,并不涉及宋代以降的群经义疏。如此说来,将南北朝至初唐义疏学称之为“衰”,固无不可,却以“衰亡”命名,那么宋代以降的义疏作品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作者在书中并没有作正面解释,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我们阅读此书必须把握的一个关窍所在,即在作者眼中,义疏学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乔先生看来,义疏固然是一种经学文献的编排方式,但义疏学并非只是以注解经,以疏释注的形式,而是有其特定的学术方法。所谓“义疏学衰亡史”,是指义疏学作为学术方法的衰亡,而非义疏作品的消失。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乔秀岩先生充分认识到了唐初以前义疏与宋人乃至清人义疏有着根本不同,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清人义疏以“实事求是”自命,然而义疏学并非实事求是之学——但义疏学到底是什么,作者却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读这部书的“书眼”,必须时刻带着这个问题进入本书的每一段讨论,故此这里请恕我先卖个关子,到了后面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本书第一章的研究对象是皇侃的《论语义疏》。对于南北朝义疏学研究者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文献不足征。尽管《隋书·经籍志》中冠以“义疏”“讲疏”之名的著作不下几十部,然而今天能够看到全貌的,却只有皇侃《论语义疏》一部而已。前人对此研究相对较多。作者将皇侃《论语义疏》的学术特点概括为两点,一为建立科段,二为整理旧说,且从皇侃引书的一些特点出发,分析皇侃整理旧说的基本手法,为前人所未曾注意之处。
本书的第二章是关于二刘即刘炫、刘焯的学术风貌。这实际上是本书写作中的第一个重大关节点。二刘著作除《孝经述议》的一部分内容以外,今天已经无法看到。然而由于孔颖达《五经正义》中对二刘多有征引,经过清儒刘文淇作《左传旧疏考正》之后,我们已经可以通过《诗》《书》《春秋》三部唐修注疏,来讨论二刘的学术特点。书中通过对孔颖达《正义》进行文本分析,确定其中出自二刘的部分。同时又与皇侃《论语义疏》、贾公彦《周礼》《仪礼》二疏进行比较,将二刘学术特点概括为“现实、合理、文献主义”,与皇侃所代表的南朝学风,以及贾公彦所代表的北朝学风,有明显不同,并说明了二刘对于孔颖达以降的影响。
刘文淇《左传旧疏考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乔氏与以往经学史家的不同之处。自皮锡瑞《经学历史》以降的传统经学史著作,均强调南北朝至隋唐的经学流变,存在南学与北学的分合问题。在《经学历史》中,皮锡瑞对于南北学的分立与统一有一个著名论断:
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1]
这段话对于后世南北朝隋唐经学史,乃至学术史、思想史的影响,研究者有目共睹,自然不必多说。在皮锡瑞看来,南学北渐,最终取而代之,正是从二刘开始。他的理由是从李延寿的《北史·儒林传序》而来。《北史》记载北方《尚书》学传习,有“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的记载,皮氏以费甝《尚书义疏》是南学产物,自然是二刘“北人而染南习”的例证。除此以外,按照北朝史料之说,北方学者《左传》用服虔注,二刘开始研究杜预《集解》,自然代表南学立场。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尚书》用孔传,《左传》用杜《解》,又广泛吸收二刘之说,充分说明了《五经正义》是立足在南学基础上的经学统一。皮氏的观点立足于史传等外缘性材料,并未对与二刘有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在今天看来,实在过于简单粗放,有其自身的时代局限在内。然而这一结论却被后来的经学史研究者甘之如饴,奉为金科玉律,并没有人去反思它成立的根据何在。
乔秀岩先生这部著作的精华恰恰在于,他直接从学者的经说个案出发,来判断学者的研究旨趣与学术特点,而非借助隔着一层的外缘史料,避免了雾里看花、管中窥豹之弊。实际上,二刘的学术风貌并不是南、北学中某一支派的延续,而是代表了义疏学研究方法的一次转折。简单来说,皇侃等人更为注重经书文句的内在逻辑,从经、注之中概括出大量的词例、句例,立说务于精巧,有时甚至不无附会之嫌。二刘的学术特点则与此大相径庭,注重史事对经书的外部证明,往往以“无义例也”否定经文义例的存在,排斥穿凿附会之说。可见由南朝至隋代,在当时最顶尖的学者之间,学术旨趣的变化是相当明显的,而且隐隐有针锋相对之意。故此本章结尾处强调义疏学的衰亡始于二刘,正因为二刘打破了南北朝义疏学的既有传统,使得“义疏学已不得更为义理、义例之思考探讨,此所以义疏学之不得不衰亡”。那么二刘何以能够不受旧有传统的约束?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二刘身份卑微,并不是在南朝建康这样的文化学术中心成长起来,而是生逢乱世,并没有接受任何学术传统,在他们眼中,传统义疏学不过是“皇帝新衣实无其物”而已。故此二刘以知识的广博代替了思考的精细,重新树立了解经的规则与方法,形式上仍为义疏之学,但在内容上已经截然不同。作者在后记中将此评述为“隋代的学术革命”,乍看起来似乎夸张,仔细品味却会觉得恰如其分。
本书第三章是《〈礼记正义〉简论》,实际仍是上一章话题的延续。因为上一章中已经说明,孔颖达《诗》《书》《春秋》三部正义,本自二刘义疏,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特点,也与二刘相合。但是《礼记正义》的性质更为复杂,按照孔颖达的说法,他“仍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也就是说,《礼记正义》是以皇侃疏为基础,参考熊安生疏编纂而成的,那么《礼记正义》是否同样具有二刘的学术特点呢?作者用了五个小节,分别从孔疏不取科段、摒弃附会之说、疏不破注、否定义例等几个方面,论证《礼记正义》学术风格仍与二刘保持一致。由此可见,尽管《礼记正义》主要参考皇侃疏,但其学术方法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正好可以说明二刘对于孔颖达影响之深,同时也可以印证作者提出的“义疏学衰亡”之论。
日本藏《礼记子本疏义》残卷本书第四章是佚书验证,即作者利用日藏皇侃《礼记子本疏义》与刘炫《孝经述议》两种佚存资料,对前三章的结论进行验证。这两种残卷目前分别藏于早稻田大学与京都大学。《礼记子本疏义》在19世纪末即已被人发现,罗振玉在1916年使用石印技术对这一残卷进行了复制并撰写题跋,当时国内学者如孙诒让、胡玉缙等人都曾对这一残卷进行过初步研究。《孝经述议》残卷出现的时间略晚于《礼记子本疏义》,是1942年武内义雄在整理舟桥清贤旧藏时发现的,仅有一、四两卷。1953年,林秀一出版了《〈孝经述议〉复原研究》一书,利用日本所藏诸钞本,恢复了此书大体面貌。由于时代原因,这两种残卷多数清代学者都无法看到,直至20世纪后半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才开始陆续出现。除了林秀一对《孝经述议》进行复原研究以外,还有铃木由次郎、山本严等人对《礼记子本疏义》所作录文及考订,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文献复原、整理层面,对于文献的学术史意义发掘犹嫌不足。比起今天的学者足不出户即可在网络上看到这两种残卷的全彩图像,本书作者在写作之初,却只能利用《子本疏义》的珂罗版复制本和林秀一书中模糊不清的图版,条件相差甚远,但这却是最早一篇针对这两部残卷,从学术史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作者比较了《礼记子本疏义》与《礼记正义》之间的文字异同,确认《礼记正义》大半袭取《礼记子本疏义》,同时又删去皇侃科段、义例等附会之说,从中可见皇侃、孔颖达的学术倾向,大体与本书第一、三两章所得到的结论吻合。至于《孝经述议》,又与本书第二章的结论吻合。由此可以确认作者所论的“义疏学衰亡”以及“隋代学术革命”之说。
本书第五、第六章分别是“贾公彦新义”与“贾疏通例”,均为有关贾公彦《周礼》《仪礼》两疏的研究。这是全书之中作者着力最深的部分,也是阅读起来最为艰涩的部分。贾公彦不仅曾经参与《五经正义》的编订工作,而且两疏成书均在《五经正义》之后,是否贾疏也如孔疏一样,是二刘的学术方法的延续呢?作者认为恰恰相反,《二礼疏》中的内容与二刘的学术方法大相径庭,有着明显不同。那么岂不是与作者的“义疏学衰亡”之论正好相反吗?作者指出,贾疏因袭南北朝旧疏,完全抄撮而成,前后矛盾之说处处可见,体裁又仿效二刘、孔颖达,堪称“新瓶装旧酒”之作。仅就态度而言,二刘、孔颖达对于南北朝旧疏不满,一一予以改正,有自己鲜明的学术立场。但贾疏却完全不同,我们通过贾疏只能看到南北朝旧疏的学术立场,贾公彦只是将旧疏删改整理,置于经注之下而已,而且态度极为草率,导致错误丛出,甚至文辞不通,故此很难就《二礼疏》来讨论贾公彦的个人特点。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作者所说“义疏学衰亡”的理由何在,二刘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虽然是对传统南北朝义疏学的否定,但他们仍然尝试提出新的经学解释,只不过这种文献主义、合理主义的解经方式并不具有活力,在孔颖达之后并无法延续下去。贾公彦的《二礼疏》已经放弃了在这方面的努力,仅仅是重新编排整理旧有文献,在《周礼》《仪礼》二疏之中没有学术理想,只是单纯弥补礼疏之阙而已。
关于第五、第六两章,我们应当注意到,不论是在正文,还是在后记中,作者都自称这部书稿其实是他在阅读《仪礼疏》时的副产品。也就是说,作者在这两章中所处理的问题,其实是作者在本书写作之初所思考的基本问题。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读者在阅读第六章“贾疏通例”时,可能会感到这部分似乎游离于本书主题之外。实际上,当第五章“贾公彦新义”结束时,其实有关“义疏学衰亡”的讨论已经可以到此为止了,但作者仍然要加上这一部分,意在回到我们前面提出的那个基本问题——“义疏学是什么”。作者将此章分作三节:第一节“义疏学不为实事求是”,明确义疏学与清人学术的不同,将义疏学确定为“文字通理之学”;第二节“通义例为义疏郑学之要旨”、第三节“训诂之固化”,说明《二礼疏》乃至义疏学整体的主要内容。这三节表明了作者对于义疏学的基本理解,这种理解恐怕没办法用鲜明的定义表现出来,以至于我们只能通过作者整整一章的分析去体悟何为义疏学。所以这三节内容看似与“义疏学衰亡”的主线无关,但却是理解这一主线的关键。而且对读者来说,第六章可能是全书最具示范意义的部分,等于在为我们一一演示,阅读义疏学著作应当留心哪些地方,遇到难解之处应当如何解决。假如读者有尝试阅读义疏的打算,那么第六章就是尤其需要我们仔细对待的部分,其中不乏金针度人之处。这里面包含着作者多年浸淫于《仪礼疏》中最为深粹的功夫。我以为如果乔秀岩先生当初不写这本书的话,第一至四章的内容,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也许会有大陆学者来完成,但是恐怕永远不会有人能够把第五、第六章写出来。
从皮锡瑞1907年在长沙思贤书局出版《经学历史》一书以来,“经学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然而回顾经学史在这百年间所取得的学术积累,我们却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现当代学者在经学史的基本问题上仍然重复着皮锡瑞、梁启超等清末民初学者的观点,比如两汉今古文问题、南北学问题、汉宋之争问题等等。他们不仅仅在经学史观上难以超过前人,而且对基本文献的掌握程度又大大不及,导致我们看到目前市面上冠以“经学史”之名的著作虽然不在少数,结果内容往往大同小异——或将中国哲学史改头换面,又或从经学的角度对中国通史加以串联,还有些干脆只是加长版的目录提要罢了。能够突破以上诸多窠臼者,不过数人而已。本书之所以能够突破传统研究思路的羁绊,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在于作者能够直接回到具体的经学文献讨论中,直接面对《五经正义》等经书注疏。当作者把一个个具体的“点”如皇侃科段说、二刘的文献主义倾向、孔颖达与二刘关系、贾公彦抄撮旧疏等等夯实之后,关于“义疏学衰亡”的这条主线也就自然浮现了出来。
关于本书的研究特点,或许作者本人不同意,但我还是认为,这与日本学者的中国经学研究积累不无关系。在日本,中国经学研究隶属于中国哲学研究方向之下,而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又少有高谈义理者,大多都以朴实的文献研究见长。在我看来,作者精读文献的功夫,包括对于文献版本的选择以及搜集文献资料的视野,都与他在东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学术训练相关。至于作者在文章中的一些用语,比如描述二刘学术时,使用的“文献主义”“合理主义”等词语,在日本前辈学者的论著中也一直使用(参见加贺荣治《中国古典解释史·魏晋篇》等),在此前的汉语学术著作中却从未见到过。然而这并不是说本书只是一部非常典型的由日本学者完成的中国经学研究专著,我们可以注意到,本书恰恰没有多数日文学术著作所具有的通病,即资料收集完备,而结论不够明晰,又或个案分析充分,但整体线索不够突出。事实上,作者在下结论时毫无日本学者惯有的迂回婉转、拖泥带水,其中某些结论反而具有相当的“穿透力”,同时主线又非常明确,经常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如果读者并无意纠缠在本书的诸多细节分析之中的话,我认为只是阅读每一章后面的结论部分,就足以了解作者的主旨了。
三联书店新版《义疏学衰亡史论》当然这并非是说本书是一部无可挑剔的学术著作。其中仍然也有问题存在。从宏观角度来说,本书讨论的是一个从南北朝至唐初学术方法的演变问题,然而实际讨论的对象却集中在礼学方面,仅有皇侃、二刘、孔颖达、贾公彦等有限的几人或几部著作,这些例子是否具有足够的普遍性?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各自时代的学术主流?由于我们没办法看到更多的义疏学资料,只能利用现存文献来讨论这一问题,故此我们只能说在现有条件下,作者的分析与结论是成立的,但“义疏学衰亡”是否是曾经存在过的一个历史过程,恐怕还仍需存疑。[2] 在全书结构上来说,现有篇章安排虽然也有完整的内在逻辑,但是略微给人以过于围绕研究对象,而非问题本身的感觉。譬如第一章讨论皇侃《论语义疏》,第四章讨论皇侃《礼记子本疏义》,是否有可能合并为一章,直接分析皇侃的学术特点,而不必再保留第四章《佚书验证》?这样似乎在结构上可以更加紧凑。在具体结论方面,本书偶尔也会出现前后摇摆不定的情况。譬如本书第二章《二刘学术风貌》第二节“二刘学术推论”中,提到“贾公彦撰疏与孔颖达同时或稍后,而其专门礼学,渊源北朝,方法态度与孔疏大异”。贾疏与孔疏内容大异,读者读过第五、六章之后应当没有异议,但贾公彦“专门礼学,渊源北朝”,作者在第五、六章中竟然没有相关论述,根据究竟何在?我猜测作者的理由在于,《旧唐书》贾公彦本传中称其为洺州人,地处北方,贾氏《仪礼注疏序》中又列举《仪礼》疏家,仅有黄庆、李孟悊二人,很可能都是北方学者,所以作者才有这样的推论。但是今天讨论北朝义疏学,仅能利用《礼记正义》中引用熊安生的只言片语而已,并不足以反映北朝义疏学的全貌,贾疏内容是否渊源北朝,根本无从判断。从第五章的内容来看,作者明确指出贾疏直接抄自旧疏,但就算《仪礼疏》抄自黄、李二家,那么《周礼疏》抄自何处,现在也不得而知。作者在第五、六两章干脆不去讨论贾疏到底应当归入南学,还是应当归入北学的问题,而是把贾疏中的一些通例作为六朝义疏学的共同特点进行介绍。如果作者仍然认为贾疏渊源于北朝的话,岂非贾疏中的通例有可能只是北朝义疏学的特点了吗?故此像这一类问题,我以为还是暂时存疑,置之不论为是。
作为乔秀岩先生的早期作品,这部书虽然在经说分析方面极具特色,堪称精妙,但尚未到达入微之境,因为当时他对于郑玄经学的深入研究还没开始,对于学术史发展的整体脉络把握尚嫌不足。如果读者是资深“乔粉”的话,当然不会漏掉他的另一本书《北京读经说记》。《北京读经说记》中所收录的是作者近年来的重要论文,两相比较之下,大家就可以看到作者在经学研究方面的进境如何。我非常期待日后乔秀岩先生能够重写这部书,立足于他对郑玄以降学术演变的理解,应当会诞生一部全新的作品。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对于一部分读者,包括作者本人而言,本书的真正价值或许并不在于“义疏学衰亡”等等历史问题,这些不过是为了符合现代学术要求而设计出来的“皮相”而已,这本书的意义其实是在引导我们与古人交流。在当代历史学者纷纷努力转变为海量知识的生产者时,这本书在历史学著作中无疑显得有些“异类”。本书作者是一位纯粹的读者。他在阅读相关文献时,能够做到放下肤浅的一己之是非,去专心倾听文献作者的观点。即使他意识到这个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他也会坚持站在作者的立场上去理解作者为什么会出错,而不是对错误结论置之不理,所以他在书前识语中说明,“本论文并非经学家之经学史,而是读书者之经学史论故也”。假如读者能够耐心看完他的每一个分析,一定能够感受到他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在与不同文献的作者进行亲密的对话。这样的阅读体验,是其他的历史论著未曾带给我的。
注释
[1]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第193页,中华书局1959年。
[2] 乔秀岩在《孝经孔传述议读本·编后记》中提出从隋唐之际至唐前期《孝经》孔传文本演变与接收的问题,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作为“义疏学衰亡史”的一个补充。参见乔秀岩、叶纯芳《孝经孔传述议读本》,叶山小书店出版部2015年,第189至221页。
* 本文原载于《哲学门》2015年第2期
《义疏学衰亡史论》读后感(五):撮述:义疏学津逮
1、皇侃《论语义疏》
1.1、儒经《论语》《周易》《礼记》最易比附佛说。皇疏修饰对仗。
1.2、“科段”为皇疏新创。三层:分篇,分章,章内分段。
①分二十篇,题下有论说,论篇次之由。②分章,言章旨。③数章合为一大段。④分段。
科段为时俗,佛学创制,儒经移用,《周易正义》亦可见。
《论语》皇疏欲发明经文前后条理。皇疏以《集解》为本。
作科段,求次序,原理一也。
①皇疏《论语》创科段,故流传广。②求前后之理,不避附会、偏至之说。③探求前后关系,皇疏之整体特点。
1.3、引旧说之例:先“一云”“一家”言其要旨,后或引前儒原文。
皇疏以《集解》为本,而不唯注是从。并列异说,不定是非,而评优劣。屡言“不及”“不胜”,而不径斥,可见皇疏分析之精审,态度之宽厚。
称名引录而无辩说者,广异闻也。亦有求简避烦处。
皇疏非据事实而破臆说,而以通理破偏理,所谓不拘细节,议论通达。
亦有强通其理。文多雕饰。
1.4、皇侃引书,知人则称名,不知则“某称某曰”。皇侃亲见《论语》郑注,而“余见郑注本”两见者,或本也,盖庸陋误抄者。皇疏重用《白虎通》,适与刘炫之轻视相反。疑南朝不行《家语》,皇侃不用。皇疏虽博考前人《论语》注,然《白虎通》《韩诗外传》外,引书绝少。间接引用,未考原文。
1.5、皇疏广搜旧说,仔细析论,集大成。方法曰“通”。
①广存异说,乖注、荒诞而不弃,存录。
②无关要旨则不论,不尚知识之多,以查检群书为末事,态度旷达。
③并列细析,归类辨异,而不论断是非。
④前后条理难见,彼此矛盾难合,仍以一边之理,附会之法,通释其理。(玄学家追求“胜理”,不以至理为准则,不顾原意,甚至超越、违反之。)
此等特点,即牟润孙所论南朝谈辩之学者。
皇疏见重于世,在于“勤”。①网罗《论》注殆尽。②章章辨微不阙。③全书施以科段。④参考前儒,评析异说,为之科段,必在其勤,贯穿全书,始集大成。
除《集解》所引,皇侃当未见苞、周、马等早训。
2、二刘
2.1、刘文淇分析刘炫说
刘文淇:“唐人所删定,仅驳刘炫说百余条,余皆刘炫《述议》。”
疏中“今赞曰”“今删定”“今知不然者”“今以为”,孔疏评语,前则旧疏也。
《毛诗》《左传》疏皆以刘炫《述议》为蓝本。
刘文淇言刘炫《述议》体例:先述杜意,后驳;孔疏或没炫名,或改“炫谓”为“刘炫规过云”。
刘文淇:《诗》《书》《左传》据刘炫,多同;《易》《礼记》不然。
三疏相同,亦有可能同据他书。如《仪礼》贾疏据黄庆、李孟悊,《礼记》孔疏据皇侃、熊安生,亦有大段同文,当别有一书为二疏因袭。
刘文淇可疑处。
①唐疏亦有“先言己意、后引刘说为别解”之例,未必皆“先引刘说而后申己见”。
②刘文淇以为前有别说,后有刘说,唐人无驳,则《正义》同刘。然同刘而略,前说反详,何故?
前有一说,后有“刘炫云”,重复则以“云云”省之。刘文淇以为刘炫引旧说,唐人见其重复而省刘说。体例不伦。
包慎言曰:“旧疏有刘炫所引,有唐人所引。唐人约其同者而曰‘云云同’。后将旧疏姓名削去,便似前为己说,乃致踳驳。”
③《述议》者,撰述义疏耳。总之,“刘炫云”以前之说,未必出于刘炫。
④刘文淇以为孔疏据刘炫,但辨规杜,别无攻击。列《正义》驳贾逵39条,驳服虔126条,驳贾服20条,谓皆旧疏,非唐人。乔秀岩以为唐人未必不攻贾服。
⑤刘文淇以为攻《公》《穀》皆刘炫语。亦未必。
小结:①孔疏有明引刘说者。“今赞曰”“今删定”以上可知为旧疏。书中前后及《诗》《书》《左传》三疏互见同文者,可知出刘炫。②刘文淇推《述议》体例,先述旧说,述杜注,后述己意,近实。《正义》“刘炫云”以上皆出刘,则未必(或唐人引旧疏)。疏文除驳规杜百余条外,皆出刘炫或沈文阿。大概然也。
2.2、二刘学术推论
“窃”语气迥异“今删定”,推为刘炫。
刘文淇:《诗》《书》《左传》三疏同文,疑出刘炫;《左传正义》大致袭刘,非特为论证者,可疑为旧疏。乔秀岩:三疏非明证知为唐人手笔,暂以为二刘旧疏。二例。
①引《说文》考兜鍪起于秦汉,非解经所需,是自为之说。见于《书》《左传》疏,而不见于《礼记》疏,可知出于二刘。
②长沙衡山,又名霍山。扬州灊县天柱山,汉武帝改名霍山。《诗》《书》《左传》三疏大同,《书》疏删简移用《传》疏。《周礼》贾疏竟以为扬州,盖义疏专门之学,分析经注语文为主,不求考订史实。贾疏后引郭璞正说而错综未中。《礼记·王制》孔疏则引郭说最简明,不同者:谶纬言扬州霍山,武帝从之耳。孔颖达未尝互勘四疏求其统一,可见三疏之多出二刘(《礼记》疏之多出皇侃)。
《诗》《书》《左传》常见“斯不然矣”:先举旧说之谬,称“斯不然矣”,下为解惑,述正解。
比较三疏与《论语》皇疏、贾公彦《二礼》疏。皇侃为梁朝学术,贾公彦专门礼学渊源北朝。《礼记正义》性质特别,在于既以皇疏为本,孔颖达又受学二刘,故与(二刘)三疏有同有异。三疏与《论语》《二礼》疏迥异,与《礼记正义》有同有异之特点,即二刘学术特点。《左传》疏本刘炫,《诗》《书》疏本二刘。
三疏学术态度,有迥异皇贾而高明卓绝者。大抵《诗》《书》疏因袭二刘;《左传》疏驳规杜较多;《礼记》疏因袭皇侃与孔颖达改编各半。
二刘异于旧学特点:现实、合理、文献主义。
据近事推论古事,是为现实主义。通曆破杜,言之有理;经师因循,世恨其才。
《诗》疏据《传》疏删简处。
二刘所重在古今不易之事实,深信历数原理,极知天谴灾异为圣贤设教之方,非事实也。
二刘亦不信纬书怪异之说,可见合理主义精神。
二刘最好孔传《书》《孝经》。
贾公彦学术,以郑注为根本,探讨郑注说之体系化,试图使郑玄学说体系更完整、更少矛盾。相比而言,二刘以现实、常情为根本,必先自考事实如何,据其结论反观先儒。若不合,则解析。可见二刘最重事实,绝不拘泥先儒说,更不为专门郑学,迥异贾公彦。
摒弃附会,疑信兼传。合理主义精神也。疏言“别无意”,异于《论语》皇疏之每见附会。三疏常以语言之自然,排除附会,又异于《仪礼》贾疏也。贾疏后于二刘、《正义》,却多本北朝旧说。
二刘特好单字、配字之说,异于当时义疏家。
言“文势”,据文法自然,以释经注文辞之参差不同,亦绝附会。据事情自然而绝穿凿,三疏常见之学术特点,而为《论语》皇疏、《二礼》贾疏所不见,《礼记正义》偶见一二而已。疑出二刘。
二刘读书精敏,于“语例”颇多心得。二刘思考不拘经文传注,综考古文事例之规律,有历史语言学之态度,异于专作义疏之学者。
亦颇通“古音”。陆德明“韵缓”,沈重“协韵”,当时通论。然无历史观点。王劭、二刘之古音说,据古今韵文实事,归纳体例,方法科学,历史观点突出,非可同日而语者。王劭、刘炫当有切磋,学术态度相通。传统义疏学家,不通诗文,不能博考汉以后诗文用韵,又囿于讨论经传文字范围,自然不能超出“韵缓”“协韵”两说。王劭博通,多勘书本,敢于改经,以致孔颖达攻驳。当知二刘学术应运而生,与颜之推、王劭同趣。
二刘常罗列事证,范围广泛,及于汉以来史事。俨然史家杂记。又考索历代史书语言习惯。据后世俗事以证经文。累举古今。此皆皇、贾等旧义疏家所不(能)为者也。
网罗事例,分析条理,而谓之“无义例”,亦二刘学术重要特点。经文彼此不同,并无规律,意义无别,即“无义例”,意即“无义意”。
①瞽,蒙,瞍。《周礼》贾疏据只文片语,强为之说,虽巧言有理,终牵强不通达。不如《诗》疏之具体现实详备。然此学风之异,不可遽断优劣。
②郑注四经“先公”,释义不同。《论语》皇疏、《二礼》贾疏,以经注语言为议论前提,见其不同,必释理由。故《周礼》贾疏一一分说四处经注。《礼记·中庸》疏乃同贾疏。《毛诗·天作》疏,乃大段驳之。盖《周礼》疏所述,乃义疏家旧说,说《诗》亦然,二刘始破之。《周礼》疏、《礼记正义》因袭旧说,未改据二刘,故异《诗》疏。乔秀岩评价新旧二说曰:旧说以经注文字为前提,专力探讨文字差异之条理;二刘则先知事同,而谓其字异为无义例。换言之:旧说探讨文字,二刘探讨事情。亦即:旧说之理在文字之间,二刘之理在文字之外。此旧义疏学与二刘学术根本差异。二刘为现实合理主义也。
就经注文之异,核例除附会而判“无义例”,《诗》《书》疏最常见。《论语》皇疏亦有,但其全书不排斥附会。《二礼》贾疏绝少见,有之者亦非贾创义。熊安生亦说“无义例”。其实此说最多最力者,曰杜预《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杜预以为:经传有事同文异、同意别文者。传欲解经,非由文生例。诸儒溺于《公》《穀》而横生义例,是于无意之中求义。乔氏以为:《释例》所以去附会。刘炫之规杜,实为法杜。《左传》疏少见“无义例”,盖杜注、《释例》已多言之故。
“无义例”之说,杜预之关键。《诗》《书》疏亦常见“无义例”。意者二刘习杜,方法取资。二刘常法,在于列举实事以破附会旧说,是同于杜预,而异于《论语》皇疏、《二礼》贾疏者也。
二刘引书广博,三疏引诗赋颇多。《论语》皇疏、《二礼》贾疏、《礼记正义》绝少。知贾公彦等旧义疏学,旨在通理,不为广征文献以证实;二刘迥异。但二刘亦限于引著名诗文以印证经事而已,又逊于孙诒让博考着实也。《论语疏》《仪礼疏》《礼记正义》不引汉以来诗赋,《周礼疏》偶引之,疑据类书。知旧义疏家以至贾公彦等,不谙汉赋,不检原文。总之:《诗》《左传》疏引汉后诗文较多,《仪礼》《礼记》疏绝无,《周礼》疏偶见一二。
三疏又常引汉后史书为证。如《晋书》等。《论语疏》不引,《三礼疏》偶引《汉书》及注,余不多见。《礼记正义》亦有孔颖达补述唐礼者。
二刘引书,亦有转引。罗列单字配语辞之事证,二刘常法。二刘参用类书。二刘不信神异。又据服虔注转引。
二刘引书又精审。①博极文献,而不拘文献。②考察文献不同性质,心有成见,不一视同仁。汉儒重声训,二刘嫌其附会。《礼记》疏引《白虎通》而《书》《左传》疏否,二刘不取也。二刘又以《孟子》多权宜。《大戴礼》多假托。《公羊传》为汉俗儒言。义疏家以《郑志》为郑玄真说,二刘不信其中《杂问志》。又论毛公事荀子,荀子在焚书前;《家语》出孔家,毛公或见其事;郑玄不见《家语》,不信《荀子》;辨纬起哀平;论刘歆、班固不见古文《尚书》,谬从《史记》。凡此无论当否,必欲讨论不同时代之作者、文献条件之关系,是为精审。辨别真伪,所在多见。三疏异于《史记》,故常言其妄。
南北朝末期,义疏学一则偏重义理,如《论语》皇疏;二则自成专门,不能广论文籍,精辨文献性质,如《二礼疏》也。顾氏曰:“止可依经诰大典,不可用传记小说。”此经学专门之态度也,异于二刘之博达。贾公彦言汉人未见《古文尚书》,贩卖之说,非心得。二刘考证文献之精博,贾等瞠后。
二刘自负博极文献,三疏常见“遍检书传”。此非皇贾所能,《论语》《二礼》疏所无。《礼记正义》偶见一二。“遍验书本”者,孔颖达等检查抄本异同耳,非广搜文献之谓也。
二刘学术超绝,失之轻慢。好立异论,欲改经传。又谩骂贬低前儒。皇侃引评而无谩骂,《二礼疏》则不明引前儒。
2.3、结论
三疏学术风貌,大概可归二刘。
疏有彼此详略不等,难辨因袭。或别有他书,三疏因袭;或一疏为先;或二刘自改;或孔颖达互补;难定。
三疏多引汉后史事,亦或因《书》《传》为史,《二礼》不然。《诗》疏又分说毛郑,而《周礼》疏专主郑。书异疏殊。但基本方法态度,贯穿全书。三疏终异于皇贾。
二刘学术特点为现实、合理、文献主义,皇贾旧义疏学特点则为:思维、推理、经注主义。旧义疏学为一学术传统,贾公彦等牵强之说在此传统中,故必如此说。二刘则不负传统,敢于打破,根据在于现实与知识。条理得之于思考,现实得之于知识。二刘罗列事实以破旧义疏家之义例,是以知识取代思考。然则入于轻薄。
二刘广引汉后诗文印证经传,终不逮孙诒让之精博。盖其引证不顾时代遥隔,印证以为满足,更不探索。知其然(历史、语文现象),不知其所以然之理(历史、语文规律原理)。旧义疏学以经注印证,二刘阑入诗赋,能事毕矣。又何曾探底。(要么如经学之体系化,要么如朴学之实证化,二刘所谓中不溜、两不靠也。)二刘以立目齐备、例证具足为能事,机械作为,不见点滴思考。
若谓旧义疏学为君子之学,则二刘学术为胥吏之学。君子之学不敷实用而精美;胥吏之学实用而厌人。二刘用知识打破传统,却无思考以建设新传统。(此则理学之能事矣。)
二刘学术之出现,即旧义疏学之衰亡。二刘打破传统,以后义疏学不得更为义理、义例之思考探讨。(体系化之夭亡。)孔、贾无所创立。然《五经正义》学术方法同于二刘,《二礼疏》仍多旧义者,盖《二礼》离郑无以言,而旧学研究郑学最得精密,“现实、合理、文献主义”与《二礼》学根本不兼容耳。(郑氏礼学体系,所以为经学之根本与生机也。)
3、《礼记正义》
3.1、《礼记正义》性质复杂
《礼记正义》以皇侃为本,熊安生为补。不称谁氏之说者,当多出皇侃。亦有孔颖达受二刘影响而作者。
3.2、皇侃科段说
皇侃义疏,例不为反切注音。
《乐记》十一章,皇侃据文义、拟篇章,分科段、言要旨,特色与《论语疏》同。
《郑目录》言十一篇,孔颖达但取皇侃十一章名,不取科段。孔疏分节,非有机结构。
孔疏分节条目,但删要经文,不抽象概括、附会条理。无层次、要旨。小不拘皇侃科段,大不囿篇目,上下串联,专意于经文内容之自然分段。
皇侃则不避抽象、附会,而旨在建立精巧复杂之层级有机结构。二刘、孔颖达限于经文之下分析罗列现实事实之细目,皇侃则追求经文之上的逻辑论理结构。
孔不取皇,又误录其文,龃龉脱讹,可见编纂草率混乱。
皇侃注意前后章节科段之论理关系。《礼记正义》全书则专据经文述事为标准之节段,常批驳皇侃前后关联之说。
《曲礼》“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皇说关联下节,孔君嫌其附会。然皇欲于经文之外建立论理结构(如线贯珠),孔则排除经文述事外一切建构(但要散珠)。
总结:皇侃科段,不嫌附会,追求论理关系之精巧结构。孔君排斥附会,专论经文述事。驳斥之余,偶有遗留,此《礼记正义》所以复杂也。
3.3、孔颖达取舍标准
孔颖达排斥皇侃委曲讨论先儒异同,繁文旁引。孔君一以释述经注文义为本旨,专注事实,一概摒弃繁言。
皇侃“横生义例”,曲说义意,建立条理结构,孔君皆以为附会而去之。
孔批皇涉及术数,无文献、事实根据。
总结:皇侃追求讲通条理,不嫌附会(所谓附会,其实就是纳入新内容而构成一更大体系。汉儒接纳五行,何尝不是附会。),孔颖达则专以释说经注事实为主,断绝枝蔓、外论、附会。孔疏之于皇疏,有驳斥,有因袭,是以复杂。
3.4、孔疏专据一家说
刘炫规杜,皇侃乖郑,孙诒让所谓“六朝义疏家不尽然”者。至孔编《五经正义》,始立“疏不破注”之例(据吕友仁《孔颖达〈五经正义〉义例研究》,则非是。)。
孔以为疏《礼》遵郑氏一家之说,无论《礼注》、《论语注》。郑注即误,仍据为说。别解可通,疏家仍申郑而不取,“礼是郑学”故也。乔氏又谓礼说有体系性,须以郑驳郑,求体系内矛盾。此亦“据郑学”之意。(吕氏则以为“礼是郑学”,但国学《礼记》注本用郑氏耳。)
乔氏以为疑杜注者出于刘炫,遵用杜学者孔颖达,二者非出一手。(吕书“一家之学”、“疏可破注”二例,未辨刘、孔,立论则含糊而不确矣。)
僖三十三年疏:“使《礼》《传》各从其家而为之说耳。”乔氏以为:此《正义》凡例也。故《礼记正义》遵郑,《左传正义》遵杜,不相混淆,亦不嫌差异。盖六朝义疏为谈辨之学,求言之通理辨析,不求得事实。不断是非,但求讲理高明而已。二刘乃驳之,依据文献实证,讨论现实,罗列事例,讥斥先儒之不实。二刘以书证事例之学,乃摧廓尽六朝论理谈辨之学。“事实”取代“论理”成为释经之标准。然二刘之学实无根基,罗列书证非出于熟虑,正说反说,皆可随意举例(若辩论赛然)。论说无定准,固不成一家学说体系(二刘若立场先行之辩手,任为正方反方,皆可举例,但求胜人。无问其所持论是否彻底之事实也。但求胜理,旧义疏学;真求事实,孙诒让是也;二刘实染旧学方式。)。故二刘书证事例之学为后世遵,具体观点则不然(本非一定之真实)。孔颖达掇拾遗说,取舍之际,姑立一标准,曰“专述注家学说”。六朝义疏谈辨论理之学,本不求事实;二刘随意破斥,不成体系;孔颖达等于废墟之上,乃立此遵守注家学说之体例。若贾公彦《二礼》疏专述郑学,则因南北朝义疏家探讨礼学,惟有郑学有体系可依,舍郑无以言礼。此与孔君取舍之际、立例遵注者不同。(贾是旧义疏家专门之学,孔是二刘破坏旧学体系之后,无所依傍,姑以遵注为例。)
3.5、孔颖达权衡谨慎
孔颖达对于皇侃曲说,去取审慎。未必事实仍存。官修谨慎,未若二刘肆意攻驳。
3.6、结论
孔颖达自为节段,纯据经文事实,排斥皇氏附会。
孔颖达立例“疏不破注”。六朝义疏学于经注之外探讨论理,非关事实,故无所谓破不破。二刘破坏谈辨通理之学,创为现实书证事例之学。先儒异说纷纭,二刘但求攻驳,事实无从定案。于是孔颖达定例,疏一家之注,则概从一家之学以为准。此例既异于六朝义疏,亦异于二刘,乃《五经正义》之新例。
孔颖达态度谨慎,不一概否定先儒,取舍审慎而不拘泥,亦无蓄意攻驳之心。
乔氏以为:《三礼》以《礼记》最难,注疏尤难。欲通此书,必先精通清人所论经注大义,次研究书中所引贺循、熊安生、崔灵恩等诸家学术,并旁通史载历代礼议,次乃考订文字,始得卒业。(《礼记》疏,须辨皇侃、二刘、孔君三个层次。)
4、佚书验证
4.1、《礼记子本疏义》
《礼记子本疏义》,皇侃弟子郑灼案语。抄本或在陈后唐初。此卷即皇侃旧疏。
郑灼每抄皇疏毕,辄发批语,插断上下文;简短浅显,无所发明。
孔疏但取皇疏原文,不取郑灼。庾、贺诸家,皆皇所引。郑案浅显,无足重要。
此书抄写体例,每录经注一段,空格写疏。以经注为“本”,疏义为“子”,分章断句,事类相从,是名“子本”。
观此书,可证孔疏不取皇疏经文上下论理关联。
孔疏分节虽繁而无条理。皇疏贯通连关,规模宏大,极尽附会,言之成理,所以风靡一世。
皇疏有论理不清,而孔疏为所误者。不取皇疏大义而取末义,又未甚解,以致论理不通、歪曲不畅。亦见孔编粗糙。
《小记》“礼,不王不禘”。孔以为记者乱录杂厕,无义例也。皇则欲据今本经文次序构筑前后论理关系,不嫌牵强附会。后人则欲恢复古本。各家学术,目的、方法不同,不必定论是非、得失。
孔疏删除皇疏声训、“因名比附”。
皇疏文辞秀巧。变言“云”“曰”“言”。喜对仗。孔疏皆不然。
总结:①皇侃科段前后连关之说尤牵强附会,孔一切不取。②孔或不甚解皇侃本意,去其说而用其语,变为己说,以致论理混乱,义不甚通。③皇侃附会声训,孔不取。④皇留意文章,言辞修饰,孔去之。
4.2、《孝经述议》
吕侯、《吕刑》。孔颖达讳言《尚书》孔传之误,删去刘炫非孔之辞。
刘炫《尚书》旧疏述孔亦攻孔。孔编一遵孔传,取述去攻。
“斯不然矣”,接以驳难,刘炫疏常例。“配字无义意”说。
《孝经》。汉儒附会,以说理宏富恰当为追求,明知附会,固非所以探求事实。(义理价值之学)刘炫但论事实(语文史实之学),驳难汉儒,貌似理胜,其实论说层次不同,不足以服汉儒。刘炫所为,根本蔑视先儒学术方法,不可谓所以纠正先儒失误。
二刘论证经典文字,常据后世俗事为说,堆累事例为证。
二刘、王劭以通假用韵之实例为据,创定新见。《述议》言四声别义,为今世借音,古无其别。
探索一家辞例。
“则天之明,因地之利。”梁武帝为一代学术宗主,皇侃等皆门客。梁武帝论“则”“因”深义,因训诂以及天地大义,风趣而论理精密。但非事实,附会说理,刘炫辩难。此非学术内部切磋琢磨,而是不同学术之自我主张。
刘炫现实主义,否定南朝附会通理之学。
《孝经述议》亦有科段。但简述要旨,不为前后关联之说,不抽象,不附会。讨论作者之意,分析文势而已。
刘炫轻视《白虎通》,与《书》《左传》疏同,与皇侃重用《白虎通》相反。
总结:《孝经述议》排斥附会、堆累事实为证、叠用诘问句攻驳先儒、利用文献广博精审。其科段,则以分析经文内容、讨论编例为宗旨,不同于皇侃之附会论理、演说前后关联。
5、贾公彦新义
5.1、《二礼疏》多因袭旧疏
《二礼疏》袭用旧疏而失于剪裁,乃致前后轩轾。论说灭裂不通处,盖贾公彦撰疏不精审也。
贾有比附彼事以释此经者。贾有望文为说,拘注妄推,乖理而自戾者。贾有泛化特例者。
贾氏草率,援彼释此,不知事异不可以相例。贾氏但剪贴旧疏而已。
《周礼》旧疏备于《仪礼》旧疏。
《二礼疏》有创说者之言,有编订者之言,即贾。
5.2、新义
贾疏何以独存?
一则旧疏不备。《周礼》独沈重四十卷,贾或取资。《仪礼》旧疏但二卷、六卷。可推《周礼疏》多袭旧,《仪礼疏》多贾自说。旧疏极简,贾欲逐句疏解全书如刘孔,无可因袭,必自撰。却态度草率,多凭联想,随意下笔,不详审文义。
二则体例。逐句全疏,可谓详备。须知六朝义疏旨在通理,未必以解经注文义为目的,故二卷可了。刘孔必欲得经文正义,乃逐句疏解。此亦新旧学差别体现于义疏体例者。但就逐句疏解体例而言,贾不同于六朝旧疏,乃同于刘孔。是贾因袭旧学内容,而模仿刘孔体裁。此亦隋唐新风使然。贾疏外形趋新,内容仍旧,所以为义疏学演变之殿军也。
然旧疏内容,贾疏亦有改造补订创新,常得于三疏新见。
三等德。《周礼疏》比附《老子》。盖贾见熊安生说,生搬硬套,论理灭裂。熊说虽附会(多引外义),却自条理清晰,结构完整。贾窃而无当。
贾两说不同者,或一仍旧,一改移。常随意变乱。
《大司徒》旧疏就语助之微,畅论深义,望文发挥,不足以移论他经。而贾移之,突兀立说。
“委貌”。贾不辨名物。附会“经记相应”,非出于文理自然,自矜仿佛皇侃。平实、牵强,虽可各自成家。然贾既破旧复仍旧,迷惑读者。贾疏改造而不全新,徒见论理混乱耳。
5.3、结论
《二礼》旧疏不备,《仪礼》尤甚。旧义疏学,重在通理,卷帙极少仍可成书。贾仿刘孔逐句疏解,自多补撰。然态度草率,强援彼此,不顾无干。故《仪礼疏》谬更多。贾又有改造旧说之例:彼经旧说,歪曲以就此经,致论理混乱,读之不得其意。不勘旧说,难明贾改制之意。
总结。孔贾皆据旧翻新。孔疏新说,或刘孔排斥附会之说,或孔遵注家、迁改旧说。贾疏新说,则多轻率引释彼此,不顾本不相通,强为比附,文理滞涩,难明其意。孔贾之新不同。贾不攻驳附会,孔不强为比附。然皆表面加工,而无创立新学说之力也。贾疏之流传,在其体例逐句疏释便于学习耳。论学术,则不如南北朝诸儒之能自力探研也。
6、贾疏通例
6.1、义疏学不为实事求是
义疏学非清人考据事实之学。
皇侃是通理之学,不顾经注原意,无关事实。二刘所攻旧学,每附会义理。二刘则为现实、合理、文献主义,类而非清学。孔贾不成一家学术。
郑注名物,贾疏概不言为何物,此常例。盖贾欲得郑注之深意,非名物之实。义疏学非考古学,非历史学,非名物学,非考据学。贾不欲此等“知识”。
贾不考实,二刘参合条理文献用字之例,亦非若清儒之历史考古探实。
义疏学为文字语言探索通理之学,绝不用古代礼器实物为之考证。(做经学,慎用考古材料与思想史追溯。)
《仪礼》贾疏,亦不须礼图。
郑注常抉发经文辞例,贾疏详为疏论,此其宗旨。义疏学以文辞观念为主,不关实际,不嫌烦琐牵强。
敖继公则靠实事求是之法别树一帜。清人宗郑而自诩实事求是,陷入矛盾。贾疏皆出于观念,不计实物、绘图。
要之,义疏学为文字通理之学,《二礼疏》以疏论郑说为旨,异于清人实事求是、考据名物之学。
6.2、“通义例”为义疏郑学之要旨
郑学自成体系,诸经注互相关联。探其条理,使郑学体系更趋精密,此乃义疏郑学之要旨。
郑注群经,相互关联,偶有矛盾,又以《郑志》调和,反覆论证,完善体系,此乃义疏郑学之目标,非训诂之学也。乃订例之学。
郑注特例,贾疏则推广以为通例,检讨诸经,探索体系化、普遍化。
义疏家滥用“地道尊右”。
普化一说而不灭裂,则可反证其说通理。义疏家乃常互引郑注,不顾与经文无关。“各举一事,一事自周,是互文。此据一边理,一边理不备,文相续乃备,故云‘互相备’。”
训诂有举类。“箪,笥。”
反复引述定说,极易趋向滥用陈词。贾疏之论理灭裂,多由牵强援用常说、通例。
引郑注,除探索郑学,亦需考虑实践因素。注疏引《论语》多郑,绝少何晏,可见义疏学背景。
总结,义疏家欲以郑注为通例,搜罗诸经例证,或说他经而用此说。异于孔编遵一家之仅为编书体例(前者是学说体系)。然或将郑君望经之说强推通例,或引无干之通例,则牵强。
6.3、训诂固化
顾炎武:“训诂出而经学衰。小辨愈滋,大道日隐。”贾疏辄引无干之通说,训诂尤显固化。乃至郑注之外,不许他义。倾向于一字一训,不兼别义。固执通说使然也。
6.4、结论
义疏郑学之主要特点,在固执郑注与义疏学常说。意在使郑注成为通论,通于他经,诸经注相明。又有义疏家自己推论礼之通例者。然多套用已成之定论,不顾不干经注。礼说外,训诂亦趋简单化。学术固化,人不思考(“思考”本旧学异于二刘之特点),沿用定论,义疏学以是废绝。
P308敖继公附说
敖继公逻辑自洽。证明“以经释经”方法行不通。南北朝唐初视郑如经,不容自由异说,不得不然。不然无所折衷,适显圣人制经之不完整性。(若圆满,何待二解?)
乔氏立场:圣经权威性瓦解。研究礼学,不必论是非,但如实呈现各家学说本貌而已。此谓“纯粹经学史研究”。
P321后语
乔氏对“经”无感,清儒阐发“经义”。乔氏泛爱古书,清儒借以为研究工具,无意甚解。乔氏自矜“经学史家”,清儒不过“经学家”。(清儒读书不如乔氏之平心得实,或如其言。然乔氏之自矜鸡蛋而憎恶母鸡,一何颠倒之甚也。)
乔氏以为不必迷信清学(从清学偏于考证而非义理而言,有理),须从纯粹文献学审查清学(即阅读国故之态度耳)。
三联版编后记
传统(三礼)义疏学,是郑学之延续。其理论形态类郑,是用郑法以治郑注。刘炫否之,可视为杜预经学之延续。郑君研究经书文本内在逻辑,为经而经的专业性文献研究。杜预探讨书后史迹,以事实为验证标准,否定汉代学者不顾事实、从文造例。郑为专业经学,杜为合理主义。班固、王充否定章句学;王肃、杜预否定东汉文本义例之学;刘炫、王劭否定为经而经之义疏学。孔编承刘,杂存旧学。后因王元感、刘知几、 唐玄宗等,专业性经学消失,啖陆大义之学开启。
《诂经精舍文集》。大言无益,须文本细读。刘文淇《左传旧疏考正》,实究义疏,孤明先发。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清儒以注疏为材料之渊薮(等之类书),未尝直面、细读注疏本身。唐前经著,语言、思维习惯大异宋后。须明其语义与逻辑。同一问题解答各异,各有其由。
2020.9.6撮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