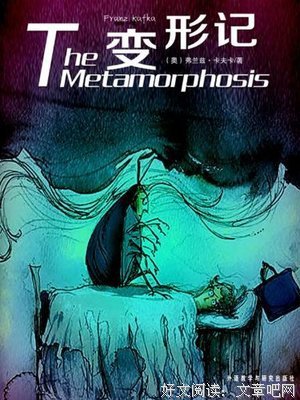读库0904的读后感10篇
《读库0904》是一本由张立宪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31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读库0904》读后感(一):我母亲78-79的一点回忆
0904上肖逢"私人编年史1978"里提到了受身边人的刺激决定报考大学的经历, 让我想起来今年25岁生日时收到的邮件里, 母亲描述的他们的78-79:
quot; 78年的夏天第2次高考就没报名,那年我们25岁,你奶奶买好了大立柜家具看什么时候办事(结婚)呢!也就在那年年底,冬季的一个周日晚上,在杨陵火车站昏暗灯光下,我俩等火车要返回在武功县城的工厂第二天上班,碰到了一老同学,人家是工农兵学员毕业在西安工作,人家要返回的是西安,是在大学工作,而我们返小县城工厂,巨大的落差震动了我,我们不比谁差啊,可难道我们今后就这样沿着这条铁轨走下去?那天晚上促使我下了决心-----高考!脱离工厂!是我决定的,我们商量赶紧复习功课,来年夏天考试!我们就没理科的底子,就考文科!文科是死记硬背的。这个决定成就了我们今后的生活。可见人一生中有许多关键时刻决定未来。我觉得我就象那个小鲤鱼要跳龙门。当我后来回家告诉家人,我父亲极力支持,他说的是你考上考不上,要有敢于试试的勇气!只要数学不是零分就有希望。而母亲劝我,又要上班又要复习太累了,实在不行有个工作以后安定些就行了。我大哥在杨陵中学当语文老师,他让我试着写篇作文,虽没上过大学,可他说比他班上的高中生强多了,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们在书店买来全套的高中课本,把90%的精力都用在了自学做数学题上,为的是不考0分!
所以25岁对我俩才是起步。第二年,26岁的我俩脱离了工厂没完没了的夜班白班,一纸录取通知挥挥手走了——其实没那么浪漫,我知道有录取通知书时,在医院里,父亲心梗病危,我知道时日不多,甚至不想及时去学校报到。我去报名第一天,学校里到处是欢迎新生喜气洋洋,我径直去找系主任请长假,人家惊讶不准假,我大哭一场。那年12月10日,我胳膊上戴上了黑纱,26岁时父亲走了,太早了。"
---------
当年规定若有一门考0分是不能被录取的, 后来母亲数学考了12分. 上了宝鸡师范学院, 也就是现在的宝鸡文理学院, 中文系.
父亲77年曾去考过一次, 只是凑热闹, 没有准备, 落榜. 79年考的比较好, 被西北大学录取, 哲学系.
因为他们上了大学, 所以我的出生推迟了5年. 否则现在我该是30岁, 不知在哪?
母亲和父亲当年工作的纺织厂, 化肥厂, 效益不好, 现在应该已停产了.
《读库0904》读后感(二):二百年来皆盛世
《读库0904》的文章选择很妙,前几篇在主题上似有一根线隐隐相连,从古到今,讲着同一个寓言。
张宏杰的《乾隆皇帝与鸦片战争》,讲述中国打开近代史大门的那次事件的原因。不同于教科书,这篇文章没有特别强调所谓帝国主义的贪婪和侵略的本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等等官方范式话语,而是主要从中国自身一方来探讨问题,并特别对以乾隆为核心的清王朝领导集团无以伦比的自大和愚昧加以分析。马戛尔尼访华,其经济利益目标是很明显的:一方面,英国对中国入超,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另一方面,英国迫切需要清楚中国的种种陋规和壁垒,以为英国商品打开市场,缔结自由贸易关系。
中国人心底对与外国的自由贸易总是存着敌意,毕竟以往的教科书中都教导国人帝国主义是想通过贸易来掠夺中国的财富,同时还打击中国的手工业和民族资本等等。在这种逻辑前提下,马戛尔尼访华自然也是不安好心,整个一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英国人,乃至整个西方为什么拼命追求自由市场?因为至目前为止,自由市场是使创造财富的最佳选择,自由市场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最佳选择。任何一个交易都是由至少两方完成的。总体来看,自由市场并非仅仅对其中一方有利,而是对多方都有利。在洋务运动时期,国人看到洋商经营轮船运输利润十分丰厚(在上海和武汉往来一趟基本就能够收回一艘轮船的成本),因此建议当时主政的曾国藩也开办官营轮船公司。但曾国藩却不愿意,因为为他的湘军提供物质支持的人中有许多是国内搞运输的,他认为运营轮船公司将会砸掉自己的支持者们赖以生存的饭碗。后来李鸿章开办了轮船招商局,的确毁掉了传统帆船运输业,但却并没有砸掉相关人员的饭碗,反而给他们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轮船也需要工人,轮船的出现有使得运输业发展迅速,然后又刺激了贸易,贸易有需要运输,形成良性循环,而这个良性循环又提供了大量的与运输行业相关的工作机会。最终,大家都在获利。
然而在清王朝这边,乾隆皇帝只是想着又有一个番邦归附,又有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稀奇古怪有趣的好玩意,并且要在新归附的番邦面前展示下大清朝的“繁荣”与“强盛”。盛大的欢迎与招待,沿途的炫耀,各种方法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正是这些炫耀,却让马戛尔尼看出了破绽——与传统欧洲对中国的想像与向往不同,马戛尔尼眼中的中国是一个思想落后,文化沉闷,政治腐败,军纪散漫,民生凋敝的国家。沿途,英国使团看到清王朝官员随意抓夫拉纤,体罚无处不在,“上一级官员随时可以名人把下一集按在地上,打一顿板子。”“英国人说,这种卑劣的顺从是‘人类灵魂的堕落,目睹这一切,你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胸中燃烧起来的愤慨之火。’这个国家不但不值得欧洲人学习和尊敬,相反,还应该接受欧洲的教化。
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带来的英国最先进的枪炮,战船模型,工业产品没有任何兴趣,更不可能从中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先进技术和生产力,于是全都当做垃圾所在了仓库中,直至被许多年后火烧圆明园的英国军队发现又原封不动的运回英国。至于英国所提出的建立通商关系的要求,也被失望的乾隆坚定地拒绝。
乾隆的行为让英国使团坚信,中国是一个愚昧且自大的国度,英国应该用武力去教训这个国家,用枪炮打开其闭锁的大门。而且,根据中国目前的国情,英国有这个能力。
悲剧就此开启。后来英国人输入鸦片,并且挑起鸦片战争,自然有其强盗逻辑在作怪。然而,中国自身的问题占的比重或许更大。一个一小撮人通过专高压政策对亿万人实施专制统治,一个官员可以随意抓夫、体罚下级及平民,一个国家不尊重保护国民的尊严和权利的国家,当然是一个落后,且应该改变的国家。
乾隆皇帝的清王朝拒绝主动学习改变以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于是,这些改变都在枪炮声中被强加来了。英国人在平等的外交谈判中没有得到的,通过鸦片战争全得到了,而且更多。
在第三篇肖逢的《私人编年史:我的一九七八》中,读者可以管窥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整人运动刚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的模样。那时候的中国和乾隆时期的中国并无二致,一样的落后,一样的贫穷,一样的愚昧,一样的专制。最重要的,都有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盛世”。
再回到第二篇马宏杰的《西部招妻》。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深有残疾的河南农村青年最近几年三番五次到甘肃娶亲的故事,字里行间多无奈与悲怆。这篇文章也展现了当代中国之“盛世景象”:西部某些贫困农村的人们为了省下一元钱的洗衣粉钱,被子真的从来都没有洗过,而能有两床完整的被子也算是好的了,更多人连御寒的被子都没有。那儿的人们依然过着与古时“卖儿鬻女”一样的生活,靠着嫁女的彩礼生活。“挣扎在贫困边远的人,他们会抓住每一个到来的希望。这种希望有时是不能用正常的伦理道德去衡量、评价的。”在那儿,乡里的一个电工下到了村里就像鬼子进村一般,家家户户闭门关窗加以躲避,因为那是厉害的大人物。
“命运,好像总是在捉弄那些贫困之人。”
如今,时逢六十甲子大庆,中国人又享受着一个“盛世”,大地上充满繁荣与和谐。依稀间,从乾隆的十八世纪初,到七八年,到2000年,再到现在的2009甲子大大庆年,二百年来,中国似乎一直都处于太平盛世。
《读库0904》读后感(三):如果个人的经历是笔迹,那么这支笔勾勒出的是时代的肖像
最新一期(0904)的《读库》里,充满了我喜欢的主题和文字。曾经写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的张宏杰的《乾隆皇帝与鸦片战争》,以对细节的留意与描述,展示了老大帝国西山残照的最后一抹余辉以及迫来的黑夜间的波谲云诡。老乡马宏杰的《西部招妻》,图文并茂地记录了家乡一个残疾菜农青年到宁夏南部买老婆的错愕历程,熔炼出人生的荒诞与悲哀的本象。还有肖逢的《私人编年史:我的一九七八》。如果把个人的经历比喻为笔迹的话,那么他的这支笔勾勒出的是一幅时代的肖像。无论是“蝴蝶效应”还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每个人的个人史都是历史的一个真实侧影。张铁志的《“我不属于运动的一部分”》,还原出一个迪伦自我认同的迪伦,让我想起李皖的一篇文章《揭穿“投降派”许巍的真面目》,其主旨都在于告诉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他人主观的投射与我无关。王鹤的《柳如是》,唤起我对近三年前自己写过的一篇《柳如是》的回忆,并与近期于陈寅恪先生神思萦绕的追慕相映照,促使我对旧文补缀,而新旧对比亦可窥见三年时光投于我身上的影子。最后,是赵瑜的《北岛三札》。
对于北岛,之前除了知道他是时代交替之际朦胧诗的先锋之一以及有关《今天》的片段传闻外,他的生平了无所知;他的作品,除了知道有《回答》和那著名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外,也毫无接触。《北岛三札》评述了北岛寓居海外后的三部散文集:《青灯》、《蓝房子》和《午夜之门》,文章的笔法和文意有种往日时光与长路风尘的味道,接通并激活了已深入骨髓化为基因的传统符码——那饱含感时伤怀与羁旅乡愁的诗意,也激发了我对北岛及其《青灯》的兴趣。
取读《青灯》,发现赵瑜书写《北岛三札》的笔触意蕴可谓是对北岛文风文法的借鉴或摹仿,而这本身也体现了对心仪作品及作者的致敬,这种笔触意蕴恰如赵瑜所言,“这种打捞岁月碎片的写作方式注定倾注着中国式的伤感”,“他简短的句子,用词精确而又隐忍,完全是一个教授古典文学作品的教授的笔法”,她们是“激情的,简洁的,有力量的”。
《青灯》由上下两辑组成,上辑是怀人,有北岛的忘年交冯亦代、熊秉明、蔡其矫,声气相投的知音魏斐德、艾基和周氏兄弟,有发小儿刘羽,有玩伴儿AD,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芥茉,其中的一些已经作古。很喜欢感怀冯亦代先生的《听风楼记》和蔡其矫先生的《远行》,因为其中作者追忆出许多鲜活灵动的细节,“细节象灰尘在阳光里的舞蹈一样,真切又动人”(赵瑜语),耐人寻味。而我们于远人与往日的记忆,又何尝不是由这样如星星般闪亮的细节构成。《远行》是上辑的末篇,由她引出的下辑,果然记录的都是作者的远行。那些刻划过作者羁旅风尘的人事,反衬出的其实是作者自己内心的漂泊。其中的一篇《旅行记》很特别,是作者本人对自己半生漂泊的综述和总结。漂泊,不是形体的位移,反而是心态的沉淀与凝聚。已过中年的北岛,用这些文字从其人生阅历和匆匆行色中回退,一直退回到出发的地方。而他于有关的远行的记叙中,并无意于描写路过的风景,其着意处也在记忆漂泊中遇到的人和体味到的友情。于是,《青灯》的上下辑,是气息相通的,她隐寓着作者于这世间寂冷的漂泊中对于友情温暖的感恩和期盼。对此,我亦心有戚戚焉。因为,旅行的意义,对我来说,并非为了寻觅那些别样的风景,而是在路上遇见别样的人,以及彼此间怦然心动的一刻,如漫天大雪中一盏青灯的火焰。
《读库0904》读后感(四):居然都是一场误会
先挑了三篇文章看,《乾隆皇帝与鸦片战争》,《暴力棋王》和《言之有误》。
《乾》文再一次让我生疑,即历史上“盛世”是不是多“盛”在朝野和谐,“盛”在开疆扩域,“盛”在明君有爱,真正惠及子民的“盛”有没有?1792年马尔戛尼眼中的“康乾盛世”中的八旗精兵不过是基本处于冷兵器时代的一堆摆设,而其子民完全是一群浑浑噩噩的“东亚病夫”。毫无悬念地,这个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能在短短的50年后被几条船上千把个英国人杀得一败涂地。
这种盛世真是一场误会!
《暴力棋王》是近年来少有的精彩的报告文学。看似斯文雅致的围棋其实盛有最暴烈的小宇宙,最冷酷的征服欲。这些欲望的冲撞在19X19的纹秤中被理性牵引和释放。古力有遗传自其父的拧棍执着和重庆的江湖杀伐之气,这是政治的聂卫平,文艺的马晓春和乖乖仔常昊不具备的。办到最后,做大事,成大业,没有一点点匪气是成不了事的。
这是不是斯文的误会呢?
《言之有误》首先在体量上让你折服,东东枪吹响了几百个他认为经典“隽永”(冷汗一身啊)的段子集结号,一次玩个过瘾。尤其是:
人不烦我,我不烦人,人偌烦我,爱慕骚锐。
臊眉耷眼的,我走了,正如我挤眉弄眼的来。
我的地盘我看行。
今夜的芥末让我如此美丽。
丑姑娘爱文艺,正如小才子都是胖墩儿。
松下问童子,言师嗑药去。
人说百花的深处,有着老情人,啃着绣花鞋。
“哪天你心情好,咱分手吧”。“成啊,我今儿心情就不错”。
。。。。。。
灰机上读这篇文章时时不常傻BB的笑一下,周围的人颇狐疑。
东东枪的旗号是“仁义道德不常在而插科打诨常在”。我总觉得这也对东同学愤青的误会。 我以为,所有段子都是通过自嘲自渎以貌似绝望的样子追求新希望。
《读库0904》读后感(五):《西部招妻》让我回想很久
其中有一篇是马宏杰的《西部招妻》,我看过去年的读库有篇他写的报道耍猴人的生活。
华北地区农村自然条件好的地方,有不少人去宁夏贫困地区招妻。西部招妻》就是通过一家人为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儿子招妻的过程,呈现这个社会现象的。
“人的生命有时就像一粒种子,随风飘落在什么地方就得生根、发芽、成长,因为这种环境不是自己能选择的。哪怕这种生长有时是扭曲的,它也要生长。恶劣环境中的人们想要改变生存条件,最好的选择就是迁移到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去。远嫁到好的环境中去,对这里的姑娘来说就是唯一的出路。家里既得到了经济补偿,自己又改变了生存环境,应该说是件好事......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人,他们会抓住每一个到来的希望。这种希望有时是不能用正常的伦理道德去衡量、评价的。”
改变是需要条件的,钱--受教育,受教育--才能有见识,有见识走出山村或者再回到山村改变它(基本也没人愿意再回去吧?)。但是女孩的家人不一定就愿意出钱让她们受教育,他们要的是直接的回报。真是解不开的死局。
即便是嫁到好的环境,生活依然是个未知数,变好还是进去另一个困境,得靠自己走。
《读库0904》读后感(六):流水行云│事关《读库0904》
引言
“流水行云”原是我几年前出差时给爱人小牛所寄明信片的总称,不过是自嘲“流水账似的边走边说”,是汇报,也是自白。2008年7月整理访书翻书日志时,想着这题目挺适合的,便拿来一用。现在挑出有关《读库》的文字,按各辑出版时间重新排序(原来是随翻随写),写作时间附于其后。诚如网友所言,“现代信息繁多,不可能每个人擅长每件事,书籍不再是‘我宣扬你接受’的单方模式,网络提供更方便快捷的交流可能,大家共同进步便是!”我将有关《读库》的文字整理发布于此,便是意在与同好互动。今后若有新篇,将陆续增加。
《读库0904》(张立宪主编,新星出版社2009年8月版)
“人类对自己处境的每一种发现,其实都不过是历史的重演。”对于李树波的《大地上的恬美与危机》,我并不感兴趣,不过他这句结语,却道出了自己阅读《读库0904》某些文章的感受。
比如张宏杰的《乾隆皇帝与鸦片战争》。“如果用暴虐、压迫和不公来描绘所谓的统治者慈父般的关心和热爱,用畏惧、欺瞒和忤逆来描绘统治者的子女般的孝顺和敬畏,恐怕更接近事实。”巴罗的话揭露了历史的真相,一定程度上,也是现实的描摹。顺着张宏杰梳理的历史脉络,比照当下的社会万象,不禁让人感叹政治意识进化的艰难:“敏感词”丛生,论坛发帖犹如过雷区;“绿坝-花季护航”横行,似乎网民都是儿童和奴隶;电影分级制度如镜花水月,公映的电影删了又减……“父权统治”阴魂不散啊。
又比如肖逢的《私人编年史:我的一九七八》。肖逢的文字平实,隐忍的叙述中,间或有冷幽默。学生打闹导致眼睛受伤,失手者逃走,肖逢说:“买单肯定是厂里了,不要说学校有责任,就凭社会主义优越性也该企业负责。”回忆成都古籍书店的背后街上的图书自由市场,肖逢庆幸:“还要感谢那时没有城管,否则成不了气候。”看到那条街上源源不断的旧书,他又感慨:“要想人为革掉一种文化的命,实在是太难了。”当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舅舅挨整几十年,后来要求组织落实政策,却被告知其档案里没有任何属于政治污点的材料,故落实政策无从谈起。想想几十年后,没有“下岗证”的失业人员,为相关统计部门所忽略,是享受不到帮扶政策的,可谓“太阳底下无新事”。
马宏杰的《西部招妻》,和《耍猴人江湖行》一脉相承,用两只脚丈量出真实的民间,用手中的笔和相机记录世态人心,正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书斋里的想象明显是单薄的。熊菂的《直至群星在你脚下》,无疑是“又贱又疯又简单”的产物,“人无癖不可交”的“癖”,或许就是指作者这种程度的。我被“哈儿”那节深深打动,并在Google搜索里输入“answer to life,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出来的答案果真是42——这大约是Google在向《银河系漫游指南》致敬吧。
挑点刺儿:P13第一段,“绵纺机”应为“棉纺机”;P13第一段第二行,P38第二段第六行,P96倒数第五行,均多了一个空格,也许应该换行的;P48第四段,“从1993年开始”应为“从1998年开始”——P50上图说明提及“这是1997年,老三和母亲到河南叶县去相亲的路上”,恐为作者笔误,疑似1998年,也有可能是正文错了,应为“从1997年开始”吧;P161第三段,“满脸胀得通红”应为“满脸涨得通红”;P167第六段,“全盛时间的李昌镐”应为“全盛时期的李昌镐”。此外,《“我不属于运动的一部分”》一文中,“Blowin' In The Wind”的译名一会儿是《在风中飘荡》,一会儿又是《飘荡在空中》,最后又成了《飘荡在风中》,应统一为好。【09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