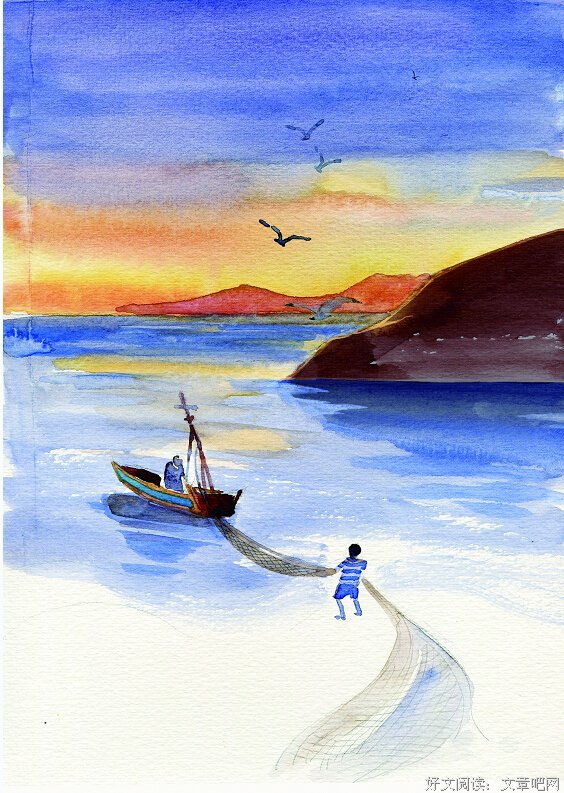《增订书目答问补正》经典读后感10篇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是一本由张之洞 / 范希曾 补正 / 孙文泱 增订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79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读后感(一):购书半月有余,一点见解
无论是从哪一方面来讲,我们需要这么一本切近实用的书籍,半月前从当当购买到孙老师的这一本书以后,这半个月以来也或多或少阅读了一些,略谈一些感受吧。
书是很好的,老师看出来用的心非是一般人所能及的。毕竟,对于百余年来这么多书籍的整理、编订,丝毫说是不逊色于新著的。
翻检起来的话,就算是鸡蛋里挑骨头的话,便是或多或少有点感觉文辞的反复,也就是说有时候写的不易理解。甚至是很多地方前面已经有讲,而后面重复了。
当然,这是新作所不能避免的,但是,在这一本书里面所最让我敬佩的便是作者能在出书以后对原书的错误还在博文里进行修订,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让我辈倒是真的敬仰的。
(《书目答问》)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馀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范希曾
(《书目答问》)或指示其内容,或详注其版本;其目皆习见之书,其言多甘苦之论。彼其所以津逮后学、启发群朦者,为用至宏。肩斯任者,然非殚见洽闻、疏通致远之儒,不足以膺此大业。——汪辟疆
但欲求读其书而知学问之门径,亦惟《四库提要》及张氏之《答问》差足当之。——余嘉锡
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鲁迅
今人漫言读书,即读书目亦非易事。——叶德辉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读后感(三):《增订书目答问补正》初见录
来自中华书局句读社区
http://bbs.guji.cn/showtopic-1217.aspx
在书店见到《增订书目答问补正》,望大家能不吝赐教!
《说文解字》
1.中國書店据商务影藤花榭本影印本(无額勒布的序)。
2.中华、上古影印《黄侃手批〈说文解字〉》。
3.小徐的《说文篆韵谱》建议放在小徐的《系传》之后。
4.《马叙伦手批〈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段注》
1.成都古籍书店影印的不是经韵楼原刻本而是翻刻本。
《广韵》
1.江苏教育影印《宋本广韵》附韵镜、七音略,巾箱本底本高宗本、矩宋本配补。
这书与《四部丛刊》本不同,《四部丛刊》是用的是泽存堂配补的。 江苏教育影印的《宋本广韵》二版时才附上《七音略》。
《集韵》
1. 中华书局古代韵书系列,影印《宋刻集韵》。
——————————
其他的例如孙星衍《孔子集语》易得到的《二十二子》本,我记得好像您的书中好像没有提到。
唐石经有中华书局影印张宗昌本,书名是《景刊唐开成石经附贾刻孟子严氏校文》。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读后感(四):经、史、子、集
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经部】
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于前代著作,撷长弃短,皆已包括其中,故于宋元明人从略。
【史部】
此类若古史及宋以前杂史、杂地志,多在通行诸丛书内,此举善本,若诸本相等,举易得者。
【子部】
周秦诸子,皆自成一家学术,后世群书,其不能归入经史者,强附子部,名似而实非也。若分类各冠其首,愈变愈歧,势难统摄。今画周秦诸子聚列于首,以便初学寻览,汉后诸家,仍依类条列之。此类若周秦诸子,及唐以前儒家议论经济之属,宋以前儒家考订之属,唐以前之杂家、释、道家,宋以前之小说家,多在通行诸丛书内,此举善本。
【集部】
楚辞卷第一
隋唐书《志》有皇甫遵训《参解楚辞》七卷、郭璞注十卷、宋处士诸葛《楚辞音》一卷、刘香《草木虫鱼疏》二卷、孟奥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始汉武帝命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其书今亡。按《屈原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又曰:“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孟坚、刘勰皆以为淮南王语,岂太史公取其语以作传乎?汉宣帝时,九江被公能为楚词。隋有僧道骞者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唐,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
【丛书目】
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读后感(五):可有可无之增订
从前读周一良先生的回忆文章,讲他年轻时求学燕京,听邓之诚先生月旦人物,有云“对于当代学者一部极见功力、十分有用的目录学巨著,他目为'沾沾自喜,刺刺不休'。”小子无知,对这位学者不敢妄加揣测,读这本《增订书目答问补正》时,“沾沾自喜,刺刺不休”八字却不时浮现。而《增订》一书既无功力可言也谈不上十分有用。
纵览全书,只需要将《续修四库》《丛书集成》《四库荟要》《石刻史料新编》上古中华经史子集各丛书子目罗列《答问》原书各条目下,已可增订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无非借助各种电子索引复制粘贴,况前人于此书笺注已多,增订不过抄撮群书,所下按语多不痛不痒之常识,无功力可言。范希增为《答问》作注至少依靠江南图书馆,有所目验。增订者多赖电子索引,所见不广,亦难细查,如张惠言《茗柯词》下注《茗柯词选》江西人民出版社。此书实张惠言所选之词,非张氏词选集。只看书名就免不了这种错误。
此书前言东拼西凑,行文拖沓,多文人稚语,网罗诸说,皆以“某某人说”罗列,烦而不要。如论《答问》作者,虽为诸家观点分类,然不能下己见。如古书注解虽多而能贯穿诸说下断语方为能(题外话)。结尾一句“可谓众说纷纭,那是相当热闹”或许增订者是抱着旁观者心态,姑置不论。
凡例亦问题不少,如“本书计划五年修订一次”。近世对《答问》一书的补订有不少,但在出版业发达的今天实在补不胜补,没必要为一本过时的书做那么多增订(版本研究不算)。黄永年先生提过现在需要的是一部便于初学古籍要目(大意)。
昔人谓“置书怀袖中,学问自增长”《增订》将薄书做厚恐怕难以置君怀袖,昔人也批评过《答问》一出,导致一种空疏学风,今人以增补新书为能事,全忘了目录学大旨。此书评价这么高,又为人辗转推荐初学,可发一笑。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读后感(六):不是书评一点感受
今天收到了孙文泱老师惠赠的新作《增订书目答问补正》,真得不是一般的高兴。因为在我今年准备购买的书目中,就有《书目答问补正》。只是,此前市面上流行的版本,我一直不太满意,主要就是校订不细,错讹太多。对于这种经典之书,我不愿将就,所以一直在期待一个善本的问世。而孙老师的这部大作恰好就是这一名著的善本。读书要读精善之本,目录方面的书,更要择善而读。
收到此书之后,立刻读了一部分。孙老师的大作,我实在无资格评论,这里只是谈谈自己的感受,“与读书人分享”。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指出,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比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每每讲中国古代史的导论之时,我都要引用这段话,既是对同学们的引导,也是一种自勉吧。作为读书人,目录之书就是一把金钥匙。目录之书种类很多,“但欲求读其书而知学问之门径,亦惟《四库提要》及张氏之《答问》差足当之。”(余嘉锡语)
而孙老师增订的部分,我个人觉得,最大特点就是“与时俱进”,特别适合文史专业的初学者。很多善本,我们这些后学晚辈,其实很难从图书馆中借阅出来,所以孙老师增订的部分“善本未经刊布者,借阅困难,一概不列”。而是更多地列举了现在的点校本、校注本,而且标注了书的册数,最大限度地方便了我辈学人。既合理,又经济,又与时俱进,反映了某一特定书籍整理方面的最新进展。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读后感(七):节选《通鉴》一节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宋司马光。元胡三省音注。胡克家仿元本,武昌局翻胡本。战国至五代。【范补】苏州局补胡氏版本,坊间石印胡本。道光间湖南翻胡本,不善。成都存古书局本,番禺任氏刻本,光绪十三年朝邑阎敬铭仿明陈仁锡刻本,长沙胡元常刻本,涵芬楼影印百衲宋本,《四部丛刊》影印宋本。常熟张瑛《宋元本资治通鉴校勘记》七卷,苏州局本。丰城熊译元《资治通鉴校字记》,刻本。
文泱按:《文渊阁四库》本第304—310册;文津阁本第104—107册。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四部备要》聚珍本,断句时有误,平装8册,精装4册。上二本多脱讹。世界书局缩印胡克家刻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世界书局本2册,1987。顾颉刚等据清胡克家本标点排印本,平装20册,古籍出版社,1955,且附章钰校记。流行最广,然底本不佳。1963年起版归中华书局,以后多次重印。“文革”后期经吕叔湘等通校正文断句标点,订正错误上千条,故标点本以1976年以后印刷本较好。据中华书局标点本横排简化字本4册,中华书局,2007。邬国义点校《资治通鉴(附〈资治通鉴考异〉)》2册,简化字横排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邬校以宋本为底本,极精审。仅有《资治通鉴》正文二百九十四卷及《通鉴考异》三十卷,无胡注。岳青标点《资治通鉴》4册,据涵芬楼本整理,岳麓书社,1990;第2版,2009。傅璇琮点校涵芬楼宋刊本《资治通鉴》,简体字排印线装本8函48册,线装书局,2004。施丁等《资治通鉴新注》10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底本用中华书局本,问题较多。新注内容较充实,文字不精练。何久香审定《新注涵芬楼本资治通鉴》8册,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正文及新注错误较多。张瑛《校勘记》、熊宿《校字记》,分见《通鉴史料别裁》第13册及第3册,学苑出版社,1998;张瑛《通鉴宋本校勘记》五卷、《元本校勘记》二卷,《四库未收书辑刊》三辑第12册影印清光绪八年(1882)江苏书局刻本。章钰《胡刻资治通鉴校宋记》三十卷,《续修四库》第342册影印上海辞书出版社藏1931年长洲章氏刻本;中国书店影印本同,1985。章氏《校宋记述略》,附于古籍出版社及中华书局版标点胡注《通鉴》前,可视为校勘学的范例及入门读物。宋谋瑒《资治通鉴校补》手稿影印本4册,三晋出版社,2008,是目前为止《通鉴》之古籍出版社及中华书局排印本最详尽的校勘记。中华再造善本《资治通鉴》,影印宋绍兴二年至三年(1132—1133)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20函116册;元至元二十六至二十八年(1289—1291)魏元祐刻本3函26册;《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据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3函20册;题吕祖谦辑《增节标目音注精议资治通鉴》5函50册,影蒙古宪宗三年至五年(1253—1255)张宅晦明轩刻本。《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一百二十卷、《目录》三卷、首一卷,宋陆唐老辑,《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3—5册影印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资治通鉴外纪详节》1函4册,据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朱熹《资治通鉴纲目》6函57册,据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宋范祖禹撰、宋吕祖谦注《东莱先生音注唐鉴》,据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元修本影印1函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和刻本东莱先生音注唐鉴》,京都中文出版社,1985。日本佐伯富编《资治通鉴索引》,台北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86。
《通鉴考异》三十卷同上。《通鉴全书》附刻本。胡注本已将《考异》散附本书各条下。【范补】《四部丛刊》影印宋刻本。
文泱按:《文渊阁四库》本第311册;文津阁本第107册。邬国义点校本《资治通鉴》下册附《考异》三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是目前唯一的《考异》三十卷单行点校本。《通鉴史料别裁》第1册缩印胡元常《通鉴全书》之三,清光绪十四年(1888)刊仿明万历本。《资治通鉴考异》2函14册,中华再造善本据国家图书馆藏宋绍兴二年(1132)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宋元递修本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读后感(八):典型的中国式劣质图书
如今已经不是手工出版的年代,反而绝大多数出版物错误百出,装帧版式丑陋不堪。这不是技术先进的罪过,而是人心或文化素质出了问题。中华书局2011年1版1印的《增订书目答问补正》(孙文泱增订,精装),不过是披上书皮的“书”罢了。略举这本书出现的两大严重问题:
一、文字错乱、排校不力。
正如附三《輶轩语•语学》(节录)上语:“读书宜先校书”。买这本书的确部分替代了出版社的排校工作,曾有读者评说“差不多每页都有错误”。还没有来得及仔细校读,不知是否属实。由增订者2012-02-05在新浪博客里发布的“勘误”百余条来看,其错讹脱漏之多定然是相当惊人的,且尚在不断发现的阶段。可见此书的排校工作是极不认真的,要不就是责编或排校者的古典文化知识很有限。出版社也不该纯以赢利为目的,而是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辞书那样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先出“征求意见”本,读者乐于参与订正,不断完善,同时也可以增长知识。这样读者似乎容易接受。
由于先看过其他读者的评论,知道这是一本问题很多的书,怕吃掺砂的食物,害人不浅,期待出修订本。但还是趁满200减80元活动便宜些时买来先睹为快——正如打靶,以此为的,拨乱反正,考校一番。
随手翻翻,除校对过增订者发布的百余条“勘误”外,错误随处可见,如:
第394页第7行 “《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合刊2册,中华书局”,后可补“《古体小说丛刊》本”。
第394页“《世说新语》”条倒9-8行更正:余氏笺疏本由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过,但不是“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1993年修订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纳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徐震锷《世说新语校笺》(1984)才是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第665页倒5行,“国朝之方姚恽、包世臣、曾国藩诸家,皆宜一览”一句,不通。标点不清,似应为“方、姚、恽”,且交待混乱,疑“方、姚、恽”后分别漏字。
还没功夫仔细检索,逐一列举。其实,只要多花些时间认真校对,绝大多数错误是可以发现并能纠正的,不至于千疮百孔。
二、更糟糕的是本书恶劣的排版,字体、字号、分段等处理得十分随意。
如“附录二”,似乎排版的意图是要将名家姓名后的“名”字体放大一号,却弄成有的是“字”大一号,有的则是“号”或生里大一号;有的加粗,有的则没有加粗。无统一体例,乱七八糟,让人莫名其妙。凡姓名后的字体字号用不着如此参差不齐,清一色处理即可。这种不堪入目的情形在全书中逐页可见。
想当年《书目答问》的补正者范曾先生在相对落后的条件下,穷其一生,以一人之功力,苦心爬梳,反复抄录,给读书人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也得到学术界的赞赏。如今出版技术进步了,电子排版工作大大便利,应该说做得要更加精美;且是经多人协作,反而搞出来的是狗屎不如的东西。也许是增订者偷懒,让学生输录文档。在学生来说,要么word文档处理技术不过关,要么粗心大意或者审美情趣低俗。老师把关不严,责编审稿粗疏,甚至看都没看就赶紧上市。
本书增订的材料就像陈列一堆杂货,取舍不严,大多数信息对读者没用;加之漏洞百出,稍不留意就要误人。这样的“学者”,纵使著作等身,不过是贩卖垃圾以谋利;跟兢兢业业地撰写或出版图书的前辈们相比,优劣自见。虽是精装一厚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略同于卖纸张。当这堆将要误人的杂货流向市场时,不知增订者及责任编辑是否有一丝羞愧感!
科技飞速发展,人心反而变坏,在出版界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已经不是主流。国内出版的图书,由雅致变为艳俗。电子版不如铅版,铅版不如木刻版。——别看现代人似乎见识的东西比古人多,变得比古人聪明,这些时代的优越性反而使得不少人浮躁趋利,尽干些投机的营生,对文化那一点点崇敬的情怀已经丧失殆尽。文化素养低下,审美趣味艳俗;市场因习惯于艳俗的趣味,并不觉其为丑,出版界投其所好,催生出恶俗的读物。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读后感(九):百年前的“好书榜”——《书目答问》的文化地位和阅读价值(12月6日《光明日报》13版刊出) 作者:孙文泱
光绪元年(1875),身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撰写《书目答问》。光绪二年(1876),在四川刊行。 后来张之洞《抱冰堂弟子记》一文曾讲过:“任四川提学时,撰《輶轩语》二卷、《书目答问》四卷以教士,宗旨纯备,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可见张之洞对自己这两部书的水准十分自信,回忆起来,志得意满。即便如此,张之洞也不会想到,也没有谁会预见到,这样一本十几万字的小书,竟然是张之洞接近一千万字的著述中最有市场、重印次数最多、流行时间最长、流通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
首先,《书目答问》与张氏《輶轩语》《劝学篇》等具有共同的撰述宗旨和理念诉求,共同构成张氏国学教育的三部曲。当然,张之洞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是培养士大夫,其间也不乏可供今日所谓通识教育设计参考的思想资源。《輶轩语》主题在阐释如何读,指示治学门径;《书目答问》提示读什么,全面展示四部之学的代表作品,尤其大力揄扬清代学术的主要成果;而《劝学篇》则申明为什么读,秉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宗旨。三书各有侧重,前后呼应,完整地体现了张氏的学术主张。时过境迁,张氏一些具体提法已经逐渐为社会所摒弃所遗忘的同时,《书目答问》以及《輶轩语》《劝学篇》的论学部分仍然有阅读价值,根本原因就在于张之洞的开阔的学术视野、深广的文化背景以及张氏对国学的透彻认识。在《书目答问》问世之初,固然有张氏门生分别印行,群起响应的现象,但长时段里《书目答问》的流行,就不能用张氏门生弟子遍天下的原因去解释,只能理解为《书目答问》的流行有其自身的学术必然性。
其次,《书目答问》改变了书目的价值取向。此前的书目,大都是针对皇家图书馆和私家藏书的,是针对少数人的书目,而《书目答问》则从设计初衷就是面向广大读书人的,把书目与读者的密切关系放在首位,这是目录学思想的一个带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与转变,从而为推荐书目和近代专业书目树立了学术典范。此前的龙启瑞《经籍举要》等书则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文化影响力。
再次,对学术路径的强调。《輶轩语》卷一《论学》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门而入,事半功倍。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下文指示各种重要书籍的作用时,又一次强调“《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以目录学作为学问门径,是清代学术界的共识,也是清代学术发展的重要表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书目答问》即秉承这一思想,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为学之道,岂胜条举,根柢工夫,更非寥寥数行所能宣罄。此为初学有志者约言之,乃阶梯之阶梯,门径之门径也。”在《书目答问》史部谱录类书目之属云:“此类各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途径。”《书目答问》2500部书的规模与整体结构,也充分体现了这种“阶梯之阶梯,门径之门径”的指导思想与收录原则。
在知道书名、作者信息之后,紧接着就是要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版本。因为图书与版本实际是密不可分的,任何一部书都有其具体的特定的版本信息。《书目答问·略例》说:“读书不得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与《四库全书》相比,《书目答问》的一大改进就是大量增加版本信息。这样,图书信息才是完整的,更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治学门径的指示,又包括了对小学的高度重视。《说文》著录约50种,远高于《尔雅》的15种,从而比较充分地展示了清代《说文》学的风貌,是《书目答问》比较精彩的片段。
又次,《国朝著述家姓名略》是《书目答问》一个极有学术特色的附录,更是一项带有创造性的贡献。《姓名略》按照经学家、史学家、理学家、经学史学兼理学家、小学家、《文选》学家、算学家、校勘之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家、骈体文家、诗家、词家、经济家14类开列名单,初步清理了学术与文学的系统和代表人物,是清代学术文化史的首次有意识的全面且系统的总结,以弥补四部之法凸显典籍而淡化人物的缺憾,是目录学史上极富创造性的学术理念及成功实践,超越了《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乃至《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汉宋藩篱和理学框架,用最简略的方式勾勒出清代思想文化的生动轮廓。《书目答问》的书目与姓名略相辅相成,构建了目、书、人、学四重要素的新型书目范式,将知识体系、代表典籍、著名学者、学术领域整合起来,以目录建立学术体系,以典籍代表文化成果,以著名学人树立学术典范,以学术领域来育化新人。同时,《姓名略》的设置,即是对四部分类法的结构性补充,又在体制内最大限度地弥补了传统目录学著作缺乏检索功能的遗憾,这也是迄今为止的目录学史研究忽略的方面。
最后,《书目答问》原有的知识空间、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有民国范希曾《补正》等为之继续扩展。又有蒋凤藻、叶德辉、伦明、周星诒、余嘉锡、王伯祥等很多藏书家、目录学家、学者的批校本,留下了丰富的版本学资料,至来新夏先生《书目答问汇补》方做一全面总结。大量名家的批校本,为《书目答问》增添了版本学价值,更灌注了新的文人趣味,开拓了《书目答问》的欣赏空间,丰富了书目的文化内涵。《书目答问》之所以是《书目答问》,就在于它提升了书目在传统文化背景与现代文化范式的转换与衔接之间的多层次价值,使得《书目答问》不再是入门级的敲门砖,它有了文化使命和历史责任,它衍生出来可供继续扩展的研究空间,增多了一份回味的馀地。
从传承学术、普及国学的角度说,张之洞确实可以说是极为成功的国学教育家,而《书目答问》则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国学书目。《书目答问》开启了近代以来推荐书目的潮流。在胡適之、梁任公这些文化名流的国学书目都被人们逐渐淡忘的时代,《书目答问》还能有生命力,还具备再开发的潜力。一百多年过去了,《书目答问》依然值得我们去阅读。
我的《增订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2011)在张《目》范《补》的基础上,补充近年来古籍影印本、点校本,不仅搜集港台学界出版界古籍整理的贡献,也尽量留意日韩在汉籍整理上的成绩,力求为当今的读者提供一种新的有实用价值的读本。为读书人而写,与读书人分享。
《增订书目答问补正》读后感(十):继往与开来——《书目答问汇补》、《增订书目答问补正》读后
孙先生此书可称现在最佳的《书目答问》版本,我从此书中学到了很多,实受益匪浅。原本想就自己目力所见对此书所列各种书的版本做些补充,另对孙先生书中偶有的讹误作点补正的,可到回家之前,此书也还有三分之一没读完,就先放这篇书评吧。
《书目答问》自光绪二年(1876)刊行以来,早已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书目,翻印之量不计其数,至“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跋》)其价值前辈先贤早有定论,无需饶舌。
在《书目答问》流传的一百三十多年中,博学硕闻之士多有批注、补正,或补版本之阙,或论版本善恶,或述内容得失,如是种种,皆有益于后学了解、学习《书目答问》。然批注之本,普通学人难以得见,甚且有年历久远,无迹可寻者。在这种情况下,来新夏先生积数十年之功,作《书目答问汇补》(中华书局,2011年4月版)一书,集十七家(包括来新夏、李国庆按语在内)为一编,开卷了然,甚便于学。
来先生《书目答问汇补》工作始于1963年,其自叙曰:“一九六三年春,我偶然想到,何不妨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之例,搜求各家批注,为书目答问作汇补工作,于是先后在我那部书目答问补正上过录有关资料,如将叶德辉、邵瑞彭、刘明阳、高熙曾诸家所标注的内容一字不遗地过录于我那部书的天头地脚和行间,甚至夹纸黏条。”(《书目答问汇补·叙》第4页)至二零零三年,李国庆先生又对来先生此本进行整理,历时四年,颇有补正。最终收集十七家批、校本(语),是为江人度校刻本、叶德辉批校本、佚名批校本、伦明批校本、孙人和批校本、某名氏批校本、赵祖铭撰书目答问校勘记、范希曾补正本、蒙文通按语、邵瑞彭批校本、刘明阳批校本、李笠撰三订国学用书提要、高熙曾批校本、张振佩校语、吕思勉经子解题相关精要语、韦力批校本和来新夏、李国庆按语。
此十七家或为版本大家(如叶德辉),或为藏书名家(如刘明阳、韦力),或为国学大家(如吕思勉、蒙文通),各人从自身所长出发,或订版本之误,或补版本之阙,或疏解内容、体例,于后学读书颇有助益。其中以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最为有名。自1931年由南京国学图书馆刊行以来,学人多将《答问》与《补正》视为一体,少有单刻《答问》者。范氏订正《答问》原有错误,并增补书目、版本1200余种,为《书目答问》的完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其他各家批注中,亦以对版本的补充最多。览卷可知,不再赘言。
其他,如来新夏“相台岳氏本古注五经”条按语曰:“张政烺先生谓相台本群经乃元初义兴岳氏据廖莹中世綵堂本校正重刻,与岳珂无涉。张说甚是。相台本群经当为飞九世孙岳浚,刊本当做‘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宜兴’。”此条订正前说相台本群经版本之误。如江人度于“《尚书正义》二十卷,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条下言曰:“旧题孔安国传者,非安国传而伪托安国,故加旧题以别之。下旧题宋孙奭疏同此例。今人皆知孔传之伪,然四库简目曰安国传。虽梅赜所依托,然去古未远,训诂皆有所授。又四库灵枢经提要曰譬之梅赜古文,杂采逸书,联成篇目,虽抵牾罅漏,赝托显然,而先王遗训,多赖其搜辑以有传,不可废也。二论最为持平。”江氏所言颇通达,比之但言其伪,弃之不观者,所胜良多。对于后学来说,读如是之言,亦颇能有得。
可以说,《汇补》对一百三十余年来《书目答问》的补充、完善与研究作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可谓无愧于前人的“继往之作”。
但案诸《书目答问·略例》,我们知道此书的目的的导后人读书、治学,其言曰:“凡所著录,并释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古人已无传本,今人尚未刊行者不录,旧椠旧钞偶一有之,无从够求者不录。”然《书目答问》所录,在七十几年前柳诒徵为《书目答问补正》作序之时已嫌疏漏,其言曰“第其书断自己亥,阅五十余年,宏编新著,影刻丛钞,晚出珍本,概未获载。故在光绪初足为学人之津逮者,至晚近则病其漏略矣。”及至今日,《答问》所著录之本不但难以够求,即便借阅亦已难能矣。是以如不对《答问》进行补充,其推荐、导读书目的意义将大大降低。所幸在《汇补》出版半年后,又一增补《书目答问》的力作问世,即孙文泱先生《增订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2011年11月版)一书。
孙先生此书是在“近年来学生阅读利用《书目答问》的困难越来越多”,“《书目答问》及《补正》所著录的版本越来越难以找到”(前言,第45页)的情况下,为便于读者、学人利用《书目答问》而作的。如孙先生自己所说:“我的编撰意图是,力争做一本能够基本反映到2008年为止的古籍整理现状的《书目答问》新读本,全面著录《书目答问》涉及古籍的整理状况,包括影印本、排印本、新校本、新注本等;凡影印本尽量附底本信息;大型丛书尽可能附册数等具体信息,以便一般读者参稽使用。”(前言,第45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书是《书目答问》津逮后人、导人以学精神最好的继承者。
但孙先生此书的功绩并不仅仅是给读者提供了丰富、完备的现代版本,作为历史学家,孙先生对《书目答问》的整体把握和对书籍的解题、论断,对后学选择、研读书籍亦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孙先生此书前言煌煌数万字,对《书目答问》的作者、版本、价值等方面作了详赡的论述,为我们全面了解《书目答问》提供了一个可供站立的坚实的“肩膀”。在《书目答问》评价问题上,孙先生提出将《輶轩语》、《创建尊经书院记》、《劝学篇》与《书目答问》作为一个整体,以此为中心,以宏观的眼光看张之洞的读书观,进而理解《书目答问》提出的历程和目的,最终把握其价值。可以说,孙先生对张之洞读书观及《书目答问》价值的把握是富有创见且较为近是的。
同时,孙先生在补充版本的同时,对各书的内容、价值、优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知道《书目答问》开列了两千多种书籍,但对各书的内容基本没有评价。初学面对这两千多种书,常有望书兴叹、不知从何入手之感。孙先生在补充版本信息的同时,对各书的版本优劣、内容、价值多有评骘,为我们读书、找书提供了门径。如孙先生于《尔雅义疏》条曰:“郝书用因声求义、音通义近的方法探求词源、考释名物、订正讹误,为清代《尔雅》学最详赡最重要的成果。郝氏有意以声音通训诂,但郝氏疏于声韵之学,尤其不通古音,故多误会。”此条以简明的言语说清了郝懿行《尔雅义疏》的方法、价值、优缺点。又如《资治通鉴》条在分析各版本优劣的同时,评价章钰《校宋记述略》曰:“可视为校勘学的范例及入门读物。”一句话点出了《校宋记述略》的价值。如此切要语颇多,甚便于学。
此外,孙先生还对《书目答问》附录及相关的文字进行疏释。如《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著录了五百多位清代学者,按经学家、史学家等分为十四类,相当于清代学术人表。但该表原文极简,仅有姓名、字号、邑里三项,对于初学来说,未免过于简略。孙先生“参稽众书,略为补充其生卒年、主要著述等内容,以供初学者参考。”(整理说明)颇便利用。
如果说《汇补》是对前人成果的总结、是继往之作的话,那么《增订》就是开来之作,是对《书目答问》编撰初衷最好的继承,其目的正在助后学进益、导学术发展。
当然,若要求全责备的话,此二书也难免白璧微瑕。
《汇补》所辑除韦力先生批注和来新夏、李国庆按语外,各作者多已作古,对于其得失,只能留待历史评价,我们在作汇补之时不能也不应删改。但来先生与韦力先生“时有交往”。那么,对于其批注不合适之处,作为编撰者,来先生有责任与其商榷,以求达到尽善。来新夏先生说“韦力批校本。稿本,今藏韦氏芷兰斋。韦补诸书版本,以得书先后为次。今仍其旧。”也就是说,韦力先生的校补是以自己的藏书次序为本的,那就产生许多问题了。首先,韦力先生收了一些丛书中的零本,是以将这些自己有的本子列入,而自己藏书中没有的部份就不再列入,如“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条下,韦力先生注曰“明崇祯元年毛氏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五十卷”、“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二条注曰“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四部备要本”。我们知道,汲古阁本、四部备要本都是十三经都有的,但韦力先生如此注,给不知道此二种书的人以什么感觉?是不是会使人觉得此二种版本只有这么几种呢?这样注似乎不太合适吧。既然知道有这种丛书,那么当注于“十三经注疏”条下为是吧。如欲注于各书之下,那也是注于第一本书,注明后此各书皆有此本,或者直接每本都注为是。其次,由于以自己的藏书为次,难免随意之处,难免出现一些与《答问》原文矛盾处。如同是“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条,韦力先生曰:“明崇祯永怀堂刻十三经古注本。”而《书目答问》本有“永怀堂古注十三经”条,何必注于“十三经注疏”子目下?作为编撰者,来新夏先生、李国庆先生对这部分批注的处理方式似乎有待商榷。
孙先生此书也有一些小问题。首先,孙先生在书名、作者著录上存在一些讹误。对于书名著录错误,孙先生勘误表中已多有订正。此处提一则作者著录错误。《周书集训校释》条,孙先生补曰:“黄怀信、张懋镕、田信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前言》中亦称田信东,案“田信东”当为“田旭东”之误。其次,对于某些重要的版本有阙漏,如《文选六臣注》未著录《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此书2008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本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亦可订正许多今本的错误,对于《文选》尤其是“六臣注”的研究意义重大,不应漏列。此外,孙先生对某些书的理解亦有误。如孙先生在前言中说,“其后的《尚书》一目,……只有《尚书今古文注疏》是含今古文在内的读本”,如笔者理解不误,孙先生似以《尚书今古文注疏》包含今文经、古文经在内,即当为经文五十八篇。但事实上《尚书今古文注疏》只有二十九篇,即今文二十八篇和《泰誓》一篇,并不包括伪古文经在内。
诚然,二书皆有些许瑕疵,但终归瑕不掩瑜。毫无疑问,二书必将成为《书目答问》发展历程中的经典著作。
(《书品》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