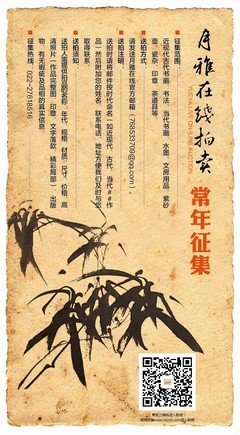关于知识分子的唯美语录
●“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淆于真知,疏于自省”
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李敖
●20 世纪非常特别,充满政治化的环境,使得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处境也非常特别,这个时代,没有退隐山林,没有袖手旁观,没有骑墙中立,就好像那句著名口号“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一样,时代逼着你不归杨则归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葛兆光《余音:学术史随笔选 1992—2015》
●补发~2016年第一天 如愿预约去了@高晓松 馆长的@杂书舘~在国学馆第一次亲手翻阅那些民国时期的旧书 小心翼翼 遥想那个思想激荡 大师云集 知识分子自由的时代 很喜欢新书馆的氛围环境 想要一天都泡在里面 再约![爱你]嗯…书是永远的情人 与书为伴 奔向诗和远方 即使天寒地冻 路遥马亡
●胖的人不怕被取笑(也没什么好怕),他们承认自身的软弱,甚至可以说是某种对体重控制的不成熟。我见过各式各样的肥胖者,不管是男是女、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市井小民或VIP,决策经理、银行家,甚至是从政者,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坐在我面前,都只能描述自己对食物的巨大软弱,就像贪吃的小孩,虽然不愿意,但无法拒绝诱惑。 ----杜坎《吃到饱减肥》
●好的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在忧心忡忡中为更好的世态人心做推动
●曾不解为何人年老了都会越发笃信宗教,知识分子或是村野农妇,无一例外。而今渐渐明白,越是接近死亡的人,有若严冬夜行,不裹一件信仰的外套,是经不住一路风霜的。他们不是迷信,而是恐惧啊。许下来生,方敢不恋今世的繁华。
●知识分子总是认为自己可以受之无愧地接受什么。 ----罗贝托·波拉尼奥《2666》
●所谓美国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第一种知识就是体育知识,产知识分子的美国名校的运动设施最好,比起普通学校来,运动的人多,项目多,接下来他们使用运动所得的专注力及纠错能力提升自己,顺便惠及社会,他们的写的书、日记中充满了自省能力——相比之下,中国的北大清华复旦差不多就是产农民的地方。 ----石康《石康微博》
●对于一个有独立精神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说,我们永远有对体制叛逆的空间,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永不属于任何体制,永远是孤魂野鬼。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
●那瞬间,百分之一秒的瞬间,你忽然理解历来知识分子的委屈是:话到咽喉,却遭砍头。 ----简嫃《随书漂浪》
●路德的势力越骂越大。再加上教权和王权的根本矛盾,终于使得这场宗教革命遍及整个欧洲,千百万神甫和知识分子卷入其中。王宫贵族们纷纷举着刀枪宣布加入其中一方,几十年后还真打了一场损失惨重的宗教战争。 不久以后,基督教分成了两大派。罗马一方被称为天主教,支持路德的则被称为新教。另外,东边的罗马帝国在此之前还搞了一个东正教。 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这就是今天基督教最主要的三大教派。新教的诞生全赖于路德的努力。 ----林欣浩《哲学家们都干了些什么?》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涅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既赞赏又疑惧的态度,正是他身上的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的反映,而这都是来自知识分子的本性的:他们既天生地有着追求群体平等的人道主义倾向,又本能地对个体精神自由、个性发展持有特殊的热情与敏感。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
●可能是由于科学特别是数学不像艺术那样具有公众性,所以也不像艺术那样吸引人。科学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少数知识分子,而艺术对公众更有吸引力。数学很难吸引公众。相对论、量子力学、人工智能和不完全性定理等等,都确确实实地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当数学家们赞美数学的美妙时,公众却感到困惑和窒息。然而计算机的使用最终把数学的美妙形象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理查德·曼凯维奇《数学的故事》
●作为一个深思熟虑的知识分子。
●罗银胜说,杨绛是一个本色的知识分子,还保留了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基因,有时候觉得某个人怪,其实老实人都是这样,很自信很自恋,只有对自己自重才能取得别人的自重。他们与世无争,实际上是这个世道太艰险太复杂了,这是对自己的保护。 ----罗银胜
●他笔下的男男女女也是典型的法国式的小人物,挤公车的上班族、爱抱怨的家庭主妇、狡黠的心理医生、做作的知识分子、商人在饮水机边上谈论哲学、宇航员在去月球的路上谈论婚外情…….
男人总是发了福,秃了顶,大鼻子,小胡子剪的整整齐齐;他们的太太顶着双下巴,发式摩登,穿着圆点花纹连衣裙。他们以法国人的特有的方式被生活抬举,也被生活羞辱,然后,全世界的布尔乔亚都从中认出自己的悲欢和哀乐——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装点门面的日常需求,小规模的胜利与中等规模的挫折之间的无尽循环。 ----陈赛《三联生活周刊》
●沉默,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 ----高希均
●知识分子精明起来,比普通人还要势利三分。 ----天真无邪《愿余生》
●我像那个看见了皇帝没有穿衣的孩子,在阳光之下,我总是会发现大树的影子;在欢乐颂的戏剧中,我总是站在幕布的另一边。人们都说温暖的时候,我感到了寒冷;人们都说光明的时候,我看到了黑暗;人们在为幸福载歌载舞的时候,我发现有人在他们脚下系绳,正要把人们集体绊倒并捆束。我看到了人的灵魂中有不可思议的丑恶;看到了知识分子为了挺直脊梁和独立思考的屈辱与努力;看到了更多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正在金钱和歌声中被权力掏空和瓦解。 ----阎连科《上天和生活选定那个感受黑暗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可是革命总是由知识份子发起的,因为他们有目标和理想,总是会干出一些激进事来想要改革。但每当革命过去之后,本来还是很高尚的革命精神也会被腐败的官僚主义吞没,而那些知识分子就会从此厌恶政治厌恶这个世界,变成愤世嫉俗的人。 ----《机动战士高达:逆袭的夏亚》
●虔诚者总是呼吁别人应该用感觉丽不是脑子去理解绝对真理。1934 年,赫斯(Rudolph He回)宣誓加入纳粹党的时候,这样对台下的听众说,不要用你们的脑子去追寻希特勒;用心的力量,你们就会全都找得到他。" 当一个群众运动开始去解释其教义,使之明白易懂时,就是这个樨众运动已经过了生气勃勃阶段的表征,现在,它的首要之务变成追求稳定。一个政权的稳定需要知识分子的效忠,而把教义条理化,是为了争取知识分子而不是促进群众的自我牺牲精神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
●1960年的“5·27”政变唤醒了左派知识分子关于进步的新土耳其即将到来的希望;但各界选举使他们的希望黯淡,一些人开始对民主化进程失去希望。 ----悉纳·阿克辛《土耳其的崛起》
●你们不要以“知识分子”自居。明明没有文化性,这么年轻就把自己当知识分子,长大以后不会有出息的。 ----《绝望先生》
●在国学馆第一次亲手翻阅那些民国时期的旧书 小心翼翼 遥想那个思想激荡 大师云集 知识分子自由的时代 很喜欢新书馆的氛围环境 想要一天都泡在里面 再约![爱你]嗯…书是永远的情人 与书为伴 奔向诗和远方 即使天寒地冻 路遥马亡 [心][/cp]
●知识分子期望整个社会就始终像学校一样,期望着在这个环境中他们照样最出色,也照样得到赏识。学校里的奖赏标准与社会上的标准如此不同,则从学校出来的拔尖者未来进入社会后通常都要经历一种心理挫折感。那些在校园等级制度中处于顶端的学生,会觉得他们不仅在校园这样的小社会中,也在更大范围社会中有资格也处于顶端,然而进入了社会,他们如果得不到如他们所期待的地位,他们就心生怨恨。因此,是学校教育制度在知识分子中间制造出了反资本主义的情绪,当然更多的是在人文知识分子中间制造出了反资本主义情绪。为什么从事跟数码打交道的知识分子没有产生同样的情绪呢?我推想是这样的:这些在数字方面有天赋的的孩子,虽也能在他感兴趣的科目中考得高分,也能得到老师的赏识,但与在人文学科方面 ----罗伯特·诺齐克《知识分子为何拒斥资本主义?》
●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干嘛 难道应该整天证明自己正确 然后对别人有智力优越感吗
一个知识分子甭管是为了出名 挣钱 还是贡献社会责任
他都是应该站在一个知识宝库的门口 高声的赞叹 吸引外面人的注意力
学习这事儿从来都是自己的事儿
谁都代替不了你 只要我引发你的兴趣
你进去找你自己的宝贝 我就是功德无量 ----罗振宇《罗辑思维》
●资中筠先生就讲到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气节,并认为这是有着许多缺点的士大夫“一个极宝贵的优良传统”。资先生这篇文章是说大专辩论赛的。她指出:“雄辩的力量在于坚定的信仰,大至哲学思想,小至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方案,总是认定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的,才值得竭尽全力为它鼓与呼;抽掉了这点‘自以为是’,等于抽掉了辩论的灵魂。”我也想跟着说一句:知识分子的力量(包括人格魅力)不在知识,而在信念。知识本身并不是力量,加上信念才是力量。这种“有知识的信念”表现于为人处世,就是“书生意气”。抽掉了这点“意气”,等于抽掉了知识分子的灵魂,而这种“意气”本是源于读书人之入世情结的。我想,这或许是入世和出世“理应不成问题”时资先生还要思考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吧? ----易中天《帝国的惆怅》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精英者,思想之精,品德之英,然后又学有所专,能沉下心来做事情,做学问。为社会之脊梁,公民之师范。国要强,先强国民。国民要强先强精英。我们常批评世风浮躁,怨青年人不成熟,文艺圈太肤浅,干部少学识等等。殊不知精英之浮,才真正是社会的危机。知识分子如何对待名利,实值深长思之。
●【教室中的中央计划制度】还要进一步补充说明一点。(未来)从事文字工作的知识分子作为正式的、官方的校园社会中的成功者,奖赏则是由作为中心权威的老师分配的。而在教室、在走廊、在学校操场上还有另一个非正式的社会群体,在这些场合,奖赏则不是由某个指导中心分配的,而是由同学们一时兴致和好恶进行分配,而恰在此处,知识分子表现得却并不怎么样。因此,毫不奇怪,那种由一个中央控制的分配机制分配物品和酬劳的制度,会令知识分子砰然心动,相反,对市场的“无政府和混乱”却是避之惟恐不及。实行中央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恰相当于由教师主导的分配与操场上和走廊内的分配之对立。 ----罗伯特·诺齐克《知识分子为何拒斥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