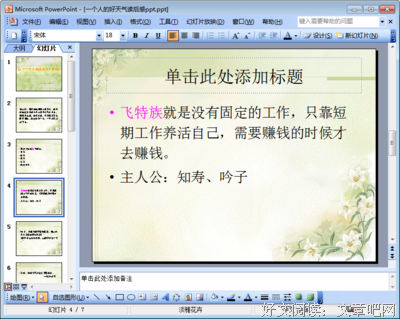《一个人办不到》读后感精选
《一个人办不到》是一本由[日] 伊坂幸太郎著作,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页数:2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离家出走的滨田青年的结局真的有点令人出乎意料,类似于推理小说。
“如果当时这么做”这句话也令人倾佩,日子一天天溜走,我们遗憾的事也越来越多,多少时候脑海中不曾蹦出“如果当时这么做就好了”。
“彗星们”指的是在列车停站7分钟内要打扫完毕的清洁人员。“我们本来就没必要吸引人注意,更没必要鬼鬼祟祟的,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是的,之前也会想:啊,这个工作又脏又累,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可是随着年龄增长,倒是越放得开了。
《一个人办不到》读后感(二):再荒唐,也要一丝不苟,也要做自己想做才对。
渐入佳境的短篇小说,每篇都会让你更加坚定自己。 前三篇应该是前段,中间三篇是后段,最后一篇是尾声。 第一篇是坂神的反转是只有坂神才可以叙述出来的,但是结局又感觉距离他的风格好远,前段的后两篇看得让人懵⭕,不过他是伊坂幸太郎啊,一定要接着看下去。后段三篇,开始温暖起来,所以说是渐入佳境,让你重回坂神风格的轨道,奇奇妙妙又温暖人心,每一篇都让你觉得世界可爱,就算像第二章《飞驰逃亡路》被蝉虫毁灭世界,像第三章《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里战争不断,我也愿意一直活在这个荒唐的世界。 尾声,把本书所有短篇串联,同事又和《杀手界疾风号》相互联系,一边告诉我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重复第四章《如果当时这么做》告诉我们的道理,一边和我们叙述温情的故事,都让我更加坚定自己,想要“一丝不苟”、不留余地的活下去。 真的是很棒的书,让人读完越想越感动啊!
《一个人办不到》读后感(三):温情依旧的伊坂幸太郎
只是薄薄的短篇集而已,每个故事也都简单至极,可是看得过程却是每每不舍翻页,每个句子都温柔至极地去抚慰我,只有在伊坂老师这里能够找回这种备受保护的感觉。写给大人的童话,让你能够回到母亲的怀抱似的,放下一切防卫的外壳,再次用孩童般的眼光去审视世界,在残酷中找到记忆中的安全感。
◆ 第1章 离家出走的滨田青年。只有第一篇还能跟推理小说扯上点关系吧(笑),而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反转或者身份的谜题,作为咨询师、作为杀手等“专业人士”的职业修养,本不该成为荒诞情节的性质,却成为最为奇异的点。“无论做什么事,只要是工作,就愉快不起来。”这也可以用来劝告每个像让爱好成为职业的人吧,最好别把爱好变成负担呢!
◆ 第2章 飞驰逃亡路。类似逃亡列车的设定,飞驰的车就像是不断前行的社会,每个乘车的人都有着各自的坚持,却也不得不随之前进,被阻碍即会被无情消灭,其他人却视若无睹;絮絮叨叨的宗教人士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世界中;永远玩着游戏机的少年也有着对世事的不满;会被欺骗贪恋美色或贪小便宜上当的人究竟是怎么样的自我催眠;遭遇中年危机的大妈认为丈夫不爱自己只是因为外星人的实验……夸张的故事中却是一个个生活中的现象的缩影。不管怎样的奇异体验,最终车辆的覆灭只会让每个弱小的乘客一起成为碎片而已。
《一个人办不到》读后感(四):姑妄言之
一个人办不到,怎么办呢?既然人是社会性动物,那不如多几个人一起来想办法看。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问题多。当然这本书不是教我们怎么解决问题,而是伊坂开脑洞,书写七个带有奇幻色彩的短篇故事合集。
《离家出走的滨田青年》故事中出现了咨询师这一职业便很有趣,开篇就卷入了一种新鲜感。随着时代变化无数的职业死去,又有无数职业诞生。正当我好奇成为见习咨询师的滨田要如何像稻垣一般开始用奇葩的回答解决顾客烦恼时,画面瞬间变成了侦探悬疑剧,傻白甜少爷滨田摇身一变成了受雇杀害滨田的杀手,至于最后追寻替人解决问题信仰的稻垣结局如何,伊坂已将故事结束了。
《飞驰逃亡路》带有一种世界末日的科幻小说既视感。蝉虫毁灭世界,人类不知不自觉中培养蝉虫。这一点很适用于现在的环境污染,过度发展之类的社会现象。完全可以拍摄成一组长镜头的电影,像《这个男人来自地球》这样仅仅通过对话,展现了语言背后蕴含的纷扰的世界漩涡。
《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首先读到的是反战,其次便是生而为人的碍难。坂本不管是慈郎分裂出来的人格还是确有其人,都不影响慈郎在无人理解的世界,焦灼不安,孤独无望。好像《人间失格》中的叶藏,在无人理解的世界中被人心折磨。周围寒风席卷,身边飞舞着落叶,遗世独立却难掩落寞。
《如果当时这么做》和广东卫视的《你会怎么做》很相似。面对需要帮助的人群,你是会伸出援助之手,还是简单的看看仅此而已。每次看到这个类型的故事总会有一点受触动,如果在相同情况下会不会伸出援助之手,不身临其境的时候想想当然是果断上前,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是如果真的到了身处其中,可能便缩手缩脚,犹豫着犹豫着就这么结束了。
《一个人办不到》书名来自这个故事。一个惊悚可怕的开头,暗恋者夜半入室图谋不轨,怎么看都应该要来一个情杀的悬疑剧了。结果画面转到了一群维护孩子童心的工作者上,引出憨豆先生式的人物松田,于是最后也如同憨豆先生模式电影中的发展,以一个搞笑的结尾皆大欢喜。松本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祸兮福所附。昨天圣诞节,坐巴士从温州到宁波,长达5个小时的路程,本该无聊至极又疲惫不堪,但也因这无聊的行程,我同坐在身边此时还是陌生人的晓晓闲聊起来打发时间,许是同为疲敝之人的亲切感,相谈甚欢加了微信,似乎也成了朋友。这段路程,配合圣诞节的氛围,阅读这个故事竟也说不出的有趣。
《彗星们》里面关于车厢内时间轴变化模式的设定很有意思,属于脑洞大开的设想,但是还是觉得他的内核是表示一个人只要愿意一直默默的努力,付出的一切总会有相关的人看到,这样的鸡汤设定。但是不管怎么说,将鸡汤变成了温暖人心的故事,那么来一起干了这碗鸡汤,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然后努力奋斗一下。
《后面的声音很吵》电影彩蛋式的故事。让所有前面几个故事中出场的人物都在同一辆列车中交汇,形成人间喜剧的效果。你某一天擦身而过的路人甲,也许就是另一个故事中闪闪发光的主人公。贺岁片《一路惊喜》也和这个故事一样,几个并行的故事相互交织,最后以各自平静人心的结尾温暖我们。
《一个人办不到》读后感(五):伊坂幸太郎作品初体验:《一个人办不到》令我有点失望
《一个人办不到》是我看的第一部伊坂幸太郎的作品。它可以吸引我,首先,因为听说作者在日本的人气比肩村上春树和东野圭吾。其次,我还听人介绍称,这本书中分七个章节,前六章是六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最后一个故事则把前面的全都串联在了一起。因此,我在看这本书之前对它可能抱有过高的期待,导致看完有点失望。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比较复杂,我觉得既有我对伊坂幸太郎及其作品的不了解,也有此版译者尤其是编辑,解读不到位的责任。
因为之前我没看过伊坂幸太郎的作品,所以不能确定这“用最后一个故事串联前面所有故事”的叙述方式,是不是他的一贯风格。但看到网上有网友评论,好像这也不是他首次尝试。关键是在我看来,最后一个故事并没有把前面所有故事的情节都进行合理化归结,只是安排了一些前面故事中的人物再登场。说难听点,这种串场对于故事情节推进造成的影响很有限,甚至是可有可无的,或者换成其他人物出场,一样可以达到相似的效果。整本书中,感觉有些故事的部分话语很有道理,值得细细回味。但个别故事读着犹如嚼蜡,令人摸不着头脑。或许是有些故事间的相互关系我还没有看透吧?
在最后一个故事“后面的声音很吵”中,那个自称“专门给人做咨询的”男人,从形象描述中可以断定他就是第一个故事“离家出走的滨田青年”中的稻垣先生。他的这次再登场就是主动跑来搭讪,所谈内容也是纯尬聊。表面上看,好像他的尬聊是从他的职业角度出发的。但实际效果就像一个卖保险的人坐上地铁就随便找个位子,然后开始向邻座的人推销保险一样。稻垣给出的买车建议反正也不涉及收咨询费的问题,如果是从其他人口中说出,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吧?不过凭良心说,第一个故事的结尾也算有意外的转折,使得这个故事读来感觉也还可以。
但从第二个故事“飞驰逃亡路”起,我的阅读就陷入了一种混乱、迷茫的状态。这个故事涉及蝉虫毁灭世界,内容本身有点不切实际,像个并不精彩的奇幻故事。在最后一个故事中,这个故事也只是以“一本杂志上的文字涂鸦”形式再现的,有种硬要返场的勉强感。紧跟着的“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的故事,更是让我感到一头雾水,好像主角精神出现了问题,总出现幻想似的。可是那个仿佛是被幻想出来的人物坂本约翰,又以年轻男子形象出现在最后一个故事中,还以占卜预言的方式印证了他最终是死于肠胃炎。这第二和第三两个故事,是我觉得整本书中最拉低评分的。它们的存在让我不明白这本书中的所有故事既然最后又是相互关联的,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或者有什么共同的主题思想?
第四个故事“如果当时这么做”中发生的劫持公交车事件,也在最后一个故事中由稻垣先生再次提及。这个故事内容涉及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后悔”问题。作者给故事中所有后悔的人创造了一次修正、弥补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治愈人心的效果。“一个人办不到”则是一个有点离奇,却又充满温暖与爱的,关于圣诞节派发礼物的故事。这版书会以此故事的标题命名,足见它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彗星们”的故事依我看在全书中更具明确的贯穿效果,把其它故事中的人物以此故事的关键参与者身份聚在一起了。而最后一个故事“后面的声音很吵”,按我的理解,只是“彗星们”的故事中,鹤田主任的外甥与其早已失联的父亲间,一次试探性的近距离接触,其他角色和情节都更像是刻意拼凑。
总体而言,伊坂幸太郎的《一个人办不到》这部作品,文笔上我觉得表现力不足。基本上只是平铺直叙地讲述着一个个故事,缺少那种打动人心、触发读者产生共鸣的扇动性描述。故事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我期待的那么合理、必然。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市川根据别人捡回来的画纸上的蜡笔画,展开联想讲述的关于鹤田主任的人生故事。如果以那段文字展开的相关故事情节评价伊坂幸太郎的作品,我还能够相信他在日本的人气应该可以比肩村上春树和东野圭吾。但综合整本书考虑,我不禁怀疑是哪里出了问题?比如:翻译效果不理想,或者是编辑对此书的理解有偏差,从而影响了我的阅读?
据我了解,伊坂幸太郎的这部《一个人办不到》,日版原名:《ジャイロスコープ》,中文即:《陀螺仪》,台湾版也是用的这个名字。且在台湾版的此书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翻开《陀螺仪》这本短篇小说集,将开启你无尽的想像力,带你徜徉在交错回旋的剧情中,偶尔为残酷生活中的小小温暖感动。最终你会发现,不论世界如何旋转,你就是自己的“轴心”,拥有一切改变的可能。
我觉得,看过此书台湾版书名和介绍的那段话后,会对整部书中的故事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感悟,关键是理清了贯穿每个故事的核心思想。比如,那个“飞驰逃亡路”的故事结尾,一车人的生命已经岌岌可危,但谁曾想仅凭一人之力就可以扭转乾坤,如何做到的?在最后一个故事中已经明确解释了,那蝉虫毁灭世界不过是“一本杂志上的文字涂鸦”。而如果把这个故事就此归结为那句贯穿全书的核心思想,也是说得通的。如此一来,也就令这个略显突兀的故事与其它故事有了关键性的连接。
此外,我发现台湾版《陀螺仪》中,还有两篇内容是《一个人办不到》中没有的。一篇是台湾作家卧斧撰写的“所有故事都绕着对‘人’的关注──关于《陀螺仪》”;另一篇是“回首十五年──访问伊坂幸太郎”。我觉得这两篇内容都会对读者理解伊坂幸太郎的这部作品起到重要的帮助作用。尤其是卧斧的那篇解读,显然是读过伊坂幸太郎大量作品后进行的综合分析,更具参考价值。
近来,我的心中产生了一个疑惑:对于一个以往并不了解的作家,究竟是从他最著名的作品开始阅读更好,还是从此人的其它随便什么作品认识他更好?如果是从最富盛名的作品开始,会不会以后再看他的其它作品越来越不如之前读过的,反而会越看越感没劲?如果是从一部并不具代表性的普通作品认识一个作家,会不会因为读到的第一部不够精彩,从而对这位作家失望,进而失去了领略其更优质作品的兴趣?而《一个人办不到》这本书,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认识伊坂幸太郎不太理想的开始。
总之,看完这本《一个人办不到》,仅就这本书而言,我对伊坂幸太郎的作品评价并不高。尽管看过卧斧的解读后,多少理解了一点此书七个故事呈现出拼凑感的原由,但仍旧无法仅凭这本书就认可伊坂幸太郎。我想也许我应该找一本他的代表名作,更深刻地感受一下他的作品特点,否则我要怀疑他的人气只是虚高了。(作者:李淑媛)
附:台湾版《陀螺仪》中的部分章节(内容来源于网络,只进行了繁体转简体)
所有故事都绕着对“人”的关注──关于《陀螺仪》
文/卧斧
初读短篇集《陀螺仪》,或许会觉得不怎么“伊坂幸太郎”。
二○○○年以《奥杜邦的祈祷》出道,伊坂幸太郎出版过许多风格多变的作品,做过许多有趣的出版实验。伊坂的作品大多包含严肃议题,但以轻松幽默的角色及节奏明快的情节包裹,是故读来非但没有沉滞感觉,反倒有种充满娱乐效果的畅快;伊坂经常使用的时空错置剪接方式、多线进行叙事技法,也常会在阅读过程当中不断制造惊奇效果。
《陀螺仪》的第一篇〈滨田青年真的吗?〉就有这种特色。
看似离家独自出现在虚构小城“虾蟇仓市”的青年滨田,莫名被外貌有点奇特的稻垣延揽为助手,不明就理地开始在铁皮屋小隔间偷录/观察稻垣进行的谘询工作──面对各式各样的谘询这个设定,本身就能发展出许多不同类型的故事(甚至有人来询问完美杀人的方法),但在伊坂层层套叠的安排之下,剧情在后半开始翻转,直至迎向出乎意外的结局。
但《陀螺仪》中的其他几篇,并非情节如此“伊坂幸太郎”的故事。
例如第二篇〈Gear〉。一片末日光景的大地上,几个坐在疾驶箱形车中的角色进行对话,主要引领情节前进的蓬田,很明显并不知道为何世界变得如此,其他角色彼此之间看起来在上车前毫无关连,箱形车分明像是在逃离什么似地横冲直撞,角色们的对话却仿佛完全不着边际。奇妙的是,随着情节开展,角色们东一段西一段的谈话内容,逐渐出现互相扣接的关键,似乎解释了文明世界毁灭的原因。
不过,事件并没有“解决”。
伊坂的小说大多不照传统推理小说的路数进行,但也大多保有推理小说的趣味,可是《陀螺仪》里的几篇小说,阅读起来似乎不见得如此:〈Gear〉是带有科幻色彩的末世寓言、〈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有点纯文学调调,〈if〉虽有惊喜,但以伊坂的功力而言,不免显得稍微平淡。
倘若把这些短篇的原初写作背景考虑进来,就会发现个中因由。
创作〈滨田青年真的吗?〉时,伊坂在写另一部长篇《瓢虫》;在后续的访问中,伊坂提到在短篇里初次处理“小孩问『为什么不能杀人?』”以及自己的答案,后来认为这个题目更适合在《瓢虫》里讨论,于是将其从短篇中抽离。事实上,〈滨田青年真的吗?〉仍碰触了这个题目,不过切入的角度没法子像长篇那么多,但埋设在情节当中,就让短篇多了一层诱发思考的转折。
又例如末世寓言〈Gear〉。
〈Gear〉的创作在〈魔王〉、〈呼吸〉两篇中篇作品之后(这两篇作品以《魔王》为名,合为一书出版),显示伊坂彼时正在思索的社会结构问题:〈Gear〉里主要角色的各自遭遇,看似独立,事实上都与“蝉虫”有关;而“蝉虫”这种虚构怪物,正是某种平时隐而未显、一旦发作便会以燎原之姿破坏一切的问题隐喻──可能是核能,可能是地球暖化,总而言之,是人类因为某些私欲的便宜行事,意料之外地提供了毁灭的燃料。在〈Gear〉之后创作的连作短篇集《末日愚者》,几乎可视为〈Gear〉中对末世人性思考的延续。
其他几篇的原初背景,也都有类似影响。
〈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发表在文艺杂志《新潮》的第一百一十期纪念号,伊坂自承受纯文学影响很深,虽然以创作娱乐小说的心态写作,但仍看得出在行文时依发表刊物的特性做了调整;〈if〉的邀稿是有页数限制的,加入这个前提,便会发现这篇作品的架构其实工整巧妙。〈一个人办不到〉和〈彗星们〉都是以“某个职业”为前提创作的作品(有一个是虚构的职业),前者原初发表在二○一四年,后者在二○一三年,都是伊坂当时作品回头聚焦在“人性”关怀上头的时间;是故,这两篇作品除了可读到伊坂在既定的框架限制当中,依旧发挥自身特色的尝试,也可读到对角色特质及人际关系的探讨。
从这个角度来看,《陀螺仪》这本“短篇集”就有了意义。
无论虚构或非虚构作品,一本“书”理论上应该是具备完整架构的成品,因此,“短篇集”常会有种尴尬──假若只是作者写的几个短篇,页数加起来可成为一本书,就凑在一起出版,难免会有架构松散、主题不一的情形;单篇阅读可能没什么问题,却很难说是一本结构完整的“书”。况且,“页数”常是纸本出版时才会出现的考量(牵涉到印刷台数、装订以及销售等等出版实务细节),但在可用电子型式发行的现今,上述“短篇集”更加没有存在的理由。
所幸,《陀螺仪》没有这个问题。
其一,伊坂在成书时,加入第七篇〈后面的声音很吵〉。这则短篇将原来在不同刊物、因不同缘由创作的短篇,巧妙收束在一起,将原本四散的短篇创作,嵌合成一本“书”;其二,是伊坂自二○○○年出道以来,不同时期的创作关注的焦点各有不同,而《陀螺仪》里不计〈后面的声音很吵〉的其他短篇,最早的〈Gear〉发表在二○○六年,最近的〈if〉则发表在《陀螺仪》出版前的二○一五年,当中的十年跨度,正好可读出伊坂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创作面向。
更要紧的是,虽然各篇主题不尽相同,但《陀螺仪》准确表现出伊坂的创作一直保有的核心概念。
《奥杜邦的祈祷》中几乎不受控的想像力、《Lush Life》里精密复杂的算计与交错回旋的故事线、《重力小丑》中对照残酷现实的轻盈温暖、《魔王》和《Golden Slumbers》里对国家机器的不信任……不管在哪部作品中使用哪种技法,构筑哪种氛围,伊坂幸太郎的作品,几乎都描述了在时光洪流中,某种宿命般的力量──与其说伊坂是个宿命论者,倒不如说伊坂相当在意群体生活里,“个人”所占的位置与重要性。
这是伊坂作品持续出现的核心概念。
“个人”或许只是“群体”中的微小齿轮,但一个齿轮的转动方向为何,其实决定了整体的运作模式。在伊坂的作品中,每个角色的举动,无论出发点为何,都会对自己不一定知道的另一个角色,甚或更巨大的局势造成影响,常常搞错该发送什么礼物的工作人员是如此,单纯受骗(或者因为好色)而答覆垃圾信件的上班族也是如此。
这个概念,同样反应在书名《陀螺仪》上。
“陀螺仪”原初是依角动量守恒特性制作而成的机械装置,后来虽然因科技发展而有不同设计,仍都有保持一定轴心、维持平衡的功能。这个装置的特质,不仅可视为伊坂核心概念的对应,也可视为《陀螺仪》中各短篇的姿态──创作成因不同、表现型式各异,但故事皆有固定的轴心,围绕着伊坂对“人”的持续关注。
虽然初读时不是这么回事,不过,《陀螺仪》其实是非常“伊坂幸太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