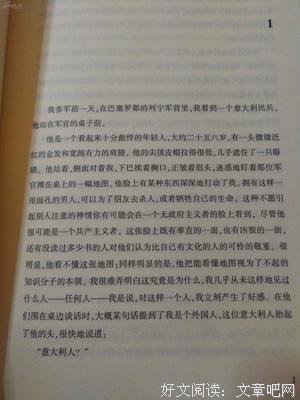《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读后感摘抄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一本由【英】乔治·奥威尔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专业作家亲自当兵(←这句怎么读着跟性感奥威尔在线发牌似的),冷静回忆往昔理想,感受翔实不忘吐槽,非常迷人。
●奥威尔终其一生都是个反对极权主义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Hatts off to George Orwell
●对了解西班牙内战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其相对浓厚的政治色彩,更准确的说非中立的观点使得本书相对来说需要辩证看待。对于我来讲,其中很多对西班牙共产党包括苏俄共产党的描述在生活中也可窥见。
●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亲身经历让他更深入了解到西班牙法西斯与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差异,从此一名自由主义战士转而倾向于社会主义。也正是这一经历,让他对二战前以及二战中欧洲各国的形势以及势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也为他日后写作中表现出的深刻洞见埋下伏笔。
●这场战争最可怕的地方在于 所有的战争宣传 所有的叫嚣 谎言和仇恨 都是来自那些没有在战斗的看客;比战争带来的伤害更可恨的是政治内部带来的迫害;理想主义驱动人投身革命 但它却无法告诉为之抛洒热血的人们在理想幻灭后该如何面对冷酷而严峻的现实的办法;我们教科书上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种浅薄的宣传手段 而只有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才知道真相;革命不会带来更好的明天 只会带来无尽的幻灭与绝望
●买了书没多久,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翻译拗口,207页最后一行西班牙后少了一个语,211页某行奥格别乌少了个奥。最后作者夫妇离开内战国家回到和平地区后的见闻,实在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叙利亚内战。
●左翼思想席卷全球的时候,多少热血青年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最后却被现实当头一棒。 为之奋斗的热血最终沦为政客手中的筹码!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读后感(一):向奥威尔致敬
1936年7月,右翼分子弗朗哥发动军事叛乱,联合反动军官试图推翻共和政府,引起西班牙内战。在这一背景下,奥威尔于当年12月怀着抗击法西斯主义的热情,奔赴加泰罗尼亚地区,加入马联工党,并奔赴前线作战。
但奥威尔很快失望的发现,这一战争包含浓厚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奥威尔在书中说的“究其本质,这是一场政治上的斗争。”他愤怒的写到“这场战争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所有的战争宣传,所有的喧嚣、谎言和仇恨,都是来自那些没有在战斗的看客。”1937年5月,奥威尔所在的马联工党遭到镇压,被共和政府定义为反动派遭到取缔,因枪伤退伍的奥威尔只得离开西班牙,在法属摩洛哥疗养时写下此书。
虽然这本书在奥威尔在世时遭到很大争议,且销量不佳,但却在之后越来越受到推崇。书中奥威尔对于其亲身经历诚恳而真挚的描写,平静中带着冷幽默,让人忘记了战争的残酷,反而更加着眼于政治斗争所反映的人性中可怕的一面。作为一本纪实文学,值得推荐。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读后感(二):豁然开朗
高中时对西班牙内战的了解少的可怜,只有弗朗哥,人民阵线,国际纵队这么几个词,似乎它就只是二战前的一小部分。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背面写着“先知在成为先知前,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下成长的奥威尔和当时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主义充满好奇与热情,认为这可以成为未来世界的改良途径,无数人涌入了西班牙自愿参加内战。奥威尔所在的马联工党民兵组织由无政府主义者构成,民兵们被分配到极其可怜的军械、接受及其可怜的军训,然后就被送往艰苦的严寒的前线。民兵中不少甚至是熊孩子,他们没有收过训练,组织纲领也并不严整,一开始让奥威尔觉得远远不如其他组织。当奥威尔休假回巴塞罗那时,却发现整个城市歌舞升平,人们只是期待战争尽早结束,装备好的部队根本就很少上前线。 西班牙内战的内部情况极其复杂,同时进行着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西班牙共产党希望得到苏俄的支持,而苏俄和西班牙共产党都不希望革命成功,民兵组织可怜的装备原因在此。 这场战斗不再是左翼认为的正义之战,事实上充斥着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党同伐异,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死在战火中,却死于自己人的迫害之后,奥威尔也是因此产生了对苏俄体质的深深怀疑,形成了反极权的政治观点。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读后感(三):有趣好读的西班牙内战史
我对西班牙内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所以百度查了一下,百度是这么介绍的:
「由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扎尼亚的共和政府军与人民阵线左翼联盟对抗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为中心的西班牙国民军和长枪党等右翼集团;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和共和政府有苏联、墨西哥和美国的援助,而佛朗哥的国民军则有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和葡萄牙的支持,因为西班牙意识形态的冲突和轴心国集团与共产势力的代理战争,使西班牙内战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前奏。」
初始奥威尔是因为《动物庄园》,心酸中透着点黑色幽默,但是这本书却向我展示了一个随时随刻都乐观幽默的奥威尔,对于党派之争以及内战发展之前没有接触过,不过奥威尔的叙述非常清晰有条理,想要了解的伙伴一定不要错过。特别是奥威尔对于前线战地的描述真的是细致又幽默,按照奥威尔的说法,前线最重要的五件事的排名依次是:“柴火、食物、香烟、蜡烛、敌人.......我们离开波塞罗山时我清点了一下子弹,发现将近三个星期以来我只朝敌人开过三枪。他们说一千发子弹才能打死一个敌人,照这样算起来得等个二十年我才能杀死第一个法西斯分子。”
其中奥威尔对于自己被法西斯军队的狙击手开枪击中喉咙,伤情危殆,但看他的描写你会有一种他只是摔了一跤的错觉,而最终奥威尔面临入狱的危险,只得逃离西班牙,辗转回到英国。
但也是这部作品让我更清晰了解为什么奥威尔会有后来的《1984》以及《动物庄园》的面世,可能亲身经历党派之争,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感受过前线士兵的经历才能写出这么深刻的作品。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读后感(四):向奥威尔致敬
奥威尔说,西班牙内战是他生命中的一段过渡期,与之前的经历和或许今后将会有的经历很不一样,他在那段时间所学到的东西是他从其他途径根本无法获取的。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尝试着揭露真相是有必要的,但我不可能纯粹只从军事角度描写这场西班牙内战,究其本质,这是一场政治上的斗争。”奥威尔以冷峻的良知和尽量客观的笔触描绘了他在西班牙内战前线及后方的所见所闻。这不止是法西斯与民主的斗争,也是一场不完整的革命,而革命之所以夭折,原因错综复杂,有国际势力的强权干预,也有兄弟阋墙的党派倾轧。
而这场奥威尔初衷为了人类共同的尊严积极投身却最终被迫离开的战争,“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所有的宣传,所有的叫嚣、谎言和仇恨,都是来自那些没有在战斗的看客”,“最让人觉得厌烦的一件事情是左翼报刊和右翼报刊一样虚伪欺诈”,党派斗争“那种感觉就像跳进一口粪坑里”。
正是亲历了西班牙内战的虚伪、复杂和斗争的残酷才成就了奥威尔日后在《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中对极权体制与人性的深刻反思。如他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所说,“自1936年后,我所进行的严肃创作的每一行话,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体制,并为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鼓与呼。”
1936年,“日本人可以在满洲为所欲为;希特勒攫取了权力,对各方面的政治反对势力大肆屠杀;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人民展开轰炸,而五十三个国家(我想是五十三个)对此缄口不言。但当弗朗哥试图政变推翻由温和左派执政的政府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西班牙人民发动起义反对弗朗哥的暴行。或许这将是局势的转折点。”
向曾经在西班牙内战中率先抗击法西斯的勇士们致敬,向曾经在加泰罗尼亚土地上浴血奋战过的、满怀纯真民主与革命理想却遭受莫须有的罪名污蔑与诽谤、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与清洗而寂寂无名于青史的英雄们致敬。
多读些文字和思考,不要迷信史书,它是献给胜利者的谎言和遮羞布。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读后感(五):奥威尔西班牙岁月的转折意义
英国著名记者、作家乔治·奥威尔以反极权主义的文学作品《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闻名于世。他曾经是一位坚定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促使他的思想发生转变,从批判外部世界的不公转而对内在体制和人性进行深刻反思的,是1936年他的西班牙之行。这一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来到加泰罗尼亚地区准备撰写新闻报道,积累写作素材。但是,由共产党以及各种左翼政党领导的共和政府与发动政变、封建保守的弗朗哥法西斯军队展开的如火如荼的战斗,以及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西班牙社会呈现出的平等自由的新气氛,立刻吸引住了充满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奥威尔,他立刻加入了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马联工党)领导的民兵组织,被派往阿拉贡前线,然后被调往韦斯卡前线。《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就是奥威尔本人亲历西班牙内战的忠实记录,也反映了他对这场战争性质的思考。
在奥威尔的笔下,当时的巴塞罗那是一个工人阶级翻身做主的城市,每一座建筑都被工人占领,到处飘扬着革命的红旗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旗帜;所有的商店、咖啡厅,甚至擦鞋匠都集体化了,理发店里张贴着理发师不再是奴隶的告示;人人平等相待,不再说“阁下”、“先生”、“您”等礼节性的词语,而已“同志”、“你”相称;街上的彩色海报,甚至有规劝妓女从良的内容。这一切,都让来自刚刚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贫富悬殊的英国的奥威尔感到新鲜。他的左翼社会主义倾向自然地让他对这些新气象产生好感。不过,职业记者的敏感和作家的敏锐,也让他察觉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战争造成整座城市破败萧条,物资短缺,牛奶买不到,肉质品很少,平民买面包要排很长的队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兵们的食物浪费却很严重,每顿饭都会倒出满满的一篮子面包。更让他不解的是,工人们几乎捣毁了每一座教堂,整个马德里只有一两处教堂才能举行宗教仪式。革命让一个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它所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也让奥威尔感到触目惊心。
尽管如此,奥威尔仍然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马联工党的民兵组织,奔向前线,因为,他的理想是帮助西班牙人民抗击法西斯,捍卫人类共同的尊严。然而,在前线的亲身遭遇与他的想象却有天壤之别。首先,武器装备极度匮乏和陈旧,他所在战区的全部炮兵火力只有四门迫击炮,每门迫击炮仅配备十五发炮弹;每五十人才配备一挺老式机枪,发给奥威尔的居然是一支产于1896年、已有40年历史的德制毛瑟枪,锈迹斑斑,老不堪用;官兵们没有钢盔,没有刺刀,也几乎没有左轮或手枪,每五到十人才有一枚手榴弹;甚至连军用地图都没有。而对阵的弗朗哥军队的军火质量也好不到那里去,发射过来的150毫米炮弹只能炸开浅浅的土坑,而且有四分之一是哑弹。双方的势均力敌与缺乏攻击力,导致谁也不敢主动发起进攻,加之战争背后的党派内斗,使战线基本处于一种相对平静与僵持的状态,除非偶尔的冷枪或己方的误伤才导致个别的伤亡。自然,奥威尔也经历了在火线上运输弹药时遭到炮击、同伴被炸伤而造成的极度惊吓,在休假后重回前线被敌人子弹击穿喉咙、九死一生这样的历险,但更多的时候是呆在肮脏污秽、臭气熏天的战壕里无所事事,驻守阵地的八十个晚上只脱过三次衣服,漫漫长夜还得忍受蚊子的叮咬和老鼠的骚扰,饱经风霜与失眠之苦。因此,奥威尔将自己轮休前在战壕里驻守的115天称为“生命中最无聊的时光”,为自己没有履行抗击法西斯主义的战斗责职而愧疚。
促使奥威尔的思想真正开始转变的,是他在前线驻守了115天后回到巴塞罗那轮休的这段时光。他发现,巴塞罗那与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完全变了,工人纠察队被勒令解散,战前的警察队伍又重回街头执法,革命气氛荡然无存。在革命的前几个月,被吓坏的资产阶级中不少人刻意穿上工装,以求保全性命。现在,一切重归战前的歌舞升平,时髦的酒店与餐馆里坐满了有钱人,豪奢地消费着昂贵的饭菜,而工人阶级却不得不面对飞涨的物价,物资奇缺,食不果腹,工资却原地踏步。最关键的是,巴塞罗那的政治气氛变得日益肃杀和恐怖。受苏联控制的西班牙共产党与马联工党的互相攻击变得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恶毒。街头爆发了巷战,进攻者并非弗朗哥军队,而是直接受苏联操纵和指挥的警察,奥威尔作为马联工党的民兵也参加了巷战,但马联工党毕竟势单力孤,其据点和建筑最后全部失守。奥威尔亲眼看到苏联秘密警察“格别乌”的人员在饭店里煽动难民,振振有词地解释整件事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不由辛辣地讽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以说谎为职业的人——如果不将记者计算在内的话。”受苏联控制的势力公开扬言战事结束后就要“清算”无政府主义,果然说到做到。巴塞罗那巷战结束后,成百上千的马联工党成员被抓入狱,而逮捕他们的理由是 “托派分子”、“法西斯恐怖团伙”等莫须有的罪名,巴塞罗那巷战被指控为由马联工党幕后指挥的“第五纵队”式的法西斯暴动。马联工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彻底取缔;其领导人尼恩因为担任过托洛茨基的秘书,尽管双方已经分道扬镳,还是被逮捕入狱,最后暴尸街头。奥威尔已经看清楚了,“斯大林派”大权在握,因此“托派分子”面临灭顶之灾。最不能让他忍受的是,他的同胞、英国独立工党的党员、优秀的格拉斯哥大学生斯迈尔利满怀理想来参加西班牙内战,却以所谓的“携带武器”罪被捕入狱,不明不白地死亡;奥威尔的上级乔治·克普抛弃了家庭、工作和祖国来到西班牙抗击法西斯主义,他帮助西班牙共和政府生产了急需的军火弹药,如果回到祖国会被宣判有期徒刑,在西班牙前线他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威望很高的军官,挽救过许多人的生命,但也被抓入狱。奥威尔多次去监狱看望他,费尽周折帮他弄来无罪的证明,但依然无济于事,直到奥威尔离开西班牙后他依然生死未卜。这一切都让奥威尔的内心无法平静,“生气只是在浪费时间,但这种歹毒而愚蠢的事情确实让你按捺不住脾气”。就连他本人,虽然因受伤而被开具证明可以退役,但因为是马联工党民兵组织的成员,住地就遭到粗暴的搜查,随时面临被捕和被迫害的危险,因而不敢回酒店,只能躲到教堂的废墟过夜,最终被迫逃离西班牙才转危为安。
显然,深受植根于英国社会的法治、人权理念影响的奥威尔,与西班牙内战的街头上暴徒拿着高音喇叭大声攻击政治对手、随意逮捕民众的做派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 而党同伐异、尔虞我诈、宣传抹黑、罗织罪名、诬陷对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党派内斗更是让奥威尔感到困惑乃至厌恶,他终于醒悟,党派斗争“那种感觉就像跳进一口粪坑里。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尝试着揭露真相是有必要的”。这一切,都源自斯大林大清洗时的无限上纲、无情斗争、残酷打击、消灭肉体的极权与暴力政治手段,从而让奥威尔感到深深的恐惧和警惕,进而开始反思,正如他自己所言:“自1936年后,我所进行的严肃创作的每一行话,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体制,并为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鼓与呼。”
虽然饱经黑暗,但奥威尔依然深信人性本善,因为在西班牙内战的前线与后方他亲身经历的几件事,让他加深了这一信念。那位被俘的法西斯士兵在农民家里惶恐而狼吞虎咽地吃饭时,周围和善地看着他并给予安慰的民兵;那位与警察局长大吵一架、帮助奥威尔拿到克普无罪证明、然后又与他主动握手的共和政府国防部官员;那位在酒店里慈祥地用红酒招待他、感叹战争毁掉了很多好东西、并温和地问他喜不喜欢西班牙、是否会回来的侍者,不仅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本阳刚之气十足的纪实作品中的温情插笔,更是严酷黑暗的西班牙内战岁月的人性闪光,奥威尔由此而感叹:“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你从西班牙人身上看到了仁义的闪耀。”
这也正是上世纪80年代,弗朗哥还政于卡洛斯国王后,西班牙的各个政治派别能够达成妥协、顺利实现民主转型、国家由此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而避免了再度掉入内战与流血陷阱的民意与心理基础。
(此系本人原创作品,未经授权或许可,不得转载,否则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