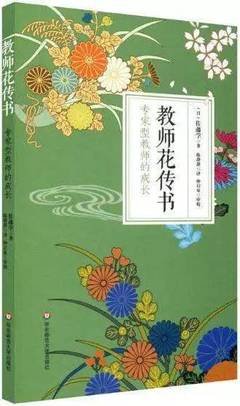近代能乐集经典读后感有感
《近代能乐集》是一本由[日] 三岛由纪夫著作,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能剧的现代演绎,与原作意象上有互文也有冲突,台词瑰丽到了中二的地步,后记题解写得很好,要是有机会在舞台上看到就好了。 「绫鼓」(所谓的恋爱,是以自己的丑陋之镜,去映照对方)、「卒塔婆小町」(纯粹的美,百年孤独)、「葵上」(氛围最恐怖的一篇)、「道成寺」(梵钟与蛇妖意象)。
●对拟剧的拟剧。三岛在能乐中留下的「破绽」是语言、情动中显而易见的某种不纯的粗俗恶意,这来自他嘲笑的战后均质化社会的缩略图,能乐本身的古意化作幕布后的地理学。万千破绽凹凸的最终延续向结尾处的“开始”,绫鼓、班女最为明显,真正的「能」开始了,人们总会迎来一场漏了最后一声鼓的永夜、一个过于残忍的春天。熊野、道成寺、弱法师则是另一种借用事件或意象实验使整个世界消长的变形剧。新译本比老版好太多了,译者匿去小言幸兵卫之类的词,也很适合排演。
●三島的作品,除了《金閣寺》,最喜歡的就是《近代能樂集》了,有了新譯本,可開心了!
●化腐朽为神奇之作,余味无穷,确如三岛本人所言“能剧总是从剧情终结的地方开始”!
●卒塔婆小町确实漂亮,台词就足够有张力,美感是很还原古典能剧精髓的。个人还非常喜欢班女,文学性高,且表达了三岛对爱情一个基本认识――“爱情应当且必须以它自身为目标”,这个想法贯穿了三岛笔下所有的爱情故事,也让我深有同感。总体来说整本剧集水平都很高,那天好好写一个长评吧。
●每一篇都真的太好了。每一个故事都那么美,都那么不幸,让人心里难受。
●三岛由纪夫抽取传统的能剧,把黄粱一梦、小野小町、源氏物语等故事放在现代思想下进行了重新的演绎。在《邯郸》中,唯有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次郎,可以抵抗枕中心想事成的世界,一梦醒来不觉人生虚无,扎扎实实的活在现实里。三岛由纪夫用诡辩跨越了世人普遍追求的意义,将虚无与务实、痴情与绝情、迟暮与青春等杂糅在一起,让原本对立的人事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和解。
●我跟三岛是真没缘分,看一本一本无感。每一本都写得那么“端”。
《近代能乐集》读后感(一):班女
《班女》讲到一个等待心上人归来的疯女人,但是重逢的那一刻,她却不认识他了。
“我只知道疯狂的花子。那样的她充满了美丽。她在保有理智的时候所做的平庸的梦,现在已经被彻底精炼出来,变成了你这种人完全无法企及的、高贵的、不可思议的梦,变成了坚硬的宝石。”
一个人,亦或者不能见面的两个恋人是难以控制爱情的,爱情是缥缈的、最纯真的东西。爱情诞生于现实,但它总不甘于现实,它总是在不断超越它本身,最终变成心中的信念,任何东西无法染指玷污的神圣,它超越了爱情本身。
不管她是不是疯了,在这个时候,爱情最起码已经从他们两个之间抽离出来,变成了坚硬的独立的存在,像宝石一样。而那个存在在现实之中的、并不完美的“爱人”,再也不配得到她的爱了。
在现实中,我们的爱情走向了哪里?又或者我们希望或者能够接受它走向哪里?我们能否接受,沉到现实中的爱情?它对于任何一个追求美好的人来说哪一种更有力量?
《近代能乐集》读后感(二):篇二《绫鼓》
大楼左边房间的岩吉和加代子,代表真实;大楼右边的服装店女老板和夫人的朋友们,代表虚伪和市侩。七十岁的岩吉,清洁工,炽热地爱恋高贵优雅的夫人,夫人的朋友们叽叽喳喳地嘲笑老朽勃发的爱情。他们嘲笑的不只是他的贫穷,年迈,没有自知之明,而且嫌恶鄙夷他的真诚。被欺负并且化身为欺负人者的人们,对于坚信着什么的人,大概是嫉妒及厌恶的。
“那老头子自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在受苦,这种自我陶醉实在令人厌恶。我们也一样在受苦,只不过没有说出口罢了。”“我们也一样啊。生活在这么坏的时代里,为了欺骗自己,要重复多少痛苦,如果这些能用眼睛看到,我还真想让他看看。”“大体来说,我们必须唾弃像那个老头子一样的家伙——那种家伙竟然相信真实的感情,我们不能饶恕那样的家伙。”
直到岩吉跳楼之后,夫人才说了第一句话。在此之前,她对朋友们的议论,以及扔一面敲不响的鼓过去的主意,始终保持缄默。缄默,可以说是反对,也可以说是默许。
信与不信如泾渭之分,爱与不爱也是。岩吉的爱有多纯净、一门心思、偏执,夫人的美就有多骄傲、无辜、狡猾。岩吉用死也得不到夫人的垂青,当然,死换不来爱。夫人也曾被爱的人辜负,所以她有足够的理由将追求者放置一旁。所有被爱的感情,都化为不断的养料,供奉夫人的不信、不爱这些男人。她的茫然懵懂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她说,你再敲一下我就能听到了,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只不过,大概没有什么代价大过死亡。生命和爱,是旗鼓相当的敌手。
《近代能乐集》读后感(三):“所有幻影必须堂堂正正地出现”
书名为《近代能乐集》,“能乐”是日本的传统戏剧,“近代”特指战后的现代日本,三岛由纪夫对日本的传统故事进行的改编,以此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在这个独特的时空环境中,“所有人都一个不剩地落入了地狱”。题解者指出:中世纪的能剧作者们追求着“彼岸的拯救”,但在“战后的现代日本”,却不存在什么“彼岸的拯救”。 《邯郸》:邯郸一梦之后便无法再接受现实生活的平庸,人们纷纷流浪,现实世界死去,花草枯萎。次郎一开始就认清生活虚妄的本质,发牢骚似的声称“世界是虚幻的”,梦无法令他做出改变,现实世界重新鲜活,花草盛开。存在主义的味道。 醒来后的次郎表示要“留下来”,留在菊为他保留的十年前的房间里,这象征日本战前的生活——战后人们失而不再得的乐园。 《绫鼓》:七十岁的老者爱上了年轻貌美的华子,因华子的捉弄——让他敲响绫子做的鼓——而死去,他爱上的是心中的幻影。变成鬼魂后,鼓被敲响一百次,老者消失,华子佯装听不到,妄图听到鼓响一百零一次,她期待的,乃是“恋爱所承诺的、超出整个世界之上的事物”。 《卒塔婆小町》:引作者自解如下: 小町是“超越了生的生”,是“形而上学的生”的象征。诗人是“肉感的生”,是“与现实一同流转的生”的象征。小町身上的悲剧,乃是她“绝不会失败”;而在诗人身上,则有着浪漫主义式的“向悲剧而去的意志”。这种误解、好奇与侮慢混合成了两人互相之间的憧憬,他们的接触就基于这种憧憬展开。 诗人对路灯下、长椅上情侣的描述太美了,见图。 《班女》:花子的爱来源于吉雄,却又超越吉雄,在长久地等待中被提炼、升华,变成坚硬的宝石,肉体凡胎的吉雄再也配不上花子的爱情。“爱情的对象是一种自杂质,它只会降低爱的纯度——爱情应当而且必须是以它自身为目标。”
《近代能乐集》读后感(四):戏剧写作与三岛的美学核心
编按:
虽然有个高冷的书名,但《能乐集》并不是阅读门槛较高的“能剧写作”。就像是三岛自己描述的,这个集子是对古代故事的现代讲述。
举一个例子,第一篇剧作《邯郸》取材于中国邯郸之枕——“黄粱一梦”的故事。这个故事流传到日本以后,在经典能剧中这样演绎:主角卢生在梦里身登帝位,体会到现世的虚幻,醒来后最终达到了佛教意义上的开悟、解脱与拯救。但当这个“古代故事”落在了三岛由纪夫的手中,他显然给出了一个非常“三岛”的现代性改编:主角次郎从一开始就明白世界虚幻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梦里依序碰到的的代表女人、金钱与权势的精灵,无非是做了一套又一套的无用功。面对一个始终满腹牢骚、“虽死犹生”的灵魂,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大彻大悟”。
对很多评议者来说,这一层强烈的虚无主义正是战后日本精神状态的写照。“中世纪的能剧作者们追求着‘彼岸的拯救’,但在‘战后的现代日本’,却不存在什么‘彼岸的拯救’。”
在这八篇剧作中,我们还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一些三岛由纪夫经典的美学营造。老与少的比照,男与女的对位,对充满青春光彩的肉体的不加掩饰的赞美,对死亡与毁灭夹杂着恐惧的向往,以及面对往昔某个绝美回忆的若有所失的追寻……正如三岛自己所讲,“能剧一直是我的文学作品中的一股暗流。”许多他在小说创作中信手拈来的经典意向,都可以在这里听到回响。
《近代能乐集》中的《卒塔婆小町》《葵上》《班女》《弱法师》等名篇被数次搬上荧屏以及话剧舞台,影响深远。其中,左1图中2013版《葵上》的主角是中谷美纪。下文是翻译者玖羽老师撰写的解题总序,这一部分收录在书中的末尾部分。
解题总序
文/玖羽
三岛由纪夫早在少年时代就对日本古典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3岁的时候,他的外祖母带他观看了能剧,祖母带他观看了歌舞伎;在剧场中体验到的“言语的优雅”使三岛大为倾心,从此,对这两种戏剧的热爱贯穿了他的一生。恰如三岛本人所述:“能剧一直是我的文学作品中的一股暗流。”能剧的典故、场景,特别是来自能剧的美学观念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不仅如此,三岛还以能剧为蓝本,撰写了一系列以现代日本为舞台的戏剧。从1950到1955年发表的五部戏剧(《邯郸》《绫鼓》《卒塔婆小町》《葵上》《班女》)于1956年以《近代能乐集》之名结集出版,在这一版本的后记中,三岛写道:“这几年来,我养成了一有空闲就浏览《谣曲全集》的习惯,但是,适合现代化改编的只有这五篇。我不得不认为,这五篇已经把所有的种子都耗尽了。”然而,从1957年到1962年,他又发表了四部同类戏剧(《道成寺》《熊野》《弱法师》《源氏供养》)。1968年,除《源氏供养》外的八部戏剧以文库版的形式出版,就是现在的这本《近代能乐集》。
在日本,对能剧进行现代化改编的尝试可以追溯到郡虎彦(1890—1924),他的《道成寺》等戏剧的确对三岛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不过,郡虎彦仅仅是用现代戏剧的形式重现能剧的情节,他的改编与原作的精神已经没有什么共通之处。另一方面,从古至今,日本能剧界一直在根据当代题材创作新的能剧,但正如唐纳德·基恩所评价的:“这种能剧只不过是世阿弥式的词句和口吻的大杂烩,不消说,三岛所作的,绝不是这种拟古剧。”
作为这部戏剧集标题的“近代”,在日语中的含义其实相当于汉语的“现代”。更加确切地说,这里的“近代”特指“战后的现代日本”。这些戏剧乃是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创作的:假如能剧的背景换成三岛生活的“现代”,它们的故事会怎样发展?用三岛的话来讲:“乍一看去,诠释与原作截然相反,但这是由于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情感截然相反的缘故。如果谣曲的作者生活在现代,大概也会采用这种方式来展开主题。”
那么,对三岛来说,他在生活中感到的是怎样一种感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从他的改编中可以窥见一斑:举例而言,佛教意义上的救赎和解脱,是传统能剧中的关键要素之一,由于中世日本极重佛教,很多能剧都具有强烈的佛教色彩(甚至有些根本就是僧侣撰写的传教剧)。然而,《近代能乐集》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重大改动:如果原剧的结尾涉及佛教意义上的拯救,则一律删除或颠覆。中世纪的能剧作者们追求着“彼岸的拯救”,但在“战后的现代日本”,却不存在什么“彼岸的拯救”。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三岛会尽可能地保留能剧原作的框架,在意境上呼应原作,但这些作品的核心概念完全出自三岛自身。《近代能乐集》中表达的情感,正是三岛在他所处的世界里感受到的情感“就算说所有人都一个不剩地落入了地狱,也不为过这就是被称为‘现代’的这个时代。”
从广义上说,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作者的内心世界的产物。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作品会比其他作品更多地反映出作者的美学和哲学、人生观和世界观,通过它们,读者可以更加便捷、深入地探索作者的心灵。《近代能乐集》中的戏剧就属于这样的作品。
青年时代的三岛由纪夫(1925-1970)《近代能乐集》读后感(五):三岛由纪夫笔下的恋情世界
本文是自己对三岛文学世界中“恋爱”这一主题的阶段性总结。自己既不是文学生也不是艺术生,没有任何专业知识,只能用自己浅薄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受,如有错误和不认同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恋”与“爱”不同。“爱”似乎是一种较为宽泛的情感,它的模式可能是A对B或A对B,C,D...但“恋”则专一的多,它基本是一对一的,带有私人性、专一性,纯度极高且不可遭外力入侵的。这个世界上“爱”成功很容易,但“恋”想要成功则极难。
我认为三岛的文学、戏剧当中所有的爱情故事,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恋情,或许在三岛的世界观中恋与爱本就应该是同样的东西吧。
本剧集中的《绫鼓》、《卒塔婆》、《葵上》、《班女》、《道成寺》,小说中的《潮骚》、《春雪》莫不是如此,为什么三岛如此在意“恋”这个主题呢?
引:“日本的男性文化几乎全假外求,另外也有不知外来文化为何物的日本男性,就像更早的《古事记》时代中的男人们,以原始得纯朴方式,单纯的凭借官能过活,对感情全无概念。在男性发现感情之前,是女性先发掘了它,而后男性宁可自囚于外来文化所引进的各种概念之中,与发掘自己的情感相比,男性更愿意从理论概念中汲取乐趣。男性益加背离情感之后,便更进一步企图用各种哲学与宗教的概念去扼杀情感”。――三岛由纪夫著《文章读本》中“男性文字与女性文字”一节。
这番话是三岛长期阅读古典日本文学中总结出来的,可以看出三岛对自己民族做过非常细致的思考。在日本历史上真正能够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的时代只在平安王朝这短暂的一瞬间,也是和族情感高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有趣的是这个时期的日本作家几乎都是女性作家,日本女性率先把握了情感世界,而日本男性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在女性面前不自卑起来,便开始拼命压制女性,用诸如武士道、男子气概等等,但是这样做的后果便是日本男性对女性的认识与审美长时间停留在官能享乐上,与之相应日本的男性文化越发冷血。这点上纵观日本民族在平安王朝之后直至今天日本社会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就可看出来,日本女性变得越来越卑微,而日本男性则越来越冷血无情。
体现在日本男性作家身上便是所书写的文学作品中所有感情的描写绝大多数都是女性人物,这个隐秘的传统直到日本战后都鲜明的存在,这绝非偶然,而是日本男性从来都不知道男性的情感世界是什么,即便书写男性充其量也就是会移动的战士,轮着武士刀砍人的主,对女性则基本个个陶醉于女性的肉体享受之中。
那么是否日本男性对女性一直没有精神上的爱呢?答案是否定的。
引:“就日本而言,从极端意义上说,所谓对于国家的爱其实是没有的,对于女性的精神之爱也是没有的。在日本人的原本的精神构造里,厄洛斯(始于肉欲,渐次脱离肉欲将情爱推向理想深渊)与阿加比(纯爱、圣爱)是一直线牵搭在一起的。如果对女性或对年轻男子的爱,倔强于纯一无暇的情愫之时,其精神质素与臣民对于主君的忠诚没有什么差别。像这种厄洛斯与阿加比全无隔离的爱情观念,在幕府时代后期又称作“恋阙之情”,是以对天皇崇拜的情愫为基础的。...中略...我相信日本人是从官能的诚实本意出发,向着舍命也必成就的理想精神,一直线,隔无可隔的递接着的。”――三岛由纪夫著《叶隐入门》
这里三岛提出一个认识,天皇始于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在人间的确证,其意义不同与我国的皇帝。天皇更接近一种“人格神”,连同“万世一系”的神话共同支配着和族的精神世界与生活模式,这种未曾斩断的神话无论真假都实实在在的影响了日本人的心灵,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是超然的存在,代表美、崇高、正确、正义等一切高于现世的价值,万世一系不可撼动,日本人所有精神上的爱通通以此为基础发展而来,日本人的精神之爱是一定以死亡为结局至死不渝的向理想之境奔跑的。
可以说这样的模式是标准的政教分离模式。这个模式直到明治维新的大政奉还之后发生了改变,天皇集精神标志与政权于一身,在明治时代确实最大限度发挥了效力,使日本迅速走上列强行列,殊不知这样的做法给整个日本文明埋下了祸根。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天皇在二战中以“民族之父”的身份对和族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都压榨到达极限,以“神”的名义发动战争,并犯下滔天罪行,之后又在战后推卸责任,自己降格为人,导致神道教中“人格神”的形象与意义崩塌,致使和族的内在价值与精神世界的纽带发生断裂,心灵中存在无法得到救赎得罪恶,再也无法获得重塑灵魂的爱。
在两颗原子弹爆炸的废墟之上只能诞生一群天生的享乐主义者;一群内心空洞的自甘堕落之人;一群只能用刺激缓解内心的痛苦的瘾君子;一群逐渐落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渺小“蚂蚁。 这样的人既不会思考过去,也不会珍惜现在,更不会畅想未来。他们内心没有爱与希望,只知道及时行乐,鸵鸟政策,混一天算一天,在堕落之中只能用更深的堕落麻痹自己,最终彻底归于平庸与虚无。
或许三岛是认识到这点吧(不管三岛所想是否正确),三岛才拼命构建“文化天皇观”,“否定现世的天皇,肯定应然的天皇”;才悲愤的说出“天皇怎能降格为人”,最终在切腹之前明知无望仍要喊出那句“天皇陛下万岁”。“天皇是神,天皇必须是神”,这话与《金阁寺》中的“金阁为什么是美的,因为你必须美”不是如出一辙么?三岛在战败之时学会了否定现世,学会认可自己的内心。
扭转天皇观的本质是要扭转日本人价值取向,将从外界获得价值与认可转回自我的心灵之中,重新接纳自己,相信自我的力量,相信自己心中的爱,而这其实就是自爱。
《绫鼓》中的岩吉与华子、《卒塔婆小町》中的诗人与小野小町、《班女》中的花子无不是如此。虽然故事的起因、发展、高潮、结局不同,但其中的内核是高度一致的――“爱情应当且必须以它自身为目标”,自爱者才用有爱与被爱的资格,凡事从他人吸取爱的人,其爱情只会变得越发易碎、卑微。“爱”理应是催人向上的力量,而绝不是向下,同理,天皇理应不是坐在皇位上发号政令的人,而应该是心中理想的“人格神”。我认为这份感悟在三岛写《春雪》中“骷髅与水”这则故事里以暗喻的方式展示的淋漓尽致,其最终的结论“心生则万法皆生,心灭则与枯骨无异”更是点名这个故事在《春雪》中的用意。
作为三岛的读者我一直想这是三岛在战前就明白的,还是战后才出现的想法?根据三岛逃过兵役来看他或许是前者吧…只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如果是前者,那三岛毫无疑问是天才;如果是后者,那证明三岛是真正对民族文化做出深入思考的伟大作家。
在三岛的文学世界中,恋爱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爱者与被爱者,而是自爱者与自爱者的关系,恋爱变成了寻找对自我所爱相一致的人,在心灵的追求上相通的人。这样的恋爱无疑是艰难且少见的,但正如我在文章开篇处所说的那样,或许这才是三岛心中的真正爱情。
引:“如今的爱情失去了品格要素,深藏于心的沉挚愈少愈好之际,我们便失去了情爱更为广大的美丽,失去了逾越阻隔的勇气,失去了变革那些旧社会道德的革命般的激情,失去了情爱可以涵盖我们普遍人生的意义。且同时,我们也失去了获得真爱的狂喜,失去了痛失真爱的忧伤。人类感情中那遥不可测的最深最广处,我们亦再无从得知。我们不再描摹想象并礼赞我们情爱的对象,而我们情爱的对象便也无线低沉下去,低到尘埃里。”――《叶隐入门》 三岛由纪夫 著
在人生的最终作《丰饶之海》首卷《春雪》中,三岛更是以一幅全景画的方式展现了自己对于恋情的全部理解,并由主人翁松枝清显内心对聪子的恋与美的认识逐渐上升至天皇神格化的爱,最终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命运式的爱,一次不可能的爱,一次禁忌之恋。这份爱所确立的东西不是只有悲剧后的哀伤,而是《丰饶之海》全四卷情感价值的基石,是一切美的种子,是奇迹与神话。这份神话被一个名为本多繁邦的男人看在眼中由此开启他的人生故事,当然这是后话了。
引:“尽管他们的爱是他们的死因,但是,用不了多久,人们会想起他们死的命运,仿佛是他们的爱的原因,即使这样想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正是这种命运式的爱,才成为人类社会、国家和民族相互爱的母胎,成为相互爱的象征,为了意识到这种博爱的太空,无论如何也需要殉情者那犹如美丽泉水般的爱。”――《残酷之美》 三岛由纪夫 著 中 殉情论 一节
综上所述,是自己对三岛文学城堡中“恋”这一主题的的阶段性总结与认识。这一主题的在我看来其地位是觉绝不亚于、甚至高于三岛文学中另一大主题“武”的思想的。后期三岛对“恋”这一主题的得探索更加深入,引入惠心僧都的《往生要集》并融入大成佛法中的“轮回转世”之说补完日本神道教的“一灵四魂”之说。同时,不能忽视西方文学、戏剧、哲学是三岛的影响,这些具体的影响现在自己尚未有能力说清,只能秉持着对三岛文章的热爱,继续阅读下去,思考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