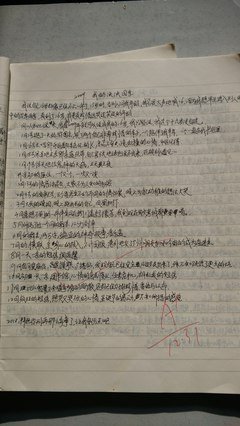《谁更了解中国》读后感1000字
《谁更了解中国》是一本由李翔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9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谁更了解中国》精选点评:
●谁更了解中国 ?
●断断续续终于把这本书读完。李翔从经济学家、知识分子、作家、企业家和大时代的小人物五个角度切入,几乎忠实地还原了对这几个群体的采访,集合成册,反映不同个体对大现状的认知。觉得更像是叙述性的直描,没有掺杂太多作者深入的思考在里面,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这本书不太吸引我的地方。最喜欢第一部分观念的历险,很多大家的言谈深刻简洁而直击要害,而最后一部分,作者就好像从高高在给予盛誉的精英阶层一下子回到地面。我想这才是中国一个大群体像最真实的浓缩,不知道为什么读到这时觉得很心酸。或许,最能激起普通读者感情的都是这些最平凡卑微的存在。
●作者稍显讨厌, 第一张经济学家的 感觉很好
●这也太实录了吧,批判性呢?好处倒是让我一个几乎不知道门在哪的人马克了大卫·哈伯斯塔姆、西奥多·怀特和威廉·曼彻斯特。
●小鱼同学教导我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书,这本书也就一般吧
●序言写得超级好!!榜样!!
●大一看的
●里面出现了总编辑,方老师的说~
●翻开这本书的第一天,是世界经济大潮里的中国,波澜壮阔,又波诡云谲。第二天是公知和作家的天马行空。第三天是商业大鳄的谨慎,“从商是我没得选择的选择”。最后是小人物们的无奈和艰辛。这个时代,注定是造就故事,淘尽英雄的时代。。
●一个应该是我的同龄人的深刻文字,让我感到汗颜。同样是而立的年纪,我是否可以感叹,自己仍然没有明确未来的人生?
《谁更了解中国》读后感(一):读还是不读
在这个信仰与物质观念模糊时代里,需要一些了解中国文化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来宣扬中国的优秀文化,并加以捍卫,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应给予新一代思想者以提醒,以便让他们时刻觉察自己,成为有一个时代的腐蚀者,更重要的是时刻激扬爱国主义精神,记住根本
《谁更了解中国》读后感(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本书说得很不错,我强力推荐大家去读读,不要一天到晚都到处嚷嚷,做一个愤青!
www.kanjd8.com青年励志网,大家可以去看看!
《谁更了解中国》读后感(三):中国的脸庞——评《谁更了解中国》
当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不断的问自己:你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放下书,闭上眼,浮现的是林立的高楼,马路上汹涌的车流,写字楼里的白领,工地上的农民工,摆摊的老人,放学的孩子,年轻或者苍老的脸庞,他们或许疲惫,或许兴高采烈,或许麻木。。。
但是这些不过是表层的影像,那些脸庞背后隐藏的真实是什么呢?这却是我的阅历和经历还无法企及的深度。
上面的疑问,也正是李翔的疑问。《谁更了解中国》里收录了他多年记者生涯的部分采访文章。当然,这些文章都是他甄选过的。从张五常开始,以平凡小人物结束,有经济学家,作家 独立知识分子,商人和小人物。这样的选择似乎就是在通过这些不同人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所经历的不同时期,不同的思维角度,竭力去呈现一个中国的样子——虽然这样庞大的命题,是难以完成的——但是李翔为我们至少提供了一个入口,去了解中国的入口。
选择从经济学家开始,先触及的是中国的经济制度,逐渐抽丝剥茧地延伸。张五常、陈志武和谢国忠等人的访谈,围绕着“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展现一个中国经济的宏观轮廓。而之后的商人访谈,选择了王石,李书福和郭广昌,他们则是中国经济更加具体的体现,他们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代表,不同的企业制度,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管理思维,不同的个体价值,折射出中国经济一副更加形象和立体的画面。对于作家和独立知识分子的访谈,从文化和思想入手,从许纪霖、袁伟时到郑渊洁和韩寒,通过对于知识分子的描述,呈现一个和经济层面并行但是又易于被一般大众忽视的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之后,李翔带来的是普通人的群像。这一部分描述了一个普通人的中国,但是这样一个中国又是和前面经济和文化制度相映衬的。浙江义乌工商学院的校长和他的学生们,代表着普通中国人在经济浪潮之下对于财富和成就的渴望,也说明了在经济和文化撕扯之下普通人选择的分裂;而处于2008年末和2009年经济危机中的制造业工人,又让读者们看到了一群无力抵挡大潮的普通中国人,他们年轻,但是也似乎只有年轻可以倚靠。
但是读完全书,却发现这是一本没有结论的书。李翔所做的只是呈现和还原,描绘出不同人眼中的不同中国,然后留给读者自己去拼图。他一直在避免出现评论和下结论,也许是为了客观,也许也是因为自身阅历还无法触及,但不管怎样,他忠实的呈现了一群不同但又相同的中国脸庞。至于如何判断和下定义,交给读者,交给时间。
《谁更了解中国》读后感(四):年轻中国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于人身”,1915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敬告青年”,此时陈独秀亦不过36岁。这是个崇尚年轻的杂志,它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他的任务是延续此前梁启超提出的“启蒙”中国。不过,梁启超可算不上那个时代“最潮”的人物,他因为主张君主立宪制显得相对“保守”,但即使这样,他还是以“少年中国说”立论,“少年强,则中国强”。一大批冒进而激烈的年轻人想要挣脱旧时枷锁,追随最新的事物,邹容和秋瑾的壮丽青春是他们的偶像,那是一个年轻的时代,它为年轻而颠倒,为青春而疯狂。
当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生命的年轻时,其实心底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希望”和“朝阳”,恰恰相反,它潜藏着绝望和无奈。尽管人们为这个民族展开一切可能的“改革”和“教育”实验,但没有人会相信,旧时代还存在救赎的必要和可能,所以鲁迅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人们利用最决绝的方式,但依然难以和过去断裂,而只能苦苦等待无药可救的旧时代能随时间而尽快死亡,同时也以最热烈的方式欢迎新生命的出现。人们很难去估量,“五四青年”、“新文化”这些如今已成符号和常识的名词带给了现在的中国一个怎样的文化气质。除去那些被人们反复强调的自由和民主外,其实它们还带给了我们对于“年轻”的无限崇拜。
今天的中国,尤其在民主和自由重新被人们以隐或显的方式再次提起时,我们发现,“80后”、“90后”成为了网络里最热门的词汇,人们热衷于传播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我们崇拜少年得志的韩寒,同样也能轻易记住年轻多金的马化腾。无须讳言,我也喜爱追捧像许知远和李翔这样的“青年才俊”,他们的年轻令我激动,我甚至会用“可爱”来形容他们,就像我形容任何一个女歌星。看完李翔的《谁更了解中国》时,说实话我真有些“意外”。之前我经常在《经济观察报》的显要位置看到“主笔李翔”,以及他浓厚的许知远风格的大篇幅文章。看他老练的文章风格,我一直认为他的年纪应该最起码和许知远差不多,是70年代生人,但不曾想他是个“80后”。
我的确想刻意强调下李翔的年纪,因为他让我想起二十几岁就成为《经济观察报》主笔的许知远,也同时会让我想起“新文化”时代的中国,那个崇拜年轻的时代,而他们的文章也乐意经常提起那个年代,仿佛那是他们的精神故乡,尽管那是中国最艰难无望的时刻。他们还未真正老去,便带着回望的忧伤记录时代;他们喜欢把大时代浓缩成个人的生命经验,他们想象这个时代和他们的年纪一样的年轻而情绪不定;他们力求把“抽象中国”置换成一个个活生生的经济学家、文学家、商人,或者任何一个普通工人的个人生命,目的是唤起人们情感和思想中相似的体验,从而能切身感受这个“抽象中国”。但是无论他们讲述多少个体的生命故事,你总会发现他们似乎总在重复讲述同一个“故事”。许知远经常会在文章里抱怨说,不是他想重复这个故事,恰恰是因为这个时代太单调、太乏味了。于是,当张五常、谢国忠、韩寒、王石,或者深圳的农民工被李翔安排在同一本叫做《谁更了解中国》时,他们的悲伤、喜悦、愤怒和无奈,其实都只是被用来证明同一个“抽象中国”的存在。
“目的论”的叙述就是我读许知远或者李翔的文章所留下的最主要印象,这是个历史叙述的困境,但并不是因为时代本身的“单调和乏味”,而是任何一个想通过新闻写作去影响和修正历史方向的作者的通病。“直到今天也没有新闻记者能够摆脱这种梦幻般的感觉,认为新闻的意义就在于对当下产生影响,修正历史或社会前进演变的方向”,李翔在后记中,纪念了美国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对那个时代的新闻写作充满向往和怀念。毫无疑问,李翔和许知远的新闻写作都无法通过描述个体的生命历程预测任何一个历史“应该”演变的方向,他们对于“方向”的把握只能通过在想象中建立一个“抽象中国”,但是后者的直接来源除了与他们年轻的骄傲、理想主义,以及由此伴随而来的幼稚和粗糙外,我想象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内容。
以“年轻”的想象代替真实的历史,这就是许知远和李翔的新闻写作,这也是“新文化”时代梁启超、陈独秀和鲁迅的关于“年轻中国”的写作方式,如果非要说出他们之间的区别,估计在于“新文化”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有意无意地利用自己的“想象”推动历史进步,而许知远或者李翔的“想象”,可能更多的只是源自他们知识结构上的“缺点”。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文艺性想象,以及学理上的反思和批判的匮乏让他们的新闻写作看起来像100年前的西方传教士对于“基督教中心论”肆意张扬。列奥•施特劳斯说,西方现代性的胜利本身就可以理解为是年轻人反抗老年人的胜利,老年人的持重和深思熟虑被年轻人的轻佻和疯狂替代,而正是“现代性”的“年轻态”契合了许知远和李翔的新闻写作中幼稚和廉价的理想主义。
内心纠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想象”,除了造就出一个“年轻中国”外,其实还有一个更具有怀旧色彩的“老年中国”,比如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对于“乡土中国”的描绘,这是历史剧烈断裂之后,人们对于过去中国人伦社会里温情一面的“想象”。如今的中国,“乡土中国”的印象已经逐渐在淡出历史的舞台,“年轻中国”似乎成为人们对于中国的唯一“想象”,这里有对中国未来命运的美好期盼,也有年轻知识分子固有的幼稚和狂狷。
刊于 信息时报 10.12.5
《谁更了解中国》读后感(五):《谁更了解中国》,访李翔:必须对未来保持乐观
《谁更了解中国》,访李翔:必须对未来保持乐观
本报记者 朱桂英
“去看生活;去看世界;去目击伟大事件;去看穷人的面孔和骄傲的人的姿态;去看奇异的东西——机器、军队、人群、丛林里和月亮上的阴影;去看人的作品——他的画、高塔和新发现;去看数千里外的世界,藏在墙后与房间里的人和事物、难以接近的危险场景;男人所爱的女人和许多小孩;去看并享受着的乐趣;去看并且感动;去看并且接受教导。”
这是亨利•卢斯在创办《生活》杂志时的创刊词。李翔许和知远等人也想效仿着创办中国的《生活》杂志,这是一群高傲又谦卑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年轻力强,他们踌躇满志。当李翔在这片土地上走入得越深,他越发感觉无力,怀有救济苍生的心,却发现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改变。
李翔的好友兼同事许知远,将自己在今年出版的书命为《祖国的陌生人》,同样呈现出了自己的困惑与彷徨。他们都在尝试着以更大的努力去了解这个转型中国,这种体验,不似19世纪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旁观,也不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在中国上层社会的游走与下层社会的体察,李翔一代人的体验,是为了改变自己身处的环境。没有异国猎奇的情趣,只有壮怀激烈的灼痛。
也许,谁都可以用感性的话语,表达对时代的失望,以及自己内心的焦虑。或者,一次次引用那些诗人的话语:每个人都在平静中,堕入自己所不知道的绝望中。时代的纷繁嘈杂,物质生活的沉重,内心世界的逼仄,每个人都是脆弱的,都可能是节节败退者。
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用内心有限的理性,有限的勇气,有限的激情,来观察世界,解读世界的人,李翔说,他不能不乐观。乐观和悲观之间他没得选。因为他生活在这个国家,志向在于描述这个国家发生的变化,并且希望能起到一些建设性的作用。
“不是我多无私,而是我必须这么做。所以我必须对未来保持乐观。即使有一万个理由悲观,我也一定得找出能让我乐观起来的那一个理由。”
对话:积极生活 爱这个世界
治疗之道,还是交流(小标)
东莞时报:从书名上讲,你认为有哪些人担当得起这句话——谁更了解中国。
李翔:其实这个问题正跟整本书对人物的选择,以及它为什么变成了这样一本包括这么多不同人的书相关。
我们每个人都会对中国有自己的理解。都会以自我为原点出发,用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力来描述自己眼中的中国。每个人对中国的理解,可以说是正确的,毕竟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但这种正确一定是片面的。就像拿着显微镜去观察中国和拿着望远镜去看中国,看到的绝对是不同的中国;坐飞机掠过一个城市时看到的中国,和你坐火车从车窗看出去的中国也是不同的。但你看到的这两个世界一定都是真实的
富士康的工人们了解的中国,最主要的一定是自己日复一日的工作,八个人或十个人的宿舍,他/她们制造出了iPhone,但是他们不会了解北京、上海、香港街头那些拿着iPhone和iPad,用信用卡注册了App store账户,玩植物大战僵尸的白领的中国。然后他们的偶像是自己的老板郭台铭,或者像马云和郭广昌这样知名的商人。但是他们一定不能理解马云和郭广昌所理解的中国。
马云会考虑“只要国家需要,自己随时可以把支付宝捐献给国家”,郭广昌要考虑宏观调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然后会根据这种影响来调整复星在各个行业中的投资比重。批判性的学者会看到贫富差距;经济学家们会考虑国进民退的问题和制造业的转型问题;而政治家们要考虑的是金融安全问题(具体到支付宝的问题上),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
他们看到的中国和自己了解的中国都不一样。制造业工人们绝望到想自杀,不然就是想着赚够多少钱可以回家,或者自己创业;白领们忧心忡忡的是房价问题,一玩苹果手机就想着“越狱”的问题;商人们忧虑的是政策变更对自己的影响;经济学家和知识分子们是拿着望远镜看中国的人,看到的基本都是缺点,企业没有社会责任、经济增长方式太落后、政府不该过于干涉经济……
所以本质上,每个人都可以说自己了解中国,但是这种“了解”一定是局限于自己的经验和视角的。要想更了解中国,那就得打破这种局限,多去看看与你不同的人在想什么,听听别人怎么说。因此,那些能够突破自己经验的局限,去了解不同的中国的人,最终会更了解中国。
东莞时报:在书中,采访的公众人物分为经济学家、知识分子、作家、企业家,你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这些人物?
李翔:选择标准首先是你的采访所能抵达的极限。比如为什么里面没有政治家,因为中国的重要政治家是不习惯于接受采访的。
其次是选择那些能够对中国大环境有敏锐的认知的人。经济学家、知识分子、作家和企业家应该都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需要有这样的认知。
对于企业家而言,这同他们的生意息息相关,举个例子,郭广昌的复星在香港上市时,他对投资者阐释复星的大商业模式,就是要通过投资来分享中国的增长,那他当然要关心中国的大环境。
经济学家、知识分子和作家则是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人群。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商人一样,可能是除了政治家之外话语权最大的人群。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整个中国的主题词就是经济增长。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一定是要被关注的人群。因为知识分子天生的使命和责任就是关心这个国家、批评这个国家、解释这个国家。至于作家,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表达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理解,比如用文学的方式。
东莞时报:你逐渐觉得,独立的知识分子们自成一圈,无法将影响力扩散到圈子之外;经济学家和那些恢弘观念的制造者,易耽溺于观念世界中而脱离脚下的土地;财富阶层则向权力献媚,共同合作。普遍的病症,你有没有发现治疗之道?或者从历史和世界的经验看到希望的端倪。
李翔:我的这种感觉可能是年轻人特有的悲观主义带来的吧。但这种感觉至少在我说出它的时候,是真实的。作为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人,并且还以观察这个国家为自己的任务,确实是经常感到无力。
我觉得治疗之道,还是交流。大家需要打破自己视野、知识和经验的局限,来同其他行业的、其他领域的人来交流。比如经常有一些批判型的知识分子指责经济学家,说他们根本很少去实地调查,说他们不体察民间疾苦,都变成了政治家和商人的附庸,整天开会,拿出场费。但是经济学家显然也并不都是对这个国家无动于衷的,靠自己智力来骗钱的人。可是大家并不交流。经济学家们继续做自己的独立董事、政府智囊、四处参会,其他人继续骂他们。大家就这样习惯了。
再举个例子,社会学家,包括一些知识分子,自费去调查中国制造业劳工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然后告诉我们工人们生活多么艰难、赚的钱多么少,资本家是多么残酷,可是为什么不跟“资本家们”交流一下?“资本家们”会跟你抱怨,我的企业税收多么重,汇率变化影响了我多少订单,最近政府还拉闸限电,我都快破产了。大家互相不交流,也不了解对方。
缺乏交流的原因是缺乏所谓的“公共平台”。大家没得交流。媒体也扮演不了这个角色。大家缺乏了解对方的途径,缺乏坐下来对话的空间和平台。
东莞时报:你对未来乐观吗?
李翔:我不能不乐观。乐观和悲观之间我没得选。因为我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以写中文为生,志向在于描述这个国家发生的变化,并且希望能起到一些建设性的作用。也就是说,我登上了一艘我不能离开的船,可能还在船上当着瞭望员。即使你告诉我这艘船是泰坦尼克号,那我已经上船了,你说我能怎么办?最好的方法是,即使都没人管了,我也得没日没夜保持警醒,随时告诉船长和乘客,前面有冰山,前面有冰山,咱们可别撞上去了。不是我多无私,而是我必须这么做。
所以我必须对未来保持乐观。即使有一万个理由悲观,我也一定得找出能让我乐观起来的那一个理由。
仅仅因为自己想做个正直的人而受到伤害,让人无力(小标)
东莞时报:除了与名人交流之外,你还为制造业工人保留了一席之地,倾听他们的心扉。深圳龙岗之行,让你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的另一种生活。谈些感受。
李翔:有时候你感觉那是一种无望的生活。你看到那么多年轻人,他们那么有活力,大部分人都应该很纯良,接触了城市的繁华,能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知道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肯定内心想往,但似乎总无法摆脱所谓“命运的重负”。你会非常非常难过。
有一次我跟朋友聊天,我说,城市里的白领是这个国家增长的“人质”,他们交那么重的税,但是却享受不到什么税收的好处,地铁挤得要死,开车很堵,空气质量糟糕,房价又那么贵,他们被这个国家绑架了,而且要一直支付赎金,没完没了;那些制造业工人们则是这个国家的“炮灰”,他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GDP和中国制造,但是他们自己,非常累非常辛苦,情感上很孤独,心理上很绝望。但是你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来帮助大家。所以搞的自己也很绝望——更何况自己也是“炮灰”和“人质”。
东莞时报:接下来,有计划去重点接近、沟通、了解哪一类社会群体吗?
李翔:其实计划有很多。比如说我曾经想过要做一系列的在思考着的中国人的访问,就叫“中国怎么想”,看他们怎么来考虑这个国家的大问题,比如民主的前途、外交变化、经济增长等。再比如我想去寻找生活在当下中国的独立者们。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总是让人想叹气嘛,所以我们要找出那些在这个时代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不被时代裹挟着前行的那些人,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计划很多,呵呵。
坚持不让每个母亲哭泣,比空洞的国家的利益要重要(小标)
东莞时报:你很诗意地喟叹“我们都在这个时代面前节节败退。”你豪情万丈地指点江山,并愿为民立言,但在不甚满意的现实面前,觉得自己在历史中就是一个多余的人。哪件事情让你产生了最大的无力感?
李翔:其实很多。比如之前讲到你觉得自己并没有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时候你就很无力。
还有一种无力感往往产生于这种情况:你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你受到了伤害。而且这种事情每天发生。
街头小贩们会有特别大的无力感,他们什么都没做错,你能因为一个人仅仅想通过正当的、不伤害他人甚至造福他人的手段来让自己不饿死,就惩罚他们吗?对于开车在北京、上海、杭州这些拥堵城市的人而言,他们也没做什么,但是他们要承受拥堵,甚至还必须得限行——他们交了那么重的税,买了那么贵的车,可是他们得承受这些后果。对每个人都是这样。有时候你甚至仅仅因为自己想做个正直的人而受到伤害。这时候真是无力。
东莞时报:你热爱沃尔特•李普曼、托克维尔、加缪,一度把他们的头像放在自己的求职简历上。请谈一下这三个人分别带给你的影响。
李翔:李普曼让我知道,记者和作家对现实是有作用的,能够像政治家、企业家、工人和农民一样,对现实产生积极的影响;托克维尔让我知道,有的人是一个好作家和记录者,但并不适合去从政或者做别的事情,《论美国的民主》是经典,可托克维尔是个倒霉透顶的不成功的政治家;加缪让我知道一个作家坚持自己的原则和良知的重要性,有一段时间加缪几乎被法国知识界所有的人排斥,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不让每个母亲哭泣比空洞的国家的利益要重要。
东莞时报:有人赞誉你是许知远的后继者,而通过你的书里自叙,能看出许知远对你颇具影响。举例说一下?
李翔:包括许知远在内的之前团队的成员,他们对我早期的影响非常大。比如,许知远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存在就告诉我,你看,一个貌似书呆子的人,貌似跟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整天焦虑得要死的人,也能活的挺好;那么你就去读书吧,去坚持理想,去继续为各种大问题焦虑吧。这种影响在我刚刚大学毕业时候最明显。因为那时我感觉自己真的是会考虑自己如何生存的问题。
东莞时报:你最近的关注领域是什么?在读哪些书?
李翔:最近关心的领域主要还在商业方面。两个方面,一个是我所谓的“公司解释报道”,去深入的了解一家公司,去了解商业人是如何思考的,公司组织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在担心什么,什么会让他们兴奋等;另一个是大的商人如何面对所处的时代,以及在面对时代时他们身上的丰富性,比如秦晓,他出身红色家庭,按级别是副部,但却发出人们完全意料不到的言论,这样的人,他的人性该有多丰富啊。
读的书很杂,包括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如《斯坦布尔列车》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以赛亚•柏林的一些东西,也包括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的演讲集《穷查理宝典》、《Facebook效应》这些商业书,很奇怪这阵子又经常会翻鲍勃•迪伦的自传和海明威写巴黎生活的《流动的盛宴》,人家写的是真的好。
《谁更了解中国》
李翔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11月版
39.00元
成稿于10-11-28
《东莞时报》2010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