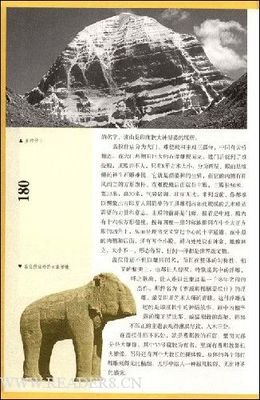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读后感精选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是一本由[英] V.S.奈保尔著作,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55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精选点评:
●这本书终于再版了
●让我看到另一个国度及一些宗教思想。
●奈保尔这样的移民后裔写印度,不偏颇不疏离,又有距离,再合适不过了
●犯罪率居高不下,警察成为帮凶,上层不作为,种姓不废除,印度教不取缔,想爬起来比登天还难,再加上人口爆炸,工业不发达,简直是雪上加霜。况且工业如此落后,再不加一把油可就没机会了,别说是30年内赶上中国,照这个发展速度300年内都别想了,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把企业都迁回去的原因,因为工业是根本。
●关于信仰,关于宗教,关于印度人的精神世界。 锡克教有最为虔诚的信仰,他们相信先知,通过师尊传承,忍受苦难,同时努力保持宗教的独立性。这份虔诚的信仰是现在比较少见的,不仅仅是对宗教,对任何东西都有女这份虔诚和专注都是太难的事情。
●大概翻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读前两本,导致读起来感觉云里雾里?感觉章节之间的整体性也不是很能摸清。
●受益匪浅
●这部是前两部的总结,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到信仰,这部格局明显更大,并且更有深度,或许这时候作者已经接受并了解了这个国家
●在瓦拉纳希的最后一天读完了三部曲的最终章,充满了仪式感和对这次旅行的重现。从印度的历史和遗迹去追寻了历史的遗迹,又从街道和人群去感受当下的印度,城市,农村,小镇,市集。尝试着理解这个大多数时间都在被“外民族”统治的国家在自由之后的无奈和努力。奈保尔的日记散文其实很可以让人共鸣,没落王宫贵族,新兴阶层,革命者,新商人…其实是非常全面地描述着印度的变迁。诺贝尔奖当之无愧。
●奈保尔的叙事张力绝了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读后感(一):一腔情怀,两种身份——奈保尔《印度三部曲》
奈保尔写作《印度三部曲》的时间跨度长达25年,自1962年第一次踏上这片他血缘上的“故土”开始,一直到1988年他第三次在这个国度旅行,才终于为这“三部曲”画上了句号。
这三部作品除了时间上的递进外,并无明显的主线。奈保尔几乎在每部书里,都对他在某一阶段在印度旅行时的观感进行了巨细靡遗的记录。然而也正因为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的作者作为一个“无根之人”——即在生活环境中被视为“少数族裔”,在自己血缘上的祖国同样被视为“外国人”,是如何一步步走近自己的祖国,那种对于祖国的复杂情感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奈保尔对于自己的祖国——印度的第一印象绝对称不上好。在第一部《幽暗国度》的开篇,他就描述了自己在孟买海关讨回被扣的酒的经历,字里行间满溢着对印度迂腐、效率低下的官僚系统的无可奈何。紧接着他的所见所闻几乎可以用“恐怖”来形容,包括城市里触目惊心的公共卫生状况,社会底层的赤贫生活,官僚阶层的虚伪和人浮于事,以及种姓制度、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所带来的尖锐对立。正是这些刺目的现实,让奈保尔的“寻根之旅”一开始就显得坎坷多舛,他对于这样一个“故乡”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甚至说印度“只属于记忆”,是“想象力停驻的地方”。
所幸奈保尔并不是一个凭借着自己现有国籍,通过贬低故乡来获得优越感的低俗之人。他对于自己的故土始终怀有一种探索与反思的热情。在经历了极具震撼的第一次印度之旅后,奈保尔又再二再三的返回印度,从各个方面观察着它。在之后的两部书中,虽然奈保尔对于他所看到的大部分东西仍然持批判态度,有时甚至语带讥讽,——比如称印度农业科学家们花费大量金钱研究的“牛车性能提升”技术,不过是把牛装备得像一个太空人而已;又比如形容一项收割机的发明是“比古罗马时代的收割机还落后几个世纪”。但在更多的篇幅里,他开始对现代印度社会的种种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他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从祭司、政客、黑帮分子到极端组织成员;他所观察的面也越来越广,城市贫民窟、宗教圣地、婆罗门小社区,甚至是极端组织发动恐怖袭击后的现场。其结果就是他对于印度社会的感情积淀愈发深厚,他从一开始的失落、愤怒,逐渐变得平和、深沉,乃至于透过这片大陆几千年来所遭受的苦难,而生发出的包容一切的悲悯之情。
当然,奈保尔直到最后也没有达成与他故土的“和解”。他在第三部的最后,写到自己重访25年前在克什米尔住过的度假酒店时,所耿耿于怀的依然是自己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印度人一样,圆滑巧妙的处理那些“烦人”的人情关系。这种纠结心态的背后,正是奈保尔两种身份的碰撞与对立——一个从小接受西式文化教育的英国公民,与一个来自植根于印度传统中的婆罗门家族的游子。这两种身份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既是让奈保尔不断进行“寻根之旅”,探求印度文化之本质的不竭动力,亦是他无法真正理解他的故土与同胞,给予他们同理与接纳的原因。纵观整个“三部曲”系列,贯穿始终的是奈保尔“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激情。一开始也许“哀”和“怒”更多一些,但透过那些令人唏嘘的现实,最终我们看到的,则是他对这个国家饱含热爱的底色。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读后感(二):变化的印度
直到二十七年之后,发现自己中年将尽、才思枯竭的奈保尔重新回到印度。这一次他承认,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如果要理解历史潮流并介入这个广大的世界,必须要“面对与我祖辈相连的土地,印度”,同时要“超越个人发现与痛苦”,才能得到一个新的看法:
印度最重要的,需要去深入接触理解而不是从外部旁观的,是那里的人。(3)他做了二十七年之前年轻的自己没有勇气做的事情。于是在《百万叛变的今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印度:它不是模糊的,而是清晰地;它不是集体的,而是个人的;它不是宏观的,而是微观的;它不是停滞的,而是变化的。他这样开始了他的叙述:
孟买人挤人。在瞬息万变的人流之中,每个人都在为奈保尔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奈保尔也从中解读,得以了解并呈现这个国家的历史与宗教的惯性以及它们在如今变化中的负担和意义。
毫无疑问,奈保尔的访谈和写作是有详细的计划,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典型并且配合的角色。他们有可能是耆那教徒证券商人,成长于祭司家庭的印度教祭司,在街头火拼的帮派首领,在现实中空耗才华的孟加拉编剧,既是诗人又是革命家的党魁,从南往北迁徙的泰米尔任,在古老的印度教传统中发掘现代知识的科学家,追随师尊反抗政府的西克教徒,为妇女提供阅读的出版商——这些人有的陷于泥淖,有的势头正高,但是作者都能以乐观主义的精神阅读出种种变动:身份、位置、认同、收入、关系、知识等等。正是在这些变动之中,作家产生了同情和包容的心理,发现了“无数人新生活的开端”,发现了“印度之成长”以及“印度之复原”。
在种种变动带来的开端、成长和复原之中,作者尤为关注宗教。了解印度与宗教的紧密关联,作者发现了所有的人都持有对宗教和信仰的看法:有时候激进,有时候保守,有时候又泰然。最具戏剧性的是卡库斯坦:他从小按照婆罗门的传统生活并长大,到十六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必须像大家一样过现代生活,”最终逃到了德里做了一个新人。到了三十八岁,父亲去世之后,他却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新选择称为一个真正、纯粹的婆罗门。奈保尔并没有对他突然之间的顿悟和转变作太多的解释,但很明显,作家并不认为这种改变是一种倒退。相反,他认可卡库斯坦一生之中经历的所有叛逆,并且认可婆罗门在适应和转变之中展现出来的活力。(289)
在最后一章,奈保尔重新回到了克什米尔的丽华大酒店,二十七年前他久居的地方。当年的亚齐兹已经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中年男子,这一次是他的儿子纳齐尔陪伴了奈保尔。作家发现,纳齐尔已经展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他不把自己视为自己的仆人,也不愿意将自己困在克什米尔的山谷之中。他感受到了整个印度整个世界的变动,并渴望参与其中。如果再有一个二十七年,作者写道,“纳齐尔将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他会有新的观点,他会有新的情怀,来日,这个山谷对他的意义将不同于今天。”(546)也许正如二十七年之后,印度对奈保尔的意义也已不同于昨天。
2020年03月27日21:01:42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读后感(三):内敛,安然
相比于第一本书《幽暗国度》这本书有很大的不一样。 首先这是一本关于人的书,通过大量的采访以及资料的收集最后组合成书,分不同板块,穆斯林人,锡克人,印度教信徒,女性等不同人物有各自独特的特点。这种采访类的书,作者个人的情感相对渗入的更少,基本是事实罗列,通过事实来反应一些社会现象。 在第一部中,作者从他乡回故乡,但是在他的话语中谁也不知道故乡是那,他乡又是那。带着浓厚的外来者的态度看待,对于印度的落后,印度生活的肮脏,破财,许许多多让作者无法忍受的东西,被视为不文明的行为。作者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想象的是为什么会这样,怎么能会这样,自己中那些神秘的古老的,或者是辉煌的岁月,都好像是虚幻的。作者甚至在离开的时候都报着终于可以走了的心态,迫不及待。 这个时候不管怎么说他的心态不是平等的,不是平等的看待所有文化的态度,而是带着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带着和别的文化比较的态度,从别的文化的落后中来找到自己文化的优越感。那个时候的作者更多是孩子气的,像个青少年,对看到的所有事物更多的凭着感情出发。 而在这本书中明显的不一样作者变得内敛很多,对于事情的看法更加乐客观。即使印度还是一样的面临很多问题,贫穷,肮脏,社会动乱,宗教各行其是,每个人在这个社会都要承受苦难,但是作者不在一味的评判社会的落后,不再带着青少年的稚气说印度,遗失的印度,那些光环却不褪去,已经找不到印度最开始得样子。现在作者企图告诉读者,印度从未遗失,他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偶然得也是必然的,很多人在传统文化的残留中出生,在社会工业化中长大,历经过很多的变迁,最后他们的选择,不管是成为一个有钱的中产阶级,还是成为领袖,或者依旧做着古老的职业,祭司,这些都是自己的选择,也是社会的选择,在做出这些选择以后大家都是理智的,也是满足的。 很多人依旧固守自己的宗教,宗教仪式,宗教教义许多的东西有的人全盘接受,有的人选择接受。有的接受我文化教育,学习哲学,学习生命科学,但是依旧做着小时候做过的宗教仪式,尽管心里不一定认同。也有的人从小见证死亡,怀疑宗教,不履行宗教职责,不做宗教仪式,人到中年却突然选择皈依,选择做回纯正的穆斯林,一点点学习宗教,把所有宗教仪式全部履行,不做任何改变。尽管困难,有些不符合时宜,但还是坚持做了,而且做的心安理得。 书中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安然,这是读完书给我最大的印象。 安然,对生活的安然,无论是社会动乱,宗教冲突,还是苦难的人生他们都露出一种安然,顺其自然。很多人都说到,因为就算你不接受贫穷(宗教/苦难)你依旧要接受的,心里的抗拒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所以便安然的接受。 在印度人有两个世界,一个物质世界,一个精神世界,这两个世界永远存在,当你一个世界难以坚持下去的时候可以选择另一个世界。一般而言都是抛弃俗世,选择精神世界,而宗教是主要的精神世界。印度的宗教复杂,各式各样,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所以回归精神世界的时候有很多选择。他们回到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每个人都是真实的,这时候现实世界可能就变成幻世,变成无足轻重的事情,所以才可以面对苦难安然处之。书中有提到印度人生活贫穷,所以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欲望,自己的需求降低到最小,这样就可以就着现有的生活继续下去。这也是种姓制度的影响。 种姓,宗教,印度人生活两大主体。种姓制度,规定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同时告诉所有人这是天生的,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所有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只要与自己无关便是真的无关,好像不存在公共概念一样。这种制度导致在公务员中很多人都只做自己的事情,办事效率慢。 同样因为种姓制度产生的贱民制度,这个制度导致人在现代社会开始反抗,寻求政治上的地位,于是政治运动频发,社会动乱不已,种姓制度也是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 故事最后讲到的锡克教徒,他们像是苦修宗教,总是承受苦难,追寻师尊。师尊便是一切的领导,是一切运行的基础,为了师尊可以做一切东西。这种虔诚的信仰把他们独立出来,独立的追求所有自己追求的东西,同时努力保持自己不被现代社会的法规改变。这份虔诚的信仰让我觉得很感动,几乎热泪盈眶。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读后感(四):读印度三部曲——冷眼看印度
《幽暗国度》、《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这三部书,合起来便是诺贝尔文学奖作者奈保尔的代表作“印度三部曲”。奈保尔出生于中美洲的印度婆罗门家庭,成年后在牛津留学,并定居英国。他的创作多为游记、小说。就我个人的观感,因为他的游记带着大家游览第三世界国家,所以比小说出色的多。我之前就读过他的《信徒的国度》、《不止信仰》等伊斯兰世界游记,因为伊斯兰教过于敏感,所以读书笔记就没有发。除了印度、伊斯兰,他还写过非洲、加勒比等地区的游记。这些读书笔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文明世界的标准妖魔化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满足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所以,我读完后比较犹豫要不要写这三本书的读书笔记,因为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我自己也不是怎么舒服。所幸又读了项飚先生的《全球“猎身”》,觉得印度民族也是有可取之处。所以,在这里先写一篇黑印度的文章,之后再写一篇吹印度的文章中和一下。正如同项飚所说,西方许多书籍表面上在写其他民族,但是实质上在通过否定这些民族来划清“中心-边缘”的界限。并不是要写这些民族为什么“不行”,而是为西方为什么“行”作背书。奈保尔的书籍就是这样一个系列。放在我国,他大概是要被称作“香蕉人”。
奈保尔关于印度的第一本游记是《幽暗国度》。这本书虽然写于1962年,但是豆瓣里评论时时刻刻提醒着我,印度现在也是如此。我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印度人的“不合作”。虽然整本游记充斥着奈保尔这个“外国人”哭笑不得的经历,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书中关于旅馆住宿的故事。
奈保尔在旅行途中因为一则豪华的广告而选定了某个旅馆。当然这里的豪华是指这家旅馆有抽水马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奈保尔的坚持下,旅店老板去其他地方拆了一个抽水马桶装在了奈保尔的房间,这也是整个旅馆唯一有抽水马桶的房间。之所以能争取到这点,是因为奈保尔看不到抽水马桶就不入驻。旅馆的其他服务,奈保尔也非常不满意,无论他怎么提要求,旅馆里的服务人员全都置之不理。比如他每天都需要和旅馆的小厮抢收音机的频道,小厮想听广告歌曲,而奈保尔想听新闻。奈保尔听一会新闻,小厮就会把频道调到广告歌曲,然后奈保尔再去调回来。这种情况在奈保尔给服务人员发钱后也没有好转,反而没有领到钱的厨师跑来质问为什么没有给他发钱,从而记恨了奈保尔。
另一方面,这些个旅馆工作人员反而向奈保尔提了很多要求。每次奈保尔进餐时,旅馆主会跑来要求奈保尔以外国人的身份给当地的旅游部门写信,邀请旅游部门负责人大驾光临。无论奈保尔如何拒绝,每次进餐时旅店主都会过来提要求。经不住软磨硬泡,奈保尔写了邀请函,只是并没有受到回音。可旅店主仍然每天跑来找奈保尔让他不断写信。上面所说的那位给奈保尔脸色的厨师,在离开旅店时,也跑来找奈保尔写工作推荐信。这些事在这些印度人看来非常寻常,没有觉得什么不妥。这些令奈保尔讨厌的印度处事方法充斥着整本游记。无论是公务员部门,还是路上的马夫,你没法对他提任何要求,但是他们会向你提出自己的要求。除非是一手交钱一手货,比如奈保尔离开旅馆面对天价的账单,威胁不付钱时,他们才会处于“合作”的态度主动找你沟通。
前几天看了《甘地传》的电影,了解了甘地的口号“非暴力不合作”。我想,这种“不合作”的心理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印度人。无论外界如何反应,我只管呆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无论殖民者想要榨取什么利益,我只是不贡献任何劳力。死猪不怕开水烫。出于这种“不合作”的态度,英国文化从来就没有融入印度。印度也因此错失了现代化的大门。自然这也不能全怪印度,英国人从来就没有想要真正的融入印度社会。莫卧儿王朝会宣称“世上的天堂就在印度”,而英国人仅仅是把这里当成一个殖民地而已。双方都把自己封闭了起来。(当然这里提一句,虽然英国人没有把印度西化,但是读了《全球“猎身”》,我发现印度强大的移民产业链做到了一部分。)
再来谈谈奈保尔的第二部印度游记《受伤的文明》。这部游记写于1975年。那年由于“不服从运动”、罢工和学生骚乱,甘地夫人下令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冻结了宪法。于是美国出版商和伦敦出版商出资,让奈保尔再次回到印度,记录那里的恐怖和暴乱。奈保尔在书里着重把矛盾引向种姓制度和土地政策的落后,但这不是我关心的重点。那段时期,印度曾想要实现工业化。网络上一个著名的论题便是,为什么印度有这么大的劳动力储备却无法崛起。这才是我的关注点。
说实话,奈保尔的游记就是流水账,读起来相当无聊。整本书翻到一半才吸引住我的眼球。“劳动变得荒诞。斋浦尔城的清洁工用手把街面上的尘土归拢到他的手推车里(这个过程风又把尘土吹回地面)。妇女用拇指和中指捏着一小块布条,在顶层铺抹水泥之前清洗着拉贾斯坦邦大坝的堤道。她蒙着头纱蹲在那儿,几乎不动,然而就在眼前,为了挣她的半卢比,她的五美分,她要用手指这样涂上一天——这工作只要一个小孩用一把长柄扫帚扫一扫就可以了。人们也不期望她做更多的事,她很难算是个人。旧印度不需要工具,不需要技术,只是需要很多人手。”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缝里有人用铅笔写着:“似乎为我在印度街头看到清洁工劳动的困惑找到了答案。”我看到这里非常惊讶,通常的感觉是印度的工人很烂,所以发展不起工业。但是按照这段话来看的话,印度人似乎相当勤劳,他们只是缺乏用勤劳换取致富的机会。
读了书中的其他部分,我觉得印度政府并不懂得如何高效的使用这些勤劳的劳力。前不久读了翟东升老师的《货币、权力与人》,其中讲到优秀的政府需要为民众提供高效的公共产品,以帮助民众扩大生产效率。这些公共产品比如“安全与和平,教育与医疗,抑制垄断欺诈,基础设施投资,维护法律和信用,统一地方和行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社保与再分配,倡导新路线的推广”。就拿最基础的水电举例子,对于村庄发展农业来讲,水和电是必须品。在那时的印度农村里,电是奢侈品。农民们并用不上电,电的作用是灌溉。官方对电的收费,大约和伦敦的电费一样贵。一个小地主一个月的电费,相当是一个劳工工资的两倍。基于这点,你就可以理解上面摘录那段话的原因,用人远比工业化便宜。
印度政府分配资源的思路匪夷所思。印度第一大党人民党曾经把印度发展核武器的原因宣传为保护圣牛。牛是圣物,这在选举中非常重要。出于这种奇葩回路,你就可以理解,印度在75年的时候,在牛车上的投资总量与在铁路上的相等。告诉作者这一统计数据的公务员信誓旦旦的说“现在,如果我们可以把牛车的性能提高百分之十。。。”奈保尔在书中吐槽到,印度的牛车比英格兰许多二手汽车都要贵许多,无论怎么改良岂不是让牛车变得更昂贵,有这个资源去引进小型发动机不好吗。最后奈保尔亲眼所见了他们研究,某头阉牛被装备上各种监控设施,像个苏联太空人,这只是为了改良牛轭的拉力。只要对技术史有最基本的知识,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来。当然,这又是印度政府在系统教育这个公共产品上缺位的缘故。(我还是要补一句,在《全球“猎身”》里,印度的教育被“美元梦”通过市场组织了起来。)
奈保尔的第三部印度游记是《百万叛变的今天》。这部书长550页,是奈保尔最出名的一部游记,在英国重印差不多四十次,在世界各地被译成各种语言。如果说《幽暗国度》奈保尔充满了愤懑,而《受伤的文明》奈保尔充满了阴郁。那么在这部1988年的游记里,奈保尔大概是心平气和的开始听人讲话。于是奈保尔抽离表象,开始思索印度的社会结构。他得到的答案就是“散”,本书访谈了各式各样的人群,有民族主义的湿婆党,公开祭祀的逊尼派,经商的耆那教徒,没落的婆罗门贵族,反抗种姓的达利特黑豹党,滞留北方的什叶派,贱民改宗的DMK运动党,被视为恐怖组织的锡克教徒,高举MZD思想的印共,寻求妇女解放的女权者。这本游记可谓做到了千人千面,然而我几乎没法提取出什么有效信息,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大概就是极端化吧。
对此,奈保尔解释道:“百万个叛变,撩拨叛变的是二十种群体的激进主张、派系的激进主张、宗教的激进主张、区域的激进主张:或许,这些是自觉的开端,重启了老早就被混乱和动荡扼杀的知识生活。但是今天的印度拥有两百年前所没有的东西:一份凝聚的意志,一套主导的知识,一个国家的理念。印度联邦大于其构成部分的总和,许多激进运动把国家视为法律和清理的依据,因此增强了国家的地位。印度联邦使大家得以卷土重来,让他们免于受某些过激行为之害——那些在另一个世纪或在其他状况下他们必然会面临的过激行为(如邻国所示)。现在,在印度,大家已经看出激进过头的问题。这百万个叛变也促进了整体知识活动的活力,巩固了所有印度人如今都觉得可以依附之价值的正当性和人道精神。而且——这结局倒奇怪,有几分讽刺——这些叛变不会眼不见就消失。它们是无数人新生活开端的一部分,是印度之成长的一部分,是印度之复原的一部分。”你看,奈保尔还嘲讽了一把我国。
对此,我也很惊异,这么多分裂的暗涌下,印度还没有裂成七块,可能是百万势力间达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这也是当年他们的可取之处,至少所有人都认可大一统,于是在这个框架下,就有一个相对通行的标准可以协商。但也正是由于这种群龙无首、各行其是的局面,使得行政效率低下。印度的十三种官方语言,在印度人看来,是一种值得自豪的地方。但是站在我国的角度,连“书同文行同轨”的天下大同基础都算不上。想到在《受伤的文明》里奈保尔同样所写,甘地最受人敬仰的时刻,便是缠着土腰布登上白金汉宫,向全世界展现印度的贫穷。这种道德上崇尚贫穷,使得印度囿于自己的旧世界。(而《全球“猎身”》里最让我惊讶的一点,就是西化可以在短短二十年之中发生。当然,在外国的印度人和本土印度人也不是一类人。)
这三本书的读书笔记就写到这里。比起奈保尔的印度游记系列,我更喜欢他的伊斯兰游记系列。《全球“猎身”》我虽然没有读完,但真是觉得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所以在这里就开始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