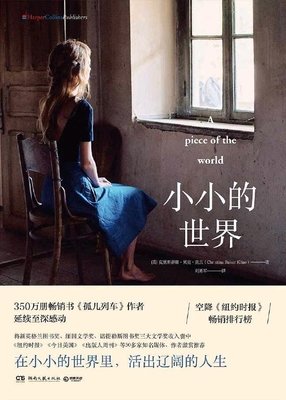战后责任论读后感摘抄
《战后责任论》是一本由(日)高桥哲哉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2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战后责任论》精选点评:
●对加藤典洋《战败后论》中去罪化的批判。如果说加藤的书是言足以饰非,高桥哲哉这本书就是质胜文则野了。论证过程乱糟糟,看不出头绪。
●为什么我看到加藤典洋的言论会觉得那么舒服呢!=_=
●不太适合初学者读,但也解答了我不少问题,就是太枯燥了点
●不要理论上扯淡了,日本战后责任清算不明,和东亚二战后冷战和共产主义扩张有必然关系,盟国为了日本抵抗赤潮,必须依靠旧势力,作为交换就是责任没完全清算,是权衡代替了彻底清算。
●读完这本书算是开拓视野,哲学角度难免枯燥特别是后半部分批判加藤。天皇 国旗 国歌的问题国内不曾见讨论过,值得国人阅读和思考
●哲学家出手谈历史问题是不一样,是吃透了阿伦特-列维纳斯-德里达的脉络再来谈战争责任、批判新民族主义的
●有点读不懂,太哲学了,不过无论是比喻还是哲学,都运用的很好
●日本左翼的书读起来特别对胃口。已经70周年了,战后责任在现在日本主流舆论中还是然并卵的存在。
●大半本是对加藤典洋“败战后论”的批判,结合阿伦特对审判的看法,观点正义,论证有些繁琐与重复。
●覺得日本國憲法第九條這件事真的很有意思
《战后责任论》读后感(一):时间脱臼了
文学作品中,有时作家会让鬼魂出场,有一种说法,“鬼魂”的意象代表着未了的事,代表着过去未解决的问题和冲突。哈姆莱特的父王死了,可是老国王是被亲弟弟谋杀而死的,而这一惨剧却无人知晓,因为所有人都以为老国王是在花园里,意外被蛇咬伤而死的。为了复仇,老国王的鬼魂不能安息,他在深夜出现,告诉哈姆莱特自己死亡的真相,并且托付给儿子为父报仇的重任。
《战后责任论》读后感(二):存档:不是书评
只是为了存档而已,因为这本书很快应该还会重读的。
大学里突然对自杀、饥荒和大屠杀发生了兴趣,陆续读了不少案例、史料、论文和书籍。也就某些具体的事件写过一些浅显的综述或论文,只是一直还未能理出特别清晰的头绪,更未能形成更深刻有效的理解和认识。但还是有兴趣,社会学方面的,文化研究方面的,等等。希望自己还能继续阅读和思考。某些案例或事件,如果能做一些田野或口述史,应该会更好的。希望有机会。
最近看了不少关于大屠杀和战争责任的影片、论文和资料,发现其实现在的研究和我们的认识真的还是有很多问题和不足的。比如南京大屠杀是一件残酷的史实,但为什么日本和西方有很多人不承认呢,一方面是日本国内的修正主义历史观导致的,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国内的历史政治化导致西方人并不信任我们的近现代史研究,还有一方面,从纯粹战争的角度讲,日本作为战败国并不是完全被中国人打败的,他们认为自己的战败是因为来自美国的两个原子弹,因而不少日本人心底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这一点也是完全不同于纳粹的大屠杀的。而德国国内对于大屠杀的研究和记忆也已经显出了公式化和图谱化的迹象。如果存在反思不足和反思过度的话,那么它们将会是同样危险的。
这些都是该认真思考的。
《战后责任论》读后感(三):日本人的战后责任——哈姆雷特的绝妙比喻
在《哈姆雷特》第一幕最后一节的几乎是最后几行中,哈姆雷特念出了非常著名的一句台词:“The time is out of joint”。这句话字面上的意思是“时间脱臼了”。然而,时间一直在均匀地流逝,如何会脱臼呢?
综合全剧,”时间“在这里或许代表的是人主观的时间,也就是记忆。在剧中,客观的时间在均匀地流逝,旧王已死,新王当立;然而,人主观上的时间,也就是国家的记忆,脱臼了,错位了,失去了连接。正如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人们仿佛瞬间就忘记了先君的死,转而开始庆祝新君的婚宴。葬礼上的烤肉,甚至可以直接端上婚礼的宴桌。所以,哈姆雷特的出现就是对于这一种遗忘的抗争。所以,他的下一句就是:“That ever I was born to set it right!" 而鬼魂对王子反复交代的一句话,不是”复仇“,而是“记住我,记住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哈姆雷特》展现的不仅仅是复仇,更深层次的是对脱臼记忆的矫正。
而到了20世纪末,当二战的阴霾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日本却发现战争的记忆突然如同鬼魂一般地复活了。高桥哲哉所应用的"time is out of joint“ 这句话,其实非常非常恰当地回答了日本人这样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半个世纪之后,那些已经沉寂许久了的战争记忆却突然鲜活地冒了出来,甚至具体地转化成战争索赔呢?为什么这些争议没有出现在战后,没有出现在50,60,70年代,而是出现在遥远的90年代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时间脱臼了”,或者“记忆脱臼了”。当五十年前战争结束的时候,人们对于战争的记忆,处于各种原因——出于冷战的考虑,出于战后重建的需求,出于战胜的亚洲各国深陷内战的原因——战争的责任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而更重要的是,战争的记忆被压抑了。记忆的载体,中国人,朝鲜人,甚至日本人,都因为各自的需要,而无暇物化各自的记忆。于是,记忆仅仅地成为一个没有物质依托的情感,正如《哈姆雷特》里中的那个没有肉身的游魂。然而,这些记忆仅仅被压抑,而没有被忘却。一旦冷战结束,压抑消失了,那么这个游魂就开始呼号。记忆的游魂需要书籍,电影,纪念碑,甚至战争赔偿来物质化,以为依托。所以,1995年的日本人会有这么一种错觉,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1945年。而早在1956年日本政府就宣布“战后状态”已经结束了,可是如今日本人却发现“战后“回来了。
这是因为,人们——包括受害者与加害者以及他们的后代——对于战争的记忆“脱臼”了。而现在,人们必须面对一个脱臼了的记忆,负担起哈姆雷特式的责任。
不过,高桥哲哉没有意识到他所举的《哈姆雷特》的例子有更深的隐喻。近代莎士比亚研究者指出《哈姆雷特》隐约地包含了心理分析中“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的特点。譬如说,Claudius明明想要压抑自己弑君的记忆,然而就在他对哈姆雷特发表的长篇大论中,他突然用到一个词组“the first corse"。熟悉圣经的人就立即联想到,这个first corse指的是Abel,亚当和夏娃的儿子之一。Abel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死去的人,而凶手正是他的兄弟,Cain. 作为弑兄者的Claudius当然非常不愿意任何人提及这个典故,可是他自己越是要压抑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越是从他的嘴中钻出。这仅仅是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在《哈》中的诸多体现之一。《哈姆雷特》展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即是:人要压抑的东西,在暂时的压抑之后反而会渐渐地回归。
如果我们继续延伸《哈姆雷特》对战后日本的寓言的话,我们发现,战后日本所压抑的记忆,在五十多年甚至更多年以后,确实排山倒海地回来了。日本人越是要拼命遗忘过去的侵略历史(就如Claudius拼命要忘记他弑君杀兄的历史一样),这个历史却越是挥之不去。要修正教科书中的”自虐史观“,反而招致家永三郎马拉松式的诉讼案并且激发了全社会的大争论,更多的战争记忆随之卷土重来。日本越是要通过颂扬山原千亩先生舍身拯救犹太人的事迹来为自己开脱,日本政府战时的犹太人政策问题反而又卷土重来。记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你越是拼命要忘掉他,你反而越是生活在他的阴影下。一个人犹如此,一整个国家更难逃脱。
在莎士比亚笔下,幽灵走后,哈姆雷特反复喃喃自语的,不是幽灵开头所说的"Revenge his foul and most unnatural murder“,而是最后的那句"remember me".
同样,历史的幽灵对于我们下一代中国人和日本人所呼号的使命,不是复仇,而是纠正那些脱臼的记忆。
《战后责任论》读后感(四):错乱的时间与记忆
2000年后的日本电影中,大概没有哪一部片子,能如2005年的《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一样能描绘出现代日本人心目中的战后奋斗史。电影选取昭和33年(1958年)东京的三丁目为舞台,以街坊邻里之间的冷暖人生,来反应日本战后物资贫乏之时人们之间的美好感情与奋斗。这并非一部历史片,毋宁说是一部对所谓美好的旧时光意淫般的乡愁。片中有最明显的两个意象:夕阳与东京塔,可谓直白地反映出电影的主题。电影的最后(必定是大团圆的结局),所有主要角色都映照在灿烂的夕阳下,夕阳映红了他们的脸庞,使得画面呈现出一种柔和幸福的红光,这无疑象征着这个贫乏的战后时代的完结。于此相对照的,是新建成的东京塔——新时代开始的象征。导演山崎贵以此片成名,他擅长讲故事和煽情,是个成功的商业片导演。这部片子也在日本大获成功,之后相继出了两个续集,很意外地也都非常成功。
然而,这部片子却给我一种说不明白的违和感。这种违和感并非来自乡愁或煽情——这是商业片的套路所以并不稀奇,而是来自于“战后”。最近读了高桥哲哉的《战后责任论》,这本书让我忽然明白这种违和感的缘由所在。
高桥哲哉是日本著名左翼知识分子,他从哲学专业出发反思日本对战争的责任。这本《战后责任论》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他关于“战后责任”的几篇论文、演讲、批评文章的合集。这本书所面向的读者是日本人,高桥哲哉作为一个同样出生于战后的知识分子,急切地呼吁日本政府与民众了解日本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和殖民事实,并能对此承担责任。
在《战后责任再考》这篇文章中,高桥哲哉就批判了“战后”这个主流思想。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上,一般把1956年视为日苏恢复邦交的一年。在战败过去了10年之后,由于朝鲜战争使得日本经济得到恢复,此后日本经济直线高度增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956年宣布“战后已经结束”。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电影《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中,发生在1958年的故事,无疑是对“战后”的庆祝。然而问题也在这里。事实上,虽然已经过去了10年,但在被侵略者与被殖民者的身上,战争的伤痕依然历历在目。日本宣布“战后的结束”无疑是从自己本国的利益出发,高桥哲哉说,“‘战后已经结束’的’战后’期间,完全没有考虑到几十年后亚洲人民的呼吁、亚洲受害者们的’战后’。” 可以说,这种宣布就是一种“封印”,对战争的封印,对自己责任的回避。
但是为什么《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这样的电影会在2005年拍摄出来,而不是在50、60年代?甚至到了2013年同样是山崎贵导演的《永远的零》这样更加右翼的电影依然大获成功?这就不得不提到90年代日本新民族主义与右翼的抬头。高桥哲哉在其书中对此用大量篇幅做了分析和批判。
高桥哲哉认为,正是因为在东京审判上,由于当时国际政治和冷战局势的原因,日本没有被追究责任。到了90年代冷战结束后,过了半个世纪,亚洲的受害者得以站出来向日本讨一个说法。而对于日本人,56年已经是战后的结束,但90年代却被要求对战争负责,这明显是无法理喻的。高桥哲哉用《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词“The time is out of joint”(“时间脱臼了”)来比喻这种诧异,并用了一个学术词语Anachronism(“时代错乱”)来命名这种错乱。在艺术史中Anachronism一般指本应属于不同时代的人或物,出现在同一幅画面上。但高桥哲哉将其解释为“与通常的时间感到相反”。这正是日本人面对亚洲各国的战争受害者的感受。
在这样的背景下,90年代日本兴起了“新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史观”这类否认歪曲侵略战争的流派。他们主张例如“殖民地的人的水准也要提高到跟日本人一样。日本就是热心肠。所以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欧洲人有根本的不同,是想把殖民地的人提高到日本人的水准”云云。这些说法当然是行不通的,但却非常流行。更可悲的是居然有台湾人支持这样的说法。2014年马志翔导演的电影《KANO》无疑是为此种言论做注脚。电影讲述了在1931年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一群棒球少年的奋斗热血故事。电影中对日本技术的向往和推崇,对被殖民这一事实无条件无批判性地接受,并以一种抒情的田园风光的视觉语言表现出来。这都让我十分反感(尽管我同情并多少理解马志翔对台湾原住民、多民族、少数族群的关注)。
另一方面书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与加藤典洋的笔战文章的集合。加藤典洋的《败战后论》中强调天皇应对死去的日本士兵负责,而非对亚洲的受害者负责;国民应该首先哀悼士兵;应该建立“我们日本人”这样一个“国民主体”等等言论,读来也真是大开眼界。
作为中国读者,除了了解日本左派和右派的争论之外,书中有几处颇值得我们思考。在《战后责任再考》这篇文章中,高桥哲哉对“日本人”这样解释:“在说’作为日本人’的责任时,不要陷入民族主义之中。……我本人不是民族主义者,我想大概也不会被误解。……我在说’作为日本人’的战后责任时,所指的日本人当然不是从’血脉的同一性’那样非科学观念的实体化考虑的,也不是从日语或所谓’日本文化’等方面可以共有的定义文化上的’日本人考虑的。我所考虑的’日本人’,是指完全属于日本国家法律定义、是’政治上’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因此也可以说是’日本国民’;具体说,从国籍上属于日本公民的一员,在日本国家宪法上具有日本本国政治主权的人,首先是法律上、政治上的存在者,这一点请牢记。”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民族主义者在现有民族国家框架下思考主体性的一个积极的例子。当我们在说“中国人”时,是否有这样的考虑?
另一方面,在前言中高桥哲哉说:“任何地方都同样要求克服民族主义,承认历史上的污点,坦诚谢罪,为恢复受害者的尊严做出足够的补偿。然而日本的情况如何,仍然是个问题。” 我想,错乱的时间和记忆不仅出现在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中。如何克服民族主义并坦诚面对历史上的污点,也是留给我们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