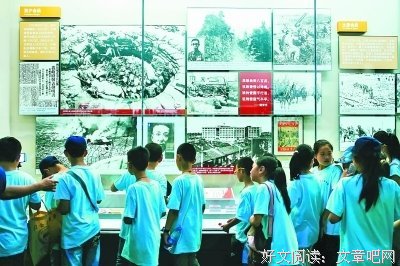《民族与国家》读后感100字
《民族与国家》是一本由(日)王柯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00,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族与国家》精选点评:
●“本书内容包括三重的天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文明论的华夷观——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万里长城的内外——成立期的中华帝国与夷狄等。”电子版。
●蛮好
●从多重天下转变为内地-边疆二重中国。
●对国民与族民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命题作文不太好看。不过重新梳理一下还是有价值
●透彻,读罢看到作者的名字以及国籍,又多了份兴趣
●头尾重中间轻,先秦部分得日本汉学传统,近代部分有博士研究积累,无奈从秦到清多转引他人结论,并无创见,所谓谱系也因此变成了民族思想的生成与两次剧变研究。当然若不苛求,末几章关于维吾尔的部分也确实十分精彩,只为这几章本书也值得一读。
●同样是博士论文,人家写的真是,不愧为78级。延续几百年的冲突,独立似乎不现实
●主要提出中国“民族”思想的传统源泉,以及面临现代民族思想冲击下的断裂。第八章后比较好看。不过对传统思想的延续性描述太多,对断裂和转变描述太少。结论过于简化、理想化,难免有武断和不真实的感觉。
●很有趣的一本书 对羁縻和土司制度的形成和评价很是赞同 清的功绩和过失真是难以让人对其下合适的评价 只有尊重历史了
《民族与国家》读后感(一):在想象与现实之间——读《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谱系》
「中国传统的民族思想……与近代以来主权国家的思想以及国民理论都迥然不同。中国之能够将多民族国家维持数千年之久,究竟与这一传统有无关系?虽然向来无人言及,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定会显得越来越有必要。」
《民族与国家》读后感(二):读后感
总体来说我对此书的评价是瑕不掩瑜 毕竟二十多万字能将先秦到建国前的民族观念与政策进行清晰的叙述实属不易 虽然作者在中古史之前的论述只能算是中平并无什么新意 但后期在唐辽元政治制度的对比、元明清对西南夷的改土归流、清朝民族政权与中国正统的双重性分析都相当出彩 诚然其中还包括诸如宗主权殖民等词汇的表述不当、引文偏重于日本学者和古籍材料等遗憾 但这些细枝末节并不影响作者全书自洽的逻辑 本文的精华部分在于结语 从先秦的天下概念入手描绘中国与蛮夷戎狄的非彼无我 天子是天的代理人从而将以德(礼)来治理天下 “以夏化夷”与“严华夷之辨”这两种观点贯穿中国历史始终 中国强盛时期待百蛮宾服万国来朝 中国弱小时强调非我族者其心必异 但从趋势来看中国的范围越来越大 多重天下的大一统覆盖地区越来越广 这一方面得益于北方民族一批接一批的入主中原从而华夏化 它们的二元政体最终融入多重天下格局 另一方面华夏文化也随南迁的中原人铺张开来 这种循环最终在清朝画上尾声 即使它通过满蒙藏回的内藩体制牵制汉地又防备沙俄 但终究挡不住殖民帝国的降维打击因此内陆与海上四面受敌 此事清政府试图进行民族--国家的转型为时已晚 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受到了根本挑战由此没有实力更难以说服藩部实现同质性 更何况民族国家的有限性与传统天下观的无限性本省就存在张力 更别提天下观暗含着四夷的主动华夏化而非民族国家的强制征服 由此民国先排满从而动员种族革命后来试图将五族同化为中华民族 但这更多只停留在笔上口头的呼吁直到CCP的强力动员 事实上这位入籍日本的学者对CCP民族政策的褒奖令我惊异 他认为否定民族独立到实施民族自治标志着CCP从在野党到执政党的成熟过度 当然话题的最后他开始与成书背景南斯拉夫解体进行呼应 提出对讲民族作为政治单元的潜在危害
《民族与国家》读后感(三):从民族意识问题去理解新疆
这是一本探讨“中华王朝”的书。
因为关注新疆和西藏的问题才关注到这本书,西藏、新疆和内蒙古是到了近代才有的民族独立的思想和运动,跟近代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统治的后遗症不无关系,创伤还未能平复,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不可能忍受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这是现状。
王珂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来分析“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演变,“中华民族”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它模糊了“民族”、“国民”、“国家”之间的界限。而对民族的认识应该有助于我理解新疆。
这本书的厉害之处在于由一个作者写出历代王朝民族政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规避了合著不能统一思想的缺点。追溯中国“天”的概念的形成,到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可以看出文献资料十分翔实,怪不得20年做出来的。
对中国“天”的解释让人真的很有认同感,“四海之内”为“天下”,在中国最古老的民族思想中,“民族”首先是一种文化的共同体。全书也是持一个观念:先秦时代的中国人认识的民族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文明共同体,文化的意义最强,民族的意思较少,而全无国家的意思,到了近代才提出“民族”。
西方一直攻击中国缺乏对少数民族实施主权的正当理由,企图分裂中国,都回避了中国这么多年多民族共同体存在的合理性。实际上,中华帝国从建立指出起,就已采用多民族国家的模式。“四夷宾服”才是中国帝国的理想模式。仔细想想看,这样分析中国统治思想的核心没什么问题,到了近现代,治理显得很难,可能就跟这些思想的变化有关吧。
这里还提到了科举考试制度对边疆地区的“华夏化”是起很大作用的,明朝开始,周边异族,像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推广科举制度,建书院,后续才有人中举,科举是接近政治中心的一种最直接的途经,这在作者的《消失的“国民”》中也提到,福建晋江丁氏一族就是通过科举制度“本土化”。
最令人瞠目的应该就是新疆地区“中国意识”薄弱的原因了,清朝对新疆的政策充满了满蒙的私心。清王朝禁止维吾尔人与汉人交流,防止维吾尔人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在新疆伊犁和乌鲁木齐都设立“旗缺”,即只能任命满族或蒙古人出任的官职,培养维吾尔人对满蒙的亲近感,对汉族防备。这一统一政策一看就知道新疆毛病在哪了,具有非常狭隘的民族性,妨碍了维吾尔人的中国国家意识和中国人意识的形成,不仅给以后清王朝的新疆统治留下了破绽,也是现代中国民族问题的直接成因。总结得太好了,确实这是一个重大原因。尽管清王朝在清代末期开始致力于建设维吾尔人的“中国意识”,但是当中国国家衰落之时,对周边民族来说中华文化已不再是唯一的具有绝对吸引力的文化,这时再希望他们建立“中国人”意识,不能不说为时已晚。再说当时新疆的交通和贸易,新疆与内地之间交通不便,而去苏联要方便得多,新疆许多突厥语系伊斯兰教民族的商人就是再20世纪20年代的“新苏贸易”中培养起来的。同时西边的伊斯兰教和突厥民族也在向新疆输送文化,这一系列对理解新疆而言简直就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民族与国家》读后感(四):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建设的演变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建设的演变
——读王柯《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
一、作者其人
王柯,1956年生,日本神户大学大学院教授。198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获民族学专业硕士学位,1994年获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学术博士学位。1996年起任神户大学副教授,2001年起任教授,专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国际关系史。曾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复旦大学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特聘教授,英国King's College London客座研究员,台湾国立交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走向民族国家——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思想诞生的国际因素》(商务印书馆)、《走向“天下”》(日本农山文化协会)、《20世纪中国的国家建设与民族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东突共和国”研究》(1995年获日本第十八届三得利学术奖)等十数种,近期出版《东突运动历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二、主要内容
本书内容包括三重的天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文明论的华夷观—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万里长城的内外—成立期的中华帝国与夷狄,分治与同化—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政权的中华王朝,多重的帝国和多元的帝国—唐、辽、元的国家和民族,大一统帝国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元、明、清的土司制度,在中华与“乌玛”之间—清王朝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统治,构筑“中华民族国家”—西方国民国家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实践,二重的中国—近代中国的边疆思想,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决定过程。
本文将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介绍《民族与国家》一书中的主要观点:
(一)“天”的概念与“天下”思想
“天下”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天下”是以“天”的存在为前提的一种先验论的逻辑推论。根据商代文献《尚书》的盘庚篇,“天其永我命于新邑”,天的概念很可能出现在商代甚至更前的时期。根据《诗经》商颂长发篇中 “帝命不违”的记载,商代的“天”与“帝”很可能是同一个概念。商代将“天”作为祭祀对象,对于商人而言,“天”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的神圣的存在。同时,“天”并不抽象,而是一个实际的存在。在“天圆地方”的宇宙想象里,“天”笼罩在大地之上,世界位于“天”的下方。先秦时代中国人对“天”与世界的关系的想象使他们得出了“天”之下的万物来自于“天”并且要无条件服从于“天”的结论。“天”的统治者是神,“天”之下的统治者是顺应“天命”的王。因为只有一个“天”,所以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即只有一个正统的王朝。“天下”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天下最高统治者受命于天,他的权力性质是代表“天”对人间实行统治。到了周代,这一统治人间的王的身份,变成了天帝之子,即“天子”。从“天”的思想出发,产生“天下”的思想,最后衍生出“天子”的思想,是先秦时代“天下思想”形成的三部曲。
中国初期国家社会时期的“天下”,是一个“三重的天下”,从地理上可以分为“九州部分”和“九州之外四海之内”两个部分,从方位上可以分为“中国”和“四夷”,在共同体层次上可以分为“华夏”和“蛮、夷、戎、狄”。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并不等同于“中国”,而是一个包括周边民族和其他异民族的体系。这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基础。
(二)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
先秦时代中国人眼中的“天下”,不仅包括作为主体的“华夏”,也包括周边的“四夷”。天下思想不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依据,而是对中国多民族社会的认知。“天下”中的主体民族“华夏”,是在中国由部族联合体社会向初期国家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由众多部族和民族通过“中原化”和“华夏化”而共同形成的,比如“舜东夷人也”,“禹兴于西羌”,“文王,西夷之人也”。
中国最初的民族思想,注重的不是人种和地域,而是以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行动方式、价值观念为代表的文明方式。先秦时代中国人眼中的民族,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物质共同体,而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文明共同体。这种以文明方式区别不同民族的意义在于,它将民族视作一种可以后期可变更的属性。“蛮夷戎狄”如果接受了“华夏”的文明方式就变成了“华夏”,“华夏”如果接受了“蛮夷戎狄”的文明方式则变成了“蛮夷”。“蛮夷戎狄”向“华夏”转变,即“蛮夷戎狄的华夏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各种手段移居中原,接受农业文化;二是“蛮戎夷狄”地区受“华夏”文化影响,采用农业生产方式,主动向“华夏”靠拢。这使得“中国”通过“四夷”的华夏化不断扩张和膨胀其边界。天下思想强调“德治主义”,即礼的秩序。“礼”的获得与丧失,是“中国”与“四夷”,或者文明与野蛮易位的关键,这为异民族建立“征服王朝”提供了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依据。
(三)中国历朝民族政策及其影响
秦在攻灭六国之后,开始了对周边民族的战争,并在征服的异民族地域建立“属邦”,实行间接统治,从制度上开中国历史上两千年中央集权制时代多民族国家体制之先河。汉王朝将原属秦势力范围之内的南越、东越、西南夷和朝鲜划为“内属”,撤销边界,统一法令。对西域则坚持“外属”原则,与各国“约为外臣”,实行间接统治。秦汉王朝建立的中华帝国的天下秩序,具有三重的构造,即“汉人”的地域;中国领域内位于周边地域的由异民族实行自治的“内属国”;位于中国之外的“外臣国”。
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在中原建立了一系列政权。尽管他们均未能统一整个中国,但他们均认为自身是中国的正统王朝,或以此为目标。出于建设政权的需要和“天子唯德”思想的影响,胡人政权通过政治制度上的中华王朝化,文化制度上的儒学化,经济形势上的农业化和社会组织上的地缘化,使得自身发生了质的变化,同化于汉族。异民族进入中原、统治中原、接受中华文明,甚至建立中华王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和传统的社会背景和主要动因。
唐、辽、元统治者同时具有民族首长和中华王朝统治者的双重身份。汉人统治者将其治下的地域分为多重来进行统治,非汉民族统治者则将其治下的地域分为多元来进行统治。唐建立羁縻府州制,形成了拥有中华文化的中国与非汉文化的周边民族共存的双重构造体制,以文化的力量变夷狄为中华。辽和元在政治文化制度上坚持民族的二元性,将“中国”和北方统治民族原来的活动地域隔离起来,形成了一种南北区隔的二元体制。征服王朝有意无意地促使自身接受中华文化的过程,对 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和多民族统一国家传统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元朝开始的土司制度,在尚未渗透中华文化的西南地区确立了国家主权,明清继承了元的土司制度,将西南地区置于自己的统治后,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变对西南地区非汉民族的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积极促进边疆地区内地化和非汉民族汉化。
(四)国民国家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现实的矛盾
由于清朝政府260年的民族压迫和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并逐渐发展。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借鉴西方的国民国家理论,主张以排满革命的方式建立汉人政权,实现汉族独立。然而,西方的国民国家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现实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西欧,nation既是民族,又是国民;nation state既是民族国家,又是国民国家,二者是同义语,民族国家是国民国家的前提,国民国家是民族国家的结果。在中国,民族不能等同于国民,民族国家也不能等同于国民国家。第二,西欧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地域型民族主义,强调统一的法律和制度之下的团体意识和共同文化。孙中山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民族型的民族主义,轻视共同的生活地域和共有文化,只强调族群的血统。第三,西欧的民族主义是要在不同的共同体中建立一个同属一个政治同心圆的民族,孙中山则是要在原有的多民族国家中以民族为要素区别各个共同体。第四,西欧民族主义的目标是打破罗马教廷的束缚,建立宗教独立和财政自主的中央集权和绝对主义的主权国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则是要打破清王朝现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秩序,这不仅容易出现地域之间的割据,也容易出现民族之间的分裂。
传统的天下思想不分夷夏,近代的民族主义则号召以民族划分你我。天下与民族国家,一个开放,一个内敛,二者的性质截然相反。孙中山在接受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之后,在革命的实践中经历了三次思想转变,从提倡汉族即中华民族的“小中华民族思想”,到主张“五族共和”,再到提出同化中国所有各族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大中华民族思想”。
(五)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演变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变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共产党自身不断变化、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解决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22年—1937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期,中国共产党《二大宣言》和《二大决议案》提出“民族自决”政策,允许少数民族独立地建设自己的民族国家;提出建立“联邦制国家”的设想,希望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建立中华联邦制国家。一方面,这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有关;另一方面,这也是作为初生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保持其无产阶级政党形象的需要。第二阶段为1937年—1945年,是中国共产党的青年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族自决论”否定了之前主张的少数民族“民族独立”。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也使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其初期的民族政策。第三阶段为1946年—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壮年期,否定了“联邦制”,逐步实施并最终确立“民族区域自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在野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之中,在提出解决中国国内少数民族问题时,不仅需要考虑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也要站稳中国国家的立场。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传统的国家里,并非只有少数民族建立独立国家才能维护自身利益,也并不是只有通过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才能使民族得到发展。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到中华民族的立场,再到中国国家的立场,正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思想的成熟和进步,才使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优秀传统得以在当下得到继承和发扬。
三、思考感悟
作为阐述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的研究,王柯的分析是全面完整的。第一,作者分析了中国人传统的“天”的概念与“天下”思想,并阐释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主张从中国人的世界观—“天下”思想出发,理解中国人对中华与“四夷”关系的认识。第二,作者梳理了中国历代王朝在“天下”思想影响下各具特色又一脉相承的民族政策,通过汉民族王朝和非汉民族王朝民族政策的对比,更加深刻地论证了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论点。第三,作者描绘了清王朝获得新疆统治权的过程和治理新疆的政策思路,提出正是清王朝竭力维持维吾尔社会传统的社会体制,防止维吾尔人与汉族进行交流,防止维吾尔被中华文化圈吸收的新疆统治政策,造成了影响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维吾尔问题。第四,他对比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民族观的不同和差异,即“天下”思想与国民国家理论的区别。他认识到近代中国在面临民族危机背景下借鉴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实现民族独立的合理性,但也批评了孙中山民族主义和民族政策的局限性。最后,作者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演变,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从制定“民族自决”政策和提出“联邦制国家”设想,到否定少数民族“民族独立”,再到否定“联邦制”并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这个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长和进步,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传统的认识和发展。
国家的三个要素是领土、主权和国民,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才是完整意义上的肇始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近代民族国家。很显然,从秦汉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都并不符合民族国家的标准,中国近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不是起源于民族国家建设,而是经历了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演变。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是一个非汉民族建立的王朝,采用了以“民族”牵制“中国”的政策,形成了一种以民族等级制度为基础、按民族异同划分地域单位的“多元型天下”的政治传统。经过多年努力,清王朝将它的统治疆域建设成为了一种旨在牵制汉人的、主权定义模糊、领土疆界不清、国民范畴分歧的“多元型天下”。在这种“天下国家”之内,领土、主权和国民的范围,三位一体,无法适应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近代国际体系的现实需要。
面对这种局面,近代中国产生了两种建设近代国家的力量:一种是来自政权内部的、推动放弃“多元型”但却保留“天下国家”的改革派;一种是来自政权外部的、以建设“汉”民族国家为口号号召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民族革命势力。1864年爆发的“新疆危机”和外国势力的侵略,促使清王朝在新疆建省,标志着清王朝放弃“多元型天下”思想,也标志着中国确立近代主权、领土和国民的建设近代国家进程的开始。“新疆建省”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国家的建设进程并不是由民族革命派所开启的,清王朝内部的改革派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且,清王朝内部改革势力的努力说明:即使建设近代国家,最终也必须正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而且,要确立近代的主权、领土和国民领域,首先必须解决国家与多民族之间关系的性质问题。革命派倡导的“排满”民族革命虽然也是一种建设近代国家思想的方式,但是以一个纯粹的“汉”的民族国家为基础而确定的近代中国的主权、领土和国民的范围,相比起清王朝的版图来说将会大幅度缩小。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让做着“汉”民族国家之梦的革命家们开始回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之中。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之后提出的“五族共和”,其实是一个折中了“天下”与“民族”的政治纲领,但是却因为得不到边疆民族中具有分裂主义倾向的上层的认同而不存在实际效力。由清王朝内部改革派从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出发而启动,但却最终为追求民族国家的革命势力掌握了主导权的近代国家建设进程,就这样最终将“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天下国家”的现实融汇交织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