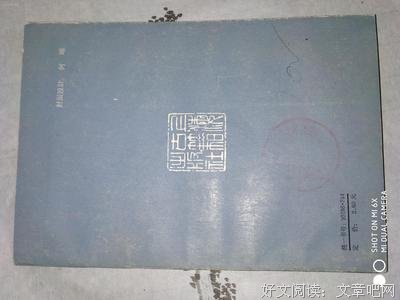《王无功文集》的读后感大全
《王无功文集》是一本由[唐]王绩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元,页数:1987-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无功文集》精选点评:
●賦多雜五七言詩句,固梁陳結習;五言詩多排偶,亦永明以降之格。
● “以真率疏浅之格,入初唐诸家中,如鸢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翁方纲太会形容了。
●隋末唐初王绩,王勃是其侄孙。好饮酒会造酒,医术琴术都善。诗文气质疏野,其人澹泊。“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不如高枕枕,时取醉消愁。”“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置酒烧枯叶,批书坐落花。”
●我还不是为了《古镜记》啊。
●唐诗 王绩
●大二补标。了解隋末初唐时期的诗歌发展。
《王无功文集》读后感(一):五斗先生、《古镜记》和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这话虽带着酒意,但不无道理。古来饮者往往个性鲜明、活泼,让人愿意亲近。比如,阮籍听说步兵营厨人善酿酒,就请求担任步兵校尉。刘伶经常乘着鹿车携着酒,随行随饮,并对随从说:“死便埋我。”隋唐之际的王绩引刘伶为同调,有“恨不逢刘伶,与闭户轰饮”的感叹,对刘伶心仪神往之意溢于言表。
王绩是我心仪的酒友,他有“兀然成一醉,谁知怀抱深”之叹,如果知道一千多年后有个酒友愿意穿越时空陪他畅饮,不知道高兴不高兴。他曾说过“酒瓮多于步兵,黍田广于彭泽”,加只酒杯、加双筷子,他应该不会介意的。
【一】
盛唐的陆淳也是王绩的粉丝。他谈到王绩时说:“余每览其集,想见其人,恨不同时,得为忘形之友。”王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不妨先读读他的《五斗先生传》,这篇文章可以看作他的自画像。
王绩笔下的五斗先生嗜酒,经常一喝就是五斗,逢请必到、逢到必饮、逢饮必醉,醉后随处而眠,醒了再喝。不要以为他是整日烂醉的酒鬼,他心里像明镜一样澄澈。他说:“天下也就这么回事。现实如此,怎么养生啊,嵇康还写啥《养生论》?阮籍何尝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穷途末路,何必每到路的尽头就放声痛哭?所以,圣人的状态是昏昏默默。”五斗先生“绝思虑,寡言语”,没有什么事让他纠结、焦虑,他什么事情也不想,甚至很少说话,像极了《庄子》里面的人物。
《五斗先生传》里面的这些话,不像是他年轻时所说的。他出生在世家大族河汾王家,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也做过“小粉红花”的梦——“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弃繻频北上,怀刺几西游。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王绩幼承家学,文武兼修,既研读经典,又学习剑器、占星,十五岁第一次到长安就崭露头角,被称为“神仙童子”。
本来以为青云有路,可是等到王绩举孝廉之后,仅仅当了个秘书正字的小官,这让他不免有些失落。当时已经是隋朝倾覆的前夜,王绩或许已经嗅到了隋朝灭亡的气息,或者对于秘书正字这个职位不甚满意,后来他请求外放,一度担任六合县丞一职。因为爱喝酒,王绩多次受到弹劾,他最终选择了解职——在一个夜晚,他将朝廷发放的俸禄堆放在县衙门外,乘着小船悄悄走了,开始了一段说走就走的旅程,游历广陵、会稽、庐山等地,三年后才回到家乡。
王绩第二次出仕是在唐高宗武德年间,因曾任隋朝六合县丞,王绩待诏门下省。七弟王静曾调侃王绩说:“待诏这个活好玩吧?”王绩回答说:“怎么说呢,俸禄少得可怜,美酒三升,还是挺让人留恋的。”按照当时惯例,有司每天给待诏三升酒。江国公陈叔达与王绩熟识,知道王绩嗜酒,破例每天给他美酒一斗,时人称王绩为“斗酒学士”。可是,每天一斗酒也没能留住王绩,贞观初年,王绩再度辞官回乡。
有人推测,王绩这次辞官是因为“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为了夺取皇位,在武德九年(626年)策划谋杀了自己的兄弟李建成、李元吉,屠杀了他们的儿女,甚至牵涉到他们的下署。在这场血雨腥风中,王绩见证了身边同僚遭受打击甚至屠杀,一定心有戚戚。后来,他在《祭杜康新庙文》中写道:“乘流则逝,遇坎则止。眷此酒德,可以全身。”他或许为自己因沉湎于醉乡保全性命而感到庆幸。可不,魏晋之际,阮籍、刘伶不也是用酒作为软猬甲保全了自己吗?
王绩第三次出仕太乐丞,是因为太乐署的焦革家擅酿美酒,这与阮籍出任步兵校尉非常像。可惜,王绩到任几个月后焦革就去世了;焦革死后,其妻袁氏依然给王绩送酒,一年多后,袁氏也去世了。王绩感叹道:“唉,老天爷这是故意不让我喝好酒啊!”他第三次辞官回乡,从此隐居故乡河汾,再也没有进入官场。
王绩的“三仕三隐”都和酒有关,有人讥笑他是不成气候的酒鬼,他就写了《无心子传》等文章,为自己争辩。除此之外,他留给我们与酒有关的美文还有《醉乡记》等篇什。但是,真正理解他的又有几个人呢?
【二】
假如有机会与王绩喝酒,真想听他讲讲在河渚的隐居生活。
王绩是绛州龙门人,出生地距离汾水、黄河交汇处不远,他们家在河渚上有十五六倾田地,四面环水,东西距离河岸各有数百步。有一段时间,他像陶渊明一样,在故乡北山的东皋耕种隐居,自称东皋子。有很长时间,王绩便在河渚隐居,他在河渚上盖了十多间茅屋,有厨房和马厩,还有奴婢数人。王绩不但下田耕耘,还带着儿子到田地中教他如何锄地。他在河渚种植的作物主要是用来酿酒的黍米和黏高粱,以保证他常年杯中不空。他还在河渚种植用来养生的药材黄精、白术、枸杞和薯蓣,养饲鸡鹅猪狗等生灵。
因为爱酒,王绩在河渚东南方为杜康立庙,将焦革牌位放在杜康牌位旁边一起祭祀。他还总结焦革制酒法写成《酒经》,梳理了杜康、仪狄以来善酿酒者的史料,编成《酒谱》,为古来酿酒者立传。
在王绩河渚茅屋中,只有《老子》《庄子》和《易经》等书,其他书他几乎不看了。茅屋中有琴,真希望能找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听王绩弹奏《汾亭操》。这首古琴曲的作者是他三哥、大儒文中子王通,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或许,王绩喝酒的时候会说到隐士仲长子光。这位隐士在与王绩邻近的北渚隐居多年了,没有妻子儿女,依靠耕作、采药自给。仲长子光有瘖疾,不能说话,但是品性高洁,文章写得极好。王绩经常和他在一起饮酒,相互给对方看自己写的诗文。《王无功文集》中收录了王绩的《仲长先生传》《祭处士仲长子光文》和他写给仲长子光的诗,记录并定格了这段伟大的友谊。
王绩有时也会给远方的朋友写信,他在给老友冯子华的信中这样描写自己的生活:“烟霞山水,性之所适。琴歌酒赋,不绝于时。时游人间,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于北山,松柏群吟,藤萝翳景,意甚乐之。箕踞散发,与鸟兽同群,醒不乱行,醉不干物,赏洽兴穷,还归河渚,蓬室瓮牖,弹琴诵书。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读来让人有说不出地羡慕,不知道收信人冯子华读后怎么看?
“醒不乱行,醉不干物”,不论醉或醒,王绩都是豁达的,世间的黑暗和不平他不是没有遇到,但是他内心强大而平和,所以不屑、不在意,也不争。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陆淳称赞王绩是真正的乐天君子。
想象着夕阳的余晖里,河渚上飘起袅袅炊烟,鸡犬之声相闻,安谧而祥和,俨然世外桃源。这里没有官场的尔虞我诈,没有虚与委蛇的应酬,更没有算计和杀戮。小船就泊在岸边,想念弟兄了,可以渡河回家,兴尽而返。天气晴朗的时候,王绩会在小船中吟诵谢灵运“乱流趋孤屿”的诗句。有时候还与渔人一起垂钓,把自己融入大自然中。这四面环水的河渚不就是王绩的Neverland(永无岛)吗,而河湾就是他的瓦尔登湖。只不过,这河水是奔流不息的,就像流逝的光阴。当然,王绩还有一个精神层面的永无岛,就是他笔下的“醉乡”,通过美酒到达这个快乐老家。
喝酒的时候,王绩少不了谈到陶渊明。如果陶渊明能穿越时空一起到河渚与我们共饮,该有多好。他们会不会交流种庄稼的经验呢?如果嵇康、阮籍、刘伶、阮咸能一起来,那就更热闹了。那样,可以亲耳听听嵇康演奏《广陵散》了。只是,假如嵇康、阮籍读过《五斗先生传》,不知道又会作何感想?
【三】
真希望王绩聊聊《古镜记》。
这篇传奇小说的作者是王绩的大哥王度,说的是王度、王绩兄弟和古镜的故事。因为叙事采用第一人称,代入感特别强,让人虚实难辨。小说中所讲的古镜据说是黄帝十五枚宝镜中的第八枚。《古镜记》提到,王度曾携古镜拜访长乐坡的程雄,程家有一个婢女叫鹦鹉,乃是千年狐狸精,被古镜照见后非常痛苦,自知死期将至,她就对王度说,希望能畅饮美酒做个醉死鬼。王度答应了她,鹦鹉酒憨之后一边跳舞一边唱歌,唱完化作老狸而死。我想问问王绩,这只爱喝酒的狐狸精身上是否有他的影子,王度这么写是否有意调侃他?
《古镜记》中说,王绩从六合县辞职后,曾携带古镜游历天下,遇到并打败了不少妖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杀死恶蛟并烹食其肉,真想问问王绩,是否确有其事?如果有的话,那蛟肉是不是太过肥腻,用来下酒是否合口?还有,王绩诗中有“前弹广陵罢,后以明光续”的句子,他是不是会弹奏《广陵散》?如果会的话,又是跟谁学的,难道是文中子王通吗?一边喝酒,一边听他摆摆龙门阵,一定非常有趣。
喝多了,我也许会对王绩说酒话:“你在光阴的上游,我在光阴的下游,逆流而上,有幸与你为友,多么让人感慨啊。你诗文中经常出现独酌、独坐,你是不是非常享受这种孤独?可是,你在《秋夜喜遇王处士》中写道,‘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遇到老友的欢欣跃然纸面。是不是因为平时拥抱孤独,才会更珍惜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不知道王绩听了这些醉话会有啥反应。
王绩晚年爱酒已经到了任性的地步,经常“乘牛驾驴,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动经数日”。我想问问他,既然家中有酒,他为什么长期借宿酒店呢?是因为家人经常唠叨他,还是他喜欢醉卧酒家的自由?他这么做一定是有原因的,真想听他解释解释。
王绩的老友吕才在《王无功文集序》中说,王绩准确预测出了自己的死期,并为自己撰写了墓志铭,文中“往往卖卜,时时著书”的表述让我想到了西汉的严遵。严遵本来姓庄,字君平,为了避汉明帝刘庄讳,被班固改了姓,成了严君平。严遵一生没有出仕,常年靠卖卜为生,但是他每天只赚谋生所需的一百个铜钱,然后就收摊回住处读书,后来他写出了《老子指归》,对后世影响非常大。他给人占卜时,喜欢因势利导,劝人向善。像严遵一样,王绩完成了《老子注》,那么,他卖卜市井是不是也像严遵一样,并非仅仅出于生计、换钱买酒,同时有劝人向善的目的。或者,他喜欢用这种方式,走进并观察问卜人的内心世界。这个问题我很好奇,可是不知道该不该请教他。
王绩去世后,他的驴子和两只狗不断哀鸣,没过几天就死了。可见,他是个对动物非常友善的人。我甚至想,他也许经常和驴子和狗们说话,就像我们村有些农民一样。或许,王绩在骨子里是孤独的,而酒是孤独的人最好的朋友。
《王无功文集》读后感(二):王无绩版本考 二
本文的立论已经被推翻,贴出来只是···毕竟作了一段时间的作业。
问题出在:三本宋代类书引王绩诗上重合的地方,并不足以证明论点,但是笔者觉得这个误会引起的思考蛮有意思。正文如下:
綜上,王績文集的主要問題是存在五卷本、二卷本和三卷本三種不同版本。五卷本雖然記錄最早,但是出現最晚,真偽存在疑問。二卷本至今從未出現,文獻記載也只有陸淳序和幾個書目記載,難辨其選詩原則和錄詩順序。三卷本最早出現在明代中後期,存本較多,但是問題最複雜。今一一論述,先從三卷本入手。
如上所述,三卷本主要存在三個系統。張錫厚先生認為林抄本可能是“明清各家開始輯補王績詩文之前具有‘原始型’的三本卷”,並且是“更加接近陸淳刪的二卷本”。田曉菲先生贊成張錫厚先生的意見,並且在張先生的文獻整理基礎上提出了兩點“佐證”:一個是林抄本的29首詩,僅有兩首絕句,且幾乎不收錄五卷本中占詩作三分之一的“准近體詩”[1],其餘全為十句以上的古體詩。而且,五卷本中其實存在大量寫王績隱逸生活的詩篇,但都不見林抄本。故此她重新判斷陸淳所謂的刪去“無為”之作的意圖:陸淳是在8世紀末刪編二卷本的,時值“復古”高潮,他的“無為”其實是將五卷本中的律詩刪去而保留古樸質直的古體詩。第二個證據是一般三卷本比林抄本所多出來的詩,一部分可以在南宋學者洪邁的《萬首唐人絕句》中找到,而且順序、題目、字句都十分契合;餘下的部分則可在宋以來的各種類書、筆記和總集中找到。所以“通行三卷本與五卷本之間沒有直接的繼承關係,它很可能源自陸淳的兩卷本,而林雲鳳抄本則是陸淳本的再現”。
陳尚君先生則認為明清以來流通的三卷本是陸淳之刪本,不過其中有後人陸續所補入的偽詩[2]。他對田曉菲先生所說的選詩標準並不贊成。他將五卷本和三卷本進行對讀以求陸淳刪詩標準時感到“茫然”,因為陸淳的確刪除了不少入世情節的詩,也刪除了文辭繁縟之作,但相比陸淳未刪的《古意六首》,內容相近而文辭更顯簡樸的《山家夏日九首》則被刪除,一些明顯能顯示王績從入世轉到出世的詩作也不入陸淳法眼,所以他認為這其中的去取標準是很難看出的。陳先生在分析時使用了林抄本無而一般三卷本有的、根據田先生分析應輯自宋以後類書的詩(如《題酒店壁》五首),可見陳先生似乎不認同田先生所揭示的林抄本與一般三卷本之間的輯補關係,而堅持一般三卷本基本就是陸淳原本。
而劉鵬先生則認為林抄本雖然出現較早,但“不僅沒有一篇一般三卷本未收的篇目,”還比一般三卷本要少,故指出林抄本為“一般三卷本的節錄本”。而一般三卷本(即上文的三卷本系統丙),則“至少在宋代以前就有了”,其證據是《文苑英華》詩文不出一般三卷本範圍,沒有三卷本無而五卷本獨有的,且《文苑英華》詩文及其題目都與三卷本基本契合[3]。也就是說,《文苑英華》很可能就是從這樣的一個“三卷本”中選錄王績的詩文的。他還指出,《文苑英華》在詩文中夾雜著當時與文集校勘所作的校記,其中寫作“集作某”的,正與五卷本同,可見校者正是用五卷本來校對“三卷本”。
以上觀點總分為兩大陣營:林抄本更接近陸淳刪本,一般三卷本為林抄本之輯補本;一般三卷本為陸淳刪本,林抄本為節本。他們的推論都建立在堅實的文獻校勘對比工作上,尤其是張錫厚和韓理洲兩位先生所作的工作,但是他們都尚未看到這些文獻之間的全部聯繫。而且他們都相信三卷本和陸淳之間存在關係。
我覺得在此要先提出幾個觀念上的更新,首先,王績文集雖經由呂才和陸淳二人編輯過,但自南宋以來,兩種版本均在主流文獻中處於隱佚狀態。陸淳刪本,今僅見著錄於《崇文總目》和《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並書為二卷,它與三卷本的關係是可有可無的。第二,就王績文集來說,我們是無法確定任何一個現存的三卷本是否就是其完整的“原本”,它極有可能經過了諸藏家的重抄和輯補。但前人的研究,都存在一個心理預設,即現存本,在長久的流傳過程中始終保持著一種相對的“完整性”。就現存的幾個三卷本情況來看,它的確在晚明時呈現出一個較為穩定的形態,但就算如此,不同藏家依然對其作了不同的輯補工作。那麼在此前,即一般三卷本的主體部分被輯補出來之前,它是如何一個形態呢?它是否真的能體現所謂的陸淳的刪詩標準?
(一)、林抄本問題
按本文的分類,一般三卷本的四個主要本子,即趙抄本、黃汝亭本、曹荃本和孫刻本,前三者的詩序完全一致,除了曹荃將一些答王績詩補于原詩之下,将《詠妓》等三詩置前,《石竹詠》、《食後》和《過漢故城》順序與其他兩本略不同,亦幾無差別,這大概就是曹荃所“定”的內容之一。而前人所說詩序大不同的孫刻本,實際上除了前29首,也與其他三本差別不大,見下表[4]:
前文已述,林抄本與孫本前29首的順序是幾乎一樣的。但表中也揭示了自《過酒家》到《詠巫山》,除了《石竹詠》和《詠妓》,孫本與其他一般三卷本(排除了曹荃重定的因素)亦別無二致。如果仔細看
孫氏自稱自己的底本是余蕭客(1732—1778)的影宋本,如果可信,那麼根據田先生的輯補分析,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這個影宋本指的是一個與林抄本十分相近的宋本,后来某個人在此宋本的基礎上作了輯補[5],而且保留了原來宋本的詩序原貌。(其他三卷本是怎麼產生的?根據宋本輯補後打亂順序?根據余蕭客本直接打亂順序?為什麼打亂順序?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但是林抄本可能是宋本嗎?林抄本共收錄《遊北山賦》一首、詩二十八首和文十篇。而明代前收錄王績作品最多的三部書,即10世紀北宋初的《文苑英華》、《唐文粹》和十二世紀中后期的《唐詩紀事》,他們收錄的王績詩作,不多、不少且不重複,正好就是林抄本的前二十七首,僅《文苑英華》中的《益州城張超亭觀妓》、《辛司法宅觀妓》和《唐詩紀事》中崔善為的《答王無功冬夜載酒鄉館詩》和《答無功九日詩》未被選錄。
按,在今本《文苑英華》中(明隆慶元年1567﹐胡維新等根據傳抄本重新刻印)[6],《益州》和《辛司法》收录于“王勣”的《詠妓》之后,並署作者為“前人”,即王勣。但五卷本不錄此二詩。在《全唐詩》裡,《益州》下注“一作盧照鄰詩,一作王勣詩”,《辛司法》則兩錄在王績和盧照鄰名下,韓先生指出王績一生未曾涉足蜀地,故《益州》詩當為盧照鄰詩[7]。我們可以考察一下兩詩在早期的收錄情況:14世紀初明人楊士宏所編《唐音》、高棅所編《唐詩拾遺》都將《辛司法》錄為盧照鄰詩;16世紀晚期的張燮所輯《幽憂子集》亦收錄此詩。《文苑英華》此處的收錄情況為:王績《詠妓》、前人《益州》、前人《辛司法》和駱賓王《天津橋上沒人》,故此處所謂“前人”極有可能是“盧照鄰”之誤。如果明刊本《文苑英華》“前人”并非讹误,那麼明初楊、高之誤則離奇無解,可見至少明初以前未有以為《益州》、《辛司法》是王績詩的。這個錯誤目前看来只能是明刊本《文苑英華》造成的,並且誤導了一般三卷本的輯補工作。如此,北宋徐鉉等人編《文苑英華》時必系此二詩於盧照鄰下,林抄本因故不錄。
另外,林抄本還收錄了《在京師故園見鄉人問》並朱仲晦答詩,從文獻上看,這兩首詩共同出現的情況最早是在朱熹第三子朱在所編的《晦庵先生文集》卷四的卷首,是集刊行于宋寧宗年間(1195-1224),尚在朱熹生前(1200年卒)。林抄本將此二詩置於最後,
就朱熹答詩和崔善為答詩的取捨,可以判斷此輯本是以王績存詩為根據,並錄他人答詩。所以崔善為的兩首,因非王績詩作,又無錄王績《九月九日贈崔使君》和《冬夜載酒鄉館詩》原詩,故林抄本不錄。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唐文萃》收錄《古意》三首、《唐詩紀事》收錄《古意》六首为重複外,《文苑英華》、《唐文粹》和《唐詩紀事》三書所收錄的詩絕無重合。如果林抄本真是接近陸淳二卷本的,在北宋前即存在的版本,那麼徐鉉、姚鉉和計有功三個時間跨越了近二百多年的人,何以能如此默契地每人都從中抄錄了不同的部分呢?而且徐鉉的《徐公文集》卷一七在談論王績時還提到了“昔人谓王绩神仙童子”,這是僅見於五卷本的呂才全序的,也就是說,徐鉉在編纂《文苑英華》時使用的應該是五卷本而不是陆淳二卷本。由此看来,林抄本是自此三书辑录而成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但是林抄本依然面临着诸多难解之题。首先是文章收錄問題。林抄本所錄文章亦不出《文苑》和《唐文粹》二書範圍,但二書共收錄王績及答王績書文十七篇,而林抄本僅錄其中十篇,缺《唐文粹》的杜之松《答王績書》、王績《重答杜君書》、《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陳叔達《答王績書》,以及《文苑英華》的《仲長先生傳》、《自擬墓誌》和《祭處士仲長子光文》。《仲長先生傳》和《五鬥先生傳》、《無心子傳》、《負苓者傳》三篇在《文苑》777689中同屬一卷,前後先連,林抄本的避而不錄是讓人費解的。
這裡也需要指出,如果排除《負》和《醉》’
,林抄本實際上沒有收錄《唐文粹》的王績存文的,只是保留了其收錄的刪節版《呂才東皋子集序》和陸淳《刪東皋子集序》。在南宋時從《文苑英華》等三書及《晦庵先生文集》中抄錄出一個三卷本,並將兩序收入,他顯然是在掇合一個“王績集”,但是他又不選取其中的某些篇章,真是讓人不解。而按照林抄本和孫本的書名,這個輯者應是將他的輯本命名為《王無功集》。這也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下文將述,五卷本在宋時尚存,故筆者猜測這個輯者可能無法得到當時尚存的五卷本,或因五卷本罕見,所以他才從總集類書中輯出一個三卷的本子,而這個本子卻意外地流傳下來,並成為明末之後三卷本的一個祖本。之所以分輯為三卷,我們據後來發現的五卷本分卷可以看出,五卷本是按文類分卷的,所以這個輯者也將其分為賦一卷,詩和文、書的數量少,故分別壓縮為一卷。這樣看來,三卷本的體例實際上是模仿呂才五卷本而不是陸淳二卷本了。
這裡筆者想進而討論一下《負》和《醉》的問題,此兩篇是王績文章中最為廣傳的。如韓愈曰“餘少時讀醉鄉記”,白居易“王績唯以醉為鄉”,宋人孫光憲在《北夢瑣言》亦言“王勣,字無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稍晚於《唐文萃》的石介在其《徂徠石先生文集·辨易》節錄了《負苓者傳》中負苓者對伏羲的批評,元人覺岸《釋氏稽古略》、明胡居仁《易象鈔》、蔡清《易經蒙引》等都全錄或節錄。我們不免猜想在石介之前,《負苓者傳》即常被易類文獻所徵引,很有可能像《醉鄉記》那樣別有單行[8]或常常見載“易”類文獻。正如下文講述的,一般三卷本從各類書中輯錄的佚詩,往往是被歸於某類文獻而被保存下來,這種形式自有其傳承關係,而非從卷子本中摘錄的。這是值得留意和深思的。
[1] 僅收錄《贈程處士》、《田家》三首和《詠妓》,這三首詩將在下文論述。
[2] 陈尚君,《诗人王绩的两种文集及其佚诗》,《文史知识》2017年第12期。這些偽詩包括《北山》、《過故漢城》、《益州城西張超亭觀妓》和《辛司法宅觀妓》等。
[3] 劉鵬,《<王無功文集>版本問題新論》,太原師範學院學報,76-79頁,2009年9月,卷8,第五期。
[4] 五卷本編次與諸本差異甚大,而且數量較多,對三卷本問題並無影響,故此處不列出。
[5] 輯補的內容是什麼?余蕭客本本來就是50多首?仔細研究下孫刻本。
[6] 中華書局出版有影印本《文苑英華》,為宋本和明刊本合集,可惜收錄此三首詩的二一三卷宋本已亡佚,今仅存明刊本。
[7] 王績,《王無功文集·五卷本會校》,韓理洲會校,20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8] 見上文“其他存本”。
《王无功文集》读后感(三):《王績集》版本考 一
课堂作业,没处发表,聊作纪念。
《王績集》版本考
王績,字無功,號東皋子,唐初太原祁人[1],新舊《唐書》皆有傳。《舊唐書·藝文志》載有《王績集》五卷,友人呂才所編。後來唐末大儒陸淳曾刪為二卷本。就目前文獻情況看,自宋至明,《王績集》五卷本和二卷本的流傳情況不明,似乎五卷本為通行本。明末到上世紀80年代,通行本為三卷本,其底本多據明人趙琦美抄本和孫星衍刻本。學界多認為三卷本為明人所編。今人韓理洲、張錫厚同時在上世紀80年代發現《王無功文集》五卷本[2],他們所據的底本為清東武李氏研錄山房校鈔本、清人朱筠家藏手抄本和清陳氏晚晴軒抄本,三本共屬一個系統。以上諸本均見《中國古籍總目·集部》著錄[3]。
一.見存本子綜述
據《中國古籍總目》,當時統計全國所存善本共16本,其中一本藏臺灣國家圖書館,現錄如下,並據各本題跋和明清書目梳理其關係及流傳(1表示存本,0表示不知去向):
三卷本系統甲:
1 《王無功集》三卷,明抄本,現藏國圖[4]。有林雲鳳跋(萬曆壬寅年,1602年),但為其家大父手錄,時間可上溯到明嘉靖年間(16世紀初)。後被何義門(1661-1722)藏,並以爛溪潘氏之“影宋本”校讀[5];之後被韓應陛(1860卒)收錄在《讀有用書齋書目》,其載有林雲鳳跋和何義門手校並跋。又王文進(1960年卒)《文錄堂書目》收錄明鈔本《王無功文集》二卷,並有松江韓德均(應陛)藏印和何義門批校本印,竹紙一冊,不知王氏此二卷本是否即為林氏抄本[6],二卷或為三卷之誤?[7]另外,大連圖書館藏有《王無功集》二卷,補遺一卷,為清末抄本,今未得見。不知道這二者關係如何。
此本前錄刪削的呂才《東皋子集序》和陸淳《刪東皋子集序》(書名卻作《王無功集》);上為《遊北山賦》1首,卷中為詩28首(比其他三卷本少25/26首[8]),卷下為文11篇(比趙抄三卷本少《祭仲長子光文》和《自擬墓誌文》),張錫厚先生認為有可能是明清輯補王績文集前的“原始型”三卷本,是更接近陸淳刪本的本子[9]。
三卷本系統乙
1 《王無功集》三卷,補遺一卷,抄本,有余蕭客題記並孫星衍的校和跋,後經祝壽慈(穉農)手,今藏臺灣國圖;此本即為下岱南閣本之底本,詳見下文。張錫厚先生稱此本為孫本,孫氏刊刻本為岱本。下文論及此兩本時或統稱孫刻本。
1 《王無功集》三卷,補遺二卷,孫星衍岱南閣刻本,叢書集成影印出版。此本的重要意義在,書中孫氏跋言稱此本乃據余蕭客藏吳松岩影北宋本而成的。田曉菲先生認為這是故意提高自己抄本价值的說辭,但是下文將證,吳松岩可能真的是一個宋本。
孫刻本孫序稱“《唐文粹》所載又有《勣與陳叔達重借隋記書》、《重答杜君書》二篇,亦不見集中(孫本)”,可知孫氏據《唐文粹》補了二書。另外孫氏還據《永樂大典》補遺了《三日賦》和十三首《贊》文。孫本和趙本的不同還在於:二者卷中詩序不同,孫本多了《詠懷》和摘自南宋人葛立方等的王績佚句;賦、文順序相同,但是孫本缺《祭處士仲長子光文》和《自撰墓誌》兩篇(有趣的是,林抄本也是缺此二篇);據張元濟校勘,孫本錯漏比趙抄本多,兩者異文達百餘處,而能校正趙抄本的僅數字,餘皆誤[10]。
此本还有一个有趣之处,其正文前錄呂才《東皋子集序》,陸淳《刪東皋子集序》及孫氏所作《東皋子集》序,書名却作《王無功集》,這與林抄本是相同的。《王無功集》的名字此前無任何書目記載,直到明代中後才出現,如明人莫旦《大明一統賦·詩文集》稱“王無功集”[11]。這足以引起我們的注意。
在某種意義上,孫本和林抄本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即缺少《祭處士仲長子光文》和《自撰墓誌》兩篇,書名和序名存在衝突,最重要的是,除了《山中敘志》順序不同,且孫本多出《石竹詠》一首,林抄本與孫本開頭的29首詩詩序完全相同,但與趙抄本的順序則區別較大。
孫刻本另有巾箱本,內容全部一樣。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1《王無功集三卷,補遺一卷》,清羅振玉刻,藏國圖;此本與孫刻本的內容和編序都完全相同,僅增補《重答陳尚書書》一篇[12],並作校勘記。羅本國內藏本甚多,此處不一一展開。
三卷本系統丙:
0 陸漻(1644~?)《佳趣堂書目集部》,錄“王無功《東皋子集》三卷”,辛未,焦弱侯太史藏本。今佚。此為丙系統的祖本。
1《東皋子集》三卷(附一卷),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趙琦美抄本。此本有趙氏校文和跋文,兼清人錢謙益題簽。據趙跋,此本錄自明焦竑家藏本。後收錄在清錢遵王(1629-1701)《讀書敏求記》。錢氏之後,是抄本為張金吾(1787-1829)所藏,錄入其《愛日精廬藏書志》。張氏書後被其侄張承渙所奪,最後輾轉歸瞿鏞(1794-1846)藏,錄入《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1908)。現藏國家圖書館[13]。是本前錄《東皋子集序》河東呂才君英撰(刪序);《刪東皋子集序》平原陸淳化卿撰;《東皋子集傳》,據《新唐書》;《書東皋子傳》,蘇軾撰;並據馬端臨《文獻通考》錄陳振孫解題、《周氏涉筆》語和晁公武解題。卷分上賦、中詩、下文,著“太原王無功著”,後附他人答王績詩四首。是本最後由《四部叢刊》影印出版,附張元濟先生跋語。
1 唐王無功《東皋子集》三卷,附一卷,明黃汝亭刊本。此本前有黃汝亭(1558-1626)序、高出(1579-1630)序。據黃序,亦為明焦竑家藏本錄出。此本後流傳不廣,清人書志未發現著錄。是本前錄黃汝亭序、高出序、《東皋子集序》河東呂才君英撰(刪序)、目錄和《刪東皋子集序》平原陸淳化卿撰。附卷收錄他人答王績詩四首,與趙抄本同,最後兩首順序不一。附卷後所收資料與趙抄本錄於書前的一致(除呂序(刪序)和陸序在前,亦一致)。兩本順序一致,幾無異文。卷中末手抄有《詠懷》一詩,自言抄自孫星衍本,應為藏家所錄。現藏國家圖書館。
1《東皋子集》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即四庫本。是本前錄《東皋子集序》河東呂才君英撰(刪序);《東皋子集序》,平原陸淳化卿撰。後有附錄,與黃汝亭刊本同。四庫館臣稱此底本為明崇禎刻本(曹荃本),且稱無陳振孫所言陸淳後序,甚是奇怪。按是本收錄順序,與黃汝亭本如出一轍,但是卻改動了呂序和陸序,不知緣由。或是此本為經黃氏之後的人所修改的黃本?
0 《東皋子集》三卷,四庫全書本,乾隆寫。但不知所藏在何處。
1《東皋子集》三卷,附錄一卷,明崇禎刻辛巳(1641)本,明梁谿曹荃元宰定[14],現藏國家圖書館。前有曹荃《東皋子集序》,根據曹序,他原本只讀過《醉鄉記》,後來方讀過三卷的《東皋子集》[15],并自己做了裁定后刻板印行。又有《東皋子集序》河東呂才君英撰(刪序);《東皋子集序》唐陸淳撰;以“卷之一、之二、之三”分卷。詩歌順序與趙抄本不同。曹荃又將他人答王績詩、書置於本首下,但缺《答王無功冬夜載酒鄉館》[16]一詩;雜著類將《登箕山祭巢許文》置於《祭關龍逢文》上,按人物時代先後排列的目的明顯。又比趙抄本多收《杜之松答王績書》和《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17]。書後附錄劉昫《王績傳》、宋人宋祁《王績傳》和蘇軾《書東皋子傳》;並有《遺事》,為晁公武所載而呂才刪序不載之事。
曹本還根據孫本增添了很多內容,與曹本之源頭無涉,此處不展開。此本在“遺事”下刻有“張燮”[18]按語,據《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載錄《東皋子集》三卷一冊,“此本明張燮所輯刻,前有崇禎辛巳曹荃序”,當與此本為同一刻本。
1《東皋子集》三卷,清抄本,藏南京。此本有丁丙(1832-1899)跋,收錄在《山本藏書室藏書志》。自言“此明梁谿曹荃定為三卷”,皆與上本同。丁丙的這個藏本,可能是李芝綬從趙宗建次侯處所得之本,因為趙宗建死後之書大部分歸為丁氏藏書。而據李芝綬跋,趙宗建此本為“王校本”,既然可以用以校對曹荃本,可能即為黃丕烈所言的“得自郡中之王西沚(王鳴盛)家抄本”。若此,則此處流傳為:曹荃本—王鳴盛藏並抄—黃丕烈得刻本和抄本—抄本歸李芝綬;刻本歸趙宗建,後又歸丁丙—兩本後皆歸國圖。
0 莫友芝(1811-1871)《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載錄《東皋子集》三卷,明崇禎中刻本。今佚。
1 《東皋子集》三卷,附錄一卷,清抄本,有清吳翌鳳校並跋,清周星詒跋,現藏國圖。前書“唐太原王無功撰”,錄呂才序,陸淳刪東皋子集序。此書張錫厚先生未歸入其所分的三卷本系統中。據周星詒《傳忠堂藏書目》記載為舊抄本,有吳翌鳳(枚庵)手校。黃丕烈上述跋文中也提到曾見吳枚庵家抄本。此後此書歸於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並有吳翌鳳手跋。吳氏手跋記載他(吳)曾見鮑廷博(1728-1814)所藏之宋版五卷本,比三卷本多三十餘篇。不過現存五卷本,比三卷本多了接近110篇詩賦文。可惜未曾與之對校,此本亦未見鮑氏書志,不得知此五卷本為何種面貌,大概已佚久矣。
二卷本系統:
1 《王無功集二卷,補遺一卷》,清抄本,藏大連圖書館;既無書志著錄,亦未得親見。實際上是孫星衍的三卷本系統。
五卷本系統[19]
0邵逸辰、邵章《增訂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註·續録》載“宋刊五卷本,汲古閣有影宋抄本”,今考毛氏書目,並無記載,不知邵氏所據。
0鮑廷博藏五卷本,據吳翌鳳跋比通行三卷本多三十餘篇,鮑氏書目不載。今佚。
0朱學勤《結一廬書目》:《王無功文集》五卷,舊抄本,原朱筠(朱笥河、朱竹君1729-1781,北京大興人,發起《永樂大典》輯遺書項目)藏書。
1《王無功文集》五卷,清乾隆間抄本,藏上海圖書館;無任何題跋、後人序文,僅錄《王無功文集序》大唐太常丞呂才序。
1《王無功文集》五卷同治陳氏晚晴軒抄本,藏國圖。此本前錄《王無功文集序》大唐太常丞呂才序。
1《王無功文集》五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清李氏研錄山房抄本,藏國圖。有校補。
這三個五卷本屬於同一源頭。《辛答》一詩,在三本目錄中皆作“辛苦”,而文中則皆改作《辛答》,明顯目錄是抄手筆誤,而三本必然是根據同一抄本,或者相互之間傳抄,才會保留這樣的錯誤。此外三本皆缺《河渚賦》、《獨居賦》、《孤松賦》、《登龍門憶禹賦》、《酒賦》五首。另外一個重要特徵,如張錫厚先生指出的,是李本和朱本保留宋代避諱缺筆習慣(如敬、恆、弘等,但陳本改了,可見五卷本之祖本應屬北宋中期以後)。張先生還指出,五卷本也失載三卷本所載詩文,李本據諸本補錄其中:《祭杜康新廟文》(李注據陸本補。三卷本皆載);《北山》、《過漢故城》、《益州城西張超亭觀妓》、《辛司法宅觀妓》、《詠巫山》;《詠懷》(據孫本)。而五卷本比三卷本和林抄本多出的篇目,下文將述。
國外藏本有:
敦煌殘卷,藏法國巴黎圖書館,P2819號。
《東皋子集》三卷,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明張燮輯刻本,有曹荃序[20]。
其他存本:
1明萬曆43-(1615)《醉鄉記》刻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可證明王績詩文有單行的現象[21]。
1甘肅圖書館藏《東皋子集》三卷,清道光孔氏嶽雪樓影鈔本。因未親見,故錄於此,猜測與三卷本丙類相似。
1《東皋子集》三卷,山西臨猗縣圖書館藏,清董文煥校並跋。此本據張錫厚《王績研究》應為二卷本,且已丟失。但張先生書是在1996年出版的,他得知此書必在此前,而中國古籍總目的項目始於1992年,終於2009年,期間或許抄本復現,不知個中曲折。
此外,王績集散見于自唐以來的書籍之中,古人筆記、類書或有摘錄,或摘取王詩文之義來作詩賦文,這些散見的資料也能幫助反映出王績詩文在抄本傳統之中的流傳,從中既可窺見抄本傳播的方式,也可瞭解後人對前人詩文的選擇。以抄本作為載體的作者、作品、抄本、讀者之間的有趣的關係。
現存版本關係示意圖
[1] 呂才序、《自撰墓誌》等皆持太原人說法,《新舊唐書》稱為絳州龍門人,詳細考辯見張錫厚先生《王績研究》,268頁,新文豐出版社,1996年。
[2] 王績,《王無功文集·五卷本會校》,韓理洲會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張錫厚先生《王績研究》,新文豐出版社,1996年。
[3] 《中國古籍總目·集部一》,第56頁,中華書局,2012年。
[4] 抄本現藏國家圖書館,南區古籍庫,編號10184。
[5] 筆者在國家圖書館查閱此書,上面並無校閱文字,故不能推知“影宋本”的面貌另外,且此“影宋本”此後再無出現。
[6] 不得知國圖此本藏書之來源,甚是苦惱。
[7] 張錫厚先生看過此目錄,又曾得知山西省臨猗縣圖書館藏有清彭元瑞抄本《東皋子集》二卷,清董文煥校並跋,可惜此書在圖書館搬遷新址時遺失了。後來在《中國古籍總目》中再次出現臨猗縣圖書館藏有《東皋子集》三卷本,見下文三卷本系統戊。
[8]比趙抄本少25,比孫本少26。
[9]見《王績研究》,張錫厚著,172頁,新文豐出版社,1996年。下文提到某些張氏觀點時,或不一一作注,皆引自此書。田曉菲亦贊同此觀點,見《誤置:一位中古詩人別集的三個清抄本》,《古典文獻研究》,2012,鳳凰出版社。下文引田曉菲觀點,皆自此文,或不一一作注。
[10] 見《王績研究》,張錫厚著,176頁,新文豐出版社,1996年
[11] 據莫旦《賦》的內容,我們可以判斷此處所列的詩文集,應為他當時所存的。詳參考本《賦》。
[12] 見蔣黼《王無功集後記》,羅振玉刻本。
[13] 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亦藏有“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明鈔本”,備錄於此。
[14] 曹荃,字元宰,生卒不詳,無錫人,明崇禎一年進士,後官至福建副使。這個本子的流傳較為複雜。此書最後有黃丕烈(1763-1825)手跋。據跋可知,此本本藏王鳴盛家,後歸黃氏。其實,王鳴盛(1722-1797)曾藏一抄本[14]及此刻本(前有藏書印),先後都歸王氏所藏。此兩本略異(刻本有增多,亦有脫落[14])。黃氏曾借吳翌鳳(1742-1819)家抄本,以墨筆對校此抄本,後又以朱筆校此刻本[14]。黃丕烈後,此書歸李芝綬(1813-1893)緘翁所藏,李氏亦作手跋於前。據跋,李氏曾借趙抄本[14]校對此本,並將抄本上“的然可信,徑改行間,有其兩通及可懂者,則記志下方···又繙《全唐文》重校一過,有其異同,書之上方”。今通檢全本,其所作批改有“行間增字”和“上方校注”的,這些內容與《全唐文》相同,並有《全唐詩》內容;有“行間徑改”和“下方校注”的,這部分與趙抄本同,這部分改注並不少。可見,曹荃本與趙抄本也是有所差異的。則可存疑曹荃本所據底本是否與趙本相同。李芝綬跋又說光緒年間從趙宗建(1824-1900)借得“王校本,倩佩書,宗弟將朱筆錄出”,不知此“王校本”是否王鳴盛之抄本。
[15] 從目前文獻所及,此《東皋子集》即應為焦氏本。
[16] 張錫厚說此本比趙抄本多一首,誤也。見《王績研究》,張錫厚著,177頁,新文豐出版社,1996年。
[17] 張錫厚認為此本是“充分吸收明人輯補王績佚詩重要成果的特點…是明人編定…”。
[18] 張燮,福建鎮江石碼人。
[19] 五卷本最早見於吳鳳岐手跋,後來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辯證》和萬曼先生《唐集敘錄》都有提及,可惜他們都沒有機會見到真本。
[20]《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卷四》,3a.
[21] 又如曹荃序明言“始余讀王先生醉鄉記···比卒讀東皋集,始知先生···”,《醉鄉記》單行,提供了一個想法,即王績的其他流傳極廣的單篇,也有可能單行。
《王无功文集》读后感(四):王绩生平及思想新证
摘要:王绩生平及思想研究,前人论述甚多,成绩斐然。但其在隋唐之际动乱中曾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为吕才序讳言,学界罕为注意,“三仕三隐”并不足以概括其生平。其思想转变自有根由、有迹可寻、脉络清晰,“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显然亦不足以概括其思想。本文姑妄从现存资料中重新梳理,补罅塞漏,以求其是。
关键词:王绩;生平;思想;新证
中图分类号: I206. 2 文献标识码: A
关于王绩的生平事迹,五卷本《王无功文集》吕才序、《全唐文》卷161及王度《古镜记》是最为原始的资料。新旧唐书、《唐才子传》、《唐诗纪事》等传记,多据吕才序而转传。
壹
王绩的早年行迹,吕才序云“年十五,游于长安”,又“谒越公杨素”。与杨素的对话里提到王通《太平十二策》(仁寿三年所献),且杨素死于大业二年(《隋书·杨素传》),《隋书·薛道衡传》云:“仁寿中,杨素专掌朝政,道衡既与素善,上(文帝)不欲道衡久知机密,因出检校襄州总管”,王绩谒见杨素时,宴中有薛道衡,且受两人同时褒奖,以情理度之,其时必在薛道衡被文帝猜忌外派为官之前,应是仁寿三年(603)或仁寿四年(604)。当时王绩“瞻对闲雅,辩论精新,一座愕然,目为神仙童子”,甚至敢当面直言质询杨素,未到二十岁就称誉士林,独步当时。由此可见,在仁寿末,王绩显然是积极求仕、渴望建功立业的。
《三月三日赋》:“余以大业四年,获游京邑,暮春三月,暂骋娱游,新停隐士之船,即赴群工(公)之席……不能默尔,聊为赋焉”。在大业四年前,曾有过一段隐居经历,故而以“隐士”自称。赋文结尾云“隐士船中药,秦王剑里铭”,以夏统曝药、秦王剑名(注:水心剑)之典,表明此时自己心清如水,无意于王侯霸业。从积极进仕到无意仕途,以及“弃襦频北上,怀刺几西游”,早年数度在仕、隐之间来回摇摆不定, 韩理洲《王绩生平求是》云:“该文铺张扬丽地描写了长安三月三日的良辰美景之后,深有感触地写道:「南渡桥边无数醉,东流水上几人醒」,只有「隐士船中药,秦王剑里铭」之类藏而不露的事物,才是永久的”,并把王绩推崇“归藏”思想归结为“经历多次干谒失败的产物”,恐怕过于简单。
仁寿末到大业四年之间,隋朝朝廷内部出现了极大的权力变动:仁寿三年(604)左右,薛道衡受文帝猜忌外派为官;仁寿四年(606),文帝驾崩;大业二年(606),杨素逝世。大业三年(607)底,薛道衡被召回京中留任秘书监,似有被隋炀帝起用的迹象。王绩在赋中以“隐士”自称,却在大业四年“暂停”隐遁、游京赴宴,很有可能与薛道衡被召回京任职有关。大业初年的政局变动,使王绩仕途“失路”,恐祸及身被迫“藏名”而选择隐遁,又因薛道衡回京,再次赴京。
《晚年叙志示翟处士》云:“失路青门隐,藏名白社游”,极有可能就是指这一段经历。青门,指长安城东门,指在京为官、求官生涯;白社,用隐士董京事,此处指民间、市井生活。王维《辋川闲居》有“一从归白社,不复到青门”之句,用法相类。但这与其说是“干谒失败”,不如说是“时运不济”。薛道衡归京,很快就因上书《高祖文皇帝颂》得罪隋炀帝,后数次忤逆、顶撞隋炀帝,早已不复当初“久当枢要,才名益显,太子、诸王争相与交,高颎、杨素雅相推重,声名籍甚,无竞一时”(《隋书·薛道衡传》)的情形。王绩对波云诡谲的政治风波有着敏锐的判断,大业四年时,恐怕早已看出薛道衡所面临的严重政治危险(大业五年薛道衡即因言被冠以悖逆之罪冤杀)。生性谨慎的王绩虽然“暂停”隐遁而赴京,但为了避祸全身起见,不打算贸然涉足政治漩涡中,自我放逐、避入山林,就不足为奇了。
吕才序云“(王绩)性简傲,饮酒至数斗不醉。常云:恨不生逢刘伶,与避户轰饮。因著《醉乡记》及《五斗先生传》,以类《酒德颂》。”从《三月三日赋》中流露的消极思想及《解六合丞还》云“但愿朝朝长得醉,何辞夜夜瓮间眠”,大业年间以“隐士”自称的王绩,有嗜酒放荡的行径是极为可信的。《醉乡记》云:“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职……仅与醉乡达焉,故四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厉,迄乎秦汉,中国丧乱,遂与醉乡绝”,指明只有太平盛世才勉强与醉乡通达,而中国丧乱之时便与醉乡隔绝,只有隐者方可遨游其中,文中歌颂醉乡之美是对黑暗现实的讽刺。这与《酒德颂》是借饮酒表达倨傲不逊、傲然世俗的态度,讽刺奔走利禄、汲汲钻营于宦途的缙绅处士,对当时黑暗腐败政治的概括和反映的主旨是一致的。此文背景与隋朝后期统治倾颓、吏治腐败是吻合的,也与王绩曾消极避世、以“隐士”自比的经历相符,《醉乡记》作于大业年间的隐遁时期,也是可信的,与《三月三日赋》中流露出“藏名”、隐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正是“有托而逃焉”的产物。
大业末①,王绩应举高第,授秘书正字。吕才序云“及为正字,端簪理笏,非其所好也,以疾罢,乞署外职,除扬州六合县丞”,唐随隋制,秘书正字(及校书郎)虽然只是九品小官,却是士子释褐官职之一,需要明经、进士、制举出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属于清官之流,颇受世人推崇。其任职经历对日后仕途影响重大,是公卿之途的起点。正字(及校书郎)是过渡性的官职,想要在仕途进一步发展就要迁出,留京城任职或转迁到地方任职。特别是唐代,迁任地方官职占大多数,主要担任县尉、主薄,或者县令、县丞;能留任京城的是小部分,却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②王绩主动乞署外职,“端簪理笏,非其所好”的理由恐怕不能解释其深层的心理动机。
《无心子传》云:“东皋子始仕,以醉、懦罢,乡人或讥之,东皋子不屑也,退著《无心子》以见趣焉”。这里的“始仕,以醉、懦罢”,显然是指大业末年罢扬州六合县丞之事。王绩数次出仕,仅有此次是因为“笃于酒德,颇妨职务”(吕才序)被屡次勘劾而归,符合“醉”、“懦”两方面的原因。该文里讲到“无心子寓居于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无喜色,泛若而从……俄而无心子者以秽行闻于王,王黜之,无愠色,退而将游于茫荡之野。……无心子曰:“尔闻蜚廉氏之马说乎?昔者蜚廉氏有二马。一者朱鬣白毳,龙骼凤臆,骤驰如舞,终日不释鞍,竟以艺死。一者重胫昂尾,驼颈貉膝,踶善蹶,弃而散诸野,终年肥遁。是以凤凰不憎山栖,蛟龙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洁以罹患,圣人不避秽而养生。”王绩以“无心子”自比,自云“拘之仕,无喜色,泛若而从”,以醉酒之名“自污”,宁愿作终年肥遁毫无用处的驽马,也不愿意作终日奔劳死于非命的良马。可见其对隋炀帝时的政治黑暗以及隋朝政权的日渐衰亡有着非常清醒的认知,于仕途并无积极作为之心,而是随波逐流、避祸全身的思想。罢官而归时,作《解六合丞还》,明确表示自己对功名利禄的淡薄,只想重返嗜酒放荡、纵情山水间的岁月。
罢六合县丞归后的事迹,吕才序没有提及。《旧唐书》云王绩从此隐居河渚,与隐士仲长子光结庐为邻,躬耕东皋,以琴酒自乐,直到贞观十八年卒。新唐书云隐居到唐高祖武德年间。《唐才子传》与新唐书此同。显然皆与其生平经历不符,皆误。《古镜记》虽然是小说家言,载“大业十年,度弟绩自六合丞弃官归,又将遍游山水,以为长往之策”,与吕才序所云罢六合丞归的事迹吻合,可信度比较高。《古镜记》载,罢官不久王绩便辞别长兄王度,从长安出发开始漫游,先游嵩山、箕山,然后经汴州、宋州(注:隋大运河通济渠沿岸重镇)南下江浙,遇潮出海后直入南浦,其后寻真至庐山等地,北归时“便游河北,西首秦路,还归长安”。晚年所作《赠薛方士》有“昔岁寻周孔,今春访老庄”之句,“寻周孔”似即指此次长游。途中所作的诗文亦多为“怀古伤今、感时伤世”,如《登箕山祭巢许》云“怀二子之高烈,背嵩岳而来游”,《祭关龙逢文》:“壮山河之旧壤,叹坟隧之余基”,《过汉故城》:“历数有时尽,哀平嗟不昌”,是对隋朝统治下江山动荡、社稷倾颓的无奈和悲叹。
贰
按《古镜记》载,王绩游历后返回长安,时在大业十三年夏六月。又,“数月,还河东”。正值隋末动乱之际,归还龙门不久,很快就再度出游。自云:“豺狼塞衢路,桑梓成丘墟。余及尔皆亡,东西各异居”(《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原因是家乡龙门陷于战火,无法安居。吕才序云“隋季版荡,客游河北。时窦建德始称夏王,其下中书侍郎凌敬,学行之士也。与君有旧, 君依之数月。……君遂去还龙门”,窦建德封“夏王”在武德元年(618)冬至,则王绩亦于此前后往依附凌敬,依之数月。
但记叙中有一点“蹊跷”几乎未为方家所注意。③吕才序云其离开河北后“遂去龙门”,但武德二年(619)前后龙门战火正燃,《旧唐书·卷二·太宗纪》:武德二年(619)十一月,“太宗率众趣龙门关”,与刘武周、宋金刚打仗,王绩是难以顺利回到家乡安居的。王绩在家乡逗留期间不足一年,倘只为避难而来河北,数月之后,龙门战火未停又匆匆再返,显然不符合情理。这段时期的踪迹看起来是难以考察,但相关诗文里透露的信息侧面证实了从事政治活动的隐晦事实。
《久客齐府病归言志》有“君王邸茅宽”之句,云“齐府”、“君王”,即“齐王”。王绩生前同期可称“齐王”者,只有隋朝杨暕、唐朝李元吉。然杨暕获封齐王在大业元年,其年隋都即迁洛阳,与诗中“羁旅别长安”不符,可见齐王是指李元吉。傅璇琮认为此诗作于武德八年秋,王绩久客齐王府邸(待诏长安时)病中思归而作。但王绩武德中应诏出仕后已是待诏(等待委任官职,亦领取官俸)之身,与“客居”身份不符。况且武德八年秋即言“病归”,焉得吕才序所云“贞观初以疾罢归”之说?云“久客”,其事必在待诏前,李元吉封齐王在武德元年,按之,只能是武德二年(619)离开河北之后。
由此推断,王绩武德二年(619)离开河北后的行踪,绝非吕才序讳言“遂还龙门”,而是前往太原,投奔李元吉。现存《辛司法宅观妓》一诗亦可为佐证。辛司法,应指辛澄。其人两唐书无考,所幸有墓志铭流传下来,生平经历颇为详细,其“起家以太学生”、“随明经举,武德二年任齐王府法曹”,任满后任瀛洲鄚县令。唐制,职官任期以三至四年为限(王府幕僚以三年为限),任满需另任他职,故辛澄在武德五年即出任瀛洲鄚县令,此诗绝不可能作于王绩“待诏”之后,亦足以作为王绩武德四年前便客居齐王府的佐证。
吕才序云“敬知君妙于历象,访以当时休咎,君曰:人事观之足可,不俟终日,何遂问此?敬曰:王生当要赠我一言。君曰:以星道推之,关中福地也。”由此可见,王绩对政治局势的变化及趋势是非常敏锐的。其少时所学的“占星望气”、“推卦演数”,并非简单的阴阳历数之术和观察星云气象,而是专注于钻研社会、政治问题,“预卜人事变化”的。值得注意的是,时李渊、李世民父子已在长安,齐王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李唐的大本营。王绩投奔李元吉,非为李元吉其人而是投奔李唐政权,这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故其离开河北时所云“关中福地”,即是从政治局势走向判断,不看好窦建德而看好盘踞关中的李渊,恐怕这才是他离开河北转投李唐政权的真正原因。
《在边三首》记叙了王绩在北方边地的经历,是五卷本里非常“特殊”诗文(注:三卷本无载):
其一
客行秋未归,萧索意多违。雁门霜雪苦,龙城冠盖稀。
穹庐还作室,短褐更爲衣。自怜书信断,空瞻鸿雁飞。
其二
羁旅滞胡中,思归道路穷。犹擎苏武节,尚抱李陵弓。
漠北平无树,关南迥有风。长安知远近,徒想灞池东。
其三
昔岁衔王命,今秋独未旋。节毛风落尽,衣袖雪霑鲜。
瀚海平连地,狼山峻入天。何当携侍子,相逐拜甘泉。
其中有“昔岁衔王命,今秋独未旋”之句,“王命”,按之生平经历而言,显然是指李元吉之命令。王绩有诗题曰《建德破后入长安咏秋蓬示辛学士》,证明其武德四年秋曾入长安(注:窦建德战败被押送长安在武德四年),而武德四年底已返回家乡龙门。而《在边三首》云“昔岁”、“今秋”,说明其在胡中逗留的时间超过一年,由此推定,《在边三首》绝不可能作于武德四年十月后,只能是武德二年(619)至武德四年(621)之间。
由“犹擎苏武节,尚抱李陵弓”等句可知,王绩在胡边是“衔王命”而去,随命出使胡中的。《晚年叙志示翟处士》又云:“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解纷曾霸越,释难颇存周”,霸越、存周,用的是纵横家子贡、周最的典故,子贡当年为保全鲁国纵横于各国间,太史公曰“子贡一出,存鲁 、乱齐 、破吴 、彊晋而霸越”;周最则利用秦、魏之间的矛盾保存了周国。王绩自云在武德年间的战乱中从事纵横、游说之事,又曰“衔王命”、“滞胡中”,则其出使的原因是“存周”,即“存唐”(太原)也。
考之史实,武德二年(619)三月,刘武周向南进攻汾州、晋州,并接受宋金刚“入图晋阳(太原),南向以争天下”的建议率兵两万南侵并州,四月,联合突厥,驻扎黄蛇岭(今山西榆次北),兵锋甚盛。刘武周有胡人势力支持,李元吉很有可能曾派使者团前去破坏其联盟或游说突厥支持李唐,王绩亦在出使的队列之中。《在边三首》的写作背景可能与此有关,似在武德二年四月之后。
由诗中推测,此次出使并不顺利,“萧索意多违”,谈判形势也日益艰难,王绩在胡中也过着“穹庐还作室,短褐更爲衣”的窘迫生活,但因为战火连绵导致书信中断、消息闭塞的原因,他尚有早日完成使命,“何当携侍子,相逐拜甘泉”的乐观期待。然而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李元吉兵败如山倒,刘武周接连攻克并州、介州,进逼晋阳。八月,李元吉已采纳宇文歆之计弃守太原(李唐发祥地),逃归长安。《在边》其二,似是得知李元吉逃归长安后所作。太原既已沦陷,李元吉也弃城而逃长安,王绩所为一切皆成枉然,并因此滞留胡中,故而自云“犹挚苏武节,尚抱李陵弓”,更发“思归道路穷”之叹。“长安知远近,徒想灞池东”,说明他此时是想要返回长安的。
武德二年(619)十月,刘武周攻陷绛州、浍州,十一月,“太宗率众趣龙门关,履冰而渡之,进屯柏壁,与贼将宋金刚相持”。此次战事持续时间很久,直到武德三年(621)二月刘武周溃败奔于突厥后,李唐才收复并、汾等旧地。《咏怀》有“桑榆汾水北,烟火浊河东”之句,桑榆,即日暮之景,烟火,即战火。汾水北,指汾河北岸汾州、晋州等地,河东,即指绛州、龙门、浍州等地。汾河北、河东地区战火缭绕,呈现出一片凄凉衰败之景,似是反映李世民与刘武周在汾河北、河东地区的长期相持战争对当地造成的毁灭和苦难。似作于武德三年(620)秋至武德四年(620)秋返回长安的途中。
王绩自胡中而归,一路漂泊辗转,历时数月,武德四年秋方入长安。《建德破后入长安咏秋蓬示辛学士》云:“遇坎聊知止,逢风或未归。孤根何处断,轻叶强能飞”,贾谊《鹏赋》:“乘流则逝兮,得坎则止”,王绩以木浮于水顺流则行、遇坎则止,比喻人生只能顺天委运,自己也无法说明为何会沦落至此,就像那漂泊无根的秋蓬,只能随风漂泊罢了。
《久客齐府病归言志》有“羁旅别长安”之句,可见是作于武德四年(620)秋返回长安之后,时逢李元吉随李世民征讨王世充(窦建德、王世充被灭,东都平定)新归。十月,(李元吉)加司空,加赐衮冕之服、前后部鼓吹乐二部、班剑二十人、黄金二千斤,正是加功行赏、春风得意之时。
久客齐府病归言志
君王邸茅宽,修竹正檀栾。构山临下杜,穿渠入上兰。
天人多晏喜,宾寀盛鹓鸾。玉舄镇花簟,金环□果盘。
斗鸡新市望,走马章台看。别有恩光重,恆嗟报答难。
沉绵赴漳浦,羈旅别长安。玄渚芦花白,黄山梨叶丹。
故人倘相念,应知归路寒。
诗中不厌其烦地描述齐王府邸的富丽堂皇及宴欢酒乐的热闹,全是一派春风得意的景象。王绩方遭大难无功而归,漂泊坎坷的经历亦导致心态变得消极,沉疴未愈,便以“久病”的理由辞归了。
古意六首(其六)
彩凤欲将归,提罗出郊访。罗张大泽已,凤入重云飏。
朝栖昆阆木,夕饮蓬壶涨。问凤那远飞?贤君坐相望。
凤言何深德,微禽安足尚?但使雏卵全,无令缯缴放。
皇臣力牧举,帝乐箫韵畅。自有来巢时,明年阿阁上。
《古意六首》是王绩诗文里不常见的咏怀组诗,是“见志”的,大体上都是表达决心归隐、远身避祸的思想。从诗意来看,似是记述辞归时受到故人追来挽留之事,王绩自比“彩凤”,自谦无德无才不足以承贤君的厚待,放弃大展宏图的机会只愿保全自身。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月,李世民和李元吉即要讨伐复据窦建德旧地的刘黑闼势力,也可能是王绩不愿再为前驱有关。
古意六首(其二)
竹生大夏溪,苍苍富奇质。绿叶吟风劲,翠茎犯霄密。
霜霰封其柯,鹓鸾食其实。宁知轩辕后,更有伶伦出。
刀斧俄见寻,根株坐相失。裁为十二管,吹作雄雌律。
有用虽自伤,无心复招疾。不如山上草,离离保终吉。
古意六首(其三)
宝龟尺二寸,由来宅深水。浮游五湖内,宛转三江里。
何不深复深,轻然至溱洧。溱洧源流狭,春秋不濡轨。
渔人递往还,网罟相萦藟。一朝失运会,刳肠血流死。
丰骨输庙堂,鲜腴藉笾簋。弃置谁怨尤,自我招此否。
馀灵寄明卜,复来钦所履。
诗中王绩以“宝龟”自比,剖析自身遭难的原因是“何不深复深,轻然至溱洧”,懊恼自己为何不继续藏名归隐,没有谨慎思虑周全,便轻然涉足政治。结果“一朝失运会,刳肠血流死”,差点招来丧身之祸(王绩滞留胡中、重返长安时期大概曾遭大难,几乎身死,故云“久病”、“但使雏卵全”),表达出对政治风险的极度忧虑。又以“翠竹”因为有用而遭到砍伐,山上绿草却因为无用而得以保全,告诫自己要谨记教训,不要重蹈覆辙。从这两首诗中不难看出,王绩归隐是“远祸避害”思想主导下“被迫”的消极选择,是“有用虽自伤,无心复招疾”的无可奈何,是仕途受挫和遭逢大难后的精神安慰。
《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注:薛收封记室参军在武德四年十月)云:“伊昔逢丧乱,历数闰当余”,闰,旧时历法,每四年有“闰”,从武德元年客游河北至武德四年底返回龙门,正是四年有余。
叁
武德五年(623)三月,朝廷下诏,令京官及总管刺史荐贤,被举荐对象有“岩穴幽居,草茅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者”(《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王绩其时在家乡龙门过着“东川聊下钓,南亩试挥锄”(《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见赠》)的生活,也在被征召之列。
《被征谢病》有“汉朝征隐士,唐年访逸人”之句,唐初只有武德五年(623)三月下诏令京官及总管刺史荐贤之事符合,此诗所作应指此事。从诗题及诗中内容来看,王绩自诩要“乐贫守道”,引用“刘公干卧病清漳”、“郑子真躬耕谷口”等典故,表达要含和养病、隐居求真之意,谢绝朝廷征召的。其不愿出仕的态度,在《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一诗中亦有反映。诗题云“见寻”,意为“寻访”,表明薛收是特意前来寻访王绩的。薛收封记室参军在武德四年十月之后,十二月即随李世民东讨,至武德五年(622)三月凯旋,以功封汾阴县男。两人投靠李唐政权时间相去不远,际遇却天差地别,“尔为培风鸟,我为涸辙鱼”是再贴切不过的形容了。诗中写两人相见多追叙故旧之事,“旧游倘多暇,同此释纷拏”等句,按情理度之,不似在薛收随李世民东讨途中,应作于武德五年(622)三月后。韩理洲以诗题曰“过”,认为薛收非专程探望王绩,而是因公路过其隐居之所,订其时为随李世民征讨刘黑闼往返途中。然“过”在古诗中非指“路过”,而是“拜访”,甚至可以指“应邀拜访”,如孟浩然《过故人庄》有“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之句,显然并非路过,而是赴约而往。诗云“何事须筌蹄,今已得兔鱼”,说明薛收有劝说王绩出仕之意,而王绩并未答应。更自比“朽木不可雕,短翮将焉摅”,流露出“人生讵能几,岁岁常不舒”的沉闷、抑郁之感。离别时也只是与薛收殷切阔叙,“旧游傥多暇,同此释纷拏”,意思是,如果你有空闲的时光,就来和我一起听北山僧讲解佛经,消除尘世的烦恼吧,消极遁世、不愿进仕的心态表露无遗。此处所提及的“北山僧”,即北山(即黄颊山)上永兴禅寺内的僧侣,王绩曾有礼拜之举。但佛家思想并不是王绩思想层面上重要的底色,现存诗文只有《游山寺》、《观石壁诸龛礼拜成咏》寥寥数首,内有“方希除八难,从此涤三灾”、“真如何处泊,坐费计人功”等语,是带有功利性的目的而非诚心皈依的信仰,是遁世、逃避现实的手段。
北山(黄颊山)、白牛溪,位于龙门东北数十里,明万历《河津县志·卷二·古迹》:“文中子洞,在黄颊山佛峪山脊,王思城记”,同卷《山川》又云:“白牛溪,在黄颊山,隋大业文中子居此溪”,证明此处乃文中子躬耕讲学之地。清光绪《山西通志·卷九十一·金石记三·碑碣》文中子讲堂碑条:“旧通志:黄颊山东岩石壁高四丈,中开罅。相距尺许,泉涌汇为池。循峪出,即白牛溪也。山上有永兴禅寺,明季山塌,古寺被压,即文中子授经地也,多断碑。”由此可知,黄颊山东岩有石壁,高四丈,王绩诗题《题黄颊山壁》即指此处,诗云“别有青溪道,斜亘碧岩隈”也与此描述相吻合。
春日山庄言志
平子试归田,风光溢眼前。野楼全跨迥,山阁半临烟。
入屋欹生树,当阶逆涌泉。剪茅通涧底,移柳向河边。
崩沙犹有处,卧石不知年。入谷开斜道,横溪渡小船。
郑玄唯解义,王列镇寻仙。去去人间远,谁知心自然。
《春日山庄言志》首句云“平子试归田,风光溢眼前”与《薛记室参军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云“东川聊下钓,南亩试挥锄”意同,应作于“躬耕东皋”即武德年间的归隐时期。“崩沙犹有处,卧石不知年”中的“卧石”,即指东坡上高四丈的“石壁”,“当阶逆涌泉”的“涌泉”,是指相距石壁尺许的“泉涌汇为池”之“泉”。“横溪渡小船”中的“溪”,即指白牛溪。吕才序所云“河渚东南隅有连沙磐石,地颇显敞”与诗中“崩沙犹有处”描述相吻合,薛收前来拜访,以“过庄”名之,即“山庄”也。《春庄走笔》云:“枕山通菌阁,临涧创茅轩”、《春日还庄》:“地形疑谷口,川势似河阳”等等描述,足可以证明其隐居之处是“坟陇寓居,倏焉五叶,桑榆成荫,俄将百年”的祖业,连山带谷。《中说·事君篇》:“(王通)子曰:“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在,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具抃粥,弹琴著书、讲道劝义自乐也。”王绩隐居之地,应是此处。石壁正位于东坡上,吕才序云“君又尝葛巾驱牛,躬耕东皋,每著书自称东皋子”是指这段经历。
王绩效仿先兄文中子王通隐居黄颊山、白牛溪,一方面因为身遭大难的原因,退归田园、含和养身,追逐求仙取道;另一方面,依然渴望有所作为,并没有放弃著书立说(如:《会心高士传》④)、续成《隋书》的理想追求,尚存遵循周孔制述、倾慕古代治国圣贤之心。其自云“仆亡兄芮城,尝典著局,大业之末,欲撰隋书。俄逢丧乱,未及终毕。仆窃不自揆,思卒余功,收撮漂零,尚存数帙”,故而修书向陈叔达借其私撰《隋纪》以补缺参考,致力于整理、续修王度未撰写完毕的《隋书》。在《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中,形容陈叔达是“应以左貂右蝉,荣冠东省,掌壶负玺”,据《汉官仪·卷上》云:“侍中,左蝉右貂”、《后汉书·舆服志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璫,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可知,此书作于陈叔达任侍中时期,即武德四年至贞观元年期间,亦即王绩武德年中的归隐时期。陈叔达《答王绩书》提及“是以薛记室及贤兄芮城,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览,真良史焉”,王绩之兄王度大业八年曾奉诏修撰《周史》⑤,《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前代史》:“至(武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诏:……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可修《周史》”,陈叔达武德五年底奉诏修撰《周史》,“研览”前人撰述,亦乃事理之必然。由此亦可推定,借《隋纪》之事是在武德六年左右。其时,王绩尚在家乡欲续成王度遗作《隋纪》,并未应诏。
《新唐书·选举志下》:“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有司移符州县,课人赴调,远方或赐衣续食,犹辞不行。至则授用,无所黜退。”移符,朝廷因事遣使持符下达命令,课人,派遣督促;朝廷征召的力度、隆重可见一斑。《被举应征别乡中故人》以“烧山出隐士,治道送征君”、“使君留白璧,天子降玄纁”比拟初唐“征隐”的隆重,也非毫无由来的夸张。
王绩武德六年后出仕的具体缘由,已不可考。从其归隐乃身遭大难的客观原因及“远祸避害”思想主导下的消极选择和精神安慰,及内心依然抱持着并未熄灭的欲有作为的渴望,在形势有所变化之时,“山鸡终失望,野鹿暂辞群”,背弃先前的“归隐”宣言选择出仕,想要在天下渐定时有所作为,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陈叔达大业年间任绛郡通守,《答王绩书》有“叔达亡国之余,幸赖前烈,有隋之末,滥尸贵郡”之句,《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云“不与骄期,遂忘昔时之好耶”,可以推定,王绩与陈叔达两人交情始于大业年间,且非泛泛之交。吕才序云“武德中,诏征,以前扬州六合县丞待诏门下省”,又云“时省官例日给良醖三升”、“(王绩)曰:待诏俸殊为萧瑟”,可见王绩待诏期间是享受官员待遇、有官俸在身的。按之,官员的征用、授职乃中书省吏部有功司的职责,此云待诏门下省,时陈叔达正是门下省侍中, 又云“侍中江国公,君之故人也。闻之曰:三升良酝未足以绊王先生也。特判日给王待诏一斗,时人号为斗酒学士”,受到陈叔达特批的超规格待遇,从其应诏情况来看,可能与陈叔达的推荐有直接关系。《新唐书·卷一〇二·令狐德棻传》云:“方是时,大乱后,经藉亡散,秘书湮缺,德棻始请帝(高祖)重购求天下遗书,置吏称录。不数年,图典略备。”武德中开始官修史书,且备略天下遗书,王绩亦有欲续成《隋书》选择出仕之可能。
武德六年后应诏,韩理洲《王绩生平求是》云:“所谓待诏,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等待委任。王绩这次等待委任拖得时间颇长。《集序》、《新唐书·本传》、《唐才子传》均云,他一直待诏到贞观初。……由于数年待诏而不得委任,所以……太宗贞观初年,王绩又罢归了。”方家亦多以此说为是。然而,王绩《自撰墓志铭》云“起家以禄位,历数职而进一阶”,提及自己的品阶是曾进一级的。品阶是指官吏级别高低的级别,而不是具体官职,授职虽然是比照品阶而授,但可以高于或低于品阶,不影响俸禄待遇。唐朝规定,凡是当朝官员,都必须经过四次考课(高祖称帝之初沿用隋朝考课,后逐渐完备)。每年举行一次小考,三年举行一次大考,三品以下官员由吏部考功司考核,对当年应考官员的功过行能,按照上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三等(中上、中中、中下)、下三等(下上、下中、下下)进行评定。考核结果直接影响到官吏的俸禄,并成为晋升或降职的主要依据,如果四年皆考“中中”,可以进一阶,提高散官品阶。考之生平,自然只能是武德中待诏出仕期间。况且,《新唐书·选举志下》亦云:“(应诏)至则授用,无所黜退”,在“士不求禄,官不充员”的情况岂有弃而不用之理,王绩亦是“至则授用”无疑。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初年考核非常严格,《唐会要·考上》云:“贞观六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臣窃见流内九品以上,令有等第,而自比年,入多者不过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在九等考核中,官员一般都不超过中上等,上下等及之上连一个也没有。故王绩虽自谦“免责而已”,实际上期间的表现是比较积极的,绝非好酒误事之徒。此次出仕历时数年,吕才序云“贞观初,以疾罢归”。
肆
《答冯子华处士书》有“所恨姚义不存,薛生已殁”之句,薛收逝于武德七年,此作必在其后。文中又云“吾所居南渚有仲长先生,结庵独处三十载”,再按,《仲长先生传》云“开皇末,始结庵河渚间”,且以开皇二十年下推三十年为贞观四年,即此文应是贞观元年至贞观四年间所作。文中“至于乡族庆吊,闺门婚冠,寂然不预者已五、六岁矣”,此句曾引起方家争议,韩理洲、夏连保据此推测王绩此时已隐居河渚五、六岁,张大新则以后文云“近复都庐弃家”,认为“不预家事不等于弃家隐居”为由,认为当作于贞观四年。贞观四年上推五、六年是武德七、八年,正好是王绩在京待诏、任职时,此句前云“家兄鉴裁通照,知吾纵恣散诞,不闲拜揖,糠比礼义,锱铢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务”,“至于”表示递进关系,“乡族庆吊、闺门婚冠”皆属“家务”,正因为“以俗外相待”才“不拘以家务”,自然不可能从任官途中时算起的。王绩武德五年隐居不欲应诏,以此时计起,下推五、六年是贞观元年、二年。文中又有“春秋岁时,以酒相续”之句,则其结庐河渚至少近一年了,此文应作于贞观二年。由此反推,王绩退隐当在贞观元年。
王绩贞观元年退隐的缘由,亦不可考。从《答冯子华处士书》所云“吾比风痹发动,常劣劣不能佳”来看,吕才序云“以疾罢归”,王绩身体不佳,的确是一个重要原因。亦有说法是玄武门事变引起朝野倾轧、惊恐不安,“及贞观之始,诸贤皆亡”(魏征语),曾入客齐王府的经历使秉持避祸全身思想的王绩选择退隐。且许多政务亦似因朝局动荡而停摆,如《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前代史》:“(修史)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陈叔达亦在贞观元年因事被罢官,这些比较复杂的政治因素可能都是导致王绩贞观元年退隐的客观原因。
吕才序云:“贞观中,京兆杜之松、清河崔善为继为本州刺史,皆请与君相见,君曰:奈何悉欲坐召严君平耶?皆不见”。杜之松招王绩出仕“讲礼”的事,见《答刺史杜之松书》、《重答杜使君书》。王绩断然拒绝出仕,但杜之松所问之礼在回信中详细答复,《重答杜使君书》云:“某昔在隋末,又尝见诸贤讲论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编诸贤之论,继诸对问,今录此篇附往,幸详之也”。王福畴撰《王氏家书杂录》提及,贞观初,王凝为监察御史时,在御史大夫杜淹(卒于贞观二年)的建议下,曾求薛收、姚义等门人所缀《中说》一百余纸,“大底杂记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则蠹绝磨灭,未能诠次”。《中说》原始稿本是隋末王通与弟子间的对话纪录,王绩云“编诸贤之论,继诸对问”,即指王凝在贞观初开始收集《中说》原始稿本并整理、编纂成书。家兄御史,即指王凝,“诸贤之论”是指《中说》,此以“家兄御史”语之,可以推定,《重答杜使君书》作于王凝犹任监察御史时,即贞观元年至贞观五年间,恰在退隐归家不久。
对自许甚高的王绩来说,杜之松此举与其说是雪中送炭、对他仕途潦倒的宽慰,不如说是对他的嘲弄和奚落,显得他的避俗遁世、狂傲不羁是仕途受挫后的故作姿态,这极大地损伤了他作为世家弟子的人格尊严。故王绩“闻命惊笑,不能已已”,云“欲令复整理簪屦,修束精神,揖让邦君之门,低昂刺史之坐。远谈糟粕,近弃醇醪,必不能矣!”,又云“去矣君侯!无落吾事!”,毫不留情地表达了恼怒。《读真隐传见披裘公及汉滨老父因题四韵》似为此事而作,其云:“被褐延陵径,耕田汉水阴。由来骄击壤,何处视遗金?季子停骖谢,张温下道寻。世人无所识,谁知方寸心!”王绩以“披裘公”自比,把杜之松伸来的“橄榄枝”视作“遗金”,披裘公对延陵季子云:“何子居之高而视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而薪,岂取金者哉!”亦是王绩借以自比斩钉截铁拒绝杜之松相招的倨傲姿态,表示自己绝非沽名钓誉、邀名取禄之徒,标榜贫贱而志不短的品质。
也许是受到仲长子光先生推崇老、易的感染,也许是同气相感,《答冯子华处士书》云:“床头素书数帙,庄、老及易而已。过此以往,罕尝或披”。与武德年间的归隐相比,此次归隐是伴随着儒家理想的完全寂灭,王绩也不再追慕古代圣贤、渴望有所作为,不再钻研、追求“周孔制述”,《春庄走笔》:“自觉勋名薄,方知道义尊”,老庄无为、出世思想成为全部的精神支柱,这是其思想上的最大的转变。
此次退隐时间较长,吕才序云“邻渚又有隐士仲长子光,服食养性,君重其贞洁,愿与相近,遂结庐河渚,纵意琴酒,庆吊礼绝,十有余年。”王绩结庐河渚在贞观二年,庆吊礼绝始于武德五年,此云“十有余年”,则其再度出仕或恢复“乡族庆吊、闺门婚冠”往来,当在贞观十五年前(武德五年下推二十年)。
伍
《游北山赋》,吕才序及新唐书等均未提及,旧唐书则云“尝游北山,因为《北山赋》见志”。此文内容较长,文中提到王通死后门人弟子“忽焉四散,于今二纪”,王通逝于大业十三年(618),下推二纪(注:一纪十二年),即贞观十五年(641)左右。
文中对生平经历进行追忆:
忆昔过庭,童颜稚龄。何赏不极?何游不经?……天未悔祸,遭家不秩。子敬先亡,公明早卒。余自此而浩荡,又逢时之不仁。天地遂闭,云雷渐屯。与沮溺而同趣,共夷齐而隐身。幸收元吉,坐偶昌辰。容北海之嘉遁,许南山之不臣。养拙辞官,含和保真。岂若冯敬通之诽世,赵元淑之尤人。殷臧耻贱,憔悴伤贫。操井臼而无乐,历山河而苦辛。岂如我家生事,都卢弃置。不念当归,宁图远志。坐青山而非隐,游碧潭而已喜。
前云“容北海之嘉遁,许南山之不臣”,后云“养拙辞官,含和保真”显然是指贞观初的退隐。表示自己不似冯敬通、赵元淑“诽世、尤人”,为身处贱、贫的处境而忧虑憔悴,躬耕不乐、出游苦劳,我的打算是统统弃置,“不念当归,宁图远志”(此典出自《三国志·蜀志·姜维传》,裴注引孙盛《杂记》:“初,姜维诣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求当归”,比喻图谋建功立业而不愿意返回故里)。王绩贞观初退隐后曾弃置“井臼”、“山河”而选择“远志”,说明其曾有离家远游甚至出仕任官的举动。后文则讲述此刻游历北山的心境:“旧知山里绝尘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时返,仲叔长游遂不来”,子平指向长(字子平),隐居不仕,好通老、易,与北海禽庆游历五岳名山不知所终;仲叔指闵贡(字仲叔),征而不就,客游四方。王绩以此自况,暗喻此文乃归乡后再度游历北山之作。
吕才序云:“贞观中,以家贫赴选”,王绩家境颇为优渥,“河渚间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顷”,隐居后亦有“奴婢数人,足以应役”,可见是远远谈不上“贫困”的。因此,其贞观中赴选的真实原因历来争议较大。其诗《性不好治产兴后言怀》及诗文里以“颜回乐道”、“原宪守贫”自喻,以及《戏题卜铺壁》云“不应长卖卜,须得杖头钱”的情况,足可证明王绩躬耕期间的生活虽然不算贫困,亦并非富裕,只是自给自足而已。倘或注意到“欲定长往之计,而困于贫”,及《游北山赋》中隐晦提到“不念当归,宁图远志”的打算以及“子平一去”、“仲叔长游”的自比,大抵可以勾勒出,王绩贞观中出仕的原因是外出长游期间或打算外出长游时身无余资所致。
王绩嗜酒放荡,由来已久。《答冯子华处士书》云:“琴歌酒赋,不绝于时,时游人间,出入郊、郭……箕踞散发,与鸟兽同群,醒不乱行,醉不干物,赏洽兴穷,还归河渚”,可见在与仲长先生相伴结庐河渚时,王绩常出入郊、郭,以酒德游于乡里。吕才序云:“或乘牛驾驴,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动经数日。往往题壁作诗,好事者寻录讽咏,并传于代”,亦似指其“酒德游于乡里”之事。
过酒家五首
洛阳无大宅,长安乏主人。黄金销欲尽,只为酒家贫。
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
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
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倚炉便得睡,横瓮足堪眠。
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
《过酒家五首》首句提及的地名即是洛阳、长安,又以“黄金销欲尽”比之,并不像乡间郊、郭普通酒馆的情景,而是大都市高档酒楼、酒筵的奢华气象,有多少金山、银山也会被挥霍殆尽。反映了王绩晚岁“醉饮无节”时,曾到过长安、洛阳这样繁华的大都市,绝非出入附近的“郊、郭”而已。《过酒家五首》正是反映王绩钻进酒肆中沉醉不归最后费尽身上所带钱财的过程,从其一所云“黄金销欲尽,只为酒家贫”,到其五“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颇有“千金买一醉,取乐不求余”的落拓不羁。
这也可以解释王绩赴选后苦求太乐丞之职的行为。吕才序云:“时太乐丞有府史焦革,家善酿酒,冠绝当时。君苦求为太乐丞,选司以非士职,不授。君再三谢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浊,天下所知。不闻庄周羞居漆园,老聃耻在柱下也。卒授之”。太乐丞之职是与“清流”相对的“浊官”。“清流”起源于汉末在野士人,用以和当朝“浊流”相对,随着在野士人入仕而将这个概念带入官场之中。魏晋以来,“清官”逐渐演变为豪门氏族的标志,形成官制的“流品”区分,知识分子皆以能担任清官为荣。南朝、北魏时,明确规定官职的清浊用以铨选,唐代官制将魏晋以来的“清浊”观念(概念上)逐渐加以制度化,官职清浊是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王绩求任“浊官”自然非为仕途积极进取而来。其自云“此中有深意”、“不闻庄周羞居漆园,老聃耻在柱下”,是效仿“庄周居漆园、老子伏柱下”的做法,在朝廷里作隐士之意。吕才序云“数月而焦革死,革妻袁氏,犹时时送酒。岁余,袁氏又死。君叹曰:天遒不令吾饱美酒。遂挂冠归”。任太乐丞不足两年,因焦革、袁氏皆逝,王绩无酒可饮,便又辞官了。
《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开篇云“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韩理洲以题云“在京”认定此诗是在长安多年、年齿较长时所作,且以武德中待诏数年符合“旅泊多年岁”,认定作于贞观初罢归时。旅泊,意为旅途中行舟暂泊,后引申为“飘泊”之意,在朝任官不得志也称不上“飘泊”,王绩贞观初不过四十岁左右(按仁寿三年为十五岁推断,贞观元年方三十九岁),称“老去不知回”颇为牵强。此诗应是王绩晚年外出长游期间所作,符合“旅泊”之意。“在京”不一定指在京多年,而是在外长游多年在京逗留期间忽逢乡人而引起思归之情,故云“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莱”,按其履迹似是辞太乐丞时。
王绩晚年出游、任太乐丞、返回龙门的具体时间,现已不可考。但以其结庐河渚的原因推之,出游似是仲长先生逝世后。诗以“旅泊多年岁”名之,出游时间应长达数年,《游北山赋》是其归乡后不久再登北山时所作,则出任太乐丞应在贞观十三年左右。
陆
贞观十五年左右,王绩旅泊多年后因思乡而返故里,不久即再度游北山,以《游北山赋》见志。在《游北山赋》中,不但再次否定早年求仙取道虚无缥缈的神仙理论,并且体现思想上再次新的转变:即不但超脱周孔之圣道,亦不复追求隐士之虚名,“觉老释之言繁,恨文宣之技痒”,转而追逐“形神两忘”、“物我俱在”的境界。
《五斗先生传》云:“(五斗先生)尝言曰:“天下大抵可见矣。生何足养,而嵇康著论;途何为穷,而阮籍恸哭”,在文中批评了为养生著述的嵇康,甚至摆脱生死观念的束缚,表明远离生世之扰、摆脱万物之累的决心,其必在晚年放弃求仙后所作,绝非吕才序所云“大业末”。文中云“万物不能萦心焉”、“遂行其志,不知所如”之志,正因为命非善求可得,途亦无谓穷通,来不可阻,去不可留,因此就没必要感慨伤怀,转而追求“昏昏默默”,委身自然、物我两忘,所以便连“穷途之哭”的阮籍也受到批评了。但这是借助“酒”来追逐的,“长醉不醒”才能“不知所如”。《五斗先生传》云“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酒成了其最后的精神寄托,追求解脱的方式和途径。吕才序云“晚年醉饮无节,乡人或谏止之,则笑曰:汝辈不解,理正当然”,理在此意。
然正因为需要借助酒来超脱,说明其并未能真正达到豁达、昏默的境界。怀才不遇的抑郁、生不逢时的遗憾,是伴随终生的,无法靠理智去弥补和消除的。仕途理想失落于大唐盛世的孤寂,又让他的抑郁悲愤与时代主流格格不入,似乎是毫无价值的。《晚年叙志示翟处士》云:“晚岁聊长想,生涯太若浮”,“自有居常乐,谁知身世忧”,其中的纠结和煎熬是难以找到共鸣的,《阶前石竹》正是这种思想困境的反映之作。
阶前石竹
上天布甘雨,万物咸均平。自顾微且贱,亦得蒙滋荣。
萋萋结绿枝,晔晔垂朱英。常恐零露降,不得全其生。
叹息聊自思,此生岂我情。昔我未生时,谁者令我萌。
弃置勿重陈,委化何所营。
咏竹,在其他诗人那里多为赞赏其高洁不屈的节气,王绩却借石竹自比,流露出造化无常、厌世消极的情绪:“叹息聊自思,此生岂我情!昔我未生时,谁者令我萌!”迷茫之中更是饱含着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诘问:既然造物主亦给予石竹甘雨滋荣,为何又舍弃它?越是想要超脱,就越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只能“古人则难与同归,纷吾则此焉将老”,在山水的慰藉中度过余生。《自撰墓志铭》云:“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最终不可避免地遁入老庄的虚无思想里以期获得灵魂的自由。贞观十八年(644),“预知终日”的王绩在写下《自撰墓志铭》后不久,就与世长辞。
注释:
①王绩应举及第时间,诸家尚有争议。吕才序云“大业末”,两唐书云“大业中”,傅璇琮按《隋书•炀帝纪》大业十年五月始置“孝悌廉洁举”,订其应制及第在是年(《文史》第八辑《唐代诗人考略》)。韩理洲据《古镜记》载“大业十年,度弟自六合丞弃官归”,认定“一年之内闪电式经历这么多曲折不合情理”,订为大业中(《文史》第十八辑韩理洲《王绩生平求是》)。张大新据《古镜记》载“大业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至度家,弟绩出见之”认为王绩大业九年尚在家乡河汾而否定韩说。今究之,王度大业八年台值时尚带宝镜,其年冬为著作郎,文中并未谈及其有归乡之举。此云“度家”当在京城,非在河汾。在尚未有确切资料证实之前,订为大业十年为宜。
②有学者统计,校书郎及正字,唐代迁出官职可考的两百五十余人,能继续留在京城任职的只占三成,转迁地方任职的占七成。
③朱刚注意到“遂去还龙门”的蹊跷之处,然却推测为“扶隋反周”,王绩仕隋时为“避祸全身”自污,毫无作为,又岂会在隋朝倾覆之际为之奔走呼号?况且后两度仕唐,更云唐初为“王途渐亨”,绝非隋朝遗老,这推测显然与王绩生平经历及对隋朝态度相抵牾。(详见朱刚《王绩生平新考论》,《渭南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④吕才序云:“君又著《会心高士传》五卷”,今不存。但《王无功文集》中的卷五杂著部分,有十九首类似四言诗的杂文,韩理洲认为它们是“《会心高士传》的‘赞语’。从这十九首杂文来看,多为歌颂帝皇将相、杰出人物之传记,颇有推崇周孔之意,从其生平经历及思想阶段来看,应作于武德年间归隐时期。
⑤《古镜记》载,“其年(大业八年)冬,(度)兼著作郎,奉诏修撰国史,欲为苏卓立传”,恺刻本、四库全书本作“国史”,明沈氏野竹斋本作“周史”,据李剑国文考证应以“周史”为是(详见李剑国《“国史”、“周史”辨——王度〈古镜记〉的一处异文》,《书品》第五期)。
参考文献:
1.王绩著.韩理洲校点:《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康金声、夏连保:《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3.韩理洲:《王绩生平求是》.《文史》第十八辑
4.韩理洲:《王绩诗文系年考》.山西:山西大学学报,1983
5.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宁:辽海出版社,1998
6.杜海斌:《唐〈辛澄墓志铭〉考释》.陕西:唐史论丛,2014年01期
7. 朱刚:《王绩生平新考论》,陕西:渭南师专学报,1994年03期
8. 张大新、张百昂:《王绩三仕三隐补辨》,唐代文学研究学会第四届学会论文集,1989
9.(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10. (宋)宋祁、欧阳修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11. (唐)王通撰:《文中子中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读书一点感想,同无处可发,聊以自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