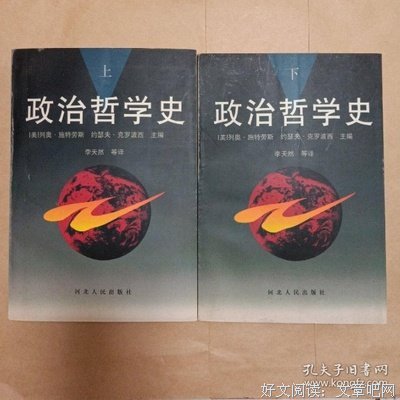《政治哲学史(全两册)》读后感1000字
《政治哲学史(全两册)》是一本由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著作,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32开图书,本书定价:46.9,页数:1112页,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政治哲学史(全两册)》精选点评:
●张广生说,什么样的自然就有什么样的德性……
●翻译不佳
●重新拿出来读
●@西方政治思想史 从修昔底德到卢梭
●翻译还不如我呢...
●上课要读的,不得不读的,这个版翻的、印刷都挺糟糕的。
●哎总觉得施特劳斯的文笔没有萨拜因有灵性,不过够朴实
●看到大家都吐槽翻译我就放心了
●一年多了,了结你
●和萨拜因的那个版本对照着
《政治哲学史(全两册)》读后感(一):国内唯一的译本
译本很一般.施特劳斯的语言不好翻译.但这是国内唯一的译本,尽管水平很差,但这本书是施特劳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译本只能给三星甚至两星,但书必须给五星.
尽管自己很多没有读懂,但它的重要性无庸置疑.
《政治哲学史(全两册)》读后感(二):从相对主义到新蒙昧主义
/ 晓波
美国杰出的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 1899-1973)认为,西方陷于现代性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东方共产主义的威胁──尽管共产极权成为覆盖半个世界的暴政;而是来自西方自身的内在的信仰危机:“西方,在其最高知识权威影响下,不再相信自己、自己的目的、自己的优越之处。”也就是相对主义的盛行。在国际政治层面,西方知识界不再相信自由民主具有普世的价值,而代之以与邪恶国家和平共处的现实主义。
施特劳斯一反西方知识界的左倾主流思潮,对政治理论中的“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作出尖锐批评:相对主义的实际结果,不仅在于使西方容易受到外部攻击,更包括西方内部的自由民主向随意的或墨守成规的市侩作风退化──不再相信自由主义及其制度安排具有引领人类历史发展的合理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相对主义是愚民的现代蒙昧主义:
2,相对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在哲学上是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在科学上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重估”并不等于“泯灭”,“相对”并不等于“怎么干都行”一样,特别是在自由与奴役的制度对峙上,只能坚持单一而完整的西方核心价值。因为,如果相对主义将自身的原则贯彻到底,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使相对主义绝对化,不但泯灭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联系,而且否定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一个社会的基本公德,也就等于否定了人类在何为政治上的正义和非正义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的任何可能,甚至连“奴役邪恶”的制度常识都被相对掉了,人的行为和国家的行为便失去了共同的底线,机会主义和绥靖主义的大行其道的时代就将降临,其现实结果必将是纵容邪恶政权的为所欲为。事实上,当爱因斯坦本人由对自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的关注时,其价值选择恰恰不是相对的,而是明确反对一切奴役制度和极权主义。
3,随着现代科学的兴盛、政教分离和基督教权威的边缘化,科学主义崇拜逐渐成为西方精神的另一副毒药,社会科学过于依赖自然科学方法,甚至沦为“实证主义”的奴仆。同时,科学主义也被无神论的极权政权所利用,沦为实施“信仰垄断”和“精神迫害”的工具。虽然,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会有所补益,其经验观察、试验证实和量化标准,皆能增强社会科学的精确性和客观性,然而,由于二者的研究对象──无伦理无精神的自然和有伦理有精神的人类──的不同,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必然有其界限,也就是人类伦理的界限。换言之,无视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也就必然忽略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和人的伦理行为的界限。同时,迷信自然科学方法,必然会贬低大量非科学的人文知识,使那些对人类的公共生活和价值选择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人文遗产──神话、宗教、伦理、意识形态、甚至哲学──被排除在政治学之外,最终形成了“自然科学方法论拜物教”。
人类在科学上的进步,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伦理上社会上的进步,道德蒙昧主义会在每个时代复活,古代有神学迷信,启蒙时代有理性迷信,现当代有科学迷信,而当代世界中最极端的“唯科学主义”,莫过于共产极权的无神论政权。神五上天和人权入狱,就是当代的科学进步和道德蒙昧主义之间的悖论的最新证明。
2004年1月6日于北京家中
《政治哲学史(全两册)》读后感(三):为什么走向施特劳斯
还要诉诸于哲学:为什么走向施特劳斯
看来中国的民间的一项知识分子,又开始在西方哲学中寻找营养和救世良方了。施特劳斯,也许会给人一些启迪。
最初听到施特劳斯是经由魏朝勇博士的介绍,后来我在刘小枫教授主编的《经典与解释》文丛中,阅读了坎特教授所著的题为《施特劳斯与当代解释学》的文本,对其中施特劳斯发现的古老的写作艺术印象深刻。其时已经是临近经济学考试的时候了,虽然非常有继续阅读施特劳斯文本的想法,但还是“刚开头,就煞了尾”。而更重要的是,我其时正在休谟的绝对怀疑的咒语里沉沦,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一时导致了价值和伦理的丧弃,也并不认为现代还有什么思维方式可以解决自己的困惑(后来海德格尔的论断证实了我的困惑)。及至漫长的考试结束,我从图书馆借出了基督教神学的论著,是要求诸信仰填充可怕的虚无吗?事情似乎到了要最后解决的时候了。
也是在那批借出的书目中,就有阿兰·布鲁姆的《巨人与侏儒》,而我之所以选了这本书,原以为那是一编文化论辑,一读而已。然而当我阅读完布鲁姆教授对于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别具一格的解读之后,我立刻读完了他《西方文明》、《自由教育的危机》等一系列才华横溢的论著。这个时候我才返回书的开篇去阅读了那篇他献给自己已故的恩师的文章——《纪念施特劳斯》,一颗伟大的心灵在布鲁姆教授虔诚的叙述下展现在我面前。
施特劳斯是谁?这种发问方式似乎在借鉴刘小枫教授在《尼采的微言大义》开篇的惊人一问。然而这样的提问方式在当今的学术语境下是必要的。即便是对于我们国人解读、引证了近一个世纪的尼采,又有多少真正“像作者那样理解自己作品”的文本呢(学人们大都成了“你们知识分子”,实际上构成了“当代大多数人的敌人”,重新开始认真提问“尼采是谁?”其实是当代最严肃的提问方式)?更何况对于那个一生都在默默解读西方经典的施特劳斯,那个名字从不见诸当代所谓“思想家”行列的施特劳斯。
布鲁姆在《纪念施特劳斯》的尾声说“下一代人如何评价我们,将取决于我们如何评价施特劳斯”。同为施特劳斯弟子的法肯海姆认为:“也许将来会有一个时候,海德格尔之所以被人们记住,只是因为没有他,施特劳斯就不会成为施特劳斯,也不会成为这样的施特劳斯”。可以想象施特劳斯是怎样的思想家,我们所有的当代人,甚至海德格尔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要成为施特劳斯的注脚。事实上,只要真正瞥见施特劳斯那博大精深的思想的一部分,我们就会认为布鲁姆和法肯海姆的评价是严谨和恰如其分的。如果有限的城邦的“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恰如其分的东西”,对施特劳斯的评价是与正义相关的,而不是远远在后的学术,更与名誉无关。
毋庸质疑,当代真正的思想家都在思索现代性的问题,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当代思想必然的使命。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还是与哈贝马斯持相同观点的思想家们,都没有能够获得一个超然于现代性的视野。施特劳斯孜孜以求的就是要超越现代性的樊篱,开启古典的西方精神世界。“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古代人和现代人之争这段公案必须重新开审”。现代性的根本逻辑是什么:是自笛卡儿肇始的主体形而上学?还是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施特劳斯敏锐地看到这只是问题的表面,现代的真正逻辑在于现代哲学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反叛。最彻底的现代性就是最彻底的虚无。现代的自由主义已经堕入了“唯法律主义”的深渊,西季威克所说的西方近世伦理概念是“准司法或法律主义的”是有先知性的。私人领域的“诸神冲突”已经导致了对正义的消解。那些主张恢复公共领域的诸如哈贝马斯这样的思想家们,实际上无法通过主体的重建或类似主体间性的构建来达致正义。事实上话语民主正是施特劳斯所批判的现代哲人的“知性真诚”。历史主义的观念经由康德、尼采到海德格尔演绎到极端,后现代主义把这种观念完全展现出来,现代也就走到了彻底的虚无。施特劳斯深受海德格尔的影响,我认为和海德格尔批判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力主回到上古世界是分不开的。但是施特劳斯反对其“前苏格拉底路向”,认为诗化哲学企图跳过政治共同体而直接进入纯真的境界是不现实的(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注56)。在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中,古典政治哲人的典范只是那个成年的苏格拉底,那个作为雅典城邦公民的苏格拉底,哲人的癫狂和锋芒被掩藏起来。但施特劳斯没有明确说明的是:要求哲人重返自然洞穴是为了保护哲人对神虔诚的模仿,还是为了保护政治社会的意见性?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离善的生活已经不太遥远了。
施特劳斯已经把我们从积重难反的现代灾难带回到了某个离“意义”不远的地方,生存重新变得严肃可能而高贵起来。谁瞥见了施特劳斯,就再也不必在休谟和后现代的诅咒中沉沦,再也不必在与现实生活的高度紧张中体味灵与肉的断裂。我所质疑的虚假生活世界被施特劳斯所证实,自己身处学术与文化的中心生产机构(大学),其实只是身处“第二层自然洞穴”的最危险地带而尚不自知,忍耐着由生命和文化自觉感应到的虚无和不义所带来的痛苦。如若再把信仰置于理智的思考与追问之下,又将如何?这是至深的危机。是施特劳斯解决了这至深的危机吗?我要感谢施特劳斯的门生布鲁姆的文本所打开的思想世界,法肯海姆说:“施特劳斯曾生活过、教诲过,这对犹太哲学的未来实为大幸事”。而我更以为重要的是,自己“懂得了一种灵魂的辉煌,懂得了一种其经验无法揭示给自己的生活方式”,那确实是一种福音,高贵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