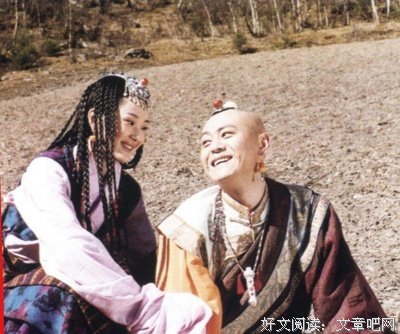《知识分子的鸦片》读后感锦集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本由[法] 雷蒙·阿隆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0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知识分子的鸦片》精选点评:
●于个人,并不算好读的一本书。虽然是冷战初期针对法国知识界而写的,但现在读也是一样针针见血。知识分子片面而虚妄的行为,一直以来都是相同的,人们在事件结果之后赋予时代的意义。前后,好坏,历史未来,在评判中而来。
●非常有分量的怀疑,对美俄法的洞察令人赞叹。巴黎高师一班校友向左转,唯独他朝右偏。
●no.83 哎,真的是才疏学浅完全看不懂。最不了解的政治学,连其中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搞清楚。从大概上只知道作者认为革命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并且认为政权的更替不过是统治方式的改变,其余的竟一律不知。真的讨厌政治,更别提敏锐度了。
●有些内容会让我心惊胆战地自己照镜子:“我有这毛病么?”另一些内容则会让我一拍大腿:“嘿!哥们,知音呐!”另外,翻译不能说差,但读着也确实不觉得好……
●所谓鸦片,是使知识分子瞻望美好未来的动力,但同时他们会陷入一种世俗宗教的教条中。但如果马克思主义是鸦片,那么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何处?阿隆通过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两本书来攻击左派和苏联的意识形态,未免失之全面。苏联的弊端人尽皆知,但是否只因为布尔什维克的出现?深层的历史原因和旧俄
●一个评论集,所以感觉内容没那么紧凑。第三编最有趣
●对知识分子有较充分、细致的研究,只可惜,视野仅限于以法国为主的欧美国家。
●“一颗正在流血却是贫血的心。”
《知识分子的鸦片》读后感(一):保持怀疑主义,警惕知识分子的鸦片
《知识分子的鸦片》读后感(二):《知识分子的鸦片》笔记
《知识分子的鸦片》读后感(三):法国知识分子为什么痴迷革命!
《知识分子的鸦片》读后感(四):读书笔记
七十年代时,对于萨特和阿隆两者,巴黎学生之间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愿跟着萨特走邪道,也不愿跟着阿隆走正道。”萨特一向是激烈的、极端的,而在这本书中,我们显然可以认识到,阿隆是一个过于严谨沉闷的知识分子,似右非右,用词古板苛刻,既不明显的表现自己的认可,又不激烈地表达否定,宛如教科书一般乏味,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法国的背景下,学生们不愿意追随这样一个模棱两可、态度不清的人了。
回归正题,通篇文章中,不管是明确地指出还是隐晦地被带到,“法兰西病”是阿隆始终没有放过的一个点,它几乎贯穿了整本书。官僚主义在法国轻佻得十分令人灰心丧气,不知道到底是这种带有强烈法国特色的官僚主义氛围中造就了当时的法国时局,还是时局造就了这种氛围。而法国人重视思想更甚于政治制度,知识分子们批判政治却又拒绝进行对政治的思考,沉醉在自己营造出来的世界中,信奉着介入的哲学却又是不介入者,不论是从政府的角度,还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
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他们生活的方式基本就是智力活动,而对于国家,他们几乎也只会进行口头上的批判,并且不可避免地将自己职业领域的想法带入政治中,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又只能通过批判来进行自我安慰。法国作为知识分子的天堂,知识分子却对国家唾弃之至,而在美国,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尊崇的待遇,却极力地颂扬国家,而法国的知识分子却从国家体制的衰败中感到失望,他们具有知识分子应该有的责任感,但是这种责任感又只能驱使他们到批判而不介入的程度,可惜的是这种批判,又不完全是逻辑上的批判。
人们总是把过去当作黄金时代,并且永远企图从过去的历史中总结出经验,但实际上这种经验也是片面的,但我们又只能从过去获得经验,因此永远无法总结出一个完全正确的结论。更何况,胡适曾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虽然在网络信息基本对等的今天也许适用性会变低,至少在中法同处于二十世纪的当时,确实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结论,因为它几乎推翻了我们过去几千年里从历史中得出的结论,并且断言人类永远无法得到一个真正意义上正确的结论。
而知识分子的这种游离,也正表明了他们只是在不断被曝光出来的新的丑闻中,更大程度上凭借这种来自外部的信息或评断来左右自己的抉择,而非更多地结合自己的思考。他们也如同所有法国人一样也受着集体主义的束缚。不过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信息仍然不够发达的二十世纪,对于获得的煽动性的信息,并且这种信息很可能已经在传播下失去了真实性与客观性,转而带上激烈的煽动性的色彩,社会的群体是很容易被这种信息牵着鼻子走的。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互联网信息爆炸的当下,人们仍然会因为某种片面的信息以至于舆论所被煽动,愿意跟从大众主流的评判或者是加入某个非主流的群体,从而失去了公正性,不愿意再去获得一些另外的相关信息来做出自己的思考。 这可能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会有的一种现象,而真正客观冷醒的人在于少数,但可惜的是这一群少数看似握有真理的人又并不是完全客观。
阿隆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在于社会批判,包括了技术批判、道德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或历史批判这三类批判功能。书中已经用了很大篇幅来描述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这三种批判,但是我认为,雷蒙·阿隆自己所反映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功能固然与家国社会有着重要的联系,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也许更可贵的是能够像阿隆一样,尽量撇开自身的政治立场以及意识形态,来相对独立地进行思考。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也从上文的批判(不论是阿隆或是我本人对于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的评断)发现,其实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对于知识分子其实还是非常苛刻的,由于他们所拥有的某一种领域的学识或是资历,而要求他们务必对社会负责,并且一面苛责他们不能用客观的思维来进行对制度的思考,又一面埋怨不介入者。所谓“士的超越性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恒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是很难界定出一个清晰的界限的。而当我们再站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去评判他们,这种评判也许非但不能够达到我们所谓的“客观”,而是更加刻薄了。
七十年代时,对于萨特和阿隆两者,巴黎学生之间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愿跟着萨特走邪道,也不愿跟着阿隆走正道。”萨特一向是激烈的、极端的,而在这本书中,我们显然可以认识到,阿隆是一个过于严谨沉闷的知识分子,似右非右,用词古板苛刻,既不明显的表现自己的认可,又不激烈地表达否定,宛如教科书一般乏味,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法国的背景下,学生们不愿意追随这样一个模棱两可、态度不清的人了。
回归正题,通篇文章中,不管是明确地指出还是隐晦地被带到,“法兰西病”是阿隆始终没有放过的一个点,它几乎贯穿了整本书。官僚主义在法国轻佻得十分令人灰心丧气,不知道到底是这种带有强烈法国特色的官僚主义氛围中造就了当时的法国时局,还是时局造就了这种氛围。而法国人重视思想更甚于政治制度,知识分子们批判政治却又拒绝进行对政治的思考,沉醉在自己营造出来的世界中,信奉着介入的哲学却又是不介入者,不论是从政府的角度,还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
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他们生活的方式基本就是智力活动,而对于国家,他们几乎也只会进行口头上的批判,并且不可避免地将自己职业领域的想法带入政治中,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但是又只能通过批判来进行自我安慰。法国作为知识分子的天堂,知识分子却对国家唾弃之至,而在美国,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尊崇的待遇,却极力地颂扬国家,而法国的知识分子却从国家体制的衰败中感到失望,他们具有知识分子应该有的责任感,但是这种责任感又只能驱使他们到批判而不介入的程度,可惜的是这种批判,又不完全是逻辑上的批判。
人们总是把过去当作黄金时代,并且永远企图从过去的历史中总结出经验,但实际上这种经验也是片面的,但我们又只能从过去获得经验,因此永远无法总结出一个完全正确的结论。更何况,胡适曾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虽然在网络信息基本对等的今天也许适用性会变低,至少在中法同处于二十世纪的当时,确实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结论,因为它几乎推翻了我们过去几千年里从历史中得出的结论,并且断言人类永远无法得到一个真正意义上正确的结论。
而知识分子的这种游离,也正表明了他们只是在不断被曝光出来的新的丑闻中,更大程度上凭借这种来自外部的信息或评断来左右自己的抉择,而非更多地结合自己的思考。他们也如同所有法国人一样也受着集体主义的束缚。不过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信息仍然不够发达的二十世纪,对于获得的煽动性的信息,并且这种信息很可能已经在传播下失去了真实性与客观性,转而带上激烈的煽动性的色彩,社会的群体是很容易被这种信息牵着鼻子走的。即使在二十一世纪互联网信息爆炸的当下,人们仍然会因为某种片面的信息以至于舆论所被煽动,愿意跟从大众主流的评判或者是加入某个非主流的群体,从而失去了公正性,不愿意再去获得一些另外的相关信息来做出自己的思考。 这可能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会有的一种现象,而真正客观冷醒的人在于少数,但可惜的是这一群少数看似握有真理的人又并不是完全客观。
阿隆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在于社会批判,包括了技术批判、道德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或历史批判这三类批判功能。书中已经用了很大篇幅来描述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这三种批判,但是我认为,雷蒙·阿隆自己所反映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功能固然与家国社会有着重要的联系,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也许更可贵的是能够像阿隆一样,尽量撇开自身的政治立场以及意识形态,来相对独立地进行思考。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也从上文的批判(不论是阿隆或是我本人对于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的评断)发现,其实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对于知识分子其实还是非常苛刻的,由于他们所拥有的某一种领域的学识或是资历,而要求他们务必对社会负责,并且一面苛责他们不能用客观的思维来进行对制度的思考,又一面埋怨不介入者。所谓“士的超越性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恒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是很难界定出一个清晰的界限的。而当我们再站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去评判他们,这种评判也许非但不能够达到我们所谓的“客观”,而是更加刻薄了。
而这种刻薄,在2020新冠病毒疫情下的无知乌合之众身上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